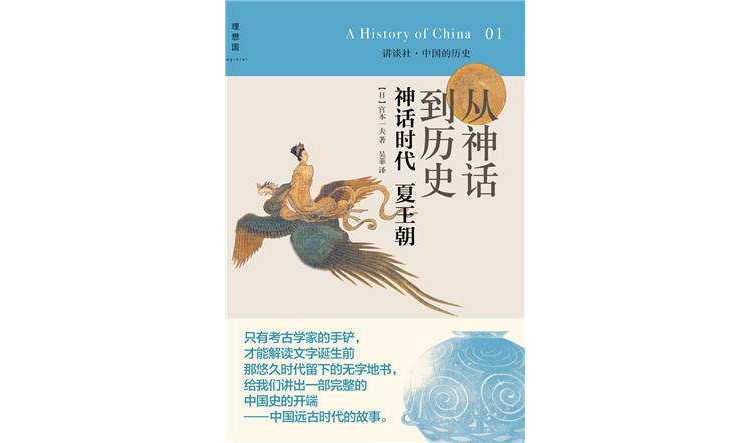本書為講談社《中國的歷史》中的“神話時代、夏王朝”一卷。
基本介紹
- 書名:從神話到歷史:神話時代 夏王朝
- 作者:(日)宮本一夫
- 譯者:吳菲
- ISBN:978-7-5495-3367-1
- 頁數:416
- 定價:49
-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4-1-1
- 開本:1/32
- 字數:203千字
前言/序言,內容簡介,目錄,
前言/序言
推薦序——許 宏
您大概已注意到,這套達十卷之多的中國通史叢書,開卷的作者——日本九州大學的宮本一夫教授是位考古學家。這是本卷與其他各卷的一個顯著的不同。另一個大不同是,其後九卷所敘述的歷史跨度(從商代到中華民國),總計為三千多年,而本卷的內容遠溯至一二百萬年前,主體敘述則始於農業起源以來的距今約一萬年前。
這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只有考古學家用他們的手鏟,才能解讀文字誕生前那悠久時代留下的無字地書,擔負起“拉長”中國歷史的任務,進而給我們講出一部完整的中國史的開端——中國遠古時代的故事。同時,可以顯見的是,與後面其他各卷相比,考古學家的這種敘述還是粗線條的。這又引出了考古學的長處和不足的話題,也即:考古學的學科特點,決定了其以長時段的、歷史與文化發展進程的巨觀考察見長,而拙於對精確年代和具體歷史事件的把握 。
上述考古學科的特點,也大致決定了本卷的敘事風格。譬如儘管書名為《從神話到歷史》,但相對晚出、後世加工痕跡明顯、無從驗證的神話傳說在被做了深度“解剖”後以十餘頁的篇幅一筆帶過,這顯然是出於專業的嚴謹。作者很快就回到考古學的話語系統,從一二百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東亞最早的人類、不同的石器工業傳統談起,娓娓道來。然後是一萬年以來新石器時代的發展,多元農業以及陶器的發明,乃至定居社會的三種經濟形態:旱作、稻作農業與狩獵採集。由自然環境到文化分區與譜系,再到大的時段劃分,則頗有指點江山、縱橫捭闔的大將風度。這些敘述對讀者而言可能略顯枯燥,似乎學術味兒重了些,但卻是解讀遠古中國必不可少的輪廓性勾畫。日後一幕幕感天動地的悲喜劇,都是在這個大的自然和文化背景下上演的,它們奠定了後世中國發展的基礎。然後,作者從多個側面對黃河和長江中下游幾個大的農耕區域的社會複雜化問題進行剖析,涉及性別、血緣、家族單位、聚落防禦和社會分層等多個角度,圖文並茂地對古人食住行葬等日常生活進行復原,當然更是考古人的拿手好戲。作者最後還比較了這些區域在社會進化上的相異與相似之處,一幅多元的史前中國的風俗畫在考古學家的筆下栩栩如生。
如果這些可以看作考古人寫史的共同特點的話,那么作者的個性特徵導致這書的若干特色更令人感興趣。
雖然本卷主要是要交代“達成了政治上的區域統一的一元中國的出現過程”,但作者以其外國學者的獨特視角,著意要“在放眼整個東亞的情況下,把中國置於廣大的多元性之中來進行考察”。在上引關於東亞大陸史前時代的敘述之後,作者進而指出,正是這些農業社會中急劇的社會進化,使得中國大陸與日本列島同時期的社會與文化產生了巨大的本質的不同。類似的比較性闡述在本卷中比比皆是。只有兼通整個東亞地區考古學文化發展的學者,才能有如此跨文化比較的宏闊視野,宮本先生正是這樣一位優秀的學者。他對自己研究方向的定位是東亞考古學,其田野考古的足跡從俄羅斯遠東地區直至中國大西南,研究的時間跨度則由新石器時代前期下延至鐵器時代前期。
在學術信息爆炸,學術研究越來越“碎片化”的今天,已很少有考古學者能兼跨不同時段、不同區域和不同的研究領域,嫻熟地駕馭眾多的學術課題。宮本先生自謙地說他自己在本卷中所進行的通史性質的、網羅全域的綜合研究還只是一個嘗試。平心而論,這個嘗試是成功的。由於教育和研究體制的差異,日本學者在“通識”上要優於中國學者,後者偏於專精而有條塊分割之嫌。作為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學者,我個人的學術視閾就偏窄,因而在與包括宮本先生在內的外國學者的交往中常有自慚之感。這也反襯出這本書對中國讀者的可貴。
本卷中“非農業地帶與農業的擴散”和“畜牧型農業社會的出現”兩章最能顯現作者學術視閾的寬闊和功力的深厚。在這裡,中國學者筆下或多或少、有意無意的中原中心觀或東亞“大兩河流域”(指黃河和長江流域)農耕區中心觀不見了蹤跡,作者給予“中國大陸文化譜系的兩極相互接觸地帶”以同等的關注,指出在這裡“農業以適應各自生態的形式誕生,農業地帶順應著環境變化與社會變化的階段分別向北、向南擴散”。而在農業向北方擴散的區域之中又產生了依存於畜牧的農業社會也即“畜牧型農業社會”。“就這樣,亞洲東部的水平方向的社會分支逐漸完成,即農業社會,從農業社會分支出來的畜牧型農業社會及其發展型即遊牧社會。並在其周邊的西伯利亞至北極、熱帶地區形成了狩獵採集社會”。
作者進而指出,“上述格局直至今日,包括無文字社會民眾在內的地理上的社會分化,其實早在新石器時代終末期就已開始了。了解到這一點之後,相信讀者對史前時代研究的重要性一定也深有感觸吧。”在這裡,貌似跟諸位沒有什麼關係的遠古與我們身處的現代接軌了。其實,作為一位具有人文關懷情結的學者,宮本先生在本卷的《前言》中即已開宗明義地指出,他是期望讀者藉此了解“以考古學為對象的區域考察如何關係著該區域近現代史的問題”。可以說,貫通古今,構成本卷的又一大特色。
全書的後半部分是整個王朝中國誕生故事的“戲眼”。關於東亞大陸從多元到一體的早期國家形成過程,作者從區域間的交流與社會的統合,犧牲與宗教祭祀兩個大的方面展開論述。最後闡明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導致早期國家的崛起。二里頭文化(作者認為即夏王朝)已“形成多重性的禮制。這正可謂是商周社會的基本道德觀念即‘禮樂’的開端”。而商王朝可以“定位為在東亞確立了早期國家階段的王朝”。
關於中國早期王朝的研究,在中國和日本考古學界有一個有趣的動向。對上個世紀中國學者積極地將傳世文獻中的國族(王朝)、都邑等與具體的考古遺存做“對號入座”式的比附研究,日本及歐美的研究者一般抱持審慎的態度。但近年來,日本學界開始有認可夏王朝真實存在的傾向。繼飯島武次 、岡村秀典教授 之後,宮本一夫教授在本卷中也開始持“二里頭文化即夏王朝,夏王朝確實曾經存在”的觀點。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自新世紀前後,一些中國中青年學者開始反思,逐漸接受20世紀上半葉以《古史辨》為核心的反思傳統,以及海外學界相對保守嚴謹的態度和觀點,“超脫”出原有的話語系統,出現了質疑傳統的“夏王朝可知論”的聲音,提倡“有條件的不可知論”(即主張沒有當時的有足夠歷史信息的文書類資料出土,不可能解決族屬和王朝歸屬問題) ,形成兩大話語系統並存的局面。
可以預見,關於夏王朝是否實際存在、是否相當於二里頭文化之類問題的討論還將持續下去。但誠如宮本先生在本卷中所言,與其執著於這類問題,“不如對二里頭文化是否達到了王朝所應有的社會進化水準的問題加以客觀論證”。這一理念成為中外學者的共識,是令人可喜的。
在展開本卷的敘述之前,宮本先生先給讀者講了中國發掘的故事。其中既有對中國考古學史的全景式的掃描,也有他個人在中國各地參加田野考古實踐的見聞和體會,可以從中了解外國學者眼中考古人的工作生活、待人接物乃至當地風土民情等,讀來饒有興味。比如看到作者提及中國人的好面子,他作為“中國通”對各地美食的評價,你可能會會心地一笑。其對外國學者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業績的評價,持論允當;他善意地指出中國當代考古的問題所在,可以作為很好的鏡鑒。
他的許多總括性認識如他山之石,發人深省:“我們不能用以中原為中心的單一的發展規律和戰國時代以後正式成形的中華的概念或者說是中國的概念來看待其後的中國史”。“以中華文明為主幹的中國史觀不過是著眼於一方的區域歷史”,“中國的歷史並不只是農業社會的歷史”。“商周文化是南方的文化軸,北方青銅器文化是北方的文化軸”,(兩條文化軸的)“接觸地帶才是生成新的社會體系的源泉所在”。種種表述,都頗富啟發意義。
著名考古學家、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倫福儒指出,“現在,(考古學)已成為世界各國許多人都感興趣的一個領域。其部分原因是,它使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充分地了解本國的歷史。但是,如果把注意力只集中於本國,那就是沙文主義。考古學還使我們有可能把每個國家的早期歷史看作整個人類更大範圍的歷史的一部分”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身為中國人讀讀外國學者眼中的中國考古和中國歷史,傾聽一下不同的聲音,不亦樂乎,不亦清醒乎?
許宏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2011年11月
您大概已注意到,這套達十卷之多的中國通史叢書,開卷的作者——日本九州大學的宮本一夫教授是位考古學家。這是本卷與其他各卷的一個顯著的不同。另一個大不同是,其後九卷所敘述的歷史跨度(從商代到中華民國),總計為三千多年,而本卷的內容遠溯至一二百萬年前,主體敘述則始於農業起源以來的距今約一萬年前。
這從一個側面告訴我們,只有考古學家用他們的手鏟,才能解讀文字誕生前那悠久時代留下的無字地書,擔負起“拉長”中國歷史的任務,進而給我們講出一部完整的中國史的開端——中國遠古時代的故事。同時,可以顯見的是,與後面其他各卷相比,考古學家的這種敘述還是粗線條的。這又引出了考古學的長處和不足的話題,也即:考古學的學科特點,決定了其以長時段的、歷史與文化發展進程的巨觀考察見長,而拙於對精確年代和具體歷史事件的把握 。
上述考古學科的特點,也大致決定了本卷的敘事風格。譬如儘管書名為《從神話到歷史》,但相對晚出、後世加工痕跡明顯、無從驗證的神話傳說在被做了深度“解剖”後以十餘頁的篇幅一筆帶過,這顯然是出於專業的嚴謹。作者很快就回到考古學的話語系統,從一二百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東亞最早的人類、不同的石器工業傳統談起,娓娓道來。然後是一萬年以來新石器時代的發展,多元農業以及陶器的發明,乃至定居社會的三種經濟形態:旱作、稻作農業與狩獵採集。由自然環境到文化分區與譜系,再到大的時段劃分,則頗有指點江山、縱橫捭闔的大將風度。這些敘述對讀者而言可能略顯枯燥,似乎學術味兒重了些,但卻是解讀遠古中國必不可少的輪廓性勾畫。日後一幕幕感天動地的悲喜劇,都是在這個大的自然和文化背景下上演的,它們奠定了後世中國發展的基礎。然後,作者從多個側面對黃河和長江中下游幾個大的農耕區域的社會複雜化問題進行剖析,涉及性別、血緣、家族單位、聚落防禦和社會分層等多個角度,圖文並茂地對古人食住行葬等日常生活進行復原,當然更是考古人的拿手好戲。作者最後還比較了這些區域在社會進化上的相異與相似之處,一幅多元的史前中國的風俗畫在考古學家的筆下栩栩如生。
如果這些可以看作考古人寫史的共同特點的話,那么作者的個性特徵導致這書的若干特色更令人感興趣。
雖然本卷主要是要交代“達成了政治上的區域統一的一元中國的出現過程”,但作者以其外國學者的獨特視角,著意要“在放眼整個東亞的情況下,把中國置於廣大的多元性之中來進行考察”。在上引關於東亞大陸史前時代的敘述之後,作者進而指出,正是這些農業社會中急劇的社會進化,使得中國大陸與日本列島同時期的社會與文化產生了巨大的本質的不同。類似的比較性闡述在本卷中比比皆是。只有兼通整個東亞地區考古學文化發展的學者,才能有如此跨文化比較的宏闊視野,宮本先生正是這樣一位優秀的學者。他對自己研究方向的定位是東亞考古學,其田野考古的足跡從俄羅斯遠東地區直至中國大西南,研究的時間跨度則由新石器時代前期下延至鐵器時代前期。
在學術信息爆炸,學術研究越來越“碎片化”的今天,已很少有考古學者能兼跨不同時段、不同區域和不同的研究領域,嫻熟地駕馭眾多的學術課題。宮本先生自謙地說他自己在本卷中所進行的通史性質的、網羅全域的綜合研究還只是一個嘗試。平心而論,這個嘗試是成功的。由於教育和研究體制的差異,日本學者在“通識”上要優於中國學者,後者偏於專精而有條塊分割之嫌。作為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學者,我個人的學術視閾就偏窄,因而在與包括宮本先生在內的外國學者的交往中常有自慚之感。這也反襯出這本書對中國讀者的可貴。
本卷中“非農業地帶與農業的擴散”和“畜牧型農業社會的出現”兩章最能顯現作者學術視閾的寬闊和功力的深厚。在這裡,中國學者筆下或多或少、有意無意的中原中心觀或東亞“大兩河流域”(指黃河和長江流域)農耕區中心觀不見了蹤跡,作者給予“中國大陸文化譜系的兩極相互接觸地帶”以同等的關注,指出在這裡“農業以適應各自生態的形式誕生,農業地帶順應著環境變化與社會變化的階段分別向北、向南擴散”。而在農業向北方擴散的區域之中又產生了依存於畜牧的農業社會也即“畜牧型農業社會”。“就這樣,亞洲東部的水平方向的社會分支逐漸完成,即農業社會,從農業社會分支出來的畜牧型農業社會及其發展型即遊牧社會。並在其周邊的西伯利亞至北極、熱帶地區形成了狩獵採集社會”。
作者進而指出,“上述格局直至今日,包括無文字社會民眾在內的地理上的社會分化,其實早在新石器時代終末期就已開始了。了解到這一點之後,相信讀者對史前時代研究的重要性一定也深有感觸吧。”在這裡,貌似跟諸位沒有什麼關係的遠古與我們身處的現代接軌了。其實,作為一位具有人文關懷情結的學者,宮本先生在本卷的《前言》中即已開宗明義地指出,他是期望讀者藉此了解“以考古學為對象的區域考察如何關係著該區域近現代史的問題”。可以說,貫通古今,構成本卷的又一大特色。
全書的後半部分是整個王朝中國誕生故事的“戲眼”。關於東亞大陸從多元到一體的早期國家形成過程,作者從區域間的交流與社會的統合,犧牲與宗教祭祀兩個大的方面展開論述。最後闡明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導致早期國家的崛起。二里頭文化(作者認為即夏王朝)已“形成多重性的禮制。這正可謂是商周社會的基本道德觀念即‘禮樂’的開端”。而商王朝可以“定位為在東亞確立了早期國家階段的王朝”。
關於中國早期王朝的研究,在中國和日本考古學界有一個有趣的動向。對上個世紀中國學者積極地將傳世文獻中的國族(王朝)、都邑等與具體的考古遺存做“對號入座”式的比附研究,日本及歐美的研究者一般抱持審慎的態度。但近年來,日本學界開始有認可夏王朝真實存在的傾向。繼飯島武次 、岡村秀典教授 之後,宮本一夫教授在本卷中也開始持“二里頭文化即夏王朝,夏王朝確實曾經存在”的觀點。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自新世紀前後,一些中國中青年學者開始反思,逐漸接受20世紀上半葉以《古史辨》為核心的反思傳統,以及海外學界相對保守嚴謹的態度和觀點,“超脫”出原有的話語系統,出現了質疑傳統的“夏王朝可知論”的聲音,提倡“有條件的不可知論”(即主張沒有當時的有足夠歷史信息的文書類資料出土,不可能解決族屬和王朝歸屬問題) ,形成兩大話語系統並存的局面。
可以預見,關於夏王朝是否實際存在、是否相當於二里頭文化之類問題的討論還將持續下去。但誠如宮本先生在本卷中所言,與其執著於這類問題,“不如對二里頭文化是否達到了王朝所應有的社會進化水準的問題加以客觀論證”。這一理念成為中外學者的共識,是令人可喜的。
在展開本卷的敘述之前,宮本先生先給讀者講了中國發掘的故事。其中既有對中國考古學史的全景式的掃描,也有他個人在中國各地參加田野考古實踐的見聞和體會,可以從中了解外國學者眼中考古人的工作生活、待人接物乃至當地風土民情等,讀來饒有興味。比如看到作者提及中國人的好面子,他作為“中國通”對各地美食的評價,你可能會會心地一笑。其對外國學者在中國考古學史上業績的評價,持論允當;他善意地指出中國當代考古的問題所在,可以作為很好的鏡鑒。
他的許多總括性認識如他山之石,發人深省:“我們不能用以中原為中心的單一的發展規律和戰國時代以後正式成形的中華的概念或者說是中國的概念來看待其後的中國史”。“以中華文明為主幹的中國史觀不過是著眼於一方的區域歷史”,“中國的歷史並不只是農業社會的歷史”。“商周文化是南方的文化軸,北方青銅器文化是北方的文化軸”,(兩條文化軸的)“接觸地帶才是生成新的社會體系的源泉所在”。種種表述,都頗富啟發意義。
著名考古學家、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倫福儒指出,“現在,(考古學)已成為世界各國許多人都感興趣的一個領域。其部分原因是,它使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充分地了解本國的歷史。但是,如果把注意力只集中於本國,那就是沙文主義。考古學還使我們有可能把每個國家的早期歷史看作整個人類更大範圍的歷史的一部分” 。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身為中國人讀讀外國學者眼中的中國考古和中國歷史,傾聽一下不同的聲音,不亦樂乎,不亦清醒乎?
許宏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2011年11月
內容簡介
《中國的歷史》(10卷)為日本講談社百周年獻禮之作,是日本歷史學家寫給大眾的中國通史讀本。叢書自上古到近代,內容涵蓋量大,撰述者均為日本該領域的代表性學者,作品大多構思巧妙,寫法輕鬆,觀點新穎,富於洞見,但同時又吸取了近些年來的諸多學術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讀性與嚴肅性兼備的重磅歷史佳作。
本卷從一二百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東亞最早的人類、不同的石器工業傳統談起,娓娓道來。由自然環境到文化分區與譜系,再到大的時段劃分,則頗有指點江山、縱橫捭闔的大將風度。這些敘述是解讀遠古中國必不可少的輪廓性勾畫。日後一幕幕感天動地的悲喜劇,都是在這個大的自然和文化背景下上演的,它們奠定了後世中國發展的基礎。
作者的許多總括性認識如他山之石,發人深省:“我們不能用以中原為中心的單一的發展規律和戰國時代以後正式成形的中華的概念或者說是中國的概念來看待其後的中國史”。“以中華文明為主幹的中國史觀不過是著眼於一方的區域歷史”,“中國的歷史並不只是農業社會的歷史”。“商周文化是南方的文化軸,北方青銅器文化是北方的文化軸”,(兩條文化軸的)“接觸地帶才是生成新的社會體系的源泉所在”。種種表述,都頗富啟發意義。
作者宮本一夫(Miyamoto Kazuo),九州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院教授。專攻東亞考古學。主要研究東亞新石器時代至初期鐵器時代的比較考古學及比較文明論。現正在中國開展關於水田農耕起源地及解明初期青銅器的共同研究。2003年獲第十六屆濱田青陵獎。
目錄
推薦序
中文版自序
前言
第一章 神話與考古學
第二章 中國發掘物語
第三章 農業的出現
第四章 區域文化的發展
第五章 社會的組織化與階層化
第六章 非農業地帶與農業的擴散
第七章 畜牧型農業社會的出現
第八章 區域間交流與社會的統合
第九章 犧牲與宗教祭祀
第十章 走向初期國家的曙光
結語
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