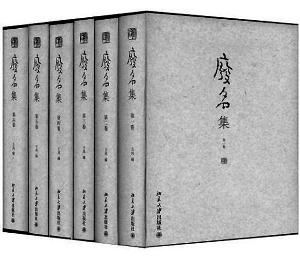人物經歷
1901年11月9日,出生於湖北省黃梅縣黃梅鎮小南街。家境殷實,從小接受傳統的私塾教育。1917年,考入國立湖北第一師範學校,開始接觸新文學。1922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英文班,成為周作人的學生,開始發表詩和小說,在北大讀書期間,廣泛接觸新文學人物,參加“
淺草社”,投稿《
語絲》。

廢名
1925年10月,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竹林的故事》。1926年6月10日,將自己的筆名定名為“廢名”。1927年,
張作霖下令解散北大,解聘周作人,改組京師大學堂,廢名憤而退學,卜居西山,後任教成達中學。
1928年,出版短篇小說集《桃園》;同年,與
馮至等人創辦《駱駝草》文學周刊並主持編務,共出刊26期。1929年,在重新改組的北平大學北大學院英國文學系畢業,受聘於國立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任講師。1931年,出版短篇小說集《棗》。1932年,出版長篇小說《橋》《莫須有先生傳》。抗日戰爭期間,前往黃梅縣任教於中國小,並在此期間寫就《阿賴耶識論》。1945年,出版詩文集《招隱集》。1946年,由
俞平伯推薦受聘北京大學國文系副教授。
1949年,任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授。1952年,調往長春東北人民大學(後更名為吉林大學)中文系任教授。1956年任中文系主任,先後被選為吉林省文聯副主席,吉林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吉林省政協常委。1957年,出版小說集《廢名小說選》。1967年10月7日,因癌症病逝於長春。
個人生活
廢名的哥哥是馮力生。廢名的女兒是馮止慈;兒子
馮思純於1935年7月出生在北京,後擔任山東省電子局副局長和浪潮集團副總裁。
主要作品
參考資料:
出版圖書
作者名稱:廢名
作者類型:
作者時間:2010年11月
廢名中篇小說《橋》被譽為“破天荒”的作品。《橋》描寫小林、琴子、細竹三人所見所歷的鄉間風物、景致、人情,不求情節而但求一種心境、一種禪意。似淡似釅,似歡樂似憂愁,如夢如畫如詩,在廢名筆下,《橋》的所在,是一處未落凡塵的世外仙境。《橋》以意境之美、語言之美,將京派文學推向新的高度。
創作特點
主題思想
人情美的哀悼
廢名早期短篇鄉土小說中,感傷的對象是生活在鄉土環境中的平凡民眾。這些民眾有著普遍善良、質樸的特性。《浣衣母》中“李媽”和“駝背兒”母女受盡命運的薄情,卻依然熱誠的溫暖他人。《火神廟的和尚》里金喜原是破落的浪人,因王四爹可憐他,“才把他推薦到火神廟做徒弟”,免去潦倒流浪。自此,金喜至死也感恩圖報,他自己一餐能吃“五海碗” ,卻將菩薩的貢果,“都一碟一碟一碟的攢積在罐頭”,留給王四爹的孫子們吃,雖然豆子都長微了,“總不能不說是一番苦心”。一年有三回上街買肉,“都是割給王四爹煨湯的”。《小五放牛》里的“陳大爺”是個童心未泯的老頑童,與“我”這個放牛娃,經常一塊玩耍。小說從一杯茶、一粒豆、一句關懷、一個關照中呈現這些人物身上微小卻實在的人性光輝,即在庸常,甚至破落的遭遇下,依然秉持著溫良的待人處事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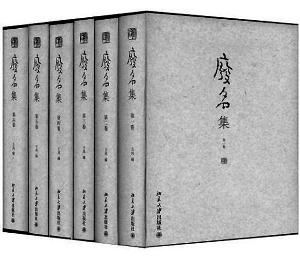
《廢名集》
這些人物所具有的品性,並不是知識分子眼中浪漫派的誇張與理想派的失真,顯得做作與矯情。而是現在已岌岌可危的,曾經流淌在中國鄉民血液里的傳統美德。這種人情美的關照與抒寫,與當時大多數鄉土小說中人民的麻木與落後,構成一種微弱的對照,又在都市文明抒寫中存在的冷漠疾病的參照下,呈現出一種緬懷式的感傷。正如劉西渭在評價沈從文作品時說過:“作者的人物雖說全部善良,本身卻含有悲劇的成分。唯其善良,我們才更易於感到悲哀的分量。這種悲哀,不僅僅由於情節的演進,而是自來帶在人物的氣質里的。自然越是平靜,‘自然人’越顯得悲哀:一個更大的命運影罩住他們的生存。”這幾乎是自然一個永久的原則:悲哀。廢名早期小說中的人物身上的善良也生存在一個巨大的命運陰影中而隱含著不可名狀的悲哀,而這個命運就是一種無緣無故的苦難。
人生苦的訴說
廢名在將以上有著美好品性的人物作為主要敘述對象加以突出描寫時,其建構的鄉土世界卻不是由這些人物所支配的理想田園,因為這些平凡民眾的人情美是建構在命運的無常底色上。《浣衣母》中“李媽”有個酒鬼丈夫,“家運剛轉到蹇滯的時候,確乎到什麼地方做鬼去了”,“李媽”寄期望於兩個兒子,卻沒有一個懂事,隨後相依為命的女兒也死了。當“李媽”最終想從接連的打擊中走出來,和那個“覓著婆婆家寄住”的單身漢共同生活時,城裡的謠言使得姑娘和孩子不再出現在茅草屋前,末了,“那漢子不能不走”。《火神廟的和尚》中,老和尚金喜三十年的寺廟生活,充滿辛酸。日子清苦,“咀嚼著如同破絮一般的炒米”當中飯。“梅雨時節,腰背酸疼”只能一個人躺床上,“三十年接不了一個徒弟”,全都圖個“滿身新衣”和“小銅菩薩”便走了。末了,請了個老頭子作伴,依舊“不會做事”,倒是“桶子的米,比以前淺得更快”。最後金喜終究孤身一人上樓梯時摔死了。《河上柳》中因營生的“木頭戲”被禁的“陳老爹”,變得無所事事,加上洪水沖家,最終沒能守住滿含美好回憶的柳樹,“引一個木匠回來”砍掉它了。《小五放牛》中的“陳大爺”表面是與“我”一起無憂玩耍的老頑童,但其實是靠妻子給屠戶“王胖”做駢頭餬口的“烏龜”。
統觀以上主人公的遭際,有著謀生的艱苦,死亡的降臨等人生諸多無常的打擊,也有封建傳統思想道德影響下根深蒂固的人性的涼薄與非議。這些苦難不是刻意安排出的戲劇性的大悲大難,以期獲得矛盾情節的衝突,已達到“攖人心”的效果。也不是與複雜而又具體的社會緣由和經濟根源緊密相連,以求就當時特定的社會事實做諷刺或者拯救式的圖解。這裡的苦難是真實又無奈的根生於鄉土世界一個恆定的常數。這個常數,對於鄉土民眾來說是不可抗拒,不可避免的命運,而這樣的命運又因為其無法捉摸,無以探求,和土地的豐收,鄉民的歡愉一樣的自然自生,理所當然,而顯示出無緣無故的愁苦特性。
鄉土靈魂的孤寂
外在的苦難隨著四季的更迭和年歲的流轉更進一步消耗著鄉土民眾的情感,影響著他們無法供給的欲望,使他們更加無力。他們在鄉土閉塞環境和壓抑的封建傳統文化中滋生而出的無形的情感的缺失,是廢名小說瀰漫著哀愁的本質性因素。《浣衣母》中的李媽和《火神廟的和尚》中的金喜最難以填平和撫慰的憂傷,是來自人生沒有那種血濃於水的愛,那種冷冷清清的無法排遣的寂寞。《浣衣母》中,就連“沒有李媽容易度日”的鄰居王媽,因為有丈夫有孩子,“門口很是熱鬧”,也比李媽幸福快樂,不比母女倆“只是冷冷的坐著”。樂於助人的母女倆其實比誰都更需要溫暖與慰藉。母女倆住的茅草屋就是李媽內心尷尬失落的外在象徵。白天,姑娘休息、孩子玩耍、“老頭子曬背,叫花子捉虱子,無一不在李媽的門口”,而晚上,只有“流水激著橋柱,打破死一般的靜寂”,熱鬧與安靜,人來人散,物質上的貧乏抵不過情感的空洞。所以,儘管兒子不聽話,沒出息,“李媽”仍“用了寂寞的眼光”望那些送柴來家裡的守城士兵,因為她必是想起了“逃到什麼地方當兵”的兒子。而在《火神廟的和尚》里,“終日陪伴著金喜的,菩薩之外只有小寶——金喜的狗”, 即使他後來招了個老頭子作伴依然不順遂,最後隻身一人意外死去。金喜日常生活有著這樣那樣的生趣,但依然掩蓋不了無親無家的寂苦,所以他無比珍惜著王四爹給予他的從未有過的親人般的關愛。《河上柳》和《小五放牛》中的兩位老伯也是失掉了愛的鄉土靈魂,陳老爹想守住承載著妻子愛的柳樹而不得,陳大爺渴望正常的家庭和關愛,卻只能裝傻充愣與“我”玩耍來藉以逃避內心的痛苦。小說末尾,當“我”快要離去,陳大爺面對“鳩占鵲巢”的王胖子時,只能“跟在我的牛後,很捨不得我的樣子”。
統觀這些鄉土民眾的寂寞,與知識分子內心形而上的超然獨立不同,是最原始,也是最本真的心靈的欲求,它作為人情美背後無法根除的哀傷,同農民的愚昧與麻木一道需要被正視,被呈現。因為它不獨在鄉土,而是每個被命運和時代所圈禁的,失去情感根基的個體共同經歷的創傷。
鄉土困境的叩問
鄉土外在的困苦和內在糾葛融合成了鄉土世界無緣無故的哀愁,而這愁苦本身與鄉土民眾的善美人情和人性意願構成無法協調的矛盾。一方面以善為美的主人公面對無端命運的隱忍態度,使小說呈現出美與苦的交融;一方面主人公內心最本質的寂寞與孤獨,在精神和物質都不豐盈的境況中,使廢名小說呈現出妥協與期盼的交融。
就前者來說,廢名小說中無盡又無果的苦難雖然阻礙著鄉土民眾基本的欲求和美好的宿願,但因鄉土民族的心性和個體在人生中的局限,有能動性的鄉土民眾只能採取自動整合悲苦的鄉土生存方式。所以小說人物“有一點憂鬱,一點向知與未知的欲望,有對宇宙光色的眩目,有愛,有憎——但日光下或黑暗,這些靈魂,依然不會騷動,一切與自然諧和,非常寧靜,缺少衝突。《浣衣母》中李媽和駝背姑娘都是善良的,但好人似乎沒有好報,而作為孱弱的女性,她們更沒有力氣反抗,她們的只能忍受。兒子沒出息,李媽“只有哭了”,發點“酒鬼害我!”的牢騷,又不然“統行吐在駝背姑娘頭上了”,而駝背姑娘“不怪媽媽,也不惱哥哥,酒鬼父親腦里連影子也沒有,更說不上怨,她只是鳴鳴咽咽的哭著”。茅草房有傾塌的危險,母女倆也只是用“斷續的談話”來‘抵抗恐怖”。《火神廟的和尚》中的金喜也是善良的,他對於生活上的不如意,口有抱怨,但也僅限於抱怨。對於因當年挑水撂下的病痛,他更不敢追想原因,因為“這樣想便是追怨師父,罪過”。受放牛孩子嘲笑,他也“依然是關在心裡嘆息”。
廢名小說主人公面對苦難,有著自己的愁和痛,但他們對待苦難的態度是隱忍的,不是向死而生的悲壯反抗與鬥爭,也不是純粹的麻木委頓,否則他們不會懷揣著人性的善美。苦難於他們而言,已化作太多太多的“不得不”和“不能不”。就後者來說,鄉土民眾內心對於愛和家本質性的渴求,不僅僅是鄉土民眾的祈願,這與以郁達夫為代表的早期創造社小說描寫特定時代下知識分子個體的情感、精神的困頓頹唐不同,是超越了時代語境,包含著所有階層的,乃至每一個人類個體最基本的需要,而這種需要在追索中往往無法強力得到,這從作者對人物實際出路的懸置中可以看出。因而個體的無法超越,和積澱千年的鄉土靈魂,鄉土性格深深結合,奏響了一曲自我守候的哀歌,牽動著以鄉土形態占到多數時間和空間的中國社會,叩問著一代代依附於鄉土,熱愛著鄉土的人們。
藝術特色
平和沖淡的生死之思
廢名小說的獨特之處在於以田園牧歌情調營造詩意古典意境,他的小說反映鄉村風景、風俗、人情之美,令人感悟到詩意的輕盈靈動和人生的靜謐恬淡。廢名尤致力於鄉間兒女情態的描寫,透露出一種哲人式的人生態度和對普通生命存在的獨特體悟。他的小說似一曲幽遠悠長的牧歌,一方面蘊藉著作家對現世人生的平和態度,另一方面也潛隱地表達了作家對生死的超越式詩性哲思。
寧靜致遠的世外桃源
廢名到北京求學時,正值新文化運動退潮,思想界分裂嚴重,新文化的統一戰線不復存在,維繫中國兩千年傳統道德秩序的儒家思想體系也已經崩潰,新的思想體系還未建立,政治依舊黑暗,大都市雖然進步,卻也充滿虛偽、邪惡、壓迫和暴力,廢名和當時大批“五四”知識分子一樣,感到孤獨苦悶虛無,精神上處於無所憑藉的流浪狀態,這在他的早期小說《講究的信封》《少年阮仁的失蹤》等都有所表現。但廢名很快就找到了精神的歸依之所,他受英國作家喬治·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影響,把深情的目光投向美麗古樸的故土,創作出一篇篇令人心馳神往的田園牧歌式作品,一唱三嘆地謳歌故鄉兒女翁媼的美好人性和鄉土中國人與自然的和諧,藉此來撫慰自己孤獨、焦慮的心靈。廢名的小說深刻地揭示了一個原型母題:對世外桃源的追尋和熱愛。
簡約典雅的世情禪心
廢名小說詩化藝術表現在詩意濃郁的語言運用上。廢名不嚴格講究句子的詞法語法,為了適應文章整體風格和至情至性的審美追求,他避開任何既定的結構和組織,無拘無束地顯現自己的感情和才情。廢名後期小說開始注重對真實性的自覺追求, 《莫須有先生傳》和《莫須有先生坐飛機以後》除了“莫須有”的名字以外,其餘都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實記錄,是自傳式的小說。此時,語言的無所顧忌與先期簡潔、晦澀形成鮮明對照,句式越來越符合常用的語法規範,語句平實悠緩,不再如先前那般短促跌宕,用詞也力避奇僻險怪。從總體上看,廢名小說語言深受古典詩詞影響,注重意象選取和意境營造,優美典雅而又內蘊深廣。
人物評價
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民主戰士
魯迅:(廢名的小說)“以沖淡為外衣”,“閃露”了“作者過於珍惜他的有限的‘哀愁’,後來連這樣的‘閃露’也收起了”,於是從率直的讀者看來,就只見其有意低徊,顧影自憐之態了。

廢名
中國現代作家
周作人:(廢名)額如螳螂、聲音蒼啞,初見者每不知其云何。
中國當代作家
汪曾祺:廢名實在是一個真正很有特點的作家。他在當時的讀者就不是很多,但是他的作品曾經對上世紀30年代、40年代的青年作家,至少是北京的青年作家,產生過頗深的影響。這種影響現在看不到了,但是它並未消失。它像一股泉水,在地下流動著。也許有一天,會汩汩地流到地面上來。
澎湃新聞:廢名筆下“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他用文字描繪的風景畫既是自然的寫照,也是心境的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