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溪玄朗大師(673-754年)為天台宗第八祖,他三學兼通,解行相應,宴坐左溪,名重天下,是故求學者無遠弗屆,擁室填門,使沉寂多時的天台教門轉而鼎盛,也為後來的湛然“中興”奠定了基礎。然而他在天台宗史上的重要地位似乎並未得到足夠的重視,治史者言之寥寥,此與其實際貢獻並不相應。天台宗第八祖左溪玄朗大師是天台宗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其門下人才輩出,影響很大,使天台宗從沉寂多年轉向復興。可以說,他與弟子湛然等共同締造了天台宗的中興大業。
基本介紹
- 本名:左溪玄朗
- 出生時間:673年
- 去世時間:754年
- 性別:男
簡介,評價,
簡介
左溪玄朗大師(673-754年)為天台宗第八祖,他三學兼通,解行相應,宴坐左溪,名重天下,是故求學者無遠弗屆,擁室填門,使沉寂多時的天台教門轉而鼎盛,也為後來的湛然“中興”奠定了基礎。
評價
這篇文章對左溪的求學經歷、整理天台教法和教示弟子等進行了初步的探討。在其求學方面,對他曾從學過的恭禪師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究,提出了幾個假說。在整理教法方面,指出其重新整理和解釋智者大師的《法華玄義》和《法華文句》的貢獻,還強調湛然的著述也是在此基礎之上進行的。在教示弟子方面,指出他的門下人才濟濟,多人見諸碑記和僧傳,改變了以往數代近乎單傳的局面,還說明湛然最初的地位並不突出。 作者簡介:徐文明,哲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有關左溪的史料,有神迥《天台法華疏序》、《法華傳記》、李華《故左溪大師碑》、《宋高僧傳》、《天台九祖傳》、《佛祖統紀》等。據諸書,左溪俗姓傅,法號玄朗,字惠明,先祖居北地郡泥陽,為漢魏大族,隨晉室南遷,居東陽義烏。他是傅大士的六世孫。母葛氏,感天降靈瑞,夢乘羊車飛空凌虛,而覺身重,乃生左溪。初生不啼,莞爾而笑。九歲出家,師授其經,一覽成誦,日過七紙。如意元年(692年)閏五月十九日敕度配義烏清泰寺。弱冠遠赴會稽龍興寺,於延載元年(694年)從光州道岸律師(654-717年)受具足戒,並從學律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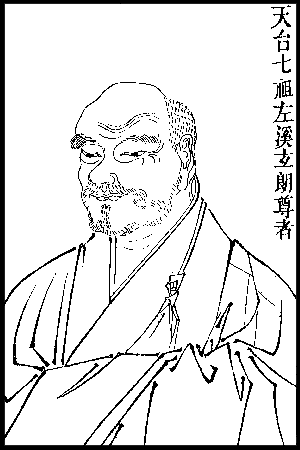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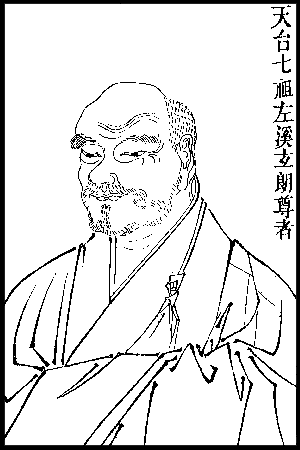
光州道岸為著名律師,玄朗因而得到了很好的律學訓練。之後,他又從學於會稽妙喜寺印宗禪師(627-713年)。依《故左溪大師碑》,他是就印宗“商律部”,1據僧傳,則是因其“博覽經論,搜求異同,尤切《涅盤》,常恨古人雖有章疏,判斷未為平允”,2故往與印宗“商榷秘要”,是商討經論特別是《涅盤經》義。不過印宗為學廣博,三學備精,無論律部還是義學,都值得當時的玄朗請教從學。然而二說都言二人商討,似乎是對等的研討,僧傳更言“雖互相述許,大旨未周”,好像二人互相推重,而“大旨未周”的責任只能落在年長的印宗頭上。其實這都是台宗後人托大之說,印宗其時已經年近古稀,而且早已是聞名天下的大師,而玄朗只有二十多歲,無法和印宗平起平坐。二者皆未提到的是,印宗作為六祖惠能的大弟子,禪門傳人,不可能只論律部經論,而不言及南宗禪法。因而更有可能的是,玄朗還從印宗學習了南宗禪法,從而奠定了禪學基礎。
在研習了戒律和禪法後,玄朗又“聞天台一宗可以清眾滯,可以趣一理”,故往從天宮寺慧威法師(634-713年),“不患貧苦,達《法華》、《淨名》、《大論》、《止觀》、《禪門》等,凡一宗之教跡,研核至精”。3看來所學經論很多,其中有《法華經》、《維摩經》、《大智度論》、《摩訶止觀》、《次第禪門》等,對於天台宗的教典,都有精深的研究。玄朗從學慧威不知始於何年,在此期間,他不僅系統學習了天台宗教義,還在相關的佛教經典義理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從而決定了他一生的歸趣。
玄朗除了學習天台教義外,又從恭禪師重修觀法。這位恭禪師不知何人,或當屬於天台宗中精通禪觀的宗師,所謂“重修”或許是由於已經從印宗等學過禪觀之法了。從恭禪師所修觀法很可能是天台宗的四種三昧和十乘觀法。也許在觀法方面,恭禪師更勝一籌,故玄朗依之重修。
這裡有一個問題,即玄朗究竟是先從慧威還是恭禪師。依僧傳,是先親附慧威,後依恭禪師重修觀法;依李華《碑》,則是“巍巍左溪,因恭禪師重研心法,唯十八種物,行頭陀教。厥後奉東陽威大師,得最上乘,詮第一義,現聲聞像,弘大覺心”,則奉事東陽在後。李華《碑》作於左溪入滅後不久,又是據其親傳弟子清辨等所述而撰,應當是比較可靠的。
如此“重研心法”,當是由於已從印宗禪師“商律部”、研心法在前。恭禪師的宗系,不出天台、三論、禪宗三家。從所謂“十八種物,行頭陀教”來看,不像是禪宗南宗,因為雖然南宗也承大迦葉之後,但六祖分明不太欣賞這種過於傳統的禪法,從後來玄覺與左溪的爭論中也可以看出來。禪宗北宗的影響當時似乎尚未到達東南一帶,據李華《潤州天鄉寺故大德雲禪師碑》,天鄉法雲(?-766年)景龍歲(707-710年)受具於本州龍興寺元(玄)昶律師,後與鶴林絢律師一起“往嵩潁求法於大照和尚”,其後南歸,“由於江表禪教有大照之宗焉”4,因此大概在左溪求學之時,北宗尚未進入江表。不過法雲之師龍興法慎(666-748年)曾謂“天台止觀是一切教門,東山法門是一切佛乘”,5對禪宗表示尊重。法慎在京的時間,正是五祖門人法如(?638-?689年)、老安(581-708年)、神秀(606-706年)等興盛之時,因而東山法門名振天下,但他是否從哪位宗師學過禪法則不得而知,他是著名律師,傳相部律,對天台宗和禪宗都有好感,因而不能視之為禪門傳人。
天台宗亦兼行頭陀,天宮慧威尤以“樂靜居山,罕交人事”著稱。不過既然此時玄朗尚未得識慧威,無由受其影響。有謂玄朗“還曾遠涉湖北當陽向恭禪師學習由智者傳授的止觀學說”,6如若此說成立,則恭禪師應當屬於玉泉系的天台宗,可惜作者未能說明此說的出處,在該書有關玉泉寺系部分也沒有提到還有一位恭禪師。
這位恭禪師亦有可能屬於原為三論宗一支但已與禪宗結緣的牛頭宗。三論宗本來就有山居坐禪的傳統,牛頭宗自法融以下,皆以苦修著稱,後世既與禪宗結緣,則更是注重繼承大迦葉的頭陀行傳統。玄朗“現聲聞像,弘大覺心”,這與天台宗奉龍樹為初祖,以大乘相標榜的作風有所不同,所謂“聲聞像”,當是指效法大迦葉的頭陀行。如果恭禪師果然屬於牛頭宗,則可能是與牛頭智威同輩的一位大師。義淨則提供了另一說法,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貞固傳》:
於時制旨寺恭?黎,每於講席親自提獎,可謂恂恂善誘,弘濟忘倦。?黎則童真出家,高行貞節,年餘七十而恆敬五篇。7
這位制旨寺的恭?黎很有可能是恭禪師。恭?黎在貞固律師於制旨寺講律時曾予以提攜,為一童真出家的高行大德,當時已經七十餘年。貞固於永昌元年(689年)年四十,當生於永徽元年(650年),其於制旨講律,當在垂拱元年(685年)至永昌元年(689年)間,因為他“以垂拱之歲,移錫桂林,適化遊方,漸之清遠峽谷。同緣赴感,後屆番禺,廣府法徒,請開律典”,8講律之後,他“還向峽山”,受到謙寺主的禮遇。貞固講律,很有可能是在垂拱三年(687年)左右,其時恭法師七十餘歲,則其應生於武德元年(618年)左右。陶靜恭?黎不見他書,其事跡難於悉考。王邦維批評了日本學者足立喜六以之為印度僧人般剌蜜帝的說法,認為“從義淨原文看,恭?黎似乎是中國僧人,可能就是制旨寺的住持”,9這一觀點是很有見地的。恭?黎與印宗相識的可能性很大,印宗曾於儀鳳元年(676年)在制旨寺講經,晚年才回到故鄉。恭?黎也有可能是長期住制旨寺的高僧,二人相識相熟是很有可能的。恭?黎應當是三學兼通的大師,與印宗一樣。義淨只提到他對律學很重視,然而他所指導過的貞固律師“既得律典斯通,更披經論。又復誦《法華》、《維摩》向一千遍。心心常續,念念恆持,三業相驅,四儀無廢。到峽山後“復欲於戒壇後面造一禪龕,立方等道場,修法華三昧”。10很顯然,貞固律師對於律禪教三學都是重視的,而且和天台宗在思想上頗有關聯,這與恭?黎有沒有關係,難於定論。玄朗從恭禪師重研心法之後,又向慧威請教,成為天台宗的傳人,而沒有順著印宗的指點成為禪宗大師,這或許與恭禪師的導向有關,而恭?黎則是有可能與天台教法有關的大師,因而二者有可能為同一個人。
如果玄朗從學慧威是在依恭禪師後,就不可能太早。玄覺與玄朗為“同友”“志朋”,二人理當是同學于慧威門下,而玄覺於神龍元年(705年)參拜六祖,此前就已經離開了慧威,因而二人同學亦在此前。由此玄朗始學慧威當在證聖元年(695年)至神龍元年(705年)十年間,其從學也不過數年,在慧威入滅前就業已離去。
在精通天台教法和佛教內學之後,玄朗又“博達儒書,兼閒道宗,無不該覽”,對於儒道外學同樣通達無礙。這樣玄朗就打下良好的知識基礎,為其日後成為一代大師準備了條件。也可以說,在學問的積累方面,玄朗有“超師越祖”之風,較大威的但以辭藻文才著稱和小威的“不交人事”確有高明之處。
玄朗樂行頭陀,故於浦陽(今浙江浦江)的一處岩穴造寺,由是號為“左溪”。玄朗居左溪,多謂“凡三十年”,其實這是概說,不只此數。據《婺州浦陽縣佐溪山朗禪師召大師山居書》,中有“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顯然確是玄朗居左溪後所作。玄覺入滅於先天二年(713年),玄朗來書必須在此前,如此其居左溪,前後至少四十多年。三十餘秋可能只是指他“獨坐一室”的時間。
自居左溪後,除開元十六年(728年)一度因刺史王上客所請出山入城說法外,似乎很少離開。據李華《衢州龍興寺故律師體公碑》,體律師(672-763年)曾請左溪大師講止觀。體公與左溪頗有因緣,生年相近,又是同年得度,還是同學,因為體公得度後“游問會稽,遇光(州)律師受其戒”,其受具足戒時在長壽二年(693年),亦與左溪相近,因而可能二人當時就認識。非但如此,體公還“入法華三昧,口不息誦,身不親席,大事因緣,我得心證”,11看來也與天台一宗有關,二人還有共同的弟子—婺州清辨。二人既有如是因緣,想來左溪也不忍拒絕,可能一度赴衢州弘法。是故玄朗雖宴坐左溪,卻也不像慧遠那樣足不離山,需要弘法的時候他還是會出山的。
玄朗一生大半在左溪度過,其經歷並不複雜。前文已述,玄朗學有根柢,然由於其著作未能傳世,故後世對其理論創造和對天台宗義的貢獻不得而知。特別是安定梁肅為舉揚其師湛然,有“頂再世至於左溪,明道若昧”12之語,以顯湛然“煥然中興”之功,將天台宗不振的罪名加諸左溪等前輩,全然不顧左溪之時門庭隆盛、“天台之教鼎盛,何莫由斯也”的事實。由於梁肅為著名文人,又是湛然弟子,故其說流傳後世,成為口實。梁肅此行,實是欲褒其父而貶其祖,不足為道。
玄朗對於整理和發展天台宗義,實有大功。他著有《法華經科文》兩卷,對於重新解釋《法華經》很有價值,可惜不存於世。最為重要的是,他對智者大師的《法華玄義》和《法華文句》進行了系統的整理,並增加了新的解釋。據神迥《天台法華疏序》:
此之《玄》、《文》,是灌頂法師私記,合二十卷。非智不禪,斯言允矣。及其滅後一百餘載,至唐天寶中,歲在戊子,有東陽郡朗和尚,法門之眉壽,涼池之目足,乘戒俱急,內外兼包,獲滿慈之寶器,坐空生之石室。每於講授之次,默然嘆曰:“觀其義趣,深契佛乘;尋其文勢,時有不次。或文續義斷,或文後義前,或長行前開其章,或從後直述其義,或偈中先舉其數,或後不次其名。然聖意難測,但仰信而已。”今因諸聽徒,頻勸請曰:“上根易悟,探賾不迷;中下之侶,尋文失旨。儻更垂次比,此則獲益巨多。”和上再三籌量,事不獲已,乃專念大師,求加可否。因夢所感,方始條倫,蓋亦隨情便宜,諒非苟求同異,輒有增減於其間矣。冀後諸學者,曉其元意,尋領索裳,擔金棄礫;說真實法,非虛妄人;助玄風之廣扇,備丹丘之添削。則百界千如,宛同符契;化城寶所,盡親津橋。賴彌勒之殷勤,回文殊之靳固;輔《發智》之六足,褒《春秋》(之)一言。神迥等,並采綜文前,輕安諦理,莫不空王佛所,同共發心;十六沙彌,鹹皆代講;翳華逢日,除瘼養珠;誠愧雁門之筆,曷窺龍盭之奧!庶探玄之士,沐道流而有本焉。13
據此,玄朗於天寶七年(748年)戊子歲曾經對《法華玄義》和《法華文句》共二十卷進行過整理,並非如《佛祖統紀》所述僅“修治《法華文句》”。整理的原因,是由於二書本身存在不少問題,特別是文勢不次、文義混亂、前後錯雜、次第不明等。雖然明知其中必有錯謬,然而玄朗還是不敢輕動,怕是聖意難測,只能信仰,不可理推。其弟子屢次勸請,以中下根機不易明其旨趣為由,求其更加條倫,以令眾生獲益,玄朗還是猶豫不決,最後只得專念智者大師,求其示下可否修治。結果感得異夢,得到大師允可,玄朗才予以整理。陶靜看來神迥等雖然殷勤勸請,又有大師垂夢為據,對此事的合法性還是不敢完全肯定,故為之百般辯解,道是這次整理不過是隨情便宜,不是為了有意與舊說有所異同,隨意增減。不過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新本確實與舊部有所異同,顯示了玄朗自己的見解,因而對舊部有所增減。這次整理恐怕不只是文勢次第的條理,而是玄朗以己意重新解釋智者原著,也可算是一部新的著作。神迥謂之如同“輔《發智》之六足,褒《春秋》(之)一言”,就足以為證了,因為以“六足”《大毗婆沙論》解釋“一身”《發智論》,六足非同於一身,《婆沙》也不等於《發智》。《法華傳記》卷三對此有類似的記載:
釋玄朗者,字慧明,俗姓傅氏,北地人也。聞天台智者止觀,一其佛法,源發龍樹,中承衡思。尋討法流,居清泰寺。法門之龍象,涼池之目足。業講佛乘,每於講肆之次,披文句,默然嘆曰:“觀其義趣,玄契佛(乘);尋其文勢,有不次第。聖意難測,但仰信耳。”因諸聽眾,頻勸請曰:“上根易悟,中下失旨,更垂次比,弘益巨多。”朗再三籌量,專念大師,求加可否。夢神僧指驚:“?辨無礙,樂說如流。顯匆記說,不悉起盡。汝於空王佛所,同聽斯典;今日靈山,同為聽眾。宿殖所資,助玄風之扇,更加添削,順徒眾情。三根俱益,弘潤巨多。”因夢所感,方始條倫,隨情便宜。朗公講《法華》,感應如斯矣。14
這一記載顯然是根據神迥所述而來,不過對神僧垂夢有詳細的描述,據此是聖僧同意“更加添削”,玄朗此舉不過是從命而已。玄朗的新著肯定有不少新意,只可惜不存於世。不過原作可能並未完全失傳,在其弟子湛然的著述中,尚有保存。據湛然自述:
開元十六年,首游浙東,尋師訪道。至二十年,於東陽金華,遇方岩和尚,示以天台教門,授《止觀》等本。遂求於左溪大師,蒙誨以大旨。自惟識昧,凡所聞見,皆紀於紙墨。暨至德中,移隸此寺。乾元以來,攢成捲軸,蓋欲自防迷謬,而四方道流,偶復傳寫。今自衰疾,諸無所任,留此本兼玄疏兩記共三十卷,以寄此藏,儻於先師遺文,碑補萬一,則不負比來之誠。幸眾共守護,以貽後學。大曆十二年祀孟秋,沙門湛然記。15
湛然大曆十二年(777年)所寄蘇州開元寺大藏的“此本兼玄疏兩記共三十卷”,指的應是《止觀輔行傳弘訣》十卷,《法華玄義釋簽》十卷,《法華疏記》十卷,是湛然解釋天台三大部的著作。這三部著作,依照湛然本人的說法,並非完全出自他個人。其中解釋《摩訶止觀》的《止觀輔行傳弘訣》十卷,主要是受到了方岩玄策的影響指教,其中也有玄朗的指誨,而解釋《法華玄義》的《法華玄義釋簽》十卷,解釋《法華文句》的《法華疏記》十卷,則主要是對玄朗原著的增補發揮,依湛然自述,是對“先師遺文”的補充。湛然將在左溪的“聞見”“紀於紙墨”,後來“攢成捲軸”,而成三部之作,因而其中顯然包含著左溪的思想。有可能正是由於玄朗的著作已經包括在湛然新作之中,已經不再有單純流傳的必要,後世才不見其書。
據此,湛然的中興天台是有條件的。如果沒有玄朗的努力在前,他也不會一下子就寫出新的“三大部”。玄朗的價值,並不只在於薪火相傳,保存法脈,玄朗也並非於台宗義學無甚建樹。這一推論建立在湛然的自述之上,或謂這不過是湛然的自謙之說,然玄朗確有著作在前,湛然想必也不會輕易妄語。玄朗教法,難於悉知。李華《碑》稱:
左溪所傳,止觀為本。癨樹園內,常聞此經;然燈佛前,無有少法。因字以詮義,因義以明理,因理以同如。定慧雙修,空有皆舍,此其略也。菩薩或以性海度,或以普門化,香象至底,彌樓最高,其餘幽贊不知,充滿法界。夫知上法易行,上法難修;上法易證,上法難明。謂左溪為有,則實無所行;謂左溪為無,則妙有常住。
可見左溪所傳法要,是以止觀為本,僧傳亦謂“雖通諸見,獨以止觀為入道之程,作安心之域”,就是“定慧雙修,空有皆舍”。這本是天台宗傳統的法門,也是所有禪宗共行之法。他還“游心十乘,諦冥三觀,四悉利物,六即體遍”,這些都是天台宗的教義。十乘,即十乘觀法,修止觀時應依次觀十種境:陰界入境、煩惱境、病患境、業相境、魔事境、禪定境、諸見境、增上慢境、二乘境、菩薩境。智者認為,在觀想每一境時還應按十個層次進行,即觀不可思議境、起慈悲心、巧安止觀、破法遍、識通塞、修道品、對治助開、知次位、能安忍、無法愛,這樣構成十重觀法。三觀,即一心三觀,是天台宗的核心理論。四悉,即:四悉檀:世界悉檀、各各為人悉擅、對治悉檀、第一義悉檀,智者大師有《四悉檀義》一卷。六即,指:理即、名字即、觀行即、相似即、分證即、究竟即,是天台圓教修行的位次。十乘修觀,三觀明理,四悉利人,六即自證,足以表明他確實做到了“一宗之教跡,研核至精”。
玄朗最為突出的,尚不在於理悟,而在其實修。在懺法上,他特別重視觀音懺。據李華《碑》,他經常“跪懺其間。……偏袒跪膝,奉觀音上聖。願生兜率天,親近彌勒。殫罄衣缽,嚴具尊儀,焚香稽首,則舍利降,靈光發”。僧傳亦謂“雖眾聖繼想,而以觀音悲智為事行良津。……有願生兜率宮,必資福事。乃構殿壁,繢觀音、賓頭盧像。乃焚香斂念,便感五色神光,道俗俱瞻,嘆未曾有。”智者大師有《請觀世音懺法》,玄朗對此嚴格奉行,雖然他生活極為簡樸,但在行懺法時卻嚴設道具,一絲不苟,焚香稽首,行止如儀。同時他還修習彌勒淨土,願生兜率天宮。
玄朗最為人稱道的是長期堅持頭陀行。依李華《碑》,這是他從恭禪師“重研心法”之後所得的指教。他於“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處岩穴。凡三十年,宴居左溪,因以為號。每曰:‘泉石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於此始,亦於此終。’……左溪僻在深山,衣弊食絕,布紙而衣,掬泉而齊;如繒纊之溫,均滑甘之飽。誦經則翔禽下聽,洗缽則騰猿跪捧。宴坐一室,如法界之樂;蕭然一院,等他方之游。或問曰:‘萬行皆空,云何苦行?’對曰:‘本無苦樂,妄習為因,眾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曰:‘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挺根于海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籠中,比大遼廓!’”
玄朗樂居山林,嚴格依照頭陀行的規定行事,特別是阿蘭若法。十八種物指楊枝、澡豆等,是指依律不可缺少的道具和生活用品。事實上,他比佛教早期僧團的作風還嚴。據僧傳及《佛祖統紀》,他“一郁多羅僧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廈,非因尋經典不然一燭,非因覲聖容不行一步”,一件上衣(郁多羅僧)用了四十多年,一個座具(尼師壇)用了一輩子,所食必用“糲蔬”,所居必是偏房,乃至掬泉而飲,以紙為衣。他這樣做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節儉,而是“細行修心”,“徇律法之制”,一舉一動,都完全依照律法,從而達到修心養性的目的。別人都認為這是苦行,他卻樂在其中,不以為苦,道是以此細行,除眾生妄。玄朗真正做到了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完全符合律制佛法,可謂念念是道,“步步踏佛階梯”。
玄朗雖然生活儉樸,被人視為苦行,但他依然蹈乎中道,並未損害身體。非但如此,他的身體還非常健康,“心不離定中,口不嘗藥味,耄期之歲,同乎壯齡”,不僅沒得過病,八十歲時還像壯年人一樣。這或許是值得營養學家和醫學家研究的一個特例,但在當時的人看來,這正是修習止觀而有實效的表現。
玄朗的實修功夫,在天台宗歷代祖師中可能是最高的。這一方面是由於玄朗本人的嚴於律己,也有賴於天下安定、諸緣俱足的外在環境,使他能夠不受干擾地宴坐左溪四十多年。他恰恰生活在唐朝最為興盛的時期,這是多數祖師無法具備的,其於安史之亂前入滅,不知是一種巧合,還是有意為之。
據李華《碑》,玄朗臨終前告門人曰:“吾六印道圓,萬行無礙,戒為心本,汝等師之。”這段話,《佛祖歷代統載》作“吾五印道成,萬行無得,戒為心本,爾等師之”,16《天台九祖傳》作“六即道圓”17,《佛祖統紀》亦然18。“印”與“即”形似,二者皆有可能。如果是“六印”,則有可能是密教法門,大藏中有題名菩提流志譯的《佛心經品亦通大隨求陀羅尼》經,其卷上有六種印契:第一菩提心契;第二菩提心成就契;第三正授菩提契;第四如來母契;第五如來善集陀羅尼契;第六如來語契19。六印法門在現代得到元音老人一系的弘揚,頗有影響。不過此經名不見於《開元錄》,內容上也有些問題,可能是後世所編的偽經。《佛祖歷代統載》為禪宗著作,天台宗的史料都作“六即”,因而可能《全唐文》本和《佛祖歷代統載》有魯魚之訛,不能由此說玄朗修習過密教法門。這表明他已經證得了六即,達到了究竟地位,而且於三千威儀、八萬細行都能具足無礙,這種境界確實不是他人所能及的。他入滅之後,鄉人夢中見其居寶閣第四重,論者以為是指第四重天兜率天宮,表明他已經往生彌勒淨土。
玄朗生活的時代和地域,既有天台宗,又有律宗(包括南山和相部二宗),禪宗南宗和牛頭宗也非常活躍,北宗也開始向這裡滲透。玄朗從當時東南最為著名的大律師光州道岸受具,並從學律范,也結識了體公等不少同學法侶。光州道岸為文綱弟子,可能在從學文綱時還受到了文綱同學玉泉弘景的影響,對天台宗也有一定的了解,因而其弟子中有不少是修習法華三昧,兼學天台宗者。弘景的親傳弟子鑒真在玄朗晚年也到東南傳法,因而天台宗與律宗的關係比較密切和融洽。玄朗和兼屬三論宗與禪宗的牛頭宗不知關係如何,如果恭禪師真是屬於牛頭宗,自然關係密切。當時除改換門庭的牛頭宗一支獨盛外,整個三論宗已經是不絕如縷了。
除律宗外,對玄朗一生有重大影響的莫過於禪宗南宗了。他最初從六祖弟子印宗受學禪律,討論經義,後來又與原為同門至交的永嘉玄覺發生爭論。他與玄覺的友誼和分歧最為令人關注。玄覺和他本為同門,同在天宮慧威門下,後來玄覺又受玄策啟發,到曹溪參拜六祖,結果一宿得道,並從此名震天下。對於玄覺的轉投禪宗,玄朗的態度如何難以悉知,有說玄覺往參六祖就是因為受了玄朗的激勵,這是後起之說,可能性其實不大。當時天台本宗人才稀少,天宮門下只有玄覺和玄朗二人最為傑出。即便不去參拜六祖,受其心要,玄覺也同樣是一個傑出的人物。二人同心協力振興天台,總比玄朗一人孤軍奮戰要好,當然可能這樣會有誰是八祖的問題,但玄朗絕對不會如此計較的。據前,在得知玄覺轉投禪宗後,玄朗特意致書玄覺:
自到靈溪,泰然心意。高低峰頂,振錫常游;石室岩龕,拂乎宴坐。青松碧沼,明月自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名花香果,峰鳥銜將;猨嘯長吟,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為氈。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倘有寸陰,願垂相訪。20
這封書信後來題名為《婺州浦陽縣佐溪山朗禪師召大師山居書》,而從書中卻看不出召其山居之意,只是委婉地請其入山相訪。依玄朗本意,恐怕不只是請其入山訪問,而是欲邀之同弘台宗。書中關鍵的話是“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地未達,方乃如斯”,特別是後兩句,頗有批評玄覺未明心地之義。
玄覺的回信出人意料地十分激烈,贊寧謂之“覺由是念朗之滯見於山,拘情於講,回書激勸。其辭婉靡,其理明白。俾其山世一如,喧靜互用,趣入之意,暗詮如是,達者韙之”21。其實玄覺的回書其理明白是真,其辭婉轉是假,其中當然有勸導之意,不過表面看來,竟像是攻擊,頗有不能仁恕之感。玄覺的回書不光是對暗示其“心地未達”的回擊,更是明白表示他已經有了別的選擇,不可能再去弘揚天台教法。或許玄覺還想讓玄朗明了禪宗,頓悟心印,不過這種意圖也不好明白相示。
二人之書已經明白顯示立場不同,見地有別,同門友誼雖然還在,宗途不一已不可回。總的來說,這次爭論給的印象是玄朗境界不夠,至少不如玄覺,一經贊寧等中立者的傳揚,更是成為口實,加上後來玄覺的名聲遠遠超過玄朗,就連天台宗後輩都認為玄朗之時“明道若昧”,無所建樹,當然不會有人理解玄朗的苦心了。
玄朗與玄覺,一重實行,一重理悟,各有千秋,難分高下。玄覺固然天才特拔,無人可及,而玄朗萬行無礙、終身不易也是極為難得的。玄朗未必不知“山世一如”,也未必“見山忘道”,但他認為山中修道,更加容易。如李華《碑》有人“又問曰:‘山水自利,如聚落何?’”這顯然是對玄覺之說的模擬,玄朗對曰:“名香挺根于海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籠中,比大遼廓!”這也是對玄覺回書的回答。即使是玄覺本人,也得承認玄朗之說無誤。據《楞伽師資記》:
又問:“學問何故不向城邑聚落,要在山居?”(五祖弘忍)答曰:“大廈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間有也。以遠離人故,不被刀斧損斫,一一長成(原作城)大樹,後乃堪為棟樑之用,故知棲神幽谷,遠離囂塵,養性山中,長辭俗事,目前無物,心自安寧,從此道樹花開,禪林盰出也。”22
這一問答與前說幾乎完全一樣,玄覺該不會指責五祖滯山忘道吧。其實玄覺本人也是山居修禪,“於岩下自構禪庵”,“滄海盪其胸,青山拱其背,蓬萊仙客歲月往還,華蓋煙雲晨昏交集”,和左溪並無差別。玄覺“絲不以衣,耕不以食,豈伊莊子大布為裳,自有阿難甘露作飯”,23似乎也是頭陀苦行,雖然可能不如左溪那樣嚴酷,卻也相去不遠。這充分表明玄覺並不反對山居頭陀,只是恐怕見山忘道。左溪也曾出山弘法,並未滯於一山,即使身不出山,也絕非不理世事,而是弘道不止,誨人匪倦,講不待眾,與只求自利者絕異。
除印宗、玄覺外,玄朗與玄策的關係也是值得關注的。玄策啟發玄覺往參六祖,使天台宗少了一個大將,然玄策又授荊溪湛然止觀,並令之往從左溪,又使天台宗添了一個中興功臣。玄策既然能授湛然止觀,則他本人同樣是精通天台教法的。從玄策的年齡和經歷來看,他既可能是天宮慧威的門人,也有可能是法華智威的弟子。四人都是兼通兩宗,玄策玄覺自天台而入禪宗,左溪荊溪自禪宗而入天台,很有意思。
遠公不過虎溪,影響遍及天下;玄朗宴坐左溪,弟子無遠弗屆。事實上,在玄朗之時,天台宗已經呈現中興之勢,門下有許多著名弟子,不少新羅僧人也慕名而來。付法弟子有:衢州龍興寺道賓、淨安寺慧從、越州法華寺法源、神邕、常州福業寺守真、蘇州報恩寺道遵、明州大寶寺道原、婺州開元寺清辨、禹山沙鬥神迥、婺州靈隱寺元淨、棲岩寺法開、杭州靈隱寺法真、靈曜寺法澄、婺州開元寺行宣、常州妙樂寺湛然、建寺的靈稟、新羅僧法融、理應、英純等。
玄朗的弟子,李華《碑》提到的有十七人,值得琢磨的是,稱道賓、法源、神邕、元淨、法開、道遵“皆菩薩僧,開左溪之密藏”,守真、法澄、法真、道源、慧從、清辨“純得醍醐,飽左溪之道味”;行宣、湛然為入室弟子,見如來性,專左溪之法門;諸新羅弟子宏左溪之妙願。似乎並無特別地區分高下,然而湛然沒有突出的地位則是可以肯定的。而在僧傳中只提到道賓、慧從、法源、神邕、守真、道遵、道源、清辨八人,加上為其寫“真贊”的神迥和建寺的靈稟,一共十人,連湛然的名字都未提及。僧傳是根據當時刺史張成綺的《行狀》而作的,屬於當時實錄,可見左溪入滅之時,湛然在其門下地位不高。《佛祖統紀》謂李華《銘》有“傳法有十二,的嗣曰荊溪”24的說法,恐怕是後來的編造,因為李華《碑》並未給湛然一個突出的位置。
開元清辨當時似乎地位最高,李華《碑》稱“清辨禪師等荷擔遺烈,見請斯文”,可見是以清辨領銜的;僧傳亦謂“婺州開元寺清辨,齠年慕道,志意求師,不逾三年,思過半矣”!可惜其具體事跡不詳。除湛然外,玄朗門下見諸僧傳的還有道遵(714-784年)、神邕(710-788年)、大義(691-779年)、神迥。皎然有《蘇州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贊寧依之而作道遵傳。
玄朗的弟子大多禪律互傳,清辨、道遵、神邕、大義都是如此。他們在律學傳承上都是與其師玄朗相同,皆屬光州道岸一系。這一方面擴大了其法系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影響了其傳承的純粹性。
玄朗使天台宗由衰到盛,其前兩代,幾乎都是一脈單傳,而左溪的知名弟子則有十八人之多,見諸僧傳的更是多達五人。在天台宗歷代祖師中,除智者大師之外,是弟子見諸僧傳最多的一個。雖然僧傳的標準不一定完全為人接受,但至少也說明了玄朗在當時的影響和地位。玄朗的新羅弟子英純還歸國傳法,“化行東表”,這是天台教法繼慧思弟子玄光、智顗弟子圓光之後再次流傳朝鮮。
玄朗內外兼通,三學俱精,弘教傳禪,功莫大焉,天台之教鼎盛,何莫由斯也!不可因梁肅一言,便誤認為左溪之時只是“向晦宴息而已”,將“明道若昧”之責加諸左溪,使“煥然中興”之功全歸荊溪。客觀來講,應該是左溪荊溪師徒兩代共同開創了天台宗中興的局面,始於左溪,成於荊溪,左溪開創之功猶不可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