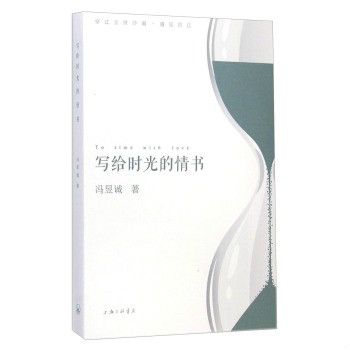選讀:
27
遠行是一個性感的辭彙。
我去過最遠的地方是營口。大學第二年,國慶假期,獨自一人坐上火車,在大雨茫茫中抵達傳說中可以觀賞夕陽墜海的城市,看望一個朋友,到了營口卻聯繫不上他。在火車站附近破舊的小旅館裡過夜,雨水會從窗戶的縫隙濺進來,敲打玻璃的聲音很動聽,他們都是我的朋友們,歡迎遠道而來的我,爭著要和我促膝長談。他們太過熱情,我心神不寧。房間裡就一張床和一台收不到節目的小電視機。公共廁所就是公共浴室,潮濕骯髒,但感覺很奇特,仿佛自己是突然出現在那裡,通過時光隧道或者夢境。
那是第一次一個人到那么遠的地方。沒有相機,沒有手機,沒有銀行卡,只有身份證、有限的人民幣和一個背包,裡面裝著我的衣服和一本書,那本書的名字叫《情人》。那時連女友都沒有更別說情人,但也正因此看的是別人的故事。還有一些餅乾和山楂片。沒有泡麵,我從來都討厭泡麵。那時白天出去到處瞎逛,雨太大天空灰濛濛。晚上回到小旅館,隔壁大叔大媽在打麻將,我就在麻將聲和雨聲中躺著直到睡去。地圖在枕頭下面,離我的思想最近,可我什麼都沒有想。我只在白天把肚子填飽後,開始想我要去哪裡。離開營口的前一天,在地圖上看到鞍山離營口很近,就臨時決定去鞍山。出了火車站後,一個男孩背著包撐著傘一直一直往前走,似乎非常享受那樣的行走,在陌生城市,走累了就停下來休息,再從路的另一邊往回走。去了千山,漫山水霧中的染霜紅葉別樣美,如同披著紅霞衣裳的仙女們款款悠悠似舞又似駐足凝息聽雨。我揀了三顆俊美的石頭裝到我的背包里,那些石頭沉了我的包,也充盈了我在獨自旅途中漫步的心。
其中一顆石頭給了鄭賢,另一顆送小施,還有一顆躺在我自己的抽屜里。
……
36
農村的夜晚,靜謐如禪。漆黑夜裡,我們在零分貝的環境中帶著醉意睡去。久違的熟睡,像在母親溫暖的懷抱里,嬰兒在夢中微笑,笑無聲,穿過雲層,瞬間多少光年,到太空化作星光眨眼,每顆星都鐫刻著一個時空。
37
清澈的夢境清晨醒來。
我們被陽台上群鳥的交響樂喚醒,分不清多少種鳥,唧唧喳喳咕咕啾啾,抑揚頓挫,好不歡快。果真如媽媽所言是大晴天,碧空萬里。四周群山薄霧輕飄,洋溢著亘古而恢弘的美。
早飯後,我們準備翻山越嶺去看蘇珂。蘇珂的墳墓在月牙溝。
月牙溝是村里祖祖輩輩的陰宅所在地,我的祖父母,我爸爸的祖父母,都在那兒。一路上會經過小時候經常玩耍的山坡、梯田、果林、幾十年前的老房子……那時候大家還未遷居山腳下,那些房子生長在花草樹木中長年累月經受風吹雨打,大部分已殘缺不全。也許某天全中國的村莊都成為城鎮乃至城市,這樣的老房子將成為古董或者諷刺。那時邱誠該寫一本《消失的鄉村》。老房子中只有一戶是完好的,因為還住著人。一對老夫婦,男的瘸,女的瞎,他們是我爺爺的同輩。山上條件雖然艱苦,但他們生活簡單幸福,平時養點兒雞鴨牛羊,種點兒果蔬稻穀。他們的孩子都在山下生活,偶爾回來探望他們,他們通常只在村裡有紅白事的時候下山參加。我們要走的路不會經過他們的房子,但可以遠遠地望見。邊走邊和馬斌說著山裡的故事,這些他不曾經歷過的故事,不知道他聽起來是否感覺像異國民謠。
這裡遠離一切喧囂,遠離大城市的欲望、煩躁和污穢,遠離人群,遠離莫名其妙的思緒。在這裡,我們的心可以跟著我們的腳一起行走,享受呼吸,體悟天地和諧。葉子上的露珠漸漸消失,但在消失前我們有幸目睹了晶瑩剔透的完美,那仿佛是一種秘密,藏在葉子的心裡,日光顯露,秘密就逐漸消失或者再次被隱藏。鄭賢曾說:秘密有三種,一個人的,兩個人的,一群人的。而這種秘密是天地間的,最原始也最真摯。露珠熱愛花葉,花葉熱愛大地,大地無言卻儘是天籟福音。
……
42
老地方是一個恆溫游泳館。游泳館的門口是一隻孤獨的海豚雕塑,眼睛裡兩顆藍色燈泡發出幽光,這種光籠罩著我,在黑暗中我感覺自己也發出幽光,直到跳入泳池,水吸走了身上的幽光,才感覺到放鬆。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光的重量。身子浮在水裡談天,是一種享受。就仿佛是飄在雲朵上,或像蝴蝶在樹葉上休憩,聽微風柔和輕語。
這個游泳館原來是市第三游泳館,後來承包給私人經營,換了個名字叫泳春館,乍看以為是教詠春拳的武館。經營者似乎比其他游泳館都更用心,在館場各角落安置音效甚好的音響設備,不時播放優美的鋼琴曲。正在播《秋日的私語》。館場四周的牆上畫滿壁畫,據說是請中國美術學院十八名學生共同完成的,畫的是海洋世界,在藍茫茫中浮游著千奇百怪千嬌百媚的生命,若看的久了,會錯覺畫上的一切都是活生生的。而牆上惟一的鐘,似乎也具有生命,你盯著它,仿佛盯的是自己身體裡的某一部分。
鄭賢在水裡不停的變換泳姿,蛙泳、蝶泳、仰泳、自由式……而我只會蛙泳。分針在我們的暢遊中走完了一圈,我們在淺水區休息,秒針繼續勻速前進。鄭賢的第一句話是:那是一個非常神奇的地方。
……
55
吸引我的,不是漂泊流亡不喜與人交往的寇德卡的坦克和吉普賽人,不是鐘情異國情調的米奇·愛潑斯坦的年輕情侶或塗口紅的警察,不是穿梭槍林彈雨的卡帕的中槍倒下的士兵,也不是放棄家族世代經營的紡織廠的布列松的小孩或畢卡索肖像,而是白白胖胖的矮個兒筱山紀信的裸體女人,樋口可南子。院裡草地上,竹椅和赤裸的軀體之間有柔軟舒適的棉墊,她斜靠著頭,半閉著眼看著相片外的我,將輪廓完美的鼻子和嘴唇置於前景,仿佛在享受午後懶洋洋的時光,雙腿輕輕併攏,右膝比左膝高出半個腿的厚度,隨意半交錯的兩隻手的陰影剛好投在三角地帶,那些黑色的陰毛是身體上的一小片原野,營養富足,充滿想像,雙乳舒緩微垂著,乳頭在空氣中還未變得硬挺,卻也不是羞答答地躲著。她仿佛是在和午後柔暖的微風戀愛,雖然是坐在椅子上,但身子表達的卻是被心愛的男子攔腰抱起的姿勢,多么幸運的竹椅,就這樣被選擇充當一個成熟男人的角色,懷抱赤裸的美女卻在告訴攝影師坐懷不亂的柳下惠應該是什麼樣子。半閉著的雙眼隱藏了她的情意流露出不帶修飾的詩意,那時最是需要一個溫柔的吻,以使世界整個兒霧化到夢境中,只清晰著愛的繾綣。這張相片之前還有一張是她穿著睡袍的迷人模樣。美好的人無論穿衣與否都讓人陶醉。記得演《睏倦之眼》的她,也便記得青春年少的自己。這個拍攝少女館的人說:不拍攝新聞攝影作品是因為覺得撒謊更有意思一些,攝影不是用來捕捉真實的東西,事情通過相機看起來會非常不一樣,把相機垂直放著時與水平放著時拍到的東西都很不一樣。他在拍攝歌舞伎時繼續說:歌舞伎本身是一個謊言,比如女人是由男人扮演的,演員的臉上塗著厚厚的化妝粉,這是一個謊言的世界,像一個迷宮一樣。不過有時候,如果你對謊言說了一個謊,反倒會得到一個真實,所謂負負得正。
他仿佛在說一個眾所周知的秘密。他用相機也用搞怪的表情。人所言說的謊言再複雜,也遠不如這個由無數謊言演繹而成的現實來的龐雜豐富。謊言常常是藝術,而真實更像是一坨狗屎。
她一張張地向我展示,並如數家珍地講述背後的故事。我驚奇於她腦袋裡容納的浩瀚宇宙,頓然反差出自己的空洞與貧乏。我所經歷的可值得回憶的東西還不夠填滿犄角旮旯,應試教育帶給我的啟示在生活面前軟弱無力暗淡無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