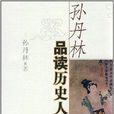《孫丹林品讀歷史人物》主要內容:歷史上的楊貴妃到底是怎樣的人,她究竟有怎樣的經歷,她與唐玄宗到底有沒有真正的愛情,她與唐玄宗皇權的衰敗到底有什麼聯繫,她到底為何而死,死於何處……陸游,作為宋代馳譽文壇的大家,他與唐琬之間的愛情如此深摯,如此執著,這不僅使這個愛情悲歌增添了無比厚重的悽美色彩,千古傳唱;而且,更重要的是極大地突出了悲劇主人公陸游那種高尚的人格魅力。正是這種高尚的人格魅力,才形成了他特有的堅定執著、深摯細膩、樸實無華的學風和詩風。唐伯虎是明代中期具有“詩書畫”三絕美稱的大才子,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後世的人們似乎忘記或是忽視了他別的方面,而把更多的議論集中在對唐伯虎風流成性的評價中。那么,歷史上真實的唐伯虎到底是怎樣的風流才子呢?“江南第一才子”究竟是怎么來的?“唐伯虎點秋香”確有其事嗎……
基本介紹
- 書名:孫丹林品讀歷史人物
- 出版社:天津教育出版社
- 頁數:254頁
- 開本:16
- 品牌:天津教育
- 作者:孫丹林
- 出版日期:2007年4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30949047, 7530949047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孫丹林品讀歷史人物》共講述了三個歷史人物:一個是唐朝頗具傳奇色彩的著名美人——楊貴妃;一個是南宋著名詩人——陸游;還有一個是明代才子——唐伯虎。作者從浩繁的史料和版本眾多的民間傳說中提煉出人物的主要方面,剝去時間罩上的面紗,還原真實的歷史人物。
作者簡介
孫丹林,渤海大學特聘教授、錦州市楹聯學會會長、遼寧省美學學會理事、中國大眾文學學會理事。 他曾發表論文及文藝作品百餘篇。2005—2006年,兩次榮獲“中國詩人節”之大獎和金獎。另有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的個人詩集《飛來石詩箋》,該書已被文化部主辦的詩歌節組委會定為永久收藏書目。另有主審、主編文集若干。 2006年以來,他先後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欄目主講《楹聯的故事》《陸游》《唐伯虎》《我讀老子》等節目。
圖書目錄
鏡子·帽子·膽子及其他 自序
·女人·貴妃·冤魂·
一、痴心夢幻的女人
難解的疑團
潛藏的夢幻
二、王妃如何變成了道姑?
壽王妃的背後
武惠妃的死由
鬱悶的玄宗皇帝
入道敕文的玄秘
三、登堂入室的楊貴妃
皇宮裡的道姑
道姑登堂入室
四、楊貴妃與唐玄宗有真正的愛情嗎?
愛情不是肉慾
愛情需要代價
五、“禍水論”可以休矣
“禍水論”的由來
楊貴妃是禍水嗎?
六、楊玉環真的死在馬嵬坡嗎?
馬嵬坡兵變原因
楊玉環死在馬嵬坡嗎?
附錄楊貴妃生平簡表
·位卑未敢忘憂國·
一、時代不幸詩人幸
二、社會和家庭對陸游的影響
三、陸游的官宦世家
四、陸游仕途的坎坷遭遇
五、陸游婚姻的慘痛挫折
六、陸游詩風的初步形成及特徵
七、陸游愛國思想的進一步形成
八、陸游詩風的豪放風格
九、陸游詩歌的廣泛題材
十、陸游詩詞的文學地位
十一、亘古男兒一放翁
附錄一:讀《劍南詩稿》
附錄二:陸放翁年譜
·一代風流才子·
一、唐伯虎點秋香的由來
二、唐伯虎的辛酸家事
三、唐伯虎的牢獄之災
四、唐伯虎是江南第一才子嗎?
五、唐伯虎到底是怎樣的風流才子
附錄:唐寅年表
參考文獻書目
·女人·貴妃·冤魂·
一、痴心夢幻的女人
難解的疑團
潛藏的夢幻
二、王妃如何變成了道姑?
壽王妃的背後
武惠妃的死由
鬱悶的玄宗皇帝
入道敕文的玄秘
三、登堂入室的楊貴妃
皇宮裡的道姑
道姑登堂入室
四、楊貴妃與唐玄宗有真正的愛情嗎?
愛情不是肉慾
愛情需要代價
五、“禍水論”可以休矣
“禍水論”的由來
楊貴妃是禍水嗎?
六、楊玉環真的死在馬嵬坡嗎?
馬嵬坡兵變原因
楊玉環死在馬嵬坡嗎?
附錄楊貴妃生平簡表
·位卑未敢忘憂國·
一、時代不幸詩人幸
二、社會和家庭對陸游的影響
三、陸游的官宦世家
四、陸游仕途的坎坷遭遇
五、陸游婚姻的慘痛挫折
六、陸游詩風的初步形成及特徵
七、陸游愛國思想的進一步形成
八、陸游詩風的豪放風格
九、陸游詩歌的廣泛題材
十、陸游詩詞的文學地位
十一、亘古男兒一放翁
附錄一:讀《劍南詩稿》
附錄二:陸放翁年譜
·一代風流才子·
一、唐伯虎點秋香的由來
二、唐伯虎的辛酸家事
三、唐伯虎的牢獄之災
四、唐伯虎是江南第一才子嗎?
五、唐伯虎到底是怎樣的風流才子
附錄:唐寅年表
參考文獻書目
文摘
唐代,是一切中國人的記憶。因此,永遠被後人一代代闡述。長生殿的故事,找到第一個傑出的闡述者白居易是在半個世紀之後(《長恨歌》作於806年),找到第二個更完整的闡述者洪異是在十個世紀之後;“又過了三個世紀。我們還在闡述,因為我們還有記憶”。(余秋雨語)
唐代的確是值得“一切中國人”記憶的朝代。因為它是中國古代歷史中最輝煌、最值得驕傲的鼎盛時代。值得我們後人記憶的唐朝,除了經濟的發達和文化的繁榮以外,還有更多的美麗動人的故事,還有更多的撲朔迷離的懸案。唐代開元、天寶年間的貴妃——楊玉環就是其中的一個。
我們現在所闡述的楊貴妃,基本上是根據前人的記憶——其中有正史,也有野史,還有民間傳說。但由於前人“記憶”內容的不同,因此,人們對同一人物或事件的闡述各異。所以,一千多年來,人們不僅不斷地闡述著發生在楊玉環身上的許多美麗而動人的故事,而且在闡述中留下了太多的爭議和至今難解的謎。
在中國提起楊貴妃,可以說是家喻戶曉,婦孺盡知了。作為“貴妃”,她只不過是歷史上自有皇帝以來無以數計的皇妃中的“一個”罷了,為什麼偏偏楊玉環的知名度這么高呢?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在歷代皇帝後宮中,她是一位極其特殊的女人。她生前,在朝野上下就聲名遠播;宮中自不必說,就連市井百姓都知道唐玄宗的寵妃——楊玉環。正是因為這樣,她死後就立即產生了一個接一個的種種傳說。圍繞著楊貴妃這個人物,歷朝歷代、各種版本的文學形式、演唱形式真是難以盡數。千百年來,人們為什麼對楊貴妃的記憶如此深刻,對她的故事的闡述如此眾多呢?
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三個原因。
(1)從歷史、政治的角度來看,楊貴妃是個值得評價的人物。歷代許多評論家認為:楊貴妃是導致唐玄宗政治衰敗、生活腐朽、政權瓦解的罪魁禍首,她在馬嵬坡兵變中致死是罪有應得。更有許多人認為,她並非兩千多年來封建皇權的後宮中普通的皇妃宮女,而是導致一代皇權崩潰的相當重要的歷史人物。因此,她被認為是“女人亂政”的禍水之一,甚至說她是淫婦、妖姬。劉禹錫在詩中所說的“天子舍妖姬”,不就是指楊貴妃嗎?那么,楊貴妃真的是“女人亂政”的禍水嗎?
(2)從文學藝術創作的角度來看,她是創作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的素材。從唐朝白居易的《長恨歌》開始,一千多年來,歷代的詩人、劇作家、小說家以及其他各類藝術家一直把楊貴妃當做藝術創作的重點。比如清代洪舁的《長生殿》、現代的京劇《貴妃醉酒》、歌舞劇《唐明皇與楊貴妃》以及諸多的藝術作品都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藝術手段來描繪和詮釋楊貴妃其人、其事。其中大部分作品意在歌頌唐明皇與楊貴妃傳奇的愛情故事。那么,楊貴妃與唐玄宗真的有愛情嗎?
(3)從廣大百姓的文化心理需要的角度來看,廣大老百姓關心和欣賞,甚至津津樂道的是她和唐明皇之間的愛情故事:一位是風流皇帝,一位是多情貴妃;儘管他們的身份與百姓的地位相差懸殊,他們的故事與今天的時代相去太遠,但是,他們之間富有人文情趣和浪漫色彩的傳說卻一直在民間流傳。楊貴妃的故事有如《大唐歌飛》所演的那樣,從大唐開始傳唱,縹縹緲緲、斷斷續續,幽怨纏綿、迴腸盪氣,一直唱到現在,唱到廣大百姓耳熟能詳的程度。白居易《長恨歌》中“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這幾句詩至今仍在廣大百姓中久傳不衰。
但是,歷史上的楊貴妃到底是怎樣的人,她究竟有怎樣的經歷,她與唐玄宗到底有沒有真正的愛情,她與唐玄宗皇權的衰敗到底有什麼聯繫,她到底為何而死,死於何處……這些難解的謎團,都是我們今天十分感興趣的話題。
(二)潛藏的夢幻
我們今天來敘述古人,或描述古人,不論她(他)是誰,即使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也必須首先以平民的心態,把她(他)看做一個“普通”的人,從普通的人性角度審視其語言、行為,並將其社會地位的變化以及特定的環境等諸方面聯繫在一起,從中揭示出她(他)的心理和性格特徵。因為所有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其“人之初”,和普天下所有家庭出生的嬰兒一樣,只是一個普通的“孩子”;其中更有可能在一段時間內,只是一個普通的人。還是陳涉(勝)說得好:“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史記·陳涉世家》)也就是說,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皇帝或天生的貴妃。
唐代的確是值得“一切中國人”記憶的朝代。因為它是中國古代歷史中最輝煌、最值得驕傲的鼎盛時代。值得我們後人記憶的唐朝,除了經濟的發達和文化的繁榮以外,還有更多的美麗動人的故事,還有更多的撲朔迷離的懸案。唐代開元、天寶年間的貴妃——楊玉環就是其中的一個。
我們現在所闡述的楊貴妃,基本上是根據前人的記憶——其中有正史,也有野史,還有民間傳說。但由於前人“記憶”內容的不同,因此,人們對同一人物或事件的闡述各異。所以,一千多年來,人們不僅不斷地闡述著發生在楊玉環身上的許多美麗而動人的故事,而且在闡述中留下了太多的爭議和至今難解的謎。
在中國提起楊貴妃,可以說是家喻戶曉,婦孺盡知了。作為“貴妃”,她只不過是歷史上自有皇帝以來無以數計的皇妃中的“一個”罷了,為什麼偏偏楊玉環的知名度這么高呢?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在歷代皇帝後宮中,她是一位極其特殊的女人。她生前,在朝野上下就聲名遠播;宮中自不必說,就連市井百姓都知道唐玄宗的寵妃——楊玉環。正是因為這樣,她死後就立即產生了一個接一個的種種傳說。圍繞著楊貴妃這個人物,歷朝歷代、各種版本的文學形式、演唱形式真是難以盡數。千百年來,人們為什麼對楊貴妃的記憶如此深刻,對她的故事的闡述如此眾多呢?
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三個原因。
(1)從歷史、政治的角度來看,楊貴妃是個值得評價的人物。歷代許多評論家認為:楊貴妃是導致唐玄宗政治衰敗、生活腐朽、政權瓦解的罪魁禍首,她在馬嵬坡兵變中致死是罪有應得。更有許多人認為,她並非兩千多年來封建皇權的後宮中普通的皇妃宮女,而是導致一代皇權崩潰的相當重要的歷史人物。因此,她被認為是“女人亂政”的禍水之一,甚至說她是淫婦、妖姬。劉禹錫在詩中所說的“天子舍妖姬”,不就是指楊貴妃嗎?那么,楊貴妃真的是“女人亂政”的禍水嗎?
(2)從文學藝術創作的角度來看,她是創作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的素材。從唐朝白居易的《長恨歌》開始,一千多年來,歷代的詩人、劇作家、小說家以及其他各類藝術家一直把楊貴妃當做藝術創作的重點。比如清代洪舁的《長生殿》、現代的京劇《貴妃醉酒》、歌舞劇《唐明皇與楊貴妃》以及諸多的藝術作品都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藝術手段來描繪和詮釋楊貴妃其人、其事。其中大部分作品意在歌頌唐明皇與楊貴妃傳奇的愛情故事。那么,楊貴妃與唐玄宗真的有愛情嗎?
(3)從廣大百姓的文化心理需要的角度來看,廣大老百姓關心和欣賞,甚至津津樂道的是她和唐明皇之間的愛情故事:一位是風流皇帝,一位是多情貴妃;儘管他們的身份與百姓的地位相差懸殊,他們的故事與今天的時代相去太遠,但是,他們之間富有人文情趣和浪漫色彩的傳說卻一直在民間流傳。楊貴妃的故事有如《大唐歌飛》所演的那樣,從大唐開始傳唱,縹縹緲緲、斷斷續續,幽怨纏綿、迴腸盪氣,一直唱到現在,唱到廣大百姓耳熟能詳的程度。白居易《長恨歌》中“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這幾句詩至今仍在廣大百姓中久傳不衰。
但是,歷史上的楊貴妃到底是怎樣的人,她究竟有怎樣的經歷,她與唐玄宗到底有沒有真正的愛情,她與唐玄宗皇權的衰敗到底有什麼聯繫,她到底為何而死,死於何處……這些難解的謎團,都是我們今天十分感興趣的話題。
(二)潛藏的夢幻
我們今天來敘述古人,或描述古人,不論她(他)是誰,即使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也必須首先以平民的心態,把她(他)看做一個“普通”的人,從普通的人性角度審視其語言、行為,並將其社會地位的變化以及特定的環境等諸方面聯繫在一起,從中揭示出她(他)的心理和性格特徵。因為所有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其“人之初”,和普天下所有家庭出生的嬰兒一樣,只是一個普通的“孩子”;其中更有可能在一段時間內,只是一個普通的人。還是陳涉(勝)說得好:“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史記·陳涉世家》)也就是說,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皇帝或天生的貴妃。
序言
本來沒有寫序或跋的打算,因為我的歷史知識實在是寥寥;自己便沒有覺得是在寫書,而是在完成一本欠時已久的自修作業。可是收筆之後,總覺得還有很多要說的話。而這些咽中之鯁又不宜插在正文中,於是就想出這非驢非馬的題目,不知是否畫蛇添足。
鏡子,古代是銅製,因此稱“鑒”。唐朝的輔臣魏徵死後,唐太宗對大臣們說:“人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史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知得失,征沒,朕失一鑒矣。”(《唐史》)這話真是由衷之語,即使現在讀來也是至理名言。
鏡子的種類很多,普通鏡、防水鏡、防霧鏡、哈哈鏡……甚至人們通常把眼鏡也叫鏡子,如花鏡、墨鏡、防風鏡……我們通過各種各樣的鏡子能看到各種各樣的事物,所看到的各種各樣的事物,又給人以各種各樣的感覺和認識。當然,人們平常用得最多的還是生活中的普通鏡。人們用它來審視自己,有時甚至還要通過它來“修改”自己。比如舞台上的演員在化妝間裡對著鏡子,如果發現自己眼睛小了,可以畫大一點,嘴巴大了再畫小一點;鼻樑不太正,還可以畫兩條直直的鼻線,用以調整……使自己的形象更美一點。如果說人生是戲劇,那么,生活就是舞台。在現實生活的舞台上,人們總是要通過鏡子來修飾自己,這是無可厚非的。而觀看歷史舞台則有所不同,我們後人在回看歷史、學習歷史的時候。既要“以史為鑑”,就必須自覺地正視並尊重鏡子所反映的客觀呈像,就不能再像演員那樣去任意“塗改”。一位詩人說:“在鏡子中發現皺紋的時候,那不是你老了,而是鏡子的變化。”這只是詩,是詩人用物我互化的手法給人以永遠年輕的自信;實際上鏡子的客觀性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我們在回看、學習歷史的時候,有時卻要戴上防風鏡。因為我們剛要開啟塵封已久的歷史的時候,不知什麼原因會突然刮來一股“風”,而且風勢很大,簡直就是“沙塵暴”。幾年前,杭州的某一位歷史學教授在央視做“課程改革”報告的時候就說,先秦的一些人物我們就不放到教材里了,因為有些人物“不好說”。比如屈原,他是為楚國而死;秦統一六國應該說是歷史的進步,所以這些先秦的歷史人物我們就不再單提了。還有一位史學家稱,今後像岳飛這樣的歷史人物不宜再說成是“民族英雄”。因為當時的金人就是我們現在滿族的前身,如今我們已經是由五十六個民族構成的中華民族了……(關於這個問題的質疑和闡述,筆者在本書——《位卑未敢忘憂國》中已有詳文,此不贅述)。像這樣干擾人們視線、攪亂人們心神的“風”和“霧”,我們要不戴上防風鏡或防霧鏡怎能正確、客觀地看清歷史呢?我們如何去確立自己的歷史觀呢?
回看歷史是通過悠遠、漫長的時空隧道去尋找真實的、富有價值的信息,從而“以史為鑑,可知興替”。既然是這樣,那么我們有時就需要望遠鏡、放大鏡,有時則需要防風鏡、防霧鏡;但千萬不可以戴墨鏡或變色鏡……
帽子也是人們生活的必需品,但其中的說法很多。其實,古人能戴帽子的人相當少。廣大老百姓沒有戴帽子的資格,只能將一頭青絲束起來,露在外面,所以稱“黎民百姓”;或者拿塊麻布裹在頭上,叫做巾幘。《宋書·陶潛傳》中記載了陶淵明“葛巾漉酒”的故事:“郡將候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由此就產生了典故——葛巾漉酒。這個典故原指用葛麻做的頭巾濾酒,因為古代的酒製作粗糙,喝前需要過濾。後來形容愛酒成癖的人,或比喻其人率真灑脫。
有資格戴帽子的人當然是有身份的人,儘管歷代的官服、官帽各有不同,但觀其服帽,一下子便能夠看出其身份。比如現代漢語中常用的皇冠、桂冠、烏紗帽……都是從帽子上便可以看出人物身份的名詞。不僅歷史上標明身份的帽子種類繁多,眼下作為名頭標誌的“帽子”也是令人眼花繚亂。其實,帽子更是身外之物,帽子的高低貴賤絕不等於腦袋的貴賤高低。有一副對聯很是耐人尋味:“劈破石榴,紅門中許多酸子;咬開銀杏,白衣里一個大仁(人)。”
“這副對聯說的是,某白衣出身之御史,春日高照,衣錦還鄉。本地縣令率一乾舉人、秀才人等出迎於城外,恭候御使大駕。中有儒生竊以為御使並非科舉出身,沒有“帽子”,蓋為才學疏淺,故顯不屑之情狀。御史盡收眼底,不禁心動,為訓誡其淺薄,口中出句日:“劈破石榴,紅門中許多酸子。”眾秀才聽罷多面面相覷,不解其意,中有二三儒生面帶斷顏亦不能對。御史則心中瞭然,笑而道出下聯日:“咬開銀杏,白衣里一個大仁(人)”。上聯說只重科舉之“黌門秀才”,其實,是徒為令人作澀之“酸子”;下聯則日切莫小覷白衣,其中競出大人物也。
賞讀斯聯亦不禁令人心生感慨:“於史中未經科舉或未能通過科舉而成大事者,古今中外代不乏人。中有蒲松齡,外有高爾基。而於今世,竟還有某某非某某學歷而因此為人不齒者,豈不知某某雖有某某學歷者,競弗如非某某學歷之某某也歟?”(摘自拙作《飛來石聯語》)
關於帽子的問題,在下倒是有兩種想法。一是我們回看歷史,千萬不要以“帽”取人。不要以為某某人因戴了某頂帽子他就一定應該怎樣,也不要因某某人沒戴某頂帽子他就一定應該沒怎么樣。比如陶淵明,千年來一直戴著一頂“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大有骨氣、大為清正的帽子的古代知識分子,殊不知他也寫過關於女人腳的詩:“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閒情賦》)
再比如,許多人說唐玄宗畢竟是皇帝,所以他與楊貴妃只能是皇帝與女人之間的肉慾關係,不可能有什麼愛情。這倒奇怪了,難道就是因為他戴了一頂帝王的“帽子”,他就不會有愛情了嗎?“愛情”本是人的“專利”,只有人才可能產生並享受愛情。這就是人和其他動物的“性活動”不可混淆、不能同比的本質區別。難道就是因為李隆基戴了唐明皇的“帽子”,他就不是“人”了,從而就可以取消他產生和享受“愛情”的權利了嗎?
還有,一些人戴著大學者、大評論家的帽子,難道他考評歷史的所有觀點,就都是正確的嗎?如果屈原不是愛國詩人,如果岳飛不是民族英雄,那還會有“歷史”嗎?在歷史隧道的邊口,風沙和霧水真是太多了。正因為如此,北宋的大政治家、大散文家、大學者王安石才能發出如此感嘆:“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更何況我們呢?為此,我覺得回看歷史,學習歷史,真不可因“帽子”取人,以“帽子”是尊。
膽子人人都有,大小有別。在文藝舞台上,有些頻頻出鏡的“走紅人物”本來沒有什麼藝術細胞,更談不上表演功力。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膽兒大不害臊,敢耍,敢造,敢於作賤自己。這也倒罷了,可是我們沒想到,一些戴著什麼“家”、什麼“者”的各種“帽子”的評審們,為了面子,或者是為了票子,竟然“大膽”拋棄了文藝評論、藝術審美的基本原則,反把這些本沒有什麼藝術含量可言的“走紅人物”又捧成了什麼“家”,最低也送他一頂什麼“星”的“帽子”。由此也可看出,眼下文藝界的“帽子”真就不是什麼值錢的玩意了。不過話又說回來,這種現象對於當今的文藝舞台也還就罷了。可是,在觀看歷史舞台上形形色色的角色的時候,我們可千萬不能電線桿上插雞毛——硬戳大撣(膽)子。
我曾經看了一出以楊貴妃為題材的地方戲,這齣戲的編導膽子就特別的大。戲一開場就讓“閒極難忍”(唱詞中的反映)的壽王妃——楊玉環跑到唐玄宗的狩獵場,並帶了一個“小鹿”的面具;這也算是頗具苦心的創意。當“小鹿”被唐玄宗“捕獲”後,那楊玉環剛一“現身”,壽王就欲以斥退,但馬上又被玄宗阻止了。唐玄宗與楊玉環兩人“對視”不久,胡亂唱幾句,楊玉環便飛身投到了唐玄宗的懷抱……
這么荒唐地構思情節,如此輕率地塑造人物,該劇編導者的膽子不是太大了么?可見從古至今罵楊玉環是“妖姬”“蕩婦”者,實在是由來久矣,毀者眾矣!其實,那楊貴妃和唐伯虎一樣,在歷史舞台上他們都不過是富有浪漫色彩的悲劇人物。本來他們生前就已經有諸多不幸,我們怎能在其長眠地下之後,還往他們身上潑“髒水”呢?文藝創作允許虛構,但必須恪守尊重歷史、尊重歷史人物基本性格的原則。否則,我們將愧對先人,貽誤後人。因此,學習和研究歷史,提倡大膽置疑,但必須小心求證。
學習真是苦差事,想做一點學問就更苦。雖然我不會做學問,但我體會所謂做“學問”,就是“三學”“三問”。
“三學”,即向書本學,向老師學,向社會學。
“三問”,即問書本——在讀書的過程中,不斷產生疑問。南宋文壇領袖朱熹說:“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裡方是長進。”比如,《論語》中“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中的“習”多數注家都解為“反覆練習”,這就值得懷疑了。至聖先師孔老夫子怎能隨便地說“學習了新的東西,經常、反覆地練習,不是很快樂的事嗎?”難怪許多學生聽老師講完這個句子後心存疑竇:“我怎么就沒感到快樂呢?”其實,“習”本作“留”,從羽、從自。其本意是鼻子,象形字。“留”的本意是說小鳥初飛的時候,頻頻振羽,且呼吸;因此用在學習上還有體味、回味和揣摩的意思,才能“樂在其中”。這樣意思就完整了——學習新的東西,能經常反覆地體味、揣摩並練習不是很快樂的事嗎?
問老師——向一切“有道”者請教,誰是老師?凡是能夠傳道解惑的人都是老師,誠如唐代韓愈所言:“無貴無賤,無長無幼,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問自己,即向自己質疑,問自己是否明白、是否信服。
我的這本拙作,是我經過“學”和“問”之後的心得,權做我向“社會大學”呈交的自修作業。這裡的偏陋、錯誤肯定不少,因此我十分懇切地希望我的“同學”和老師能夠“橫挑鼻子豎挑眼”,多加批評指正,讓我今後能做出更好一點的功課。
鏡子,古代是銅製,因此稱“鑒”。唐朝的輔臣魏徵死後,唐太宗對大臣們說:“人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史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知得失,征沒,朕失一鑒矣。”(《唐史》)這話真是由衷之語,即使現在讀來也是至理名言。
鏡子的種類很多,普通鏡、防水鏡、防霧鏡、哈哈鏡……甚至人們通常把眼鏡也叫鏡子,如花鏡、墨鏡、防風鏡……我們通過各種各樣的鏡子能看到各種各樣的事物,所看到的各種各樣的事物,又給人以各種各樣的感覺和認識。當然,人們平常用得最多的還是生活中的普通鏡。人們用它來審視自己,有時甚至還要通過它來“修改”自己。比如舞台上的演員在化妝間裡對著鏡子,如果發現自己眼睛小了,可以畫大一點,嘴巴大了再畫小一點;鼻樑不太正,還可以畫兩條直直的鼻線,用以調整……使自己的形象更美一點。如果說人生是戲劇,那么,生活就是舞台。在現實生活的舞台上,人們總是要通過鏡子來修飾自己,這是無可厚非的。而觀看歷史舞台則有所不同,我們後人在回看歷史、學習歷史的時候。既要“以史為鑑”,就必須自覺地正視並尊重鏡子所反映的客觀呈像,就不能再像演員那樣去任意“塗改”。一位詩人說:“在鏡子中發現皺紋的時候,那不是你老了,而是鏡子的變化。”這只是詩,是詩人用物我互化的手法給人以永遠年輕的自信;實際上鏡子的客觀性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我們在回看、學習歷史的時候,有時卻要戴上防風鏡。因為我們剛要開啟塵封已久的歷史的時候,不知什麼原因會突然刮來一股“風”,而且風勢很大,簡直就是“沙塵暴”。幾年前,杭州的某一位歷史學教授在央視做“課程改革”報告的時候就說,先秦的一些人物我們就不放到教材里了,因為有些人物“不好說”。比如屈原,他是為楚國而死;秦統一六國應該說是歷史的進步,所以這些先秦的歷史人物我們就不再單提了。還有一位史學家稱,今後像岳飛這樣的歷史人物不宜再說成是“民族英雄”。因為當時的金人就是我們現在滿族的前身,如今我們已經是由五十六個民族構成的中華民族了……(關於這個問題的質疑和闡述,筆者在本書——《位卑未敢忘憂國》中已有詳文,此不贅述)。像這樣干擾人們視線、攪亂人們心神的“風”和“霧”,我們要不戴上防風鏡或防霧鏡怎能正確、客觀地看清歷史呢?我們如何去確立自己的歷史觀呢?
回看歷史是通過悠遠、漫長的時空隧道去尋找真實的、富有價值的信息,從而“以史為鑑,可知興替”。既然是這樣,那么我們有時就需要望遠鏡、放大鏡,有時則需要防風鏡、防霧鏡;但千萬不可以戴墨鏡或變色鏡……
帽子也是人們生活的必需品,但其中的說法很多。其實,古人能戴帽子的人相當少。廣大老百姓沒有戴帽子的資格,只能將一頭青絲束起來,露在外面,所以稱“黎民百姓”;或者拿塊麻布裹在頭上,叫做巾幘。《宋書·陶潛傳》中記載了陶淵明“葛巾漉酒”的故事:“郡將候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由此就產生了典故——葛巾漉酒。這個典故原指用葛麻做的頭巾濾酒,因為古代的酒製作粗糙,喝前需要過濾。後來形容愛酒成癖的人,或比喻其人率真灑脫。
有資格戴帽子的人當然是有身份的人,儘管歷代的官服、官帽各有不同,但觀其服帽,一下子便能夠看出其身份。比如現代漢語中常用的皇冠、桂冠、烏紗帽……都是從帽子上便可以看出人物身份的名詞。不僅歷史上標明身份的帽子種類繁多,眼下作為名頭標誌的“帽子”也是令人眼花繚亂。其實,帽子更是身外之物,帽子的高低貴賤絕不等於腦袋的貴賤高低。有一副對聯很是耐人尋味:“劈破石榴,紅門中許多酸子;咬開銀杏,白衣里一個大仁(人)。”
“這副對聯說的是,某白衣出身之御史,春日高照,衣錦還鄉。本地縣令率一乾舉人、秀才人等出迎於城外,恭候御使大駕。中有儒生竊以為御使並非科舉出身,沒有“帽子”,蓋為才學疏淺,故顯不屑之情狀。御史盡收眼底,不禁心動,為訓誡其淺薄,口中出句日:“劈破石榴,紅門中許多酸子。”眾秀才聽罷多面面相覷,不解其意,中有二三儒生面帶斷顏亦不能對。御史則心中瞭然,笑而道出下聯日:“咬開銀杏,白衣里一個大仁(人)”。上聯說只重科舉之“黌門秀才”,其實,是徒為令人作澀之“酸子”;下聯則日切莫小覷白衣,其中競出大人物也。
賞讀斯聯亦不禁令人心生感慨:“於史中未經科舉或未能通過科舉而成大事者,古今中外代不乏人。中有蒲松齡,外有高爾基。而於今世,竟還有某某非某某學歷而因此為人不齒者,豈不知某某雖有某某學歷者,競弗如非某某學歷之某某也歟?”(摘自拙作《飛來石聯語》)
關於帽子的問題,在下倒是有兩種想法。一是我們回看歷史,千萬不要以“帽”取人。不要以為某某人因戴了某頂帽子他就一定應該怎樣,也不要因某某人沒戴某頂帽子他就一定應該沒怎么樣。比如陶淵明,千年來一直戴著一頂“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大有骨氣、大為清正的帽子的古代知識分子,殊不知他也寫過關於女人腳的詩:“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閒情賦》)
再比如,許多人說唐玄宗畢竟是皇帝,所以他與楊貴妃只能是皇帝與女人之間的肉慾關係,不可能有什麼愛情。這倒奇怪了,難道就是因為他戴了一頂帝王的“帽子”,他就不會有愛情了嗎?“愛情”本是人的“專利”,只有人才可能產生並享受愛情。這就是人和其他動物的“性活動”不可混淆、不能同比的本質區別。難道就是因為李隆基戴了唐明皇的“帽子”,他就不是“人”了,從而就可以取消他產生和享受“愛情”的權利了嗎?
還有,一些人戴著大學者、大評論家的帽子,難道他考評歷史的所有觀點,就都是正確的嗎?如果屈原不是愛國詩人,如果岳飛不是民族英雄,那還會有“歷史”嗎?在歷史隧道的邊口,風沙和霧水真是太多了。正因為如此,北宋的大政治家、大散文家、大學者王安石才能發出如此感嘆:“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更何況我們呢?為此,我覺得回看歷史,學習歷史,真不可因“帽子”取人,以“帽子”是尊。
膽子人人都有,大小有別。在文藝舞台上,有些頻頻出鏡的“走紅人物”本來沒有什麼藝術細胞,更談不上表演功力。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膽兒大不害臊,敢耍,敢造,敢於作賤自己。這也倒罷了,可是我們沒想到,一些戴著什麼“家”、什麼“者”的各種“帽子”的評審們,為了面子,或者是為了票子,竟然“大膽”拋棄了文藝評論、藝術審美的基本原則,反把這些本沒有什麼藝術含量可言的“走紅人物”又捧成了什麼“家”,最低也送他一頂什麼“星”的“帽子”。由此也可看出,眼下文藝界的“帽子”真就不是什麼值錢的玩意了。不過話又說回來,這種現象對於當今的文藝舞台也還就罷了。可是,在觀看歷史舞台上形形色色的角色的時候,我們可千萬不能電線桿上插雞毛——硬戳大撣(膽)子。
我曾經看了一出以楊貴妃為題材的地方戲,這齣戲的編導膽子就特別的大。戲一開場就讓“閒極難忍”(唱詞中的反映)的壽王妃——楊玉環跑到唐玄宗的狩獵場,並帶了一個“小鹿”的面具;這也算是頗具苦心的創意。當“小鹿”被唐玄宗“捕獲”後,那楊玉環剛一“現身”,壽王就欲以斥退,但馬上又被玄宗阻止了。唐玄宗與楊玉環兩人“對視”不久,胡亂唱幾句,楊玉環便飛身投到了唐玄宗的懷抱……
這么荒唐地構思情節,如此輕率地塑造人物,該劇編導者的膽子不是太大了么?可見從古至今罵楊玉環是“妖姬”“蕩婦”者,實在是由來久矣,毀者眾矣!其實,那楊貴妃和唐伯虎一樣,在歷史舞台上他們都不過是富有浪漫色彩的悲劇人物。本來他們生前就已經有諸多不幸,我們怎能在其長眠地下之後,還往他們身上潑“髒水”呢?文藝創作允許虛構,但必須恪守尊重歷史、尊重歷史人物基本性格的原則。否則,我們將愧對先人,貽誤後人。因此,學習和研究歷史,提倡大膽置疑,但必須小心求證。
學習真是苦差事,想做一點學問就更苦。雖然我不會做學問,但我體會所謂做“學問”,就是“三學”“三問”。
“三學”,即向書本學,向老師學,向社會學。
“三問”,即問書本——在讀書的過程中,不斷產生疑問。南宋文壇領袖朱熹說:“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裡方是長進。”比如,《論語》中“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中的“習”多數注家都解為“反覆練習”,這就值得懷疑了。至聖先師孔老夫子怎能隨便地說“學習了新的東西,經常、反覆地練習,不是很快樂的事嗎?”難怪許多學生聽老師講完這個句子後心存疑竇:“我怎么就沒感到快樂呢?”其實,“習”本作“留”,從羽、從自。其本意是鼻子,象形字。“留”的本意是說小鳥初飛的時候,頻頻振羽,且呼吸;因此用在學習上還有體味、回味和揣摩的意思,才能“樂在其中”。這樣意思就完整了——學習新的東西,能經常反覆地體味、揣摩並練習不是很快樂的事嗎?
問老師——向一切“有道”者請教,誰是老師?凡是能夠傳道解惑的人都是老師,誠如唐代韓愈所言:“無貴無賤,無長無幼,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問自己,即向自己質疑,問自己是否明白、是否信服。
我的這本拙作,是我經過“學”和“問”之後的心得,權做我向“社會大學”呈交的自修作業。這裡的偏陋、錯誤肯定不少,因此我十分懇切地希望我的“同學”和老師能夠“橫挑鼻子豎挑眼”,多加批評指正,讓我今後能做出更好一點的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