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山孩·鄭珍:人與詩》內容簡介:貴州建省晚,僻處西南一角,較少受先進地區、主流文化的青眼。在中國進入近代歷史的分娩陣痛期,貴州遵義出了一位被清詩學者譽為“清詩冠冕”的詩人兼經學大師鄭珍(字子尹)。鄭珍生性淡泊,人生願景是鄉居奉母、讀書著述,卻被貧窮逼著一再跨進八股考場;他與世無爭,戰亂卻弄得他家破人亡。他的詩猶如日記,是他生活歷程和心路歷程的實錄,是這個萬方多難的歷史時期的一部極其生動的詩史。田園、母親、讀書和友情,苦旅、游觀、民瘼和戰亂,在詩集中交織成一個強大的氣場。作者耗數年時間,寫成這部“人詩互證”、體裁獨特的詩傳,以表達對這位鄉先賢的心儀和敬慕。此系作者“貴州往事系列”的第三部(前兩部為《安順舊事:一種城記》和《物之物語》)。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子午山孩·鄭珍:人與詩》這部寫鄭珍的“詩傳”,讀了經他精心摘引、解讀的鄭詩,貴州這片曾經多災多難、邊鄙貧瘠的土地,變得於他親切起來,詩人鄭子尹的身影,也在他的親人、鄉鄰、摯友和學生之間,像浮雕一樣突現出來。
作者簡介
戴明賢,貴州安順人,生於1935年9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西泠印社社員。著有《安順舊事:一種城記》《物之物語》《掬藝錄》《黑白記》《石城引》《采蕨集》《戴明賢散文小說選》《戴明賢書印集》《水寨龍珠》《夜郎新傳》《諾德仲》等文學、書法、戲劇、影視等作品二十餘種。
媒體推薦
多年來,明賢兄不僅對貴州歷史文化的開掘與書寫,不遺餘力,而且每有新作,必要進行學術文體、敘述文體的自覺試驗,從《一個人的安順》,到《物之物語》,再到這部集編年、紀事、譯述、註解與評議為一體的復調文本《子午山孩:鄭珍人與詩》,一步一個台階,顯示了不竭的創造活力。
——錢理群
二十年來,讀到戴明賢默默地寫的好幾本書,例如關於安順,他如數家珍,我從他的筆下,真正感到了一個作家對家鄉熱土的感情,與對這片土地上的文化遺存和風土人情的熟悉是分不開的,也是做不得假的。戴明賢如此,一二百年前的鄭子尹也是如此。讀了戴明賢這部寫鄭珍的“詩傳”,讀了經他精心摘引、解讀的鄭詩,貴州這片曾經多災多難、邊鄙貧瘠的土地,變得於我親切起來,詩人鄭子尹的身影,也在他的親人、鄉鄰、摯友和學生之間,像浮雕一樣突現出來。
——邵燕祥
尼采說他只愛“用血寫成的書”,鄭珍的詩真正是用血寫成,具有極大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
——錢理群
二十年來,讀到戴明賢默默地寫的好幾本書,例如關於安順,他如數家珍,我從他的筆下,真正感到了一個作家對家鄉熱土的感情,與對這片土地上的文化遺存和風土人情的熟悉是分不開的,也是做不得假的。戴明賢如此,一二百年前的鄭子尹也是如此。讀了戴明賢這部寫鄭珍的“詩傳”,讀了經他精心摘引、解讀的鄭詩,貴州這片曾經多災多難、邊鄙貧瘠的土地,變得於我親切起來,詩人鄭子尹的身影,也在他的親人、鄉鄰、摯友和學生之間,像浮雕一樣突現出來。
——邵燕祥
尼采說他只愛“用血寫成的書”,鄭珍的詩真正是用血寫成,具有極大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
圖書目錄
自序 鄭珍家世
子午山孩
_鄭珍:人與詩
後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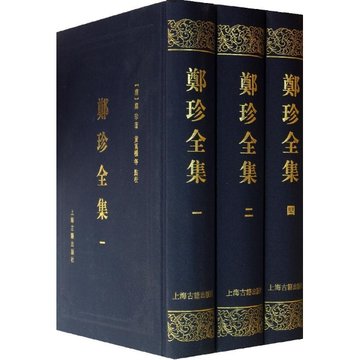
子午山孩
_鄭珍:人與詩
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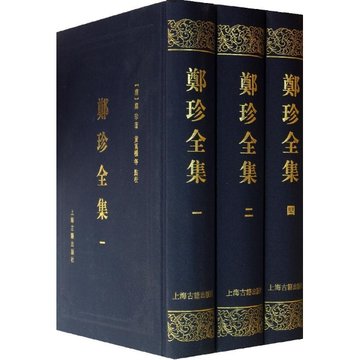
後記
鄭珍的《巢經巢集》,我小時候就從父親的書櫥里看得眼熟,但只記住了這個怪怪的書名,內容一句沒讀過。國中以後自己選詩讀了,多年裡只知道那些名聲顯赫的大詩人,其餘不屑一顧,很有點勢利眼。文化大革命鬧起來時,我已與四十位同仁一起,在此前的“四清”運動中,從供職的省廣播電台下放到大方縣百納中學教書,躲開了城市裡的紅色恐怖。學校經常停課,教師空閒很多,有的學中草醫,有的學剪裁縫紉,有的終日清談,各行其是。我知道寫小說不能碰了,就拾起了丟荒多年的兒時愛好:刻印臨帖;同時起意學做舊體詩詞,抱著杜甫和蘇東坡的五古七古惡補。一九七三年初回到貴陽,與春茗詞人陳恆安前輩恢復了聯繫,他看了我的兩首習作,欣慰於有人不忘此道,鼓勵了一番,並鄭重地說:我們貴州人學五七古有“不二法門”,就是巢經巢。不久,父執志齋吳曉耕先生從安順專程來貴陽探視臥病的先父,我陪他去省博看陳先生,兩位老詩人談得很開心。分別後互贈七律,陳詩說“別集共尊三不惑,漢亭惟仰一且同”,上句說的是他倆的老師楊覃生(詩文集名《三不惑集》),下旬即指鄭子尹(別號之一日且同亭長,且念居音)。於是我知道鄭詩非讀不可。
但那時找不到。連陳先生自己的一部,也在此前送給從蘇州回貴陽探親的老友謝孝思先生了。幾年後,“文革”結束了,文藝創作又合法了,我出差上海,在舊書店發現一部《巢經巢集》:中華書局聚珍版,小開本,連史紙精印四冊,品相極好,一時間心跳怦然,驚為艷遇。要問定價幾何?定價一元六角,合四毛錢一冊。攜去拜望陳先生,他愛不釋手,但我尋覓多年方得如願,也實在難以割捨。如今,我已藏有鄭集數種,包括珍貴的家刻本(五之堂主人舒奇峰君搜獲兩部,慨然分賜),而陳師謝世已近三十年了。
得了鄭詩,趕快補課。他是學者兼詩人,詩作風格多樣,其中典故多多的一類,我從白文本讀得雲山霧沼;另一類以白描手法寫鄉居生活的詩,則如話如畫,非常可愛。後來獲讀學者的注釋本,才把“生澀奧衍”的那一類詩,大致弄明白了,發現有很多是彌足珍貴的“詩史”。漸漸由詩及人,覺得與這位鄉前輩非常親近,種種情懷,感同身受。於是產生了寫他的念頭。最初試寫的兩段,錢理群兄見了,覺得這種寫法有趣,此後幾年,他每與杜應國兄通電話,總不忘讓應國向我問問進展,使我不好半途而廢。竟不妨說,這本小書有一半是他催出來的。
初稿拉出來,十分粗糙,很無自信。先後懇請摯友袁本良、王堯禮、楊宛、龔勤舟諸君分別認真審讀,除校對電腦誤植外,對複述不愜之處,也多有指導。堯禮正疵尤多。勤舟並為手繪鄭珍行旅地圖。在此稽首致謝。雖然如此,但鄭詩理解難度大,謬誤仍然難免,敬候高明指教。特別感謝詩人邵燕祥先生賜序。還要感謝責任編輯杜麗女士不棄這種逆時尚而動的文字,這本書已是她與我的第三次愉快合作了。 黔中戴明賢
2012年8月28日謹敘於適齋
但那時找不到。連陳先生自己的一部,也在此前送給從蘇州回貴陽探親的老友謝孝思先生了。幾年後,“文革”結束了,文藝創作又合法了,我出差上海,在舊書店發現一部《巢經巢集》:中華書局聚珍版,小開本,連史紙精印四冊,品相極好,一時間心跳怦然,驚為艷遇。要問定價幾何?定價一元六角,合四毛錢一冊。攜去拜望陳先生,他愛不釋手,但我尋覓多年方得如願,也實在難以割捨。如今,我已藏有鄭集數種,包括珍貴的家刻本(五之堂主人舒奇峰君搜獲兩部,慨然分賜),而陳師謝世已近三十年了。
得了鄭詩,趕快補課。他是學者兼詩人,詩作風格多樣,其中典故多多的一類,我從白文本讀得雲山霧沼;另一類以白描手法寫鄉居生活的詩,則如話如畫,非常可愛。後來獲讀學者的注釋本,才把“生澀奧衍”的那一類詩,大致弄明白了,發現有很多是彌足珍貴的“詩史”。漸漸由詩及人,覺得與這位鄉前輩非常親近,種種情懷,感同身受。於是產生了寫他的念頭。最初試寫的兩段,錢理群兄見了,覺得這種寫法有趣,此後幾年,他每與杜應國兄通電話,總不忘讓應國向我問問進展,使我不好半途而廢。竟不妨說,這本小書有一半是他催出來的。
初稿拉出來,十分粗糙,很無自信。先後懇請摯友袁本良、王堯禮、楊宛、龔勤舟諸君分別認真審讀,除校對電腦誤植外,對複述不愜之處,也多有指導。堯禮正疵尤多。勤舟並為手繪鄭珍行旅地圖。在此稽首致謝。雖然如此,但鄭詩理解難度大,謬誤仍然難免,敬候高明指教。特別感謝詩人邵燕祥先生賜序。還要感謝責任編輯杜麗女士不棄這種逆時尚而動的文字,這本書已是她與我的第三次愉快合作了。 黔中戴明賢
2012年8月28日謹敘於適齋
序言
一個詩人的存在和發現
邵燕祥
鄭珍,生卒於一八0六至一八六四年間,是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一代詩家,更是中國詩史上一個巨大的存在。然而這位生於偏遠的貴州山鄉,曾短期出任小官卻大半生窮愁潦倒的詩人,雖為鄉邦文獻所記載,也只獲少數文史鉅公給以青睞,而對於現代一般的新舊文學愛好者,他幾乎是從沒聽說過的陌生人。
這正像一顆行星,就其體量看是一個巨大的存在,然而高懸天邊,寂然悄然,泯然於眾星之間,等待著發現。
我之知有鄭子尹,是一九八二年一個偶然的機遇,來貴陽和遵義旁聽黎庶昌國際研討會,才了解到鄭子尹和莫友芝與黎庶昌同為“沙灘文化”的代表人物,但那一次除了弄清遵義市區子尹路命名的由來以外,於其人其詩仍是一無所知。
本書的作者戴明賢,據他在自序中說,對這位鄉先賢也是從懵然不知,經人點撥,在十年動亂中偷暇精讀,乃得成其知音。戴明賢對遙遠天際這顆詩星的發現,並著為此書,帶領我,也將啟發眾多今天與爾後的讀者感知這顆星的存在,接受這顆星光芒的牽引。
套一句熟語,如果子尹先生在地下或天上有知,也該會感謝戴明賢為他寫這卷“詩傳”的勞績。讓更多後人走近這位寂寞百年的詩人及其詩作,也讓這些心血澆溉的生命史、社會史不致湮沒於歲月塵沙。說來可憐,我剛打開書稿時,竟不知道鄭珍是鄭子尹的本名,子午山是他家鄉的山,別署“子午詩孩”則寄託著他對慈母的孺慕之情。待讀到最後一頁,這位陌生的詩人,已經成為我聲息相聞的近鄰,忘年相交的契友,可以月下同游,可以花前對飲,可以雨夜聯床,甚至是結伴奔波在逃難路上,可以互相傾訴共同的憂患與各自的悲歡,而不問是十九世紀還是二十一世紀了。
戴序中介紹了晚清以來諸家對鄭詩的崇高評價,皆是有所據而云然,並非溢美之詞。人們將他置於唐宋以來的大家、名家之間加以論列,多是從他與各家風格的異同來突出他的優長。這是學者之言。在像我這樣的詩歌愛好者,或多或少讀過一些傳統詩作,且各有偏好,自會根據自己的閱讀體會,有所欣賞,有所品鑑,不必拘泥於論者的排名,也可以說,讀詩,讀好詩快我胸襟,斯為得之,又豈在為詩人排座次哉!
不過,從接受心理來看,一個讀詩的人總有更容易引起共鳴的題材和風調。讀鄭子尹寫自己親歷的窮愁坎坷,寫周圍的民間疾苦,總使我想到杜甫、白居易以至皮日休,偶寫鄉居閒情,又使我想起儲光羲、范成大,而詩人主體,更使我想起黃仲則、龔自珍。然而這只是某些近似而已。鄭珍就是鄭珍。這部“詩傳”的好處,正在戴明賢創為“以人馭詩,以詩證人,因人及詩,人詩共見”的體例,避免了單純的傳記“見人不見詩”(往往需要另找詩集合參)和單純的詩集“見詩不見人”(往往需要另找有關詩人的史料),為讀者節省了翻檢之勞,也更利於知人論世~不但有助於讀者了解了歷史的大背景,而且交代了詩人的具體處境,乃知一詞一語,都自有心路歷程,不是無病呻吟了。
戴明賢這樣的寫法,也許不是學術論著的取徑,卻十分適合向一般讀者“普及”一位詩人詩作,猶如陪同遊客進入一條花徑,一片叢林,隨引隨行,即景指點,遠勝遙對著草木花樹,空泛地說花有多么香多么好看,樹為什麼有的曲有的直了。
我之知遠在貴州的戴明賢,比我之知鄭子尹早十來年;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拜讀了他寫的歷史小說《金縷曲》,心嚮往之。文革後的文學界不斷發現被不正常年代埋沒的人,也發現了戴明賢,《金縷曲》選載於《小說選刊》。後來1992年我在貴陽見到了他,這是我們締交之始,於今也有二十年了。二十年來,讀到他默默地寫的好幾本書,例如關於安順,他口數家珍,我從他的筆下,真正感到了一個作家對家鄉熱土的感情,與對這片土地上的文化遺存和風土人情的熟悉是分不開的,也是做不得假的。戴明賢如此,一二百年前的鄭子尹也是如此。讀了戴明賢這部寫鄭珍的“詩傳”,讀了經他精心摘引、解讀(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串講”,而是融入了自己的心會)的鄭詩,貴州這片曾經多災多難、邊鄙貧瘠的土地,變得於我親切起來,詩人鄭子尹的身影,也在他的親人、鄉鄰、摯友和學生之間,像浮雕一樣突現出來。
我相信,鄭珍——子尹先生和他的詩的巨大存在,一經這次的發現,將永遠不會被中國人忘記或忽略。
2012年12月25日
邵燕祥
鄭珍,生卒於一八0六至一八六四年間,是十九世紀上半葉的一代詩家,更是中國詩史上一個巨大的存在。然而這位生於偏遠的貴州山鄉,曾短期出任小官卻大半生窮愁潦倒的詩人,雖為鄉邦文獻所記載,也只獲少數文史鉅公給以青睞,而對於現代一般的新舊文學愛好者,他幾乎是從沒聽說過的陌生人。
這正像一顆行星,就其體量看是一個巨大的存在,然而高懸天邊,寂然悄然,泯然於眾星之間,等待著發現。
我之知有鄭子尹,是一九八二年一個偶然的機遇,來貴陽和遵義旁聽黎庶昌國際研討會,才了解到鄭子尹和莫友芝與黎庶昌同為“沙灘文化”的代表人物,但那一次除了弄清遵義市區子尹路命名的由來以外,於其人其詩仍是一無所知。
本書的作者戴明賢,據他在自序中說,對這位鄉先賢也是從懵然不知,經人點撥,在十年動亂中偷暇精讀,乃得成其知音。戴明賢對遙遠天際這顆詩星的發現,並著為此書,帶領我,也將啟發眾多今天與爾後的讀者感知這顆星的存在,接受這顆星光芒的牽引。
套一句熟語,如果子尹先生在地下或天上有知,也該會感謝戴明賢為他寫這卷“詩傳”的勞績。讓更多後人走近這位寂寞百年的詩人及其詩作,也讓這些心血澆溉的生命史、社會史不致湮沒於歲月塵沙。說來可憐,我剛打開書稿時,竟不知道鄭珍是鄭子尹的本名,子午山是他家鄉的山,別署“子午詩孩”則寄託著他對慈母的孺慕之情。待讀到最後一頁,這位陌生的詩人,已經成為我聲息相聞的近鄰,忘年相交的契友,可以月下同游,可以花前對飲,可以雨夜聯床,甚至是結伴奔波在逃難路上,可以互相傾訴共同的憂患與各自的悲歡,而不問是十九世紀還是二十一世紀了。
戴序中介紹了晚清以來諸家對鄭詩的崇高評價,皆是有所據而云然,並非溢美之詞。人們將他置於唐宋以來的大家、名家之間加以論列,多是從他與各家風格的異同來突出他的優長。這是學者之言。在像我這樣的詩歌愛好者,或多或少讀過一些傳統詩作,且各有偏好,自會根據自己的閱讀體會,有所欣賞,有所品鑑,不必拘泥於論者的排名,也可以說,讀詩,讀好詩快我胸襟,斯為得之,又豈在為詩人排座次哉!
不過,從接受心理來看,一個讀詩的人總有更容易引起共鳴的題材和風調。讀鄭子尹寫自己親歷的窮愁坎坷,寫周圍的民間疾苦,總使我想到杜甫、白居易以至皮日休,偶寫鄉居閒情,又使我想起儲光羲、范成大,而詩人主體,更使我想起黃仲則、龔自珍。然而這只是某些近似而已。鄭珍就是鄭珍。這部“詩傳”的好處,正在戴明賢創為“以人馭詩,以詩證人,因人及詩,人詩共見”的體例,避免了單純的傳記“見人不見詩”(往往需要另找詩集合參)和單純的詩集“見詩不見人”(往往需要另找有關詩人的史料),為讀者節省了翻檢之勞,也更利於知人論世~不但有助於讀者了解了歷史的大背景,而且交代了詩人的具體處境,乃知一詞一語,都自有心路歷程,不是無病呻吟了。
戴明賢這樣的寫法,也許不是學術論著的取徑,卻十分適合向一般讀者“普及”一位詩人詩作,猶如陪同遊客進入一條花徑,一片叢林,隨引隨行,即景指點,遠勝遙對著草木花樹,空泛地說花有多么香多么好看,樹為什麼有的曲有的直了。
我之知遠在貴州的戴明賢,比我之知鄭子尹早十來年;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拜讀了他寫的歷史小說《金縷曲》,心嚮往之。文革後的文學界不斷發現被不正常年代埋沒的人,也發現了戴明賢,《金縷曲》選載於《小說選刊》。後來1992年我在貴陽見到了他,這是我們締交之始,於今也有二十年了。二十年來,讀到他默默地寫的好幾本書,例如關於安順,他口數家珍,我從他的筆下,真正感到了一個作家對家鄉熱土的感情,與對這片土地上的文化遺存和風土人情的熟悉是分不開的,也是做不得假的。戴明賢如此,一二百年前的鄭子尹也是如此。讀了戴明賢這部寫鄭珍的“詩傳”,讀了經他精心摘引、解讀(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串講”,而是融入了自己的心會)的鄭詩,貴州這片曾經多災多難、邊鄙貧瘠的土地,變得於我親切起來,詩人鄭子尹的身影,也在他的親人、鄉鄰、摯友和學生之間,像浮雕一樣突現出來。
我相信,鄭珍——子尹先生和他的詩的巨大存在,一經這次的發現,將永遠不會被中國人忘記或忽略。
2012年1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