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歷
 埃德加·斯諾
埃德加·斯諾埃德加·斯諾1928年離開
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來到中國,在上海任《密勒氏
評論報》助理主編,以後又任《
芝加哥論壇報》、倫敦《
每日先驅報》駐東南亞記者。他踏遍中國大地進行採訪報導,“9·18”事變後曾訪問東北、上海戰線,發表報告通訊集《遠東戰線》。在上海,他見到了
宋慶齡和
魯迅,引發了他對記錄中國人民苦難與嚮往的中國新文藝的興趣,後來他對
蕭乾講,“魯迅是教我懂得中國的一把鑰匙”。他慶幸自己能在上海結識魯迅先生和宋慶齡女士,他是在他們的指引下認識中國的。
1932年聖誕節,斯諾與
海倫·福斯特·斯諾(Peg snow,即Helen Foster Snow,1907—1997)在東京美國駐日本使館舉行婚禮,後遊歷日本、東南亞、中國沿海一帶。1933年春天在
北平安家,住址在東城
盔甲廠胡同13號。1934年初,斯諾以美國《紐約日報》駐華記者身份應邀兼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為教書方便,他在
海淀鎮軍機處4號院購買了一處住宅,位置在現在
北京大學西南門一帶,坐西朝東,有一個黑色鐵柵欄門,這原是一位燕大出身的銀行家的房子,中西合壁式,寬敞的院子裡種有果樹、竹子,還有一座小型游泳池,位置就在現在北大西南門外的海淀路上。因為坐落在海淀台地之上,可以遠眺頤和園和西山風景。斯諾和夫人非常喜歡
燕京大學的美麗風光,說:“它的一部分占了
圓明園的舊址,保持了原來的景色,包括花園一般的校園中心那個可愛的小湖(即
未名湖)。”
斯諾熱愛中國,熱愛
海淀。他努力學習中文,還請了一位
滿族老先生指導,他認為“海淀的居民成分複雜,但他們都操優美的北京話,因此,這裡是外國人學講中國話最理想的地方”。來北平之前,他就接受
魯迅先生的建議,編選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活的中國》,想通過小說來向西方揭示中國的現實。到燕大後,他又請在新聞系讀書的蕭乾和英文系學生楊繽(剛)一起進行編譯。他在編者序言中認為中國的新文藝運動既不是鑽象牙之塔,也不是茶餘飯後的消遣,而是同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同人民為民主與自由的鬥爭分不開的。1936年此書出版。
抗戰
1937年7月7日,
七七事變爆發,斯諾在北平
南苑目睹了中日戰爭的開端。他在參加日軍召開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大聲質問:“為什麼要在中國領土上進行軍事演習?為什麼藉口士兵失蹤動用大兵?為什麼侵略者不撤兵回營,反叫中國守軍撤出宛平?”斯諾這一連串的問題,問得日軍新聞發言人狼狽不堪,無法正面回答,只得倉促宣布記者招待會結束。
 圖書封面
圖書封面9月末,斯諾在上海目睹了八一三事件。在報導中,斯諾稱讚這場戰爭是“偉大的表演”,中國人所表現出來的勇敢和軍事技能,是許多人所沒有料想到的。
接著,斯諾沿著日軍在中國的侵略戰線,橫越中國國土,去了漢口、
重慶、
西安,並再一次去
延安,撰寫了一系列的新聞報導。在
漢口,他為中國工業所遭到的破壞而痛心:“最令人氣餒的是中國在各處所犯的同樣的錯誤,那就是沒有把工業企業和有技術的工人加以改組和撤退,而在放棄南京、漢口兩座戰略城市之前,又沒有作出巨大的努力使兩個城市不致變成敵人的戰爭基地。日本利用了掠得的資源和工廠,把侵略更深一步向內地推進。”
他驚異地發現:儘管日本人取得了所有重大戰役的勝利,但從來沒有贏得一項政治決定,從來沒有能夠勝利地結束這場戰爭。任何甘心承認失敗的人,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對,人們不承認他的權威。
汪精衛叛國投敵,成了南京傀儡政府的首腦,人民就唾棄他,他的影響也就消失了。如果
蔣介石投降,也會發生同樣的情況。
他稱讚
新四軍:最大資產,也許就是他的革命傳統,那就是有組織方法,百折不撓的精神以及戰鬥的戰術。他誇獎八路軍:已經成為一種英勇的傳說,這傳說在它萬次戰鬥的記錄中,象徵著每一個作戰的人都必須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戰鬥的品質:忍耐、敏捷、勇敢、指揮的天才、不屈不撓以及——也許最重要的——精神的不可戰勝。所有這些結論,都顯示了斯諾作為一個進步新聞記者敏銳的洞察力。都被收入他在1941年出版的《為亞洲而戰》一書中。
革命
斯諾是一個正直的美國人,愛好和平,主持正義,他十分關切中國的命運,熱情支持和保護學生的愛國熱情。1935年6月,斯諾又被聘為英國《每日先驅報》特派記者,不久即搬回東城盔甲廠13號居住。
 埃德加·斯諾
埃德加·斯諾當時正是
一二·九運動前夕,燕京大學是中共領導學生運動的重要陣地,斯諾積極參加燕大新聞學會的活動,他們家也是許多愛國進步學生常去的場所,
燕京大學的王汝海(黃華)、
陳翰伯,
清華大學的姚克廣(姚依林),
北京大學的俞啟威(
黃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地下黨員們在斯諾家裡商量了“
一二·九”運動的具體步驟,並把(1935年)12月9日、16日兩次大遊行的路線、集合地點都告知斯諾夫婦。遊行前夕,斯諾夫婦把《平津10校學生自治會為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連夜譯成英文,分送駐北平外國記者,請他們往國外發電訊,並聯繫駐平津的許多外國記者屆時前往採訪。
斯諾夫婦則在遊行當日和其他外國記者跟著遊行隊伍,認真報導了學生圍攻西直門、受阻宣武門的真實情況。他給紐約《太陽報》發出了獨家通訊,在這家報紙上留下了有關“一二·九”運動的大量文字資料和照片。斯諾還建議燕大學生自治會舉行過一次外國記者招待會,學生們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
北平淪陷後,斯諾在自己的住所里掩護過不少進步學生,幫助他們撤離北平死城,參加抗日游擊隊或奔赴延安。
西行漫記
1936年6月,在宋慶齡的安排下,斯諾首次訪問了
陝甘寧邊區,拜訪了許多中共領導人。在延安,他曾將親眼見到的
一二·九運動實況講給
毛澤東同志聽。
 斯諾採訪毛澤東
斯諾採訪毛澤東10月末,斯諾回到北平之後即發表了大量通訊報導,還熱情向北大、清華、燕大的青年學生介紹陝北見聞。1937年3月5日和22日借燕大新聞學會、歷史學會開會之機,在
臨湖軒放映他拍攝的反映蘇區生活的影片、幻燈片,展示照片,讓國統區青年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
彭德懷等紅軍領袖的形象,看到了“紅旗下的中國”。
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斯諾完成了《西行漫記》的寫作。10月《
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在英國倫敦公開出版,在中外進步讀者中引起極大轟動。1938年2月,中譯本又在上海出版,讓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真正形象。
為了取得更詳盡的第一手人物資料,斯諾夫人海倫·斯諾於1937年4月衝破國民黨憲兵、特務的阻撓,經西安、
雲陽到延安訪問,採訪了大量的八路軍和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寫出了《紅區內幕》(《續西行漫記》)、《
中共雜記》等書。
 埃德加·斯諾
埃德加·斯諾1939年,斯諾再赴延安訪問。
斯諾1928年初到上海時曾給自己起了一個漢文名字:施樂,並一直使用。後來,
胡愈之先生等翻譯《西行漫記》一書時,因不知他還有過這樣一個漢文名字,而譯作“斯諾”二字,並一直沿用下來。
援助
幫助他人
七七事變後,日本侵略軍占領了北平。日軍大肆搜捕、迫害中國的抗日愛國人士和革命青年。當時,斯諾參加了在北平的外國人(歐美)援華社會團體,積極掩護和幫助中國的愛國者,使他們免遭日軍捕殺,他的公寓成了抗日愛國分子的避難所,斯諾熱情地幫助這些避難者化裝成乞丐、苦力和小販逃出北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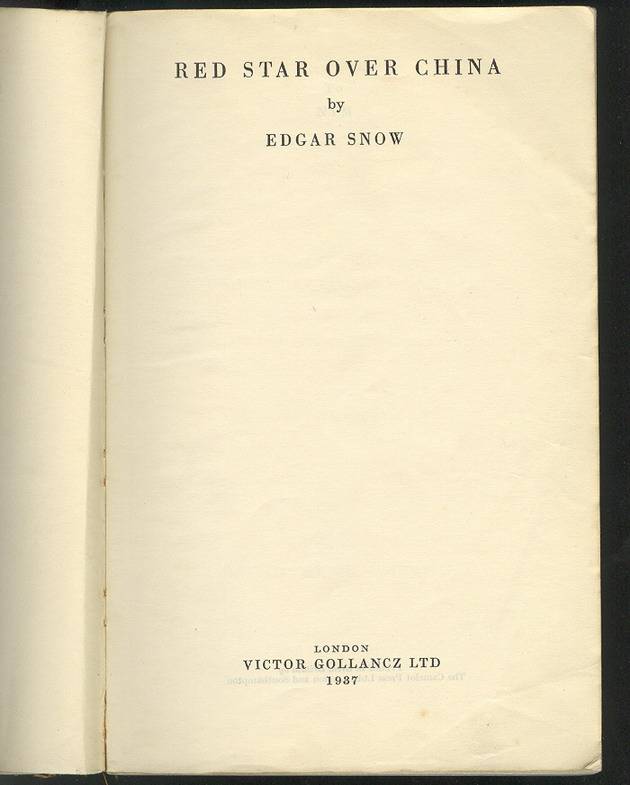 《西行漫記》
《西行漫記》斯諾家中還存放著一些中國人暫存的財物,從私人汽車到游擊隊從日本人手裡奪回的黃金、珠寶和玉器。有一次,西山的抗日游擊隊派了一位聯絡員來找斯諾,請他幫助變賣從日軍手中奪回的珠寶、黃金,以解決游擊隊急需購買槍枝彈藥的經費,並提出給斯諾高額的回扣。斯諾說:“我一分錢也不要。但是我建議,你們把在西山一個修道院扣留的幾名義大利修道士釋放了。”他對游擊隊員說:“這樣做不好,會損害你們的抗日事業,不能獲得國際上的同情。”“我是為中國著想。”斯諾說:“一次只能同一個敵人作戰,不宜樹敵太多。”
接受建議
游擊隊接受了斯諾的建議,釋放了那幾個義大利修道士,斯諾也找到了肯幫忙的人幫助游擊隊把珠寶、黃金變賣了出去。
在斯諾家花園的地下,愛國學生埋藏了許多被日軍查禁的進步書刊。斯諾甚至還同意在他家中設定了一部秘密電台,斯諾除了忙於新聞採訪,報導中日戰況,每天還要為眾多的避難者的吃飯問題奔忙。
當時,西方各國在中日戰爭中保持中立,日本占領軍對在北平的歐美等國的人士還沒有敢公然侵犯。斯諾說:“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種地下工作總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個‘中立者’了。”
掩護脫險
斯諾掩護
鄧穎超從北平脫險,頗有些傳奇色彩。七七事變時,鄧穎超正在北平治病,為了儘快離開戰亂地區,鄧穎超在愛潑斯坦的幫助下找到了斯諾,請斯諾設法帶她出去。為了應付沿途日軍盤查,鄧穎超化裝成斯諾的“保姆”。和斯諾一起乘火車離開北平。列車到達天津站,日軍在月台檢查所有的中國旅客,凡是他們認為可疑的,都會被抓走。“我是美國人,美國記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斯諾對日本檢察員說。日本檢察員揮手放斯諾他們出站。到達天津之後,斯諾把鄧穎超託付給自己的一位好友、紐西蘭記者吉姆·伯特倫,請他把鄧穎超帶過封鎖線。令人驚奇的是,斯諾當時並不知道所幫助的人是鄧穎超。實際上,斯諾幫助中國人已經是習以為常的事。
交往蕭乾
1928年,斯諾懷揣母校美國
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教務長的介紹信來到中國上海,成為英文周刊《密勒氏評論報》主編鮑威爾的助手,後又任《芝加哥論壇報》和“統一報業協會”的駐東南亞記者,從此便與中國結下不解之緣。
1933年至1935年,斯諾在燕京大學新聞系開了“特寫的寫作”課,此時
蕭乾剛從輔仁大學西語系轉到燕大新聞系,成為他班上的學生。
結識
課餘時間,蕭乾協助美國青年安瀾編輯《中國簡報》,這是一份介紹現代中國文藝界動態及社會大眾之趨向和背景的英文周刊。斯諾看到了蕭乾為《中國簡報》所寫的有關中國新文藝的介紹。此時的斯諾,通過與魯迅和宋慶齡等人的接觸,對中國新文藝運動有了初步認識。想把中國“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介紹給西方讀者。在姚莘農(姚克)的協助下,他把魯迅自選的7篇小說譯成英文,作為英文版《活的中國》的第一部分,又邀蕭乾等人將
茅盾、
丁玲、
柔石、
巴金、
沈從文、
林語堂、
郁達夫、
張天翼、
郭沫若等人的作品譯後作為第二部分收入書中,其中還有斯諾點名要的蕭乾自己的作品《皈依》。譯文發表後,斯諾曾將滿滿一信封的鈔票塞給蕭乾,說是他應得的稿費。蕭乾說,通過斯諾的加工潤色,他所學到的遠遠超出他付出的勞動,堅決不肯收。
 青年蕭乾
青年蕭乾1935年7月蕭乾畢業時,斯諾夫婦送給他一皮箱英文書,可惜焚毀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的侵華戰爭中。
當年,斯諾的足跡遍及中國大江南北,通過大量通訊報導,反映中國民生凋敝的現狀,向世界報導中國人民反抗外來侵略的鬥爭。
“九一八”事變後,他赴東北採訪。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上海,他又在現場目睹了上海4萬多工人舉行的反日大罷工,支援
十九路軍對日作戰。在題為《遠東戰線》的報告通訊集中,斯諾揭露了日本“不宣而戰”的事實真相。
1935年在“一二·九”運動爆發當天,斯諾聯絡了好幾個國家的記者到示威現場採訪。他和夫人海倫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的橫幅標語之下。那時蕭乾在天津《
大公報》工作,從當晚的新聞電訊稿中獲悉遊行的壯舉以及學生被毆打受傷一事,次日趕回北平,陪斯諾夫婦走訪幾家醫院,慰問被打傷的同學。當年6月,斯諾被聘為英國《每日先驅報》的特派記者,但仍在燕大兼課,積極從事燕大新聞學會的活動。由於以斯諾夫婦為首的眾多中外記者的努力,“一二·九”運動的訊息很快傳播到全世界。
採訪
1936年6月,蕭乾採訪了在南京擔任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的
馮玉祥將軍。豈料報導見報時,新聞檢察官把蕭乾所寫的訪問記中關於譴責日本關東軍的侵略暴行和對“一二·九”學生運動讚揚的內容統統砍掉了。蕭乾將此事告知正在上海的斯諾,斯諾立即讓蕭乾寫封介紹信,他立刻去會見馮玉祥將軍。不久,上海一家英文報紙就刊登了東京政府向南京政府強烈抗議的訊息,指責馮玉祥向美國記者斯諾發表了對日本不友好的言論。
重逢
1939年,蕭乾赴英國
倫敦大學東方學院執教,兼《大公報》駐英記者,斯諾則在中國工作到1941年2月。
1944年8月15日巴黎解放。入秋,攜帶著美軍隨軍記者證的蕭乾,在巴黎的斯克里勃旅館走廊里偶然遇見了斯諾。蕭乾正要隨美國第七軍向萊茵挺進,斯諾則是蘇聯準許在東線採訪的6位美國記者之一。那一次他是特意從羅馬尼亞趕到巴黎來觀光的。舊友重逢,他們在酒吧間海闊天空地聊了一個下午。斯諾告訴蕭乾,《皈依》備受美國讀者的重視,因為它反映了東西方文化的衝突。他深情地說:“中國是我的第二故鄉,魯迅是教我懂得中國的一把鑰匙。”當蕭乾問起海倫的近況時,斯諾沒有正面回答,蕭乾隱約感到這對夫婦的感情可能出了問題。他有些替海倫抱屈。他說,海倫刻意讓斯諾在旅華的洋人中穿得最考究,為斯諾不知操了多少心,而斯諾只顧工作,完全不在乎吃穿。
 蕭乾小說《皈依》
蕭乾小說《皈依》敬重
1993年4月,蕭乾在家中接待中美合拍《斯諾》影片的攝製組,講述他與斯諾的交往。但此片終因資金短缺而擱淺。
蕭乾在與斯諾的交往中,對他善於觀察,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洞察力欽佩不已。1936年,斯諾在《星期六郵報》上預言:“日本不久要招來一場行將震撼全世界的抵抗。”1944年4月9日,他又在該報上預言,
殖民主義必將滅亡。
從斯諾身上蕭乾學到了作為新聞記者的優秀品質:揭露邪惡,反對橫暴,扶持正義,捍衛真理;到民眾中,了解他們擁護什麼,反對什麼;嚮往什麼,憎恨什麼。
友誼
訪問
1941年,斯諾回到美國後,仍然向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宣傳中國的抗日戰爭。他說:“我依然贊成中國的事業,從根本上說,真理、公正和正義屬於中國人民的事業,我贊成任何有助於中國人民自己幫助自己的措施,因為只有採用這種方法,才能使他們自己解救自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斯諾對中國進行了三次長期訪問。這在美國政府對新生的中國實行孤立政策和武裝支持台灣
蔣介石的年代裡,對一名美國人來說,真是一件獨一無二的事。1960年,斯諾訪問北京,他意識到中國領導人希望他的到來,可能有助於建立起一座中美兩國的友誼橋樑,他表示:“前途是艱險的,但橋樑能夠架起,而且最後必將架起。”
支持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他和
路易·艾黎等人在
宋慶齡的支持下,發起了工業合作運動。從內蒙到雲南,開辦了2300所小工廠,為後方生產紡織品和日用品,為前方製造手榴彈,緩解了戰時物資的短缺和失業問題。
斯諾回美國後,3次到白宮去見
羅斯福總統。每一次會晤,他都強調美國應力促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共同抗擊侵略者,攜手建設新中國。
解凍
1971年,美國桌球隊出乎意外的被邀請訪問北京,中美關係解凍,美國《
生活》雜誌抓住時機發表了斯諾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斯諾透露了中國領導人毛澤東曾告訴他的話:如果
理察·尼克森訪問中國,無論是以旅遊者的身份還是以總統的身份都會受到歡迎。這篇文章是斯諾的最後一篇“獨家內幕新聞”。就在尼克森開始前往北京的同一個星期,斯諾死於癌症。
 斯諾與毛澤東
斯諾與毛澤東中國情結
迫害
抗戰爆發後,海倫去上海和報導
淞滬抗戰的斯諾會合,並與
路易·艾黎中外進步人士發起開展中國工業合作運動,支持中國抗戰。1941年,斯諾接受《紐約先驅論壇報》的任務,去東南亞和印度採訪,離開了中國。
新中國成立後,斯諾先生在美國遭受
麥卡錫主義的迫害,行動不自由。1959年,舉家移居瑞士日內瓦,但他仍然關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1960年6月,他終於來到北京,見到了毛澤東等領導人。他來到北京大學(1952年院系調整時,北大搬到了未名湖畔原燕京大學的校址),會見了師生和當年友人,訪問進行了5個月。1963年出版的《大洋彼岸》一書中指出:“從前最重要的是
國立北京大學,在那裡,培養了共產黨最重要的創造者,到如今,北大還是雄心勃勃的藝術和科學系學生以及畢業的研究人員嚮往的地方”。
重返
1970年秋天,斯諾和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諾又一起來到中國,並於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和毛澤東親切交談,
毛澤東高度評價他:“我沒有變,你也沒有變”。隨後,斯諾發表了《我同毛澤東談了話》、《周恩來的談話》等文章。在京期間,他和夫人又重返燕園。洛伊斯後來回憶說:“我們在一個略為發灰的淺紅色的亭子(指
慈濟寺山門)邊停了下來,眼光穿過它的拱頂,凝視陽光下碧波蕩漾的一片湖面。在我們身後,拾幾步石階向上的那塊稍為高起的地方,有一片蔓草叢生的空地,四周松樹圍繞,遮住了我們的視線……”
逝世
1972年2月15日,斯諾在瑞士
日內瓦因患癌症病逝。病重期間,斯諾留下遺囑:“我愛中國,我願在死後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裡,就像我活著時那樣……”遵照斯諾的遺囑,經中國政府同意,1973年10月19日,斯諾一部分骨灰的安葬儀式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舉行。墓基座為長方形未經雕磨的青色岩石,上邊橫臥漢白玉墓碑一方,臨時用黑色膠紙貼著楷書:“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碑前放著毛澤東送的花圈,緞帶上寫著:“獻給埃德加·斯諾先生”,宋慶齡、
朱德、周恩來也送了花圈,黨和國家領導人
周恩來、
李富春、
郭沫若、
鄧穎超、
廖承志、
康克清以及北大師生代表參加了安葬儀式。洛伊斯攜女兒茜安·斯諾出席儀式,她感謝中國政府和人民,說:“我丈夫在他遺言中表達了他對中國的熱愛,並表示了他生前一部分身心常在中國,希望死後也將他的一部分遺體安放在新中國的古老的土地下,安放在中國的新人中間,在這裡,對人類的尊重達到了新的高度,在這裡,世界的希望發射著新的光芒。”
 埃德加斯諾墓
埃德加斯諾墓安葬
斯諾的另外一部分骨灰安葬在美國
赫德森河畔一位朋友家的花園中。
1977年12月13日,
葉劍英同志為斯諾墓親筆題寫了碑名:“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後被鎏金鐫刻在墓碑之上。
家庭
斯諾先後結過兩次婚,第一任妻子是海倫·斯諾,兩人於1932年結婚,1949年5月分手,兩人之間沒有子女,之後海倫一直沿用斯諾的姓氏(
海倫·福斯特·斯諾)並住在斯諾購置的在美國康乃狄克州
麥迪遜鎮一棟建於1752年的農舍里,而且沒有再婚。在尼克森總統訪華後,她於1972年末和1978年兩次再訪中國。80年代兩次獲
諾貝爾和平獎提名。1996年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授予海倫“人民友好使者”的榮譽證書和證章。1997年1月,海倫去世。
斯諾與海倫離婚後,與美國女演員洛伊斯·惠勒結婚,婚後生有一對兒女
克里斯托弗和茜安·斯諾。
紀念
為了緬懷中國人民三位親密的朋友——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埃德加·斯諾(即3S,因三人英文名字第一個字母均為S,故名),我國原郵電部於1985年6月25日發行一套《中國人民之友》紀念郵票3枚,其中第三枚80分的郵票就是埃德加·斯諾。這枚郵票圖案上的埃德加·斯諾的形象,那凝視而深思的目光,緊閉的雙唇,既表現出他具有果斷、幹練而富於洞察力的性格特點,也揭示出了一個新聞記者為真理獻身的精神,值得中國人民的尊敬。
 《中國人民之友》紀念郵票 1985年
《中國人民之友》紀念郵票 1985年2009年9月14日,他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之一。
《
西行漫記》的作者埃德加·斯諾於1905年出生在美國
密蘇里州堪薩斯市,是家中三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他父親開了一家小印刷廠,家裡過著小康生活。父親要他也從印刷業開始自己的生涯。但他卻走上了一條與父親截然不同的道路,成為世界著名的記者。
著名作品
 埃德加·斯諾
埃德加·斯諾 圖書封面
圖書封面 埃德加·斯諾
埃德加·斯諾 埃德加·斯諾
埃德加·斯諾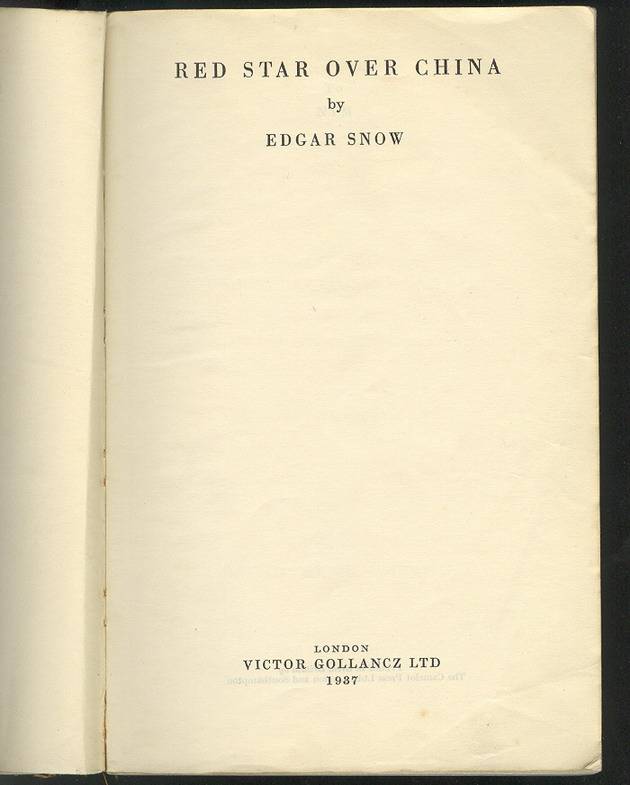 《西行漫記》
《西行漫記》 青年蕭乾
青年蕭乾 蕭乾小說《皈依》
蕭乾小說《皈依》 斯諾與毛澤東
斯諾與毛澤東 埃德加斯諾墓
埃德加斯諾墓 《中國人民之友》紀念郵票 1985年
《中國人民之友》紀念郵票 1985年
 斯諾採訪毛澤東
斯諾採訪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