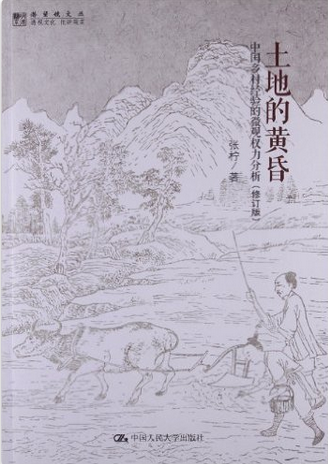《土地的黃昏:中國鄉村經驗的微觀權力分析(修訂版)》是2013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張檸。本書是《明德書系·潛望鏡文叢》之一。本書結合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哲學等研究方法,對中國鄉土文化結構、鄉村經驗及其微觀權力形態進行了全面分析,通過對時間、空間、器物、實踐的符號分析,細膩地敘述了巨觀權力結構在鄉村經驗各個層面的相互轉化過程。通過對鄉土社會的“事實呈現”,該書進一步將分析引向農民心理學、鄉土哲學和精神現象學領域,可視為一部鄉土文化“小百科”。該書將理論邏輯融會於文學敘述之中,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基本介紹
- 書名:土地的黃昏:中國鄉村經驗的微觀權力分析(修訂版)
- 作者:張檸
- ISBN:7300171834, 9787300171838
- 頁數:316頁
- 定價:55.00元
-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3年4月1日
- 裝幀:平裝
- 開本:16開
- 語種:簡體中文
作者簡介,內容簡介,目錄,文摘,
作者簡介
張檸,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當代新詩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學術領域為20世紀中國文學經驗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史、文化理論與文化批評等,著有《敘事的智慧》、《文化的病症》、《沒有烏托邦的言辭》《想像的衰變》、《再造文學巴別塔》、《白堊紀文學備忘錄》、《中國現代文學六家——文學觀念史研究》等。
內容簡介
這是一本文化研究中國化的實驗性著作。作者結合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哲學等研究方法,對中國鄉土文化結構、鄉村經驗及其微觀權力形態進行了全面分析,通過對時間、空間、器物、實踐的符號分析,細膩地敘述了巨觀權力結構在鄉村經驗各個層面的相互轉化過程。通過對鄉土社會的“事實呈現”,該書進一步將分析引向農民心理學、鄉土哲學和精神現象學領域,可視為一部鄉土文化“小百科”。本書將理論邏輯融會於文學敘述之中,具有很強的可讀性。
目錄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鄉村時間
第一節生態時間和結構時間
第二節時間經驗中的皈依和救贖
第三節數位化和鄉村時間的語義
第四節時間財富化和經驗的斷裂
第三章 鄉村空間
第一節地理空間和血緣空間
第二節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
第三節神聖空間和世俗空間
第四節空間的死寂和再生產
第四章 鄉村器物之一:家具
第三節神聖空間和世俗空間
第四節空間的死寂和再生產
第四章 鄉村器物之一:家具
第一節鄉村器物與身體能量
第二節家庭器物的分類
第三節家庭器物的功能
第四節家庭器物的現代化
附錄:移動的器物
第五章 鄉村器物之二:農具
第一節農具與農民的能量耗費
第二節農具的物理和心理慣性
第三節現代符號價值中的農具
第四節農具與身體管理和肉體記憶
第六章 農民和食物
第三節家庭器物的功能
第四節家庭器物的現代化
附錄:移動的器物
第五章 鄉村器物之二:農具
第一節農具與農民的能量耗費
第二節農具的物理和心理慣性
第三節現代符號價值中的農具
第四節農具與身體管理和肉體記憶
第六章 農民和食物
第一節能量的攝入和支出
第二節勞動方式和腸胃習慣
第二節勞動方式和腸胃習慣
第三節農民和主食強迫症
第四節綠色土地和黑色食品
第五節食物研究者的盲視
附錄:農民與服裝
第七章 鄉村的玩具和遊戲
第一節鄉村的遊戲
第二節鄉村玩具的特性
第三節遊戲與鄉土意象
第四節遊戲和玩具的世俗功能
第四節綠色土地和黑色食品
第五節食物研究者的盲視
附錄:農民與服裝
第七章 鄉村的玩具和遊戲
第一節鄉村的遊戲
第二節鄉村玩具的特性
第三節遊戲與鄉土意象
第四節遊戲和玩具的世俗功能
第五節超越現實原則的遊戲
第八章 巨觀權力和農民的自由
第一節族長和“卡里斯瑪”
第二節鄉村秩序的坐標
第三節權力鏈條中的農民
第九章 鄉村變態人格的誕生
第一節 柔情似水的文化壓抑
第二節農婦人格畸變的類型
第三節家庭內部的權力之爭
第四節農夫的抵抗和多重人格
第五節手工業學徒的變態心理
附錄:傻女婿故事的原型意義
第十章 陌生人社會:熟人社會的鏡像
第一節陌生人及其簡明分類
第二節血緣性永久介入的陌生人
第三節明顯的行為介入的陌生人
第四節明顯的非介入性陌生人
第五節潛在陌生人與日常經驗介入
第六節潛在陌生人與神秘經驗介入
第十一章 鄉村的婚姻、生育和性愛
第一節鄉土婚姻的異端
第二節妻與妾和性別政治
第三節子嗣文化中的婚姻和性愛
第十二章 鄉村的勞動分化和職業歧視
第一節手工業和重農學派
第二節農耕生產之外的職業
第三節輔助農耕的次等職業
第四節否定農耕的地下職業
第十三章 鄉村生活中的兒童經驗
第一節鄉村兒童的形象
第二節鄉村兒童的名號
第三節兒童的勞動和學習
第四節兒童記憶中的節日
附錄:逃離鄉村的夢想
第十四章 農民的姿態、表情和聲音
第一節日常生活中的農民
第二節農民的表情分析
第三節鄉村的聲音系統分析
附錄:記一位民間歌手
第十五章 中國詩歌中的農耕精神
第一節古詩的節奏及其精神秘密
第二節古典詩意和農耕經驗
第三節新的詩意的發生學問題
第四節現代詩歌中的農耕情結
第十六章 中國小說中的鄉土經驗
第一節敘事作品中的家族:崩潰或重構
第二節啟蒙運動中的“鄉土文學”
第三節當代鄉村文化破碎的寓言
主要參考書目
關鍵字索引
第八章 巨觀權力和農民的自由
第一節族長和“卡里斯瑪”
第二節鄉村秩序的坐標
第三節權力鏈條中的農民
第九章 鄉村變態人格的誕生
第一節 柔情似水的文化壓抑
第二節農婦人格畸變的類型
第三節家庭內部的權力之爭
第四節農夫的抵抗和多重人格
第五節手工業學徒的變態心理
附錄:傻女婿故事的原型意義
第十章 陌生人社會:熟人社會的鏡像
第一節陌生人及其簡明分類
第二節血緣性永久介入的陌生人
第三節明顯的行為介入的陌生人
第四節明顯的非介入性陌生人
第五節潛在陌生人與日常經驗介入
第六節潛在陌生人與神秘經驗介入
第十一章 鄉村的婚姻、生育和性愛
第一節鄉土婚姻的異端
第二節妻與妾和性別政治
第三節子嗣文化中的婚姻和性愛
第十二章 鄉村的勞動分化和職業歧視
第一節手工業和重農學派
第二節農耕生產之外的職業
第三節輔助農耕的次等職業
第四節否定農耕的地下職業
第十三章 鄉村生活中的兒童經驗
第一節鄉村兒童的形象
第二節鄉村兒童的名號
第三節兒童的勞動和學習
第四節兒童記憶中的節日
附錄:逃離鄉村的夢想
第十四章 農民的姿態、表情和聲音
第一節日常生活中的農民
第二節農民的表情分析
第三節鄉村的聲音系統分析
附錄:記一位民間歌手
第十五章 中國詩歌中的農耕精神
第一節古詩的節奏及其精神秘密
第二節古典詩意和農耕經驗
第三節新的詩意的發生學問題
第四節現代詩歌中的農耕情結
第十六章 中國小說中的鄉土經驗
第一節敘事作品中的家族:崩潰或重構
第二節啟蒙運動中的“鄉土文學”
第三節當代鄉村文化破碎的寓言
主要參考書目
關鍵字索引
初版後記
修訂版後記
選摘
選摘
文摘
第一章 緒論
1
天色已黃昏。大地的輪廓消失了。黃昏是“明”與“暗”、“生”與“死”、“動”與“靜”的交界處。越過這個界限,一切可見的“動”都變成了“靜”。大地上的一切事物,都以一種仿佛“死寂”的形式在悄然生長。土地沉睡了,但它的分子和元素還在悄悄地行動,塵土的微粒和草葉的根莖都在喃喃自語。農民也沉睡了,但他們的夢還沒有睡,夢在召喚稻穀和子嗣的種子。黃昏之後的土地和生物,在一種可見的“靜”和不可見的“動”中運動。這是一種看不見但能夠感受到的生生不息的動和靜。這是一種來自土地的經驗,是感官和土地元素融為一體的經驗。按照這種經驗,黎明和白天,就是在用“動”的形式表現靜;黃昏和暗夜,就是在用“靜”的形式表現動。這就是“動靜合一”、“天人合一”、“生死一如”的價值觀念的自然基礎。靜是動的極端形式,就像動是靜的極端形式一樣。自然和天道的運行,明暗交替和四季循環的過程,並不是給明和暗、動和靜劃界,恰恰是在模糊它們的界限。農民對這種邊界模糊的明暗和動靜的體驗,與自然運行的天道是合而為一的。這種體驗或經驗的中斷,也就是體驗者與土地的關聯或與自然的關聯的中斷。
真正將“明”與“暗”、“動”與“靜”截然分開和對立的,不是自然,而是人工;不是土地和農民,而是城鎮和市民;不是感性,而是智性。城鎮徹夜不滅的燈光,在昏暗的大地上劃出了一道道虛無的邊界。在那個由燈光和鐘錶的嘀嗒聲劃定的邊界之內,我們看到一個顛倒了的世界在靜穆的世界之中狂歡不已。這個喧鬧不已的世界原本是不存在的,它是土地和農民文化中的另一極,也是被“生產價值”所抑制的一極,它只存在於農民想像的“魑魅魍魎世界”之中。現在,它“真實”地出現在土地上和農民的面前,充滿了誘惑,猶如向他們頻頻招手的“欲望”,仿佛要將他們從土地中連根拔起。毫無疑問,這個人為世界的邊界正在不斷擴大,以至於土地和農民的邊界越來越小,“生產”的邊界越來越小,“勞動價值”變得越來越成問題。城市以一種人為的方式消除了黃昏的景觀,改寫了黃昏的經驗,它沒有黃昏。在一個被城市經驗和城市價值支配的世界和時代,真正的“黃昏經驗”,或者說與之相關的土地經驗、鄉村經驗、農民經驗正在迅速消失。這就是我所說的“土地的黃昏”。無論人們為此找到什麼樣的理由(自然的理由、社會的理由),如果不說它是悲劇性的,那么至少也是無奈的。
2
獵人、漁民、牧民、農民,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居民。這種居民身份,與其說是社會分工的結果,不如說是自然分工的結果。獵人,就是及時將動物殺死的人。牧人,就是對動物執行“死緩”的人。最初的“農民”甚至就是茹毛飲血的野蠻人(也就是最初的獵人)。學會種地是文明開化史上的一個重大進步。中國農民開化得比較早,他們也最能與動物和睦相處。進入開化初期的農業社會,分工也十分細緻。先秦典籍《周禮》中記載的職業分類極其複雜,殺豬宰羊剖魚都有專人負責,負責釀酒的官叫“酒人”,負責制飲料的官叫“漿人”,負責製冷飲的官叫“凌人”。還有製造車輛的“輪人”、“輿人”,冶金鑄造的“冶氏”、“築氏”,製造兵器的“弓人”、“矢人”,等等。《考工記》中的原始手工業的“百工”(大約30種職業),作為國家管理系統的六大職業(六大職業是:坐而論道的“王公”;作而行之的“士大夫”;整治五材、製造器具的“百工”;使四方貨物流通的“商旅”;通過身體的勞動使土地生財的“農夫”;治理絲麻、紡紗織布的“婦功”(後面兩種就是所謂的“男耕女織”)。見《周禮·冬官考工記第六》)中的一種,也排在農夫前面。農夫不過是“飭力以長地財”的人(我稱農民為“用身體與自然進行能量交換的人”)。在國家職業分工系統中,農民們並不直接跟動物打交道,動物不過是他們的難兄難弟。那些馴養動物、管理動物、宰殺動物的,都是最早為祭祀服務的宗教人士或朝廷官員。農民主要是跟植物打交道,為的是收穫充飢的稻、黍、麥、豆、瓜果、蔬菜,他們也漸漸跟植物精神合而為一,植物漸漸成了農民的集體潛意識。施賓格勒說:“人自己變成了植物--即變成了農民。……敵對的自然變成了朋友;土地變成了家鄉。在播種與生育、收穫與死亡、孩子與穀粒間產生了一種深刻的因緣。”([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上冊),19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農民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歷史觀念,實際上就是沒有“現代性”觀念支配下的線性物理時間觀念。他們的歷史就像是稻穀和草木的歷史,從生到死,從播種到收割,循環往復。他們的歷史同時也是自然意義上的身體生長史。這是一種在經驗表層顯得短暫(從天亮、醒到天黑、睡,從子宮到墳墓),但在經驗深層卻是無始無終的循環的時間觀(個體的消亡,子嗣的不斷繁衍,家庭與宗族的昌盛,就像植物的種子一樣)。這種農耕文化,支配了中國歷史和文化幾千年,形成了一種“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觀,與生物界的“生久必死,死久必生”的意思相近,就像植物一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就是他們的“形上學”。從生存空間的角度看,中國農民生活在一種奇特的建築布局之中,這種布局空間同樣跟他們的價值觀相關:將生長與死亡交織在一起,從居室的後窗,就能看到宗族的墓地,前院是人與牲畜、家禽生活的地盤;左右兩邊就是蔬菜、果樹和莊稼,他們就像叢生的植物中的一員。他們追求一種元素層面上的“天人合一”。這既是一種“時間的結構化”,也是一種“空間的時間化”。對此,我將在本書的第一、二兩章詳細討論。
農民十分依戀土地,土地就是家鄉,他們自己就像稻穀,土地是他們生長的基礎和死後的歸宿。年紀大的農民住不慣城市的樓房,他們的理由很奇怪:“住在樓上不習慣,沾不到地氣。”意思就是不能每天生活在泥土上。如果他們不是在潛意識裡將自己當作植物,這種觀念無論如何都是不可理解的。事實上農民就是植物,就是土地,就是沒有時間和歷史的輪迴。這正是他們在現代這個由線性觀念支配的世界中無可適從、甚至遭遇悲慘的根本原因。農民沒有絕對意義上的肯定和否定的“二元論”,也就是沒有絕對的“價值觀”。他們對事物的態度中隱含著一種由“植物模式”引申出來相對價值模式--沒有絕對的死亡,復活也包含在其中;沒有絕對的毀壞,生長也在其中;沒有絕對的否定,肯定也在其中。愛恨交加、褒貶合一、模稜兩可,都是他們典型的話語方式。全盤否定,或者全面接受的思維,不是農民的思維方式,而是市民對待農民的方式。甚至在農婦罵人的話中,也可以發現這種不符合“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她們的辱罵中沒有絕對的否定和絕對的貶低,而是採用一種否定和肯定合而為一的方式。讚美也是如此,比如她們經常稱自己的丈夫為“冤家”,既愛又恨,愛極恨極的兩端情感包含在一個辭彙之中。錢锺書稱之為“相反兩意融會於一字”(錢锺書:《管錐編》,第1冊,1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相同的例子還有:“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尚書》),其中的“亂”即“治”之義。,這種詞義的原始“兩歧性”,包含了農耕文明深層的精神基因。這種精神基因,已經被理性和邏輯解碼。其結果是一切都變得清晰可知,並且被簡單化。
中國的主要問題,至今依然是農民或變種農民的問題。中國當代文化經驗中,隱含著大量的農民經驗,或者被扭曲了的農民經驗。傳統的中國農民只是種地的,更極端的農民,連手工業者也不肯兼顧。“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的說法,是針對離城鎮較近的農村而言的。越是偏遠的農村,傳統的價值觀念越根深蒂固,社會分工也就越不發達。他們崇尚的是勞動或者生產價值,而不是交換和消費價值。所謂“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意思就是,無論自己的生活中需要什麼,都靠自己解決,種稻穀、種菜、養豬、釀酒、製糖,等等。比如要穿衣,他們會先種棉花,然後摘棉花--軋花(除棉花籽)--紡紗--織布--染布--裁剪--縫紉,自我服務一條龍,萬事不求人。這中間也包含了另外一層意思:他們是完整的人,他們的能力是多種多樣的,潛能的實現也是全方位的。如果是他們自己不能製造的東西,那就不是生活必需品,屬於他們很忌諱的奢侈品,要不要無所謂。一些技術比較複雜的、生活和生產又必不可少的物品,催化了鄉村手工業的發生,這是社會分工的最初結果,像鐵匠、木匠、泥水匠等。但在鄉村,這些手工業者完全專職的並不多,春耕秋收的時候,他們照樣要參與農業生產。我的老家,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依然是這種狀況。因此,這是一個拒絕消費的社會。所以他們既不需要商人,更不會成為商人。只有在廟會上,農民才短暫地成為了“商人”,帶著祭祀者與交換者的雙重身份。此外的絕大部分時間裡,他們依然是農民。他們的思維,並沒有因十天半月一次的廟會而發生變化。他們的歷史觀、人生觀,依然像一根玉米棒一樣。這只是就生產實踐和日常生活的領域而言。在價值觀念領域裡,他們從來就不認為一個人自己能夠“自給自足”,他們是一個整體,是一個從空間到時間、從個體和家庭再到家族和宗族的整體。這種整體性,體現在他們的人際關係、家庭關係等社會實踐的每一個細小的領域。
中國的現代化和都市化進程,改變了中國農民一統天下的局面。傳統的農民隊伍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分化和瓦解,產生了兩種基本類型的變種農民,一種是城外的農民,他們為了擺脫農業生產難以維生的尷尬局面,不得不將過去自給自足的農副業變成商業,給農貿販子提供大量的農副產品。另一種是進城的農民(也就是農副產品的倒賣者),他們有著農民的外表和商人的心靈。他們唯一的快樂就是數錢,像點鈔機一樣。他們最大的威脅,來自工業產品。只有在工業品的成本和利潤面前,他們才感到害羞、煩躁、焦慮。我們一直簡單地認為,都市化過程中首先獲利的是農民。因為都市化的前提就是將農業資源變成貨幣資本。實際上不是這樣。真正獲利的,除了一部分能控制資源的權貴之外,主要是一批從事農業資源批發的中介人。他們的職能,就是將農業文明的資源,轉換成現代都市中商品市場上的交換品。與這種可見的轉換相關的,是一種隱秘的變化,那就是文明中永恆的因素轉換成了短暫的、過渡性的因素。傳統社會的農耕精神,那些與土地、自然和血緣社會密切相關的和諧狀態,轉換成了市民精神,也就是時刻追求轉瞬即逝的時尚,轉化為對商品交換和剩餘價值的迷戀。
1
天色已黃昏。大地的輪廓消失了。黃昏是“明”與“暗”、“生”與“死”、“動”與“靜”的交界處。越過這個界限,一切可見的“動”都變成了“靜”。大地上的一切事物,都以一種仿佛“死寂”的形式在悄然生長。土地沉睡了,但它的分子和元素還在悄悄地行動,塵土的微粒和草葉的根莖都在喃喃自語。農民也沉睡了,但他們的夢還沒有睡,夢在召喚稻穀和子嗣的種子。黃昏之後的土地和生物,在一種可見的“靜”和不可見的“動”中運動。這是一種看不見但能夠感受到的生生不息的動和靜。這是一種來自土地的經驗,是感官和土地元素融為一體的經驗。按照這種經驗,黎明和白天,就是在用“動”的形式表現靜;黃昏和暗夜,就是在用“靜”的形式表現動。這就是“動靜合一”、“天人合一”、“生死一如”的價值觀念的自然基礎。靜是動的極端形式,就像動是靜的極端形式一樣。自然和天道的運行,明暗交替和四季循環的過程,並不是給明和暗、動和靜劃界,恰恰是在模糊它們的界限。農民對這種邊界模糊的明暗和動靜的體驗,與自然運行的天道是合而為一的。這種體驗或經驗的中斷,也就是體驗者與土地的關聯或與自然的關聯的中斷。
真正將“明”與“暗”、“動”與“靜”截然分開和對立的,不是自然,而是人工;不是土地和農民,而是城鎮和市民;不是感性,而是智性。城鎮徹夜不滅的燈光,在昏暗的大地上劃出了一道道虛無的邊界。在那個由燈光和鐘錶的嘀嗒聲劃定的邊界之內,我們看到一個顛倒了的世界在靜穆的世界之中狂歡不已。這個喧鬧不已的世界原本是不存在的,它是土地和農民文化中的另一極,也是被“生產價值”所抑制的一極,它只存在於農民想像的“魑魅魍魎世界”之中。現在,它“真實”地出現在土地上和農民的面前,充滿了誘惑,猶如向他們頻頻招手的“欲望”,仿佛要將他們從土地中連根拔起。毫無疑問,這個人為世界的邊界正在不斷擴大,以至於土地和農民的邊界越來越小,“生產”的邊界越來越小,“勞動價值”變得越來越成問題。城市以一種人為的方式消除了黃昏的景觀,改寫了黃昏的經驗,它沒有黃昏。在一個被城市經驗和城市價值支配的世界和時代,真正的“黃昏經驗”,或者說與之相關的土地經驗、鄉村經驗、農民經驗正在迅速消失。這就是我所說的“土地的黃昏”。無論人們為此找到什麼樣的理由(自然的理由、社會的理由),如果不說它是悲劇性的,那么至少也是無奈的。
2
獵人、漁民、牧民、農民,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居民。這種居民身份,與其說是社會分工的結果,不如說是自然分工的結果。獵人,就是及時將動物殺死的人。牧人,就是對動物執行“死緩”的人。最初的“農民”甚至就是茹毛飲血的野蠻人(也就是最初的獵人)。學會種地是文明開化史上的一個重大進步。中國農民開化得比較早,他們也最能與動物和睦相處。進入開化初期的農業社會,分工也十分細緻。先秦典籍《周禮》中記載的職業分類極其複雜,殺豬宰羊剖魚都有專人負責,負責釀酒的官叫“酒人”,負責制飲料的官叫“漿人”,負責製冷飲的官叫“凌人”。還有製造車輛的“輪人”、“輿人”,冶金鑄造的“冶氏”、“築氏”,製造兵器的“弓人”、“矢人”,等等。《考工記》中的原始手工業的“百工”(大約30種職業),作為國家管理系統的六大職業(六大職業是:坐而論道的“王公”;作而行之的“士大夫”;整治五材、製造器具的“百工”;使四方貨物流通的“商旅”;通過身體的勞動使土地生財的“農夫”;治理絲麻、紡紗織布的“婦功”(後面兩種就是所謂的“男耕女織”)。見《周禮·冬官考工記第六》)中的一種,也排在農夫前面。農夫不過是“飭力以長地財”的人(我稱農民為“用身體與自然進行能量交換的人”)。在國家職業分工系統中,農民們並不直接跟動物打交道,動物不過是他們的難兄難弟。那些馴養動物、管理動物、宰殺動物的,都是最早為祭祀服務的宗教人士或朝廷官員。農民主要是跟植物打交道,為的是收穫充飢的稻、黍、麥、豆、瓜果、蔬菜,他們也漸漸跟植物精神合而為一,植物漸漸成了農民的集體潛意識。施賓格勒說:“人自己變成了植物--即變成了農民。……敵對的自然變成了朋友;土地變成了家鄉。在播種與生育、收穫與死亡、孩子與穀粒間產生了一種深刻的因緣。”([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上冊),198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農民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歷史觀念,實際上就是沒有“現代性”觀念支配下的線性物理時間觀念。他們的歷史就像是稻穀和草木的歷史,從生到死,從播種到收割,循環往復。他們的歷史同時也是自然意義上的身體生長史。這是一種在經驗表層顯得短暫(從天亮、醒到天黑、睡,從子宮到墳墓),但在經驗深層卻是無始無終的循環的時間觀(個體的消亡,子嗣的不斷繁衍,家庭與宗族的昌盛,就像植物的種子一樣)。這種農耕文化,支配了中國歷史和文化幾千年,形成了一種“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觀,與生物界的“生久必死,死久必生”的意思相近,就像植物一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就是他們的“形上學”。從生存空間的角度看,中國農民生活在一種奇特的建築布局之中,這種布局空間同樣跟他們的價值觀相關:將生長與死亡交織在一起,從居室的後窗,就能看到宗族的墓地,前院是人與牲畜、家禽生活的地盤;左右兩邊就是蔬菜、果樹和莊稼,他們就像叢生的植物中的一員。他們追求一種元素層面上的“天人合一”。這既是一種“時間的結構化”,也是一種“空間的時間化”。對此,我將在本書的第一、二兩章詳細討論。
農民十分依戀土地,土地就是家鄉,他們自己就像稻穀,土地是他們生長的基礎和死後的歸宿。年紀大的農民住不慣城市的樓房,他們的理由很奇怪:“住在樓上不習慣,沾不到地氣。”意思就是不能每天生活在泥土上。如果他們不是在潛意識裡將自己當作植物,這種觀念無論如何都是不可理解的。事實上農民就是植物,就是土地,就是沒有時間和歷史的輪迴。這正是他們在現代這個由線性觀念支配的世界中無可適從、甚至遭遇悲慘的根本原因。農民沒有絕對意義上的肯定和否定的“二元論”,也就是沒有絕對的“價值觀”。他們對事物的態度中隱含著一種由“植物模式”引申出來相對價值模式--沒有絕對的死亡,復活也包含在其中;沒有絕對的毀壞,生長也在其中;沒有絕對的否定,肯定也在其中。愛恨交加、褒貶合一、模稜兩可,都是他們典型的話語方式。全盤否定,或者全面接受的思維,不是農民的思維方式,而是市民對待農民的方式。甚至在農婦罵人的話中,也可以發現這種不符合“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她們的辱罵中沒有絕對的否定和絕對的貶低,而是採用一種否定和肯定合而為一的方式。讚美也是如此,比如她們經常稱自己的丈夫為“冤家”,既愛又恨,愛極恨極的兩端情感包含在一個辭彙之中。錢锺書稱之為“相反兩意融會於一字”(錢锺書:《管錐編》,第1冊,1頁,北京,中華書局,1979。)相同的例子還有:“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尚書》),其中的“亂”即“治”之義。,這種詞義的原始“兩歧性”,包含了農耕文明深層的精神基因。這種精神基因,已經被理性和邏輯解碼。其結果是一切都變得清晰可知,並且被簡單化。
中國的主要問題,至今依然是農民或變種農民的問題。中國當代文化經驗中,隱含著大量的農民經驗,或者被扭曲了的農民經驗。傳統的中國農民只是種地的,更極端的農民,連手工業者也不肯兼顧。“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的說法,是針對離城鎮較近的農村而言的。越是偏遠的農村,傳統的價值觀念越根深蒂固,社會分工也就越不發達。他們崇尚的是勞動或者生產價值,而不是交換和消費價值。所謂“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意思就是,無論自己的生活中需要什麼,都靠自己解決,種稻穀、種菜、養豬、釀酒、製糖,等等。比如要穿衣,他們會先種棉花,然後摘棉花--軋花(除棉花籽)--紡紗--織布--染布--裁剪--縫紉,自我服務一條龍,萬事不求人。這中間也包含了另外一層意思:他們是完整的人,他們的能力是多種多樣的,潛能的實現也是全方位的。如果是他們自己不能製造的東西,那就不是生活必需品,屬於他們很忌諱的奢侈品,要不要無所謂。一些技術比較複雜的、生活和生產又必不可少的物品,催化了鄉村手工業的發生,這是社會分工的最初結果,像鐵匠、木匠、泥水匠等。但在鄉村,這些手工業者完全專職的並不多,春耕秋收的時候,他們照樣要參與農業生產。我的老家,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依然是這種狀況。因此,這是一個拒絕消費的社會。所以他們既不需要商人,更不會成為商人。只有在廟會上,農民才短暫地成為了“商人”,帶著祭祀者與交換者的雙重身份。此外的絕大部分時間裡,他們依然是農民。他們的思維,並沒有因十天半月一次的廟會而發生變化。他們的歷史觀、人生觀,依然像一根玉米棒一樣。這只是就生產實踐和日常生活的領域而言。在價值觀念領域裡,他們從來就不認為一個人自己能夠“自給自足”,他們是一個整體,是一個從空間到時間、從個體和家庭再到家族和宗族的整體。這種整體性,體現在他們的人際關係、家庭關係等社會實踐的每一個細小的領域。
中國的現代化和都市化進程,改變了中國農民一統天下的局面。傳統的農民隊伍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分化和瓦解,產生了兩種基本類型的變種農民,一種是城外的農民,他們為了擺脫農業生產難以維生的尷尬局面,不得不將過去自給自足的農副業變成商業,給農貿販子提供大量的農副產品。另一種是進城的農民(也就是農副產品的倒賣者),他們有著農民的外表和商人的心靈。他們唯一的快樂就是數錢,像點鈔機一樣。他們最大的威脅,來自工業產品。只有在工業品的成本和利潤面前,他們才感到害羞、煩躁、焦慮。我們一直簡單地認為,都市化過程中首先獲利的是農民。因為都市化的前提就是將農業資源變成貨幣資本。實際上不是這樣。真正獲利的,除了一部分能控制資源的權貴之外,主要是一批從事農業資源批發的中介人。他們的職能,就是將農業文明的資源,轉換成現代都市中商品市場上的交換品。與這種可見的轉換相關的,是一種隱秘的變化,那就是文明中永恆的因素轉換成了短暫的、過渡性的因素。傳統社會的農耕精神,那些與土地、自然和血緣社會密切相關的和諧狀態,轉換成了市民精神,也就是時刻追求轉瞬即逝的時尚,轉化為對商品交換和剩餘價值的迷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