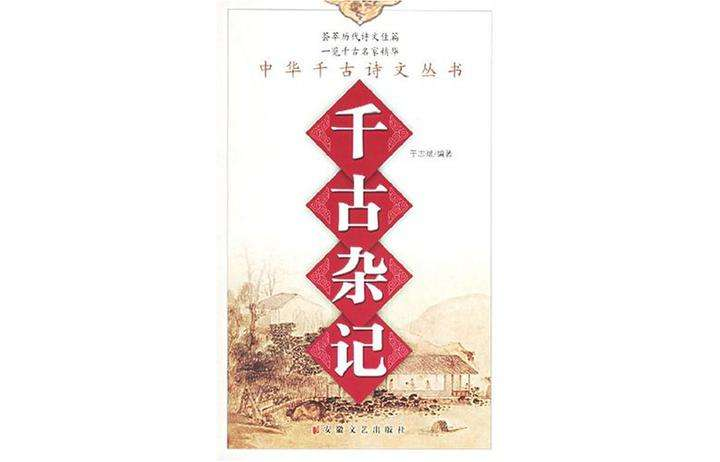《千古雜記》 是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圖書, ISBN是 9787539626802
基本介紹
- 作者:於志斌
- ISBN:9787539626802
- 頁數:294
- 定價:14.80元
- 出版社:安徽文藝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6-4
- 裝幀:簡裝本
內容介紹
“雜記”是什麼?雜記是古人在劃分文章體裁中確定的一種文體。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講到這種文體:“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序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古人劃分文體,為編選文章提供了很大便利。如梁蕭統《文選》,宋姚鉉《唐文粹》、呂祖謙《宋文鑒》,清姚鼐《古文辭類纂》等名選,走的都是分類編選這一路子。古往今來,文章的編選工作一直沒有停止過。大概在編選中,各家愈來愈難以控制雜記文章的範圍了;同時,有人又總想界定清楚“雜記”的性質和規制。姚鼐在其《古文辭類纂·序》中說:“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即為一例。
文體隨著時代發展而越來越豐富,這是一般規律;漢字在表現主客觀事物上的創造性和張力,充分表現出來。今人睿智地說:狹義地說,雜記似可以簡約地分為四類:即台閣名勝記、山水遊記、書畫雜物記和人事雜記;廣義地說,雜記包括了一切記事、記物之文;甚至可以講:包括正史以外的傳記以及同傳記性質相近的行狀、碑誌等一切記敘文,統可稱為雜記。
“雜記”這兩個字及其作為文體的含義,早在《禮記》中出現。這部文化原典是一冊儒學雜編,其中有通論禮意及學術的,專釋《儀禮》的,記錄孔子及弟子時人雜事問答的,有記載古代制度禮節的,等等。在《禮記》中有“雜記上” “雜記下”兩節,前人鄭玄《禮記目錄》稱:“名曰‘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孫希坦說:“此篇所記……以其所記者雜,故曰‘雜記’。”
雜記體作品至遲在魏晉時代就已經產生,其標誌物之一是這個時代創作了大量的雜記體“志怪小說”。唐宋以後古文家所寫的雜記,往往於記敘中夾議論、兼抒情,有時議論、抒情的份量相當多。有的專發議論的雜記,實際上已可歸入論的一體了。
??? 在歷代說部和史部的筆記作品中,各家所記內容豐富多彩,諸如文化藝術、科學技術、風土人情、遺聞佚事,無所不記,成為“雜記”的淵藪。魏晉時代的傑出作品、亦為“志怪小說”的《世說新語》,就是一部筆記文學作品集。而宋代沈括的《夢溪筆談》(還有他的《補筆談》、《續筆談》),被前人評為“記事周詳,屬詞嚴正”,顯示出雜記體在史部中的重要作用。
雜記文字一般不刻意求工,風格清簡而自然,有“質勝之文”的美譽,價值不在以文學筆法所寫的作品之下。
今天對“雜記體”的研究還在繼續著,“雜記體”的範圍及其作品在擴大。顧頡剛指出“左傳原本”在劉歆以前早已存在,“《左傳》原亦雜記體之史,猶《國語》、《戰國策》、《說苑》、《新序》、《世說新語》、《唐語林》、《宋稗類鈔》……”有人認為:《老子》一書是隨想式的雜記體,是老子把平時思考的問題,用詩一般的語言記錄下來;《包公案》,又名《龍圖公案》,乃是一部雜記體的小說;《西遊記》應該是地理遊記而非小說,因為有“游”字;吳承恩以寫雜記著稱,那么他的《西遊記》應該是雜記體(以上為網上搜尋所得)。
在確定本書編選範圍時,編者首先將“中華千古詩文叢書”選目瀏覽一遍,發現叢書已有《千古碑銘》、《千古遊記》兩種。其次發現: 國筆記文學亦浩如瀚海,僅編者寒架上《筆記小說大觀》,就收集了從晉到清的筆記作品二百餘部,《舊小說》收有筆記七百餘篇。這套叢書是安徽文藝出版社用與時俱進的發展觀,努力構築的一個為普羅大眾所喜歡的文學國粹館;旨在普及、傳承 國傳統文學優秀作品和凸顯延續根脈的人文精神。從雜記中析出碑銘、遊記作品,是有其實用意義的,可以讓讀者、觀眾對這兩類作品看得更加仔細和系統。 向出版社建議:叢書再從歷代雜記中析出筆記作品,單獨形成為《千古筆記》。
於是,編者之《千古雜記》沒有碑銘、遊記、筆記作品,在所選百餘篇雜記中,近百分之八十的篇目是以題名為記的文章,如《冷泉亭記》、《醉翁亭記》、《汾湖石記》。剩餘各篇目中,一是題名為“書”為“志”為“題”者,如《書何易於》、《項脊軒志》、《書王尚甫事》、《書魯亮儕》、《題東坡笠屐圖》、《書繼洲及對山事》、《題詞〈江南臥遊冊·橫塘〉》,前人早就認定“書”、“志”、“題”就是“記”;其中,為繪畫作品題寫的文字也叫做“題畫記”或“畫記”(從這個意義上講,“題”字就是“題畫記”或“畫記”的略稱)。二是題名為“傳”者,如《方山子傳》、《童區寄傳》、《徐文長傳》、《息庵翁傳》、《李賀小傳》、《戴文進傳》、《黃山人小傳》、《閻典史傳》,它們的行文體式和風格都符合雜記體,而與所謂傳記體並不一致。三是題名中沒有“記”、“書”、“志”、“題”、“傳”者,但又的確是雜記作品,如《斗蟻》、《斗蟻》、《觀潮》、《左忠毅公逸事》;又如《景林寺》、《三峽》,它們分別選自《洛陽伽藍記》和《水經注》,足以說明魏晉時代確實是 國雜記體成熟期;而《跋李莊簡公家書》一文則是閱讀雜記;《說居庸關》一文最特別,文題中一個“說”字,讓人以為它是一篇論文,可是一讀之下 們便能發現它是一篇以夾敘夾議見長的雜記。
有人為解說以“志”為題的雜記,說記人敘事的《項脊軒志》是雜記,因而這裡的“志”與“記”是同義的。如此推論,記人敘事的《徐文長傳》等是雜記,因而這裡的“傳”與“記”是同義的。其實,中國文字字義很複雜,如果查一查專業辭典就會發現,“書”、“志”、“題”、“傳”、“寫”(甚至“跋”)等等,都有“記”的意義。這與 們國家有著五千年書寫文明的歷史是相稱的。 想:文章題目不是 們判別雜記體的準衡;《千古雜記》聊備數“格”有好處,它能使讀者更多了解雜記體作品的紛繁多樣性。
編者之《千古雜記》選文在五篇以上的雜記作家共有五人,他們是:歐陽修(7篇)、蘇軾(6篇)、袁宏道(8篇)、方苞(6篇)、姚鼐(5篇)。這些雜記大家的作品不得不多選一些。歐陽修、蘇軾是文章“唐宋八大家”中的兩位,他們把人生經歷和情感世界寄寓在台、閣、亭、堂、園、廟諸名勝上,林林總總,讓 們堪足玩味;後來者在台閣名勝雜記上的所興所託、所賦所議,都難出其右。袁宏道斗蟲鬥雞雜記則別具一格,人與動物理趣一也;它們連同袁氏其餘諸作,既為“性靈”張目,也替“公安派”爭足了面子。方苞、姚鼐的雜記,是雄霸清代文壇的桐城文派關心世態民情、注重人文精神的典型篇章,學“桐城”章法當從這裡入手。 沒有理由不多選一些上述前輩的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