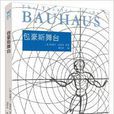基本介紹
- 書名:包浩斯舞台
- 作者:奧斯卡·施萊默 (Oskar Schlemmer) 等
- 出版日期:2014年3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15509068, 7515509066
- 外文名:The Theater of the Bauhaus
-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 頁數:114頁
- 開本:16
- 品牌:金城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奧斯卡·施萊默的文學遺產在形式和內容方面堪稱經典,特別是由他撰寫的《人與藝術形象》一章,也是本書最重要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以雋美而簡潔的文風為舞台藝術演員確立了一些基本的價值,以清晰且克制的思考強調了在視覺中的個人。這些寫作有著廣闊而恆久的生命力。
—— 瓦爾特·格羅皮烏斯 (包浩斯創始人)
—— 瓦爾特·格羅皮烏斯 (包浩斯創始人)
作者簡介
奧斯卡·施萊默(Oskar Schlemmer,1888—1943),出生於德國,是著名畫家、雕刻家、設計師、現代舞蹈與劇場的實驗者和藝術理論家,1920年被聘為包浩斯的形式大師,1923年開始主持包浩斯舞台作坊,是包浩斯黃金時期影響最大的幾位大師之一。其舞台代表作《三人芭蕾》作為西方現代戲劇史中的名作,是20世紀重新探索舞蹈與劇場結合的最早嘗試之一。其主要著作有《包浩斯舞台》、《施萊默通信與日記》、《“人”課筆記》等書。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這是本世紀在美學上意義最為重大的出版物之一。
——《戲劇藝術》(Dramatics )雜誌
對一個特定時期而言,這是一本至關重要的劇場之書。
——《進步建築》(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雜誌,(後更名為《建築》雜誌)
——《戲劇藝術》(Dramatics )雜誌
對一個特定時期而言,這是一本至關重要的劇場之書。
——《進步建築》(Progressive Architecture )雜誌,(後更名為《建築》雜誌)
名人推薦
這本書反映了包浩斯在舞台工作坊這一特定領域中的探索。在包浩斯這個共同體中,奧斯卡·施萊默扮演了一個關鍵角色。奧斯卡·施萊默的文學遺產在形式和內容方面堪稱經典,特別是由他撰寫的《人與藝術形象》一章,也是本書最重要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以雋美而簡潔的文風為舞台藝術演員確立了一些基本的價值,以清晰且克制的思考強調了在視覺中的個人。這些寫作有著廣闊而恆久的生命力。
——瓦爾特·格羅庋烏斯(包浩斯創始人)
這本書展現了至今看來仍然非常廣博多樣的,並且一定程度上還相互對抗著的劇場與舞台實踐方法,它們處於魏瑪包浩斯時期和德紹包浩斯時期之間的情境中。此書出版時,施萊默是否會在德紹繼續他的舞台工作,他是否能最終將一種新的人造人類形象視覺化,以及某種刻板的機械化劇場是否將變成包浩斯的中心主題,這一切都還沒有明朗。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有可能把這本書視為願景之書,或者視之為關於諸多開放性的觀念的檔案。它至今仍為我們提供著具有特殊價值的包浩斯的想像力。
——托爾斯坦·布魯姆(德紹包浩斯基金會研究員、藝術家、策展人)
——瓦爾特·格羅庋烏斯(包浩斯創始人)
這本書展現了至今看來仍然非常廣博多樣的,並且一定程度上還相互對抗著的劇場與舞台實踐方法,它們處於魏瑪包浩斯時期和德紹包浩斯時期之間的情境中。此書出版時,施萊默是否會在德紹繼續他的舞台工作,他是否能最終將一種新的人造人類形象視覺化,以及某種刻板的機械化劇場是否將變成包浩斯的中心主題,這一切都還沒有明朗。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有可能把這本書視為願景之書,或者視之為關於諸多開放性的觀念的檔案。它至今仍為我們提供著具有特殊價值的包浩斯的想像力。
——托爾斯坦·布魯姆(德紹包浩斯基金會研究員、藝術家、策展人)
圖書目錄
人與藝術形象
劇場,馬戲團,雜耍
U 型劇場
舞台
附:1961年英譯本序
譯後記
劇場,馬戲團,雜耍
U 型劇場
舞台
附:1961年英譯本序
譯後記
序言
譯叢總序
BAU,超越建築與城市——當代-歷史條件中的包浩斯
(一)
包浩斯(Bauhaus)在上世紀那個“沸騰的20年代”,扮演了重要的、頗具神話色彩的角色。它從未宣稱要傳承某段“歷史”,它以基礎課程取而代之,它被認為是“反歷史主義的歷史性”……但是相對於當下的“我們”,它似乎已經是公認的“歷史”了。幾乎所有設計與藝術的專業人員都知道,包浩斯這一理念原型是現代主義歷史上不可迴避的經典。它甚至經典到了,即使人們不知道它為何經典,也知道關於它的諸多經典論述,即使人們不知道歷史,也知道將這一顛倒了“房屋建造”(haus-bau)而杜撰出來的“包浩斯”,視作歷史。
它甚至過於經典到了,即使人們不知道這些論述,不知道它的命名由來,它的理念與原則也已經在設計與藝術的基礎課程中得到了廣泛的實踐。對公眾而言,包浩斯或許就是一種風格。無須諱言,正在當前中國工廠中代加工和山寨的被稱為“包浩斯”的家具,同任何被稱為其他名字的家具一樣,圍繞著如何創建品牌並使其脫穎而出的問題,儘管“包浩斯”之名曾經與一種對超越特定風格的普遍性法則的追求緊密相連。
(二)
歷史的“包浩斯”,作為一所由美術學院和工藝美術學校組成的教育機構,被看做是設計史、藝術史的歷史的某一開端。但是我們如果仍然把包浩斯當做設計史的對象去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只能是一種同義反覆。透過闡釋、元闡釋到實踐、社會生產的幾個層次,我們可以將“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的意義推至極限:一切被我們當下稱為“歷史”的,都只是為了成為其自身情境中的實踐,因此它必然是“當代”的實踐。
因此,歷史檔案需要重新歷史化。只有把我們當下的社會條件寫入這一歷史的情境中,不再預設將包浩斯作為已經凝固的歷史檔案和歷史經典,這一“寫入”才可能成為我們與當時的實踐者之間的對話。它是對“歷史”本身之所以存在的真正條件的一種評論。歷史的“包浩斯”不僅是時間線上的一個節點,它已經融入我們當下的情境,或者說,已經構成了當代條件下的包浩斯情境。然而“包浩斯情境”並非僅僅是一個既成事實,當我們與包浩斯檔案在當下這一時間點上再次遭遇時,歷史化將以一種顛倒的方式再次發生,意即歷史的“包浩斯”構成了我們的條件,而我們的當下成為了“包浩斯”未曾遭遇過的情境。
這意味著必須將“當代-歷史”條件的轉變,放置在“當代”包浩斯的視野中,才能更為切要地解讀和譯出那些曾經的文本。歷史的包浩斯提出的目標,“藝術與技術的新聯合”,已經從機器生產、新人構成、批量製造,轉變為網路通訊、生物技術與金融資本的全球新模式。它所處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帝國主義競爭關係,已經擴編為由此而來的向美國轉移的中心與邊緣的關係,以及在國際主義名義下的新帝國主義,或者說由跨越國家邊界的空間、經濟、軍事等機構聯合的新帝國等等。
只有將“當代”看做是“超脫歷史地去承認歷史”,才可能在構築經典的同時,瓦解這一歷史之後的經典話語。包浩斯不再僅僅是設計史、藝術史中的歷史,我們希望通過對其檔案的重新歷史化,將它為所處的那一現代時期的不可能,提供的可能性條件,轉化為重新派發給當前的一部思想的、社會的、革命的歷史。對應於這部歷史,包浩斯研究將是一種具體的、特定的、預見性的設定,而不是一種普遍方法的抽象而系統的事業,後者沉浸在“終會有某個更為徹底的闡釋版本存在”的幻象之中。
(三)
陸續出版於1925至1930年間的“包浩斯叢書”(Bauhausbücher)作為包浩斯德紹時期發展的主要里程碑之一,是一系列富於冒險性和實驗性的出版行動的結晶。叢書由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和莫霍利-納吉(Laszlo Moholy-Nagy)合編,一共出版了14本,除了當年包浩斯的教師格羅皮烏斯、莫霍利-納吉、施萊默(Oskar Schlemmer)、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克利(Paul Klee)等人的著作以及師生的作品之外,還包括了杜伊斯堡(Theo van Doesburg)、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馬列維奇(Kasimier Severinovich Malevich)等等這些與包浩斯理念相通的藝術家的論述。此外這套叢書曾經計畫但最終未能出版的,還有立體主義、未來主義以及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等人的文章。
我們於此刻開啟“包浩斯叢書”的翻譯計畫,並不是因為這套被很多學者忽略的叢書是一段必須遵從的歷史。我們更願意將這一翻譯工作看做是促成當下回到設計原點的對話,是適時於這一當下-歷史時間點上的實踐。重新檔案化的計畫是一次沿著他們與我們的主體路線潛行的歷史展示,它試圖在物與像、批評與創作、學科與社會、歷史與當下之間建立某種等價關係。這一系列的等價關係,也是對雷納·班納姆(Reyner Banham)敏感地將這套“包浩斯叢書”判定為“現代藝術著作中最為集中,同時也是最為多樣性的一次出版行動”的積極回應。
當然,這一系列出版計畫,也可以成為面向2019年——包浩斯誕生百年——這一重要節點的令人激動的事件,但是真正促使我們與歷史遭遇並再度進入“包浩斯叢書”的是連線起這百年相隔的“當代-歷史”條件中的行動的“理論化的時刻”。我們以“包浩斯叢書”的譯介為開端的出版計畫,無疑與當年的“包浩斯叢書”一樣,也是一次面向未知的“冒險的”決斷,去論證“包浩斯叢書”的確是一系列的實踐之書、關於實踐的構想之書、關於構想的理論之書——同時去展示它在自身的實踐與理論之間的部署,以及這種部署如何對應著它刻寫在文本內容與形式之間的“設計”。
與這一“理論化的時刻”相悖的是,現實中的對包浩斯歷史的研究方案已經被隔離在各自分屬的專業領域,這與當年包浩斯圍繞著“秘密社團”展開的總體理念愈行愈遠。如果我們將當下的出版視作再一次的媒體行動,那么關於出版的計畫就是媒體行動的媒介,在行動發生之前就對既有邊界發起拷問。媒介-歷史學家伊尼斯(Harold A. Innis)曾經認為他那個時代的大學體制對知識進行分割肢解的專門化處理是不光彩的知識壟斷,“科學的整個外部歷史就是學者和大學抵抗知識發展的歷史”。這一情形在我們當前所處的時代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扭轉,正是學科專門化的弊端,令包浩斯的成果在今天被切割、分派進建築設計、現代繪畫、工藝美術等領域。而“當代-歷史”條件中真正的寫作,應當向對話學習,讓寫作成為一場場的論戰,並相信只有在所有題材的多方面相互作用中,真正的“發現”與“洞見”才可能產生。正是在此意義上,“包浩斯叢書”被我們視作“歷史”中的一次寫作的典範,成為支撐我們這一系列出版計畫之核心的“基礎課程”。
(四)
“理論化的時刻”並不是把可能性還給歷史,而是要把歷史還給可能性。只有在當下社會生產的可能性條件的視域中,才有了“歷史”的發生,否則人們為什麼要關心歷史還有怎樣的可能?持續的出版,便是持續地回到包浩斯的發生、接受與再闡釋的雙重甚至是多重的時間中去。全球化的生產帶來的物質產品的景觀化,新型科技的發展與技術潛能的耗散,藝術形式及其機制的循環與往復,地緣政治與社會運動的變遷,風險社會給出的承諾及其破產,以及看似無法挑戰的硬體資本主義的神話等等,這些新的命題很可能正是“當代-歷史”條件中包浩斯情境的多重化身。
多重的可能的時間,以一種共時的方式降臨中國,全面地滲入並包圍著人們整個的日常生活。正是“此時”的中國,提供了比新自由主義的普遍地形更為複雜的空間條件,讓此前由諸多理論描繪過的未來圖景,逐漸失去了針對這一現實的批判潛能。這一當代的發生是政治與市場、理論與實踐奇特綜合的正在進行時,亟需尋求新的開端。因此,“此地”的中國不僅是在全球化狀況中重演的某一個區域版本,它劇烈地感受著全球資本與媒介時代的共同焦慮,同時更是反思從特殊性通往普遍性的更為敏感的出發點,是由不同的時空混雜出來的從多樣的有限到無限的行動點。時間的配置激發起空間的鬥爭,撬動著藝術與設計及對這二者進行區分的根基。
辯證的追蹤,是識得這些多重化身的必要之法。比如,格羅皮烏斯在《新建築和包浩斯》(The New Architecture and the Bauhaus ,1935)開篇中強調通過“新建築”恢復日常生活中使用者的意見與能力。如今社會公眾的這種能動性已經不再是他當年所說的有待被激發起來的興趣,而是對應於更多的參與和自己動手的需求,並且目前看來,似乎參與和DIY的需求已經如此的多樣,無須再加以激發。然而真正由此轉化出的當代問題是,在一個已經被分隔管制的消費社會中,或許被多樣的需求製造出來的諸多差異恰恰導致了更深的受限於各自技術分工的眼與手的分離。
再如,格羅皮烏斯1927年為無產階級劇場的倡導者皮斯卡托制定的總體劇場方案,在歷史中未曾實現,而當前的“總體劇場”已經衰變為景觀自動裝置的隱喻。觀眾與演員之間的舞台幻象已經打開,劇場本身的邊界卻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放。現代性發生的時期,藝術或多或少地運用了更為廣義的設計技法與思路,而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的論述中,藝術的生產更趨於商業化,商業則更多地吸收了藝術化的表達手段與形式。精英文化堅守的、與大眾文化對抗的界線事實上已經難以分辨。作為超級意識形態的資本提供的未來幻象——在樣貌上甚至沿襲現代主義的某些總體想像——早已藉助專業職能的技術培訓和市場運作,將分工和商品作為現實的根本支撐,朝著截然相反的方向運行。它並非將人們監禁在現實的困境中,而是對每個人所從事的專業領域中的想像加以控制,將其安置在單向度發展的進程軌道上,例如在狹義的設計機制中自詡的創新,以及在狹義的藝術機制中自慰的批判。
(五)
當代-歷史條件中的包浩斯,讓我們回到已經被各自領域的大寫歷史遮蔽的原點。這一原點是對包浩斯情境中的資本、商品形式以及之後的設計職業化的綜合反思,它或許將有助於研究者們超越對設計產品的僅僅拘泥於客體的分析,超越以運用為目的的操作性批評,超越缺乏技術批判的陳詞濫調和固守進步主義的理論空想。“包浩斯情境”中的實踐曾經是這樣一種打通,它連線起巴迪歐(Alain Badiou)所說的構成政治本身的“沒有部分的部分”的兩面:一面是未被現實政治計入在內的情境條件,另一面是未被想像的“形式”。這裡所指的並非是通常意義上的形式,而是一種新的思考方式的正當性。
在包浩斯當年的宣言中,人們可以感受到一種振聾發聵的烏托邦情懷:“讓我們建立一個嶄新的行會,其中工匠與藝術家互不相輕,亦無等級隔閡。讓我們共同創立新的未來大廈,它將融建築、雕塑和繪畫於一體。有朝一日它將從成百萬工人手中矗立起來,猶如一個新的信仰的晶瑩的象徵物升向天國。”
除了第一句中指出了技術與藝術的連線之外,它描繪的是“當代”版本的面向上帝神力的建造事業:從諸多藝術手段融為一體的場景,到出現在宣言封面上由費寧格(Lyonel Feininger)繪製的那一座蓬勃的教堂,跳躍、鬆動、並不確定的“當代”意象,賦予了包浩斯更多神聖性的色彩,超越了通常所見的烏托邦藍圖。它超越了僅僅對一個特定時代的材料、形式、設計、藝術、社會做出更多貢獻的願望,而是“有朝一日”,社群與社會的連線將要掀起的運動:一場以崇高的感性能量為支撐的促進社會更新的激進演練,它選擇“晶體”作為閃現著全人類光芒的、面向新的共同體信仰的喻示。我們更願意相信曾經在整個現代主義運動中蘊含著的突破社會隔離的能量,同樣可以在當下的時空中得到有力的釋放。
包浩斯初期階段的一個“作品”,也是格羅皮烏斯的作品系列中最容易被忽視的一個“作品”,布拉克豪斯佐默費爾德(Blockhaus Sommerfeld,佐默費爾德的小木屋),它是“包浩斯第一個集體工作的真正產物”。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對它的重新肯定,將“建築的本源應當是怎樣的”這一命題,從物的實證引向了對觀念的回溯。我們從此類對包浩斯的再認識中,看到了一種我們深為認同的觀點,即歷史的包浩斯,不僅如通常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是對機器生產的時代回應,更是對機器生產時代的超越和反思。我們回溯歷史,並不是為了在現有的歷史框架中去取證包浩斯遺留給我們的物件,恰恰相反,繞開它們去追蹤包浩斯之情境,方為設計之道。我們回溯建築的歷史,如同一次命運的救贖,正如里克沃特在別處所說的,任何公眾人物如果要向他的同胞們展示他所具有的“美德”(virtues),那么,建築學就是他所必須賦予他的命運的一種救贖。我們在此引用這句話,並非為了作為歷史的包浩斯而抬高建築學,而是將美德與命運聯繫在一起,將個人的行動與公共性聯繫在一起,方為設計之德。
(六)
阿爾伯蒂將“美德”理解為在與市民生活和社會有著普遍關聯的事務中進行的一些有天賦的實踐。如果我們並不強調設計者所謂天賦能力或素養,而是將設計的活動放置在“開端的開端”,那么我們有理由將現代性的發生與建築師的命運推回到文藝復興時期。當時的“美德”綜合了上述的設計之道與設計之德,消除了它的“道德”表象。它意指卓越與慷慨的行為,一種賦予形式從內部的部署向外延伸的行為,它將建築師的意圖和能力與“上帝”在造物時的目的和成就,以及社會的人聯繫在一起。
正是對和諧的關係的處理,使得建築師自身進入了社會,但是,這裡的“和諧”必然是一種新的運動,甚至與它字面意義相反,在包浩斯時期的和諧已經被“構型”(Gestaltung)所替代。包浩斯的命名及其教學理念結構圖中居於核心位置的“BAU”暗示我們,正是所有的創作活動圍繞著“建造”展開,才得以清空歷史中的“建築”,進入到當代-歷史條件中的“建造”。因此,建築師是這樣一種“成為”(becoming),他重新建構而不是維持某種關係,他進入社會,將人們聚集在一起;同時他的進入,必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進入社會現實,而是面向“上帝”之神力並擾動著現存秩序的“進入”。這一“進入”,在包浩斯整個集體工作的理念中,很容易理解:教師與學生在工作坊中儘管處於合作狀態,但是教師決不能將自己的方式強加於學生,而學生的任何模仿意圖都會被嚴格禁止。
包浩斯的歷史檔案不只作為一份探究其是否被背叛了的遺產,用以糾偏“我們”的行為。它被吸納為“我們”的歷史計畫,這意味著如塔夫里(Manfredo Tafuri)所言“透過一個永恆於舊有之物中的概念之鏡頭,去分析現況”。作為當代-歷史條件中的“政治”,作為已展開在當代的“歷史”,它是人類現代性的發生以及對社會更新具有遠見的總歷史中一項不可或缺的條件。它不斷地被打開,又不斷地被關閉,正如它自身及其後繼機構的歷史命運那樣,但是,或許只有在這一基礎上,對包浩斯的評介及其召喚出來的新研究,才可能將此時此地的“我們”捲入面向未來的反思與實踐。
我們需要用包浩斯的方法去批判包浩斯,這是一種既直接又理論的實踐。從拉斯金(John Ruskin)到莫里斯(Wilhelm Morris),都想讓民眾互相聯合起來,人人成為新設計師;格羅皮烏斯,想讓設計師聯合起大資本家,做出新人;而漢斯·梅耶(Hans Meyer),想讓設計師聯合起民眾,做出新社會……每一次對前人的轉譯,都是正逢其時的斷裂。而缺失了作為新設計師、新人、新社會夢想之前提的“聯合”,所謂“創新”至多只能強調出個體差異之“新”,它只能讓當前的設計師淪為將自身的道德與善意轉化為公共展示的群體。在包浩斯百年之後的今天,對包浩斯的批判性“轉譯”,是對正在消亡中的包浩斯的雙重行動,這樣一種既直接又理論的實踐似乎與建造沒有直接的關聯,然而它所關注的重點正是,新的“建造”將由何而來?
(七)
柏拉圖認為,“建築師”在建造活動中唯一的當務之急是實踐——當然,我們今天應當將理論的實踐也包括在內——在柏拉圖看來,那些諸如表現人類精神、將建築提到某種更高精神境界等等的毫無技術和物質介入的決斷,並不是建築師們的任務。在這個意義上,建築是人類嚴肅的需要和非常嚴肅的性情的產物,並通過人類所擁有的最高價值的方式去實現。也正是因為恪守於這一“嚴肅”與最高價值的“實現”,他將草棚與神廟視作同等,二者間只存在量上的區別,並無質上的不同。我們可以從這一“嚴肅”的行為開始,去打通已被隔離的“設計”領域,而不是利用從包浩斯的歷史遺物中論證出來的“設計”美學,去連線湯勺與城市。
柏拉圖把人類所有創造“物”並投入到現實的活動,統稱為“人類修建房屋,或更普遍一些,定居的藝術”。但是投入現實的活動並不等同於通常所說的實用藝術,恰恰相反,他將建造人員的工作看成是一種高尚而與眾不同的職業,將其置於更高的位置。這一意義上的“建造”,是建築與政治的聯繫,甚至正因為“建造”的確是一件嚴肅得不能再嚴肅的活動,必須不斷地爭取更為全面包容的解決方案,建築才可能成為一種精彩的“遊戲”。
由此我們可以這樣去理解“包浩斯情境”中的“建築師”,因其“遊戲”,它遠非當前職業工作者陣營中的建築師,因其“嚴肅”,它也不是指職業者的另一面,所謂刻意的業餘或民間,或加入藝術陣營中的建築師。誠如塔夫里所指出,包浩斯以及勒·柯布西耶等人在當時並非努力模仿著機器的表象,而是抽身進入機器背後的法則之中。當下的“建築師”,如果仍願選擇這種態度,則要抽身進入媒介的法則中,抽身進入諸眾之中,將就手的專業工具當做可改造的武器,去尋找和激發某種共同生活的新紋理。這裡的“建築師”,位於建築與建造之間的“裂縫”,它真正指向的是:超越建築與城市的“建築師的政治”。
超越建築與城市(Beyond Architecture and Urban),是為BAU,是為“BAU叢書”之序。
王家浩
2013年10月於上海
BAU,超越建築與城市——當代-歷史條件中的包浩斯
(一)
包浩斯(Bauhaus)在上世紀那個“沸騰的20年代”,扮演了重要的、頗具神話色彩的角色。它從未宣稱要傳承某段“歷史”,它以基礎課程取而代之,它被認為是“反歷史主義的歷史性”……但是相對於當下的“我們”,它似乎已經是公認的“歷史”了。幾乎所有設計與藝術的專業人員都知道,包浩斯這一理念原型是現代主義歷史上不可迴避的經典。它甚至經典到了,即使人們不知道它為何經典,也知道關於它的諸多經典論述,即使人們不知道歷史,也知道將這一顛倒了“房屋建造”(haus-bau)而杜撰出來的“包浩斯”,視作歷史。
它甚至過於經典到了,即使人們不知道這些論述,不知道它的命名由來,它的理念與原則也已經在設計與藝術的基礎課程中得到了廣泛的實踐。對公眾而言,包浩斯或許就是一種風格。無須諱言,正在當前中國工廠中代加工和山寨的被稱為“包浩斯”的家具,同任何被稱為其他名字的家具一樣,圍繞著如何創建品牌並使其脫穎而出的問題,儘管“包浩斯”之名曾經與一種對超越特定風格的普遍性法則的追求緊密相連。
(二)
歷史的“包浩斯”,作為一所由美術學院和工藝美術學校組成的教育機構,被看做是設計史、藝術史的歷史的某一開端。但是我們如果仍然把包浩斯當做設計史的對象去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只能是一種同義反覆。透過闡釋、元闡釋到實踐、社會生產的幾個層次,我們可以將“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的意義推至極限:一切被我們當下稱為“歷史”的,都只是為了成為其自身情境中的實踐,因此它必然是“當代”的實踐。
因此,歷史檔案需要重新歷史化。只有把我們當下的社會條件寫入這一歷史的情境中,不再預設將包浩斯作為已經凝固的歷史檔案和歷史經典,這一“寫入”才可能成為我們與當時的實踐者之間的對話。它是對“歷史”本身之所以存在的真正條件的一種評論。歷史的“包浩斯”不僅是時間線上的一個節點,它已經融入我們當下的情境,或者說,已經構成了當代條件下的包浩斯情境。然而“包浩斯情境”並非僅僅是一個既成事實,當我們與包浩斯檔案在當下這一時間點上再次遭遇時,歷史化將以一種顛倒的方式再次發生,意即歷史的“包浩斯”構成了我們的條件,而我們的當下成為了“包浩斯”未曾遭遇過的情境。
這意味著必須將“當代-歷史”條件的轉變,放置在“當代”包浩斯的視野中,才能更為切要地解讀和譯出那些曾經的文本。歷史的包浩斯提出的目標,“藝術與技術的新聯合”,已經從機器生產、新人構成、批量製造,轉變為網路通訊、生物技術與金融資本的全球新模式。它所處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帝國主義競爭關係,已經擴編為由此而來的向美國轉移的中心與邊緣的關係,以及在國際主義名義下的新帝國主義,或者說由跨越國家邊界的空間、經濟、軍事等機構聯合的新帝國等等。
只有將“當代”看做是“超脫歷史地去承認歷史”,才可能在構築經典的同時,瓦解這一歷史之後的經典話語。包浩斯不再僅僅是設計史、藝術史中的歷史,我們希望通過對其檔案的重新歷史化,將它為所處的那一現代時期的不可能,提供的可能性條件,轉化為重新派發給當前的一部思想的、社會的、革命的歷史。對應於這部歷史,包浩斯研究將是一種具體的、特定的、預見性的設定,而不是一種普遍方法的抽象而系統的事業,後者沉浸在“終會有某個更為徹底的闡釋版本存在”的幻象之中。
(三)
陸續出版於1925至1930年間的“包浩斯叢書”(Bauhausbücher)作為包浩斯德紹時期發展的主要里程碑之一,是一系列富於冒險性和實驗性的出版行動的結晶。叢書由格羅皮烏斯(Walter Gropius)和莫霍利-納吉(Laszlo Moholy-Nagy)合編,一共出版了14本,除了當年包浩斯的教師格羅皮烏斯、莫霍利-納吉、施萊默(Oskar Schlemmer)、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克利(Paul Klee)等人的著作以及師生的作品之外,還包括了杜伊斯堡(Theo van Doesburg)、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馬列維奇(Kasimier Severinovich Malevich)等等這些與包浩斯理念相通的藝術家的論述。此外這套叢書曾經計畫但最終未能出版的,還有立體主義、未來主義以及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等人的文章。
我們於此刻開啟“包浩斯叢書”的翻譯計畫,並不是因為這套被很多學者忽略的叢書是一段必須遵從的歷史。我們更願意將這一翻譯工作看做是促成當下回到設計原點的對話,是適時於這一當下-歷史時間點上的實踐。重新檔案化的計畫是一次沿著他們與我們的主體路線潛行的歷史展示,它試圖在物與像、批評與創作、學科與社會、歷史與當下之間建立某種等價關係。這一系列的等價關係,也是對雷納·班納姆(Reyner Banham)敏感地將這套“包浩斯叢書”判定為“現代藝術著作中最為集中,同時也是最為多樣性的一次出版行動”的積極回應。
當然,這一系列出版計畫,也可以成為面向2019年——包浩斯誕生百年——這一重要節點的令人激動的事件,但是真正促使我們與歷史遭遇並再度進入“包浩斯叢書”的是連線起這百年相隔的“當代-歷史”條件中的行動的“理論化的時刻”。我們以“包浩斯叢書”的譯介為開端的出版計畫,無疑與當年的“包浩斯叢書”一樣,也是一次面向未知的“冒險的”決斷,去論證“包浩斯叢書”的確是一系列的實踐之書、關於實踐的構想之書、關於構想的理論之書——同時去展示它在自身的實踐與理論之間的部署,以及這種部署如何對應著它刻寫在文本內容與形式之間的“設計”。
與這一“理論化的時刻”相悖的是,現實中的對包浩斯歷史的研究方案已經被隔離在各自分屬的專業領域,這與當年包浩斯圍繞著“秘密社團”展開的總體理念愈行愈遠。如果我們將當下的出版視作再一次的媒體行動,那么關於出版的計畫就是媒體行動的媒介,在行動發生之前就對既有邊界發起拷問。媒介-歷史學家伊尼斯(Harold A. Innis)曾經認為他那個時代的大學體制對知識進行分割肢解的專門化處理是不光彩的知識壟斷,“科學的整個外部歷史就是學者和大學抵抗知識發展的歷史”。這一情形在我們當前所處的時代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扭轉,正是學科專門化的弊端,令包浩斯的成果在今天被切割、分派進建築設計、現代繪畫、工藝美術等領域。而“當代-歷史”條件中真正的寫作,應當向對話學習,讓寫作成為一場場的論戰,並相信只有在所有題材的多方面相互作用中,真正的“發現”與“洞見”才可能產生。正是在此意義上,“包浩斯叢書”被我們視作“歷史”中的一次寫作的典範,成為支撐我們這一系列出版計畫之核心的“基礎課程”。
(四)
“理論化的時刻”並不是把可能性還給歷史,而是要把歷史還給可能性。只有在當下社會生產的可能性條件的視域中,才有了“歷史”的發生,否則人們為什麼要關心歷史還有怎樣的可能?持續的出版,便是持續地回到包浩斯的發生、接受與再闡釋的雙重甚至是多重的時間中去。全球化的生產帶來的物質產品的景觀化,新型科技的發展與技術潛能的耗散,藝術形式及其機制的循環與往復,地緣政治與社會運動的變遷,風險社會給出的承諾及其破產,以及看似無法挑戰的硬體資本主義的神話等等,這些新的命題很可能正是“當代-歷史”條件中包浩斯情境的多重化身。
多重的可能的時間,以一種共時的方式降臨中國,全面地滲入並包圍著人們整個的日常生活。正是“此時”的中國,提供了比新自由主義的普遍地形更為複雜的空間條件,讓此前由諸多理論描繪過的未來圖景,逐漸失去了針對這一現實的批判潛能。這一當代的發生是政治與市場、理論與實踐奇特綜合的正在進行時,亟需尋求新的開端。因此,“此地”的中國不僅是在全球化狀況中重演的某一個區域版本,它劇烈地感受著全球資本與媒介時代的共同焦慮,同時更是反思從特殊性通往普遍性的更為敏感的出發點,是由不同的時空混雜出來的從多樣的有限到無限的行動點。時間的配置激發起空間的鬥爭,撬動著藝術與設計及對這二者進行區分的根基。
辯證的追蹤,是識得這些多重化身的必要之法。比如,格羅皮烏斯在《新建築和包浩斯》(The New Architecture and the Bauhaus ,1935)開篇中強調通過“新建築”恢復日常生活中使用者的意見與能力。如今社會公眾的這種能動性已經不再是他當年所說的有待被激發起來的興趣,而是對應於更多的參與和自己動手的需求,並且目前看來,似乎參與和DIY的需求已經如此的多樣,無須再加以激發。然而真正由此轉化出的當代問題是,在一個已經被分隔管制的消費社會中,或許被多樣的需求製造出來的諸多差異恰恰導致了更深的受限於各自技術分工的眼與手的分離。
再如,格羅皮烏斯1927年為無產階級劇場的倡導者皮斯卡托制定的總體劇場方案,在歷史中未曾實現,而當前的“總體劇場”已經衰變為景觀自動裝置的隱喻。觀眾與演員之間的舞台幻象已經打開,劇場本身的邊界卻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放。現代性發生的時期,藝術或多或少地運用了更為廣義的設計技法與思路,而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的論述中,藝術的生產更趨於商業化,商業則更多地吸收了藝術化的表達手段與形式。精英文化堅守的、與大眾文化對抗的界線事實上已經難以分辨。作為超級意識形態的資本提供的未來幻象——在樣貌上甚至沿襲現代主義的某些總體想像——早已藉助專業職能的技術培訓和市場運作,將分工和商品作為現實的根本支撐,朝著截然相反的方向運行。它並非將人們監禁在現實的困境中,而是對每個人所從事的專業領域中的想像加以控制,將其安置在單向度發展的進程軌道上,例如在狹義的設計機制中自詡的創新,以及在狹義的藝術機制中自慰的批判。
(五)
當代-歷史條件中的包浩斯,讓我們回到已經被各自領域的大寫歷史遮蔽的原點。這一原點是對包浩斯情境中的資本、商品形式以及之後的設計職業化的綜合反思,它或許將有助於研究者們超越對設計產品的僅僅拘泥於客體的分析,超越以運用為目的的操作性批評,超越缺乏技術批判的陳詞濫調和固守進步主義的理論空想。“包浩斯情境”中的實踐曾經是這樣一種打通,它連線起巴迪歐(Alain Badiou)所說的構成政治本身的“沒有部分的部分”的兩面:一面是未被現實政治計入在內的情境條件,另一面是未被想像的“形式”。這裡所指的並非是通常意義上的形式,而是一種新的思考方式的正當性。
在包浩斯當年的宣言中,人們可以感受到一種振聾發聵的烏托邦情懷:“讓我們建立一個嶄新的行會,其中工匠與藝術家互不相輕,亦無等級隔閡。讓我們共同創立新的未來大廈,它將融建築、雕塑和繪畫於一體。有朝一日它將從成百萬工人手中矗立起來,猶如一個新的信仰的晶瑩的象徵物升向天國。”
除了第一句中指出了技術與藝術的連線之外,它描繪的是“當代”版本的面向上帝神力的建造事業:從諸多藝術手段融為一體的場景,到出現在宣言封面上由費寧格(Lyonel Feininger)繪製的那一座蓬勃的教堂,跳躍、鬆動、並不確定的“當代”意象,賦予了包浩斯更多神聖性的色彩,超越了通常所見的烏托邦藍圖。它超越了僅僅對一個特定時代的材料、形式、設計、藝術、社會做出更多貢獻的願望,而是“有朝一日”,社群與社會的連線將要掀起的運動:一場以崇高的感性能量為支撐的促進社會更新的激進演練,它選擇“晶體”作為閃現著全人類光芒的、面向新的共同體信仰的喻示。我們更願意相信曾經在整個現代主義運動中蘊含著的突破社會隔離的能量,同樣可以在當下的時空中得到有力的釋放。
包浩斯初期階段的一個“作品”,也是格羅皮烏斯的作品系列中最容易被忽視的一個“作品”,布拉克豪斯佐默費爾德(Blockhaus Sommerfeld,佐默費爾德的小木屋),它是“包浩斯第一個集體工作的真正產物”。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對它的重新肯定,將“建築的本源應當是怎樣的”這一命題,從物的實證引向了對觀念的回溯。我們從此類對包浩斯的再認識中,看到了一種我們深為認同的觀點,即歷史的包浩斯,不僅如通常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是對機器生產的時代回應,更是對機器生產時代的超越和反思。我們回溯歷史,並不是為了在現有的歷史框架中去取證包浩斯遺留給我們的物件,恰恰相反,繞開它們去追蹤包浩斯之情境,方為設計之道。我們回溯建築的歷史,如同一次命運的救贖,正如里克沃特在別處所說的,任何公眾人物如果要向他的同胞們展示他所具有的“美德”(virtues),那么,建築學就是他所必須賦予他的命運的一種救贖。我們在此引用這句話,並非為了作為歷史的包浩斯而抬高建築學,而是將美德與命運聯繫在一起,將個人的行動與公共性聯繫在一起,方為設計之德。
(六)
阿爾伯蒂將“美德”理解為在與市民生活和社會有著普遍關聯的事務中進行的一些有天賦的實踐。如果我們並不強調設計者所謂天賦能力或素養,而是將設計的活動放置在“開端的開端”,那么我們有理由將現代性的發生與建築師的命運推回到文藝復興時期。當時的“美德”綜合了上述的設計之道與設計之德,消除了它的“道德”表象。它意指卓越與慷慨的行為,一種賦予形式從內部的部署向外延伸的行為,它將建築師的意圖和能力與“上帝”在造物時的目的和成就,以及社會的人聯繫在一起。
正是對和諧的關係的處理,使得建築師自身進入了社會,但是,這裡的“和諧”必然是一種新的運動,甚至與它字面意義相反,在包浩斯時期的和諧已經被“構型”(Gestaltung)所替代。包浩斯的命名及其教學理念結構圖中居於核心位置的“BAU”暗示我們,正是所有的創作活動圍繞著“建造”展開,才得以清空歷史中的“建築”,進入到當代-歷史條件中的“建造”。因此,建築師是這樣一種“成為”(becoming),他重新建構而不是維持某種關係,他進入社會,將人們聚集在一起;同時他的進入,必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進入社會現實,而是面向“上帝”之神力並擾動著現存秩序的“進入”。這一“進入”,在包浩斯整個集體工作的理念中,很容易理解:教師與學生在工作坊中儘管處於合作狀態,但是教師決不能將自己的方式強加於學生,而學生的任何模仿意圖都會被嚴格禁止。
包浩斯的歷史檔案不只作為一份探究其是否被背叛了的遺產,用以糾偏“我們”的行為。它被吸納為“我們”的歷史計畫,這意味著如塔夫里(Manfredo Tafuri)所言“透過一個永恆於舊有之物中的概念之鏡頭,去分析現況”。作為當代-歷史條件中的“政治”,作為已展開在當代的“歷史”,它是人類現代性的發生以及對社會更新具有遠見的總歷史中一項不可或缺的條件。它不斷地被打開,又不斷地被關閉,正如它自身及其後繼機構的歷史命運那樣,但是,或許只有在這一基礎上,對包浩斯的評介及其召喚出來的新研究,才可能將此時此地的“我們”捲入面向未來的反思與實踐。
我們需要用包浩斯的方法去批判包浩斯,這是一種既直接又理論的實踐。從拉斯金(John Ruskin)到莫里斯(Wilhelm Morris),都想讓民眾互相聯合起來,人人成為新設計師;格羅皮烏斯,想讓設計師聯合起大資本家,做出新人;而漢斯·梅耶(Hans Meyer),想讓設計師聯合起民眾,做出新社會……每一次對前人的轉譯,都是正逢其時的斷裂。而缺失了作為新設計師、新人、新社會夢想之前提的“聯合”,所謂“創新”至多只能強調出個體差異之“新”,它只能讓當前的設計師淪為將自身的道德與善意轉化為公共展示的群體。在包浩斯百年之後的今天,對包浩斯的批判性“轉譯”,是對正在消亡中的包浩斯的雙重行動,這樣一種既直接又理論的實踐似乎與建造沒有直接的關聯,然而它所關注的重點正是,新的“建造”將由何而來?
(七)
柏拉圖認為,“建築師”在建造活動中唯一的當務之急是實踐——當然,我們今天應當將理論的實踐也包括在內——在柏拉圖看來,那些諸如表現人類精神、將建築提到某種更高精神境界等等的毫無技術和物質介入的決斷,並不是建築師們的任務。在這個意義上,建築是人類嚴肅的需要和非常嚴肅的性情的產物,並通過人類所擁有的最高價值的方式去實現。也正是因為恪守於這一“嚴肅”與最高價值的“實現”,他將草棚與神廟視作同等,二者間只存在量上的區別,並無質上的不同。我們可以從這一“嚴肅”的行為開始,去打通已被隔離的“設計”領域,而不是利用從包浩斯的歷史遺物中論證出來的“設計”美學,去連線湯勺與城市。
柏拉圖把人類所有創造“物”並投入到現實的活動,統稱為“人類修建房屋,或更普遍一些,定居的藝術”。但是投入現實的活動並不等同於通常所說的實用藝術,恰恰相反,他將建造人員的工作看成是一種高尚而與眾不同的職業,將其置於更高的位置。這一意義上的“建造”,是建築與政治的聯繫,甚至正因為“建造”的確是一件嚴肅得不能再嚴肅的活動,必須不斷地爭取更為全面包容的解決方案,建築才可能成為一種精彩的“遊戲”。
由此我們可以這樣去理解“包浩斯情境”中的“建築師”,因其“遊戲”,它遠非當前職業工作者陣營中的建築師,因其“嚴肅”,它也不是指職業者的另一面,所謂刻意的業餘或民間,或加入藝術陣營中的建築師。誠如塔夫里所指出,包浩斯以及勒·柯布西耶等人在當時並非努力模仿著機器的表象,而是抽身進入機器背後的法則之中。當下的“建築師”,如果仍願選擇這種態度,則要抽身進入媒介的法則中,抽身進入諸眾之中,將就手的專業工具當做可改造的武器,去尋找和激發某種共同生活的新紋理。這裡的“建築師”,位於建築與建造之間的“裂縫”,它真正指向的是:超越建築與城市的“建築師的政治”。
超越建築與城市(Beyond Architecture and Urban),是為BAU,是為“BAU叢書”之序。
王家浩
2013年10月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