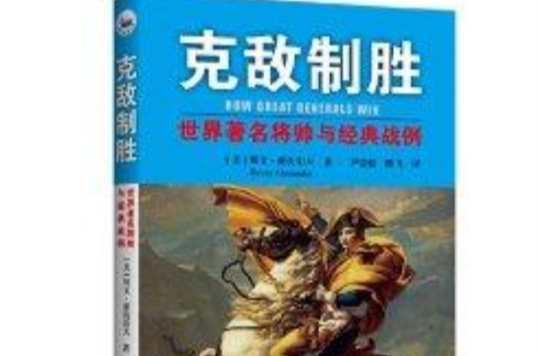本書蒐集了漢尼拔、成吉思汗、拿破崙、“石壁”傑克遜、謝爾曼、隆美爾、麥克阿瑟等人類歷史上最著名將帥的經典戰例。他們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展示出了非凡的戰略和戰術天才。作者深入分析了軍事領域中高明者與平庸者迥異的心態。偉大的將帥通常高瞻遠矚、出其不意,擁有獨特的個人魅力和強大的心理戰能力。中國著名戰略家孫子於公元前200年寫道:“兵者,詭道也”。本書將向我們闡明不同時代的領導人是如何理解這一點的,以及它為什麼在今天仍舊是真理。
基本介紹
- 書名:克敵制勝:世界著名將帥與經典戰例
- 作者:貝文·亞歷山大 (Bevin Alexander)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4年6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16609958
- 外文名:How Great Generals Win
- 譯者:尹宏毅
- 出版社:新華出版社
- 頁數:254頁
- 開本:16
- 品牌:新華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90年代暢銷書再版,更新了戰場地圖和將帥肖像,生動再現了古今中外的經典戰例,及其背後的制勝策略。
作者簡介
貝文‧亞歷山大(Bevin Alexander),美國著名軍事歷史學家、軍事戰略專家,任教於維吉尼亞大學,專門從事各類戰爭史研究,著有戰爭作品《朝鮮,我們第一次戰敗》《美國國內戰爭》《克敵制勝》等近十部作品。
圖書目錄
前言
序言:戰爭的規則雖然簡單,但是很少得到遵守
第1章打敗漢尼拔的將軍
第2章蒙古人的奧秘:速度和詭計
第3章拿破崙和殲滅戰
第4章石壁”傑克遜:“迷惑、引入歧途和出其不意”
第5章謝爾曼:贏得南北戰爭勝利的將軍
第6章1918年的巴勒斯坦戰役:打破塹壕戰的僵局
第7章毛澤東:贏得中國
第8章1940年的法蘭西戰事:出奇制勝
第9章沙漠之狐”隆美爾
第10章麥克阿瑟:在韓戰中表現出兩重性的人物
第11章戰爭的持久統一性
序言:戰爭的規則雖然簡單,但是很少得到遵守
第1章打敗漢尼拔的將軍
第2章蒙古人的奧秘:速度和詭計
第3章拿破崙和殲滅戰
第4章石壁”傑克遜:“迷惑、引入歧途和出其不意”
第5章謝爾曼:贏得南北戰爭勝利的將軍
第6章1918年的巴勒斯坦戰役:打破塹壕戰的僵局
第7章毛澤東:贏得中國
第8章1940年的法蘭西戰事:出奇制勝
第9章沙漠之狐”隆美爾
第10章麥克阿瑟:在韓戰中表現出兩重性的人物
第11章戰爭的持久統一性
序言
我對高明的將帥們如何決勝的理解,是從認識到平庸的將帥們何以不勝開始的。這個了解過程始於1951年8月炎熱的一天;那時我擔任美國陸軍第五戰史小分隊的指揮官,正站在韓國東部太白山的一個山谷中,目睹美軍炮火轟炸我面前大約1000碼(914.4米)處的983高地。
這座山峰和它北面緊靠的一座相似的山峰那時還沒有獲得其名字——“流血嶺”和“傷心嶺”。在那個夏日裡,站在那裡目睹炮彈消滅983高地上的所有植被痕跡的我們,已經知道即將發生什麼事情。
這次攻擊將是正面的——直接地沿陡峭的山坡而上,升至海拔3200英尺(975.36米)。這次進攻還將是意料之中的:炮兵部隊在山南的大量集結使北韓防守者們知道,駐朝美軍最高指揮官詹姆斯·范弗利特少將選中了他們的防禦陣地作為襲擊目標。
因此,這場令人毛骨竦然的戰爭,以及緊接著發生的爭奪“傷心嶺”的更加可怕的戰鬥,從一開始就是按計畫進行的,好像拿到了一個劇本,準確地照著它演出一樣。
美軍的炮火摧毀了山上所有的植被,但對共軍士兵在其中隱藏的,被泥土、岩石和木料掩蓋著的掩體,破壞卻很少。然後,美國、韓國——在“傷心嶺”上還有法國——的步兵沿著羊腸小道攀登險峰,因為這是唯一的路徑。北韓和中國的士兵們像聯合國軍一樣熟悉這些上山的道路,他們將其自動武器和迫擊炮的火力集中對準這些小徑,造成一片火海,以大量殺傷登山的聯合國軍步兵。
一切都像計畫好的一樣進行——聯合國軍的優勢火力終於使這些山峰從共軍手中被奪取過來——但是,代價是驚人的。聯合國軍的傷亡—一主要是美國人——總計為6400人,而共軍的損失可能達到了4萬。儘管如此,聯合國軍司令部一無所獲。它在朝鮮的戰略地位絲毫也沒有提高,在戰術上也幾乎沒有獲得任何好處:在“傷心嶺”後面聳立著另一座同樣布滿掩體的山嶺。它的背後屹立著許多其它的這種山峰,它們都可以由掩體來武裝。
這兩場令人傷心的流血廝殺,以及駐朝美國陸軍第八集團軍於1951年秋季下令進行的爭奪制高點的所有多次戰鬥的唯一收穫是,美軍司令部終於認識到,對嚴陣以待的共軍陣地發動正面進攻是徒勞的。對這項政策之魯莽的認識用不著什麼大徹大悟。原因很簡單:再發動這樣的攻擊代價太高。在從7月間“和談”開始到1951年10月底爭奪制高點的進攻停止的這段時間裡,聯合國軍傷亡達到6萬人,共軍的傷亡估計為23.4萬人。
汲取這樣一個明顯的教訓非要經過這樣的大流血不可,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從有組織的戰爭初次發生起,對有準備的防禦工事發動的正面攻擊通常就是失敗的;這個事實在軍事史書中醒目地寫著,所有將領都可以看到。更為切題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塹壕戰——韓戰的這一階段對此進行了幾乎絲毫不差的模仿。說它更為相干,是因為它是朝戰中高級將領們的現役經歷或培訓內容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為正面進攻蓋棺定論,表明它是不能成功的,除非付出大量傷亡的代價,以致於“勝利者”一詞變得帶有嘲諷意味,因為在西部前線上兩軍對壘時與死神的約會中,沒有任何贏家。
但是,人們並沒有汲取這一教訓。正是那些目睹過或者研究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塹壕戰的人們,在韓戰中又一次下令這樣做。這種做法在朝戰中的結果與在歐戰中的結果是相同的:人員損失慘重,戰術或戰略上的效益卻很小。
我從“流血嶺”和“傷心嶺”戰鬥中所領教到的一點是,高明的將帥們不像朝戰中下令爭奪山嶺的將帥們那樣行事。高明的統帥不重蹈前人的覆轍。他們不把部隊投入敵人嚴陣以待的戰鬥。恰恰相反,高明的統帥們出其不意,專攻敵人力量虛弱和組織薄弱的地方。
韓戰以來,軍事技術上的巨大進步並沒有改變這個基本的真理。技術只決定著我們採用什麼方法實現軍事決策。武器的改進實際上使統帥們更需要避開有重兵把守的危險陣地,尋求在敵人沒有預料到會遭到打擊的地方決戰。
特別是從越南戰爭以來,由於採用衛星精確導航和利用雷達、紅外線、雷射和其他探測裝置引導“智慧型”炸彈和飛彈打擊目標,火箭和常規(非核)武器的命中精度和殺傷力驚人地提高了。這種技術進步帶來了一種預言,即未來戰爭將在“自動化戰場”上展開,武器將會十分有效,以致人員在戰場上將無法倖存,戰鬥將由機器人和各種無人操縱的飛機、車輛和武器來進行。
但是,有一股重要的逆反潮流,它預示著戰爭將較少地依賴占壓倒優勢的火力,而較多地依靠隱蔽的小部隊的行動;這種小部隊通過出其不意、伏擊和難以預料的調動實現其目標。
戰爭之所以可能正朝著這個貌似矛盾的方向轉變,是因為產生了主戰坦克、攻擊機、戰艦和火箭的技術,也造就了能夠摧毀許多這種進攻性武器的武器。防禦性武器比進攻性武器要廉價得多。其中有些武器一個人即可操縱。20世紀80年代蘇聯干預阿富汗期間,阿富汗用來擊落直升飛機的高效“毒刺”式飛彈就是這類武器。“愛國者”飛彈在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中摧毀了伊拉克的“飛毛腿”飛彈,並能夠摧毀攻擊機;而其造價只有一枚“飛毛腿”飛彈價格的很小一部分,僅占一架戰鬥轟炸機的1%左右。
如果像技術專家們所認為的那樣,坦克已經過時,有人駕駛的飛機和大型戰艦造價太高,結構太複雜而且太容易受到打擊,因而在防禦性飛彈面前無法長期倖存,那么未來的戰爭可能很少由無人操縱的武器和機器人在“自動化戰場”上打,而較多地依靠分散的、訓練有素和武器精良的小部隊來打;它們狡詐地悄悄繞過障礙,其戰略戰術就像我們今天對游擊或半游擊力量所聯想的那樣。蘇聯在阿富汗輸掉了這樣一場戰爭。
人類不大可能訴諸於核戰爭。任何採用核彈的做法都將立即招致核報復;這種報復可能愈演愈烈,超過人類所能控制的程度,使得地球的絕大部分地方無法居住。沒有任何明智的統治者想要給自己的人民判死刑。即使一個瘋狂的獨裁者弄到一個核裝置並使用它,理智的世界領導人也幾乎肯定會採取徹底解決的辦法,消滅他和他的科學家們,而不會甘心遭受核毀滅。
我們這一代是看不到未來了。但是未來戰爭中大概將遇到統帥們從有武裝衝突以來一直遇到的難題:怎樣避開敵人的主力,以及如何給敵人以決定性打擊。戰爭將發生變化,但是戰爭的原則將保持不變。
英格蘭戰略家哈特說,高明將帥的目標與3000年前的希臘傳說的特洛伊戰爭中的帕里斯的目標是一樣的。帕里斯在與希臘大鬥士阿喀琉斯的戰鬥中避實就虛,把箭射向阿喀琉斯的唯一弱點,即他的腳跟。
美國南北戰爭中南方軍中傑出的騎兵指揮官弗里斯特概括了高明統帥的奧秘,他說,獲勝的訣竅是“率領最多的力量捷足先登”。
然而,對高明統帥的真正考驗範圍比這要廣泛:是判斷弱點在哪裡,在哪裡才能找到阿喀琉斯的腳跟。因為成功的指揮官集中力量打擊的地方一定是敵人的要害部位。要想捷足先登,軍事指揮者必須明白和實踐另外一位偉大的南軍領導人“石壁”傑克遜的目標——使敵人“迷惑、誤入歧途和猝不及防”。
因為沒有任何聰明的敵方指揮官願意暴露自己的要害部位。他只有在被迫或受騙上當的情況下才會這樣做。為實現這種強迫或迷惑,高明的統帥幾乎總是以兩種方式之一行事。他調兵遣將,以使敵方統帥以為他瞄準的是另外一個部位。抑或用美國南北戰爭中的北方軍隊最偉大的統帥謝爾曼的話來說,他將使敵方指揮官“左右為難”,無力守衛兩個或更多的地點或目標,因而被迫為保住一地而起碼讓出另外一地。
縱觀全部歷史,有關高明統帥的引人注目的事實之一就是,除非在擁有壓倒優勢的情況下,他們的成功行動都是對敵人的側翼或後部採取的,不是實際上就是在心理上。高明的統帥認識到,攻敵後部使之分散精力、猝不及防,往往使敵人潰敗,因為敵人的給養、通信和增援被切斷,從精神上講,其信心和安全感也被大大削弱。另一方面,高明的統帥們知道,正面進攻使敵人的防禦力量得到鞏固,即使被擊潰,也只不過迫使它退到後備力量和供應所在地。
長期以來,這些概念在許多軍隊中被普遍接受。用來對付一個虛弱或不勝其任的敵人,它們採用起來是得心應手的。例如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美國陸軍上將施瓦茨科普夫採用這一經典理論,在100小時內打敗了擁有50萬人的伊拉克軍隊。他以從海上發動一次兩棲入侵相威脅,並派遣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兩個師和另外一些兵力正面進攻科威特,從而使侵入科威特的伊拉克軍隊主力滯留原地;與此同時,派遣兩個機動軍團西進差不多200英里,進入阿拉伯沙漠。這兩支部隊繞到伊軍後方,切斷其供應線和通向巴格達的退路,將其逼人幼發拉底河、波斯灣和南來挺進的海軍陸戰隊之間的一個狹窄的角落中。伊軍數以千計地投降,抵抗力崩潰。
並非所有戰爭都像1991年的海灣戰爭那樣一邊倒;敵人也並非都這樣願意投降。戰爭中最難以估計的就是人的抵抗力。由於敵人的反應無法預料,普通平庸的統帥們往往不了解側面或後部進攻的全部重要性;此外,通常由於敵人的頑強抵抗,統帥們不由自主地採取直截了當的戰略和正面進攻,而這種做法很少具有決勝意義。
高明的統帥之所以高明並且罕見,一個因素就是他能夠頂住大多數部下的要求,不急急忙忙地正面交戰,並且能夠認識到怎樣才能避實就虛地打擊敵人。
這種將領所以難得,一個原因是軍界像整個社會一樣,讚賞直截了當的解決辦法,對不直接和不熟悉的方法持懷疑態度,給它們戴上狡詐、不誠實或偷偷摸摸的帽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人之所以憎恨日本人,一大原因是日本人對夏威夷的珍珠港這個始料未及的地點發動“偷襲”。軍界和公眾普遍認為,只有光明磊落地面對敵人的、直截了當的英雄的“好漢”美德才是理想的。這種英雄在美國西部的牛仔身上被浪漫化了,他一直等到對手已經伸手掏槍時才掏出自己的六響左輪手槍。
幾代軍人一直把戰爭比喻為體育。惠靈頓伯爵說,滑鐵盧之戰是在伊頓公學的體育場上打贏的。在當今的美軍中,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就是把戰爭同美式橄欖球畫等號。這並非偶然。橄欖球——而不是棒球——成了戰爭的象徵,因為橄欖球主要包括進攻者對防守者的直接挑戰。同棒球相比,它肯定不是一種採用微妙伎倆、出奇制勝和施展詭計的運動項目,儘管橄欖球也能具有避實擊虛的方面。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美軍的理論很像20世紀中葉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學進行的這種“三碼和一股塵煙”的、直截了當的實力競賽。雖然從那時以來,教學重點已經轉向運動戰,但是直接的解決辦法和正面攻擊在軍界的心理中根深蒂固,很難根除。
真誠、坦率、光明磊落的領導人一直是人們的理想。因此,成功的高明統帥必須具有兩面性格,一方面向部下表現出誠實和公開性,另一方面隱藏或掩蓋品格中得以使敵人“迷惑、誤人歧途和猝不及防”的部分。
一些高明的統帥發現這是一項艱難的任務,並在執行過程中吃了許多苦。“石壁”傑克遜就因守口如瓶,不願把計畫告訴部下而臭名遠揚。雖然他的士兵因他給他們帶來勝利而崇拜他,但是他們認為他很古怪、不平易近人,他的主要上司們認為他難以共事、苛求、不善於溝通。他對這些指責的回答令人很受啟發:“如果我能瞞過我的朋友們,我就能確保瞞過敵人。”
能夠表現出高明統帥所必須具備的兩面矛盾人格的人寥寥無幾。此外,軍隊中的體制也往往使直率的人比胸有城府的人較多地獲得提升。因此,大多數將帥是老實厚道的、單純的武士,率眾發動硬拼的戰役,下令從正面進攻。他們所造成的成為大多數戰爭特點的慘重傷亡和久攻不下是預料之中的。
就連一些德高望重的統帥實際上也是胸無城府的軍人,並且給自己一方帶來災難。羅伯特·E·李就是一位這樣的統帥——南部邦聯心目中十全十美的人物。他極為正直,有正義感和忠誠;作為一名指揮官,他的能力也遠遠超過與他對陣的北方軍將領。但是,李自己並不是一位高明的統帥。
李在正常的和十分關鍵的情況下總是選擇直接硬拼的做法,而不是避實就虛。例如,當1862年攻占馬里蘭州的行動流產時,李並沒有迅速撤回到維吉尼亞州,而是任憑自己捲入發生在安蒂坦的一場正面對抗。他沒有絲毫希望獲勝。這場戰鬥成為美國歷史上流血最多的一場戰鬥。由於南方邦聯在兵力上同北方相比處於嚴重劣勢,所以這種傷亡很大的血戰只有在爭取戰略上的巨大好處的時候才應當進行。堅守安蒂坦是徒勞無益的,而撤退到維吉尼亞會保住南方的進攻力量。安蒂坦之戰還使林肯獲得了他發表解放黑奴的宣言所需要的北方勝利,從而確保英法兩國不會援助南方邦聯。
1863年,李任憑自己捲入了一場相同的消耗戰。當李靠直接硬拼擊潰聯邦部隊的努力失敗後,他一錯再錯,使北維吉尼亞軍的最後一點進攻實力在穿越將近一英里彈坑累累的開闊地的皮克特衝鋒中被摧毀。這場正面進攻在開始之前就注定要失敗。朗斯特里特等將領認識到這一點,李本人在戰鬥災難性的結尾時也承認了失誤;而此時衝鋒的1.5萬名士兵當中只有一半回到南方邦聯的陣地。
但是,當李在葛底斯堡與波托馬克聯邦軍遭遇時,他的處境並不危險。他當時位於聯邦軍的北面;由於在這一方向上的給養比撤回到維吉尼亞要多得多,所以他本來能夠不費吹灰之力就衝破聯邦軍的阻攔,攻占哈里斯堡或約克,從而在一個方向上威脅費城,在另一方向上威脅巴爾的摩,在第三個方向上威脅華盛頓。倘若波托馬克軍的主力撤退回去守衛首都,李本來可以沿薩斯奎哈納河向東南挺進,威脅費城或巴爾的摩。假如聯邦軍司令米德按兵不動,守衛華盛頓,李本來可以攻占巴爾的摩。那裡是通往北方的所有鐵路線的匯聚點,因而他本可切斷華盛頓的增援和給養。如果米德出兵保衛巴爾的摩,李可以渡過薩斯奎哈納河,奪取費城。費城當時是美國第二大城市,對北方來說,失去它會是一場災難。
另外一位很有名氣但幾乎輸掉南北戰爭的統帥是北方的尤利塞斯·S·格蘭特。在1864年的維吉尼亞戰役中,格蘭特一次又一次地將其軍隊投人對嚴陣以待的南方邦聯軍隊的正面進攻中。格蘭特的目的是要摧毀李的部隊,但他差一點毀掉自己的軍隊,從春季的野戰到仲夏的彼得斯堡僵局為止,他損失了自己全部實力的一半。到這次戰役後期,格蘭特的部隊不再願意竭力進攻了,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會被打敗。的確,在冷港,聯邦軍的士兵們確信自己必死無疑,因而在衝鋒之前把自己的名字和住址貼在軍裝背後,以便家人在戰鬥結束後能夠得到通知。
格蘭特唯一的戰略成功不是靠戰鬥,而是靠部隊的轉移獲得的。他渡過詹姆斯河,逼近南方供給里奇蒙給養的主要鐵路,因為他沒有再次直接硬拼,而是決定悄悄渡過詹姆斯河,使敵人猝不及防,攻占彼得斯堡。他幾乎失敗;維吉尼亞的戰爭出現僵持局面;是謝爾曼,而不是格蘭特,通過襲擊南軍的尾部打破了這一僵局。
類似於李和格蘭特行動思路的直接行動促使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德軍司令毛奇破壞了謝里芬伯爵的著名計畫,即派遣德軍主力“迂迴”到巴黎西面和南面。這個德軍主力之“錘”按計畫將回到北面,利用位於法德邊境上的堡壘之中的德軍之“砧”粉碎法軍和英軍。毛奇放棄橫渡塞納河的迂迴包抄,而是在河北面發動正對巴黎的直接進攻。這使法軍得以阻止德軍的前進道路,制止德軍的進攻,造成持續到1918年的塹壕戰僵局,從而創造“馬恩奇蹟”。
1942年年底,希特勒堅持主張正面進攻史達林格勒,而不是在還來得及的時候撤走德軍,結果使一支龐大的德國軍隊毀於一旦,並失去了在東線的主動地位,最終將戰爭輸給了俄國人和其他盟國。
本書旨在利用具體實例表明,以往的高明統帥們如何套用由來已久的戰爭規則和原理而制勝,即使只不過因為他們搶在對手前面運用了它們。這些規則不是像代數公式那樣需要機械地照搬的方法,而是必須技藝高超地看情況而套用的概念。它們不是只有軍事專家和軍事指揮及參謀學院的高年級學生才能懂得的、深奧的抽象理論,而是兩個國家或國家集團進行殊死的戰爭時用來解決常見問題的對常識的運用。
每個交戰者的目的都是使對手服從他的意志,試圖引誘別人遵照其意願行事。這是適用於個人、集團和國家的很平常的人類宗旨。普通的人類爭端和戰爭的唯一區別在於,戰爭是一方對另一方施加武力的暴力行動。倘若一方不動用武力即能實現其目的,它當然會這樣做,因為除非存在抵抗力量,沒有任何國家會發動攻擊。19世紀普魯士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所下的定義是,戰爭是國家政策通過其他途徑的繼續。 看來可能很明顯的一點是,捲入任何衝突的每個個人、集團和國家都始終應當採用帕里斯在特洛伊戰爭中所採取的策略,只打擊阿喀琉斯的腳跟。但是,戰爭和人際關係的歷史結論性地表明,人類經常忽視或看不到對敵人或對手迂迴包抄的機遇,而是正面打擊他們所看到的最明顯的目標。
人們並不經常實際或比喻陛地迂迴到其對手的後面去。經過100萬年的文化薰陶,人類已經習慣於在一個集團中合作。這種薰陶使得我們忠誠於自己的集團,對自己集團的敵人採取好鬥態度。不論是與朋友合作還是同敵人鬥爭,我們的趨勢都是直截了當,而不是避實就虛或迂迴包抄。
只有非凡的人才能把與敵人正面對抗的原始欲望,同為使敵人猝不及防和易受打擊而掩蓋或隱藏自己的行動的必要性相分離。但這卻是成為高明統帥的唯一道路。大約在公元前400年,中國著名戰略家孫子寫道:“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孫子還寫到,在戰爭中,“避實而擊虛”。
許多人誤解了戰爭中的真正目的。這一目的並不像眾多軍界和文職領導人所認為的那樣,是在戰場上摧毀敵人的武裝力量。這一簡稱為“拿破崙主義”的觀念在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軍事教科書和規章的編寫和制訂中,以及在參謀學院的教學中,都曾占據主導地位。
拿破崙本人並不是這一理論的始作俑者,儘管正如哈特所指出,它來自於拿破崙在1806年的耶拿之戰以後的做法,即倚仗重兵,而不是依靠機動性;機動性在此之前一直主宰著他的戰略。耶拿之戰後,拿破崙只關心戰鬥,信心十足地認為,短兵相接,他能夠毀滅對手。
拿破崙後來的以純粹進攻實力為基礎的戰役使得早些時候的戰役中可供借鑑之處變得不明顯了;在早期戰役中,拿破崙把詭計、機動性和出其不意結合起來,在節省大量實力的情況下取得巨大戰果。克勞塞維茨對拿破崙後期的戰役印象最深刻,並且成為“大兵團作戰的鼓吹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規模戰鬥上。這一理論適合於普魯士為實現“全民皆兵”目標而大量徵兵的制度。這一觀念在1870至1871年的法普戰爭中獲得勝利,因為普魯士的優勢兵力占據了有利地位。此後,另外一些強國迫不及待地模仿了德國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戰表明,統帥們的廝殺欲望與最新研製出的機關槍使戰爭淪為大規模屠殺。雖然其結果是給歐洲的青年們造成大量傷亡,但是認為戰爭是為了在戰鬥中消滅敵人主力的觀點繼續影響——在許多情況中還指導了——我們的思維,直到今天仍舊是這樣。
但是戰爭的目的根本不是廝殺,而是實現更加完善的和平。要實現和平,戰鬥者必須破壞敵國人民打仗的意志。沒有任何國家為打仗而發動戰爭。它發動戰爭是為了實現國家的宗旨。一個國家要實現這一目的,可能必須消滅敵人的軍隊。但這種毀滅並不是目的,而只不過是達到目的的附帶副產品或者是手段。
倘若一位指揮官研究一下他在戰爭結束時所要尋求的和平,他可能會發現許多這樣的實現和平的途徑,即避開敵人主力,打擊一些目標,從而破壞敵人作戰的願望或能力。第二次布匿戰爭中偉大的羅馬軍隊統帥西庇阿不理睬敵軍,而是出其不意地攻占敵軍大本營、今天的卡塔赫納,從而削弱了迦太基對西班牙的控制。在1814年的拿破崙戰爭末期,盟軍避開他的軍隊,而攻陷巴黎,從而使法國人民喪失信心,放棄努力,迫使拿破崙投降。1864年年底和1865年年初,謝爾曼的軍隊很少打仗,但是卻向喬治亞州和南北卡羅來納州進軍,從而破壞了南方人民打仗的意志,使許多叛軍士兵紛紛開小差回家。
克勞塞維茨懂得,戰爭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軍事性的,並且在其著作中實際表達了這一觀點。但是,他的句法和邏輯晦澀難解,以致從他的著作中獲得靈感的軍人們不大注意他的觀點的限制條件,而較多地注意了他的概括性語句——“流血的解決辦法,摧毀敵軍是戰爭的長子”;“讓我們對有的將領不造成流血就實現征服的論點充耳不聞吧”。克勞塞維茨對作戰的重視顯示出了其理論的一個矛盾。因為假如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中所要實現的目標就是主要目的。但是,克勞塞維茨重視戰爭的勝利,因而只期待著戰爭結束,而不是戰爭結束後的和平。
雖然克勞塞維茨實際上是說,戰爭是達到一國目標的最通常的辦法,但是幾代喜歡正面作戰的軍人未能權衡其論點的矛盾之處,也不能理解其晦澀的論點,因而理解為戰爭是唯一的途徑。
我們現在能夠給軍事戰略或指揮戰爭的目的下定義了。這就是縮小抵抗的可能性。高明的統帥利用運動戰和出其不意等手段消滅或縮小抵抗的可能性。正如孫子所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為實現這一目的,孫子為成功的統帥出謀劃策:“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如果統帥率軍出現在敵人必須迅速前往保衛的地點,那么敵人的精力很可能分散,並且很可能削弱其他地點的防禦力量,或者將其放棄,因而促成自己戰敗,或者使自己失敗無疑。速度和機動性是戰略的基本特點。拿破崙說:“空間我們能夠收復,時間絕對不能。”
在以下的本書各章中,我們將考察像拿破崙這樣高明的統帥們是怎樣實踐戰爭原理的。在這裡簡要概述一些最主要的原理可能是有益的,為的是使高明統帥們的行動易於追蹤。
B·H·利德爾·哈特的兩句格言體現了巨大的軍事智慧。他說:“成功的統帥選擇(敵人)最沒料到的路線或行動方向;他利用抵抗力量最弱的路線。”
雖然這兩則警句聽起來似乎是不說自明的,但是統帥們很少按其行事,在它們被用來對付他們時也不知曉。“流血嶺”和“傷心嶺”之戰是在敵人最預料到的和其抵抗力量最強大的戰線上展開的。1940年5月,當德軍入侵低地國家時,英軍和法軍的指揮官所考慮的只是迅速出兵比利時,以便從正面抗擊他們所認為的德軍主要的、也是正面的進攻。這使德軍得以出其不意,越過“不可逾越的”阿登高原,在色當突破敵人防線。德軍既已迂迴到盟軍背後,便能夠奔向英吉利海峽,沿途所向披靡。類似的,1941年12月,美國領導人預料,敵人將在東印度群島,也許還有菲律賓發動進攻。因此,日軍對珍珠港的空襲使之猝不及防。
成吉思汗及其大將速布台實行了用兵的另外一項原則;這項原則在速布台1241年入侵東歐時得到完美的運用。我們不知道蒙古人對它的稱呼,但是,18世紀初的法軍戰略家皮埃爾·鮑塞獨立地構思了同一原理,稱之為“分進合圍的計畫”。
速布台向歐洲派遣了4支彼此分離的部隊。一支部隊沖人喀爾巴阡山脈以北的波蘭和德國,在那一方向上吸引了所有的歐洲力量。其他三支部隊在相距很遠的不同地點進入匈牙利,威脅若干不同目標,因而使奧地利等國的軍隊無法同匈牙利軍隊聯合。這三支蒙古部隊然後在布達佩斯附近的多瑙河畔會師,以對付現已孤立無援的匈牙利人。
鮑塞建議,將帥們應當將其進攻力量分散成兩支或更多的前進部隊,這些部隊在必要時能夠迅速重新會合,但卻採取威脅多個目標的行動路線,從而使敵人不得不守衛這些眾多目標,被迫分散力量,無法集中兵力。倘若敵人封鎖一條進攻路線,統帥們便能夠立即在另外一條路上形成攻勢,以便為同一目的服務。聯邦軍將領謝爾曼在1864年至1865年的喬治亞和南北卡羅來納進軍中採用了這一方法。他的彼此相距很遠的分進部隊威脅著兩個或更多的目標,使邦聯軍被迫分散力量保衛所有的目標,因而無法守衛任何一個目標。這使叛軍在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戰而放棄保衛兵力薄弱的陣地。
像謝爾曼和速布台一樣,採用“分進合圍計畫”的進攻者往往能夠在敵人作出反應、集中兵力對付他之前將兵力合起來奪取一個目標。一個與此大同小異的做法是部分兵力匯集起來攻擊一個已知目標,而其餘兵力包抄其後部。
在1862年的謝南多厄谷地戰役中,“石壁”傑克遜利用純粹的詭計實施了略加修改的這種計畫;他沿著主要道路正面進攻聯邦軍主力,然後悄悄改變路線,翻越一座高山,出其不意地降臨在聯邦軍側翼和後方。
拿破崙對鮑塞的分進合圍計畫加以發揮,他把單獨挺進的部隊分散得彼此相距很遠,猶如一張沉重的漁網。這些部隊能夠迅速集中起來包圍在路上遇到的任何孤立的敵人。
拿破崙的戰績在很大程度上還歸功於另外一位18世紀法國理論家——吉伯特。吉伯特提倡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以集中優勢兵力攻擊敵人的一個弱點,迂迴到敵人側翼或後方。拿破崙充分利用了機動的戰術,張開一張浮動的大網。這使他的敵人大惑不解,無法揣摩拿破崙的真實目的。他們通常分散自己的兵力,希望反擊拿破崙的迷惑行動。這時拿破崙便迅速集中起其分散的部隊,以便在一支單一敵軍獲得增援之前將其消滅,抑或用自己的全部軍隊猶如神兵天降,打擊敵人的後部。
拿破崙的戰略絕招就是“迂迴包抄,攻其後部”。他的用兵之道體現了孫子的訓諭: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避實擊虛。戰爭的藝術妙就妙在在敵人的弱點上形成強大兵力。
拿破崙增添了一個獲勝的要素,即經常占據敵人後方的優勢地形,譬如一條山脈、峽道或河流,在那裡建立戰略要塞,防止敵人撤退或獲得給養和增援。例如,在1800年的義大利馬倫戈戰役中和導致他於1805年在奧斯特利茨獲勝的烏爾姆戰役中,拿破崙就是利用戰略要塞而獲勝的。到美國南北戰爭時,已經沒有必要奪取有利地形了。軍隊依靠鐵路供給給養和兵源。只要在敵後阻塞一條鐵路線,就能建立一個戰略要塞。1863年,格蘭特將軍在密西西比州的傑克遜就是這樣做的,從而在維克斯堡使南方軍孤立無援。這導致該市的投降、密西西比河向聯邦船隻的開放和南方邦聯失去密西西比河流域各州。
攻敵後方由於一些原因而具有毀滅性。敵人如果被迫改變前線位置,他往往會方寸大亂,無力應戰或降低作戰效率。一支軍隊像一個人一樣,對來自後方的威脅比對前方的威脅要敏感得多。因此,攻其後部容易造成恐懼和混亂。此外,包抄敵後往往打亂敵軍的部署和組織,可能使之彼此分離,威脅其退路並危及給養和增援部隊的運送。一支現代軍隊在沒有食物增添的情況下能夠生存一段時間;但是,在缺乏彈藥和機動車燃料的情況下只能維持幾天。
攻敵後部對敵軍士兵造成嚴重的心理效應。而對敵軍指揮官尤為如此。這樣做往往在敵軍指揮官的心裡造成中計和無力抗拒的恐懼。在極端情況下,這可能會導致敵軍指揮官決策能力的喪失和軍隊的潰敗。
攻敵側翼或後部必須出奇,才能完全制勝。不論戰術、實戰還是戰略,都應遵循這一原理。倘若敵人預料到後方受到攻擊,他往往能夠調兵遣將來應戰,並且通常做好自衛的準備。此外,在一般情況下,只有當敵人被前方其他部隊所牽制而騰不出兵力的時候,或者當他無法及時派兵應付突然襲擊的時候,攻敵後部才能成功。
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沒有充分理解這一原理,戰鬥中損失慘重,以致他幾乎喪失自己的國家。雖然腓特烈總是採取迂迴戰術,但是他的側面和後方攻擊的迂迴路線太短,而且並沒有出其不意。例如,1757年,他發現奧地利軍隊牢固地駐守在布拉格的河畔。他只把少量兵力留下來掩蓋自己的計畫,率軍沿河而上,渡過河去,挺進到奧軍右側。奧軍探知了這一行動,及時改變了前線方位。普魯士步兵試圖越過一個被火力嚴密封鎖的緩坡發動正面進攻,結果成千上萬地倒下。多虧了普魯士騎兵出其不意地到來,才扭轉了敗局。
實戰的基本方案是一場會合式的進攻。指揮官通過把攻擊力量分成兩個或更多部分來達到這一目的。在理想情況下,所有部分都在同一時刻襲擊同一目標,並密切配合,但攻擊的方向或路線卻各不相同,從而使敵軍的所有兵力都疲於應戰,無法相互援助。有時一部分兵力牽制住敵人或分散其注意力,而其他兵力迂迴突襲攻破防線。
一場真正的分進合擊與由一支部隊佯攻或牽制敵人,以分散敵人對主攻的注意力是截然不同的。千百年來,無數的指揮官採取被精明的敵人識破的、明顯是佯裝的行動,以致使自己的希望破滅;抑或試圖打擊的目標很分散,以致敵人的兵力沒有分散,能夠擊退每次攻擊。
一個分進合圍的主要戰例發生在“三十年戰爭”期間的1632年:瑞典的古斯塔弗斯·阿道弗斯架起大炮並點燃秸稈以製造煙幕,同時在巴伐利亞的萊希河上的一點發動進攻,從而使奧地利的蒂利元帥被牽制;與此同時,另外一支瑞典部隊從上游一英里處的一架浮橋上渡過萊希河。在來自兩個方向的同時夾擊下,蒂利無法保衛兩點之中的任何一點。他的軍隊敗退下來,他本人也受了致命傷。
拿破崙的典型作戰計畫是“包圍、突破和擴大戰果”。他發動強大的正面進攻,從而吸引住敵人的注意力,使敵軍全部後備力量都投人戰鬥。這時,拿破崙調遣大軍進攻緊靠敵人給養和撤退路線的敵人側面或後部。當敵人從前線調兵保衛側翼時,拿破崙便在正面主要前線的一個被削弱的部位打開突破口,派騎兵和步兵從此處造成突破,然後用騎兵擊敗和迫擊潰不成軍的敵人。
在韓戰中,挺進中的中共部隊採用了類似的策略。他們把主要的攻擊放在夜間進行。他們的一般計策是出兵攻打敵人陣地的側翼,以切斷其逃跑路線和給養道路。然後,他們在黑暗中發動正面和側面的夾擊,以便與敵人短兵相接。中國部隊一般從幾方包圍一支敵軍小部隊的陣地,直至實現突破,要么消滅之,要么使之被迫撤退。中國人然後悄悄前進,再攻擊下一支小部隊的暴露著的側翼。
偉大統帥們所恪守的原則都不高深難懂。實際上,一旦採用成功,這些原則便暴露出其內在的簡單,看上去很顯而易見,有時還是唯一合乎邏輯的解決辦法。但是,一切偉大思想都是簡單明了的。訣竅在於,要趕在別人前面明白它們。本書所講述的就是高瞻遠矚,在別人之前認識到明顯道理的統帥們的事跡。
這座山峰和它北面緊靠的一座相似的山峰那時還沒有獲得其名字——“流血嶺”和“傷心嶺”。在那個夏日裡,站在那裡目睹炮彈消滅983高地上的所有植被痕跡的我們,已經知道即將發生什麼事情。
這次攻擊將是正面的——直接地沿陡峭的山坡而上,升至海拔3200英尺(975.36米)。這次進攻還將是意料之中的:炮兵部隊在山南的大量集結使北韓防守者們知道,駐朝美軍最高指揮官詹姆斯·范弗利特少將選中了他們的防禦陣地作為襲擊目標。
因此,這場令人毛骨竦然的戰爭,以及緊接著發生的爭奪“傷心嶺”的更加可怕的戰鬥,從一開始就是按計畫進行的,好像拿到了一個劇本,準確地照著它演出一樣。
美軍的炮火摧毀了山上所有的植被,但對共軍士兵在其中隱藏的,被泥土、岩石和木料掩蓋著的掩體,破壞卻很少。然後,美國、韓國——在“傷心嶺”上還有法國——的步兵沿著羊腸小道攀登險峰,因為這是唯一的路徑。北韓和中國的士兵們像聯合國軍一樣熟悉這些上山的道路,他們將其自動武器和迫擊炮的火力集中對準這些小徑,造成一片火海,以大量殺傷登山的聯合國軍步兵。
一切都像計畫好的一樣進行——聯合國軍的優勢火力終於使這些山峰從共軍手中被奪取過來——但是,代價是驚人的。聯合國軍的傷亡—一主要是美國人——總計為6400人,而共軍的損失可能達到了4萬。儘管如此,聯合國軍司令部一無所獲。它在朝鮮的戰略地位絲毫也沒有提高,在戰術上也幾乎沒有獲得任何好處:在“傷心嶺”後面聳立著另一座同樣布滿掩體的山嶺。它的背後屹立著許多其它的這種山峰,它們都可以由掩體來武裝。
這兩場令人傷心的流血廝殺,以及駐朝美國陸軍第八集團軍於1951年秋季下令進行的爭奪制高點的所有多次戰鬥的唯一收穫是,美軍司令部終於認識到,對嚴陣以待的共軍陣地發動正面進攻是徒勞的。對這項政策之魯莽的認識用不著什麼大徹大悟。原因很簡單:再發動這樣的攻擊代價太高。在從7月間“和談”開始到1951年10月底爭奪制高點的進攻停止的這段時間裡,聯合國軍傷亡達到6萬人,共軍的傷亡估計為23.4萬人。
汲取這樣一個明顯的教訓非要經過這樣的大流血不可,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從有組織的戰爭初次發生起,對有準備的防禦工事發動的正面攻擊通常就是失敗的;這個事實在軍事史書中醒目地寫著,所有將領都可以看到。更為切題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塹壕戰——韓戰的這一階段對此進行了幾乎絲毫不差的模仿。說它更為相干,是因為它是朝戰中高級將領們的現役經歷或培訓內容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為正面進攻蓋棺定論,表明它是不能成功的,除非付出大量傷亡的代價,以致於“勝利者”一詞變得帶有嘲諷意味,因為在西部前線上兩軍對壘時與死神的約會中,沒有任何贏家。
但是,人們並沒有汲取這一教訓。正是那些目睹過或者研究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塹壕戰的人們,在韓戰中又一次下令這樣做。這種做法在朝戰中的結果與在歐戰中的結果是相同的:人員損失慘重,戰術或戰略上的效益卻很小。
我從“流血嶺”和“傷心嶺”戰鬥中所領教到的一點是,高明的將帥們不像朝戰中下令爭奪山嶺的將帥們那樣行事。高明的統帥不重蹈前人的覆轍。他們不把部隊投入敵人嚴陣以待的戰鬥。恰恰相反,高明的統帥們出其不意,專攻敵人力量虛弱和組織薄弱的地方。
韓戰以來,軍事技術上的巨大進步並沒有改變這個基本的真理。技術只決定著我們採用什麼方法實現軍事決策。武器的改進實際上使統帥們更需要避開有重兵把守的危險陣地,尋求在敵人沒有預料到會遭到打擊的地方決戰。
特別是從越南戰爭以來,由於採用衛星精確導航和利用雷達、紅外線、雷射和其他探測裝置引導“智慧型”炸彈和飛彈打擊目標,火箭和常規(非核)武器的命中精度和殺傷力驚人地提高了。這種技術進步帶來了一種預言,即未來戰爭將在“自動化戰場”上展開,武器將會十分有效,以致人員在戰場上將無法倖存,戰鬥將由機器人和各種無人操縱的飛機、車輛和武器來進行。
但是,有一股重要的逆反潮流,它預示著戰爭將較少地依賴占壓倒優勢的火力,而較多地依靠隱蔽的小部隊的行動;這種小部隊通過出其不意、伏擊和難以預料的調動實現其目標。
戰爭之所以可能正朝著這個貌似矛盾的方向轉變,是因為產生了主戰坦克、攻擊機、戰艦和火箭的技術,也造就了能夠摧毀許多這種進攻性武器的武器。防禦性武器比進攻性武器要廉價得多。其中有些武器一個人即可操縱。20世紀80年代蘇聯干預阿富汗期間,阿富汗用來擊落直升飛機的高效“毒刺”式飛彈就是這類武器。“愛國者”飛彈在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中摧毀了伊拉克的“飛毛腿”飛彈,並能夠摧毀攻擊機;而其造價只有一枚“飛毛腿”飛彈價格的很小一部分,僅占一架戰鬥轟炸機的1%左右。
如果像技術專家們所認為的那樣,坦克已經過時,有人駕駛的飛機和大型戰艦造價太高,結構太複雜而且太容易受到打擊,因而在防禦性飛彈面前無法長期倖存,那么未來的戰爭可能很少由無人操縱的武器和機器人在“自動化戰場”上打,而較多地依靠分散的、訓練有素和武器精良的小部隊來打;它們狡詐地悄悄繞過障礙,其戰略戰術就像我們今天對游擊或半游擊力量所聯想的那樣。蘇聯在阿富汗輸掉了這樣一場戰爭。
人類不大可能訴諸於核戰爭。任何採用核彈的做法都將立即招致核報復;這種報復可能愈演愈烈,超過人類所能控制的程度,使得地球的絕大部分地方無法居住。沒有任何明智的統治者想要給自己的人民判死刑。即使一個瘋狂的獨裁者弄到一個核裝置並使用它,理智的世界領導人也幾乎肯定會採取徹底解決的辦法,消滅他和他的科學家們,而不會甘心遭受核毀滅。
我們這一代是看不到未來了。但是未來戰爭中大概將遇到統帥們從有武裝衝突以來一直遇到的難題:怎樣避開敵人的主力,以及如何給敵人以決定性打擊。戰爭將發生變化,但是戰爭的原則將保持不變。
英格蘭戰略家哈特說,高明將帥的目標與3000年前的希臘傳說的特洛伊戰爭中的帕里斯的目標是一樣的。帕里斯在與希臘大鬥士阿喀琉斯的戰鬥中避實就虛,把箭射向阿喀琉斯的唯一弱點,即他的腳跟。
美國南北戰爭中南方軍中傑出的騎兵指揮官弗里斯特概括了高明統帥的奧秘,他說,獲勝的訣竅是“率領最多的力量捷足先登”。
然而,對高明統帥的真正考驗範圍比這要廣泛:是判斷弱點在哪裡,在哪裡才能找到阿喀琉斯的腳跟。因為成功的指揮官集中力量打擊的地方一定是敵人的要害部位。要想捷足先登,軍事指揮者必須明白和實踐另外一位偉大的南軍領導人“石壁”傑克遜的目標——使敵人“迷惑、誤入歧途和猝不及防”。
因為沒有任何聰明的敵方指揮官願意暴露自己的要害部位。他只有在被迫或受騙上當的情況下才會這樣做。為實現這種強迫或迷惑,高明的統帥幾乎總是以兩種方式之一行事。他調兵遣將,以使敵方統帥以為他瞄準的是另外一個部位。抑或用美國南北戰爭中的北方軍隊最偉大的統帥謝爾曼的話來說,他將使敵方指揮官“左右為難”,無力守衛兩個或更多的地點或目標,因而被迫為保住一地而起碼讓出另外一地。
縱觀全部歷史,有關高明統帥的引人注目的事實之一就是,除非在擁有壓倒優勢的情況下,他們的成功行動都是對敵人的側翼或後部採取的,不是實際上就是在心理上。高明的統帥認識到,攻敵後部使之分散精力、猝不及防,往往使敵人潰敗,因為敵人的給養、通信和增援被切斷,從精神上講,其信心和安全感也被大大削弱。另一方面,高明的統帥們知道,正面進攻使敵人的防禦力量得到鞏固,即使被擊潰,也只不過迫使它退到後備力量和供應所在地。
長期以來,這些概念在許多軍隊中被普遍接受。用來對付一個虛弱或不勝其任的敵人,它們採用起來是得心應手的。例如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美國陸軍上將施瓦茨科普夫採用這一經典理論,在100小時內打敗了擁有50萬人的伊拉克軍隊。他以從海上發動一次兩棲入侵相威脅,並派遣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兩個師和另外一些兵力正面進攻科威特,從而使侵入科威特的伊拉克軍隊主力滯留原地;與此同時,派遣兩個機動軍團西進差不多200英里,進入阿拉伯沙漠。這兩支部隊繞到伊軍後方,切斷其供應線和通向巴格達的退路,將其逼人幼發拉底河、波斯灣和南來挺進的海軍陸戰隊之間的一個狹窄的角落中。伊軍數以千計地投降,抵抗力崩潰。
並非所有戰爭都像1991年的海灣戰爭那樣一邊倒;敵人也並非都這樣願意投降。戰爭中最難以估計的就是人的抵抗力。由於敵人的反應無法預料,普通平庸的統帥們往往不了解側面或後部進攻的全部重要性;此外,通常由於敵人的頑強抵抗,統帥們不由自主地採取直截了當的戰略和正面進攻,而這種做法很少具有決勝意義。
高明的統帥之所以高明並且罕見,一個因素就是他能夠頂住大多數部下的要求,不急急忙忙地正面交戰,並且能夠認識到怎樣才能避實就虛地打擊敵人。
這種將領所以難得,一個原因是軍界像整個社會一樣,讚賞直截了當的解決辦法,對不直接和不熟悉的方法持懷疑態度,給它們戴上狡詐、不誠實或偷偷摸摸的帽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人之所以憎恨日本人,一大原因是日本人對夏威夷的珍珠港這個始料未及的地點發動“偷襲”。軍界和公眾普遍認為,只有光明磊落地面對敵人的、直截了當的英雄的“好漢”美德才是理想的。這種英雄在美國西部的牛仔身上被浪漫化了,他一直等到對手已經伸手掏槍時才掏出自己的六響左輪手槍。
幾代軍人一直把戰爭比喻為體育。惠靈頓伯爵說,滑鐵盧之戰是在伊頓公學的體育場上打贏的。在當今的美軍中,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就是把戰爭同美式橄欖球畫等號。這並非偶然。橄欖球——而不是棒球——成了戰爭的象徵,因為橄欖球主要包括進攻者對防守者的直接挑戰。同棒球相比,它肯定不是一種採用微妙伎倆、出奇制勝和施展詭計的運動項目,儘管橄欖球也能具有避實擊虛的方面。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美軍的理論很像20世紀中葉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學進行的這種“三碼和一股塵煙”的、直截了當的實力競賽。雖然從那時以來,教學重點已經轉向運動戰,但是直接的解決辦法和正面攻擊在軍界的心理中根深蒂固,很難根除。
真誠、坦率、光明磊落的領導人一直是人們的理想。因此,成功的高明統帥必須具有兩面性格,一方面向部下表現出誠實和公開性,另一方面隱藏或掩蓋品格中得以使敵人“迷惑、誤人歧途和猝不及防”的部分。
一些高明的統帥發現這是一項艱難的任務,並在執行過程中吃了許多苦。“石壁”傑克遜就因守口如瓶,不願把計畫告訴部下而臭名遠揚。雖然他的士兵因他給他們帶來勝利而崇拜他,但是他們認為他很古怪、不平易近人,他的主要上司們認為他難以共事、苛求、不善於溝通。他對這些指責的回答令人很受啟發:“如果我能瞞過我的朋友們,我就能確保瞞過敵人。”
能夠表現出高明統帥所必須具備的兩面矛盾人格的人寥寥無幾。此外,軍隊中的體制也往往使直率的人比胸有城府的人較多地獲得提升。因此,大多數將帥是老實厚道的、單純的武士,率眾發動硬拼的戰役,下令從正面進攻。他們所造成的成為大多數戰爭特點的慘重傷亡和久攻不下是預料之中的。
就連一些德高望重的統帥實際上也是胸無城府的軍人,並且給自己一方帶來災難。羅伯特·E·李就是一位這樣的統帥——南部邦聯心目中十全十美的人物。他極為正直,有正義感和忠誠;作為一名指揮官,他的能力也遠遠超過與他對陣的北方軍將領。但是,李自己並不是一位高明的統帥。
李在正常的和十分關鍵的情況下總是選擇直接硬拼的做法,而不是避實就虛。例如,當1862年攻占馬里蘭州的行動流產時,李並沒有迅速撤回到維吉尼亞州,而是任憑自己捲入發生在安蒂坦的一場正面對抗。他沒有絲毫希望獲勝。這場戰鬥成為美國歷史上流血最多的一場戰鬥。由於南方邦聯在兵力上同北方相比處於嚴重劣勢,所以這種傷亡很大的血戰只有在爭取戰略上的巨大好處的時候才應當進行。堅守安蒂坦是徒勞無益的,而撤退到維吉尼亞會保住南方的進攻力量。安蒂坦之戰還使林肯獲得了他發表解放黑奴的宣言所需要的北方勝利,從而確保英法兩國不會援助南方邦聯。
1863年,李任憑自己捲入了一場相同的消耗戰。當李靠直接硬拼擊潰聯邦部隊的努力失敗後,他一錯再錯,使北維吉尼亞軍的最後一點進攻實力在穿越將近一英里彈坑累累的開闊地的皮克特衝鋒中被摧毀。這場正面進攻在開始之前就注定要失敗。朗斯特里特等將領認識到這一點,李本人在戰鬥災難性的結尾時也承認了失誤;而此時衝鋒的1.5萬名士兵當中只有一半回到南方邦聯的陣地。
但是,當李在葛底斯堡與波托馬克聯邦軍遭遇時,他的處境並不危險。他當時位於聯邦軍的北面;由於在這一方向上的給養比撤回到維吉尼亞要多得多,所以他本來能夠不費吹灰之力就衝破聯邦軍的阻攔,攻占哈里斯堡或約克,從而在一個方向上威脅費城,在另一方向上威脅巴爾的摩,在第三個方向上威脅華盛頓。倘若波托馬克軍的主力撤退回去守衛首都,李本來可以沿薩斯奎哈納河向東南挺進,威脅費城或巴爾的摩。假如聯邦軍司令米德按兵不動,守衛華盛頓,李本來可以攻占巴爾的摩。那裡是通往北方的所有鐵路線的匯聚點,因而他本可切斷華盛頓的增援和給養。如果米德出兵保衛巴爾的摩,李可以渡過薩斯奎哈納河,奪取費城。費城當時是美國第二大城市,對北方來說,失去它會是一場災難。
另外一位很有名氣但幾乎輸掉南北戰爭的統帥是北方的尤利塞斯·S·格蘭特。在1864年的維吉尼亞戰役中,格蘭特一次又一次地將其軍隊投人對嚴陣以待的南方邦聯軍隊的正面進攻中。格蘭特的目的是要摧毀李的部隊,但他差一點毀掉自己的軍隊,從春季的野戰到仲夏的彼得斯堡僵局為止,他損失了自己全部實力的一半。到這次戰役後期,格蘭特的部隊不再願意竭力進攻了,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會被打敗。的確,在冷港,聯邦軍的士兵們確信自己必死無疑,因而在衝鋒之前把自己的名字和住址貼在軍裝背後,以便家人在戰鬥結束後能夠得到通知。
格蘭特唯一的戰略成功不是靠戰鬥,而是靠部隊的轉移獲得的。他渡過詹姆斯河,逼近南方供給里奇蒙給養的主要鐵路,因為他沒有再次直接硬拼,而是決定悄悄渡過詹姆斯河,使敵人猝不及防,攻占彼得斯堡。他幾乎失敗;維吉尼亞的戰爭出現僵持局面;是謝爾曼,而不是格蘭特,通過襲擊南軍的尾部打破了這一僵局。
類似於李和格蘭特行動思路的直接行動促使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德軍司令毛奇破壞了謝里芬伯爵的著名計畫,即派遣德軍主力“迂迴”到巴黎西面和南面。這個德軍主力之“錘”按計畫將回到北面,利用位於法德邊境上的堡壘之中的德軍之“砧”粉碎法軍和英軍。毛奇放棄橫渡塞納河的迂迴包抄,而是在河北面發動正對巴黎的直接進攻。這使法軍得以阻止德軍的前進道路,制止德軍的進攻,造成持續到1918年的塹壕戰僵局,從而創造“馬恩奇蹟”。
1942年年底,希特勒堅持主張正面進攻史達林格勒,而不是在還來得及的時候撤走德軍,結果使一支龐大的德國軍隊毀於一旦,並失去了在東線的主動地位,最終將戰爭輸給了俄國人和其他盟國。
本書旨在利用具體實例表明,以往的高明統帥們如何套用由來已久的戰爭規則和原理而制勝,即使只不過因為他們搶在對手前面運用了它們。這些規則不是像代數公式那樣需要機械地照搬的方法,而是必須技藝高超地看情況而套用的概念。它們不是只有軍事專家和軍事指揮及參謀學院的高年級學生才能懂得的、深奧的抽象理論,而是兩個國家或國家集團進行殊死的戰爭時用來解決常見問題的對常識的運用。
每個交戰者的目的都是使對手服從他的意志,試圖引誘別人遵照其意願行事。這是適用於個人、集團和國家的很平常的人類宗旨。普通的人類爭端和戰爭的唯一區別在於,戰爭是一方對另一方施加武力的暴力行動。倘若一方不動用武力即能實現其目的,它當然會這樣做,因為除非存在抵抗力量,沒有任何國家會發動攻擊。19世紀普魯士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所下的定義是,戰爭是國家政策通過其他途徑的繼續。 看來可能很明顯的一點是,捲入任何衝突的每個個人、集團和國家都始終應當採用帕里斯在特洛伊戰爭中所採取的策略,只打擊阿喀琉斯的腳跟。但是,戰爭和人際關係的歷史結論性地表明,人類經常忽視或看不到對敵人或對手迂迴包抄的機遇,而是正面打擊他們所看到的最明顯的目標。
人們並不經常實際或比喻陛地迂迴到其對手的後面去。經過100萬年的文化薰陶,人類已經習慣於在一個集團中合作。這種薰陶使得我們忠誠於自己的集團,對自己集團的敵人採取好鬥態度。不論是與朋友合作還是同敵人鬥爭,我們的趨勢都是直截了當,而不是避實就虛或迂迴包抄。
只有非凡的人才能把與敵人正面對抗的原始欲望,同為使敵人猝不及防和易受打擊而掩蓋或隱藏自己的行動的必要性相分離。但這卻是成為高明統帥的唯一道路。大約在公元前400年,中國著名戰略家孫子寫道:“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孫子還寫到,在戰爭中,“避實而擊虛”。
許多人誤解了戰爭中的真正目的。這一目的並不像眾多軍界和文職領導人所認為的那樣,是在戰場上摧毀敵人的武裝力量。這一簡稱為“拿破崙主義”的觀念在一個多世紀以來的軍事教科書和規章的編寫和制訂中,以及在參謀學院的教學中,都曾占據主導地位。
拿破崙本人並不是這一理論的始作俑者,儘管正如哈特所指出,它來自於拿破崙在1806年的耶拿之戰以後的做法,即倚仗重兵,而不是依靠機動性;機動性在此之前一直主宰著他的戰略。耶拿之戰後,拿破崙只關心戰鬥,信心十足地認為,短兵相接,他能夠毀滅對手。
拿破崙後來的以純粹進攻實力為基礎的戰役使得早些時候的戰役中可供借鑑之處變得不明顯了;在早期戰役中,拿破崙把詭計、機動性和出其不意結合起來,在節省大量實力的情況下取得巨大戰果。克勞塞維茨對拿破崙後期的戰役印象最深刻,並且成為“大兵團作戰的鼓吹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規模戰鬥上。這一理論適合於普魯士為實現“全民皆兵”目標而大量徵兵的制度。這一觀念在1870至1871年的法普戰爭中獲得勝利,因為普魯士的優勢兵力占據了有利地位。此後,另外一些強國迫不及待地模仿了德國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戰表明,統帥們的廝殺欲望與最新研製出的機關槍使戰爭淪為大規模屠殺。雖然其結果是給歐洲的青年們造成大量傷亡,但是認為戰爭是為了在戰鬥中消滅敵人主力的觀點繼續影響——在許多情況中還指導了——我們的思維,直到今天仍舊是這樣。
但是戰爭的目的根本不是廝殺,而是實現更加完善的和平。要實現和平,戰鬥者必須破壞敵國人民打仗的意志。沒有任何國家為打仗而發動戰爭。它發動戰爭是為了實現國家的宗旨。一個國家要實現這一目的,可能必須消滅敵人的軍隊。但這種毀滅並不是目的,而只不過是達到目的的附帶副產品或者是手段。
倘若一位指揮官研究一下他在戰爭結束時所要尋求的和平,他可能會發現許多這樣的實現和平的途徑,即避開敵人主力,打擊一些目標,從而破壞敵人作戰的願望或能力。第二次布匿戰爭中偉大的羅馬軍隊統帥西庇阿不理睬敵軍,而是出其不意地攻占敵軍大本營、今天的卡塔赫納,從而削弱了迦太基對西班牙的控制。在1814年的拿破崙戰爭末期,盟軍避開他的軍隊,而攻陷巴黎,從而使法國人民喪失信心,放棄努力,迫使拿破崙投降。1864年年底和1865年年初,謝爾曼的軍隊很少打仗,但是卻向喬治亞州和南北卡羅來納州進軍,從而破壞了南方人民打仗的意志,使許多叛軍士兵紛紛開小差回家。
克勞塞維茨懂得,戰爭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軍事性的,並且在其著作中實際表達了這一觀點。但是,他的句法和邏輯晦澀難解,以致從他的著作中獲得靈感的軍人們不大注意他的觀點的限制條件,而較多地注意了他的概括性語句——“流血的解決辦法,摧毀敵軍是戰爭的長子”;“讓我們對有的將領不造成流血就實現征服的論點充耳不聞吧”。克勞塞維茨對作戰的重視顯示出了其理論的一個矛盾。因為假如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中所要實現的目標就是主要目的。但是,克勞塞維茨重視戰爭的勝利,因而只期待著戰爭結束,而不是戰爭結束後的和平。
雖然克勞塞維茨實際上是說,戰爭是達到一國目標的最通常的辦法,但是幾代喜歡正面作戰的軍人未能權衡其論點的矛盾之處,也不能理解其晦澀的論點,因而理解為戰爭是唯一的途徑。
我們現在能夠給軍事戰略或指揮戰爭的目的下定義了。這就是縮小抵抗的可能性。高明的統帥利用運動戰和出其不意等手段消滅或縮小抵抗的可能性。正如孫子所說:“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為實現這一目的,孫子為成功的統帥出謀劃策:“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如果統帥率軍出現在敵人必須迅速前往保衛的地點,那么敵人的精力很可能分散,並且很可能削弱其他地點的防禦力量,或者將其放棄,因而促成自己戰敗,或者使自己失敗無疑。速度和機動性是戰略的基本特點。拿破崙說:“空間我們能夠收復,時間絕對不能。”
在以下的本書各章中,我們將考察像拿破崙這樣高明的統帥們是怎樣實踐戰爭原理的。在這裡簡要概述一些最主要的原理可能是有益的,為的是使高明統帥們的行動易於追蹤。
B·H·利德爾·哈特的兩句格言體現了巨大的軍事智慧。他說:“成功的統帥選擇(敵人)最沒料到的路線或行動方向;他利用抵抗力量最弱的路線。”
雖然這兩則警句聽起來似乎是不說自明的,但是統帥們很少按其行事,在它們被用來對付他們時也不知曉。“流血嶺”和“傷心嶺”之戰是在敵人最預料到的和其抵抗力量最強大的戰線上展開的。1940年5月,當德軍入侵低地國家時,英軍和法軍的指揮官所考慮的只是迅速出兵比利時,以便從正面抗擊他們所認為的德軍主要的、也是正面的進攻。這使德軍得以出其不意,越過“不可逾越的”阿登高原,在色當突破敵人防線。德軍既已迂迴到盟軍背後,便能夠奔向英吉利海峽,沿途所向披靡。類似的,1941年12月,美國領導人預料,敵人將在東印度群島,也許還有菲律賓發動進攻。因此,日軍對珍珠港的空襲使之猝不及防。
成吉思汗及其大將速布台實行了用兵的另外一項原則;這項原則在速布台1241年入侵東歐時得到完美的運用。我們不知道蒙古人對它的稱呼,但是,18世紀初的法軍戰略家皮埃爾·鮑塞獨立地構思了同一原理,稱之為“分進合圍的計畫”。
速布台向歐洲派遣了4支彼此分離的部隊。一支部隊沖人喀爾巴阡山脈以北的波蘭和德國,在那一方向上吸引了所有的歐洲力量。其他三支部隊在相距很遠的不同地點進入匈牙利,威脅若干不同目標,因而使奧地利等國的軍隊無法同匈牙利軍隊聯合。這三支蒙古部隊然後在布達佩斯附近的多瑙河畔會師,以對付現已孤立無援的匈牙利人。
鮑塞建議,將帥們應當將其進攻力量分散成兩支或更多的前進部隊,這些部隊在必要時能夠迅速重新會合,但卻採取威脅多個目標的行動路線,從而使敵人不得不守衛這些眾多目標,被迫分散力量,無法集中兵力。倘若敵人封鎖一條進攻路線,統帥們便能夠立即在另外一條路上形成攻勢,以便為同一目的服務。聯邦軍將領謝爾曼在1864年至1865年的喬治亞和南北卡羅來納進軍中採用了這一方法。他的彼此相距很遠的分進部隊威脅著兩個或更多的目標,使邦聯軍被迫分散力量保衛所有的目標,因而無法守衛任何一個目標。這使叛軍在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戰而放棄保衛兵力薄弱的陣地。
像謝爾曼和速布台一樣,採用“分進合圍計畫”的進攻者往往能夠在敵人作出反應、集中兵力對付他之前將兵力合起來奪取一個目標。一個與此大同小異的做法是部分兵力匯集起來攻擊一個已知目標,而其餘兵力包抄其後部。
在1862年的謝南多厄谷地戰役中,“石壁”傑克遜利用純粹的詭計實施了略加修改的這種計畫;他沿著主要道路正面進攻聯邦軍主力,然後悄悄改變路線,翻越一座高山,出其不意地降臨在聯邦軍側翼和後方。
拿破崙對鮑塞的分進合圍計畫加以發揮,他把單獨挺進的部隊分散得彼此相距很遠,猶如一張沉重的漁網。這些部隊能夠迅速集中起來包圍在路上遇到的任何孤立的敵人。
拿破崙的戰績在很大程度上還歸功於另外一位18世紀法國理論家——吉伯特。吉伯特提倡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以集中優勢兵力攻擊敵人的一個弱點,迂迴到敵人側翼或後方。拿破崙充分利用了機動的戰術,張開一張浮動的大網。這使他的敵人大惑不解,無法揣摩拿破崙的真實目的。他們通常分散自己的兵力,希望反擊拿破崙的迷惑行動。這時拿破崙便迅速集中起其分散的部隊,以便在一支單一敵軍獲得增援之前將其消滅,抑或用自己的全部軍隊猶如神兵天降,打擊敵人的後部。
拿破崙的戰略絕招就是“迂迴包抄,攻其後部”。他的用兵之道體現了孫子的訓諭: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避實擊虛。戰爭的藝術妙就妙在在敵人的弱點上形成強大兵力。
拿破崙增添了一個獲勝的要素,即經常占據敵人後方的優勢地形,譬如一條山脈、峽道或河流,在那裡建立戰略要塞,防止敵人撤退或獲得給養和增援。例如,在1800年的義大利馬倫戈戰役中和導致他於1805年在奧斯特利茨獲勝的烏爾姆戰役中,拿破崙就是利用戰略要塞而獲勝的。到美國南北戰爭時,已經沒有必要奪取有利地形了。軍隊依靠鐵路供給給養和兵源。只要在敵後阻塞一條鐵路線,就能建立一個戰略要塞。1863年,格蘭特將軍在密西西比州的傑克遜就是這樣做的,從而在維克斯堡使南方軍孤立無援。這導致該市的投降、密西西比河向聯邦船隻的開放和南方邦聯失去密西西比河流域各州。
攻敵後方由於一些原因而具有毀滅性。敵人如果被迫改變前線位置,他往往會方寸大亂,無力應戰或降低作戰效率。一支軍隊像一個人一樣,對來自後方的威脅比對前方的威脅要敏感得多。因此,攻其後部容易造成恐懼和混亂。此外,包抄敵後往往打亂敵軍的部署和組織,可能使之彼此分離,威脅其退路並危及給養和增援部隊的運送。一支現代軍隊在沒有食物增添的情況下能夠生存一段時間;但是,在缺乏彈藥和機動車燃料的情況下只能維持幾天。
攻敵後部對敵軍士兵造成嚴重的心理效應。而對敵軍指揮官尤為如此。這樣做往往在敵軍指揮官的心裡造成中計和無力抗拒的恐懼。在極端情況下,這可能會導致敵軍指揮官決策能力的喪失和軍隊的潰敗。
攻敵側翼或後部必須出奇,才能完全制勝。不論戰術、實戰還是戰略,都應遵循這一原理。倘若敵人預料到後方受到攻擊,他往往能夠調兵遣將來應戰,並且通常做好自衛的準備。此外,在一般情況下,只有當敵人被前方其他部隊所牽制而騰不出兵力的時候,或者當他無法及時派兵應付突然襲擊的時候,攻敵後部才能成功。
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沒有充分理解這一原理,戰鬥中損失慘重,以致他幾乎喪失自己的國家。雖然腓特烈總是採取迂迴戰術,但是他的側面和後方攻擊的迂迴路線太短,而且並沒有出其不意。例如,1757年,他發現奧地利軍隊牢固地駐守在布拉格的河畔。他只把少量兵力留下來掩蓋自己的計畫,率軍沿河而上,渡過河去,挺進到奧軍右側。奧軍探知了這一行動,及時改變了前線方位。普魯士步兵試圖越過一個被火力嚴密封鎖的緩坡發動正面進攻,結果成千上萬地倒下。多虧了普魯士騎兵出其不意地到來,才扭轉了敗局。
實戰的基本方案是一場會合式的進攻。指揮官通過把攻擊力量分成兩個或更多部分來達到這一目的。在理想情況下,所有部分都在同一時刻襲擊同一目標,並密切配合,但攻擊的方向或路線卻各不相同,從而使敵軍的所有兵力都疲於應戰,無法相互援助。有時一部分兵力牽制住敵人或分散其注意力,而其他兵力迂迴突襲攻破防線。
一場真正的分進合擊與由一支部隊佯攻或牽制敵人,以分散敵人對主攻的注意力是截然不同的。千百年來,無數的指揮官採取被精明的敵人識破的、明顯是佯裝的行動,以致使自己的希望破滅;抑或試圖打擊的目標很分散,以致敵人的兵力沒有分散,能夠擊退每次攻擊。
一個分進合圍的主要戰例發生在“三十年戰爭”期間的1632年:瑞典的古斯塔弗斯·阿道弗斯架起大炮並點燃秸稈以製造煙幕,同時在巴伐利亞的萊希河上的一點發動進攻,從而使奧地利的蒂利元帥被牽制;與此同時,另外一支瑞典部隊從上游一英里處的一架浮橋上渡過萊希河。在來自兩個方向的同時夾擊下,蒂利無法保衛兩點之中的任何一點。他的軍隊敗退下來,他本人也受了致命傷。
拿破崙的典型作戰計畫是“包圍、突破和擴大戰果”。他發動強大的正面進攻,從而吸引住敵人的注意力,使敵軍全部後備力量都投人戰鬥。這時,拿破崙調遣大軍進攻緊靠敵人給養和撤退路線的敵人側面或後部。當敵人從前線調兵保衛側翼時,拿破崙便在正面主要前線的一個被削弱的部位打開突破口,派騎兵和步兵從此處造成突破,然後用騎兵擊敗和迫擊潰不成軍的敵人。
在韓戰中,挺進中的中共部隊採用了類似的策略。他們把主要的攻擊放在夜間進行。他們的一般計策是出兵攻打敵人陣地的側翼,以切斷其逃跑路線和給養道路。然後,他們在黑暗中發動正面和側面的夾擊,以便與敵人短兵相接。中國部隊一般從幾方包圍一支敵軍小部隊的陣地,直至實現突破,要么消滅之,要么使之被迫撤退。中國人然後悄悄前進,再攻擊下一支小部隊的暴露著的側翼。
偉大統帥們所恪守的原則都不高深難懂。實際上,一旦採用成功,這些原則便暴露出其內在的簡單,看上去很顯而易見,有時還是唯一合乎邏輯的解決辦法。但是,一切偉大思想都是簡單明了的。訣竅在於,要趕在別人前面明白它們。本書所講述的就是高瞻遠矚,在別人之前認識到明顯道理的統帥們的事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