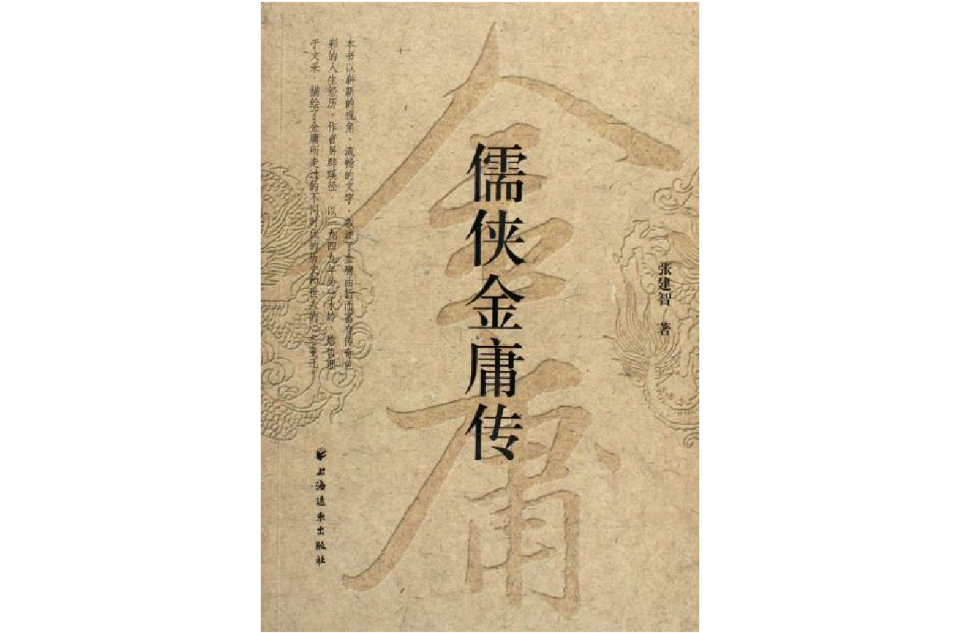基本介紹
出版信息,內容簡介,相關導語,作者簡介,內容目錄,第一章 如日初升,第二章 海寧查家,第三章 漫漫求學路,第四章 抗戰後的生涯,第五章 五十年代的日子,第六章 創立《明報》,第七章 審慎而靈活的報業生涯,第八章《明報》集團的崛起,第九章 從“俠”到“儒”,第十章 二十八年後的回歸故土,第十一章 為香港回歸參政議政,第十二章竹里坐消福 花間補讀書,第十三章 退而不休,第十四章 金庸生活談片,第十五章 浙大辭職風波,第十六章 再探求一個燦爛的新世紀,書籍前言,書籍後記,
出版信息
內容簡介
《儒俠金庸傳》,這是繼冷夏的《文壇俠聖金庸傳》和傅國涌的《金庸傳》之後,第三部關於金庸的傳記。與同類作品最大的區別在於,張建智的這部傳記不是從金庸出生寫起,而是從1949年其進京求職開始。本書將金庸個人命運的軌跡放置在時代巨變之中,融哲理於文采,敘述了許多金庸鮮為人知的生活軼事及其所走過的那個時代的歷史變遷。
相關導語
《儒俠金庸傳》,這是繼冷夏的《文壇俠聖金庸傳》和傅國涌的《金庸傳》之後,第三部關於金庸的傳記。與同類作品最大的區別在於,張建智的這部傳記不是從金庸出生寫起,而是從1949年其進京求職開始。本書將金庸個人命運的軌跡放置在時代巨變之中,融哲理於文采,敘述了許多金庸鮮為人知的生活軼事及其所走過的那個時代的歷史變遷。
作者簡介
張建智,我之煮字生涯,既有坐冷板凳寫出的學術論文和專著,也有對人生追求和對生命精神探索的散文隨筆。我讀書很雜,所寫更雜,不喜妙冷飯,總想另闢蹊徑把所感所悟撰寫成文,以自好並與人共析。
主要著作:《張靜江傳》、《中國神秘的獄神廟》、《嘉業南潯》、《易經與經營》。
內容目錄
時代的金庸與武俠的金庸(代序) 張建智/1
上篇 1949年前的金庸
第一章 如日初升
一、新生的共和國/3
二、一石激起千層浪/5
三、為了燦爛的前途/7
四、踏上故都北京/9
五、夢斷外交官/12
第二章 海寧查家
一、袁花鎮的傳說/14
二、江南有數人家/17
三、查文清與丹陽教案/20
四、父親的藏書/22
第三章 漫漫求學路
一、老師章克標/27
二、母校如慈母/33
三、母親病亡/35
四、惜別碧湖聯高/38
五、爛柯山的石樑/41
六、留戀湘西/45
七、到重慶讀大學/47
第四章 抗戰後的生涯
一、新聞事業的開端/50
二、進入《大公報》/52
三、白手赴香江/55
四、一個時代的終結/57
下篇 1949年後的金庸
第五章 五十年代的日子
一、從《大公報》到《新晚報》/63
二、俠氣滿香江/66
三、書劍碧血露鋒芒/69
四、別了,《大公報》/71
五、“觸電”長城/74
六、射鵰一出、莫與爭鋒/77
第六章 創立《明報》
一、告別“長城”/81
二、初創《明報》/82
三、苦撐局面/85
四、《明報》發展的契機/88
第七章 審慎而靈活的報業生涯
一、健筆寫社評/92
二、參悟佛經寫“天龍”/95
三、世界,你好/98
四、風雨飄搖中的《明報》/101
五、政治寓言:笑傲江湖/105
第八章《明報》集團的崛起
一、海上升“明月”/108
二、《明報》的多元發展/111
三、《明報周刊》的亮相/113
四、《鹿鼎記》問世/116
五、儒俠的經營風格/119
第九章 從“俠”到“儒”
一、掛印封筆/123
二、十年修訂/125
三、寶島之行/128
四、離婚與喪子/130
五、董橋接手《明報月刊》/134
第十章 二十八年後的回歸故土
一、北望神州/137
二、見到鄧小平/139
三、廖承志的宴請/141
四、故國萬里游/143
第十一章 為香港回歸參政議政
一、回港後的暢談/146
二、關注香港的前途/148
三、為基本法草案再赴北京/149
第十二章竹里坐消福 花間補讀書
一、部署引退/153
二、淡出《明報》/156
三、在牛津做訪問學者/161
四、筆戰彭定康/163
第十三章 退而不休
一、與第三代領導人的會面/166
二、放下無求心自在/167
三、《明報》再度易主門71
四、任浙大教授和院長/173
五、《鹿鼎記》尋根湖州行/178
第十四章 金庸生活談片
一、在北大演講/186
二、嶽麓書院講“中國歷史大勢”/189
三、“崇拜”女性/191
四、評點的風波/193
五、王朔詰難金庸/200
六、頻活動、漫話人生/206
七、影視劇中的金庸小說/212
第十五章 浙大辭職風波
一、風波緣起/216
二、金庸站在風波口/218
三、塵埃落定/221
四、風波後的反思/222
第十六章 再探求一個燦爛的新世紀
一、作客《南方人物周刊》/226
二、金庸小說終結版的問世/229
三、金庸小說進課本的是與非/232
四、從為金庸塑像說起/235
五、燦爛的新世紀與金庸/238
附錄金庸生平大事年表/243
主要參考書(篇)目/255
後記/260
書籍前言
江南十月,南太湖平原,一派天高氣爽,桑林掩映著秀麗景色,風光無限。20世紀的最後一個秋天,一代儒俠金庸開始了他的湖州之行。金庸此行一為水鄉踏秋,二為他的小說《鹿鼎記》尋根,筆者作為“東道主”全程陪同,與“金大俠”近距離接觸,感觸頗多。在為金庸送行後,望著他遠去的背影,看著他與夫人乘坐之車離開,心頭依依不捨,我仿佛進入了“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的境界。
這“江南”二字,蘊含著多少故事傳說、多少淒迷婉轉。而金庸的人生歷程也正如“江南”一樣,滄桑變幻,如雨似煙。筆者所寫的《金庸湖州行》一文曾引起許多讀者的興趣,在不少讀者和朋友的鼓勵下,我想忙裡偷閒把金庸的人生故事娓娓道來。
50年前的今 天,也正巧是“畫船聽雨眠”、“壚邊人似月”的江南最美好的季節,只是那時世上還沒有“金庸”這個名字,只有一位叫做查良鏞的青年。查良鏞正接到一份加急電報,電報來自北京,拍報人是新中國成立後被聘為外交部顧問的梅汝■先生。這位人稱“外交界老資格”的梅博士邀請查良鏞北上,到外交部工作。查良鏞接到電報後,不顧部分親友的猶豫和反對,立即簡裝動身北上,時正值年輕有為、風華正茂之際。
那時,查良鏞壓根沒想到,日後的他會成為文壇儒俠“金庸”。當一名叱吒風雲的外交官,興許才是他夢寐以求的人生之旅。這個青年人的理想,始於他撰寫了一篇有名的國際評論:《從國際法論中國人民在國外的產權》。此文於1949年11月15目和18日,分兩次在香港《大公報》發表。
這篇文章引起了當時首屈一指的權 威學者、時任東京法庭中國首席大法官的梅汝■博士的注意,於是“查良鏞”這個名字,被深深記在梅博士的心中了。不久梅博士路過香港,特約請查良鏞面晤。當看到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就能寫出這么有分量的文章,梅汝■先生頗感意外。年輕的查良鏞能為梅博士這般大名人所賞識並約見,也確實是欣喜若狂。學者型的大法官仔細地看了查良鏞的其他-些論文,包括直接用英語寫的國際法方面的文章,閱後更驚嘆其才,兩人一見如故。
新中國成立後,渴求人才,不拘一格,梅汝礅作為外交部顧問,想到查良鏞這位年輕才俊正可為新中國所用。求賢若渴,梅汝■一回到北京即發來電報。而查良鏞也正想實現自己的理想,故一拍即合。
查良鏞接到梅邀他北上的電報後,一時竟像唐代大詩人李白被詔征出山時那樣,似乎也想高吟起“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古詩。
他想起過往的人生瑣事,一夜難眠。13歲入省立嘉興中學,16歲考入高中,爾後進入大學,由毛頭少年到長大成人。抗戰時經歷了與故鄉苦難的千日之別,也行了悲壯的萬里之路。戰爭的硝煙剛滅,他由內地東還,回到闊別已久的浙江海寧老家,全家人悲喜交集。雖說故鄉的一草一木、一房一瓦倍覺親切,但小小的海寧縣袁花鎮,也確非他施展抱負之地。家中雖不缺藏書,衣食頗豐,但對一個有遠大志向的青年人來說,畢竟非久居之處。
隨後,他離家去杭州《東南日報》做外勤記者,但在他看來,對自己的人生旅途來說,這也只是一次小小的過渡。他對西子湖畔的人文歷史和秀麗景色雖無限留戀,但仍覺得非久留之地。終於有一天,他跑到上海,如願進了東吳大學法學院修習國際法專業。這是查良鏞人生途程中追求另一種人生抱負的標誌,亦是他志向遠大、胸懷世界的一種表現…… 當一輪明月從維多利亞港灣漸漸升起時,他想,如果永遠在香港當《大公報》電訊編譯及國際新聞編輯,終非他的人生理想,如今已接到北上電邀,亦是平生施展抱負的不可多得的機會。他終於作出決定,他必須換一種活法,調換一下人生角色,他決心大踏步朝著他心中渴望已久的遠大理想走去。那一年,正是公元1949年,是一個新生的共和國剛剛誕生不久的新的時代 …… 1949年,是歷史與時代的分水嶺,從某種意義上講,如果沒有1949年的變遷,也許就沒有了時代的金庸與武俠的金庸……
書籍後記
近年來,在積累史料的基礎上,手頭正寫著已構思好的幾部人物傳記。
拙著《張靜江傳》與廣大讀者見面後,上海遠東出版社向我約一部長篇傳記。鑒於1999年秋,我曾陪金庸先生遊覽、考察了南太湖畔一帶的江南水鄉,可以說從那之際,我就想為集“時代的金庸與武俠的金庸”於一身的查良鏞先生寫一部傳記。長期以來,我對中國古代小說以及二十世紀的優秀小說心存喜歡,也作過一些研究,且對金庸的武俠小說更情有獨鐘。在我讀了在美國的夏志清和夏濟安兄弟倆對金庸最初發表的幾部小說的評論後,也非常有認同感。而金庸的一部《鹿鼎記》正是從我的家鄉南潯寫起,我曾特地陪金庸先生去那裡作了一次意味深長的尋根活動。這些都是我著手撰寫這部《儒俠金庸傳》心靈上的動力。我想,如果沒有了這諸多的因素,也許我就不可能去完成這部作品。
無論在我和金庸先生直接的接觸、相談中,抑或在我閱讀了他的所有作品之後的感受,我總深深感到對金庸之研究,絕不是一個“俠”字所能概括。所以冷夏先生曾稱他為“俠聖”,我不敢苟同。當然他寫的傳是加了“文壇”二字,以我的認知似也不太確切。傅國涌先生的《金庸傳》索性把他從神壇上請了下來,我個人管見,也並非帖切。當然,無論是香港的冷夏,或傅國涌先生寫金庸,他們的文字都記述精當絕不旁枝,對於我寫金庸無不都有幫助之處。其實,就我的體會,以金庸所寫文字,以他的個性,以他的素質,以他祖祖輩輩相遞的文人資質對他的傳承,在他有了物質而不忘教育,有了身價而始終流連於校園生活,甚或到了八十以上之高齡,在他的古稀之年,還饒有興味去英國劍橋攻讀博士學位。這一切心靈之驅使,以及珍惜自己個體生命的存在,並以“學”來珍惜自己作為一個小說家與報人的運命,我想,這不就是有如孔子所說的“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嗎 ?於此,我認為金庸的資質、在他血脈中流淌的,是更接近於一種“儒”的本色。所以,當我動筆寫他的傳記時,跳入我腦海並隨之寫下而定格的便是這“儒俠”兩字。
我與金庸相見相敘是在1999年,是人類即將跨入新世紀之際。如果,我們把時間移至半個世紀之前,那便是1949年,也正是金庸本人命運的轉折之際。正如在《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金庸、池田大作對話錄》中,池田大作曾對金庸開篇就說:“‘相見時難別亦難’,人生際遇的‘戲劇’各有各精彩,各有各不同。”的確,在1949年與1950年之際,確是決定金庸後五十年人生之“命運的偶然”時期。又誠如池田大作在此書中所說:“人會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種令人懷念的——以佛家之言而論,就是‘宿世之緣’的命運之線在操控……”我追溯金庸80多年以來人生旅途之軌跡,深深感到1949— 1950年之際,也正是“命運之線在操控”著他走向人生的另一個渡口。正是在那樣的時刻,一種對生活的強烈的渴望,猶如一個船夫重新掛起一片白帆、一隻急駛的獨木船,使他又另闢蹊徑奔向了另一個生活的大海…… 出於這樣的寫作理念,我截取了傳主人生的一個橫斷面開始敘述,即從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寫起,分上下兩篇進行撰寫,上篇是《1949年前的金庸》,下篇是《1949年後的金庸》。如今,呈現 在讀者面前的這部《儒俠金庸傳》,也許正如金庸自己所說“不曾識面早相知”,也一如池田大作所言“人生何處不相逢”。當我在電腦上寫完最後一個字時,我相信與讀者早已共存在這部金庸先生的傳記中了,我們的心也早相知和相識,於此,我深深地期盼! 野人獻芹,這篇原本可以更短些的後記,已拉雜了些。但如果在這部傳記中,讀者對我寫金庸人物之歷史,可獲點滴知識,那將使我更感喜出望外、夙願足矣! 張建智 2005年10月8日 記於湖州苕溪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