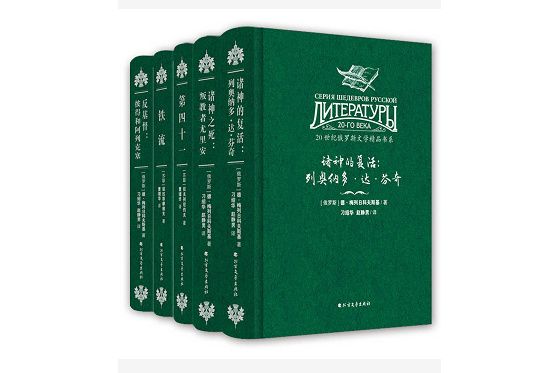18世紀文學
彼得一世時期的文學仍然是新舊雜陳,具有過渡性質。沙費羅夫(1669~1739)和費奧方·普羅科波維奇(1681~1736)的政論反對守舊,宣傳開明君主專制,從中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矛盾和動向。30年代在彼得改革的基礎上興起的古典主義,是此後將近半個世紀中俄羅斯文學的基本流派,表現了啟蒙主義同中世紀思想原則之間的鬥爭。康捷米爾(1708~1744)的諷刺詩著重批評20至30年代社會上的愚昧主義流毒和封建等級觀念,到50年代還在廣泛傳誦。羅蒙諾索夫(1711~1765)寫頌詩褒揚開明君主,讚美科學文化造福人類。他使文學體裁和語體規範化,並將音節體詩改為更適合俄語特性的音節和重音並重體詩,對統一的俄羅斯民族文化的形成和詩歌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詩人和劇作家蘇馬羅科夫(1717~1777)也有過很大影響,同時代人認為他的悲劇和羅蒙諾索夫的頌詩標誌著俄羅斯新文學的真正開端。古典主義代表作家還有特列佳科夫斯基(1703~1768)、赫拉斯科夫(1733~1807)。在古典主義文學中,諷刺作品成長較快。50年代,嘲諷性的寓言詩和喜劇先後再現。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諷刺雜誌盛行,其中最突出的是諾維科夫 (1744~1818)主編的《雄蜂》(1769~1770) 和《畫家》(1772~1773)。前者主要暴露象雄蜂一樣過寄生生活的地主,後者側重抨擊上流社會的崇洋媚外風氣。此外還有艾明(1735~1770)的《地獄郵報》(1769)和楚爾科夫(1744~1792)的《雜拌兒》(1769)。70年代末,傑爾查文(1743~1816)的頌詩開始問世。他把諷刺與歌頌、批判與肯定結合起來(《費麗察頌》,1782;《權貴》,1798),又把“鄙俗”的日常生活引進詩中(《茲萬卡的生活》,1807),從而多少突破了古典主義的模式。馮維辛(約1744~1792)在其優秀喜劇《紈袴少年》(1782)中雖然還遵守“三一律”,卻深刻揭露了農奴主的殘暴和寄生性,點出農奴制是俄國的萬惡之源,向現實主義邁進了一步。
18世紀末葉,在英、德、法等國文學的催化下,感傷主義在俄國勃興,反映了1773至1775年普加喬夫起義後貴族的憂傷情緒。其倡導人卡拉姆津(1766~1826)打破古典主義的禁忌,將卑賤者的形象引入文學,在《苦命的麗莎》(1792)中寫一個農家姑娘和貴族青年相愛,最後見棄自殺。小說著力渲染人物的內心感受,格調新穎,語言清雅流暢,發表後風行一時。感傷主義詩人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以寓言、歌謠見長。偉大貴族革命家拉季舍夫(1749~1802)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1790)是俄羅斯文學史上第一部強烈反對農奴制的力作。他真實地寫出了農民的困苦和抗議,並用書中《自由頌》一詩大膽歌頌17世紀英國革命,而抒發作者感受的章節仍保持感傷主義的特點。這部作品沒有對當時的文學產生直接影響,其效果到十二月黨人革命時才顯示出來。
19世紀文學
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俄國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激盪和1812年衛國戰爭所引起的民族意識的高漲,專制農奴制的危機加深,終於爆發了1825年十二月黨人起義,俄國解放運動史上的貴族革命階段(大約從1825到1861年)從此開始。同這次起義前後錯綜複雜的社會狀況相適應,文學中各種流派和思潮紛然並立,互相排斥而又互相滲透。感傷主義雖已出現,古典主義派尚未完全退出,他們以希什科夫(1754~1841)和傑爾查文為首,結成“俄羅斯語言愛好者座談會”(1811~1816),同擁護卡拉姆津的“阿爾扎馬斯社”(1815~1818)就新舊文體問題激烈論戰。
19世紀初,一些保守貴族對動盪的社會甚為不滿,流露出悲觀遁世的思想,消極浪漫主義遂應運而生。其鼻祖茹科夫斯基(1783~1852)原是從感傷主義蛻化而來,他的大部分詩歌遠離現實,追求內心的自由和諧,宣揚神秘的宗教觀念,但他發展和深化了卡拉姆津對人物的心理剖析。巴丘什科夫(1787~1855)的後期詩作也有類似之處。隨著貴族革命的醞釀,又湧現了反對暴政、頌揚自由的積極浪漫主義詩歌,如十二月黨詩人雷列耶夫(1795~1826)的《致寵臣》(1820)、《公民》(1825),普希金(1799~1837)早期的《致恰達耶夫》(1818)、《高加索的俘虜》(1820~1821)。雷列耶夫、拉耶夫斯基 (1795~1872)、丘赫爾別凱(1797~1846)和馬爾林斯基(1797~1837) 等十二月黨詩人認為文學是宣傳和戰鬥的武器,注意從民間創作吸取營養,強調作品的民族獨特性。這時現實主義文學也有進展。克雷洛夫(1768~1844)的寓言廣泛地表現社會的弊端和俄羅斯民族的智慧,形式活潑,文辭通俗。格里鮑耶陀夫(1795~1829)的喜劇《智慧的痛苦》(1824)以個性化的語言,通過對保守反動勢力的鬥爭,刻畫出一個反映十二月黨人革命情操的20年代貴族知識分子恰茨基的形象。馬爾林斯基的中篇小說、拉熱奇尼科夫(1792~1869)的歷史小說和柯里佐夫(1809~1842)的詩,也包含許多現實主義的成分。 普希金的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插圖
20年代下半期,普希金在保持和發揚早期詩作的優點的情況下,完成了由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的過渡。悲劇《鮑里斯·戈都諾夫》(1825)表明他已進一步認識到人民民眾在歷史上的巨大作用。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1823~1831)是俄羅斯現實主義的奠基之作,它第一次在本國文學中展示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塑造了當時大多數進步貴族青年的代表奧涅金,他們厭惡上流社會,但又遠離人民而無法自拔,結果一事無成。
30年代起,散文,特別是小說,逐步取代浪漫主義時期詩歌在文學中的支配地位,普希金加速了這一轉化過程。他的小說《驛站長》(1830)寫一個卑微的驛站長的不幸遭遇,從此文學界描繪“小人物”蔚為風氣。他最後一部小說《上尉的女兒》(1836)取材於普加喬夫暴動,作者繼續探索社會歷史發展規律,並有力地促進了文學主題的民主化。他在30年代所寫的文論肯定現實主義和人民性,批駁了囂張的反動文人布爾加林(1789~1859)之流。普希金的多方面的創作活動、現實主義方法和純淨優美的語言,為此後的俄羅斯文學奠定了廣闊而堅實的基礎。 30年代的萊蒙托夫(1814~1841)繼承積極浪漫主義詩歌的傳統,在作品中表達了對自由的強烈追求和對貴族社會的憤怒譴責(《詩人之死》,1837;《詠懷》,1838;《童僧》,1839;《惡魔》,1829~1841)。但尼古拉一世的殘酷統治,有時使萊蒙托夫的詩作帶上一種孤獨感和悲觀色彩。他的現實主義小說《當代英雄》(1840)的主人公畢巧林才華出眾,但對個人事業和生活完全陷於絕望,是“多餘的人”奧涅金在30年代的變種。書中深刻的心理分析對後世作家有很大教益。 果戈理(1809~1852)使俄羅斯文學的批判成分顯著增強,他如實地揭示了外省地主的猥瑣無聊(《米爾戈羅德》,1835)、“小人物”的悲慘境遇和大城市的社會矛盾(“彼得堡故事”)。《欽差大臣》(1836)和《死魂靈》第一部(1842)將鋒芒指向整個官僚地主階級,以辛辣的諷刺鞭撻了專制農奴制俄國的全部腐朽性和反動性。果戈理“從平凡的生活中吸取詩意,用對生活的忠實描繪來震撼心靈”(別林斯基),為俄羅斯文學指明了航向。
40年代,農奴制危機愈益嚴重,俄國的發展方向成為全國矚目的中心問題。斯拉夫派代表保守的地主階級,主張返回彼得改革以前“淳樸的”宗法制社會。西歐派大多是自由主義貴族,希望俄國完全走西方的道路。以別林斯基(1811~1848)和赫爾岑(1812~1870)為首的革命民主派則站在廣大農民一邊,要求用暴力推翻專制農奴制度,嚮往社會主義。 屠格涅夫的作品《獵人筆記》插圖 別林斯基根據他對俄羅斯文學的歷史和現狀的研究與總結,建立了他的現實主義美學和評論,認為生活是文藝的源泉,果戈理的批判現實主義是方向。他極力反對“純藝術”論,強調藝術的社會功能,但“藝術首先必須是藝術”,內容和形式應該有機地結合。他對典型性作過透徹的闡釋,將典型化視為創作中的首要課題。1839至1848年他先後主持《祖國紀事》(1839~1884)和《現代人》(1847~1866)評論欄,大大加強了這兩家雜誌的戰鬥力。《給果戈理的一封信》(1847)表達了他的革命民主主義信念。 由於果戈理的示範和別林斯基的指引,40年代俄羅斯文學同生活的聯繫比30年代更加廣泛深入,批判現實主義取得完全勝利,並具有更明確的社會性和目的性。其主力果戈理派或“自然派”聚集了一大批反專制農奴制的作家,從赫爾岑(《誰之罪?》,1841;《偷東西的喜鵲》,1848)、屠格涅夫(1818~1883;《獵人筆記》,1847~1852)到格里戈羅維奇(1822~1899;《鄉村》,1846;《苦命人安東》,1847)。
50年代,尤其是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中被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英、法大敗以後,反封建的主題在文學中得到進一步的發掘。屠格涅夫的《羅亭》(1856)和《貴族之家》(1859)實際上是貴族知識分子的一闋輓歌。岡察洛夫(1812~1891)的《奧勃洛莫夫》(1859)更無情地道出了“多餘的人”蛻化的極限和地主階級的沒落。皮謝姆斯基(1821~1881)的《一千個農奴》(1858)和蘇霍沃—柯貝林(1817~1903)的喜劇《克列欽斯基的婚事》(1855),描寫貴族的墮落和官場的黑幕。奧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的《肥缺》(1856)和《大雷雨》(1859)等預示著宗法制必將崩潰。杜勃羅留波夫 (1836~1861) 把《大雷雨》女主人公、禮教的背叛者卡捷林娜譽為“黑暗王國的一線光明”。為了奪取貴族在解放運動中的領導權,平民知識分子登上政治舞台。運動轉入第二階段,大致從1861至1895年。
1861年農奴制廢除前夕,貴族自由派希望保留君主制和地主土地所有制,自上而下地逐步改良;平民知識分子和革命民主派領袖車爾尼雪夫斯基(1828~1889)等則揭穿政府和自由派的騙局,積極發動農民起義。為此雙方展開激烈爭論。農奴制改革後,其殘餘勢力仍然強大,專制政權對人民的控制也未放鬆;資本主義加速發展,推動了社會的進步,但又不可避免地帶來新的矛盾。革命派和自由派之間的鬥爭並未結束。社會上這些大變動,為容量最大的體裁
長篇小說在50、60年代的空前繁榮創造了前提,並首先反映在雜誌的論戰中。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於50年代中期加入涅克拉索夫(1821~1877)主持的《現代人》編輯部,使這份刊物成為革命民主陣營的講壇;《現代人》的諷刺副刊《口哨》(1859~1863)、詩人庫羅奇金(1831~1875)的諷刺雜誌《火星》(1859~1873)、主要由革命民主主義評論家皮薩列夫(1840~1868)供稿的《俄國言論》(1859~1866),都發揮了戰鬥作用。與這些刊物相敵對的有自由主義的《祖國紀事》和《讀者文庫》(1834~1865),以及反動文人卡特科夫(1818~1887)的《俄國導報》(1856~1887)。
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是別林斯基的繼承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著名美學論文《藝術對現實的審美關係》(1855)中,針對德魯日寧(1824~1864)、費特(1820~1892)、阿·邁科夫(1821~1897)等人宣揚的“純藝術”論,提出“美就是生活”的唯物主義論斷,要求文學再現生活,說明和評判生活,作“生活的教科書”,發揮積極的社會功能。他和杜勃羅留波夫的文學評論通過對作品的深入分析,引導讀者正確認識和努力變革現實(車爾尼雪夫斯基:《不是轉變的開始嗎?》,1860;杜勃羅留波夫:《什麼是奧勃洛莫夫性格?》,1859;《真正的白天何時到來?》,1860)。
在車爾尼雪夫斯基思想的薰陶下,平民知識分子作家茁壯成長,他們不能滿足於同情“小人物”的命運,象19世紀上半葉的作家那樣,而是去著力描述人民民眾的經濟生活和社會地位,代表作有尼·烏斯賓斯基(1837~1889)關於農民的特寫、列舍特尼科夫 (1841~1871)的《波德利普村的人們》(1864)和《礦工》(1866)、波米亞洛夫斯基(1835~1863)的《小市民的幸福》(1861)和《神學校特寫》(1862)、斯列普佐夫(1836~1878)的《艱難時代》(1865)等。
涅克拉索夫同平民知識分子站在一邊,在50至60年代創作了大量訴說人民苦難的傑出詩歌(《大門前的沉思》,1858;《伏爾加河上》,1860;《貨郎》,1861;《嚴寒,通紅的鼻子》,1864;《鐵路》,1864),但他相信人民中間蘊藏的力量。1866年《現代人》雜誌被查封后一年半,涅克拉索夫又和革命民主主義作家謝德林(1826~1889)主辦了另一進步刊物,即改組後的《祖國紀事》。
“新人”──戰鬥的平民知識分子進入文學作品是時代的要求和標誌。1860年,屠格涅夫的《前夜》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這種時代精神。接著,他又在《父與子》(1862)里進一步塑造了巴扎羅夫的形象。巴扎羅夫信奉唯物主義和民主主義,反對專制農奴制度和自由主義貴族,但他的虛無主義傾向不符合當時先進人物的風貌。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1862~1863)中,“新人”才顯出了他們的全部光輝,其中的拉赫美托夫更是俄羅斯文學裡第一個職業革命家。作品洋溢著浪漫主義激情,鼓舞了同時代人和後世的鬥志。“新人”的出現引起敵對陣營的憤怒,“反虛無主義”小說流行一時,如列斯科夫(1831~1895)的《走投無路》(1864)、皮謝姆斯基的《渾濁的海》(1863)。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在《群魔》(1871~1872)中雖然辛辣地嘲笑了自由派,卻把革命民主派歪曲為無政府主義者和陰謀家而加以惡毒攻擊。 列·托爾斯泰的作品《戰爭與和平》插圖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優秀小說充滿對弱者的同情和對社會的抗議。《死屋手記》(1861~1862)揭示苦役犯的非人生活,而他60年代發掘最深的基本主題則是資本主義強大攻勢在城市造成的種種危機:《被欺凌與被侮辱的》(1861)、《罪與罰》(1866)和《白痴》(1868),通過細膩的、鞭辟入裡的心理描寫,反映了不能掌握自己命運的市民、小官吏、窮學生等的悲慘處境和絕望的掙扎,作品貫穿著人道主義精神;同時作者又直接違反人道主義原則,把受苦受難當作淨化靈魂的一種磨鍊,鼓吹奴隸主義和宗教狂熱。托爾斯泰(1828~1910)的史詩性巨著《戰爭與和平》(1866~1869),歌頌俄國人民在1812年反拿破崙戰爭中的勇敢和愛國主義,譴責上層社會的荒淫無恥,並繼續發揮《哥薩克》(1853~1863)的主題思想,肯定進步貴族知識分子苦苦探索正確的人生道路,力求接近人民。書中宏偉的歷史場面與個人的複雜內心活動交織在一起,充分顯示出托爾斯泰深厚的藝術功力。赫爾岑的大型回憶錄《往事與隨想》(1852~1868) 同樣以廣闊的社會歷史為背景,但從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記述了他和他的戰友對專制農奴制的搏鬥和對俄國革命思想的求索。
民粹派掀起“到民間去”運動(見屠格涅夫的《處女地》)後,從70年代中期起,納烏莫夫(1838~1901)、茲拉托夫拉茨基(1845~1911)、扎索津斯基 (1843~1912) 等民粹派作家主要以特寫的體裁報導農奴制改革後農民的分化,但又希望利用村社抵制資本主義,建立“俄國式”的社會主義。奧西波維奇(原姓諾沃德沃爾斯基,1853~1882)和稍後的斯捷普尼亞克(原姓克拉夫欽斯基,1851~1895)的長篇小說,則描述知識分子的作用與活動,以及他們如何尋求同人民相結合的道路。格·烏斯賓斯基(1843~1902)的特寫集《鄉村日記》(1877~1880) 、《農民和農民勞動》(1880)和《土地的威力》(1882)雖有民粹主義幻想,但他證明,在資本主義滲透下,富農的產生和村社的解體乃是歷史的必然。在採用農民題材的70年代作品中,涅克拉索夫的《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1866~1876)居於首位。這部長詩是他一生創作的總結,全面反映了農民改革前後的社會生活,刻畫了有反抗性的農民和獻身農民革命的平民知識分子形象。
謝德林也在70年代取得豐碩的成果。繼《外省散記》(1856)之後,他在《一個城市的歷史》(1869~1870)中以極大的悲憤和高度的概括力,運用誇張怪誕的手法,更深入地揭露昏官酷吏和國家制度,批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宣揚的逆來順受、消極無為的處世哲學。《塔什乾的老爺們》(1869~1872)和《金玉良言》(1872~1876)描述改革後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地主的破落、富農與新型商人的得勢。《戈洛夫略夫一家》(1875~1880)以家庭紀事的形式和深刻的心理剖析,寫出整個地主階級的空虛靈魂和必然滅亡的命運。書中偽善奸詐的猶大什卡形象,是俄羅斯諷刺文學的最大成就之一。由資本主義勢力膨脹所引起的人事代謝,同樣再現於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戲劇《來得容易去得快》(1869)、《森林》(1870)、《狼與羊》(1875)和《沒有陪嫁的女人》(1878)。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後一部巨著《卡拉馬佐夫兄弟》(1879~1880),一方面真實而深刻地揭露貴族地主的腐化墮落,指出苦難深重的世界必然要產生叛逆的思想;另一方面卻繼續反對革命,宣揚基督教的寬恕精神。70年代在資本主義衝擊下動盪不安、新舊交替的俄國社會,特別是俄國農村,在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1876~1877)中反映得最鮮明。安娜在忠於封建操守和要求個性解放的尖銳矛盾中死去;另一主人公列文企圖以他獨特的農事改革來抗拒資本主義潮流,失敗後皈依宗教。
70年代末,托爾斯泰目睹農村破產,在民主主義運動影響下,同貴族階級一切傳統觀念決裂,轉到宗法制農民的立場上。
1881年民粹派炸死亞歷山大二世,政府瘋狂反撲,一個持續多年的反動時期從此開始。謝德林苦心經營了16年(1868~1884)的《祖國紀事》被查封,無聊的幽默雜誌《蜻蜓》之類暢銷各地。革命民粹派蛻化成一個自由主義派別,其作家美化資本主義農村生活,鼓吹“小事論”,提倡點點滴滴的改良。唯美主義重新抬頭,頹廢派公然露面。甚至在小說家迦爾洵(1855~1888)和詩人納德松(1862~1887)等民主主義者的創作中,也響起了沉鬱憂傷的調子。
但謝德林仍然撐持著革命民主主義的大旗,他的《童話集》(1882~1886) 等猛烈抨擊形形色色的反動派和投機分子。列斯科夫捐棄他對“虛無主義”的偏見後,在80年代寫出《左撇子》、《巧妙的理髮師》、《崗哨》這類顯示人民力量的短篇小說和一些諷刺教會的作品。民粹派作家卡羅寧(1853~1892)矢忠於革命民主主義。馬明—西比利亞克(1852~1912)的長篇小說《普里瓦洛夫的百萬家私》和《礦巢》(均1884),表現了資本主義對城鄉生活的決定性影響和勞資矛盾的加深。柯羅連科(1853~1921)奮力抗拒政治逆流,他的《奇女子》(1880)、《馬卡爾的夢》(1883)、《在壞夥伴中》(1885)、《弗洛爾的故事》(1886)和《盲音樂家》(1886)等號召人民為自由和正義而奮鬥,在他們心中激發了樂觀精神,帶有積極浪漫主義情調。
從80年代中期起,契訶夫(1860~1904)的創作達到新的深度,寫了人民的痛苦 (《哀傷》,1885;《苦惱》和《萬卡》,1886)和知識分子的思想探索(《沒意思的故事》,1889)。為了及時報導資本主義迅速發展所帶來的問題,民粹派作家和迦爾洵、柯羅連科、契訶夫等大多採用特寫或中短篇小說的體裁。小型散文作品的發達,成為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初葉俄羅斯文學的一個特色。
90年代初,俄國社會又呈現活躍的氣象。
從90年代中期起,更興起強大的工人運動。新的形勢鼓舞了作家的情緒。柯羅連科寫出《嬉鬧的河》(1892)、《瞬間》(1900),契訶夫創作了《第六病室》(1892)、《醋栗》(1898),發出“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的呼聲(《套中人》,1898),相信新的生活即將到來(《新娘》,1903;劇本《櫻桃園》,1903~1904)。托爾斯泰在《復活》(1889~1899)中從宗法制農民的角度,對“一切國家制度、教會制度、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列寧),同時又宣傳“道德上的自我完成”、“勿以暴力抗惡”的反動學說。他的歷史小說《哈澤—穆拉特》(1904)借古諷今,抨擊了沙皇暴政。
90年代還湧現了一批文學新秀:魏列薩耶夫 (1867~1945) 、庫普林(1870~1938)、布寧(1870~1953)、安德列耶夫(1871~1919)、綏拉菲莫維奇(1863~1949)。20世紀初,他們團結在高爾基(1868~1936)主持的知識出版社周圍,積極展開創作活動,同托爾斯泰、柯羅連科一起,有力地打擊了俄羅斯詩歌中猖獗一時的頹廢派,其中有象徵派的巴爾蒙特(1867~1942)、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吉皮烏斯(1869~1945),阿克梅派的古米廖夫(1886~1921)、阿赫馬托娃(1889~1966)和未來派的布爾柳克(1882~1967)等人。
90年代中期,俄國解放運動進入無產階級時期,俄羅斯文學也相應地踏上一個新階段,其主要標誌是普列漢諾夫(1856~1918)、列寧和高爾基的有關著作。普列漢諾夫早在19世紀末就為馬克思主義藝術社會學奠下基礎(《沒有地址的信》,1899~1900)。他的《藝術與社會生活》(1912~1913)等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美學和文藝學的方法論、任務和發展道路。列寧的《黨的組織和黨的文學》(1905)、1908至1911年間論托爾斯泰的文章、《紀念赫爾岑》(1912)和《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1913)中提出的反映論、文藝的階級性和黨性、“兩種文化”的學說、文化遺產的繼承批判,對於無產階級文學的發展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沃羅夫斯基(1871~1923)和盧納察爾斯基(1875~1933)也為馬克思主義文學評論的建立作過許多工作。高爾基的早期作品反映了人民民眾對地主資產階級社會的自發抗議和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阿爾希普爺爺和廖恩卡》,1894;《切爾卡什》,1895;《二十六個和一個》,1899),用浪漫主義的彩筆勾勒了一些熱愛自由的英雄形象(《伊則吉爾老婆子》和《鷹之歌》,均1895;《海燕之歌》,1901)。1906年成書的戲劇《敵人》和小說《母親》宣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業已誕生。以後高爾基又創作了《童年》、《在人間》(1913~191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