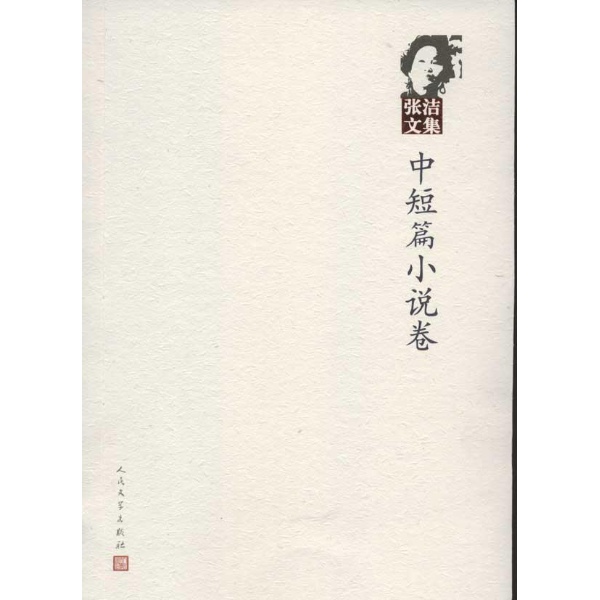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目錄,精彩內容,相關閱讀,
內容簡介
《張潔文集:中短篇小說卷》收錄張潔結集的中短篇小說二十二篇,包括:《懺悔》、《“冰糖葫蘆——”》、《未了錄》、《雨中》、《方舟》、《楞格兒里格兒楞》、《走紅的諾比》、《山楂樹下》、《“尤八國”體檢》、《祖母綠》、《他有什麼病》、《尾燈》、《橫過馬路》、《魚餌》、《柯先生的白天和夜晚》等,
作者簡介
張潔(1937~ )當代女作家、小說家,中共黨員。
原籍遼寧撫順,生於北京,幼年喪父,從母姓。讀國小和中學時愛好音樂和文藝。1960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計畫統計系,到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翌年加入中國作協。1982年加入國際筆會中國中心,並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赴美國參加第一次中美作家會議。任北京市作協副主席。1992年被美國文學藝術院選為榮譽院士,國際筆會中國分會會員,中國作協第四、五、六屆全委會委員、第七屆名譽委員。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現為國家一級作家、國務院授予的有特殊貢獻作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市作協副主席、北京市政協委員。張潔以"人"和"愛"為主題的創作,常引起文壇的論爭。她不斷拓展藝術表現的路子,作品以濃烈的感情筆觸探索人的心靈世界,細膩深摯,優雅醇美。是唯一一個獲得兩次茅盾文學獎的女作家。
目錄
懺悔
“冰糖葫蘆――”
未了錄
雨中
方舟
楞格兒里格兒楞
走紅的諾比
山楂樹下
“尤八國”體檢
祖母綠
他有什麼病
尾燈
橫過馬路
魚餌
柯先生的白天和夜晚
上火
她吸的是帶薄荷味兒的煙
.com
聽彗星無聲地滑行
玫瑰的灰塵
四個煙筒
一生太長了
“冰糖葫蘆――”
未了錄
雨中
方舟
楞格兒里格兒楞
走紅的諾比
山楂樹下
“尤八國”體檢
祖母綠
他有什麼病
尾燈
橫過馬路
魚餌
柯先生的白天和夜晚
上火
她吸的是帶薄荷味兒的煙
.com
聽彗星無聲地滑行
玫瑰的灰塵
四個煙筒
一生太長了
精彩內容
懺悔
――給不幸的孩子
完了。
最後一朵光焰閃動了一下,很快就熄滅了。
這就是兒子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個形態。六十五公斤,一米八七,有血有肉的兒子,已經化為一縷青煙,一撮白灰。經過幾千萬年進化才獲得的生命,這么容易地就毀滅了,容易得讓人不能相信。
從火葬場回家後,他本能地回憶起兒子的一生――把二十七個年頭稱為一生,似乎有些誇張。那么短暫,又那么匆忙――可又好像什麼也回憶不起來,他對兒子知道得太少了。
人們常說,男人之間不像女人之間那么容易披露心懷。難道只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才像路人似的生活在一起?
可他算什麼男人?他甚至沒有戀愛過,沒有充分享受過太陽的照耀。
他看著兒子留下的這些東西:一本“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安徒生童話》,一個破舊的鐵皮鉛筆盒,唯一一張一寸“免冠半身正面照”,一本卷了邊兒的《珠算口訣》。
《安徒生童話》是他們家的忌諱,兒子一清二楚。可為什麼他偏偏固執地留存下這本書?
當他被甩出正常的生活軌道時,兒子正是拿著玩具手槍,認準自己便是天下頂了不起的英雄豪傑的年齡。可這位英雄卻不能明白因為什麼,自己便成了頂低下、頂齷齪的東西。
要是有哪個父親,明知自己便是那個砸碎親生兒子的夢想的錘子,而又深深懂得無法逃脫命運的這種安排,他一定體會得到那種痛苦得無法呼吸,像在火里焚燒的滋味。
那時候,兒子還能睜著一雙圓圓的飽含眼淚的眼睛問他:“爸爸,為什麼小朋友都不和我玩了?”
他回答不出。他又怎能讓兒子明白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事情。
有好長一段時間,院子裡那棵桃樹下的螞蟻窩,便是孤寂的兒子的寄託。兒子久久地蹲在那裡,全神貫注地看著忙忙碌碌、來回奔波的螞蟻。它們那充滿生機的、單純而友愛的生活,一定引他生出許多感觸和渴慕。他問過:“爸爸,為什麼螞蟻老是大家一起玩,誰也不丟掉誰呢?”
“不知道。”
“您是大人,為什麼不知道呢?”
兒子哪裡知道,許多問題是大人也回答不了的。
一天,另外一個孩子走了過來,幾腳就蕩平了那個與人無爭的螞蟻王國。
不但他們不和兒子一起玩,甚至也不能容忍兒子和螞蟻一起玩。他知道,小兒子有多么的寂寞,可是他不敢再給他一個弟弟或妹妹來陪伴他,因為,他沒有能力去保護這些無辜的小心靈。
長大一些後,兒子似乎有些明白他的地位,便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著他。仿佛他會傳染一種疾病,凡是得了這種疾病的人,就會被生活拋棄,變成一個孤零零的人。
天真的兒子並不明白,其實他早已被傳染上了這種“疾病”。
他永遠不能忘記,兒子是帶著怎樣可望而不可即的神情,看著飄在別的孩子胸前的紅領巾,如同一個淪落地獄的人,懷著超度來世的虔敬,巴望著天堂。
他曾聽見兒子向妻子發問:“他究竟幹了什麼壞事?”
“誰?”
“他。”
“他是誰?”
“他――父親。”
他感覺得到妻子十分困難地挑選著字眼,“因為他對一位領導,講了一個安徒生的童話。”
“哪個?”
“《皇帝的新衣》。”
“瞎說,為什麼沒有人說安徒生是‘右派’?他講了那么多童話。”
兒子,從那張“免冠半身正面照”里,帶著可憐巴巴的神情瞧著他。要不是為了領工作證,兒子是絕對不拍照的。他想像得出兒子的心理,他一定覺得在他的生活里,沒有哪一個瞬間值得留念。
他巴不得兒子像別的孩子一樣,淘氣、喧鬧、撒野、打架……可是不,他總是顯出這種可憐巴巴的樣子。最使他揪心的是,兒子臉上,除了這種可憐巴巴的神情外,在和別人打交道的時候,不論對誰,都顯出一副討好的笑臉,就像一條搖尾乞憐的狗。這比啐他自己的臉,還讓他難受。這種神情,早應該隨著舊生活一同埋葬了。
七二年,兒子被分配到菜站賣肉。他本是個思想開化的人,從來沒想到過以職位高低作為衡量人的價值尺度,也並不介意人們在社會分工上的差別,但是這個社會的常識告訴他,兒子之所以賣肉,當然是因為他的緣故。
從那以後,這本卷了邊兒、磨損了書脊的《珠算口訣》和一把舊算盤,便是兒子業餘時間的全部內容。他或是坐在那張既當餐桌又當書桌的小桌子前,翕動著嘴唇,不出聲地背誦《珠算口訣》,或是噼里啪啦地敲打那箇舊算盤。
而從樓上的視窗里,飄來鄰家姑娘拉《赫曼練習曲》的提琴聲……兒子這時便會讓人聽不出地輕嘆一聲,起身把家裡的玻璃窗關好,也不管是不是三伏天……兒子的算盤早已打得相當出色,在加法和減法的運算上,幾乎可以比肩計算機的準確。可一下班,他還是不停地背誦著、敲著,好像這一切已同吃飯、睡眠一樣,成為兒子生理上的一種需要。
那些不知道兒子出身的顧客,都很喜歡他,讚賞地稱他“一刀準”,他曾悄悄站在那個菜站附近,看兒子賣肉。他看得出來,兒子確實從稱肉和算賬那無盡的循環往復里,得到了工作的滿足和享受。他那慘澹的面孔上,甚至泛起淺淺的紅潤,顯出興奮的神色。那時,他一定感到還有很多人需要他,而不是嫌棄他。
可是,只要一離開那個肉案子,他就會變成另外一個人。
1979年3月
P1-4
完了。
最後一朵光焰閃動了一下,很快就熄滅了。
這就是兒子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個形態。六十五公斤,一米八七,有血有肉的兒子,已經化為一縷青煙,一撮白灰。經過幾千萬年進化才獲得的生命,這么容易地就毀滅了,容易得讓人不能相信。
從火葬場回家後,他本能地回憶起兒子的一生――把二十七個年頭稱為一生,似乎有些誇張。那么短暫,又那么匆忙――可又好像什麼也回憶不起來,他對兒子知道得太少了。
人們常說,男人之間不像女人之間那么容易披露心懷。難道只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才像路人似的生活在一起?
可他算什麼男人?他甚至沒有戀愛過,沒有充分享受過太陽的照耀。
他看著兒子留下的這些東西:一本“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安徒生童話》,一個破舊的鐵皮鉛筆盒,唯一一張一寸“免冠半身正面照”,一本卷了邊兒的《珠算口訣》。
《安徒生童話》是他們家的忌諱,兒子一清二楚。可為什麼他偏偏固執地留存下這本書?
當他被甩出正常的生活軌道時,兒子正是拿著玩具手槍,認準自己便是天下頂了不起的英雄豪傑的年齡。可這位英雄卻不能明白因為什麼,自己便成了頂低下、頂齷齪的東西。
要是有哪個父親,明知自己便是那個砸碎親生兒子的夢想的錘子,而又深深懂得無法逃脫命運的這種安排,他一定體會得到那種痛苦得無法呼吸,像在火里焚燒的滋味。
那時候,兒子還能睜著一雙圓圓的飽含眼淚的眼睛問他:“爸爸,為什麼小朋友都不和我玩了?”
他回答不出。他又怎能讓兒子明白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事情。
有好長一段時間,院子裡那棵桃樹下的螞蟻窩,便是孤寂的兒子的寄託。兒子久久地蹲在那裡,全神貫注地看著忙忙碌碌、來回奔波的螞蟻。它們那充滿生機的、單純而友愛的生活,一定引他生出許多感觸和渴慕。他問過:“爸爸,為什麼螞蟻老是大家一起玩,誰也不丟掉誰呢?”
“不知道。”
“您是大人,為什麼不知道呢?”
兒子哪裡知道,許多問題是大人也回答不了的。
一天,另外一個孩子走了過來,幾腳就蕩平了那個與人無爭的螞蟻王國。
不但他們不和兒子一起玩,甚至也不能容忍兒子和螞蟻一起玩。他知道,小兒子有多么的寂寞,可是他不敢再給他一個弟弟或妹妹來陪伴他,因為,他沒有能力去保護這些無辜的小心靈。
長大一些後,兒子似乎有些明白他的地位,便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著他。仿佛他會傳染一種疾病,凡是得了這種疾病的人,就會被生活拋棄,變成一個孤零零的人。
天真的兒子並不明白,其實他早已被傳染上了這種“疾病”。
他永遠不能忘記,兒子是帶著怎樣可望而不可即的神情,看著飄在別的孩子胸前的紅領巾,如同一個淪落地獄的人,懷著超度來世的虔敬,巴望著天堂。
他曾聽見兒子向妻子發問:“他究竟幹了什麼壞事?”
“誰?”
“他。”
“他是誰?”
“他――父親。”
他感覺得到妻子十分困難地挑選著字眼,“因為他對一位領導,講了一個安徒生的童話。”
“哪個?”
“《皇帝的新衣》。”
“瞎說,為什麼沒有人說安徒生是‘右派’?他講了那么多童話。”
兒子,從那張“免冠半身正面照”里,帶著可憐巴巴的神情瞧著他。要不是為了領工作證,兒子是絕對不拍照的。他想像得出兒子的心理,他一定覺得在他的生活里,沒有哪一個瞬間值得留念。
他巴不得兒子像別的孩子一樣,淘氣、喧鬧、撒野、打架……可是不,他總是顯出這種可憐巴巴的樣子。最使他揪心的是,兒子臉上,除了這種可憐巴巴的神情外,在和別人打交道的時候,不論對誰,都顯出一副討好的笑臉,就像一條搖尾乞憐的狗。這比啐他自己的臉,還讓他難受。這種神情,早應該隨著舊生活一同埋葬了。
七二年,兒子被分配到菜站賣肉。他本是個思想開化的人,從來沒想到過以職位高低作為衡量人的價值尺度,也並不介意人們在社會分工上的差別,但是這個社會的常識告訴他,兒子之所以賣肉,當然是因為他的緣故。
從那以後,這本卷了邊兒、磨損了書脊的《珠算口訣》和一把舊算盤,便是兒子業餘時間的全部內容。他或是坐在那張既當餐桌又當書桌的小桌子前,翕動著嘴唇,不出聲地背誦《珠算口訣》,或是噼里啪啦地敲打那箇舊算盤。
而從樓上的視窗里,飄來鄰家姑娘拉《赫曼練習曲》的提琴聲……兒子這時便會讓人聽不出地輕嘆一聲,起身把家裡的玻璃窗關好,也不管是不是三伏天……兒子的算盤早已打得相當出色,在加法和減法的運算上,幾乎可以比肩計算機的準確。可一下班,他還是不停地背誦著、敲著,好像這一切已同吃飯、睡眠一樣,成為兒子生理上的一種需要。
那些不知道兒子出身的顧客,都很喜歡他,讚賞地稱他“一刀準”,他曾悄悄站在那個菜站附近,看兒子賣肉。他看得出來,兒子確實從稱肉和算賬那無盡的循環往復里,得到了工作的滿足和享受。他那慘澹的面孔上,甚至泛起淺淺的紅潤,顯出興奮的神色。那時,他一定感到還有很多人需要他,而不是嫌棄他。
可是,只要一離開那個肉案子,他就會變成另外一個人。
1979年3月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