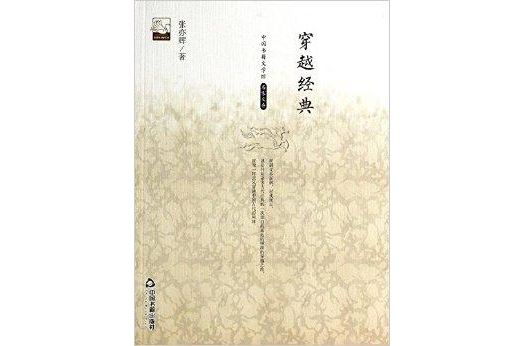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書籍文學館·名家文存:穿越經典
- 出版社:中國書籍出版社
- 頁數:279頁
- 開本:16
- 品牌: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
- 作者:張亦輝
- 出版日期:2014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6839488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中國書籍文學館·名家文存:穿越經典》由中國書籍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張亦輝,1964年出生於浙江東陽,物理學學士,管理學碩士,經濟學副教授,省作協會員。曾長期從事小說寫作,在《作家》、《北京文學》、《小說界》、《世界文學》等雜誌發表過許多作品。已出版小說集《布朗運動》,研究專著《敘述之道》和評論集《小說研究》。近年來潛心研究中國古代經典,對國學有獨特造詣,新著《穿越經典》將在年內出版,曾舉辦過多次國學講演,深受好評。現供職於浙江工商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已有二十八年教學生涯,其中,講授物理十年,講授經濟十年,講授文學八年。
圖書目錄
第一輯《詩經》新義
詩與空間
詩與時間
詩與修辭
詩與原型
興之所至
第二輯《論語》新義
微言大義
疑難章句
有詩為證
第三輯《莊子》新義
道出常道
世外高手
莊子之踵
第四輯《史記》新義
先說刺客
新鞋硌腳
細節制勝
筆法如神
第五輯《陶潛》新義
亦儒亦道
無弦之琴
詩與空間
詩與時間
詩與修辭
詩與原型
興之所至
第二輯《論語》新義
微言大義
疑難章句
有詩為證
第三輯《莊子》新義
道出常道
世外高手
莊子之踵
第四輯《史記》新義
先說刺客
新鞋硌腳
細節制勝
筆法如神
第五輯《陶潛》新義
亦儒亦道
無弦之琴
序言
中華人文精神圖譜與文學敘述譜系的構建
李驚濤
張亦輝先生新近出版專著《穿越經典》,囑我寫序,令我惶恐而又溫暖。惶恐在於我的序文純屬忝列,溫暖在於讓我有了表達對著者了解、對著作理解的機會。有關我對著者了解的敘寫,對於讀者閱讀本書應該是有益的;而對這部專著體系與價值的理解,則是我就教於大方之家的珍稀機會。
按照敘事的時間軸,先從1984年說起,也許是必要和明智的。那年的夏末或秋初,有個20歲的年輕人,提著輕便的行李,從杭州大學啟程,登上了開往中國東部一座沿海城市的火車,到那裡的一所高校任教。行李輕便,是因為夢想沉重;或者說,年輕人用相伴終生、如影隨形的夢想,加重了那座海濱城市在文壇上的分量。因為他的小說創作,文學界對那座中等城市的評價遠超中等;《作家》《小說界》《北京文學》《世界文學》等雜誌,都知道先鋒作家張亦輝先生,即本書著者,就生活、工作在江蘇省的連雲港市。那樣的影響,持續了十幾年,直到張亦輝先生調回闊別的故土——自古繁華的浙江省杭州市,進入浙江工商大學執教。38歲的張亦輝先生重遊西子湖畔,業已不再年輕;但在10年之前,他的辭別依然成為連雲港市文壇的失重事件,給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許多作家和詩人傷心欲絕,有人當場號啕大哭;以至5年以後,有人甚至辭官不做,追隨張亦輝先生來到錢塘江邊,在浙江工商大學附近安了家,見證了本書著者精神上的巨大吸引力量。
說起來匪夷所思,28年前,張亦輝先生獲得的學士學位,是物理學;之後不久,讀取的碩士學位是管理學;高級職稱定位的學科,是經濟學。而他現在執教的學科與專業,卻既非物理學,亦非管理學或經濟學,而是文學,是小說,是寫作,是人文經典。為什麼會是這樣?跨度的確令人驚訝,但卻昭示出張亦輝先生人生追求的定力和清晰的方向感。他2005年出版的專著《敘述之道》,透露出答案的蛛絲馬跡:“生命中有過多年的小說創作經歷,始終倡導先鋒文學的《作家》雜誌曾讓我體驗到寫作的成功大約是怎么一回事。”情況差不多就是這樣。事實上,張亦輝先生的社會影響,正是緣於其先鋒小說的創作成就。在江蘇省,他與畢飛宇、韓東、朱文等作家齊名;在《作家》雜誌,他的小說不僅被推為頭條,還刊發過“個人小輯”——同期登載兩個短篇小說《牛皮帶》《上樓或者下樓》,並配作家創作談,從而奠定了他在先鋒作家行列中的位置。
以小說為夢想,以夢想為天馬,既打造了張亦輝先生在中國東部那座沿海城市的傳奇色彩,也鑄就了他在這個意義不斷被消解的時代中令人費解的價值取向:對金錢和地位的漫不經心甚至無動於衷,對於文學及敘述藝術近乎古怪的激情與摯愛。在我們所處的世界上,擁有類似執拗個性的人,不是沒有,不是很多:瑪麗·斯可羅多夫斯卡是,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也是。張亦輝先生,顯然行走在他們這一脈人當中:“對我而言,文學既是夢想又是宿命,給過我狂喜也給過我絕望,但不管怎樣,我依然認為文學永遠是讓拘束糾結的內心完全敞開的最好方式或途徑。在這個喧譁與騷動的世界上,我始終覺得只有文學才能讓人真正體味到生命的充實和寧靜,在這樣的寧靜里,你方可聽見靈魂的聲音。”
寫到這裡,想必讀者能夠理解我為什麼以壓倒謹慎的大膽,在本書開卷之前,先行介紹著者的相關信息了。不錯,從我的角度理解,本書首先是一位先鋒作家與國學經典的對話,其次才是一位人文學者在對經典的闡釋。儘管對於張亦輝先生而言,他早已將作家與學者複合為一體,成為了“作家型學者”。不過在我看來,經典固在,在圖書館的書架或書房的書櫥里,在網際網路的電子文庫中,安靜地等待著;它們是人類先哲的精神,是期待對話的靈魂,而不是靜候解剖的標本。作家觀照經典,能夠在“生髮學”機理上,與創造經典的前賢擁有更多的思想契合與情感共振;而學者看待經典,通常會先行構建視角,再用放大鏡甚至顯微鏡,按照理論體系自身的方法,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尋找與其觀點相洽的關目,然後或六經注我,或我注六經,最終寫出一摞批評學意義上的自說白話——儘管也自洽和不無道理。這樣的區別,對於釐清“作家型學者”複合體中先“作家”而後“學者”的順序,意味是深長的。
時間被標註為21世紀的今天,張亦輝先生淡出江蘇省連雲港市文壇,已經10年。在錢塘江畔執教期間,他先後出版了文學論著《小說研究》、中短篇小說集《布朗運動》和理論專著《敘述之道》,基本完成了一個先鋒作家有關創作實踐與理論思考的“互文”,將小說創作與敘述之道、作家作品與思潮現象的探索,系統地展示給了讀者。《人民文學》新近推出的張亦輝先生的長篇散文《敘述》,更是見證了本書著者對於敘述藝術的深切感悟與思考。然則一個以漢語為主要武庫進行小說創作的先鋒作家,轉身以學者眼光打量中華人文經典時,會有怎樣的氣象,就有理由成為人們的期待。特別是張亦輝先生在中國東部那座沿海城市結識的朋友們,期待尤甚。張亦輝先生知道這樣的期待,一如他知道對於熙來攘往的世界,經典同樣期待激活,渴望重生。他沒有辜負這份期待,用了5年時間,遴選了部分華文經典,進行了“創造性閱讀”:“那些整體意義上的情感共性與精神原型,以及內部與細部的魔力與神性”(著者語),不僅被他發現,而且獲得了深入、系統的闡釋。《穿越經典》凡五章十九節,拜讀之後,令我憶起厄普代克對於博爾赫斯的評價:“他的小說具有論辯的緊密質地;他的批評論文則有虛構作品的懸念和強度。”我的感受則是:張亦輝先生的小說為漢語寫作創造了“一種難得的‘閱讀一省察’性”;他的理論著述則體現了“作家型學者”在審美精神領域充分的理性自由。
有關本書著者的信息,只是拙文補綴的維度之一。而書中涉及的經典,即呈現給讀者的為什麼是《詩經》《論語》《莊子》《史記》與陶潛詩文,的確令人思量。以我的淺見,上述經典文本,幾近勾勒出1500多年前中華人文精神的一個圖譜。研究華文經典,儒道當為首推,故《論語》《莊子》以兩極入圍,乃是應有之義。南懷瑾先生曾謂儒為“糧店”、道為“藥店”,雖為調侃,或許從某個角度道出了孔子與莊子哲學的分野。但無論人世出世,其世相最終都要通過歷史中人來譜寫,故本書又將《史記》納人觀照範疇。而華人精神序列所衍射的豐富圖景,修齊治平、仁恕孝悌,抑或養生主、逍遙遊並不能夠窮盡;至少,用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說法,還有一個“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的問題。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六經”之中,《詩經》居焉;有詩,而後可以“詩意地棲居”。因此,本書從《詩經》介人,便疏浚了華人精神世界的源頭,亦即探賾到了靈魂的家園。說到這裡,我想起英國作家愛·摩·福斯特試圖給小說下定義時的一個有趣的比方,大意是小說是兩座山峰之間的一片沼澤。福斯特比方的缺陷我們姑且不論,他所說的“兩座峰巒連綿但並不陡峭的山脈”,即指的是“詩”與“歷史”。張亦輝先生同樣是小說家。在他的視野里,詩與歷史,正如中國古典哲學中的儒、道一樣,想必也同樣處於兩極。因此,將《詩經》與《史記》一併輯人本書,也就順理成章、不難理解。作為綰結該書的典型個案,張亦輝先生選取了陶潛詩文,大約緣於此人儒道鹹宜、亦官亦民、但卻真正體現了“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的境界。這樣,本書中涉獵的經典文本,就中華人文精神圖譜而言,雖非巨細無遺,卻也擇其概要,算得上是擷英咀華了。
當然,描繪出中華人文精神圖譜的全息影像,殊為不易;如果在更大尺度的時空坐標中掃描,讀者或許覺得本書似有遺珠之憾。在這裡,我得說,對於中華人文精神圖譜的大致勾勒,實際上是我對本書所涉經典文本的粗淺認知,並非張亦輝先生著述初衷。特別是,張亦輝先生以陶潛詩文綰結全文,還有更為重要而又隱秘的意圖,這一點我們將在後文述及。而本書的治學方法——“穿越”,張亦輝先生倒是有意為之,從而構成了本書與眾不同的特質。
“穿越”的涵義和語境,讀者不難在張亦輝先生的“自序”中廓清;本書中對經典文本以什麼方式和作了哪些“穿越”,開卷即可察知,拙文不便饒舌。張亦輝先生之所以能夠在螺旋時空和不同學科之間從容穿越,可以從詩歌、散文、小說、電影等不同的體裁之間自由進出,並且在古今中西的諸多經典作品裡信步往返,這樣的“穿越”,推想起來,當與他跨越物理學、管理學、經濟學和文學等多種學科,進而形成了複合性知識結構不無關係。這是其一。其二,能夠如此“穿越”,可以認為本書具備了一定的方法論色彩。實際上,春秋以降至於秦漢,中國的文、史、哲並無明顯分野:一部《論語》,哲學、文學、政治學、倫理學、教育學等多種學科,幾乎都可以從中追根溯源。按門類、學科和專業對人類早期的知識集成分門別類。是工業文明帶來的“科學思維”的產物。因此必須承認,從混沌到有序,並非事物本身主動按門類與學科作了自我區分,而是人們在認知過程中受“科學思維”影響生成的錯覺。由此看來,張亦輝先生對華文經典所作的“穿越”,上窮碧落下黃泉,眾里尋他千百度,以作家的創造性思維為主導學理機制,其渠道融通諸多領域,其方法貫通各種學科,突破了理論體系之間的壁障,無疑是一種富有活力的研究方法。而假如學科之間壁壘森嚴,角度與方法雞犬之聲不聞,經典中那些貌似無關、實則神秘存在的聯繫,即張亦輝先生所說的“那些整體意義上的情感共性與精神原型,以及內部與細部的魔力與神性”,便有可能被切割、肢解、醃製、風乾,審美客體只能失去耦合狀態下的整體鮮活性。法無定法,張亦輝先生的方法,渾然而又靈活,庶幾可以抵達真諦的最大臨界值。
既然我們知道混沌是事物的自在狀態,既然我們不難承認張亦輝先生的研究方法新穎有益,那么,現在,也許是面對本書發現的時候了。作為全書壓卷的《無弦之琴》,無疑格外值得關注。張亦輝先生在充分闡釋了陶氏文學敘述的“緘默詩學”的“忘言、不言、互文”等要義之後,騰出筆墨,寫了一段“尾聲或高潮”的文字。正是這段文字,道出了這部專著選擇《詩經》《論語》《莊子》《史記》和陶潛詩文人書的初衷或日最終意圖:藉助上述人文經典,著者發現並建構起了“文學敘述譜系”——文學寫作的“極大值一中間值一極小值”表達序列!這是全書最為核心的理念,亦可以理解為張亦輝先生以此書打造的漢語寫作“敘述之道”。讀者讀罷“尾聲或高潮”後驀然回首,會發現此道在全書中“一以貫之”,即從莊子的“極限表達”到陶潛的“緘默詩學”,足可系統整合、梳理諸多表達範式,諸如微言大義、寓言述道、春秋筆法、互文見義、言此意彼、異位移植、細節制勝、心理還原、形象說事、話語現場、虛詞連綴、復沓、累疊、比、賦、興……,均可以像梁山泊英雄一樣,順利地在敘述譜系中一一排定座次。在這樣的基礎上,張亦輝先生讓我們信服了為什麼《詩經》是漢語修辭的發軔、《論語》是微言大義的富礦、莊子是極限表達的至尊、司馬遷是中國文學的敘述之父、陶潛是沉默詩學的達人。
當然,本書的發現星羅棋布,文字行雲流水,論述縱橫捭闔,剖析遊刃有餘,引證左右逢源,真正體現了“作家型學者”著述的風采。任何文字,都應“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這篇序文也不例外。在文末句號出現之前,我想告訴讀者的是,當年在張亦輝先生餞行宴會上情不自禁、號啕大哭的人,是作家李建軍先生;後來追隨張亦輝先生來到錢塘江畔,並在浙江工商大學附近安家的人,是我。張亦輝先生曾說,我們的友情不受時空的磨損。因此,李建軍先生無需為當年灑淚而赧顏,我卻為自己延宕了五年才辭官不做而羞愧。
謹以為序。
2013年1月7日於錢塘江畔雲水苑
(本序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計量學院人文社科學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李驚濤
張亦輝先生新近出版專著《穿越經典》,囑我寫序,令我惶恐而又溫暖。惶恐在於我的序文純屬忝列,溫暖在於讓我有了表達對著者了解、對著作理解的機會。有關我對著者了解的敘寫,對於讀者閱讀本書應該是有益的;而對這部專著體系與價值的理解,則是我就教於大方之家的珍稀機會。
按照敘事的時間軸,先從1984年說起,也許是必要和明智的。那年的夏末或秋初,有個20歲的年輕人,提著輕便的行李,從杭州大學啟程,登上了開往中國東部一座沿海城市的火車,到那裡的一所高校任教。行李輕便,是因為夢想沉重;或者說,年輕人用相伴終生、如影隨形的夢想,加重了那座海濱城市在文壇上的分量。因為他的小說創作,文學界對那座中等城市的評價遠超中等;《作家》《小說界》《北京文學》《世界文學》等雜誌,都知道先鋒作家張亦輝先生,即本書著者,就生活、工作在江蘇省的連雲港市。那樣的影響,持續了十幾年,直到張亦輝先生調回闊別的故土——自古繁華的浙江省杭州市,進入浙江工商大學執教。38歲的張亦輝先生重遊西子湖畔,業已不再年輕;但在10年之前,他的辭別依然成為連雲港市文壇的失重事件,給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許多作家和詩人傷心欲絕,有人當場號啕大哭;以至5年以後,有人甚至辭官不做,追隨張亦輝先生來到錢塘江邊,在浙江工商大學附近安了家,見證了本書著者精神上的巨大吸引力量。
說起來匪夷所思,28年前,張亦輝先生獲得的學士學位,是物理學;之後不久,讀取的碩士學位是管理學;高級職稱定位的學科,是經濟學。而他現在執教的學科與專業,卻既非物理學,亦非管理學或經濟學,而是文學,是小說,是寫作,是人文經典。為什麼會是這樣?跨度的確令人驚訝,但卻昭示出張亦輝先生人生追求的定力和清晰的方向感。他2005年出版的專著《敘述之道》,透露出答案的蛛絲馬跡:“生命中有過多年的小說創作經歷,始終倡導先鋒文學的《作家》雜誌曾讓我體驗到寫作的成功大約是怎么一回事。”情況差不多就是這樣。事實上,張亦輝先生的社會影響,正是緣於其先鋒小說的創作成就。在江蘇省,他與畢飛宇、韓東、朱文等作家齊名;在《作家》雜誌,他的小說不僅被推為頭條,還刊發過“個人小輯”——同期登載兩個短篇小說《牛皮帶》《上樓或者下樓》,並配作家創作談,從而奠定了他在先鋒作家行列中的位置。
以小說為夢想,以夢想為天馬,既打造了張亦輝先生在中國東部那座沿海城市的傳奇色彩,也鑄就了他在這個意義不斷被消解的時代中令人費解的價值取向:對金錢和地位的漫不經心甚至無動於衷,對於文學及敘述藝術近乎古怪的激情與摯愛。在我們所處的世界上,擁有類似執拗個性的人,不是沒有,不是很多:瑪麗·斯可羅多夫斯卡是,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也是。張亦輝先生,顯然行走在他們這一脈人當中:“對我而言,文學既是夢想又是宿命,給過我狂喜也給過我絕望,但不管怎樣,我依然認為文學永遠是讓拘束糾結的內心完全敞開的最好方式或途徑。在這個喧譁與騷動的世界上,我始終覺得只有文學才能讓人真正體味到生命的充實和寧靜,在這樣的寧靜里,你方可聽見靈魂的聲音。”
寫到這裡,想必讀者能夠理解我為什麼以壓倒謹慎的大膽,在本書開卷之前,先行介紹著者的相關信息了。不錯,從我的角度理解,本書首先是一位先鋒作家與國學經典的對話,其次才是一位人文學者在對經典的闡釋。儘管對於張亦輝先生而言,他早已將作家與學者複合為一體,成為了“作家型學者”。不過在我看來,經典固在,在圖書館的書架或書房的書櫥里,在網際網路的電子文庫中,安靜地等待著;它們是人類先哲的精神,是期待對話的靈魂,而不是靜候解剖的標本。作家觀照經典,能夠在“生髮學”機理上,與創造經典的前賢擁有更多的思想契合與情感共振;而學者看待經典,通常會先行構建視角,再用放大鏡甚至顯微鏡,按照理論體系自身的方法,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尋找與其觀點相洽的關目,然後或六經注我,或我注六經,最終寫出一摞批評學意義上的自說白話——儘管也自洽和不無道理。這樣的區別,對於釐清“作家型學者”複合體中先“作家”而後“學者”的順序,意味是深長的。
時間被標註為21世紀的今天,張亦輝先生淡出江蘇省連雲港市文壇,已經10年。在錢塘江畔執教期間,他先後出版了文學論著《小說研究》、中短篇小說集《布朗運動》和理論專著《敘述之道》,基本完成了一個先鋒作家有關創作實踐與理論思考的“互文”,將小說創作與敘述之道、作家作品與思潮現象的探索,系統地展示給了讀者。《人民文學》新近推出的張亦輝先生的長篇散文《敘述》,更是見證了本書著者對於敘述藝術的深切感悟與思考。然則一個以漢語為主要武庫進行小說創作的先鋒作家,轉身以學者眼光打量中華人文經典時,會有怎樣的氣象,就有理由成為人們的期待。特別是張亦輝先生在中國東部那座沿海城市結識的朋友們,期待尤甚。張亦輝先生知道這樣的期待,一如他知道對於熙來攘往的世界,經典同樣期待激活,渴望重生。他沒有辜負這份期待,用了5年時間,遴選了部分華文經典,進行了“創造性閱讀”:“那些整體意義上的情感共性與精神原型,以及內部與細部的魔力與神性”(著者語),不僅被他發現,而且獲得了深入、系統的闡釋。《穿越經典》凡五章十九節,拜讀之後,令我憶起厄普代克對於博爾赫斯的評價:“他的小說具有論辯的緊密質地;他的批評論文則有虛構作品的懸念和強度。”我的感受則是:張亦輝先生的小說為漢語寫作創造了“一種難得的‘閱讀一省察’性”;他的理論著述則體現了“作家型學者”在審美精神領域充分的理性自由。
有關本書著者的信息,只是拙文補綴的維度之一。而書中涉及的經典,即呈現給讀者的為什麼是《詩經》《論語》《莊子》《史記》與陶潛詩文,的確令人思量。以我的淺見,上述經典文本,幾近勾勒出1500多年前中華人文精神的一個圖譜。研究華文經典,儒道當為首推,故《論語》《莊子》以兩極入圍,乃是應有之義。南懷瑾先生曾謂儒為“糧店”、道為“藥店”,雖為調侃,或許從某個角度道出了孔子與莊子哲學的分野。但無論人世出世,其世相最終都要通過歷史中人來譜寫,故本書又將《史記》納人觀照範疇。而華人精神序列所衍射的豐富圖景,修齊治平、仁恕孝悌,抑或養生主、逍遙遊並不能夠窮盡;至少,用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說法,還有一個“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的問題。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六經”之中,《詩經》居焉;有詩,而後可以“詩意地棲居”。因此,本書從《詩經》介人,便疏浚了華人精神世界的源頭,亦即探賾到了靈魂的家園。說到這裡,我想起英國作家愛·摩·福斯特試圖給小說下定義時的一個有趣的比方,大意是小說是兩座山峰之間的一片沼澤。福斯特比方的缺陷我們姑且不論,他所說的“兩座峰巒連綿但並不陡峭的山脈”,即指的是“詩”與“歷史”。張亦輝先生同樣是小說家。在他的視野里,詩與歷史,正如中國古典哲學中的儒、道一樣,想必也同樣處於兩極。因此,將《詩經》與《史記》一併輯人本書,也就順理成章、不難理解。作為綰結該書的典型個案,張亦輝先生選取了陶潛詩文,大約緣於此人儒道鹹宜、亦官亦民、但卻真正體現了“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的境界。這樣,本書中涉獵的經典文本,就中華人文精神圖譜而言,雖非巨細無遺,卻也擇其概要,算得上是擷英咀華了。
當然,描繪出中華人文精神圖譜的全息影像,殊為不易;如果在更大尺度的時空坐標中掃描,讀者或許覺得本書似有遺珠之憾。在這裡,我得說,對於中華人文精神圖譜的大致勾勒,實際上是我對本書所涉經典文本的粗淺認知,並非張亦輝先生著述初衷。特別是,張亦輝先生以陶潛詩文綰結全文,還有更為重要而又隱秘的意圖,這一點我們將在後文述及。而本書的治學方法——“穿越”,張亦輝先生倒是有意為之,從而構成了本書與眾不同的特質。
“穿越”的涵義和語境,讀者不難在張亦輝先生的“自序”中廓清;本書中對經典文本以什麼方式和作了哪些“穿越”,開卷即可察知,拙文不便饒舌。張亦輝先生之所以能夠在螺旋時空和不同學科之間從容穿越,可以從詩歌、散文、小說、電影等不同的體裁之間自由進出,並且在古今中西的諸多經典作品裡信步往返,這樣的“穿越”,推想起來,當與他跨越物理學、管理學、經濟學和文學等多種學科,進而形成了複合性知識結構不無關係。這是其一。其二,能夠如此“穿越”,可以認為本書具備了一定的方法論色彩。實際上,春秋以降至於秦漢,中國的文、史、哲並無明顯分野:一部《論語》,哲學、文學、政治學、倫理學、教育學等多種學科,幾乎都可以從中追根溯源。按門類、學科和專業對人類早期的知識集成分門別類。是工業文明帶來的“科學思維”的產物。因此必須承認,從混沌到有序,並非事物本身主動按門類與學科作了自我區分,而是人們在認知過程中受“科學思維”影響生成的錯覺。由此看來,張亦輝先生對華文經典所作的“穿越”,上窮碧落下黃泉,眾里尋他千百度,以作家的創造性思維為主導學理機制,其渠道融通諸多領域,其方法貫通各種學科,突破了理論體系之間的壁障,無疑是一種富有活力的研究方法。而假如學科之間壁壘森嚴,角度與方法雞犬之聲不聞,經典中那些貌似無關、實則神秘存在的聯繫,即張亦輝先生所說的“那些整體意義上的情感共性與精神原型,以及內部與細部的魔力與神性”,便有可能被切割、肢解、醃製、風乾,審美客體只能失去耦合狀態下的整體鮮活性。法無定法,張亦輝先生的方法,渾然而又靈活,庶幾可以抵達真諦的最大臨界值。
既然我們知道混沌是事物的自在狀態,既然我們不難承認張亦輝先生的研究方法新穎有益,那么,現在,也許是面對本書發現的時候了。作為全書壓卷的《無弦之琴》,無疑格外值得關注。張亦輝先生在充分闡釋了陶氏文學敘述的“緘默詩學”的“忘言、不言、互文”等要義之後,騰出筆墨,寫了一段“尾聲或高潮”的文字。正是這段文字,道出了這部專著選擇《詩經》《論語》《莊子》《史記》和陶潛詩文人書的初衷或日最終意圖:藉助上述人文經典,著者發現並建構起了“文學敘述譜系”——文學寫作的“極大值一中間值一極小值”表達序列!這是全書最為核心的理念,亦可以理解為張亦輝先生以此書打造的漢語寫作“敘述之道”。讀者讀罷“尾聲或高潮”後驀然回首,會發現此道在全書中“一以貫之”,即從莊子的“極限表達”到陶潛的“緘默詩學”,足可系統整合、梳理諸多表達範式,諸如微言大義、寓言述道、春秋筆法、互文見義、言此意彼、異位移植、細節制勝、心理還原、形象說事、話語現場、虛詞連綴、復沓、累疊、比、賦、興……,均可以像梁山泊英雄一樣,順利地在敘述譜系中一一排定座次。在這樣的基礎上,張亦輝先生讓我們信服了為什麼《詩經》是漢語修辭的發軔、《論語》是微言大義的富礦、莊子是極限表達的至尊、司馬遷是中國文學的敘述之父、陶潛是沉默詩學的達人。
當然,本書的發現星羅棋布,文字行雲流水,論述縱橫捭闔,剖析遊刃有餘,引證左右逢源,真正體現了“作家型學者”著述的風采。任何文字,都應“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這篇序文也不例外。在文末句號出現之前,我想告訴讀者的是,當年在張亦輝先生餞行宴會上情不自禁、號啕大哭的人,是作家李建軍先生;後來追隨張亦輝先生來到錢塘江畔,並在浙江工商大學附近安家的人,是我。張亦輝先生曾說,我們的友情不受時空的磨損。因此,李建軍先生無需為當年灑淚而赧顏,我卻為自己延宕了五年才辭官不做而羞愧。
謹以為序。
2013年1月7日於錢塘江畔雲水苑
(本序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計量學院人文社科學院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