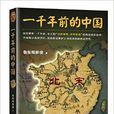《一千年前的中國》內容簡介:這是一個任誰都不敢反叛,卻又任誰都可以欺侮的帝國。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叛亂造反,建立大宋。登基之後,他擔心也有人用同樣的辦法奪權篡位,便連續下令,挑選地方精兵加入自己的禁軍隊伍,只留下一群老弱殘兵守衛地方;將地方政府的錢財賦稅也統統收入國庫,唯恐地方勢力過度發展;並阻止本地人做官,選派親信的中央官員掌握地方大權,試圖將整箇中國都緊緊攥在手中。對內過於嚴苛的統治使得地方各州日益貧弱,無法繼續拱衛中央,宋的對外優勢盡失,無力持續對外作戰,只能軟弱求和,甚至在戰爭獲勝的情況下也步步退縮,與遼議和、與西夏議和、與金議和,煊赫一時的大宋王朝,終於在蒙古戰馬的踐踏下,灰飛煙滅……
基本介紹
- 書名:一千年前的中國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4年3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55900122
- 作者:魯東觀察使
- 出版社:河南文藝出版社
- 頁數:255頁
- 開本:16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一千年前的中國》深度解析一千年前,宋王朝“對內強勢、對外軟弱”的畸形政治選擇;全面揭示選擇背後,統治階層維護自身統治的政治必然性。富有、繁榮的大宋,對內實行密不透風的統治,將半箇中國牢牢掌控在手中;對外卻一再妥協退讓,任憑廣大的領土被外來政權一步步蠶食殆盡。這是一個任誰都不敢反叛,卻又任誰都可以欺侮的帝國!
翻開本書,看一味嚴防內患的大宋,如何在對外敵的軟弱妥協中一步步被蠶食,最終難逃轟然倒塌的命運!
翻開本書,看一味嚴防內患的大宋,如何在對外敵的軟弱妥協中一步步被蠶食,最終難逃轟然倒塌的命運!
作者簡介
魯東觀察使,原名安豐文,長期專注於歷史、國學及經濟學研究,對時代變遷中歷史格局的劇烈轉變有著獨到的體悟,因而決心下筆著書,為讀者揭示每個歷史階段中截然不同的時代主題。
圖書目錄
前 言 軟弱而富足的宋帝國
第一章 一千年前的開封
第二章 挽回對遼戰敗尊嚴:造神運動的興起
第三章 縱容造神的宰相:王旦
第四章 力主抗遼的強硬派人物:寇準
第五章 造神運動的抵制者:楊億
第六章 搜刮民財的財稅專家:丁謂
第七章 宋遼議和的使臣:曹利用
第八章 平壓叛亂的能臣:李迪
第九章 帝國統治的維護者:王曾
第十章 不得重用的良將:楊延昭
第十一章 相安無事的宋遼關係
第十二章 西夏的反攻
第十三章 北宋國策的延續
魯東觀察使曰 宋之興亡
第一章 一千年前的開封
第二章 挽回對遼戰敗尊嚴:造神運動的興起
第三章 縱容造神的宰相:王旦
第四章 力主抗遼的強硬派人物:寇準
第五章 造神運動的抵制者:楊億
第六章 搜刮民財的財稅專家:丁謂
第七章 宋遼議和的使臣:曹利用
第八章 平壓叛亂的能臣:李迪
第九章 帝國統治的維護者:王曾
第十章 不得重用的良將:楊延昭
第十一章 相安無事的宋遼關係
第十二章 西夏的反攻
第十三章 北宋國策的延續
魯東觀察使曰 宋之興亡
序言
軟弱而富足的宋帝國
公元1013年,正是北宋王朝大中祥符六年。
提起大宋朝,難免會引發爭議,一部分人對它扼腕嘆息,頓足捶胸;而另一部分人則對它不吝讚美,慕而神往之。
持貶議者譏它為積貧弱宋,罵它軍事不振,缺乏開疆拓域的氣魄與能力,先受欺於北遼,又受困於西夏,最後錯判形勢,被金國攻破首都汴梁(今河南開封),擄去徽、欽二帝,只餘下半壁江山苟延殘喘。
這些人多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近代受人尊重的歷史學家錢穆先生,他在名著《國史大綱》中明確提出宋朝積貧積弱的觀點。新中國成立後,歷史學家翦伯贊先生在教科書《中國史綱要》中也作如此論述,由此成為官方定論,流布開來。
這種觀點流行的背景,可能與20世紀國中國危機四伏,險遭瓜分豆剖有關。那時,國人急需強國自救,所以感念昔日的漢唐榮光;而宋朝國力不振,屢受欺辱,自淪為反面教材。
對宋朝持讚賞態度者正相反,他們著眼於宋朝的繁榮與溫隋,稱之為中國歷史上最宜居的朝代。這派人喜歡列舉宋朝的財政收人數據,描述它市井的繁華,以證明其富足;談論它技術的進步與商業擴張,以證明其生機與活力;敘說朝廷的寬容與人性化,以證明其理智與開明。他們還常引用北宋易學大師邵雍先生的一段話,證明那個時代為士大夫的樂園。
邵雍的那段話我沒有找到原始出處,權轉引如下:
我幸福,因為我是人,而不是動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國人,而不是蠻族人;我幸福,因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陽。
說明一下,邵雍先生在公元1013年時才兩周歲,還沒上幼稚園,而洛陽當時是宋朝的西京。
有人把宋朝納入全球視野比較,得出的結論是:在一千年前,宋朝是全世界最發達的經濟體,是全球文明的最光明之域,比現今美國在全球體系中的地位還要高。 這種論調的出現,顯然與中國近些年對外開放深化,及國民商業意識的增強相關。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有些人,尤其是許多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開始談論宋朝的現代性問題。在他們看來,宋朝是個很前衛的朝代,它有資本主義的商業元素與科技元素,有現代的中產階級精英元素與市民元素。它繁榮、富足、優雅、溫和、自由,隱隱有成熟的現代已開發國家的影子。
當前,持讚美論者的聲音很大,這些人可分為兩部分:其中主流的一部分,是因為受了某些西方歷史學家的影響,為跟風者;而另一部分雖然小眾,但較踏實——他們通過仔細研究史料,確實發現宋朝雖然軍事上稍弱,但卻經濟繁榮,繁花似錦,據說其經濟總量占當時全球經濟總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對宋朝的地位,海外的研究者一般都不吝讚美之辭,試舉幾例:
美國學者羅茲·墨菲在《亞洲史》中這樣說:“在許多方面,宋朝在中國都是個最令人激動的時代,它統轄著一個前所未見的發展、創新和文化繁盛期……從很多方面來看,宋朝算得上一個政治清明、繁榮和創新的黃金時代。”
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在《東洋近代史》中感嘆:“中國宋代實現了社會經濟的躍進,都市的發達,知識的普及,與歐洲文藝復興現象比較,應該理解為並行和等值的發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東方的文藝復興時代’。”
英國劍橋大學的李約瑟博士認為宋代文化和科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說:“中國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英國或歐洲的水平。”
耶魯大學中國現代史教授史景遷在2000年1月1日《新聞周刊》上刊登文章,稱:“上一個中國世紀是11世紀。當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國家。它的領導地位源於一系列的因素,從技術上的發明到工業企業的興起和管理良好的農業,從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試驗的傳統到對宗教和各種哲學思想的寬容……上一個一千年的中國,是世界超級大國,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當時宋朝的首都在東京汴梁,就是現在的河南開封,人口達百萬,是世界最先進最繁榮最龐大的城市。”
這種讚美的背後其實隱含著這樣一種觀點:一個國家的最高境界應該是社會富足、人民幸福。兵強馬壯反倒是其次。
這讓很多人豁然開竅,原來,一個國家的富與強,並不必然呈因果關係——富了未必強,或者強了未必富,兩者完全能夠分開。換句話說,一個不熱心開疆拓土、揚威域外的國家,照樣能富裕繁榮;反之,一個熱心於軍備、武裝力量強大的國家,也可能非常貧困。
由此牽扯出了一個很有現實意義的問題。
一個國家能像今日的美國一樣,既富且強誠然很好。可是,假如因為各種條件的限制,它沒法實現既富且強,那么它是選擇富而弱呢,還是選擇貧而強?
這也迫使我們思考,當今的中國應該怎樣選擇?假如我們能實現既富且強,當然求之不得,可是假如現實條件不允許我們兩者兼得,我們是放棄強呢,還是放棄富?
有人建議應該搞一次調查,問一問人們,是願意生活在半軍事化管理的秦帝國呢,還是願意生活在軟弱而富足的宋帝國?
這確實很有意思。從情緒上講,很多人可能會選擇一個強字,希望國家能建立起一套秦朝那樣令人望而生畏的戰爭機器,在全球範圍內確立自己的霸權,把所有過去喪失的或有爭議的領土都悉數收回,更莫論東海、南海那幾個小破島。可是從理性上考慮,這卻意味著極大的風險。如果貿然行事,在當前的國際局勢下,極有可能會被人打回原形,重新過一窮二白的日子。基於此,大多數人可能願意選擇低調且富足的生活,希望政府少惹是生非,埋頭髮展經濟,搞好民生問題。
事實上,一千年前的中國——宋真宗時代,也面臨這樣的問題。
宋朝開國,即面臨一個可怕的對頭——北方的超級軍事強國大遼。新興的宋朝試圖挑戰遼國在東亞的霸主地位,雙方爆發了大規模戰爭。
從綜合國力上講,宋朝的實力遠超過遼國。但宋朝的開創者趙匡胤從一開始就不想使自己的帝國軍事化,也不想恢復漢唐的疆域。在他看來,漢唐邊疆地區的許多領土都荒涼貧瘠,不適合農耕,收復得不償失。有了這種理念,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一幕,當王全斌將軍平定西川後,獻上地圖,請求趁勢收復西南諸地區,趙匡胤拿玉斧沿地圖於大渡河上一划,說:“此外非吾有也。”告誡他的將領們不要貪功。他雖沒有再拿玉斧沿著長城劃一划,但他顯然對長城以外的舊日疆土也不抱興趣,他的理想只是要收復陷於遼國的燕雲十三個半州。
在此思想的指導下,他迫不及待地推行倡文抑武的政策,設計出了許多制度,以限制軍隊在帝國體制中的影響力。他的這一努力,正面作用是解除了軍方干預國家政治的風險,負面作用是大大降低了軍隊的戰鬥力。
在這種情勢下,宋朝的經濟雖然增長很快,但在對遼戰爭中卻越來越被動。
到宋真宗執政時,他已充分意識到繼續戰爭沒有出路,遂在公元1004年冬天,忍辱與遼國簽訂了和平條約,結束了那場討厭的戰爭。自此宋朝專心發展國內經濟,開創出一片盛世局面。
不過,戰爭雖然結束了,但其政治後遺症卻一直困擾著朝廷。到公元1013年時,我們依然能看到真宗皇帝與這種後遺症鬥爭的努力。
公元1013年,正是北宋王朝大中祥符六年。
提起大宋朝,難免會引發爭議,一部分人對它扼腕嘆息,頓足捶胸;而另一部分人則對它不吝讚美,慕而神往之。
持貶議者譏它為積貧弱宋,罵它軍事不振,缺乏開疆拓域的氣魄與能力,先受欺於北遼,又受困於西夏,最後錯判形勢,被金國攻破首都汴梁(今河南開封),擄去徽、欽二帝,只餘下半壁江山苟延殘喘。
這些人多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緒,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近代受人尊重的歷史學家錢穆先生,他在名著《國史大綱》中明確提出宋朝積貧積弱的觀點。新中國成立後,歷史學家翦伯贊先生在教科書《中國史綱要》中也作如此論述,由此成為官方定論,流布開來。
這種觀點流行的背景,可能與20世紀國中國危機四伏,險遭瓜分豆剖有關。那時,國人急需強國自救,所以感念昔日的漢唐榮光;而宋朝國力不振,屢受欺辱,自淪為反面教材。
對宋朝持讚賞態度者正相反,他們著眼於宋朝的繁榮與溫隋,稱之為中國歷史上最宜居的朝代。這派人喜歡列舉宋朝的財政收人數據,描述它市井的繁華,以證明其富足;談論它技術的進步與商業擴張,以證明其生機與活力;敘說朝廷的寬容與人性化,以證明其理智與開明。他們還常引用北宋易學大師邵雍先生的一段話,證明那個時代為士大夫的樂園。
邵雍的那段話我沒有找到原始出處,權轉引如下:
我幸福,因為我是人,而不是動物;是男人,而不是女人;是中國人,而不是蠻族人;我幸福,因為我生活在全世界最美好的城市洛陽。
說明一下,邵雍先生在公元1013年時才兩周歲,還沒上幼稚園,而洛陽當時是宋朝的西京。
有人把宋朝納入全球視野比較,得出的結論是:在一千年前,宋朝是全世界最發達的經濟體,是全球文明的最光明之域,比現今美國在全球體系中的地位還要高。 這種論調的出現,顯然與中國近些年對外開放深化,及國民商業意識的增強相關。隨著中國經濟的騰飛,有些人,尤其是許多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開始談論宋朝的現代性問題。在他們看來,宋朝是個很前衛的朝代,它有資本主義的商業元素與科技元素,有現代的中產階級精英元素與市民元素。它繁榮、富足、優雅、溫和、自由,隱隱有成熟的現代已開發國家的影子。
當前,持讚美論者的聲音很大,這些人可分為兩部分:其中主流的一部分,是因為受了某些西方歷史學家的影響,為跟風者;而另一部分雖然小眾,但較踏實——他們通過仔細研究史料,確實發現宋朝雖然軍事上稍弱,但卻經濟繁榮,繁花似錦,據說其經濟總量占當時全球經濟總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對宋朝的地位,海外的研究者一般都不吝讚美之辭,試舉幾例:
美國學者羅茲·墨菲在《亞洲史》中這樣說:“在許多方面,宋朝在中國都是個最令人激動的時代,它統轄著一個前所未見的發展、創新和文化繁盛期……從很多方面來看,宋朝算得上一個政治清明、繁榮和創新的黃金時代。”
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在《東洋近代史》中感嘆:“中國宋代實現了社會經濟的躍進,都市的發達,知識的普及,與歐洲文藝復興現象比較,應該理解為並行和等值的發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東方的文藝復興時代’。”
英國劍橋大學的李約瑟博士認為宋代文化和科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說:“中國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英國或歐洲的水平。”
耶魯大學中國現代史教授史景遷在2000年1月1日《新聞周刊》上刊登文章,稱:“上一個中國世紀是11世紀。當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國家。它的領導地位源於一系列的因素,從技術上的發明到工業企業的興起和管理良好的農業,從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試驗的傳統到對宗教和各種哲學思想的寬容……上一個一千年的中國,是世界超級大國,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當時宋朝的首都在東京汴梁,就是現在的河南開封,人口達百萬,是世界最先進最繁榮最龐大的城市。”
這種讚美的背後其實隱含著這樣一種觀點:一個國家的最高境界應該是社會富足、人民幸福。兵強馬壯反倒是其次。
這讓很多人豁然開竅,原來,一個國家的富與強,並不必然呈因果關係——富了未必強,或者強了未必富,兩者完全能夠分開。換句話說,一個不熱心開疆拓土、揚威域外的國家,照樣能富裕繁榮;反之,一個熱心於軍備、武裝力量強大的國家,也可能非常貧困。
由此牽扯出了一個很有現實意義的問題。
一個國家能像今日的美國一樣,既富且強誠然很好。可是,假如因為各種條件的限制,它沒法實現既富且強,那么它是選擇富而弱呢,還是選擇貧而強?
這也迫使我們思考,當今的中國應該怎樣選擇?假如我們能實現既富且強,當然求之不得,可是假如現實條件不允許我們兩者兼得,我們是放棄強呢,還是放棄富?
有人建議應該搞一次調查,問一問人們,是願意生活在半軍事化管理的秦帝國呢,還是願意生活在軟弱而富足的宋帝國?
這確實很有意思。從情緒上講,很多人可能會選擇一個強字,希望國家能建立起一套秦朝那樣令人望而生畏的戰爭機器,在全球範圍內確立自己的霸權,把所有過去喪失的或有爭議的領土都悉數收回,更莫論東海、南海那幾個小破島。可是從理性上考慮,這卻意味著極大的風險。如果貿然行事,在當前的國際局勢下,極有可能會被人打回原形,重新過一窮二白的日子。基於此,大多數人可能願意選擇低調且富足的生活,希望政府少惹是生非,埋頭髮展經濟,搞好民生問題。
事實上,一千年前的中國——宋真宗時代,也面臨這樣的問題。
宋朝開國,即面臨一個可怕的對頭——北方的超級軍事強國大遼。新興的宋朝試圖挑戰遼國在東亞的霸主地位,雙方爆發了大規模戰爭。
從綜合國力上講,宋朝的實力遠超過遼國。但宋朝的開創者趙匡胤從一開始就不想使自己的帝國軍事化,也不想恢復漢唐的疆域。在他看來,漢唐邊疆地區的許多領土都荒涼貧瘠,不適合農耕,收復得不償失。有了這種理念,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一幕,當王全斌將軍平定西川後,獻上地圖,請求趁勢收復西南諸地區,趙匡胤拿玉斧沿地圖於大渡河上一划,說:“此外非吾有也。”告誡他的將領們不要貪功。他雖沒有再拿玉斧沿著長城劃一划,但他顯然對長城以外的舊日疆土也不抱興趣,他的理想只是要收復陷於遼國的燕雲十三個半州。
在此思想的指導下,他迫不及待地推行倡文抑武的政策,設計出了許多制度,以限制軍隊在帝國體制中的影響力。他的這一努力,正面作用是解除了軍方干預國家政治的風險,負面作用是大大降低了軍隊的戰鬥力。
在這種情勢下,宋朝的經濟雖然增長很快,但在對遼戰爭中卻越來越被動。
到宋真宗執政時,他已充分意識到繼續戰爭沒有出路,遂在公元1004年冬天,忍辱與遼國簽訂了和平條約,結束了那場討厭的戰爭。自此宋朝專心發展國內經濟,開創出一片盛世局面。
不過,戰爭雖然結束了,但其政治後遺症卻一直困擾著朝廷。到公元1013年時,我們依然能看到真宗皇帝與這種後遺症鬥爭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