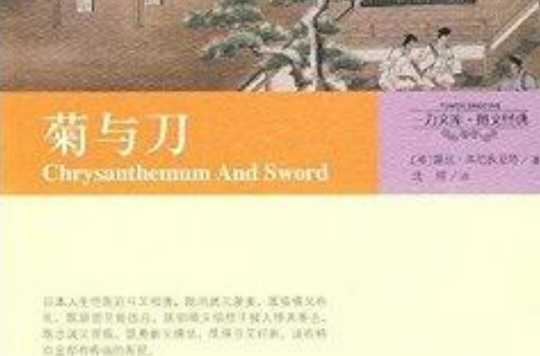《菊與刀》內容簡介:日本人生性既好鬥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有禮,既頑固又能適應,既馴順又惱怒於被人推來推去,既忠誠又背叛,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好新。這些特點全都有極端的表現。
基本介紹
- 書名:一力文庫·圖文經典:菊與刀
- 作者:露絲·本尼狄克特(Ruth Benedict)
- 出版社:文匯出版社
- 頁數:271頁
- 開本:16
- 品牌:鳳凰壹力
- 外文名:Chrysanthemum And Sword
- 譯者:北塔
- 出版日期:2010年3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807415398, 9787807415398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菊與刀》:一力文庫·圖文經典。
作者簡介
露絲·本尼狄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美國人類學家。初學英國文學,後入社會研究新學院學習,開始對人類學產生興趣。其文化形貌論對大眾產生深遠影響,成為美國最著名的人類學家之一。曾獲美國大學婦女聯會傑出女性獎,並擔任美國人類學學會主席、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代表著作《菊與刀》《文化模式》《種族:科學與政治》《人類的種族》等。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全書並不長,除前述首尾兩章外,從對戰爭的看法講起,講到明治維新,再分述日本人風俗習慣、道德觀念,一直到怎樣“自我訓練”(修養)和孩子怎樣學到傳統。全書夾敘夾議,貫串著作者的人類學文化類型論的觀點,一點也不枯燥。
——金克木
1951年此書被列入日本《現代教養文庫》,至1963年已重印三十六次。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紹“日本學”名著的書中稱讚此書是現代日本學的鼻祖,是文化人類學者研究日本的經典性著作。1986年一篇綜述戰後日本研究狀況的文章列舉七種代表性觀點,說《菊與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種。凡此都表明,此書影響至今不衰。
——呂萬和
——金克木
1951年此書被列入日本《現代教養文庫》,至1963年已重印三十六次。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紹“日本學”名著的書中稱讚此書是現代日本學的鼻祖,是文化人類學者研究日本的經典性著作。1986年一篇綜述戰後日本研究狀況的文章列舉七種代表性觀點,說《菊與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種。凡此都表明,此書影響至今不衰。
——呂萬和
名人推薦
新京報 2005年5月13日
我讀《菊與刀》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曉峰
“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美國著名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如是評說。
“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美國著名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研究日本文化的重要著作《菊與刀》中如是概括“最琢磨不透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在她看來,醉心於菊花栽培和崇尚刀劍兩者都是日本民族性這幅繪畫的組成部分。理解《菊與刀》這本書的書名,通常是從這一涵義上。但我認為本尼迪克特以《菊與刀》為這本書命名,用意不止於此。
一場空戰結束,一位日軍大尉第一批飛回基地,他站在那裡,數著歸來的飛機,數完最後一架後他寫了報告,到司令部向基地司令匯報完畢。接著他便倒在地上,身體涼得如冰塊一樣。原來他胸部中了致命傷早已死亡,“因為一個剛斷氣的人身體不可能是涼的”。原來已死去的他,用他的精神、他的“強烈的責任感”支撐著完成了這次報告。這是《菊與刀》的作者選取的一段堂而皇之在戰時日本正式廣播的極端“奇蹟”的報導,來說明戰爭中日本人比西方人更重視精神的作用。要回答那支要“以吾等之訓練對抗敵軍數量上之優勢,以吾等之血肉對抗敵軍之鋼鐵”的軍隊的精神世界是什麼,要理解日本人的這種思維傾向,就要對明治以來統治日本的精神結構進行分析。
如眾所知,《菊與刀》不是通常的學者著書。這本書的基礎是一位人類學家為戰爭期間的美國政府提供對日決策參考而做的研究報告。它的一切論述都服從於一個目的,即揭示一個未知民族的靈魂深處的世界。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則是武士文化的象徵。作者正是從日本人對待天皇的態度入手,通過明治維新以來天皇與武士關係的變化來解剖日本統治思想的演進,從而對上述一問題作出了回答。
本尼迪克特敏銳地注意到,從鎌倉幕府到江戶幕府,天皇儘管權力衰微,仍執有祭祀權力,並一直與以幕府為核心的武家統治方式並存。明治維新後,明治政府把幕府將軍、藩、武士階層取消了,但等級秩序並沒有取消。重新獲得權力的天皇,成為日本內部等級秩序的最頂端,成為超越一切的日本精神的象徵。民眾取代將軍、大名和武士,直接面對天皇盡“忠”。天皇的命令則通過敕令或通過大臣等間接傳遞給民眾。“菊”與“刀”由是重新結構成一個本尼迪克特稱為“雙重體系”的意識結構。
在這個結構里,對所有日本人來說,天皇就是一切。所有的日本軍人,也都是“皇軍”,是天皇的部屬,是神的選民。這一構造的成功之處,在於迅速完成了日本國民意識的整合,而其軟肋則是對已經落後時代的非理性給以絕對強調。由此她得出結論——-日本會投降,要利用日本原有的統治秩序,美國不能直接統治日本。事實果然是即便戰爭勝利無望,神風特攻隊仍拚命用自殺式攻擊報答“皇恩”,但一旦天皇宣布投降,日本人馬上採取完全合作的態度。
《菊與刀》中,還蘊涵著本尼迪克特對日本未來發展的期待。她認為,日本人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付出很大的代價。但是,戰後日本轉入了擴大精神自由的過渡期,一切將有所改變。
在全書將要結束的部分,她講到一位叫杉本的日本夫人。這位夫人在東京教會學習英語時體會到了自由種植花草時的喜悅之情。在日本,那些為參加展覽的盆栽菊花,每朵花瓣均經過栽培者細心修整,用看不見的金屬線圈維繫,以保持形狀。在她的筆下,杉本夫人最後摘掉了那些金屬線圈。那些恢復自然的盆栽菊花滿心喜悅。
本尼迪克特強調,要解放一朵朵被看不見的線圈捆綁的菊花,日本人要負責擦掉自己“刀上的銹”。而這刀“不是進攻的象徵,而是理想和敢於自我負責者的比喻”。讀到這裡我不由得回憶起在日本京都參觀菊展的情形。今天日本盆栽的菊花,栽培時大多依舊纏繞著那些線圈,可見一個民族要改變審美是很難的。不過京都鴨川河原上,秋天裡盛開的野菊花,那份燦爛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轉載自《中國社會學網》
我讀《菊與刀》
周 穎
文化人類學中文化模式論學派的創始人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是一部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名著,有人說是研究日本的文化的一本必讀的書。該書出版於1946年,寫於二戰期間,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戰爭的產物,因為成書的緣由是作者受命於當時的美國戰時情報局,其目的是為給美國對戰後的日本採取何種具體措施提供文化上的參考,它最初僅僅是一份研究觀察報告而已。儘管如此,該書通過對等級制度、“恩”與“報恩” 、義理與人情、恥感文化、修養和育兒方式等的考察,從結構上深入探討了日本人的價值體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為及深藏於其行為之中的思考方法,論述了日本宗教、經濟生活、政治和家庭,探討了日本人有關的生活方式,書中所提出的關於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論和觀點,對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為方式,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時至今日,60年已經過去了,日本的實際情況與本尼迪克特寫作《菊與刀》時已大不一樣了,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為方式也有了相應的變化,甚至還可能與該書中所體現的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為方式截然相反了,但我想,基於文化的傳承性,我們還是可以從中找出其內在的聯繫,對於該書的閱讀在一定程度上也還是有助於我們對日本文化和日本人行為方式的理解的。
《菊與刀》一書主要採用了跨文化比較的方法:與美國、歐洲、中國社會文化對比來分析日本社會文化。因為處於美日兩國交戰時期,本尼迪克特不能夠進行實地調查,因而她退而求其次,採取了人類學家最倚重的方法——與被研究的人民直接接觸。其次利用文獻,分析歷史事件及統計資料、日本的文字宣傳和口頭宣傳看在日本編寫、攝製的電影並與看過的日本人討論。就像很多學者評價的那樣由於作者沒有到過日本,該書存在資料和信息方面的限制等缺陷和不足。我很贊同這個評價——由於作者對中國文化不了解,在中日的比較中,作者的分析也不是很深入,點及即止,因而在閱讀本書時,我做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將日本與我們中國進行了一個比較,發現日本文化與我國文化儘管被認為存在很多的共性,但還是存在很多差異的。
日本是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文化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尤其是中國唐朝文化的影響,但由此就得出日本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簡單的複製的結論,那就錯了。文化是歷史地凝結成的穩定的生存方式,它像血脈一樣,熔鑄在總體性文明的各個層面中,以及人的記憶體規定性之中,自發地左右著人的各種生存活動(衣俊卿 2001,10 轉引自莊嚴2005,29)。人類行為的方式有多種多樣的可能,但是一個民族,只能在這樣無窮的可能性里選擇其中的一些行為方式,形成其獨具特色的文化,這也使得一個民族為一個民族,因為“文化是社會或民族分野的標誌”(鄭杭生2003,75)。文化就是人類行為可能性的不同選擇,“選擇的行為方式包括對待人之生、死、青春期、婚姻的方式,以至在經濟、政治、社會交往等領域的各種規矩,習俗,並通過形式化的方式,演成風俗,禮儀,從而結合成一個部落或部族的文化模式”。文化選擇之初,有一種偶然性的因素。經過歷史的傳替形成文化模式之後,就對生活於其中的個體起到型塑的作用。(衣俊卿2001,10;轉引自莊嚴2005,29)。因而作者從日本人的日常社會生活中來分析日本的文化模式是可能的。“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時代人們普遍認同的,由記憶體的民族精神或時代精神、價值取向、習俗、倫理規範等構成的相對穩定的行為方式”(衣俊卿2001,10;轉引自莊嚴2005,91)。另外文化在傳播過程中必然會有丟失和變化的現象,而在其文化的受者方面也存在著選擇和再加工現象,我們都知道日本特別善於吸收他者文化,因而日本文化異於中國文化就絲毫不奇怪了。
文化人類學研究的主要是“他者”的文化,而對人類學家來說研究在整體上具有許多共性的各民族間的差異最有益。(本尼迪克特2002,7)雖然說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一樣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我們似乎仍然難以理解日本人的奇異行為,多數中國人都是憎恨日本人——這裡有深刻的歷史根源,在此我們無需多談——認為日本人多是一種變態的心理:這樣一個喜歡看相撲的民族,這樣一個極度自我壓抑又自我放縱的民族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侵略戰爭中那些殘暴無人性的獸行,剖腹自殺對天皇的無限效忠都讓我們困惑,就如《菊與刀》中所體現的日本人行為中那種特別的自反對立性:尚禮而又黷武,祥和而激烈,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創新而固執等等——這也是為什麼本尼迪克特給其書命名為《菊與刀》,她以菊的柔美和刀的剛強來分別象徵共存於日本人身上那種對立的雙重性格。
人文社科論衡(BBS)上一個名為legend74在其《菊與刀:“像已死者一樣生活”》說:和中國文化比較起來,日本文化是一種“死亡文化”。中國人重生輕死,認為“不知生,焉知死”,日本人則反過來,他們崇信:不知死,焉知生。死亡狀態是日本人的最高追求,世界上沒有那個民族對死亡像日本人一樣如此痴迷。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言:日本人修身的最高“無我”境界的哲學基礎就是“像已死者一樣生活”。通過這種死亡體驗,日本人將所有的心智都集中在目標上,忘卻自我,“像死人一樣去戰鬥”,基於此日本人所崇尚的“剖腹”、“忍者”就不難理解了。死亡,在日本文化中被賦予了一種至高的美學幻想。只有在死亡中,愛情、道義、責任、忠誠……才成為其所是,才達到最後的完美,《失樂園》中女主角所醉心的“在最美的時候死去”就是最好的體現。既然是已死之人,那么當然就什麼事情都能做的出來,什麼善惡觀念都可以拋棄。但是,一群“死人”又怎么能組成有秩序的活人的社會?於是日本人便將“恥” 納入了其道德體系,“知恥為德行之本”, 對恥辱敏感就會促使人們去實踐善行,因而“知恥之人”也被譯成“有德之人”或“重名譽之人”。日本人認為不遵守明確規定的各種善行標誌,不能平衡各種義務或者不能預見到偶然性的失誤,都是恥辱。《菊與刀》中本尼迪克特說,這個“恥”不同於西方的罪惡,日本人的恥辱於善惡無關,更與原罪無關,而是與所謂的 “榮譽”相關。也就是說,日本人不會因為自己做了惡的事情恥辱,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超越性的善惡觀念。他們的恥辱都是來自他人的評判,只要覺得別人看不起他或者讓他受辱,日本人就會殺人或者自殺。這就是本尼迪克特所說的日本文化是一種“恥感文化”,這與西方的“罪感文化”是不同的。罪感文化提倡建立道德的絕對標準並依靠它發展人的良心,是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所奉行的——人生來就帶有“原罪”,但通過懺悔坦白、贖罪則可以得到解脫,他們是依靠罪惡感在內心的反映來做善行。而日本的恥感文化社會裡那些在罪感文化社會應感到是犯罪行為他們卻只是感到懊惱——不良行為不暴露在社會就不必懊喪,因而依靠外部的強制力來做善行。這也足可以解釋為何德國能夠坦率地承認自己在戰爭對他國所造成的侵略,而日本卻百般否認,不願承認。在我們中國人眼裡的恥辱,歸根結蒂在於求善求仁不能所產生的,在於不能善生,而不在於求死。古人云,知恥近乎勇。這句話在中國人看來,是勇於追求仁善;而在日本人看來,是勇於毀滅一切。
都說日本人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本尼迪克特卻指出,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差之大也,最核心的表現就在對“仁”的態度上。“仁”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為人立身之根本。相反,在日本人那裡,“仁”被貶低地一文不值,被排斥在其倫理體系之外,“是法律範圍以外之事”,“行仁”是即使身居高位也不是必須具備的道德(本尼迪克特2002,83)。所以我們能夠理解為什麼日本人在戰爭中是如此的慘無人道;所以儘管中日都重視“忠”、“孝”,但因為日本人講忠孝,沒有“仁”,這種忠孝就沒有一個超越的本體來制約,最終只能是愚忠和愚孝。因為“忠”、“孝”在日本人看來是無條件的,而對中國人來說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 “仁”。對中國人來說,統治者不仁,大家就可以揭竿而起,父母不仁,孩子就可以以死拒之,甚至大義滅親。而在日本,這是絕不可能被接受的。由於追求無條件的“忠”、“孝”,導致日本從未改朝換代過,而直到90年代,跳槽在日本也是難以被人接收的;而另一方面,日本的婆媳關係、夫妻關係仍然像中國封建社會時期一樣。我們也從這個角度來解釋日本參拜神社的問題——對於日本人來說,山本五十六作為軍人,一生盡“忠”職守,這就夠了,不論他究竟做了什麼都是值得敬奉的,因為根本就沒有“仁”的概念,所以他們一點也不會因為山本五十六的反人類的作為而譴責它,故此他們也無法理解中韓刻骨銘心的反對觀點。
本尼迪克特認為日本社會仍然還是個貴族社會,人們的每一次寒暄、接觸都必須表現出雙方社會距離的性質和程度,他們認為繁密的等級制度就等同於安全穩定,出於對等級制度的信仰和信賴,他們認為必須為建立等級秩序而戰,而以性別、輩分以及長嗣繼承等為基礎的等級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本尼迪克特2002,35)。而等級的差別是以適當的禮儀(如:鞠躬)來確認的,因為行禮就意味著原打算自己處理的事,現在則承認對方有權乾與,受禮的一方則也要承認要承擔與其地位相應的某種責任(本尼迪克特2002,35)。日本社會中每個人的身份都是世襲固定的在皇室和宮廷貴族(公卿)之下,分別是士(武士)、農、工、商,底下是賤民,但賤民往往被排除在社會之外。這些等級之間允許存在流動:通過經商而成為富人的商人可以通過典押和地租的方式成為地主,這與中國封建時期的富人通過買田置地擴大家產成為地主極為相似,此外還可以通過與下層的武士通婚、過繼和收養躋身於武士之列。與崇尚自由平等的美國人不同,日本人並不反對等級制度,相反他們安於此,因為日本人提倡“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只要“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得以維持,日本人就會毫無不滿地活下去。他們就感到安全。他們感到安全是由於視等級制度合法(本尼迪克特2002,66) 。
日本人非常強調“恩”與“報恩”, 同時又有對“恩”的具體理解和獨特的報答方式。所謂“恩”就是一種“被動發生的義務,是承受的負擔、債務和重負”。日本人不主動幫助別人就是出於“隨便插手會讓對方背負恩情” 的考慮,他們甚至認為接受同輩人的“恩”是對自己的一種侮辱。日本人每個人都把自己看作是巨大的負恩者,所以自覺地履行義務而無怨言,並高度重視道德上的報恩。在中國也有“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說法,以怨報德的行為也是被社會所唾棄的。但本尼迪克特認為中國人的恩限定在血緣關係中,但是日本人卻將恩泛化到整個社會結構中,他們將所有的社會關係都理解成受恩和報恩的關係,君主和臣民之間、父母和兒女之間、老師和學生之間,歸根到底都是由“恩”將他們連線在一起。這樣,每個人處於不同的社會角色,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恩情,使得他們自覺履行義務而毫無怨言,實際上也就從社會心理層面闡釋了等級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同時,恩也是一把雙刃劍,人們在受恩的同時常常懷矛盾情緒,“在公認的社會關係中,巨大的欠恩感推動每個日本人竭盡全力以求報恩。但是欠恩又是很難受的,因而也很容易產生反感。”(本尼迪克特2002,74)。
日本社會中與“恩”相對應產生的是“義務”和“情義”。“義務”在時間上是無限的,無論如何償還都是無法全部還清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體現為在對天皇、法律和國家的義務——被稱之為“忠”的“義務”。正是這個“忠”的觀念,讓日本人有了一種對天皇的絕對信仰和服從。我們知道日本的天皇並沒有實權,而只是在等級制度中有個“恰當”的地位,是“軍事將領的某種政治犯”(本尼迪克特 2002,49)而已,但日本人把天皇看作是“國家神道的核心”,認為每一個人都受天皇的“恩”,所以都應該履行對天皇的義務,效忠天皇。因而日本人不管做什麼都覺得自己是在為天皇效忠,包括其參與的各種戰爭,這也是為什麼日本人並不認為他們侵略了其他國家的原因——他們只是執行天皇的命令;這也是為什麼在戰爭失利的情況下人們仍然認為日本這樣一個頑固的民族將拒不投降的時候,日本人能夠在上午簽署休戰條約,下午就放下武器上街購物,並對美國兵採取友好態度的原因——因為是天皇下令的,他們應該服從;這也是日本人為什麼能夠做出剖腹自殺這樣一種極端的自我犧牲行為的原因——這也是為報答天皇的“恩”,而 “榮譽就是戰鬥到死”,“死亡本身就是精神勝利”,自殺是“光榮的、有意義的行為,是最體面的辦法”(本尼迪克特2002,115)。
另外一種則是“情義”,這是應當如數償還的恩情債,在時間上不是無限的。其中有一項是對自己的名聲的情面,具體指的是受到侮辱或遭到失敗時,有“洗刷”污名的義務亦即指報復或復仇的義務。“他們認為,只要受到的侮辱、毀謗及失敗未得到報復,或者未被雪除,'世界就不平穩'一個正派的人就必需努力使世界恢復平衡。這是人的美德,絕不是人性中的罪惡。”(本尼迪克特2002,101)因而在日本,社會允許人們為了洗刷污名而採用各種手段和方法,因為這是正當的。這點與我們中國所提倡的“得饒人處且饒人”、“大人有大量”、“宰相肚裡好撐船”恰恰相反,為我們所熟知的“六尺巷”、以德報怨的故事一直是社會的美談,這些人也是社會頌揚的對象,我們認為通過不正當暴力來肆意報復所遭遇的侮辱是錯誤的,而容忍退讓是暴露對方卑鄙的最好辦法。然而在日本一個人若對自己受辱不採取任何措施的話將被他人瞧不起,因為每個人都有“義務”為自己洗刷污名。但對於社會來說,復仇無法隨時隨地地實行,在任何制度社會中,都會受到時空條件的限制。於是,對復仇的渴望和嚮往在某些時候還會演化成另一種模式,那就是對自我的克制,其最極端的行為也就是自殺——日本人認為自殺是洗刷污名的最高形式,是最體面的辦法。
在日本“情義”是所有階級的共同道德,其準則是必須報答,當“情義”與“忠”相衝突時,人們可以堂堂正正地堅持“情義”,為了情義可以不堅持正義,可以拋妻、棄子、弒父。本尼迪克特在書中提到的日本民族敘事詩《四十七士物語》其主題就是對主君的“情義”。在日本人心裡它寫的是“情義”與“忠”、 “情義”與“正義”的衝突及“單純情義”與無限“情義”的衝突。故事講述的是1703年封建制度鼎盛時期,一大名因沒有送禮而在晉見幕府將軍時著裝錯誤而覺得受辱砍傷對方而被迫剖腹自殺,其家臣即47位勇士為報答其“情義”而犧牲一切,包括名聲、父親、妻子、妹妹、正義,想方設法、忍辱負重為其洗刷恥辱,最後以自殺殉“忠”的故事。在日本為實現“情義”有兩種方法:一、使用侵略手段,二、遵守互敬關係。當前者失敗,則自然地轉向後者,他們並不覺得心理上對自己有何壓力——所以為了維護戰敗的榮譽,日本自然地採取了友好的態度。
本尼迪克特認為日本人矛盾的雙重性格是由日本幼兒教養與成人教養的不連續性造成的。在日本,人生曲線是根很大的淺底的“U”型曲線,社會允許嬰兒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這個時期可以稱為“自由的領地”(本尼迪克特 2002,177)。隨著幼兒期的過去,約束逐漸增加,直到結婚前後個人自由降至最低線,這個過程貫穿了整個壯年期,過了60歲則又可以像幼兒那樣不為羞恥和名譽所煩惱。在美國,人生曲線卻是根倒過來的“U”型曲線:美國的幼兒教育非常嚴格,但隨著孩子的成長而放鬆,直到其能夠自立找到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就幾乎可以不受別人的任何制約,其壯年期是自由個主動性的鼎盛時期。隨著年齡的增長,精力日益衰退,以至成為他人的累贅,就又要受到約束。日本人並不排斥在年輕力壯時受到前所未有的約束,因為他們“相信約束是最好的精神訓練(修養),能夠產生靠自由所不能達到的效果”(本尼迪克特2002,177)。其中,在日本具有特權的幼兒時代,有兩件事情是父母在撫育下一代時為了使其日後能履行義務奠定基礎而必須做的:一是固執地訓練幼兒便溺的習慣並糾正孩子的各種姿勢,如:坐姿、睡姿等;二是父母訓誡、嘲弄孩子,將孩子與其他人進行比較,嚇唬說要遺棄他(她)。通過這些發生使得孩子們有所準備,能夠接受嚴格的約束,以免被“世人”恥笑、遺棄(本尼迪克特2002,198)。在日本,孩子幼年時期建立的一面是“不知恥的自我”,而童年後則是以恥感為道德基礎的各種約束,正是日本這種兒童教養的不連續造成了日本人的兩面性格。(本尼迪克特2002,199)對於本尼迪克特的這個解釋,我覺得是缺乏解釋力的。因為在中國,人們在教養下一代的時候也與日本的方式相差無幾:尊老愛幼一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孩子年幼,所以大人們對他們呵護有加,孩子也如日本的孩子一樣是擁有特權的,他們的要求一般也能夠得到第一位的重視和滿足。而老人,在中國社會裡一直是敬重的對象,不管其在理不在理,人們對老人總是禮讓三分,儘管不像日本那樣是無條件的“孝”,但中國的老人也是有其一定的權威和特權的。而中日對下一代的撫育方式也是相差不大的——中國家長也注重孩子的各種姿勢、禮儀,也固執地訓練幼兒便溺的習慣,對孩子慣常採用的也是訓誡和嘲弄,在孩子不聽話的時候,也會嚇唬孩子說“不要你了”,“你不如某某,知不知羞”等等,筆者就有過類似的經驗,經常被嚇唬說“不要你了,讓那個老乞丐把你帶走好了”,所以一直都對乞丐存有心理上的恐懼。但為什麼中國人沒有出現日本人像那樣矛盾的雙重性格呢?因而對日本人矛盾的雙重性格的形成原因還得從其他方面去尋求。
《菊與刀》一書問世以來受到了不少的讚譽,日本人更是將其作為“鏡中的我”來看待,並以此從中借鑑和認識自我,從而欣賞著者的獨特的見解,再因此而對自我進行調整(川口敦司2000,122),但也存在不少的批評,如美國人道格拉斯·魯米思(C.Douglas Lumis)就指責 《菊與刀》是引導人們誤解日本文化的元兇。中國學者李紹明,則批評本尼迪克特的學派是種族優越論(川口敦司2000,122);另外川口敦司也說“她(本尼迪克特)好象也不太喜歡特殊的個性或非一般性的例證,主要是從習慣、傳統、風俗等類普遍與共性的特點上,去區別和歸納日本文化的模式樣態,這樣也就難免普泛化”(川口敦司2000,122)。儘管大家都質疑本尼迪克特在“遙研”基礎上寫作的此書是否具有解釋力,但我覺得時至今日本尼迪克特這本《菊與刀》仍然是研究日本文化不得不讀的書就足以說明它還是能夠幫助我們去認識和了解日本文化的,在某些事情上——正如我在文章中舉的某些例子——還是有一定的解釋力的。此外,本書所採用的跨文化的比較方法更是文化人類學著作中的經典範本,而本尼迪克特在當時的條件下能夠寫出這樣一本經久不衰的著作更是不能不讓人佩服。 --此文字指本書的不再付印或絕版版本。
我讀《菊與刀》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曉峰
“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美國著名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如是評說。
“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美國著名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她研究日本文化的重要著作《菊與刀》中如是概括“最琢磨不透的”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在她看來,醉心於菊花栽培和崇尚刀劍兩者都是日本民族性這幅繪畫的組成部分。理解《菊與刀》這本書的書名,通常是從這一涵義上。但我認為本尼迪克特以《菊與刀》為這本書命名,用意不止於此。
一場空戰結束,一位日軍大尉第一批飛回基地,他站在那裡,數著歸來的飛機,數完最後一架後他寫了報告,到司令部向基地司令匯報完畢。接著他便倒在地上,身體涼得如冰塊一樣。原來他胸部中了致命傷早已死亡,“因為一個剛斷氣的人身體不可能是涼的”。原來已死去的他,用他的精神、他的“強烈的責任感”支撐著完成了這次報告。這是《菊與刀》的作者選取的一段堂而皇之在戰時日本正式廣播的極端“奇蹟”的報導,來說明戰爭中日本人比西方人更重視精神的作用。要回答那支要“以吾等之訓練對抗敵軍數量上之優勢,以吾等之血肉對抗敵軍之鋼鐵”的軍隊的精神世界是什麼,要理解日本人的這種思維傾向,就要對明治以來統治日本的精神結構進行分析。
如眾所知,《菊與刀》不是通常的學者著書。這本書的基礎是一位人類學家為戰爭期間的美國政府提供對日決策參考而做的研究報告。它的一切論述都服從於一個目的,即揭示一個未知民族的靈魂深處的世界。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則是武士文化的象徵。作者正是從日本人對待天皇的態度入手,通過明治維新以來天皇與武士關係的變化來解剖日本統治思想的演進,從而對上述一問題作出了回答。
本尼迪克特敏銳地注意到,從鎌倉幕府到江戶幕府,天皇儘管權力衰微,仍執有祭祀權力,並一直與以幕府為核心的武家統治方式並存。明治維新後,明治政府把幕府將軍、藩、武士階層取消了,但等級秩序並沒有取消。重新獲得權力的天皇,成為日本內部等級秩序的最頂端,成為超越一切的日本精神的象徵。民眾取代將軍、大名和武士,直接面對天皇盡“忠”。天皇的命令則通過敕令或通過大臣等間接傳遞給民眾。“菊”與“刀”由是重新結構成一個本尼迪克特稱為“雙重體系”的意識結構。
在這個結構里,對所有日本人來說,天皇就是一切。所有的日本軍人,也都是“皇軍”,是天皇的部屬,是神的選民。這一構造的成功之處,在於迅速完成了日本國民意識的整合,而其軟肋則是對已經落後時代的非理性給以絕對強調。由此她得出結論——-日本會投降,要利用日本原有的統治秩序,美國不能直接統治日本。事實果然是即便戰爭勝利無望,神風特攻隊仍拚命用自殺式攻擊報答“皇恩”,但一旦天皇宣布投降,日本人馬上採取完全合作的態度。
《菊與刀》中,還蘊涵著本尼迪克特對日本未來發展的期待。她認為,日本人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付出很大的代價。但是,戰後日本轉入了擴大精神自由的過渡期,一切將有所改變。
在全書將要結束的部分,她講到一位叫杉本的日本夫人。這位夫人在東京教會學習英語時體會到了自由種植花草時的喜悅之情。在日本,那些為參加展覽的盆栽菊花,每朵花瓣均經過栽培者細心修整,用看不見的金屬線圈維繫,以保持形狀。在她的筆下,杉本夫人最後摘掉了那些金屬線圈。那些恢復自然的盆栽菊花滿心喜悅。
本尼迪克特強調,要解放一朵朵被看不見的線圈捆綁的菊花,日本人要負責擦掉自己“刀上的銹”。而這刀“不是進攻的象徵,而是理想和敢於自我負責者的比喻”。讀到這裡我不由得回憶起在日本京都參觀菊展的情形。今天日本盆栽的菊花,栽培時大多依舊纏繞著那些線圈,可見一個民族要改變審美是很難的。不過京都鴨川河原上,秋天裡盛開的野菊花,那份燦爛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轉載自《中國社會學網》
我讀《菊與刀》
周 穎
文化人類學中文化模式論學派的創始人魯思·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是一部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名著,有人說是研究日本的文化的一本必讀的書。該書出版於1946年,寫於二戰期間,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戰爭的產物,因為成書的緣由是作者受命於當時的美國戰時情報局,其目的是為給美國對戰後的日本採取何種具體措施提供文化上的參考,它最初僅僅是一份研究觀察報告而已。儘管如此,該書通過對等級制度、“恩”與“報恩” 、義理與人情、恥感文化、修養和育兒方式等的考察,從結構上深入探討了日本人的價值體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為及深藏於其行為之中的思考方法,論述了日本宗教、經濟生活、政治和家庭,探討了日本人有關的生活方式,書中所提出的關於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論和觀點,對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為方式,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時至今日,60年已經過去了,日本的實際情況與本尼迪克特寫作《菊與刀》時已大不一樣了,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為方式也有了相應的變化,甚至還可能與該書中所體現的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為方式截然相反了,但我想,基於文化的傳承性,我們還是可以從中找出其內在的聯繫,對於該書的閱讀在一定程度上也還是有助於我們對日本文化和日本人行為方式的理解的。
《菊與刀》一書主要採用了跨文化比較的方法:與美國、歐洲、中國社會文化對比來分析日本社會文化。因為處於美日兩國交戰時期,本尼迪克特不能夠進行實地調查,因而她退而求其次,採取了人類學家最倚重的方法——與被研究的人民直接接觸。其次利用文獻,分析歷史事件及統計資料、日本的文字宣傳和口頭宣傳看在日本編寫、攝製的電影並與看過的日本人討論。就像很多學者評價的那樣由於作者沒有到過日本,該書存在資料和信息方面的限制等缺陷和不足。我很贊同這個評價——由於作者對中國文化不了解,在中日的比較中,作者的分析也不是很深入,點及即止,因而在閱讀本書時,我做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將日本與我們中國進行了一個比較,發現日本文化與我國文化儘管被認為存在很多的共性,但還是存在很多差異的。
日本是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文化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尤其是中國唐朝文化的影響,但由此就得出日本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簡單的複製的結論,那就錯了。文化是歷史地凝結成的穩定的生存方式,它像血脈一樣,熔鑄在總體性文明的各個層面中,以及人的記憶體規定性之中,自發地左右著人的各種生存活動(衣俊卿 2001,10 轉引自莊嚴2005,29)。人類行為的方式有多種多樣的可能,但是一個民族,只能在這樣無窮的可能性里選擇其中的一些行為方式,形成其獨具特色的文化,這也使得一個民族為一個民族,因為“文化是社會或民族分野的標誌”(鄭杭生2003,75)。文化就是人類行為可能性的不同選擇,“選擇的行為方式包括對待人之生、死、青春期、婚姻的方式,以至在經濟、政治、社會交往等領域的各種規矩,習俗,並通過形式化的方式,演成風俗,禮儀,從而結合成一個部落或部族的文化模式”。文化選擇之初,有一種偶然性的因素。經過歷史的傳替形成文化模式之後,就對生活於其中的個體起到型塑的作用。(衣俊卿2001,10;轉引自莊嚴2005,29)。因而作者從日本人的日常社會生活中來分析日本的文化模式是可能的。“文化模式是特定民族或特定時代人們普遍認同的,由記憶體的民族精神或時代精神、價值取向、習俗、倫理規範等構成的相對穩定的行為方式”(衣俊卿2001,10;轉引自莊嚴2005,91)。另外文化在傳播過程中必然會有丟失和變化的現象,而在其文化的受者方面也存在著選擇和再加工現象,我們都知道日本特別善於吸收他者文化,因而日本文化異於中國文化就絲毫不奇怪了。
文化人類學研究的主要是“他者”的文化,而對人類學家來說研究在整體上具有許多共性的各民族間的差異最有益。(本尼迪克特2002,7)雖然說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一樣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我們似乎仍然難以理解日本人的奇異行為,多數中國人都是憎恨日本人——這裡有深刻的歷史根源,在此我們無需多談——認為日本人多是一種變態的心理:這樣一個喜歡看相撲的民族,這樣一個極度自我壓抑又自我放縱的民族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侵略戰爭中那些殘暴無人性的獸行,剖腹自殺對天皇的無限效忠都讓我們困惑,就如《菊與刀》中所體現的日本人行為中那種特別的自反對立性:尚禮而又黷武,祥和而激烈,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創新而固執等等——這也是為什麼本尼迪克特給其書命名為《菊與刀》,她以菊的柔美和刀的剛強來分別象徵共存於日本人身上那種對立的雙重性格。
人文社科論衡(BBS)上一個名為legend74在其《菊與刀:“像已死者一樣生活”》說:和中國文化比較起來,日本文化是一種“死亡文化”。中國人重生輕死,認為“不知生,焉知死”,日本人則反過來,他們崇信:不知死,焉知生。死亡狀態是日本人的最高追求,世界上沒有那個民族對死亡像日本人一樣如此痴迷。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言:日本人修身的最高“無我”境界的哲學基礎就是“像已死者一樣生活”。通過這種死亡體驗,日本人將所有的心智都集中在目標上,忘卻自我,“像死人一樣去戰鬥”,基於此日本人所崇尚的“剖腹”、“忍者”就不難理解了。死亡,在日本文化中被賦予了一種至高的美學幻想。只有在死亡中,愛情、道義、責任、忠誠……才成為其所是,才達到最後的完美,《失樂園》中女主角所醉心的“在最美的時候死去”就是最好的體現。既然是已死之人,那么當然就什麼事情都能做的出來,什麼善惡觀念都可以拋棄。但是,一群“死人”又怎么能組成有秩序的活人的社會?於是日本人便將“恥” 納入了其道德體系,“知恥為德行之本”, 對恥辱敏感就會促使人們去實踐善行,因而“知恥之人”也被譯成“有德之人”或“重名譽之人”。日本人認為不遵守明確規定的各種善行標誌,不能平衡各種義務或者不能預見到偶然性的失誤,都是恥辱。《菊與刀》中本尼迪克特說,這個“恥”不同於西方的罪惡,日本人的恥辱於善惡無關,更與原罪無關,而是與所謂的 “榮譽”相關。也就是說,日本人不會因為自己做了惡的事情恥辱,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超越性的善惡觀念。他們的恥辱都是來自他人的評判,只要覺得別人看不起他或者讓他受辱,日本人就會殺人或者自殺。這就是本尼迪克特所說的日本文化是一種“恥感文化”,這與西方的“罪感文化”是不同的。罪感文化提倡建立道德的絕對標準並依靠它發展人的良心,是為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所奉行的——人生來就帶有“原罪”,但通過懺悔坦白、贖罪則可以得到解脫,他們是依靠罪惡感在內心的反映來做善行。而日本的恥感文化社會裡那些在罪感文化社會應感到是犯罪行為他們卻只是感到懊惱——不良行為不暴露在社會就不必懊喪,因而依靠外部的強制力來做善行。這也足可以解釋為何德國能夠坦率地承認自己在戰爭對他國所造成的侵略,而日本卻百般否認,不願承認。在我們中國人眼裡的恥辱,歸根結蒂在於求善求仁不能所產生的,在於不能善生,而不在於求死。古人云,知恥近乎勇。這句話在中國人看來,是勇於追求仁善;而在日本人看來,是勇於毀滅一切。
都說日本人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本尼迪克特卻指出,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差之大也,最核心的表現就在對“仁”的態度上。“仁”乃是中國傳統文化為人立身之根本。相反,在日本人那裡,“仁”被貶低地一文不值,被排斥在其倫理體系之外,“是法律範圍以外之事”,“行仁”是即使身居高位也不是必須具備的道德(本尼迪克特2002,83)。所以我們能夠理解為什麼日本人在戰爭中是如此的慘無人道;所以儘管中日都重視“忠”、“孝”,但因為日本人講忠孝,沒有“仁”,這種忠孝就沒有一個超越的本體來制約,最終只能是愚忠和愚孝。因為“忠”、“孝”在日本人看來是無條件的,而對中國人來說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 “仁”。對中國人來說,統治者不仁,大家就可以揭竿而起,父母不仁,孩子就可以以死拒之,甚至大義滅親。而在日本,這是絕不可能被接受的。由於追求無條件的“忠”、“孝”,導致日本從未改朝換代過,而直到90年代,跳槽在日本也是難以被人接收的;而另一方面,日本的婆媳關係、夫妻關係仍然像中國封建社會時期一樣。我們也從這個角度來解釋日本參拜神社的問題——對於日本人來說,山本五十六作為軍人,一生盡“忠”職守,這就夠了,不論他究竟做了什麼都是值得敬奉的,因為根本就沒有“仁”的概念,所以他們一點也不會因為山本五十六的反人類的作為而譴責它,故此他們也無法理解中韓刻骨銘心的反對觀點。
本尼迪克特認為日本社會仍然還是個貴族社會,人們的每一次寒暄、接觸都必須表現出雙方社會距離的性質和程度,他們認為繁密的等級制度就等同於安全穩定,出於對等級制度的信仰和信賴,他們認為必須為建立等級秩序而戰,而以性別、輩分以及長嗣繼承等為基礎的等級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本尼迪克特2002,35)。而等級的差別是以適當的禮儀(如:鞠躬)來確認的,因為行禮就意味著原打算自己處理的事,現在則承認對方有權乾與,受禮的一方則也要承認要承擔與其地位相應的某種責任(本尼迪克特2002,35)。日本社會中每個人的身份都是世襲固定的在皇室和宮廷貴族(公卿)之下,分別是士(武士)、農、工、商,底下是賤民,但賤民往往被排除在社會之外。這些等級之間允許存在流動:通過經商而成為富人的商人可以通過典押和地租的方式成為地主,這與中國封建時期的富人通過買田置地擴大家產成為地主極為相似,此外還可以通過與下層的武士通婚、過繼和收養躋身於武士之列。與崇尚自由平等的美國人不同,日本人並不反對等級制度,相反他們安於此,因為日本人提倡“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只要“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得以維持,日本人就會毫無不滿地活下去。他們就感到安全。他們感到安全是由於視等級制度合法(本尼迪克特2002,66) 。
日本人非常強調“恩”與“報恩”, 同時又有對“恩”的具體理解和獨特的報答方式。所謂“恩”就是一種“被動發生的義務,是承受的負擔、債務和重負”。日本人不主動幫助別人就是出於“隨便插手會讓對方背負恩情” 的考慮,他們甚至認為接受同輩人的“恩”是對自己的一種侮辱。日本人每個人都把自己看作是巨大的負恩者,所以自覺地履行義務而無怨言,並高度重視道德上的報恩。在中國也有“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說法,以怨報德的行為也是被社會所唾棄的。但本尼迪克特認為中國人的恩限定在血緣關係中,但是日本人卻將恩泛化到整個社會結構中,他們將所有的社會關係都理解成受恩和報恩的關係,君主和臣民之間、父母和兒女之間、老師和學生之間,歸根到底都是由“恩”將他們連線在一起。這樣,每個人處於不同的社會角色,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恩情,使得他們自覺履行義務而毫無怨言,實際上也就從社會心理層面闡釋了等級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同時,恩也是一把雙刃劍,人們在受恩的同時常常懷矛盾情緒,“在公認的社會關係中,巨大的欠恩感推動每個日本人竭盡全力以求報恩。但是欠恩又是很難受的,因而也很容易產生反感。”(本尼迪克特2002,74)。
日本社會中與“恩”相對應產生的是“義務”和“情義”。“義務”在時間上是無限的,無論如何償還都是無法全部還清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體現為在對天皇、法律和國家的義務——被稱之為“忠”的“義務”。正是這個“忠”的觀念,讓日本人有了一種對天皇的絕對信仰和服從。我們知道日本的天皇並沒有實權,而只是在等級制度中有個“恰當”的地位,是“軍事將領的某種政治犯”(本尼迪克特 2002,49)而已,但日本人把天皇看作是“國家神道的核心”,認為每一個人都受天皇的“恩”,所以都應該履行對天皇的義務,效忠天皇。因而日本人不管做什麼都覺得自己是在為天皇效忠,包括其參與的各種戰爭,這也是為什麼日本人並不認為他們侵略了其他國家的原因——他們只是執行天皇的命令;這也是為什麼在戰爭失利的情況下人們仍然認為日本這樣一個頑固的民族將拒不投降的時候,日本人能夠在上午簽署休戰條約,下午就放下武器上街購物,並對美國兵採取友好態度的原因——因為是天皇下令的,他們應該服從;這也是日本人為什麼能夠做出剖腹自殺這樣一種極端的自我犧牲行為的原因——這也是為報答天皇的“恩”,而 “榮譽就是戰鬥到死”,“死亡本身就是精神勝利”,自殺是“光榮的、有意義的行為,是最體面的辦法”(本尼迪克特2002,115)。
另外一種則是“情義”,這是應當如數償還的恩情債,在時間上不是無限的。其中有一項是對自己的名聲的情面,具體指的是受到侮辱或遭到失敗時,有“洗刷”污名的義務亦即指報復或復仇的義務。“他們認為,只要受到的侮辱、毀謗及失敗未得到報復,或者未被雪除,'世界就不平穩'一個正派的人就必需努力使世界恢復平衡。這是人的美德,絕不是人性中的罪惡。”(本尼迪克特2002,101)因而在日本,社會允許人們為了洗刷污名而採用各種手段和方法,因為這是正當的。這點與我們中國所提倡的“得饒人處且饒人”、“大人有大量”、“宰相肚裡好撐船”恰恰相反,為我們所熟知的“六尺巷”、以德報怨的故事一直是社會的美談,這些人也是社會頌揚的對象,我們認為通過不正當暴力來肆意報復所遭遇的侮辱是錯誤的,而容忍退讓是暴露對方卑鄙的最好辦法。然而在日本一個人若對自己受辱不採取任何措施的話將被他人瞧不起,因為每個人都有“義務”為自己洗刷污名。但對於社會來說,復仇無法隨時隨地地實行,在任何制度社會中,都會受到時空條件的限制。於是,對復仇的渴望和嚮往在某些時候還會演化成另一種模式,那就是對自我的克制,其最極端的行為也就是自殺——日本人認為自殺是洗刷污名的最高形式,是最體面的辦法。
在日本“情義”是所有階級的共同道德,其準則是必須報答,當“情義”與“忠”相衝突時,人們可以堂堂正正地堅持“情義”,為了情義可以不堅持正義,可以拋妻、棄子、弒父。本尼迪克特在書中提到的日本民族敘事詩《四十七士物語》其主題就是對主君的“情義”。在日本人心裡它寫的是“情義”與“忠”、 “情義”與“正義”的衝突及“單純情義”與無限“情義”的衝突。故事講述的是1703年封建制度鼎盛時期,一大名因沒有送禮而在晉見幕府將軍時著裝錯誤而覺得受辱砍傷對方而被迫剖腹自殺,其家臣即47位勇士為報答其“情義”而犧牲一切,包括名聲、父親、妻子、妹妹、正義,想方設法、忍辱負重為其洗刷恥辱,最後以自殺殉“忠”的故事。在日本為實現“情義”有兩種方法:一、使用侵略手段,二、遵守互敬關係。當前者失敗,則自然地轉向後者,他們並不覺得心理上對自己有何壓力——所以為了維護戰敗的榮譽,日本自然地採取了友好的態度。
本尼迪克特認為日本人矛盾的雙重性格是由日本幼兒教養與成人教養的不連續性造成的。在日本,人生曲線是根很大的淺底的“U”型曲線,社會允許嬰兒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這個時期可以稱為“自由的領地”(本尼迪克特 2002,177)。隨著幼兒期的過去,約束逐漸增加,直到結婚前後個人自由降至最低線,這個過程貫穿了整個壯年期,過了60歲則又可以像幼兒那樣不為羞恥和名譽所煩惱。在美國,人生曲線卻是根倒過來的“U”型曲線:美國的幼兒教育非常嚴格,但隨著孩子的成長而放鬆,直到其能夠自立找到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就幾乎可以不受別人的任何制約,其壯年期是自由個主動性的鼎盛時期。隨著年齡的增長,精力日益衰退,以至成為他人的累贅,就又要受到約束。日本人並不排斥在年輕力壯時受到前所未有的約束,因為他們“相信約束是最好的精神訓練(修養),能夠產生靠自由所不能達到的效果”(本尼迪克特2002,177)。其中,在日本具有特權的幼兒時代,有兩件事情是父母在撫育下一代時為了使其日後能履行義務奠定基礎而必須做的:一是固執地訓練幼兒便溺的習慣並糾正孩子的各種姿勢,如:坐姿、睡姿等;二是父母訓誡、嘲弄孩子,將孩子與其他人進行比較,嚇唬說要遺棄他(她)。通過這些發生使得孩子們有所準備,能夠接受嚴格的約束,以免被“世人”恥笑、遺棄(本尼迪克特2002,198)。在日本,孩子幼年時期建立的一面是“不知恥的自我”,而童年後則是以恥感為道德基礎的各種約束,正是日本這種兒童教養的不連續造成了日本人的兩面性格。(本尼迪克特2002,199)對於本尼迪克特的這個解釋,我覺得是缺乏解釋力的。因為在中國,人們在教養下一代的時候也與日本的方式相差無幾:尊老愛幼一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孩子年幼,所以大人們對他們呵護有加,孩子也如日本的孩子一樣是擁有特權的,他們的要求一般也能夠得到第一位的重視和滿足。而老人,在中國社會裡一直是敬重的對象,不管其在理不在理,人們對老人總是禮讓三分,儘管不像日本那樣是無條件的“孝”,但中國的老人也是有其一定的權威和特權的。而中日對下一代的撫育方式也是相差不大的——中國家長也注重孩子的各種姿勢、禮儀,也固執地訓練幼兒便溺的習慣,對孩子慣常採用的也是訓誡和嘲弄,在孩子不聽話的時候,也會嚇唬孩子說“不要你了”,“你不如某某,知不知羞”等等,筆者就有過類似的經驗,經常被嚇唬說“不要你了,讓那個老乞丐把你帶走好了”,所以一直都對乞丐存有心理上的恐懼。但為什麼中國人沒有出現日本人像那樣矛盾的雙重性格呢?因而對日本人矛盾的雙重性格的形成原因還得從其他方面去尋求。
《菊與刀》一書問世以來受到了不少的讚譽,日本人更是將其作為“鏡中的我”來看待,並以此從中借鑑和認識自我,從而欣賞著者的獨特的見解,再因此而對自我進行調整(川口敦司2000,122),但也存在不少的批評,如美國人道格拉斯·魯米思(C.Douglas Lumis)就指責 《菊與刀》是引導人們誤解日本文化的元兇。中國學者李紹明,則批評本尼迪克特的學派是種族優越論(川口敦司2000,122);另外川口敦司也說“她(本尼迪克特)好象也不太喜歡特殊的個性或非一般性的例證,主要是從習慣、傳統、風俗等類普遍與共性的特點上,去區別和歸納日本文化的模式樣態,這樣也就難免普泛化”(川口敦司2000,122)。儘管大家都質疑本尼迪克特在“遙研”基礎上寫作的此書是否具有解釋力,但我覺得時至今日本尼迪克特這本《菊與刀》仍然是研究日本文化不得不讀的書就足以說明它還是能夠幫助我們去認識和了解日本文化的,在某些事情上——正如我在文章中舉的某些例子——還是有一定的解釋力的。此外,本書所採用的跨文化的比較方法更是文化人類學著作中的經典範本,而本尼迪克特在當時的條件下能夠寫出這樣一本經久不衰的著作更是不能不讓人佩服。 --此文字指本書的不再付印或絕版版本。
圖書目錄
第一章 任務:日本研究
第二章 戰爭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就其位
第四章 明治維新
第五章 歷史和社會的債務人
第六章 報恩於萬一
第七章 “最難承受”是報答
第八章 洗清名聲
第九章 人之常情
第十章 美德:進退兩難
第十一章 自我修煉
第十二章 童蒙
第十三章 投降後的日本人
第二章 戰爭中的日本人
第三章 各就其位
第四章 明治維新
第五章 歷史和社會的債務人
第六章 報恩於萬一
第七章 “最難承受”是報答
第八章 洗清名聲
第九章 人之常情
第十章 美德:進退兩難
第十一章 自我修煉
第十二章 童蒙
第十三章 投降後的日本人
序言
在人類文明豐富多彩的歷史畫卷上,多少人物,在不同的時代,對不同的問題,從哲學、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論、歷史學與社會學的更深層次上,提出了獨具慧眼的解答,顯示出哲人思想家的睿智。他們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寶貴的思想遺產,為後人繼續探索、不斷前進指明了道路與方向。這次出版的第三批《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書》,涉及不同的學科領域,其內容關係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重大的、思索不息的話題,如:國家的政治制度、科學方法、戰爭與和平、權利與義務、民族獨立、思想自由、制海權力、制度經濟、文明與社會發展、民族人格等。為讀者閱讀方便,這裡分別對各書作簡要的介紹。 --此文字指本書的不再付印或絕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