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一個人的好天氣
- 外文名稱:ひとり日和
- 作品別名:飛特族青春自白:一個人的好天氣
- 創作年代:2007年2月
- 作品出處:日本文學季刊《文藝》2006年秋季號
- 文學體裁:小說
- 作者:青山七惠
內容簡介,作品目錄,創作背景,人物介紹,作品鑑賞,作品主題,創作手法,作品評價,作品影響,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高中畢業的少女知壽隻身來到東京投靠遠房親戚——一個寡居多年的老太婆。知壽不想繼續上學,只想打發日子般地打工,對她來說生活唯一目標就是把日子過下去。當然,她對自己也有個要求,就是存錢存到一百萬日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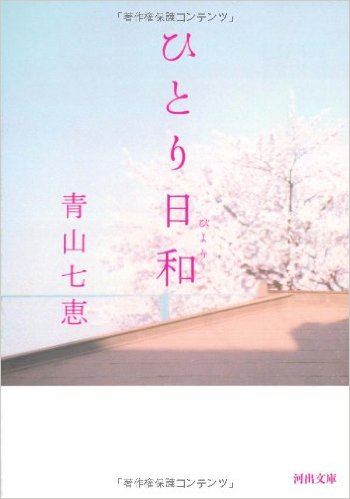 原文作品封面
原文作品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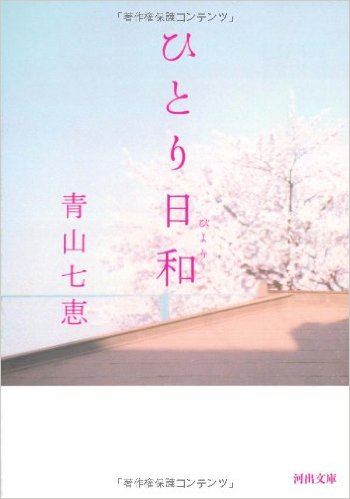 原文作品封面
原文作品封面父母離異,和知壽一直生活在一起的母親終歸也要有自己的生活,對於知壽來說,繼父以及母親離開後的生活,都是難以克服的哀傷;高中畢業,沒有合適穩定的工作,沒有一個明亮的前程,一個不鹹不淡的男朋友一開始看上去就可有可無,身邊沒有聊得來的朋友,更沒有關心她的骨肉親人。知壽作為一個成年人,終日面對一個古稀老人,對於剛過二十歲生日的知壽來說,其中的尷尬可想而知,儘管舅奶奶無論是看上去還是實際上都是好相處的人,可年輕的知壽無論如何還總是難免帶著幾分哀傷。她沒有為自己的未來發愁,卻時常因為乏味的生活而感到愁緒湧上心頭。
作品目錄
 譯者竺家榮簽名版
譯者竺家榮簽名版| 第一章 | 春天 | P3-P34 |
|---|---|---|
| 第二章 | 夏天 | P37-P70 |
| 第三章 | 秋天 | P73-P102 |
| 第四章 | 冬天 | P105-P133 |
| 第五章 | 迎接春天 | P137-P141 |
| *備註 | 目錄頁碼以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出版品為例。 | |
創作背景
據日本官方統計,15至34歲的短期僱工在1996年到2004年之間,達到21.4萬人。調查也顯示,打零工的人收入不穩定,結婚生子的幾率大減,這對少子化嚴重的日本來說是一大警訊。作者青山七惠表示,她之所以寫作該作品,是想告訴日本的年輕一代——只要肯邁出第一步,自然會有出路。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版-封面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版-封面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版-封面
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版-封面寫《一個人的好天氣》時,青山七惠在旅遊公司工作,彼時的她,23歲剛剛大學畢業開始工作。這一年對青山七惠和所有同齡年輕人來說,都是有些矛盾和殘酷的日子,這一年他們都適應成為社會人。從大學的氣氛中邁向社會,殘酷不甘心的心態促成青山七惠創作了該作品。懷著跟過去自己告別的心理,通過《一個人的好天氣》告訴對進入社會懷有恐懼心理的年輕人,其實進入社會並不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人物介紹
知壽
高中畢業的少女,從琦玉到東京生活,寄居在七十歲的東京遠房親戚吟子家中。沒有合適穩定的工作,沒有一個明亮的前程,一個不鹹不淡的男朋友一開始看上去就可有可無,身邊沒有聊得來的朋友,更沒有關心她的骨肉親人。
吟子
知壽的姨奶奶,七十歲獨居在東京的老人。一輩子愛貓、養貓,並把所有去世的貓的照片都掛在房間裡,它們全部叫“徹羅基”。她深知生命的短暫,於柔弱之中保有堅強樂觀的心,經過無數次的“人總是要走的”事實後,最終抵達一種平靜。
作品鑑賞
作品主題
青山七惠以不事雕琢的文風,細膩地講述了一個名叫知壽的日本“飛特族”(自由職業者)在東京生存的細枝末節,突出表現了存在於日本現代青少年身上的心理問題:崇高理想喪失後精神上的隱形疾病。
這篇小說的主人公知壽是一個普通的“飛特族”(自由職業者)。自由職業者在日本是指沒有固定工作的人,也就意味著是沒有社會、醫療保障的打散工人群。在日本社會觀察家三浦展所著的《下流社會》中,這個人群被很現實地描述成下層階級,這個下層階級主導的社會就是一個“下流社會”。作者通過描寫這個身處下層階級的少女“知壽”身上發生的一些生活變故,以及她面對這些時的心情、態度和感受,把一個初入社會的青年應該以何種態度面對社會、人生融入了字裡行間。
在青山七惠筆下,沒有刻意地製造噱頭以滿足年輕人對上一代人的反叛,認同的世俗生活跟常人見到和經歷的沒有什麼不同。
創作手法
青山七惠擺脫了小說必須宏大敘事、引人入勝的羈絆,讓小說各人在幾乎沒有甚么情節可言的生活中生活,更讓《一個人的好天氣》展現著難得一見的乾淨。但乾淨不等於空白,剖白不等於自戀。死去的貓咪照片、車站的離合聚散,點到即止的道理、淺酌輕嘗的抒情,細節中夾雜著每個人物的呼吸和心跳。
小說的講述貌似漫不經心實則苦心經營,文字貌似輕盈實則沉重如鐵,“春、夏、秋、冬、春”這種迴環式的篇章結構富有意味,對虛無感的刻畫深入肌理。如果青山把小說中那些稍嫌冗長的語句去掉,這部小說會更精緻一些。
作品評價
開始的時候,覺得那些對話寫得很真實,漸漸地又為作者的觀察力,或者說是眼光的準確性感到驚喜。《一個人的好天氣》這部作品的“核心”場所是這樣設定的:主人公寄宿的房屋“小院籬笆牆對面就是捷運站,中間只隔著一條小路”。
小說一開始就很不經意地介紹了這個小站。之後它又多次出現在與主人公心情相對應的各種場合,就連在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結尾也出現了。這個車站的站台,是作者依據自己的眼光和觀察力“構築”的,而且它在整個作品中還具有標誌性建築般的象徵意義。主人公以這一場所為媒介,眺望世界,描繪別人眼裡的自己。作者並非“有意識地”設定這一場所及其意義的。應該說是憑藉直覺捕捉了無意中浮現在腦海里的東西。
一個作家,是要通過磨亮視線,接觸從比意識或理性更深一層的領域浮現的東西,並將其掬取來。(日本作家村上龍評)

 芥川獎·受賞儀式
芥川獎·受賞儀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