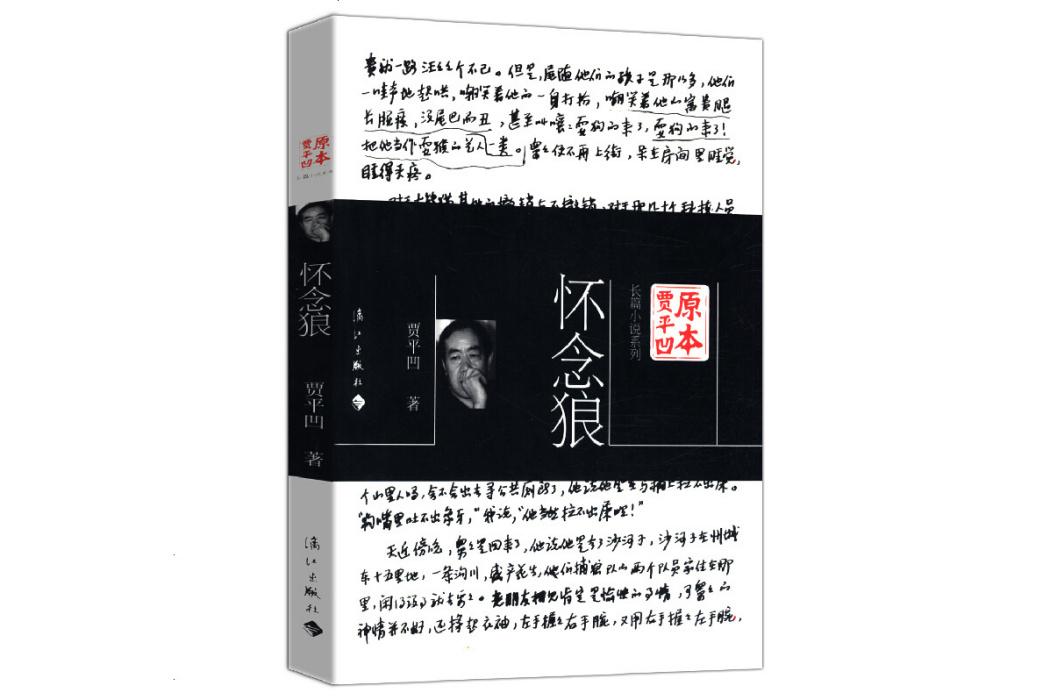內容簡介
商州自古便是野狼肆虐的地區,人和狼發生過不少慘烈的爭鬥。“我”的表舅小時被狼叼走了,後來人們又把他從狼口中奪回,從此脖子上留下了3個怎么也消失不了的疤痕。舅舅後來做了獵人,以打狼為生,並因此享受過不少殊榮。然而世事難料,今天的狼已經成了被保護動物,舅舅也成了行署的生態環境保護委員會的成員,普查了商州所剩15隻狼的詳細情況。
“我”和舅舅在熊貓基地巧遇,在專員的安排下與舅舅一起為這15隻狼照相存檔。在尋找狼的過程中,“我”和舅舅遇到了許多離奇古怪的事情。人與狼的衝突終究不可避免,村里人為打死最後一隻狼而後快,而“我”最終也未能實現保護狼的抱負,獵人們也因為見不到狼的影子而虛弱,一個個得了各種怪病死去。
創作背景
全球化、現代化大背景下,極端發達的高科技、網際網路虛擬世界所導致的人類與大自然隔離,以及由此導致的肌體能力退化和生命危機,以至於在多樣生物面前喪失了安全感;與之相對的是虛擬世界所培育出的征服力的膨脹,靈魂被物質欲望所淤塞的精神生態危機。保護狼這樣一個普通而又平常的生態題材,成為對於人類和地球生物的大關懷與大悲憫,對人性和人的生命力的大批判、大反省。《懷念狼》作品完稿於2000年3月24日。
人物介紹
高子明——“我”
“我”在西京城裡住慣了,久而久之,“我”的生活熱情開始消失。“我”是來自城市的作家兼記者,“我”在鄉下尋狼拍照採風。“我”尋找狼實際上是一次文化上的尋根,“我”與傅山傳奇式的舅甥相認,是“我”尋找到“父親”的開始,而後來與傅山的分離以及傅山的變成人狼,“我”尋找狼拍照的願望未成,都宣告了“我”文化尋根或尋父的失敗。“我”重新成為一個無父的人,一個精神無所皈依的漂泊者。
“我”並沒有成熟的“生態保護”思想,“我”之所以保護狼,竟然是由這樣一些混亂的缺乏科學性的消極思想支持著的:“我”崇拜世間的聲音,總以每日聽到的第一聲音來預測這一天的凶吉禍福,但現在什麼聲音都沒有。由於過高地認識狼對人類生存的“生態”作用和價值,認為雄耳川人由於“長時期的沒有狼,他們在生存競爭中已經變得很虛弱了,“我”竟然建議“專員”向商州投放新的狼種。這個荒唐的建議,理所當然地遭到“村人”的不滿和反對:村人都知道“我”是建議過專員投放新的狼種的,對“我”就冷淡起來。到最後,當狼群真的來了以後,“憤怒的人群”甚至要揍“我”。當狼群已經瘋狂地傷害村人和牲畜的時候,“我”依然站在狼的立場,幫助被圍困的狼逃命,甚至,狐假虎威地抬出“行署”和“公安部門”來威脅那些與狼群進行殊死鬥爭的老百姓。難怪“村里人”要說:“打這狗日的城裡人,城裡人日子過得自自在在,只圖保護狼哩,是這狗日的給傅山灌迷糊湯了,把他捆起來,捆起來。”接著,一陣如雨的拳腳,“我”被打倒了。“我”雙手摟抱了頭,蹲在地上,立即有人從後襠處再次將“我”扳翻,“我”的頭髮被揪起來,衣服也被撕破了,眼前晃動的是無數血紅的眼睛、咬得咯吱咯吱響的牙齒,一口濃痰就落在了“我”的鼻子上。“我”最終是被用一條麻繩捆在了門前的柿樹上。“我”大聲地叫喊我的舅舅,舅舅回頭看了“我”一下,他沒有來救“我”,連一句制止的話也沒有。“我”還在叫:狼只剩下三隻了。眾人哈哈大笑。到最後,在“我”看來,狼被打死,人活的意義也失去了。
傅山
傅山是20世紀50年代全縣聞名的打狼英雄,後來卻奉命去保護已面臨滅種危險、碩果僅存的10隻狼。然而卻因為他思維中所存留的對於狼這種動物生命力旺盛、兇猛而又殘忍、狡猾的定勢,最終陰差陽錯地將狼全部消滅。傅山這個形象既是人類的輝煌與勇敢的象徵,也是人類專制、麻木、偏執與自身生命力萎頓,心理精神生出了病患的生動象徵。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對人類盲目自大、狂妄自尊的自我中心主義的反思與批判
在工業文明高奏凱歌的今天,人類藉助工具理性向大自然猛烈進軍,創造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輝業績。然而,人類也在主體性狂妄的勝利中迷失了自己,走進了人類中心主義的歷史迷霧之中。隨著生態危機的日益嚴峻,人類的生態意識漸漸覺醒,以人與自然關係為核心的生態書寫走向了文學創作的歷史前台。站在動物視角,思考人與自然萬物的關係成為生態文學與生態反思的獨特場域。
1、生態意識之憂
在中國傳統價值觀念體系中,歷來是以人的利益為標尺,把動物分別按“益”“害”“善”“惡”“兇殘”“馴良”等分類,以確定它們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以此傳統,狼幾乎集所有動物之負面形象於一身,被視為貪婪自私、野蠻兇殘的象徵。狼承載了人太多的誤解和惡謚,當人們換種角度不再如此狹隘地看待它時,完全可以從其身上發現生命的莊嚴與高貴。《懷念狼》中幾處對狼之情感意識的書寫,如狼為死去的熊貓獻花以表哀思,為死去同伴悲痛欲絕,集體悼念恩人等情節,體現了賈平凹對動物獨有的生命意識和主體性的關懷與尊重。人並不是這個世界唯一的價值主體,狼有其存在的獨立價值,這種價值並不需要人的主觀賦予,它是客觀存在的。狼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著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和感受,它們應該和人一樣有自己的意識和存在的權利。
《懷念狼》小說中對狼的怪異行為和心理的描寫,可以不認為狼通人性,但至少應該看作狼有狼性。這種狼性也是狼的靈性,作者將其擴而廣之,象徵著自然的靈性。高子明被這種狼性所感染,對狼產生了同情與敬意。其實,對自然生命的敬意源於對其內在價值的承認,人應該像愛護同類一樣去愛護芸芸眾生,因為自然萬物有自身的內在價值。“‘我’堅持靈魂是隨物賦形而上世的,人雖然是萬物之精華,從生命的意義來說,任何動物、植物和人都是平等共處的,強食弱肉或許是生命平衡的調節方式,而狼是生命鏈條的一環。”狼有自身內在的價值,從生命意義和維護生命鏈條的角度而言,狼的內在價值應該得到人的認可與尊重。高子明對狼萌生了價值同情與生命敬意,由被動“尋狼”到自覺“護狼”,生態意識逐步覺醒。面對狼崽,“我”產生了深切的同情。“‘我’想到了‘我’的孩子,孩子在看電視時,一旦有槍戰鏡頭就嚇的將頭塞進母親的懷裡,而這狼目睹了它的長輩被槍殺,它的哥哥或者姐姐被一下子摔死,狼崽也是長心的,它該有多么的恐怖呢?”
在傅山和爛頭的極力圍剿下,數隻狼已經殞命,當他們再次舉起獵槍時,“我”下意識地發出了憤怒的吼叫,“不要打死它。你們殺紅了眼了嗎,一槍也把‘我’打死吧。”並站在狼與傅山中間,企圖阻止傅山和爛頭對狼的屠戮。高子明對狼的處境萌生了深切的同情,並逐漸意識到了狼對於生態平衡的重要意義,狼是整個生命鏈條的一環,沒有了狼,自然和人也必然會蒙受災難。“狼被屠殺的幾近絕跡,如果舅舅和爛頭的病算是一種懲罰,那么更大的懲罰可能就不僅僅限於獵人了。”在這種生態意識的支配下,“我”以個體的行為,以一己之力抗衡著以傅山、爛頭和整個雄耳川人對狼的仇恨與屠戮。然而,無論是對傅山的勸誡,還是對雄耳川人屠狼行徑的阻止,“我”都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該小說中的“我”是一個生態保護者的身份角色,而這種角色並未得到眾人的認同與認可,在族人冷漠的污衊與圍毆下,不得不狼狽地逃回西京。面對毫無生態意識的大眾,個體生態意識的覺醒顯得微弱而蒼白無力。“我”尋狼、護狼行動的失敗,暗含著作者對當下人們生態危機意識不覺醒的深重憂患。
人類認識到以動物為代表的自然界對生態平衡的重要作用,為了生態系統的長久運行應該保護處於“弱勢”地位的自然,然而這種維護生態平衡的意識在人類內心並沒有達到自覺的高度,仍然充斥著現代社會的功利考量,體現著當今社會的浮躁心態。商州行署雖然建立了大熊貓繁殖基地,頒布了禁獵條例,然而以行署專員為代表的地方官員此舉之目的是為了自己的政績;大熊貓繁殖基地的黃姓專家想以繁殖大熊貓來為自己申報職稱;就連“飽含”生態意識的“我”當初也希望為狼拍照建檔而一舉成名。這種不自覺的生態意識正是作者對人類生存困境深深憂患的體現。
2、價值立場之議
賈平凹以“我”尋狼、護狼行動的失敗,表達了對當下生態意識不覺醒的憂思,而當下生態意識的不覺醒不是因為生態問題不夠觸目驚心,而是人類對自己賴以生存的自然界所持的價值立場偏誤所致。在《懷念狼》中,賈平凹對人類這種偏誤的價值立場給予了揭露與批判。人類愚昧地認為,只有人才是這個世界的中心,人之外的所有一切都是為人服務的。在這種愚蠢的自我意識支配下,人類對大自然採取徹底的利用和征服態度,幾乎完全喪失了對大自然內在價值最低限度的尊重和敬畏,對人在大自然中的位置也缺乏基本的理性認識和清醒反思。人總是先驗地把人類視為唯一具有內在價值的生命存在,把其他自然生命僅作為工具對待。其實“人根本不是萬物之冠:每種生物都與他並列在同等完美的階段上。”人不是世界的唯一,只是其中的一員,人不能極端地只考慮自身的利益,完全不顧其他生物的存在。
人類中心主義是一種利己主義,它遵從自利的原則,從自己出發、以自我為中心是其行為主體做出選擇的唯一動機。該作品中的傅山,時刻認為自己是個獵人,而獵人就是為了打狼而生,不能打狼,也就不是獵人了。他將獵狼看作是獵人的天職,將消滅狼作為實現人生價值的目標,這顯然是以人自身的價值和生存為中心來定位人與狼之關係。“人見了狼是不能不打的,這就是人。”人見了狼必然要打,這就是人,這是由人性決定的。因為“人性的首要法則,是要維護自己的生存,人性的首要關懷,是對於其自身應有的關懷”,因為狼威脅到了人的生存,而人要維護自己的生存必須要獵殺狼。人完全是以自己為中心,以自身的利益來考慮這個世界,人之外的一切對人來說只是工具。凡是能夠為人服務的,凡是能夠為人帶來利益的,人便肆無忌憚地去做,什麼都乾,什麼都能幹,什麼都敢幹。人們自私地認為除人以外的一切都是死寂的,沒有生命、意識和內在價值,一切都是以我為中心的,這是一種愚昧無知、低級幼稚、自欺欺人的可怖意識。不可否認,人類自身的生存應該是第一位的,人類的生存也是在對自然的消費和利用中實現的,從人的立場出發,自然理應為人服務,但是自然承載的負荷是有限度的,超出了底線,自然終將走向人類的反面。
《懷念狼》通過人與狼關係失衡的書寫,展開了對人類中心主義價值立場的揭露與批判。人與狼的關係某種意義上而言就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二者相互依存,緊密統一。沒有了獵人狼會自殺,沒有了狼獵人會得各種各樣奇奇怪怪的疾病,獵人和狼是生態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任何一方脫離其間,都難以健康、長久地存在。傅山和爛頭奉行自我中心主義,以滿足自己的私利與私慾為中心,對狼趕盡殺絕,人變成了“人狼”。人是萬物之一,也是這個世界中唯一能夠用關於這個世界的理論來指導其行為的物種。從生態序位來看,人與萬物在這個自然生態系統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如果說人類是其中進化的最高級的物種,是唯一能夠用相應理論來指導其行為的物種,那么人應該認識到這一點,更應該為這個生態系統的健康、長久發展貢獻一己之力,而非一味地占有與索取。該小說結尾,人變成了“狼”,這是賈平凹對人與狼關係失衡的一種思考,也是對人類盲目自大、狂妄自尊的自我中心主義的一種反思與批判。作者提出了一則關於生態危機的警示:如果人類繼續在人類中心主義意識的支配下一意孤行,只能加劇自然與人類的疏離,自然野性的消失必然致使神性與人性的分裂,只能使自命為世界中心的人類失去自然和精神家園,成為無家可歸的病態的幽魂。
3、人性異化之思
生態分為: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自然、社會和人三者是一個相互關聯、不可分割的生態系統。人類對自然界價值立場的偏誤導致人類中心主義觀念的猖行,致使人類的主體性之欲膨脹到了極端的境地,人性漸漸迷失。人與自然關係處理失當,必然引起人與社會、人與自身關係的不和諧。生態危機不僅發生在自然和社會領域,也發生在精神世界。賈平凹敏銳地觀察到了由生態危機帶來的人類精神失衡的危機,並將其通過人與狼的關係表現出來。
人與狼的關係實質上是人與自身的關係。“人見了狼是不能不打的,這就是人。但是人又不能沒有了狼,這就又是人。”人要在與狼的鬥爭中生存,體現生命的力量,因此要打狼;沒有了狼,獵人就喪失了生機與鬥志,失去了生存的動力與意義,故而人離不開狼。人在與狼的鬥爭中征服了狼,體現了主體性的勝利,在征服狼的勝利中確認了人的本質力量;而離開了狼,人便失去了確認本質力量的對象,必然會陷入孤獨、萎靡與異化之中。“人是在鬥爭中成人的,狼的消失使人陷入了驚恐、孤獨、衰弱和卑鄙,乃至於死亡的境地。”沒有了狼,人將會陷入恐懼、孤獨和心態失衡的精神變異之中。正如該小說中所描述的那樣,沒有了狼,獵人患上了莫名其妙的怪病:人極快地衰老和虛弱,神情恍惚,先是精神萎靡、乏力無氣,繼而視力衰弱、手腳發麻,日漸枯瘦。狼被禁止獵殺,捕狼隊解散,獵手們整日將時日消磨在索然無趣的生活之中,似乎除了打架鬥毆、酗酒滋事,他們無所可為,精神上變得異常孤寂、萎靡。精神的病變使得那些曾經彪悍健壯的獵手們患上了無法醫治的稀奇怪病。“動物與其他自然資源構成了人類生存的維持系統,動物的滅絕也意味著人類自身的危機,這是無以逃脫的自然規律。”狼的滅絕,使獵手們陷入了身體變異與精神危機的雙重災難之中,而狼與獵手的關係隱喻著自然與人的關係,人在與狼的鬥爭中維持著自然生態和人性生態的和諧,而人強勢擠壓了狼的生存空間致使了狼的滅絕也直接誘發了自然生態的危機和人的生理病變與精神危機。
賈平凹感受到了人與自然關係失衡之後,必然給人類帶來災難——人性迷失、異化的精神之殤。通過人與狼關係的描寫,賈平凹將目光對準了人與自身的和諧統一,展開了對人性的思考,投射出對當下人類生存境況與精神迷失的憂慮。作者用魔幻手法表達了對現代人性異化的批評與責難。狼消失了,人狼出現了,異化的人性與殘忍的獸性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新物種”的出現,是人性異化的結果,是狼和人變異之後的產物,它沒有遺傳人的善良天性與狼的純真野性,而是將人的貪婪與狼的殘忍變異到了極致。沒有了狼,雄耳川人漸漸浸染上了狼的行為與習性。人異化為了狼,這是使人始料不及的偶然,也是生態危機與精神失衡後的一種必然。為了維護生態的平衡,自然界需要狼;為了人性的和諧,我們要消滅人狼,克服異化。面對日益惡劣的生態危機,人類在精神上越發孤獨、寂寞。戰爭、災難及道德的淪喪使人陷入了深深的恐慌之中。賈平凹對現代社會異化的人性給予了尖銳的批判,對人類現實的生存境況與未來命運展露了思考與憂慮。人類中心主義觀念是生態危機發生的重要因素,也是人類生態意識不覺醒的阻力所在,賈平凹通過人與狼關係的勾勒,對生態意識之薄弱、人類中心主義觀念和人性異化的現狀給予了反思與批判,也通過人與狼之關係建構了人與自然和諧共在的審美理想。
4、審美理想之建
該小說中,如果說高子明與狼之間的關係體現了作者關於生態環境的關注與思索,傅山和爛頭與狼的關係展現了其對人類中心主義思想與人性異化的反思與批評,那么紅岩寺老道士與狼的關係則代表著人與自然審美共在之理想的建構與嘗試。由於人類中心主義觀念的猖行,人類生態意識處於被遮蔽的狀態,在此情景下人類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時採取了極端的征服與利用的方式,致使人類陷入了生存與身心危機之中。賈平凹通過紅岩寺老道士與狼的和諧共處,為人們指明了人與自然審美共在的方向與道路。人與狼之間不能僅僅是對抗,而應是一種主體間性的關係。對抗緩解不了人與自然關係的緊張,只有對話才是正確的航向。人與自然萬物之間,不是主與仆、征服與被征服、主體與客體的關係,而是人類與自然兩個主體之間的互動主體性的平等友愛的對話關係。人與自然萬物都是生態系統中的一個物種,而生態系統中的每個物種都有主體性,都有自己的存在方式與獨特的生存空間,且與生態系統內部其他物種之間都是互動主體性的關係。狼作為生態系統中的一員,它和人一樣有自己感受外部世界的方式,有自己的生存空間和生存權利,而這種生存空間與權利不能被人為侵占與剝奪。只有擺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才能處理好人與自然萬物之間的關係,在人類生存中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在。
《懷念狼》中,人與自然間“與狼共舞”式的審美理想狀態在紅岩寺老道士與狼的關係中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在老道士眼中,狼不是兇殘貪婪的代表,而是像人一樣通情理、有靈性。他像對待同類一樣對待狼和其他生物:紅岩寺有一個神秘的地方。那裡餵養了各種幼小的野獸,一旦這些野獸有了生存的能力,老道就放生了。正是老道士向狼敞開了友好的胸懷,狼也心領神會地讀懂了老道士的善意,當狼生病時便會到紅岩寺來讓老道士醫治,而老道士用木棍清理了狼的膿瘡之後,狼竟前爪跪地嗚嗚了三聲後離去。老道士與狼之間沒有像獵人與狼見面格外眼紅的那種劍拔弩張式的緊張,而是人與人友善和諧的場景。老道士深諳平等相待、和諧共處的生態倫理。他尊重狼的意志,關心狼、愛護狼,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和眾生平等的信念取得了狼的信任。當他歸西彌留之際,仍然對狼心存掛念。
當然,老道士的良苦用心與誠心實意也並沒白費,當他駕鶴歸西之後,狼群自發前來弔唁:以前被老道士醫治過的大狼帶領著五六隻狼,口銜金香玉,在柏樹叢里閃動著綠瑩瑩的光點。狼群前來弔唁老道士,並且帶來了珍貴的禮物,是感恩,也是無言的懷念。這是一幅人狼和諧共處的溫馨畫面。老道士與狼這兩個生態系統中的主體,通過對話建立了一種超越人與動物恩怨的親密和諧的關係,這樣的故事情節看似不切實際,卻暗喻著賈平凹構建人與自然萬物和諧共在的審美理想的嘗試。
《懷念狼》通過對人與狼神秘離奇故事的演繹,蘊含了豐富的生態思想,表達了賈平凹對人類現實生存境況的關注與憂慮、對人與自然審美關係的解讀與構建。通過高子明尋狼、護狼行動的失敗,表達了生態意識不覺醒與缺席的深沉思考;通過人打狼、消滅狼、變成人狼過程的揭示,對人類所持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立場和人性異化的精神現狀給予了尖銳的批判和嚴厲的控訴;通過老道士與狼的和諧共處,展現了其對緩解人與自然緊張關係,構建與狼共舞的審美理想的嘗試與努力。狼在時,人要打狼;狼不在了,人卻需要狼、懷念狼。沒有了狼,人要活下去,只能在心裡有狼了。這是一種生態的悖論。懷念狼,用賈平凹的話是:“懷念勃發的生命,懷念英雄,懷念世界的平衡”,也懷念自然的野性和純性。
藝術特色
《懷念狼》結構線索單純而清晰、脈絡分明。作者主要通過“打狼、尋狼、保狼”“三段式”場景結構構築全篇。它使眾多的事件情節在“段”與“段”之間密切聯繫,互動發展。這些“場”、“段”情節的發展往往都有一個能夠生髮、拓展的物象,它們構成情節三段發展的基本元素和審美意蘊的象徵意象。它們或是關於狼的傳說,或是金香玉石頭,或是狼皮褥子,雖然僅從單一物象上看,它不具有審美的豐富效應,但是它們合構起來就突破了線性因果關係的敘述內容,構成復調、合聲的表意效果,既增強了《懷念狼》整部小說的表現力,又平添了該小說的可讀性和感染力。
打狼:打狼是《懷念狼》情節三段論主線的開端。作為打狼的因由性開端,該文本一開始就向讀者描繪了一幅令人怵目驚心的“狼災匪害”的圖景。而且還將狼災和匪患並行敘述,指出狼、匪本來就一家。正由於狼的猖狂和肆虐,才導致了獵人和捕狼隊的出現。
尋狼:尋狼是《懷念狼》情節三段論主線的發展。在政府干涉下,肩負著“普查”和“拍照”兩項任務,獵人、記者、爛頭一行三人一起找狼。人們尋狼的過程也是贖罪和自我更新的過程。人們尋找狼,也就是希望親和自然和尋覓人類靈魂棲息的最後的家園。
保狼:保狼是《懷念狼》情節三段論主線的結局。傅山也想保狼,他也意識到無狼的恐慌,然而他的英雄獵手的身份決定了他只能站在狼的對立面。爛頭作為一個幫手,在人與自然關係中,他沒有“記者”和“傅山”那么多的顧慮,遊戲、享受人生的生活態度,決定了他不可能有太多的責任感和憂患意識。而明子自始至終是以生態保護者自居,而且為“保狼”付出諸種努力。
“三次找狼”:《懷念狼》中三次寫到找狼,作者從三個斷面展開情節。三次找狼,看似循環往復,但決不是簡單的重複,每一次都有意蘊提升。第一次找狼,人們發現被人馴化的大熊貓生命力脆弱,產仔也不能成活。動物原本是自然生態鏈中的一員,它一旦被人所馴養,就失去自然生命本能,變得脆弱不堪。這種人化的自然現象令人對曾經主體性高揚的現代性反思不已。第二次找狼,人們發現郭財泯滅人性,竟將親生兒女推往車輪下訛人錢財。尤文更是喪心病狂,殺人如麻,竟然有48人死在他的刀下。第三次找狼,作者以誇張的手法,描繪出傅山老家雄耳川人“狼化”的變形現象,暗示著人與自然為敵的結果,只能是自取滅亡。
賈平凹在《懷念狼》簡單的情節結構中,通過“犯中見避”的三段手法使相類似的情節表現出迥不相侔的敘事張力。它使原本就充滿著商山民間信仰生活文化內涵的文本,更顯出古樸而玄妙的意蘊。
魔幻敘述手法
《懷念狼》以魔幻現實主義手法著稱,並通過誇張的描寫讓人真切地感受到狼的智與勇,詭與異。狼會扮人扮豬扮狗,經常迷惑人,並讓人產生幻覺。一個具有魔幻性質的符號是金香玉,舅舅的金香玉來自紅岩寺里的老道士,而老道士的金香玉則來自狼,他救過狼,狼為報恩就送金香玉給老道士。該小說中動物與人的變幻、動物尋常的靈性、山里埋了多少的古時軍隊的喊殺聲仍然時時作響、老道士與狼的和平共處、狼的感恩、相機關鍵時刻莫名其妙地出毛病,無一不具有魔幻性質。從題材的選取、思路的轉換、意境的獨特、人物的怪誕、情事的奇異以至在文字的運用上,《懷念狼》達到了一種新的境界。賈平凹欲借狼來匡時濟世,拯救人類,這是一種抽象精神的呼喚,就不可避免地帶上某種魔幻的氣質。
賈平凹借魔幻的手法讓“狼來了”的故事以新的面目上演。“‘我’的記憶深處出現了在上國小時讀過的那篇《狼來了》的故事,是一個放羊的孩子在高高的山上惡作劇地喊:狼來了——”這個故事裡,狼真的來了,它們原本可以躲進深山老林里更安全的地方,但是,它們來到了雄耳川,以一種自殺式的悲壯姿態,引來人類的殺伐,全軍覆沒。這是全書的結局,也是全書的高潮部分。雄耳川人對狼的恐懼與期盼,狼和人雙方的仇恨與鬥爭,天上下起了瘋狂的大雨,而人卻不停止對狼的獵殺,狼變幻成老者,變幻成配種站的豬,但最後無一倖存。“我”也在子夜時分離開了雄耳川。這個時候,再也沒有狼了,“我”要為狼建立檔案而成為了不起的攝影家的幻想破滅了,將在省城裡更加百無聊賴了。“舅舅從此將真真正正地不是了獵人,同施德主任他們一樣,他活著的意義又將在哪裡呢?這個時候,在‘我’的心裡,‘我’也感覺到在舅舅的心裡,‘我們’都是在真切地懷念狼了。”在該小說結尾處,“我”像古老的“狼來了”的那個故事裡的孩子一樣吶喊,不同的是,那個孩子喊的是“狼來了”,而“我”喊的是“可我需要狼。‘我’需要狼”。
《懷念狼》故事的敘述是從“舅舅”那個關於狼的夢正式開始,以“我”的一個關於狼的夢而結束,狼是夢的主要意象,也是《懷念狼》整部小說的中心意象。在《懷念狼》這部小說中,賈平凹描述了大量的實實在在的人物所做的夢,其中詳細描述了五個夢。該小說中出現的第一個夢是“舅舅”做的夢,“數百隻狼圍住了他,與他謀皮,語氣溫柔,喋喋不休,而且都愛嗔似的在他的手背上點一下趾頭,但數百次在一個部位點,他手背的肉就爛了,白生生的骨頭露出來。”在“舅舅”做這個夢的時候,“州行署頒布了關於保護野生動物禁止捕殺狼的條例,捕狼隊自然而然解散”,並且叫這位曾帶著捕狼隊馳騁野外的獵人去收繳隊友們的獵槍,這於他而言是一個很大的諷刺,所以在此時他做了這個夢。而這個夢的主要意象是狼,所以也可以說這是“懷念狼”的開始。
狼在這裡的象徵意味很濃厚,首先它們象徵著獵人內心的恐懼,這種恐懼表面上是獵人對狼的恐懼,由於獵人賴以生存的工具獵槍已被政府收繳,所以他害怕受到狼群的的報復。而實際上獵人的恐懼並不是源自於狼的威脅,而是源自於狼的即將消失,因為狼的消失便意味著獵人的消失。對於“舅舅”來說,曾經由於狼的存在,他成為了一位備受人們尊敬的大英雄,那是他人生中最輝煌的時刻。狼證明了他生命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當狼消失,他存在的價值也就隨之消失,所以他的潛意識裡才會感到如此的恐懼。其次,這個夢也有一定的預兆性,“舅舅”的這個夢也預示了後來獵人們得了各種怪病的悲慘命運,這也是引發他恐懼的重要因素。作者對這個夢的描寫,細膩地表現了人物的內心恐懼。像“舅舅”這樣的大英雄,他的內心恐懼沒有比通過夢的形式來表現更為恰當的了。因為不管是英雄還是普通人,內心總會有感到恐懼的時候,普通人可能會通過語言或神情傳達出來,而英雄卻不會那么直接表現出來,他會把它壓抑住,從而維持自己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形象。因此,在夢境潛在地表現人物的真實恐懼層面上,賈平凹處理得很到位,他讓“舅舅”的恐懼感通過這種潛意識的夢境表達出來,不僅呼應了主題對狼的恐懼,更是細緻入微地刻畫了“舅舅”這位英雄的深層性格。
“舅舅”的第二個夢,是在銀耳川和村民們大規模捕殺剩下的最後幾隻狼之前喝了酒之後所做的,他夢見了小時候曾經差點把他吃掉的那隻狼,這隻狼已經一百五十歲了,這是他第一次夢見這隻狼。這個夢暗示了“舅舅”對於狼的一種極深的恐懼和捕殺狼的欲望。在這五個夢裡,有兩個是“舅舅”所做的夢,都和狼有關,狼的意象貫穿著他夢裡夢外的生活。
其餘的三個夢都是高子明做的。同樣,這三個夢也很好地刻畫了高子明當時的心理活動,並推動了故事情節的發展。比如,高子明的第一個夢是在“舅舅”離他們而去之後做的。“舅舅”的離去是因為“舅舅”殺了狼,高子明因此沒收了他的獵槍並且養了狼崽。高子明夢見“舅舅”就像野獸一樣要死在一個山洞裡,這暗含了高子明對“舅舅”的想念和憂慮,其實也是高子明對於野性的呼喚。高子明的最後一個夢是在該小說的結尾,這夢和《懷念狼》小說一開始“舅舅”做的那個夢一樣,都是夢見狼,夢見和狼掙皮。《懷念狼》做的夢預示了獵人們的病,夢是該小說中人物內心恐懼的暗示。
詞語意象
1、狼
狼是《懷念狼》中的核心形象。作者既想讓它成為推動情節發展的動力源,又把它當做主題和意義的承載體。狼可以被處理成兩種完全不同的象徵形象。一種是消極的。它的兇險而殘忍的本性,使它適合用來象徵那些給人帶來恐懼、威脅和傷害的否定性力量。狼的這種消極的象徵形象,在該小說中,是最為常見的。對於殘忍的人,狼就是他最好的象徵符號。
狼的惡象徵:狼是一種具有野性的動物,兇猛異常,毀過城池,傷過人類,被人們深惡痛絕,是兇惡的化身。自從鬧了狼災後,狼的野蠻、兇殘、對血肉的追逐像釘子一樣留在了人們的意識深處。狼的惡名就這樣傳了下來。
而賈平凹在向讀者灌輸的是保護生態平衡的思想,導入的角度卻獨特新穎,他從人與狼的關係著手,告訴人們一個不易察覺的道理:人的生活中不能沒有狼/動物,人與狼/動物的關係既對立又統一,正是狼/動物的存在,顯示了人生命的偉力,一旦沒有了狼/動物,人失去了較量的對象,處在無物之陣中,便只能退化。
狼的另一種象徵形象是積極的。它象徵著孤獨、憤怒、被逼入絕境的絕望的生存者,象徵著那些拒絕接受現存生活秩序和價值體系,而與社會保持疏離姿態甚至對抗姿態的人。這樣的象徵形象,具有令人震驚的諷喻力量,有助於人們更深刻地認識時代生活所存在的問題,所面臨的價值危機和道德困境。
狼作為人類的恐懼象徵,人卻在世世代代的恐懼中生存繁衍下來,如今與人相鬥相爭了幾千年的狼突然要滅絕,似乎沒有了狼,人類就活不下去,世界就要毀滅。重視狼的生態價值是應該的,但把它當做影響人類生死存亡的重大因素,則是荒唐的。然而,有了荒唐的想法,就會有荒唐的行為。
2、頭痛
《懷念狼》小說共有處直接或間接提到獵人爛頭頭痛病發作河以說他的頭痛病貫穿故事始終。爛頭剛一出場,作者交代他名字的緣由就是他患有頭痛病。接著,讀者可以感受到他發病時的痛苦。他頭痛起來,就得讓人用拳頭捶打他的腦袋才垂得咚咚地響,看過了許多醫生,卻斷不清病因,只是每日服三次藥來緩解痛苦。
頭痛病是一種常見的疾病,病因複雜。頭痛病隱喻人性的萎縮。爛頭在隨著傅山、“我”尋狼的途中,路上講的是性玩笑,一路上拈花惹草。爛頭首次犯病,是講述烏龜發情的故事,故事沒有講完,爛頭的頭就痛起來了,他“額頭上的血管,蚯蚓一樣地暴起來”。他服了藥,請“我”舅舅用手背在他頭上重重地敲打後,才緩解頭疼。頭痛隱喻人性的萎縮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矛盾。
作品評價
《懷念狼》既不是消極意義上的象徵,又不是真正積極意義上的象徵;既缺乏必要的明晰性,又缺乏充分的深刻性。
——李建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懷念狼》頗具有尋根文學“異鄉異聞”的味道。
——王軍(大連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懷念狼》具有荒誕色彩的敘述。
——黃亞清(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作者簡介
賈平凹,中國當代作家。1952年出生於陝西南部的丹鳳縣棣花村。父親是鄉村教師,母親是農民。“
文化大革命”中,家庭遭受毀滅性摧殘,淪為“可教子女”。1972年以偶然的機遇,進入西北大學學習漢語言文學。此後,一直生活在西安,從事文學編輯兼寫作。出版的主要作品:《商州》《浮躁》《
廢都》《白夜》《
高老莊》《懷念狼》《
秦腔》《古爐》《
帶燈》等。

賈平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