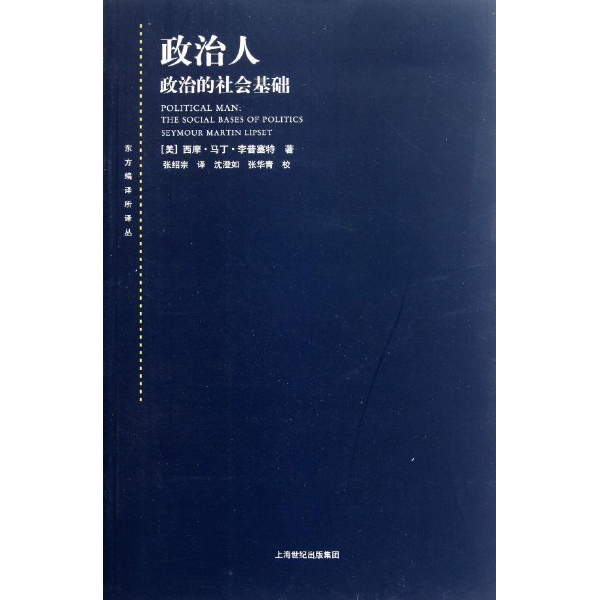基本介紹
- 中文名:“政治人”假設
- 概述:“政治人”是人類對於自身本
- 提出:“政治人”假設最早是由
- 內涵:根據亞里士多德在《政
基本介紹,提出,內涵,理論價值,實踐意義,
基本介紹
“政治人”是人類對於自身本質的第一個認識。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和古代中國的思想家荀子幾乎同時形成了這樣的認識。此後兩千多年,“政治人”成為人性假設中最主要的內容,在日常社會交往中,政治活動也就成了最重要的活動之一。亞里士多德當時所要探討的問題是:人類為何一定要過這種“城邦”(今天歐洲語言中的“政治”[polifies]一詞就是古希臘“城邦”[poHs]一詞的衍化)的演化。他提到,相互依存的兩個生物必須結合,其種類才能得到延續。對於人類,這種結合的形式就是家庭,在家庭的基礎上,由若干個家庭聯合組成村莊,再由若干個村莊聯合組成城邦。這時,社會就進化到高級而完備的境界。如此看來,城邦的形成是由於人類生活的自然發展,其存在的理由是為了使人類過上“優良的生活”。也就是說,“城邦”是自然的產物,是社會團體發展的終點,體現了自然的本性。亞里士多德寫道:“由此可以明白城邦出於自然的演化,而人類自然是趨向於城邦生活的動物。” 這裡的後一句話,按其本義,也可譯為:“人類在其本性上,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這就是後人廣泛引用的亞里士多德那句名言— — “人是政治的動物”的藍本。接著亞里士多德進一步探討:作為動物,人類為什麼能比蜂類或其它群居動物所結合的團體達到更高的政治組織呢?答案就在於人類有語言和理性。有了理性,人類就可以辨認善和惡、正義和不正義以及其它類似的觀念;有了語言,人類就可以把這種理性的認識相互傳達;有了語言和理性,人類就可以形成思想上的共識,進而結成政治上的共同體——“城邦”。
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的協調發展是以人對自己的認識為思想前提的。關於人性的認識則是人對自己的認識的核心內容。在關於人性的認識中,“經濟人”假設、“政治人”假設和“文化人”假設是幾個最為基本的認識。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按其發展的側重點可以邏輯地依次分為經濟發展史、政治發展史和文化發展史,其中政治發展史(或稱政治文明建設史)處於人類社會發展的中間階段,成為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中介。相應的,“政治人”假設則是政治發展、政治文明建設的必要的人性基礎。為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對“政治人”假設這一政治發展、政治文明的人性基礎進行深人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提出
“政治人”假設最早是由古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提出來的。這個假設通常的表達是:“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
亞里士多德關於“政治人”的假設是在分析古希臘城邦時代人們的生存狀態時做出來的。他首先注意到當時人們生存的一個基本事實;凡人都生活於城邦之中。他說:凡脫離城邦的人,“如果不是一隻野獸,那就是一位神祗”,“不是一個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那么,人為什麼要過這樣的城邦生活呢?他作了一個簡單的還原分析:兩個生物必須結合,其種類才能得以延續,對於人類來講,這種結合的形式就是家庭。若干個家庭就組成了村坊,再由若干個村坊就組成了城邦。因此,“城邦”是自然的產物。在總結城邦生成的這一自然過程時,亞里士多德說到:“由此可以明白城邦出於自然的演化,而人類是趨向於城邦生活的動物”。由於“政治”(Politis)就是由“城邦”(Polis)一詞衍化而來的,“人類是趨向於城邦生活的動物”這個假設也就可以解讀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
“政治人”假設除了字面上告訴我們的信息外,它內在的豐富內涵是什麼?它於人的全面發展,社會的協調發展有何重要價值呢?
內涵
根據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對“政治人”假設的各種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政治人”假設以下三方面的豐富內涵。
1.人是具有合群性、群居性、社會性的動物。
人是具有合群性、群居性、社會性的動物,這是“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這一“政治人”假設的最基本的含義。“人是政治動物”的含義首先在於表達:“像某些種類的動物一樣,人在任何地方都聚合為大於家庭的群體,甚至當他們並不需要相互幫助的時候也力求群聚”在這裡,“政治性”就等於“群居性”、“合群性”、“社會性”。馬克思在談到亞里士多德這個假設時,也明確指出了“政治人”假設的社會性含義,他說:“人即使不像亞里士多德所說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他在另一個地方還說到:“人是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
2.人是具有利益協調能力,即“政治能力”的動物。
僅僅看到“政治人”假設表達的人的合群性、群居性、社會性的人性特徵是不夠的。深入發掘“政治人”假設的內涵,我們就會看到“政治人”假設對人的利益協調能力即政治能力的肯定。這是亞里士多德在把人類的合群性與其它動物做比較後得出的結論。他認為,人與任何蜂群和獸群相比更大意義上是“政治動物”。因為在動物中只有人有語言和理性,語言和理性可以用來揭示利害,因而也揭示正義和不正義;善與惡。在理性的引導下,在語言的溝通中,人類實現了利益協調。? ”這種理性認識、溝通能力與利益協調能力就是政治能力。因此,人比任何群居動物有著更高級的特性,即利益協調性,也就是狹義的政治性。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
3.人是具有合作精神的動物
按照亞里士多德的分析,人不僅是合群的、群居的社會性動物,也是具有利益協調能力的政治性動物,而且是“最優秀的政治動物” ,”這個最優秀的動物“優秀”在哪裡,就在於因人聚合而成的城邦,就在於以合作為本質的城邦關係。亞里士多德反覆講到:以為城邦僅僅由其成員對外在利益的分享而構成的觀點是錯誤的——城邦是這樣一種合作關係,它的構成的一個關鍵方面,是人們分享某種有關善或正義的生活方式的概念。亞里士多德假定了一種獨一無二的合作關係,它比其它合作關係具有權威性且包含了它們的特殊目的或目標,這種合作關係即是城邦。因此,他認為,城邦是一種合作關係,是聯合體或共同體,亦即共同分享或持有某些東西的一群人。他進一步認為,好公民的基本職能在於維護政治合作關係。( 亞里士多德在這裡一再強調城邦(政治)的合作本性,強調城邦(政治)追求至善的價值目標,它構成“政治人”假設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內容。
把上述三個方面的內容結合起來,“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這個“政治人”假設的基本內涵就是:人是一種具有社會性的、具有利益協調能力的,並追求友善合作,追求社會的至善和諧的動物。
理論價值
將“政治人”假設的豐富內涵與人類政治生活結合起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政治人”假設在人類社會政治治理,政治國家的形成及存在,以及人類政治文明發展中的重要價值。
1.“政治人”假設為人類社會政治治理提供了必要的人性假設。
“政治人”假設首先是一個“人性假設”,即首先是對人的本性、人的本質、人之為人的基本規定的一種假定說明。這個人性假設與“經濟人”假設,“文化人”假設一道構成了人類社會治理的人性基礎。對此,有學者認為,正是對人的本性的不同認識,構成了人類社會管理的不同理念和發展階段。“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認識到‘人是政治動物’,揭示了人類管理史上的政治人時代;二百多年前,英國學者亞當·斯密認識到‘人是經濟的動物’,開啟了人類管理史上的‘經濟人’時代;今天,在跨人21世紀的時候,人們認識到‘人是文化的動物’,我們進人了人類管理史上的‘文化人’時代”。一部人類管理史也就可以大致劃分為“經濟管理”時代、“政治管理時代”和“文化管理時代”。 這個認識無疑是極有價值的。但是,我們不能由此就得出結論:“政治管理”已經退出人類社會管理的歷史舞台而進人了歷史博物館。恰恰相反,“政治人”任何時候都是人之為人的基本性質,“政治管理”任何時期都是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
對比“政治人”、“經濟人”和“文化人”三個人性假設,“經濟人”假設雖然晚於“政治人”假設提出(這實際上是“西方中心論”的觀點,中國人早就知道,“人不為已,天誅地滅”),但是“經濟人”的現實卻是人與生俱來的。從某種意義上講,經濟人的自利性實際上是一切生命體的共性,而不是人之為人的個性。相比之下,“政治人”卻真是人從動物中挺立起來,人類社會從自然界中分化出來首先獲得的第一個本性。至於“文化人”的性質則是一種後天逐步獲得,並且日新月異發展變化的性質。因此,如果硬要對“政治人”、“經濟人”和“文化人”三個性質排一個序的話,從歷史的角度,似乎應是從“經濟人”到“政治人”再到“文化人”的發展。並且,這三個性質不是歷時性地一個取代一個,而是後者包含前者,三者是以各自不同的份量共時共存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這一“政治人”假設是人永恆的本性假設,以“政治人”假設為其人性基礎的政治管理,則是以“經濟管理”為基礎,以“文化管理”為牽引的社會管理,並成為人類社會管理的永恆的組成部分。
2.“政治人”假設為政治國家的形成和存在提供了必要的社會基礎。
“政治人”假設不僅是一個人性假設,它還是一個“國家起源假設”。亞里士多德本來就是在描述古希臘城邦國家的自然形成時提出“政治人”假設的。“家庭—— 村坊—— 國家”這一國家的“自然生成論”破除了關於國家起源問題上的一切奇談怪論。首先,國家不是神的意志的體現,不是上帝、上天的安排。國家關係不是人與神的結合,而是人與人的結合。正如<國際歌=}裡面唱到的一樣,“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其次,國家也不是從來就是強權階級謀取私利的暴力工具。雖然在人類幾千年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國家確實一度扮演了這樣的角色。但是,國家一開始並不是這樣的,它也不會永遠是這樣的。因為國家的本質是利益協調,“城邦是一種合作關係”。人們組成國家生活在一起,是為了協調而平息爭鬥,通過合作增強力量以生活得更美好,而不是為了相互爭鬥,相互傾軋,相互撕殺。國家蛻變為階級統治的工具是國家本質的異化,隨著社會的進步,國家必然會恢復它的本來面目。
3.“政治人”假設為政治文明的發展奠定了邏輯前提。
“政治人”假設在作為人性假設、國家起源假設的同時,還是“政治文明假設”。幾千年的人類政治活動史,本來就是人類文明發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把“政治”與“文明”兩個辭彙連在一起,形成“政治文明”概念,卻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就中國的政治治理實踐和政治科學研究來看,對“政治文明”關注的歷史似乎更短。與之相對應的是,人們對政治有著太多的灰暗的理解。政治似乎總是與蒙昧、甚至野蠻聯繫在一起。特別是在野心家、政客們爾虞訛詐、勾心鬥角的搏殺中,在殘酷的階級鬥爭的漩渦中,人們常常對“政治”望而生畏,退而卻步,不到陷入生存危機時,儘量側身其外。“莫談國事”是這種狀態的最直觀的寫照。
然而,“政治”的面孔就應該是這樣的嗎?回答是否定的。亞里士多德的“政治人”假設內含著“政治文明假設”。他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就意味著每個人都是政治人,他說“人是最優秀的政治動物”就意味著政治從本質上講就是合作關係,協調關係。因此,政治從本質上講並不必然是少數人(或某個特定階級)謀取利益的私器。它可以,並且必須以最廣大社會成員的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這樣的政治追求人們之間,國家之間,以及整個人類的和諧相處。這樣的政治就告別了政治生活中的蒙昧、野蠻和黑暗,從而走向了文明。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政治人”假設中本來就隱藏著政治文明的種子。
實踐意義
企業家作為現實社會中的人,究竟有沒有政治性,是不是政治主體,以及如何成為政治主體,如何實現其政治主體性,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現實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中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
“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但“它不是直接由經濟決定的,而是由那些在經濟基礎上成長起來的社會關係決定的”。這就是說企業家“政治人”假設是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么一個特定社會現實決定了的,它當然要和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相一致,並把執政黨的目標和宗旨的先進性體現出來。
(1)一般意義上的“政治人”
亞里士多德提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的命題,多次強調“人類在本性上應該是一個政治動物”。馬克思稱這一命題“標誌著古典時代的特徵”。這一命題清楚地表明了政治與人類之間不可分離的關係,也揭示了個人對群體的依賴關係。
關於人與政治的關係,托馬斯·阿奎那宣稱:“人天然是一個社會和政治動物,注定比其他一切動物要過更多的合群生活。”狄德羅更是提出了“政治上的人”的嶄新概念。他說:“人從單獨或個人的狀態,進而到社會狀態,於是他訂出了許多普遍原則,擁有至高無上主權的統治者,就根據這些原則,由人的手裡取得儘可能取得的一切利益,我們已經把這叫做‘政治上的人’。”在這裡,狄德羅已經初步揭示了人怎樣從自然人到社會人再到政治人的演進過程。
社會生活是由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構成的。從表面上看,經濟生活(也可以稱為物質生活)似乎是人的第一需要。馬克思在批判18世紀流行的資產階級人性論觀點時指出,那種認為“自然狀態是人類的真正狀態”的看法是“一種臆想”。他說:“吃、喝、性行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機能。但是,如果使這些機能脫離了人的其他活動,並使它們成為最後的和惟一的終極目的,那么,在這種抽象中,它們就是動物的機能。”馬克思特彆強調,人總是社會的人,“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這就是說,人除了要過經濟生活外,還必須過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由於生產勞動,伎人與動物區別開來;由於社會交往,人與人之間必然要進行思想交流,於是產生了文化生活;也是由於社會交往,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係需要調整,於是產生了政治生活。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和心理學家哈羅德·D·拉斯維爾認為,“不管在政治上表現為什麼特殊形式,所有政治人格的一個共同特性就是對尊敬所具有的強烈要求。當這樣一種動機縱橫掉閱的技能相結合,又遇到適宜的環境時,一個活生生的政治家就應運而生。一個充分發展的典型政治人格總是以公共利益為名,在充滿公共事物的世界中實現他的命運的。他總是打著集體利益的旗號,把私人動機轉移到公共事物上面。”在西方,不乏許多成功的企業家成為政治家的先例,中國也有象徵意義上的政治企業家如榮毅仁等。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企業家作為“政治人”的一般特性,也就是說,由於中國社會的倫理政治化與政治倫理化的文化傳統,中國的企業家“天生”就具有“政治人”的特質。
(2)企業家作為“政治人”的特殊性
企業家的社會交往與經濟行為並不是毫無目的的自在行為,而是目的性十分明確的自覺行為。具體來說,企業家的交往都是為了獲得某種利益或實現某種價值,這就必然要形成一定的利益關係。為了協調這種利益關係,就需要制定一些規則,保障一定的利益要求,約束一定的利益欲望,以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當然,就一個個具體的企業家來說,可能不一定參與制定規則、決策等活動,但必然要接受這些規則和決策的約束或影響。在實際生活中,企業家總是在執行或違抗這些規則。比如,一個工商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可能根本就沒有參加什麼會議或參與有關規則的制定,但他卻在按章登記和納稅,或者他在想辦法逃稅。他的行為實際上都會影響到政府的決策,因而他並未逃出政治體系和脫離政治生活。
我國的企業家作為政治主體具有不同於其他政治主體的特殊性。所謂政治主體,就是現實政治關係中的人,他們既支配政治又被政治所支配。只有承認企業家是政治主體,人們才會自覺地、有意識地去為企業家的政治主體性實現創造條件,積極推進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充分發揮企業家的積極性、創造性、自主性、自覺性,使得企業家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達到和諧與統一。
企業家的政治主體性實現是漸進的、曲折的、逐步展開的。當然,企業家的政治主體性地位與企業家的政治主體性實現是兩回事。我們不能因為受歷史條件限制,一部分企業家或大部分企業家未能發揮政治主體作用而否認他們是政治主體。如果我們將企業家的政治主體性作一邏輯思考,就可以清楚地得出如下結論:企業家的政治主體性是絕對的,是不容忽視的;企業家的政治主體性是相對的,是逐步實現的;企業家的政治主體性實現是有條件的,是要努力爭取的。
事實上,政治並不神秘,也並不遙遠,政治就在人們身邊,是存在於人們中間的、具體而實在的東西。近年來國有企業改革,有一些職工可能要下崗待業,這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或社會問題,也是一件事關職工切身利益和社會穩定的大事,是個嚴肅的政治問題。這也是作為“政治人”的企業家不容迴避的重大社會問題。
遺憾的是,人們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政治管理者(官員或統治者)和政治管理工具(國家機關或公共權力)當成政治主體,‘而把真正的政治主體(勞動者或民眾)當成客體、當成工具,進而形成對國家、權力和官僚的崇拜。這一趨嚮導致企業家自身的誤解和人們對企業家的錯誤認識,結果是,企業家一個個都希望成為政治管理者,從而影響了企業的主要目的,導致他們作為企業家身份的錯位。
正如密爾所言,“國家的價值,從長遠看來,歸根結底還在組成它的全體個人的價值。一個國家若只圖在管理技巧方面或者在事務細節實踐上所表現的類似的東西方面稍稍較好一些,而競把全體個人智力的擴展和提高這一基本利益推遲下來;一個國家若只為——即使是為著有益的目的——使人們成為它手中較易駕馭的工具而阻礙他們的發展,那么,它終將看到,小的人不能真正做出大的事;它還將看到,它不惜犧牲一切而求得的機器的完善,由於它為求機器較易使用而寧願撤去了機器的基本動力,結果將使它一無所用。”這就意味著我們不僅要重視企業家作為“政治人”的一般性,也要重視其特殊性,因為每一個企業家個體都有不同於一般人的需求與欲望。而這些需求與欲望的滿足44影響到企業家形成與發展。
(3)國有企業經營者作為“政治人”的特殊性
在我國特定階段,國企經營者充當著政治管理者的角色,A既具有一般“政治人:’的特性,又具有不同於其他性質的企業色營者的特殊性。其實,“政治人”並不是說國企經營者就是官玉或政治家,而是說作為國有企業的經營者,他必須具有相當的因治思想素質,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從全局出發,協調、兼顧國另(社會)、集體(企業)、職工(個人)三者利益和關係。
國有資本具有二重性,既是資金又是資本。作為資金,它多有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基本屬性,資金運動的目的也就是市場的目的,即滿足人民民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作為資本。它又具有與私有資本相同的求利性、積累性和擴張性等資本增值的本能衝動,生產的目的是為了得到更多的利潤。社會主義市技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即努力探索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契合關係之後,國有資本便把資金的屬性和資本的屬性這兩個方面都繼承了下來。這種二重性的對立統一運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的外在表現形式,同時也是推動國有資本不斷進步、國有企業不斷發展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前進的內在動力。
改革後的國有企業,在以資本的形式作為法人實體和競爭主體進入市場時,同樣必須擁有人格模式的規定性。市場主體的本位主義要求國有資本首先表現為經濟人;同時,國有資本的全民性質規定了它在本質上又是“資金”,相應的人格是團隊精神。也就是說,國有企業“資金”和“資本”的雙重屬性決定了其人格的二重性。也就是說,國有資本的人格二重性決定和要求它的配置、整合者——國企經營者,同樣必須具有二重性人格的特性:“經濟人”和“政治人”。“經濟人”是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對企業的經營管理能力、自利與追求企業利益最大化;“政治入”是社會主義制度所要求的大公無私、公而忘私、無私奉獻、團隊精神精神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新時期,我們對國有企業職能的基本定位是:第一,作為政府巨觀調控的工具,在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點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支配地位,主要涉及三大行業: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第二,作為國有資本參與市場競爭,為國家提供利稅。這兩種功能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以社會效益為原則,後者以經濟效益為原則。為實現這一目標,達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的,國有企業就不可能像其他所有制企業一樣只在市場競爭中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必須在確保自身生存、不斷提高競爭力與影響力的同時,充當政府巨觀調控的工具。國有企業的這一特殊職能要求國企經營者必須具有上述“政治人”的基本特徵。
國有企業的經營者,他們代表著中國國有企業的形象、中國企業家的形象,參與競爭,擴大貿易,多掙外匯,本身就是對祖國的貢獻。代表國家是“政治人”,多掙外匯是“經濟人”,同樣兩個方面缺;不可。企業家的真正使命不應該是財富的占有,而應是財富的積累,是為國家和民族做出成就。
一個國家的社會、文化傳統對其經濟體制的形成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我們知道,同樣是資本主義國家,由於社會、文化傳統不同,它們選擇的市場經濟制度的類型也不一樣。比如,美國的社會、文化傳統是多元化和自由放任的,這種社會、文化傳統使它選擇了有比較弱的政府干預的市場經濟制度;相反,幾乎所有走上有國家計畫,即有巨觀調控的市場經濟道路的國家,其社會、文化傳統都具有強烈的國家主義傾向或社會主義思潮。中國經歷了兩乾多年的中央集權的封建主義社會,同樣具有強烈的國家主義傾向的社會、文化傳統。新中國成立後,我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思想又深深紮根於人民心中。就像恩格斯在闡明人民創造歷史時指出的“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縈迴於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馬克斯·韋伯在其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早就為我們提出過一個社會學假設,即透過任何一項事業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後發現有一種無形的、支撐這一事業的時代精神力量;這種以社會精神氣質為表現的時代精神,與特定社會的文化背景有著某種內在的淵源關係;在一定條件下,這種精神力量決定著這項事業的成敗。無疑地,這種社會的文化類型會深深地影響著企業家作為“政治人”的人格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