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經歷
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 1924- 1987) 美國黑人作家。出生在紐約市黑人聚居區哈萊姆。他的父親是不受教區供養的窮牧師,有子女9人,他是長子。因家貧受教育不多,主要靠自學。12歲發表一篇描寫西班牙革命的短篇小說,以後一直練習寫作歌曲和劇本。他的父親一心要他當牧師,極力反對他的創作活動。他14歲開始在教堂布道,3年後自稱“看透了宗教的虛偽”,從此離開教堂,不信宗教。這段經歷對他影響很大,他後來寫的散文也帶有布道時的說教口吻和激情。
 詹姆斯·鮑德溫
詹姆斯·鮑德溫鮑德溫離開教堂後不久,在他所謂的“美國工商業世界”中謀生,充當過飯館侍者和僕役,業餘時間寫作書評和小品文,其中一部分後來收在散文集《土生子的札記》(1955)中。1944年他結識黑人作家理查·賴特,並在賴特的幫助和鼓勵下從事創作。4年後步賴特的後塵離開美國僑居
巴黎和歐洲。1957年美國爆發警察鎮壓黑人示威的小石城事件,鮑德溫認為他身為作家,“責任是在美國”,因而回到美國從事寫作和鬥爭。
主要作品
他參加黑人民權運動,同時寫了許多文章,就反對種族歧視、黑人解放的道路等問題發表意見。其中有著名的散文集《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1961)、《下一次將是烈火》(1963)、《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1972),還有政論、文藝評論、回憶錄、隨筆、遊記、報告文學等多種文字,文筆犀利潑辣,洋溢著火一般的熱情,西方有不少評論家認為他是20世紀傑出的散文作家,“他的散文充滿無人能模仿的激情,這種激情……出自作者的內心,無法與作者本人的思想感情分割開來。”
除散文外,鮑德溫也寫作劇本和小說。他的劇本《黑人怨》(1964)在百老匯上演後獲得好評。他出版有一部短篇小說集和五部長篇小說,較優秀的是第一部長篇小說《向蒼天呼籲》(1953),主要描寫美國黑人青少年面臨兩種抉擇:不是進教堂,就是進監獄。後來出版的三部長篇小說《喬瓦尼的房間》(1956)、《另一個國家》(1962)和《告訴我火車開走多久了》(1968),企圖通過複雜的性關係(包括同性戀)來反映美國現實社會中的種族關係,猥褻的描寫較多。1974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假若比爾街能夠講話》,寫一對黑人青年男女遭受一個白人警察的迫害和誣告的悲劇,反映種族問題較前深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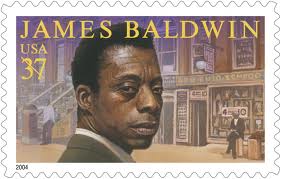 詹姆斯·鮑德溫
詹姆斯·鮑德溫鮑德溫關於種族問題的基本看法是:美國的“複合命運”使白人和黑人的生活及利害關係在20世紀的美國變得不可分割。他認為要解決美國黑人問題,關鍵在於美國白人必須尋找出一條道路來與黑人共處。他一方面警告白人世界必須停止種族歧視,因為物極必反,黑人的怒火會一發不可收拾;另一方面又規勸黑人不要採取極端的行動,以免煽起種族仇恨,自取滅亡。他的觀點雖遭到某些黑人領袖的指責,但在黑人民眾中有一定的影響。
作品主題
父子關係是美國當代著名黑人作家詹姆斯·鮑德溫畢生探究的一大主題,他的許多作品中都體現了對心目中理想的黑人父親的渴求。此外,其作品中濃郁的宗教情結同樣不容忽視。鮑德溫在不同時期創作的三部作品——《向蒼天呼籲》、《阿門角》和《假如比爾街能夠說話》——中塑造了三種不同類型的黑人父親形象,而且這些父親形象都可以從《聖經》以及鮑德溫本人的生活中找到原型。從《聖經》原型的角度解讀這些作品中的黑人父親形象無疑對理解作者本人及其作品很有助益。
鮑德溫的作品往往以他本人的親身經歷為藍本,因而大多具有自傳色彩。在他的作品中反映最多的是他對繼父愛恨交加的矛盾心理,對父親形象的刻畫貫穿於他的許多作品,比如,小說《向蒼天呼籲》(1953)中脾氣暴戾的繼父加布里埃爾,戲劇《阿門角》(1968)中具有深刻思想卻疲軟無力的父親盧克,以及另一部小說《假如比爾街能夠說話》(1974)中兩位性格迥異的父親弗蘭克和約瑟夫。為什麼鮑德溫要在他的這些作品中反覆刻畫黑人父親形象?為什麼這些黑人父親的形象隨著作品寫作時間的變化而不同?這些都是的德溫留給讀者的思考,解讀這些作品中的黑人父親形象無疑對理解作者本人及其作品很有助益。
此外,鮑德溫作品中濃郁的宗教情結同樣不容忽視。年輕時的鮑德溫曾在當地教堂做過三年牧師,這一段生活經歷對鮑德溫的思想及其創作有著極大的影響。
黑人信仰基督教源自17世紀初期。那時,首批黑人剛被販運至美洲大陸,身心備受白人奴役卻無力反抗。而且,同一個莊園的黑奴往往來自非洲的不同部落,持不同的語言,相互之間根本無法述說內心的苦楚。此時,基督教在黑人群體中廣泛傳播,成為黑奴精神上唯一的慰藉。信徒們被告知,上帝安排著各人的命運,人們應該默默忍受塵世的痛苦與折磨,死後在天國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寵。根據基督教教義,黑人自然應該聽從上帝的安排,接受比白人低劣的命運。因而,從一開始宗教就是白人藉以矇騙黑人並控制黑人身心的強有力的工具。
有過三年牧師經歷的鮑德溫清醒地意識到了這一點。誠如他在《下一次將是烈火》(1963)中所剖析的那樣,在教堂內做牧師“就像是在劇院內”工作,因為他可以“在布景的後面了解到幻覺是怎么產生的”。他也看透了神職人員對教民剝削的伎倆,明白他們是怎樣操縱和影響會眾“直到最後一枚硬幣被捐獻出來”。宗教的欺騙性以及教堂內愛心的匱乏令他深感失望。於是,他拋棄了宗教轉而投身文學。後來,鮑德溫在他的許多作品中對宗教進行了深入的批判。
儘管鮑德溫後來因為看透了宗教愚弄黑人的本質而離開了教堂,但是宗教對他的影響伴隨著他的一生,並影響著他的創作。他那令人折服的雄辯的文風得益於做牧師時的布道經驗,他的許多作品中的人物都可以從基督教中找到原型,甚至很多名字都源自《聖經》。而且,鮑德溫雖然從來沒有終止過對宗教的批判,但他卻不可避免地吸收了基督教教義中一些積極因素,比如教民們應該遵行上帝的指令而愛他人,直至愛仇敵。這種博愛思想深深影響了鮑德溫,他後來成為一位種族和解思想的倡導者的根源在於宗教,而體現在他寫作中的是那永久不變的愛的主題。正是在基督教博愛思想的指引下,鮑德溫才得以超越他曾信奉的黑人抗議傳統,引導人們從整個美國人的角度而不是單從黑人角度來看待種族歧視的危害。也正因為如此,鮑德溫在其作品中才能夠更全面地展示黑人的人性,弘揚黑人文化,從而將美國黑人文學提升到一個更高的水平。因此,了解鮑德溫的宗教情結是解讀其作品的一個重要途徑。本文主要從《聖經》原型的角度分析鮑德溫於不同時期創作的三部作品——《向蒼天呼籲》、《阿門角》及《假如比爾街能夠說話》(下文中分別簡稱為《向》、《阿》和《假》)——中三類父親的形象,並將作品中的父親與鮑德溫本人現實生活中的父親,以及曾被他視為父親並對他有著深刻影響的幾位人物進行比較分析,從而解讀鮑德溫的創作主旨,揭示其作品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內涵。
一、冷漠偏狹的繼父 根據《舊約》,以色列入的始祖亞伯拉罕虔誠侍奉上帝,深得上帝庇佑。最初亞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不能生育,亞伯拉罕納使女夏甲為妾生下以實瑪利。亞伯拉罕100歲、撒拉90歲的時候,上帝賜與撒拉生育能力,生下以撒。儘管同為亞伯拉罕的兒子,以撒和以實瑪利的命運卻截然不同。以撒因為是亞伯拉罕妻子的兒子,被認定為亞伯拉罕“獨生的兒子”,其產業的繼承者,並延續上帝與亞伯拉罕之間的約定,他的後裔將繼續蒙受上帝特別的恩寵。而以實瑪利由於是妾所生,他的地位遠在以撒之下。亞伯拉罕臨終時“把一切所有的都給了以撒”,以實瑪利則無權享有父親的財產與祝福。在成長的過程中,他只能作為一名弓箭手生活在巴蘭的曠野。不公平的待遇抹去了兄弟間的親情,以實瑪利的後裔後來成為以色列民族的死敵。
鮑德溫早期的小說《向》描述了黑人少年約翰14歲生日那天在繼父家中所過的令人窒息的生活,約翰皈依宗教時的思想活動,以及他的繼父、母親、姑姑在教堂祈禱時的回憶,深刻地揭露了宗教的虛偽,無情地抨擊了宗教對黑人的麻醉和欺騙。在該小說中,鮑德溫借用《聖經》中墨守成規冷落私生子(即不受法律保護的兒子)的父親亞伯拉罕這一原型,塑造了一個冷漠偏狹的繼父形象。繼父加布里埃爾是當地教堂的一名主要執事,他脾氣粗暴,動輒打罵約翰。在父親看來,約翰不過是一個“懦弱而傲慢的女人同某個輕率的傢伙生的兒子”,一個長著“撒旦的臉”、眼裡露出“撒旦凝視的目光”、充滿了“惡毒的自尊”、奇醜無比的小魔鬼。
與亞伯拉罕一樣,在繼父心中,他與妻子所生的兒子羅伊才是上帝許諾給他的兒子,他唯一“合法的繼承人”。他認為羅伊將“傳宗接代,繼承父親的姓和幸福的血統,他將為主服務,直到基督再臨、帶來聖父的天國的那一天”。繼父對寄託著自己全部希望的羅伊寵愛有加,但是偏偏羅伊不服管教,整天在外惹是生非。想著將要繼承自己事業的人不是自己的兒子羅伊而是約翰這個私生子,父親感到失望、憤怒與恐懼,他對約翰更加冷漠與粗暴。極度的絕望和刻骨銘心的恐懼時時刻刻地攫住約翰那顆稚嫩的心。在別無他法的情況下,他決定皈依宗教,希望從中尋求庇護和安慰。
《向》中約翰皈依宗教的經歷源自鮑德溫本人青少年時三年的牧師生活。鮑德溫在其著名的散文集《下一次將是烈火》中詳細地述說了他在14歲那年信仰宗教兩個最主要的原因。首先,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美國社會,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依然嚴重,教堂成為黑人最好的避難所。其次,繼父冷漠嚴酷,經常打罵鮑德溫,繼父對他的歧視更令他憤恨,父子關係非常緊張。於是,對人世間的愛感到了絕望的少年鮑德溫為了躲避哈萊姆街上的墮落和擺脫繼父的控制並最終戰勝繼父而逃進了教堂。
此外,在鮑德溫看來,繼父的偏狹不但體現在對待私生子的粗暴態度上,也反映在他不分青紅皂白排斥一切白人的種族主義思想。鮑德溫自小受到白人民主人士的關心與照顧,成年後所結交的白人朋友也對他進行過無私的支持與幫助,這些使他“一直無法真正憎恨白人”。但是,繼父對鮑德溫與白人交往非常反感,甚至厭惡那些熱心幫助鮑德溫以及家人的白人教師,懷疑他們幫助黑人孩子的動機,因而他一直反對鮑德溫進學校讀書。《向》中的繼父也是如此。在內心對白人暗藏著巨大仇恨的繼父眼裡,約翰接受白人的教育與白人交好是一種“邪惡”,他將黑人的一切不幸歸咎於所有的白人。繼父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讓約翰感到非常反感。
後來,隨著年齡和社會閱歷的增長,鮑德溫對美國社會的現實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與此同時,與20世紀四五十年代許多青年黑人作家一樣,鮑德溫這個時候也深受前輩作家賴特的“抗議”小說的鼓舞。賴特的聲聲抗議喊出了長期鬱結在黑人心頭的憤恨,也加深了鮑德溫對繼父的理解,他逐漸意識到繼父狂暴的外表下掩藏著的悲涼與無奈。這也正是當初鮑德溫創作《向》的動機之一:鮑德溫曾希望通過寫作來理解繼父的痛苦從而諒解繼父對他的傷害。
其實,鮑德溫在《向》中所刻畫的這樣一個冷漠偏狹的父親形象還有著更為深刻的寓意:“美國黑人是美國文明的私生子”。他在《無人知道我的名字》(1961)、《街上無名》(1972)等多部散文集中指出,不公正的國家(隱喻著偏狹的父親)不僅給黑人身體和精神上帶來了巨大傷害,而且也造就了白人對真實歷史的盲目認識以及由此而生的殘忍與恐懼。白人長期生活在美國是他們的、黑人不過是他們財產中的一部分這樣一個謊言中。即便黑人已經在法律上獲得了獨立身份後,白人打心眼裡依然不願放棄白人至上的神話。鮑德溫仔細分析了白人的重重顧慮:如果拋棄這個神話,他們將付出沉重的代價,他們將不得不拋棄他們的特權與財富,意味著他們的理想將不復存在。同樣,黑人由於世世代代在美國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殘酷壓迫,他們對白人的怨恨根深蒂固。用鮑德溫的話來說,“如此的挫折,如此漫長的忍耐,使許多強壯得令人欽佩的男男女女——他們唯一的過錯就是膚色——變成了偏執狂”。他們永不停歇地採用各種暴力手段進行反抗,因而造就了白人內心的恐慌。一些明智的白人民主人士開始意識到白人至上主義是一個歷史錯誤,並有意與黑人接近。即便如此,黑人依然心存芥蒂,不願意接受他們。這顯然是因為不公正的父親在黑白兄弟之間埋下了相互仇恨的種子。鮑德溫在許多作品及其演說中反覆表達了他對美國種族問題的擔憂與失望。
但是,在傳承抗議精神並付諸實踐的過程中,鮑德溫敏銳地注意到了抗議作家思想中的局限性及其毀滅性的力量。鮑德溫感覺到,黑人的暴力反抗行為雖說在一定程度上震懾了白人,但是,黑人本身往往也被內心的怒火燒灼得傷痕累累。於是,鮑德溫在《人人的抗議小說》(1949)以及《啊啦,可憐的理察》(1961)等文章中對曾一度被他視為“精神之父”的賴特的抗議主張提出了質疑。在隨後的一些作品中,鮑德溫倡導黑人“丟掉頭腦中的憤怒”“諒解白人,用關愛來引導他們“迷途的兄弟”走出歷史的誤區,並用愛去對抗“無愛的世界”,從而達到共同改進社會的目的。
鮑德溫對抗議文學由推崇到批判的轉變引起了不少評論家們關注,他因此招來以克利弗為代表的眾多黑人激進青年的猛烈攻擊。其實,創作思想的不穩定並不是的德溫獨有的特點。幾乎所有黑人作家都不可避免地承受著美國社會無處不在的種族歧視帶給黑人民族的屈辱、憤怒以及深深的困惑。在白人種族主義盛行的美國,黑人作家既對白人的壓制深惡痛絕,又囿於它的強橫,找不到抵制它的力量,同時他們也不能忽視白人民主人士的存在。就連賴特和克利弗也不例外。對於鮑德溫創作中表現出來的矛盾心理,史蒂芬尼。鄧寧給予了充分的理解:鮑德溫在其作品中表達了在探索解決種族衝突問題時遇到的挫敗感,表達了美國種族矛盾本質上的悲哀與模稜兩可。
鮑德溫力圖突破黑人抗議傳統的禁錮宣揚種族融合思想的嘗試深深影響了沃克、莫里森、福勒和威爾遜等許多後來的黑人作家,為他們提供了一種探討種族問題的新思路。20世紀70年代以來,這些作家逐步擺脫了表現種族對抗、把黑人簡單描繪成種族壓迫犧牲品的傳統模式,而是致力於保存和弘揚黑人文化,並在小說的主題和形式方面進行新的探索,美國黑人文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詹姆斯·鮑德溫
詹姆斯·鮑德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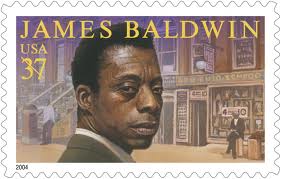 詹姆斯·鮑德溫
詹姆斯·鮑德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