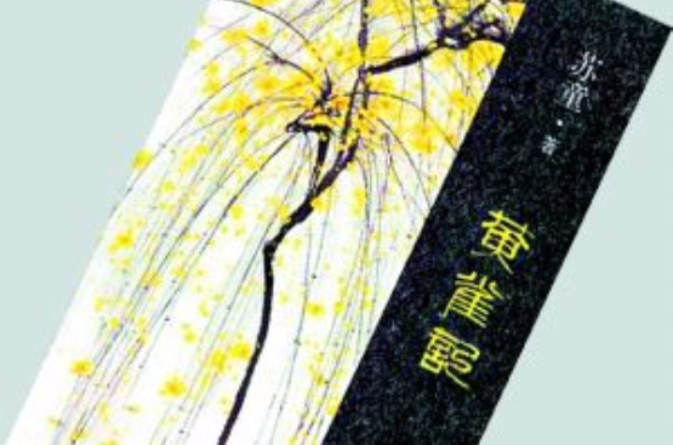梁文道:我們走到今天這一步,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是情非得已的,比如說我繼續給大家介紹蘇童的這本《黃雀記》裡面的這個仙女,後來慢慢成為了一個幾乎淪落風塵的白小姐,他越來越漂亮了。
基本介紹
- 書名:開卷八分鐘:蘇童《黃雀記》(二)
- 作者:蘇童
- 出版社:麥田
- 出版時間:2013年5月
基本信息,作品內容,作者簡介,
基本信息
書名:《黃雀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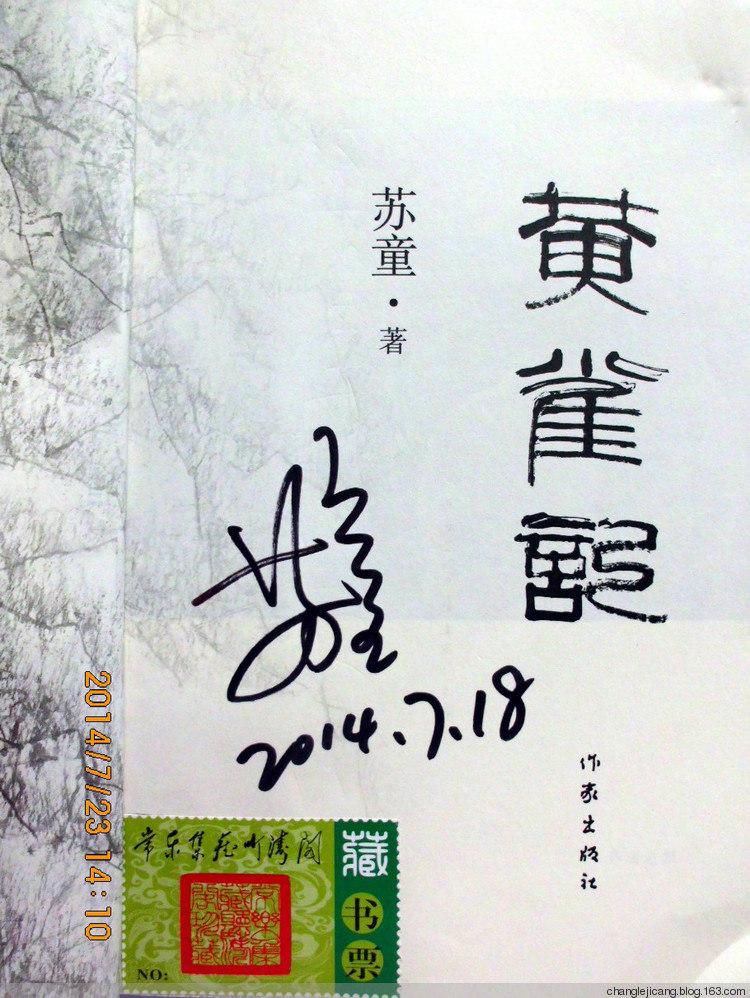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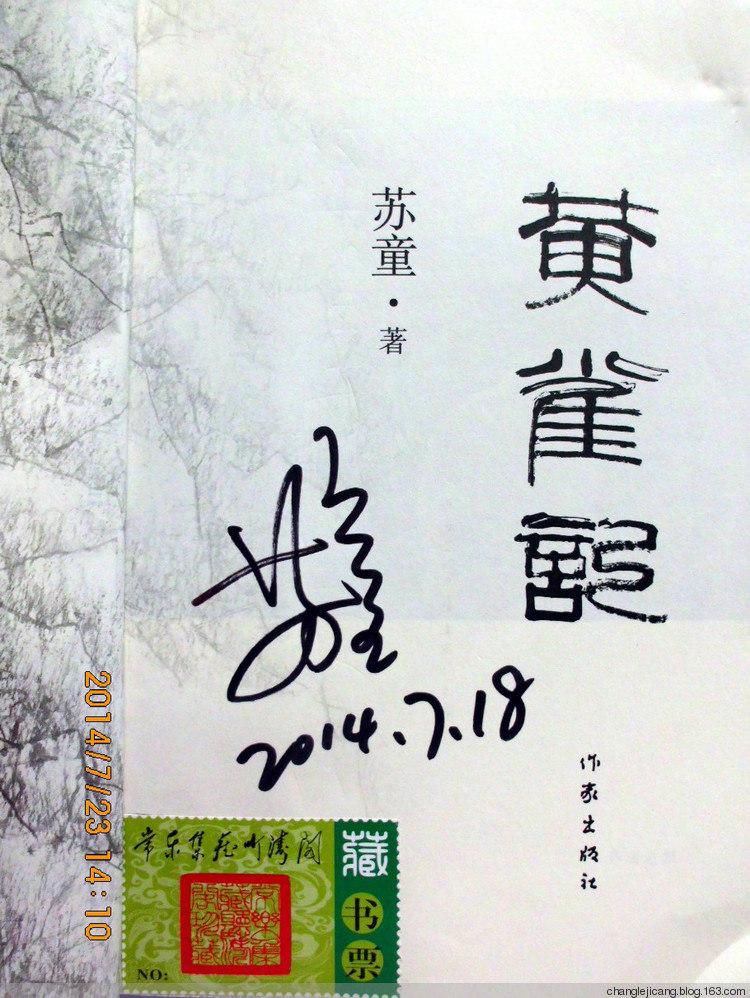
撰文:李禾
欄名:新書場
定價:380新台幣
作品內容
梁文道:我們走到今天這一步,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是情非得已的,比如說我繼續給大家介紹蘇童的這本《黃雀記》裡面的這個仙女,後來慢慢成為了一個幾乎淪落風塵的白小姐,他越來越漂亮了。
小時候是個很可愛很天真的女孩,只是知道自己美麗而已,長大之後,開始利用自己的美麗,逐步逐步慢慢的出賣各種各樣的東西,儘管他非常的小心計算,但是仍然不可避免的要發生很多讓自己難堪的事情。
這種女人我們今天也說看到就會直接怪罪他們,我們就會說你看這女人怎么那么下賤,跟那幾個有錢老闆搞在一起,這個那個的,但是這樣的一種女人,我們往往欠缺的是對他們的同情,他們是怎么來的呢?
他們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我覺得蘇童有時候對他筆下的一些人物的同情感,他一方面很殘酷,但是又有一種同情,比如說對這些女性角色的同情,我覺得是同情到一個想為他安排一個說得通的過去的地步,比如說原來這個女人曾經被強姦過。
被強姦了以後,好像大概也就如此墮落下去了,這是一個很常見的一個說法,我覺得這個說法坦白講,對我來講好像有一點俗套了,他怎么會走到這樣一個地步。
但是回過頭來看,你又發現他事後對這個所謂的強姦,又不是那么計較,而當時對那個事情真正計較的卻是我們昨天跟大家說到的,我們的一號男主角保潤,他因為這個事情,莫名其妙的含冤坐了十年的牢。
坐完這個牢出來之後,好像跟當年陷害他,或者是使致他入獄的那個人,也就是柳生好像沒事了,變成朋友了,但是這過去的事情真的就能夠這么過去嗎?
我們在這整本小說裡面看到的就是,原來今天中國發生很多現實都是過去造成的,這些過去的事情,能不能就這么過去呢?實在不能,他始終是要未來,始終是要報酬,該還的債始終是要還清楚。
儘管這裡面每一個人好像都很無奈,好像沒有人你能夠特別譴責,但是你當年做過這件事,你就得還回去。
這個還回去還給誰呢?我們這裡面說到的好像一種繩結,從過去到現在,把我們人們都捆綁起來了,的確繩結是這本書裡面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意向。
比如說我們擅長綁繩結的保潤,他的雙手能夠征服越來越多陌生的身體,捆一個陌生人比捆綁自己的祖父更加新鮮,更加刺激,看繩索沙沙切入棉質衣物,咬住那些陌生的皮膚,猶如一條蛟龍遊走於草地,叢草無聲倒伏。
他能夠察覺那些肉體從反抗到掙扎漸漸柔順,漸漸空洞,最後開始迎合繩子的思想,保潤玩轉繩子,每根手指都放射出探索的鋒芒,他的繩子是有規劃的,他的繩子是有理想的,他的繩子可以滿足你對曲線的所有想像。
這些繩子他本來捆綁的就是他的祖父,他的祖父才是他捆綁的主要目標,但是後來慢慢的這個繩子大大小小的,有時候是一個像遊魂一樣的出現,比如說出現在後來的鄭先生,白小姐要照顧的那個有錢的精神病人。
這個鄭先生他的病房內內外外,但是到了後來我們發現,這個繩結要捆綁住的那個失魂了的祖父,這個祖父發心瘋了,被送去精神病院了,因為他年年都要給自己拍遺照,他生怕後人對不起自己,他很計較自己死了之後後人看到的自己相片中的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他可以死,但是他的照片,人家對他憶記必須永遠長存,這樣的一個老人,繩子捆得住他嗎?
我們看到後來,這繩子是捆住他了,但是這個捆住了之後,他從精神病院出來的那一天,他看到了過去熟悉的老家完全變了,人山人海,一片繁忙的建設景象,祖父說,祖國的面貌日新月異,然而這樣的日新月異能不能追得過這個祖父呢?實在不能。
我覺得這個祖父跟繩子的關係是這本小說裡面核心的兩個意向隱喻跟象徵,繩子當然是捆綁,但這個捆綁好像在這個書裡面變成是一個下一代用來對上一代,或者說用來馴服過去的一種工具,可以十分有效,可以十分好,可以產生很多暴力。
但是這個過去,他會怎么樣呢?我們看看在這個書裡面,這個可怕的過去,他是怎么樣來的?這裡面當我們要尋找這家人的全家福的時候,全家福照片被水漬浸泡過,影像的侵蝕效果很離奇,產生了神秘的取捨。
一家人,這個保潤他胸前的紅領巾還在,但是頸部以上被腐蝕了,保潤的母親剩下半邊身體,依稀可見他穿著白色的襯衫黑色的裙子,保潤的父親幾乎完全消失,唯一殘存的是一隻皮鞋。
全家福照片裡只有祖父倖存,祖父在時間與水滴的消失中完好無損,祖父的蒼老常在,祖父的猥瑣常在,祖父的怯懦常在,祖父穿神色的中山裝,腳上是一雙解放鞋,頭髮梳的整齊光亮,祖父當時尚屬健康,拘謹的眼神透露出一道狹窄的靈魂之光。
他用躲躲閃閃的目光注射著攝影師的鏡頭,似乎向未來表達著某種深奧的歉意,對不起,你們都將消失,只有我長壽無疆。
這段很容易讓人想起在蘇童過去小說裡面常常,你感覺到的一種,那是什麼呢?就是我們這么多的事情,這么多的可怕的事件,仿佛我們每一個事件的發生背後都有一個導演,這個導演同時是一個囚籠,他就是有人會說那是中國的所謂的封建禮制,一些什麼禮教吃人的東西。
你更可以說是一種非常老的古老的一個傳統,這個傳統,他靈魂都失去掉了,他不見了,他要的只是繼續存在下去,他要的只是被後人憶記,當所有人都死光了,所有的遭遇悲劇之後,他繼續安安穩穩的在那裡,他好好的活著,甚至連一些新生下來的一些孽種,未來我們下一代,在小說結尾我們看到,一個生下來就臉部有缺陷的小孩,苦啊鬧啊,但是一進入這個詩的心魂的這個老爺爺的懷抱之中,他安定了,沒有問題了。
看到這裡,你就會發現,蘇童始終是那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蘇童。
小時候是個很可愛很天真的女孩,只是知道自己美麗而已,長大之後,開始利用自己的美麗,逐步逐步慢慢的出賣各種各樣的東西,儘管他非常的小心計算,但是仍然不可避免的要發生很多讓自己難堪的事情。
這種女人我們今天也說看到就會直接怪罪他們,我們就會說你看這女人怎么那么下賤,跟那幾個有錢老闆搞在一起,這個那個的,但是這樣的一種女人,我們往往欠缺的是對他們的同情,他們是怎么來的呢?
他們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我覺得蘇童有時候對他筆下的一些人物的同情感,他一方面很殘酷,但是又有一種同情,比如說對這些女性角色的同情,我覺得是同情到一個想為他安排一個說得通的過去的地步,比如說原來這個女人曾經被強姦過。
被強姦了以後,好像大概也就如此墮落下去了,這是一個很常見的一個說法,我覺得這個說法坦白講,對我來講好像有一點俗套了,他怎么會走到這樣一個地步。
但是回過頭來看,你又發現他事後對這個所謂的強姦,又不是那么計較,而當時對那個事情真正計較的卻是我們昨天跟大家說到的,我們的一號男主角保潤,他因為這個事情,莫名其妙的含冤坐了十年的牢。
坐完這個牢出來之後,好像跟當年陷害他,或者是使致他入獄的那個人,也就是柳生好像沒事了,變成朋友了,但是這過去的事情真的就能夠這么過去嗎?
我們在這整本小說裡面看到的就是,原來今天中國發生很多現實都是過去造成的,這些過去的事情,能不能就這么過去呢?實在不能,他始終是要未來,始終是要報酬,該還的債始終是要還清楚。
儘管這裡面每一個人好像都很無奈,好像沒有人你能夠特別譴責,但是你當年做過這件事,你就得還回去。
這個還回去還給誰呢?我們這裡面說到的好像一種繩結,從過去到現在,把我們人們都捆綁起來了,的確繩結是這本書裡面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意向。
比如說我們擅長綁繩結的保潤,他的雙手能夠征服越來越多陌生的身體,捆一個陌生人比捆綁自己的祖父更加新鮮,更加刺激,看繩索沙沙切入棉質衣物,咬住那些陌生的皮膚,猶如一條蛟龍遊走於草地,叢草無聲倒伏。
他能夠察覺那些肉體從反抗到掙扎漸漸柔順,漸漸空洞,最後開始迎合繩子的思想,保潤玩轉繩子,每根手指都放射出探索的鋒芒,他的繩子是有規劃的,他的繩子是有理想的,他的繩子可以滿足你對曲線的所有想像。
這些繩子他本來捆綁的就是他的祖父,他的祖父才是他捆綁的主要目標,但是後來慢慢的這個繩子大大小小的,有時候是一個像遊魂一樣的出現,比如說出現在後來的鄭先生,白小姐要照顧的那個有錢的精神病人。
這個鄭先生他的病房內內外外,但是到了後來我們發現,這個繩結要捆綁住的那個失魂了的祖父,這個祖父發心瘋了,被送去精神病院了,因為他年年都要給自己拍遺照,他生怕後人對不起自己,他很計較自己死了之後後人看到的自己相片中的自己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他可以死,但是他的照片,人家對他憶記必須永遠長存,這樣的一個老人,繩子捆得住他嗎?
我們看到後來,這繩子是捆住他了,但是這個捆住了之後,他從精神病院出來的那一天,他看到了過去熟悉的老家完全變了,人山人海,一片繁忙的建設景象,祖父說,祖國的面貌日新月異,然而這樣的日新月異能不能追得過這個祖父呢?實在不能。
我覺得這個祖父跟繩子的關係是這本小說裡面核心的兩個意向隱喻跟象徵,繩子當然是捆綁,但這個捆綁好像在這個書裡面變成是一個下一代用來對上一代,或者說用來馴服過去的一種工具,可以十分有效,可以十分好,可以產生很多暴力。
但是這個過去,他會怎么樣呢?我們看看在這個書裡面,這個可怕的過去,他是怎么樣來的?這裡面當我們要尋找這家人的全家福的時候,全家福照片被水漬浸泡過,影像的侵蝕效果很離奇,產生了神秘的取捨。
一家人,這個保潤他胸前的紅領巾還在,但是頸部以上被腐蝕了,保潤的母親剩下半邊身體,依稀可見他穿著白色的襯衫黑色的裙子,保潤的父親幾乎完全消失,唯一殘存的是一隻皮鞋。
全家福照片裡只有祖父倖存,祖父在時間與水滴的消失中完好無損,祖父的蒼老常在,祖父的猥瑣常在,祖父的怯懦常在,祖父穿神色的中山裝,腳上是一雙解放鞋,頭髮梳的整齊光亮,祖父當時尚屬健康,拘謹的眼神透露出一道狹窄的靈魂之光。
他用躲躲閃閃的目光注射著攝影師的鏡頭,似乎向未來表達著某種深奧的歉意,對不起,你們都將消失,只有我長壽無疆。
這段很容易讓人想起在蘇童過去小說裡面常常,你感覺到的一種,那是什麼呢?就是我們這么多的事情,這么多的可怕的事件,仿佛我們每一個事件的發生背後都有一個導演,這個導演同時是一個囚籠,他就是有人會說那是中國的所謂的封建禮制,一些什麼禮教吃人的東西。
你更可以說是一種非常老的古老的一個傳統,這個傳統,他靈魂都失去掉了,他不見了,他要的只是繼續存在下去,他要的只是被後人憶記,當所有人都死光了,所有的遭遇悲劇之後,他繼續安安穩穩的在那裡,他好好的活著,甚至連一些新生下來的一些孽種,未來我們下一代,在小說結尾我們看到,一個生下來就臉部有缺陷的小孩,苦啊鬧啊,但是一進入這個詩的心魂的這個老爺爺的懷抱之中,他安定了,沒有問題了。
看到這裡,你就會發現,蘇童始終是那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蘇童。
作者簡介
蘇童,原名童中貴,1963年生於蘇州。1980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1984年到南京工作,一度擔任《鐘山》編輯,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江蘇分會駐會專業作家。1983年開始發表小說,迄今有作品百十萬字,其中中短篇小說集七部,長篇小說二部。隨著其中篇小說《妻妾成群》被著名電影導演張藝謀改編成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獲奧斯卡金像獎提名,名聲蜚聲海內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