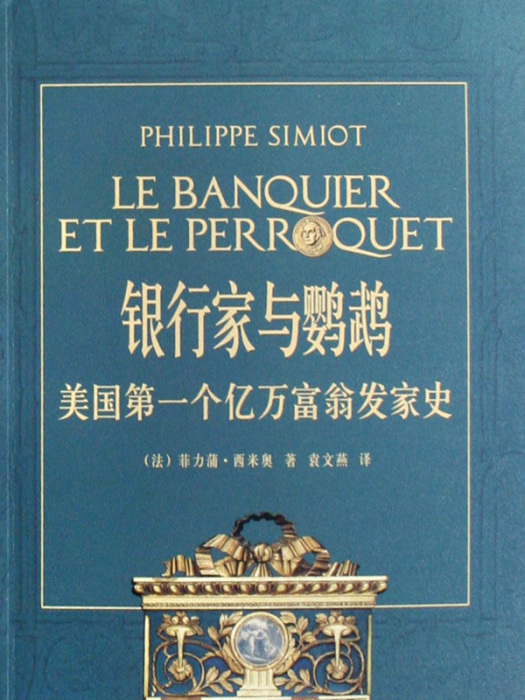《銀行家與鸚鵡:美國第一個億萬富翁發家史》是200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袁文燕。
基本介紹
- 書名:銀行家與鸚鵡:美國第一個億萬富翁發家史
- 作者: (法)菲力蒲·西米奧
- 原版名稱:Le banquier et le perroquet
- 譯者:袁文燕
- ISBN:9787506343541
- 頁數:338
- 定價:32.00元
-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8-06-01
- 裝幀:平裝
- 開本:18開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文摘,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1776年7月4日美國宣布獨立那天,一個被英國人追殺的法國船長逃命到了費城,在酒吧遇見了班傑明·富蘭克林、約翰·亞當斯和托馬斯·傑斐遜。30年後,他成了美國最有錢的富人。作為一個大船東,他開展了從北美到中國的貿易,收購了美國銀行,並資助了1812年對英戰爭。他見證了美國建國初期克服重重困難擺脫英國控制、完善憲法制度、建立堅挺的國家貨幣政策等一系列重要的歷史進程。
這個叫傑拉德的法國人,大膽而執著,他憑藉自己不懈的努力和獨特的商業遠見,積累了大量財富,戰勝了無數敵人和嫉妒他仇視他的人,影響著美國的政局和金融,消滅了跨國集團的野心。然而,這個獨眼的商業奇才相貌醜陋,極端孤獨,他唯一的朋友也許就是那隻老是命令人“幹活了!”的鸚鵡。
這是一部小說,書中的人物栩栩如生,情節生動曲折。
這也是一部歷史著作,書中的一切都是真的,所有的人物都有據可查,包括那隻鸚鵡。
作者簡介
作者:(法國)菲力蒲·西米奧(Philippe Simiot) 譯者:袁文燕
文摘
9月27日
威廉?豪的部隊攻進了費城。儘管兵力懸殊,9月11日,華盛頓將軍還是在南面25英里遠的布蘭迪萬河展開反攻,試圖擊退敵軍。一整天炮聲隆隆。9月21日,華盛頓將軍參謀部的一位軍官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上校趕來向國會報告:威廉·豪的部隊正往費城進軍,勢不可擋。聽到這個訊息,各州的代表們就像一群山鶉般竄到60英里外的蘭卡斯特。他們準備捨棄15個月前市政廳鐘樓里敲響獨立第一聲的自由鐘。當晚,漢密爾頓上校在城市酒吧分析了當前形勢:
“布蘭迪萬河一役,我們損失了1500人,昨天在保利(賓夕法尼亞州城市),我們又失去了250名士兵。當前,在北方,敵軍沿尚普蘭湖大舉南下進軍哈得孫河谷,顯然是要孤立新英格蘭,這也是華盛頓將軍在未來幾周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阻止的首要威脅。在這種形勢下,繼續死守費城可能會使我們勢單力薄的軍隊全軍覆沒;其次,隨著冬天的到來,戰鬥將停止,我們將重新行動起來。我們希望得到法國的幫助,已經有許多志願者加入了我們的行列,其中有拉法耶特侯爵,還有一位19歲的年輕貴族,他在布蘭迪萬河戰役中負了傷,所幸並無大礙。”
這時,上校突然朝我看來,大概是有人向他示意我是法國人,但他很快又把目光移開了。對於這種迴避,我已經習以為常。當人們發現我那隻幾近全白的眼睛和似乎想遠遠躲在眼角外面的虹膜時,他們就會自然而然地作出這樣的反應。他們還不知道這只可怕的眼睛看不見任何東西。
我很欣賞這位漢密爾頓上校。他身材矮小,目光熾熱有神。若是雙眼都完好無缺,就不難擁有這樣的目光。他站得筆直,說話清晰,聽者很容易就能跟上他的思路,因為他視野開闊,說話不拐彎抹角。心胸狹窄這個詞應該與他毫不沾邊。在轉移目光之前,上校也許正要問我是否也想像拉法耶特侯爵那樣加入他們的隊伍。我該怎么回答呢?是不是要說我不是侯爵,我要賺錢養活自己,而且還得養活家人?可能吧,但我還會加上一句:我的心與愛國者同在,而且為了不為英國人服務,我會馬上遠離費城。
瑪麗和我把雜貨店的存貨和一些衣物裝到一艘單桅帆船上。9月22日,我們揚帆起航,沿著德拉瓦河北上航行十多英里,接著向東轉,順蘭科克斯河一直到新澤西州的小鎮芒特霍利。那兒正好有幢房子等待出售,我低價買下了,用大陸幣付了錢。我們在一樓開了家雜貨店。恬靜的田園風光包圍著我們,廣闊的田野向南延伸,正值耕種的季節,我看見士兵們帶著他們的戰馬幫農民幹活。北面連綿著被森林覆蓋的山丘,我不禁想起秋天,在多爾多涅河畔,環繞我奶奶房子周圍的樹木也是這種色彩。倘若軍事形勢不是這么令人沮喪——紐約和費城淪陷,3500名英軍對1500名美軍,300艘皇家戰艦對幾艘私掠船——我會因許多事情而感到高興,全靠它們,我才能與瑪麗日夜相伴,寸步不離。自從我們結婚後,瑪麗以各種方式占據了我的身心,遠遠超乎我的想像。對於愛的體驗,我知道的不外乎水手妓院和之後的船長之家。我的同伴在那兒扯著個嗓門,放聲大笑,大聲地吵吵嚷嚷。而我總是獨自一人默默地去,生怕她們會因為我嚇人的眼睛而多收我錢。瑪麗並不顯得驚恐,她熱烈地,有時甚至是狂熱地回應我的激情,這種狂熱讓我不禁擔心自己會心醉神迷。瑪麗,滿臉溫柔的笑容,是家中的歌聲。有時,她舉手投足會讓我依稀看到母親的身影。當人們在學校叫我“魚眼”時,她會輕撫我的臉頰,手指滑過我的雙唇撫慰我,母親是在我12歲時去世的。瑪麗重新開啟了我塵封已久的對絕望童年的回憶。有好長一段時間,一個個畫面從記憶深處浮現在我面前。
10歲時,我被送到一所貴族中學。這是專為富裕的人家,為比我家富裕的家庭的孩子開辦的學校,父親的期望總是很高。課間休息時,我只能靠戰鬥保衛自己。我在右眼上綁了根布條,我有紅褐色的頭髮,我是紅髮埃蒂安,受人尊重。不幸的是,聖約瑟夫學校有一幫搗蛋鬼。戰鬥達到高潮時,我扯掉布條,揚言我的斜眼可以看到後面的敵人。我嚇唬他們,他們變本加厲地向我進攻,最勇猛的一個人把一塊木頭戳進我的病眼。我感到一陣劇痛,四周突然鴉雀無聲,空蕩蕩的走廊里就剩我一人。一個黑影走過來,對我說:
“是上帝懲罰了你。”
母親日以繼夜地守在我床邊。她懷孕了,第七個孩子即將出生。她為我從此徹底瞎了的眼睛換藥。我聽到醫生在爭論是否應該把它摘除,最後,他們保住了眼球,縫合了撕裂的眼皮。
再也沒人敢正視我,沒人,除了我母親,直到她去世;沒人,除了瑪麗,從去年開始。少年時,我懷著希望詢問鏡子,試圖聽到它回答我事實並非我想像中那么可怕。然而每照一次,情況都更糟。
10月22日
上星期,蓋特將軍率領的美軍在薩拉托加包圍了南下哈得孫的英軍縱隊,柏高英將軍率五千士兵投降,與此同時,豪將軍正準備在費城舒舒服服地過冬。效忠派似乎對他表示熱烈的歡迎,一場場晚會奢侈華麗,女人們優雅迷人,英國軍官風度非凡。要是豪率他的部隊向北推進,與柏高英會合,我們就一定會吃敗仗。不過駐紮在佛吉峽谷的華盛頓將軍潰散的軍隊可能阻截了他們。這不是由於英國人的寬恕,也許,我們更應把這戰爭間隙的喘息歸功於效忠派公民毫不吝惜的仁慈,儘管並非出於自願,他們還是為被其稱作造反者的愛國者的事業盡心盡責。
威廉?豪的部隊攻進了費城。儘管兵力懸殊,9月11日,華盛頓將軍還是在南面25英里遠的布蘭迪萬河展開反攻,試圖擊退敵軍。一整天炮聲隆隆。9月21日,華盛頓將軍參謀部的一位軍官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上校趕來向國會報告:威廉·豪的部隊正往費城進軍,勢不可擋。聽到這個訊息,各州的代表們就像一群山鶉般竄到60英里外的蘭卡斯特。他們準備捨棄15個月前市政廳鐘樓里敲響獨立第一聲的自由鐘。當晚,漢密爾頓上校在城市酒吧分析了當前形勢:
“布蘭迪萬河一役,我們損失了1500人,昨天在保利(賓夕法尼亞州城市),我們又失去了250名士兵。當前,在北方,敵軍沿尚普蘭湖大舉南下進軍哈得孫河谷,顯然是要孤立新英格蘭,這也是華盛頓將軍在未來幾周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阻止的首要威脅。在這種形勢下,繼續死守費城可能會使我們勢單力薄的軍隊全軍覆沒;其次,隨著冬天的到來,戰鬥將停止,我們將重新行動起來。我們希望得到法國的幫助,已經有許多志願者加入了我們的行列,其中有拉法耶特侯爵,還有一位19歲的年輕貴族,他在布蘭迪萬河戰役中負了傷,所幸並無大礙。”
這時,上校突然朝我看來,大概是有人向他示意我是法國人,但他很快又把目光移開了。對於這種迴避,我已經習以為常。當人們發現我那隻幾近全白的眼睛和似乎想遠遠躲在眼角外面的虹膜時,他們就會自然而然地作出這樣的反應。他們還不知道這只可怕的眼睛看不見任何東西。
我很欣賞這位漢密爾頓上校。他身材矮小,目光熾熱有神。若是雙眼都完好無缺,就不難擁有這樣的目光。他站得筆直,說話清晰,聽者很容易就能跟上他的思路,因為他視野開闊,說話不拐彎抹角。心胸狹窄這個詞應該與他毫不沾邊。在轉移目光之前,上校也許正要問我是否也想像拉法耶特侯爵那樣加入他們的隊伍。我該怎么回答呢?是不是要說我不是侯爵,我要賺錢養活自己,而且還得養活家人?可能吧,但我還會加上一句:我的心與愛國者同在,而且為了不為英國人服務,我會馬上遠離費城。
瑪麗和我把雜貨店的存貨和一些衣物裝到一艘單桅帆船上。9月22日,我們揚帆起航,沿著德拉瓦河北上航行十多英里,接著向東轉,順蘭科克斯河一直到新澤西州的小鎮芒特霍利。那兒正好有幢房子等待出售,我低價買下了,用大陸幣付了錢。我們在一樓開了家雜貨店。恬靜的田園風光包圍著我們,廣闊的田野向南延伸,正值耕種的季節,我看見士兵們帶著他們的戰馬幫農民幹活。北面連綿著被森林覆蓋的山丘,我不禁想起秋天,在多爾多涅河畔,環繞我奶奶房子周圍的樹木也是這種色彩。倘若軍事形勢不是這么令人沮喪——紐約和費城淪陷,3500名英軍對1500名美軍,300艘皇家戰艦對幾艘私掠船——我會因許多事情而感到高興,全靠它們,我才能與瑪麗日夜相伴,寸步不離。自從我們結婚後,瑪麗以各種方式占據了我的身心,遠遠超乎我的想像。對於愛的體驗,我知道的不外乎水手妓院和之後的船長之家。我的同伴在那兒扯著個嗓門,放聲大笑,大聲地吵吵嚷嚷。而我總是獨自一人默默地去,生怕她們會因為我嚇人的眼睛而多收我錢。瑪麗並不顯得驚恐,她熱烈地,有時甚至是狂熱地回應我的激情,這種狂熱讓我不禁擔心自己會心醉神迷。瑪麗,滿臉溫柔的笑容,是家中的歌聲。有時,她舉手投足會讓我依稀看到母親的身影。當人們在學校叫我“魚眼”時,她會輕撫我的臉頰,手指滑過我的雙唇撫慰我,母親是在我12歲時去世的。瑪麗重新開啟了我塵封已久的對絕望童年的回憶。有好長一段時間,一個個畫面從記憶深處浮現在我面前。
10歲時,我被送到一所貴族中學。這是專為富裕的人家,為比我家富裕的家庭的孩子開辦的學校,父親的期望總是很高。課間休息時,我只能靠戰鬥保衛自己。我在右眼上綁了根布條,我有紅褐色的頭髮,我是紅髮埃蒂安,受人尊重。不幸的是,聖約瑟夫學校有一幫搗蛋鬼。戰鬥達到高潮時,我扯掉布條,揚言我的斜眼可以看到後面的敵人。我嚇唬他們,他們變本加厲地向我進攻,最勇猛的一個人把一塊木頭戳進我的病眼。我感到一陣劇痛,四周突然鴉雀無聲,空蕩蕩的走廊里就剩我一人。一個黑影走過來,對我說:
“是上帝懲罰了你。”
母親日以繼夜地守在我床邊。她懷孕了,第七個孩子即將出生。她為我從此徹底瞎了的眼睛換藥。我聽到醫生在爭論是否應該把它摘除,最後,他們保住了眼球,縫合了撕裂的眼皮。
再也沒人敢正視我,沒人,除了我母親,直到她去世;沒人,除了瑪麗,從去年開始。少年時,我懷著希望詢問鏡子,試圖聽到它回答我事實並非我想像中那么可怕。然而每照一次,情況都更糟。
10月22日
上星期,蓋特將軍率領的美軍在薩拉托加包圍了南下哈得孫的英軍縱隊,柏高英將軍率五千士兵投降,與此同時,豪將軍正準備在費城舒舒服服地過冬。效忠派似乎對他表示熱烈的歡迎,一場場晚會奢侈華麗,女人們優雅迷人,英國軍官風度非凡。要是豪率他的部隊向北推進,與柏高英會合,我們就一定會吃敗仗。不過駐紮在佛吉峽谷的華盛頓將軍潰散的軍隊可能阻截了他們。這不是由於英國人的寬恕,也許,我們更應把這戰爭間隙的喘息歸功於效忠派公民毫不吝惜的仁慈,儘管並非出於自願,他們還是為被其稱作造反者的愛國者的事業盡心盡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