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代表作家,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傑拉德,馬爾科姆·考利,約翰·多斯·帕索斯,背景,文學特點,分析,戰爭,美國精神,在歐洲,影響,
來源 關於“迷惘的一代”的來源,
海明威 在他的散文中提到過。當時
格特魯德·斯坦因 小姐使用的
T型福特車 的發火裝置出了故障,車行里那位戰爭(
一戰 )最後一年當過兵的小伙子在修理斯坦小姐的舊車時技術不熟練,而且工作態度也不夠認真,斯坦小姐提出抗議後,車行老闆狠狠地批評了他。這位老闆對他說:“你們都是迷惘的一代。”
於是斯坦因小姐回去之後就對海明威說:“你們就是這樣的人。你們全是這樣的人,你們所有在戰爭中當過兵的人。你們都是迷惘的一代......你們不尊重一切,你們醉生夢死......別和我爭辯,你們就是迷惘的一代,與車行老闆說得一模一樣。“
後來,海明威把這句話作為他第一部長篇小說《
太陽照常升起 》的題詞,“迷惘的一代”從此成為這批雖無綱領和組織但有相同的創作傾向的作家的稱謂。所謂“迷惘”,是指他們共有的彷徨和失望情緒。“迷惘的一代”儘管是一個短暫的潮流,但它在美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確定了的。
代表作家 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 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海明威 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 (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美國作家和戰地記者,被認為是20世紀最著名的小說家之一。是美國“迷惘的一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作品中對人生、世界、社會都表現出了迷茫和彷徨。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授予銀制勇敢勳章,1954年因為“他精通於敘事藝術,突出地表現在其近著《
老人與海 》之中;同時也因為他對當代文體風格之影響”獲
諾貝爾文學獎 ,代表作品有《老人與海》、《
吉力馬札羅的雪 》。作品主題集中在對戰爭的反對和對“硬漢”精神的倡導。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傑拉德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傑拉德 (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1896年9月24日-1940年12月21日),二十世紀美國最傑出作家之一。1925年《
了不起的蓋茨比 》問世,奠定了他在現代美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成了20年代“爵士時代”的發言人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品有《了不起的蓋茨比》、《
夜色溫柔 》。作品主題集中在“美國夢”及其幻滅,展示大蕭條時朗美國上層社會“荒原時代”的精神面貌。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傑拉德 馬爾科姆·考利 馬爾科姆·考利 (Malcolm Cowley,1898-1989年),美國評論家、詩人、編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他旅居法國,成為“迷惘的一代”的一員。他一生都致力於文學事業,尤其是他在20世紀20年代參與“迷惘的一代”的活動,備受學界關注。1934年,他發表《
流放者歸來 》,談論了那個時期的經歷。考利也是一個關心社會並積極參與的人,然而即使他積極參與,但是並不清楚美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因此導致他在政治立場和觀點上左右搖擺。因此,不像海明威對這個稱號嗤之以鼻,考利自己將自己稱為“迷惘的一代”,並且詳細地分析了這一現象。
馬爾科姆·考利 約翰·多斯·帕索斯 約翰·多斯·帕索斯 約翰·多斯·帕索斯 (John Dos Passos,1896-1970),小說家。代表作品是《美國》三部曲。作品早期集中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並帶有一定的左翼思想。後來的作品大多宣揚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對美共和蘇共多所指責。和考利一樣,帕索斯也是一個在立場上搖擺不定的人,對美國社會未來感到擔憂又不知如何解決,找不到確定的方向。這使他也加入了“迷惘的一代”的陣容。
背景 “迷惘的一代”的作家誕生原因和他們的觀點與美國的本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這一切都要追溯到美國這個國家及其精神:“美國精神(
美國夢 )”的建立。
格特魯德·斯坦因 18世紀中後期英國的北美殖民地造反長達15個月,1776年7月4日,這些造反殖民地的代表召開了
大陸會議 通過了令當時的“美國人”一聽到便會心潮澎湃的《
獨立宣言 》。《獨立宣言》中聲稱:“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Liberty,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獨立宣言》對美國當地殖民者的反抗(尤其是士兵)起到了很強的鼓舞作用。這句話也可以被認為是美國精神的雛形,雖然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並不是殖民者孤軍奮戰取得的,但是當時美國人的決心與勇氣確實遠遠超出英國人想像。
在歐洲人到達美洲之前,美國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多數人類學家相信他們是穿過了遠古時代連線美洲大陸和亞洲大陸的
白令陸橋 而來的。在17世紀左右,歐洲人開始在美洲定居,主要的起源點在
詹姆斯敦 和
普利茅斯 。在這些地方的人的身上也可以看到今天美國精神的影子——這些人有的是追求宗教自由的清教徒,有的則希望在這篇未知的充滿可能性的新大陸上追求全新的生活,有的則希望看看能否發家致富。簡言之,美國人是由一群不懈尋求希望的人組成。美國歷史上不存在封建制度,大多數美國人都信仰
自由主義 。正是對自由、平等的夢想把歐洲人吸引到美國來的。他們是來尋求希望的。自然環境帶來的困難沒有打垮美國人的精神,反而堅定了他們尋求自由的決心。這些人在經歷了一段相當困難的時期後漸漸開始征服荒野,走向繁榮,建立了13個早期殖民地,並在經濟上引起了英國王室的重視。
獨立戰爭 以後,一批龐大而並不情願的西非黑人作為奴隸移民到美國,這些奴隸在美國的經濟繁榮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也是
南北戰爭 的導火索。在美國,南方的經濟主要依靠農業來維持,美國的“白色黃金”——棉花,是當時占主導地位的作物,產量最高時可達世界總產量的三分之二,然而種植、收成棉花卻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多數就是由美國黑奴來完成的。因此,美國南方的農業經濟對奴隸具有高度的依賴性,也是為什麼美國在多數歐洲國家廢除奴隸制後依然保持奴隸制的原因。美國作家
威廉·福克納 非常細緻地描繪了這一時期南方社會的狀況,並對奴隸制社會進行了嚴肅地批判。正如福克納一樣,美國北方對南方的奴隸制是難以容忍的,反奴隸制的呼聲也越來越響,類似“
地下鐵路組織 ”的網路也隨之出現。南方的農業社會和北方的工業社會本身無形中就已經將國家一分為二,因此,包括出於對
亞伯拉罕·林肯 總統的不信任,在林肯總統就職前後美國南方的7個州宣布獨立,直接引起了南北戰爭的爆發。起先以維持美國領土完整為目的的南北戰爭後來漸漸地演變成了以廢除奴隸制,建立自由、民主社會為目的的革命戰爭,但這也是美國歷史上最血腥、最殘酷的戰爭,戰爭造成了約75萬士兵死亡,大概占當時美國人口的百分之二,同時,南北戰爭也是
第一次工業革命 之後第一次大規模的戰爭,因此也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南北戰爭隨南方軍隊領袖
羅伯特·李 簽署投降書而結束。重建時期,聯邦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給予黑人公民權,第十五條給予黑人投票權,並實行了一系列保護政策,而實際上,種族問題依然沒有間斷。另外,美國歷史上還有著名的
西進運動 。在這些事件中,無論是獨立戰爭還是南北戰爭,都包含了美國人希望通過自己的不懈奮鬥去追求美好生活的努力和願望,在美國人看來,這就是他們的美國精神。
南北戰爭 從南北戰爭結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這半個世紀中,美國經歷了一個無論就深度還是就廣度而言都前所未有的工業化進程。這一進程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社會的面貌:它已經真正成為了一個工業發達的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新興巨頭。
20世紀初,美國國內掀起一股
進步主義 熱潮,進步主義者相信只有在有秩序的社會中,美國才能有希望找到政治合作並為美國公司供過於求的產品和資本提供長期市場。進步主義是美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局部調整。進步主義思想對美國乃至世界都有廣泛影響,塑造了美國近代的政治經濟體制。其中的一些思想在
羅斯福新政 中亦有所體現。因此美國在
第一次世界大戰 時採取的政策與進步主義脫不開干係,
伍德羅·威爾遜 總統在1917年4月向參議院發表演講時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為人道而非為單純的征服而戰。總統及其支持者為美國介入戰爭辯護的理由是德國支持的是反動,即極端的政治保守主義,而美國及其盟國是為自由主義而戰。進步主義者確信美國的勝利將在世界範圍維護美國的民主牌號。
伍德羅·威爾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迷惘的一代”作家繼承了美國精神的精髓,對現實是抱有幻想的、頭腦里充滿了
理想主義 的。這些二十左右歲的青年人懷著夢想,為了“捍衛世界民主”,帶著
十字軍 東征的情緒爭先恐後的加入了戰爭。比如
海明威 就聽從了政府的誘導,在年僅19歲就加入了救護隊任汽車駕駛員,開赴義大利前線。有一次,
奧地利 軍迫擊炮在他身邊爆炸,身旁的兩名士兵被炸死,海明威身負重傷。義大利政府為表彰他的英勇事跡,授予他兩枚勳章。起初,他對自己的負傷充滿了光榮和自豪,“這是為一樁大事業而受傷。這場戰爭沒有英雄人物,我們都願意獻出我們的身軀……我的身軀被選中,我覺得驕傲和高興……”在美國精神的支撐下,“迷惘的一代”作家在其作品中也體現了美國人對自由和幸福的追求。這集中體現在對金錢財富的追求和對永恆的青春和美的追求,後者“即富於幻想的美國人對幸福的追求、精神需求的追求。”但是戰後簽署的《凡爾賽和約》讓他們發現所有這一切只不過是歷史對他們的玩弄。一戰結束後,這批年輕人離開了戰場,在反思這場戰爭的同時,開始尋找能夠重新指引他們生活的思想和文化。他們中的很多人來到了
巴黎 ,企圖在歐洲文化中心能夠找到他們心中的答案,其中就包括後來的海明威等人。
《
凡爾賽和約 》是一戰結束以後對於德國方面的不平等條約。《凡爾賽和約》序言宣布,以“鞏固公正及永久之和平”代替交戰狀態。全約包括15章440條,第一章為
國際聯盟 盟約,其餘各章主要涉及領土割讓、軍備限制和賠款三個問題。總的來說,《凡爾賽和約》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關於建立國際聯盟以防止戰爭;另一部分是對德國的全面限制,防止德國重新發動戰爭。實際上,《凡爾賽和約》是英法等戰勝國對德國的壓榨,英法等國在戰勝以後,一直是想從戰敗國身上得到大量的戰爭賠款,並沒有過多地考慮戰敗國國家人民的感受,使這些戰敗國不能夠很好地融入到國際社會。面對這樣的懲罰,德國是很難接受的,始終想重新回到一流國家行列,並對英法充滿仇恨。首先,在《凡爾賽和約》中法德矛盾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其次,《凡爾賽和約》在領土劃分時沒有考慮德國人的意願,而是強行把眾多的德國人分割出去,這深深地刺痛了德國人民的情感,也為德國日後發動戰爭提供了藉口。關於領土變遷,德國原希望一切通過民族自決。實際情況卻是德國的大塊領土沒有經過公民投票,也不顧居民的實際情況便被分割出去,“特別是把但澤和東
普魯士 同德國主體分割開來一事,引起了懷恨在心的德國人的不滿”。再者,《凡爾賽和約》最終把發動戰爭的全部責任完全推到德國身上,這是迫使德國承擔賠款義務的“道義根據”。但是,德國人民是不同意把責任全部推到德國身上的,是不能接受這種罪責的。這些在“迷惘的一代”看來是不人道的,有悖於他們參加戰爭初衷,有悖於他們所理解的美國精神。並且事實上,這個和約也為
第二次世界大戰 埋下了隱患。
凡爾賽條約後的德國領土形勢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社會出現了短暫的繁榮時代,稱為“
柯立芝繁榮 ”。在這一段時期,由於歐洲剛剛經歷一戰,經濟發展陷入停滯。便於美國經濟勢力向外擴張。美國國內通過技術革新,固定資本革新和企業生產及管理的合理化,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程度空前加速,經濟發展迅速。然而,發展起來的不僅僅是經濟,還有令老一輩人費解的事物:爵士樂、飆車、出國留學,許多與傳統觀念格格不入的社會現象開始出現。許多美國青年去歐洲參戰,打開了眼界,特別欣賞法國人的瀟灑而浪漫的情調。許多青年男女刻意模仿,形成新的流行時尚;男青年穿著烷熊皮茄克,背著旅行水壺;女青年燙了頭髮,穿著超短裙,行動和衣著不受傳統的約束。美國人之間的隔閡消失了,人們相互交往增加了,新的傳媒出現了,大家可以隨時聯繫和交談。歐洲的新風尚席捲了美國。巴黎人可以隨意喝酒,美國1919年通過禁酒令第18條修正案,但是年輕人根本不理睬,白酒銷量劇增,雞尾酒會開得更豪爽。美國進入了一個追求物質、容易掙錢的新時代。
1929年
赫伯特·胡佛 作為聲望卓著的博愛主義者入主白宮。胡佛幾乎是美國最榮耀地接掌政權並且最丟臉地下台的一任總統。1920年,胡佛曾表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無限信心。他在《美國的個人主義》中斷言,通過提倡機會均等,美國的制度將使“才能、品格和智慧暢通無阻地發揮”。而實際上,這個時期美國高度繁榮的背後存在著巨大的泡沫。以英格蘭銀行調高利率為誘因,觸發了紐約股市的動盪和最終崩潰。紐約股市的崩潰引起美國各個經濟環節的連鎖反應,甚至波及到歐洲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胡佛的“自力更生”、“放任自由”的經濟政策不但沒有挽救美國,反而使美國進一步陷入了巨大的經濟漩渦。從1929年到1933年,美國國民總產值由1040億美元降至740億美元,國民收入由880億降至400億。1930年1350家銀行破產,1931年有2290家銀行破產,1932年有1453家銀行破產。一戰後的美國社會的
大蕭條 進一步促進了“迷惘的一代”的確立。
赫伯特·胡佛 文學特點 “迷惘的一代”小說所植根的時代具有兩大特徵:一度的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繁榮和美國國民的精神空虛與道德墮落。當然,以歐內斯特·海明威、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約翰·多斯·帕索斯、
托馬斯·沃爾夫 等為代表的美國作家雖然都稱做“迷惘的一代”,卻並沒有徹底消沉下去。他們雖流落他鄉,但仍自願回國;他們雖抨擊市儈作風,但仍熱愛祖國。正是他們在這一過程中為美國奉獻了文學史上最有生氣、最激動人心的作品。“迷惘的一代”作家在藝術形式上借鑑了歐洲尤其是法國的現代主義手法,在思想意識上受到歐洲存在主義等哲學思潮的影響,同時繼承了
馬克·吐溫 、
惠特曼 和
豪威爾斯 的
民主主義 傳統和美國人獨有的探索精神,拓展了小說創作題材的範圍,對小說的語言與形式進行各種大膽創新與實驗,形成了獨特的風格,表現出一種“現代派的現實主義”精神,其作品對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影響,是美國文學的“第二次繁榮”。
“迷惘的一代”小說是20世紀20年代美國現代主義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儘管海明威、菲茨傑拉德、帕索斯的長篇小說不像
喬伊斯 等作家的意識流小說那樣在形式和技巧上進行徹底的革新,也不像他們的作品那樣一味潛入人的意識領域。不遺餘力地描繪連綿不絕的感性生活,但他們的小說至少在以下兩個方面體現了現代主義的基本特徵。首先,“迷惘的一代”小說充分反映了創作題材的現代性。它同意識流小說一樣旨在揭示現代經驗,即戰後瀰漫於西方世界的異化感、孤獨感和絕望心理,並深刻反映現代人的道德困境與“性格認同危機”。這與20世紀初
貝內特 和
高爾斯華綏 的現實主義小說所關注的焦點和表現的題材截然不同。其次,“迷惘的一代”小說在作品形式和創作技巧上同樣顯示了現代主義的藝術特徵。正如
勞倫斯 的小說與喬伊斯的作品存在著明顯的區別一樣,“迷惘的一代”小說也具有其獨特的藝術風格。不過,它同時也體現了美國現代主義小說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特徵。在作品的敘述形式上往往擯棄通曉一切的全知敘述,而經常採用像《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尼克那樣有限的、不可靠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敘述角色。不少作品在結構上打破了時間順序,巧妙地採用隱喻、意象和象徵的手段表現主題,並通常以含混的、“開放性”的方式結尾,這與其他現代主義小說有著驚人相似之處。顯然,“迷惘的一代”作家與同時代的其他現代主義作家被某種具有親緣關係的藝術共性聯繫在一起,使他們表現出與當時的現實主義小說家截然不同的藝術傾向。
在寫作手法上,“迷惘的一代”小說擯棄現實主義小說以塑造人物性格為核心、以情節為主體的結構框架,以及開頭—發展—高潮—結局的傳統套路,而是以非連續性結構、碎片式描寫和高度實驗的語言表達為基本特徵,以象徵與傳統的決裂,突破傳統現實主義小說正常的時間和空間結構,從根本上否定事件發展的連貫性和線性因果關係。不連貫與非邏輯時序能夠表現出連續講故事方式所達不到的效果。在《美國》三部曲中,作者帕索斯集中描寫的12個人物沒有一個是貫穿始終的主人公,他們各自活動;故事獨立成章,間或有些情節上的交叉聯繫。“迷惘的一代”小說在寫作手法上另一個特點是沒有以往常有的解釋、評論和總結,有的是種種能調動讀者視覺、聽覺 、觸覺的意象和細節的堆砌。它經常留出許多空白讓讀者去填補,因此使閱讀更具挑戰性和新鮮感。
從“迷惘的一代”小說中可以看到作家同作品之間有著更直接的聯繫,海明威和菲茨傑拉德的作品都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了作家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帶有明顯的自傳性傾向。與19世紀現實主義小說不同的是,“迷惘的一代”小說不再把反映和摹寫外部世界的現實作為自己的任務,而轉向了對人的主觀世界或精神狀態的探索與挖掘。然而儘管他們反映的是主觀,卻極力用客觀的形式去表達。小說的敘述者也不再無所不知,而往往是故事的主要人物,如《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尼克·凱洛威 、《太陽照樣升起》中的傑克·巴恩斯等。
“迷惘的一代”小說對傳統小說的挑戰還表現在對“人”的詮釋上。小說注重揭示人性的醜惡面,闡述人物的“非英雄化”本質,以及人內心世界的卑微、混亂、無聊與荒謬。呈現出畸形物質世界裡具有病態心理人群的生活畫面,或是走向病態心理的人。《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人物幾乎都是病態的,他們渾渾噩噩,雖生猶死,無所適從。作者塑造這些人物旨在從根本上打破傳統的秩序,推翻傳統的信仰。《太陽照樣升起》深刻地揭示了戰後移居歐洲的美國青年極其嚴重的異化感和幻滅感,使廣大讀者首次目睹了美國現代主義小說中像傑克這樣的典型的反英雄人物,標誌著美國小說創作的一個重大轉折。
“迷惘的一代”的創作還存在語言上的簡約主義和口語化傾向。“迷惘的一代”在戰爭期間深受戰爭宣傳的欺騙之苦,對所有崇高的字眼都棄之如敝屣:“什麼神聖、光榮、犧牲這些空泛的字眼兒,我一聽就害臊……我可沒見到什麼神聖的東西,光榮的東西也沒有什麼光榮,至於犧牲,那就像
芝加哥 的屠宰場,不同的是肉拿來埋掉罷了。”所以他們在文學創作時推崇文字上的簡約主義。海明威更是把這種簡約風格推到了極致。他採用電報式的語言,通過簡約的對話和細節,用含蓄的、間接的手法暗示人物內心的戲劇性變化,而不是像傳統的作法那樣通過描述來鋪陳人物內心。結尾也常常是戛然而止,絕不拖泥帶水,也不煽情作秀,即所謂的“零度結尾”,反而賦予了作品更為震撼人心的力量。海明威因為精通敘事藝術而獲得
諾貝爾文學獎 ,他的“
冰山原則 ”就是他現代敘事藝術的集中體現,作家只寫露在水面上的八分之一,其餘的八分之七僅通過暗示留給讀者去補白。這種創作原則極大地影響了他同時代及後輩作家的創作傾向。口語化成為一代人散文風格的普遍特色。
埃德蒙·威爾遜 甚至在他的文學評論中也摒棄學究字眼,選用口語辭彙。亨利·米勒在《
北回歸線 》(1934)中把這種傾向推到極端,成為用粗鄙的語言來表現道德冷漠和感覺精微的迷惘特徵,結果被
蕭伯納 罵作是“為下流而下流”(dirt for dirt’s sake),難登大雅之堂。
“迷惘的一代”創作的另一個特點是形式上勇於創新。二十世紀初的美國文壇正是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和現代主義交匯的時期。這些青年作家們融合了戰後對傳統的反叛精神,吸收了各流派的藝術成就,並各自創造出自己的風格特色:
菲茨傑拉德 浪漫精巧、
海明威 樸素遒勁、
多斯·帕索斯 巨觀大氣。在法國的流放生涯讓他們充分養成了對形式實驗和
福樓拜 的興趣。他們學習福樓拜客觀冷靜、無動於衷的敘述態度,學他的作者隱退的敘述技巧,學他的簡練風格和反覆修改的寫作精神。他們感到傳統的文學敘述手法已無法表達現代工業社會的種種特徵,於是轉向
意識流 、象徵、電影的“
蒙太奇 ”,有限人物視角、多重視角等創作手法。多斯·帕索斯是形式試驗的大師,他在小說領域中開拓性的技巧試驗也許比他小說本身的價值更令人矚目。他第一部令人難忘的試驗小說《
曼哈頓中轉站 》(1925) 交叉運用了
印象主義 、
表現主義 、
蒙太奇 和新聞報導等多種藝術手法。各種社會鏡頭和生活畫面雜相交錯,水和火的隱喻表達了戰後西方世界的荒原意識,充分體現了多斯·帕索斯的實驗精神。此後,多斯·帕索斯在其恢弘巨著《
美國三部曲 》(1937)中,在小說常規敘述之外穿插了“新聞短片”、“攝影機眼”和“人物小傳”等,來揭示了二十世紀前三十年美國社會的動盪與變遷。這種以美國社會為主角而不是以個別人物為主角的文獻新聞手法在美國文學史上留下了獨特的印記,對諸如
諾曼·梅勒 ,道格多羅等後繼作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為1960年代新聞報導的興起提供了歷史的源流和借鑑。同時,後現代非虛構小說也能從他的寓非小說於小說之中的試驗獲取靈感。雖然現在看來,多斯·帕索斯的文學試驗多少有些機械、呆板,“攝影機眼”的語言晦澀,“新聞短片”已經成為湮沒的歷史,讓現代讀者難以理解,但他試圖用現實的新聞材料與小說敘述部分相平行,從而給小說創造一種時代氣氛的嘗試卻是他的成功之處。相比之下,海明威保留了較多的現實主義因素,他的小說還常能清晰地分出開頭、高潮和結尾。但形式上的實驗還是顯而易見的,除了電報式對話的獨創外,他突破了福樓拜的人物內部聚焦常為第三人稱的局限,改用第一人稱的內聚焦,更縮短了人物與讀者之間的心理距離。在其主要作品中他也試驗了意識流、內心獨白、閃回等多種敘述技巧。
福克納 則是大刀闊斧的運作
意識流 ,在這方面的徹底性遠遠超過海明威。他在諸多的作品中嘗試多角度敘述方法和意識流,以及“神話模式”,即有意識地使他講述的故事與神話故事平行展開,從而創造了一個讓人流連忘返的
約克納帕塔法世系 。詩人肯明斯突破傳統標點符號、大小寫、句法的束縛,創造了成為肯明斯標記的小寫的第一人稱單數“I”,展示了語言更本質的活力。此外他在詩歌的排字法上標新立異,如把“一葉落下/孤獨”豎排成數字1的形狀,更突出了孤零零的孤獨意象,使詩歌同時具有繪畫般的視覺衝擊力。被譽為“迷惘的一代”最後一位天才的韋斯特更是以形式實驗著稱,在敘事技巧上非常前衛、激進。他在《
鮑爾索·斯奈爾的夢幻生活 》(1931)和《孤心小姐》(1933)中藉由理性控制的夢境來講述存在的寓言和充斥現實夢境的荒誕意象,在創作意識和寫作技巧方面直接影響了後起的美國作家如
卡森·麥卡勒斯 ,
奧康納 ,霍克斯和
塞林格 等人。
另外,一戰後的美國文學多採用象徵主義來表達幻滅感。如《永別了,武器》中的雨代表的就是厄運,常與死亡相伴。當凱瑟琳告訴亨利:“我害怕雨,因為有時我看見自己死在雨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那種厄運的陰森。所以,最後小說以雨作為結尾時,讀者已經意識到了凱瑟琳的死亡。再如,《太陽照常升起》中的羅伯特·科恩在失戀後去找人決鬥,以求一死。科恩所代表的就是理想的磨滅和傳統道德信念的破碎。
分析 “迷惘的一代”的作家雖然在作品中流露出濃厚的悲觀情調,對戰爭抱著消極、厭惡的態度,缺乏積極的反對戰爭,爭取和平的行動,但他們的作品無論在內容或藝術形式上都突破了傳統的束縛。特別是其中的一些作家後來獨樹一幟,成為現代文學的大師。所以,“迷惘的一代”儘管是一個短暫的潮流,但它在美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是確定了的。考利在《
流放者歸來 》中談到:“對年紀大一些的人來說,這個詞很有用,因為他們一直在尋找適當的詞來表達他們的不安之感,他們感到戰後的年輕人的人生觀以他們自己不同。現在他們用不著不安了:當年年輕人閱讀冒犯社會道德準則或文學傳統習俗的最新言論,只要說一聲”那是迷惘的一代“就行了。然而這個詞對年輕人也很有用。他們是在迅速變化的時期里長大並進入大學的,在這樣一個時期里,時間本身似乎比階級的影響或地域的影響更為重要。現在他們終於有了一步口號能宣告他們與老一輩作家的隔絕之感,與同輩作家的親切之情。這個口號中的名詞比形容詞更為重要。他們可能惘然不知所終,可是他們已經有了共同的冒險經歷,形成了共同的觀點,從而有可能把他們說成是一代人”。在他看來,“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首先是因為他們是無根之木,在外地上學,幾乎和任何地區或傳統都失卻維繫。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是因為他們所受的訓練是為了適應另一種生活,而不是戰後的那種生活,是因為戰爭使他們只能適應旅行和帶刺激性的生活。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是因為他們試圖過流放的生活。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是因為他們不接受舊的道德準則,並因為他們對社會和作家在社會中的地位形成了一些錯誤的看法。”
“迷惘的一代”也可以稱為“迷失的一代”,意思是迷失了前進方向而又不知道該怎么辦的一代人。這些人大多是歐美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著類似亨利那樣的經歷(亨利是作家海明威作品《
永別了,武器 》的主人公)。一方面,戰爭摧毀了他們的政治信仰、人生理想、道德標準,使他們以前奉為神聖的價值觀念土崩瓦解。他們憎惡戰爭,但又不知道如何消滅戰爭,心情苦悶,感到前途茫茫。一如亨利的內心獨白“我每逢聽見人家提起神聖、光榮、犧牲這些字眼,總覺得不好意思。這些字眼我們早己經聽過,有時還是站在雨中聽的,站在聽覺達不到的地方聽,只聽到一些大聲喊出來的字眼;況且我們也讀過這些字眼,從貼在層層舊布告上的新布告上讀到過。但是到了現在,我觀察了好久,可沒有看到什麼神聖;所謂光榮的事物,並沒有什麼光榮;所一謂犧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場,只不過這些屠宰好的肉不是裝進罐頭,而是掩埋掉罷了,有許多字眼我現在再也聽不下去……”
另一方面,
大蕭條 摧毀了他們的生活,當他們帶著身心的雙重創傷返回戰後腐朽的資本主義世界時,迎接他們的卻是各種無法克服的社會危機,這無疑加重了他們的幻滅。他們未嘗不想使自己再度振奮,然而靠個人努力卻無能為力。於是他們竭力迴避現實,以一種畸形的桀驁不馴投身於各種富有刺激性的活動中。然而消極遁世和放浪形骸畢竟不是療救他們精神危機的良方,當他們遠離社會後,依然找不到出路,反而陷入悲觀絕望而不能自拔。理想與現實的雙重破滅使得他們成為“迷惘的一代”。
戰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拋開美國政府不談,美國人民是嚮往和平的,只想建立他們理想中的家園。因此,美國人民起初對美國插手一戰持有的是反對態度。美國人民為美國遠離戰火而感到安慰。雖然大多數美國人同情英、法一方,但這僅僅是道義上的支持,要親自參加戰爭又是另外一回事了。1917年,
威爾遜 召集國會,把美國的參戰描繪成一場保衛世界民主的“聖戰”。然而他們在肉體遭受巨大的創傷同時也承受著精神上的困惑。雖然若干年後戰爭已經過去,但是戰爭的陰影卻讓他們心靈遭受嚴重創傷。於是,以海明威為首的美國青年一代作家們藉助他們的筆,來宣洩他們的反戰思想。他們的作品中的每一個人都經歷了戰爭的磨難,心靈遭到了創傷。所以他們筆下的人物都是“迷惘的一代”的真實寫照。
然而,用“迷惘的一代”概括戰後的一代文學青年其實是非常籠統且不確切的。海明威在《
流動的盛宴 》中頗為不屑地說:“讓她(
斯泰因 )說的什麼迷惘的一代那一套跟所有那些骯髒的隨便貼上的標籤都見鬼去吧。”應該看到,這批作家們雖然在反戰、自我流放等生活經歷方面有共同之處,但這並不意味著就能將他們簡單地歸於“迷惘的一代”的大旗下而忽略其個人特色。相反,個性和個人風格正是他們致力追尋的東西,也是推動他們進行文化反叛的初衷。事實上,“迷惘的一代”雖然人數眾多,但大多數已經湮沒於歷史,到如今默默無聞,究其原因恰恰是因為這些人的作品太符合“迷惘的一代”的“共性”而缺乏能垂名青史的個人特色。這也是一個有趣的文化悖論,一方面他們以其反叛舊文化的標新立異加入了“迷惘的一代”的陣營,但是一旦這些標新立異被主流文化接納,他們的先鋒性就迅速褪色,終至湮沒於“迷惘的一代”的共同話語中。倒是海明威,多斯·帕索斯,肯明斯,福克納等作家不拘泥於“迷惘的一代”的束縛,在1930年代之後逐漸轉向,不斷成長,逐漸形成自己獨特的題材與風格,從而在美國文學史上占據了牢固而持久的位置。
迷惘的一代”從其嶄露頭角的那一刻起就具有鮮明的文化反叛性。這批青年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脫下軍裝,衝上文壇。憑著他們親身參與戰爭的特殊體驗,以及流放歐洲親身感受的歐洲現代藝術的啟蒙,他們的作品在表達反戰情緒和現代青年的幻滅意識上獨樹一幟,令中年作家難以企及。早已成名的
舍伍德·安德森 和
辛克萊·劉易斯 等人雖然只年長二十來歲,但相比之下已經儼然老去。他們的作品在年輕讀者看來似乎過於溫和平淡,成了昨日黃花。“迷惘的一代”作家迅速衝垮了這些中年溫和派作家在文壇的統治以及其代表的“高雅斯文傳統”(the genteel tradition),征服了編輯、出版商和讀者,成為1920年代美國民族文學的主導聲音。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永別了,武器》中作者就通過主人公亨利的內心獨白說道:“什麼神聖、光榮、犧牲這些空泛的字眼兒,我一聽就害躁......”然而在此之前,海明威也曾說過:“這(一戰)是為一樁大事業而受傷。這場戰爭沒有英雄人物,我們都願意獻出我們的身軀……我的身軀被選中,我覺得驕傲和高興……”。換言之,“迷惘的一代”厭惡的不是在獻身正義的情況下可以接受的戰場中的流血和犧牲,而是在戰爭中扭曲的傳統的價值觀念對他們的冷酷欺騙。他們在戰爭中見到的只是屠殺和死亡。他們認為,這場戰爭是歐洲各國的混戰,美國被捲入其中僅僅是替歐洲做了一件它不論從道德,還是人力物力方面都無法完成的骯髒事。為這樣的戰爭而犧牲掉一批最優秀的年輕人的生命是毫無意義的,甚至是可恥的。
永別了,武器 其次,戰爭對知識分子造成了更為深刻而持久的另一種精神創傷,這也是他們反戰的一個原因。這場戰爭使他們看到了曾令他們引以為榮的歐洲文明的破產,戰爭暴露出來的資本主義文明的虛偽本質使他們產生了歐洲文明該何去何從的困惑。曾為他們的父輩所珍視、所格守的一些傳統價值觀念在這場戰爭中被無情地摧毀了,他們感到個人和社會之間出現了無法彌合的裂縫。舊的體制已經被摧毀,而新的體制又尚未建立,他們處於一種孤獨的境地。
亨利·F·梅在其著作《美國天真時代的終結》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化革命”論點。梅認為,以清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理性為基礎的美國文化傳統,自十八世紀形成之後,歷經民主革命、工業革命的推動和加固,一直未曾大動根本,只是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才產生激烈的變革。一戰好像一條歷史鴻溝,割裂了傳統的綿延和發展,成為現代意識和新文化的起點。溝的那邊站著
歐·亨利 和
亨利·詹姆斯 ,而這邊則是
海明威 和
艾略特 。但是這一切的激變並不能簡單地歸咎於一戰。早在大戰爆發之前,支撐舊文化的三根支柱,即對傳統道德、社會進步與紳士文化的信念,已被進步主義改革所帶來的政治與經濟變化腐蝕並鑿空了基礎。一遇上世界大戰的強烈衝擊,整箇舊文化轟然崩塌,留下的殘垣斷壁便成為新文化各陣營的狼奔豕突之地。
而“迷惘的一代”作家就擔當了新文化的衝鋒手的角色。其社會影響遠遠超出文學範疇,在文學和文化領域都觸發了革命性的轟動,影響了青年一代的思想和行為方式。《
太陽照常升起 》發表後,“青年男子試著像小說中的男主角那樣沉著冷靜地喝醉酒,大家閨秀則像小說中的女主角那樣傷心欲絕地一個接一個地談情說愛,他們都象海明威的人物那樣講話”。
菲茨傑拉德 的小說精確紀錄放浪形骸、夜夜狂歡的名士派和摩登女(flapper girls),使這一生活方式一時盛行於美國社會。挾著新文化運動之勢,“迷惘的一代”文學在風靡美國的同時,帶動起文藝百家和大眾生活方式上的現代主義潮流。再加上哈萊姆黑人文藝復興、女權運動和多種移民文化的興起,現代美國文化中斑駁絢麗、雅俗並舉的多元格局開始逐漸形成。
美國精神 當戰後的美國青年們帶著身心的雙重創傷返回戰後腐朽的資本主義世界時,迎接他們的卻是各種無法克服的社會危機,這無疑加重了他們的失望和幻滅感。paula.S.Fass 在The Damned and the beautiful——American youth ln the 1920's(《錯誤而美麗的美國青年》)這樣寫道:Youth suddenly became a social problem in the1920's. The Problem of youth was connected to changes in family nurture,education,sexroles,leisure habits and social values and behavioral norms. Aboveall,youth hadbecome a challenge to an older social order. While it is difficult to separate the youth problem from the many social issues to which it was linked in the public mind,contemporaries were quite right to understand that the problem of youth is not anisolated phenomenon. The public usually invested youth with too many hopes or fears,thus draining them of theirs pecific reality,but the perception of youth's vitalrelevance was never misplaced. Anxiety about has long become an Americanindulgence.(“二十世紀的青年突然成了一個社會問題。青年問題與他們的家庭生長環境變化、受教育程度、性別角色、休閒習慣、社會價值與行為道德有關。畢竟,年輕人對更加古老的社會秩序構成了一種挑戰。但是人們是很難把青年問題與許多社會問題分隔開來的,因為青年問題不是一種孤立的現象。社會公眾通常是帶著太多的希望或者是畏懼來研究青年問題,因而長期以來焦慮成了美國的一種社會現象”。)
自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後,那些離鄉背井的人都把美洲視為天國,他們懷著宗教理想,乘坐著滿懷希望的“
五月花號 ”來到美洲大陸,他們為了自由而來,他們渴望在這片土地上建立一個理想中“山顛之城”。“美國夢”就始於這些早期移民對自由信仰、自由創造的渴望和夢想。美國早期的歲月雖然充滿困難,但是卻充滿希望,人們對未來是樂觀的。最初的移民到達美洲大陸克服了種種困難,經歷千難萬險。西部邊疆的開發成功也使人們充滿了希望,鼓勵大家艱苦奮鬥。美國獨立戰爭勝利後,美國人感到離他們的理想越來越近了。美國人是由一群不懈尋求希望的人組成。美國歷史上不存在封建制度,大多數美國人都信仰自由主義。正是對自由、平等的夢想把歐洲人吸引到美國來的。他們是來尋求希望的。自然環境帶來的困難沒有打垮美國人的精神,反而堅定了他們尋求自由的決心。
在美國精神的支撐下,“迷惘的一代”作家在其作品中也體現了美國人對自由和幸福的追求。這集中體現在對金錢財富的追求和對永恆的青春和美的追求,後者“即富於幻想的美國人對幸福的追求、精神需求的追求。”比如,《
了不起的蓋茨比 》中的蓋茨比是典型“美國夢”的追求者,他相信資本主義社會所謂的機會均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大發戰爭財,經濟上有了一定的發展,人們的精神面貌產生了很大的變化。蓋茨比在為了夢想奮鬥中所表現出的精神就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他堅毅勇敢,為了愛情,或者說是理想中的愛情,犧牲了自己的一切。在蓋茨比的心中,女主人公黛西已經成為了理想的化身,象徵美國一切美好的事物,“他花了大量的錢財,用盡畢生的經歷,去恢復舊夢。他在腦子裡虛構了一個美麗的境界,這裡描一下,那裡添一筆,把他能想到的優美色彩統統加上去,把自己的一切貢獻給這個夢。”
了不起的蓋茨比 海明威、菲茨傑拉德等“迷惘的一代”作家,都經歷了一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社會還在宣揚高尚人性和上帝的存在,美國人民不但有理想,有希望,而且還有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和社會秩序,人們仍然堅信他們祖輩傳下來的拓荒精神和“
美國夢 ”,美國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依舊是實現自由夢想的天堂。第一次世界大戰原本與美國並沒有多大關係,直到1917年由於德國展開了無限制的潛艇戰才加入到戰爭中。戰爭雙方都造成了極大的損失,死傷無數。而美國在一戰中的損失是較小的,參戰僅一年,戰火併沒有燃燒到美國本土。如果單純從物質方面衡量,美國在戰爭中是獲利的。但是經濟上暫時的繁榮掩蓋不住人們心理道德上極大恐慌,美國對這場戰爭所付出的代價是在心靈上的。
然而,即便是戰後的經濟也好景不長。緊隨
柯立芝繁榮 的是美國社會一次空前的經濟
大蕭條 。面對著一個經濟危機、百業凋零、市場蕭條、失業成災的社會,“迷惘的一代”在美國精神的支持下也想再度振奮,但是經過痛苦的奮鬥,結果不是被碰得頭破血流,就是心靈變得更加枯萎,對人生的態度也就變得更加悲觀。他們退伍後需要工作;工業系統也要從戰爭時期恢復常態;但是物價暴漲,給工人造成很大困難;尤其是,背井離鄉的軍隊的生活,以及戰爭的殘酷對這個國家的青年一代產生了一種深遠的敗壞道德的影響。戰爭是過去了,但是它並沒有給美國社會帶來太多進步的東西。許多人懷疑參加這場戰爭是否根本就是鑄成大錯。他們想忘記那個惡夢。但是,怎么才能做到呢?如今,從他們的經驗,他們親身經歷的事情中,他們看到早先教給他們的什麼道德、什麼信義似乎全是一派謊言。這種殘酷的鬥爭,這種騷亂,夭折了的和平,所有這一切都使他們覺得世界是毫無意義的,他們不得不逃避現實了。在青年中,風行的是以放蕩為榮,特別是“及時行樂”的性放蕩行為,全然不顧任何道德規則和舊式戒律。這些頹廢的行為可以從當時很多美國作家的作品中得到驗證。在《太陽照樣升起》中,海明威刻畫了一群被社會遺棄的美國青年們的精神狀態和人生觀,他們把各自的不幸,把一切社會道德標準、價值觀念統統拋到了腦後。
另一位迷惘的一代作家菲茨傑拉德的作品中就表現了這一主題。
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傑拉德 是“迷惘的一代”中最有才華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體現了年輕的一代對“美國夢”的幻滅。在菲茨傑拉德的處女作《
人間天堂 》中展現的是大學生中的“迷惘的一代”。小說如實反映了戰爭對美國國內風氣帶來的影響,包括資產階級傳統道德的動搖與年輕一代放蕩不羈而又焦躁不安的心情。他們是“嶄新的一代”,“長大後發現所有的神都己經死去,所有的戰爭都已經打完、所有對人類的信念都己經動搖。通過這部小說可以看到失望、迷惘的情緒並非位參戰士兵所獨有。美國精神不再能支持年輕一代人在混亂的社會中再到人生的方向和立足點,“美國夢”也逐漸的變為美國整整一代人身上的噩夢。
在歐洲 馬爾科姆·考利 在《
流放者的歸來 》一書中認為“迷惘的一代”這個名詞適用於這樣一個作家群體:他們大多於 1900年前後出生,成長在中產階級家庭,在公立學校接受教育,一戰行將結束之時參軍到歐洲去,大多數人去了法國,在戰爭中受到生理上或心理上的創傷,回國後一部分人聚集在美國原本是窮文藝家聚居地
格林威治村 ,卻不甘心過茫然無謂的生活,一有機會便又紛紛返回歐洲,然而在歐洲的生活卻並不盡如人意,幾年的時間裡,歐洲已經變得與他們記憶中不一樣,他們漸漸體會到了歐洲的衰敗和落後,又重新萌發了回到美國去的念頭。
因此“迷惘的一代”在成長中與社會環境格格不入,一直在尋求精神的歸宿,卻一直無所收穫,在思想的苦難中逡巡徘徊,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和他們的個人生存體驗決定了他們神經症人格中焦慮與迷惘的情緒。逃避與追尋看似是一對意義相反的詞,但是體現在“迷惘的一代”身上,卻具有了行動上的一致性。“迷惘的一代”逃往歐洲,表面上看是對美國國內生活的一種不滿和逃避,他們從歐洲戰場歸來後,感受到祖國的平庸與無聊,轉而投奔歐洲大地,想要生活在與自己理念相符的環境中,其實內在的也是一種對理想生活的追尋。日常生活使“迷惘的一代”感受到了想像與現實的區別,這引發了他們不安與焦慮的情緒,為了擺脫這種焦慮,他們努力想回到心目中藝術與生活的聖地,所以,“迷惘的一代”逃避的同時,也是在追尋。這種向歐洲的逃避和對歐洲文化的追尋反而體現了他們的“迷惘”。
迷惘的一代在歐洲的據點——法國巴黎 1929年12月第一個星期的一起自殺事件宣告了“迷惘的一代”的歸來。一個名叫哈里·克羅斯比的人,作為這一代人中的極端分子,由於始終不適應戰後的生活落差,儘管生活優渥,養尊處優,卻仍然為信仰的缺失選擇了告別這個世界。“他的自殺就像是一首二流的,但誠實坦率而激動人心的詩後面的簽名”。伴隨著這次自殺事件,“迷惘的一代”已經名實不符了,他們中的極少一部分人像哈里·克羅斯比那樣絕望死去,但更多的人在世界上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地位,這意味著他們個人取得了自我調適的成功。“流放者和藝術避難者都回來了。”然而“迷惘的一代”歸國的意義並非局限於此,
存在主義 哲學家
雅斯貝爾斯 認為:人必須通過理性超越自身。他這樣解釋自己的觀點:由於人的深層本質是分裂的——分裂為精神和肉體,理智和感覺,責任和意欲,因此人必須憑藉理性,避免墮落和任意性,超越分裂,最終走向自由。這種超越的意義不在於成功,而在於努力爭取。每個人都有局限性,即使在無望的情況下也不放棄進取,不失掉希望和信心,這是理性的勝利和意義。具體到“迷惘的一代”身上,他們的逃避與追尋不僅是出自本能的指引,更是自己理性的選擇,到歐洲戰場上去幫助無助的人,開拓眼界,回國後希望看到國家現實與理想不符,轉而返回歐洲尋找生活的意義,但在歐洲的生活並不盡如他們所期待的那樣,他們這次歸來體會到的是古老的歐洲衰敗和沉滯的氣息,同時他們通過思考逐漸建立起自己的想法,在海明威早期作品中,處處可以看到“迷惘”和反戰的元素,在《
印第安人營地 》里,海明威寫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印第安人因為不忍目睹臨產妻子的痛苦而用剃刀割斷了自己的喉管。這樣一種恐怖的場面引起同父親出診的孩子尼克的一串串的疑問,如“我們將去哪裡?為什麼他要自殺?我會死嗎?”表現了一個孩子的迷惘。在《
拳擊家 》、《殺人者》和《世界的光》里,海明威描寫主人公少年尼克初次接觸一系列充滿暴力的場面和性的邪惡的世界,感到本能的恐懼和困惑不解。少年尼克正是海明威巧歲時離家出走時得到的心理印象。他的出走擴大了他的視野,但也加深了他的迷惘。而在後期的作品中,海明威似乎漸漸找到了方向海明威在二十年代末發表的長篇小說《
有錢人和沒錢人 》在思想上有所進步,雖然不是他的重要作品,但標誌著他思想的轉變。故事講述了主人公摩根不擇手段地企圖從貧窮上升到富有的過程。在當時美國經濟恐慌的打擊下,他被迫從事非法活動:買賣人口,走私烈性酒,最後為了弄到錢,幫助搶劫銀行的歹徒們逃走,在槍戰中受了致命的傷。在他臨終時他才悟出了花了他整整一生才懂得的道理:“一個人單槍匹馬是毫無希望成功的”。海明威的這部作品雖然沒有涉及戰爭,但我們可以看到他那時似乎也意識到只有通過集體鬥爭,才能改變現實,消滅人間不平。另一方面,他們開始懷念美國進步的社會文化,於是紛紛回到祖國。以上的這種種選擇並不是盲目的,而是有著理性指引的。“迷惘的一代”所經歷的曲折的意義就在於,通過自我理性的判斷,不停止追尋,不停止挑戰,最終達到了一種對生命本真意義的超越。
“迷惘的一代”是時代環境造就的一代人,他們的追求收穫甜蜜也採摘苦澀,他們在戰爭中度過了成人禮,青年時代經歷社會的分崩離析,追崇歐洲,嚮往自由生活,伴隨著對理想的醒悟步入中年,他們曾經徘徊迷惘,逃避現實,追求理想,並最終通過自己的努力,運用自己的學識超越了現實的困頓,在平凡或不平凡的生活中感受著人生目標的本真。正如海明威在《太陽照常升起》的扉頁上所感悟的那樣:“一代人來,一代人走,大地永存;太陽升起,太陽落下,太陽照常升起。”
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戰後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以及流行於美國的二十世紀西方世界的死亡意識、虛無思想等諸多因素導致了“迷惘的一代”的產生。“迷惘的一代”的存在雖然只是短短的幾十年,但是它對美國所產生的影響卻是巨大而深遠的。最大的影響就是形成了二十世紀“迷惘的一代”文學。美國著名詩人、文學評論家馬爾科姆·考利把二十年代的美國文學與
愛默生 時代的新英格蘭文學繁榮相提並,稱之為“美國文學的第二次繁榮”並對歐洲文化與文學產生了有力的衝擊。在這種衝擊中,“迷惘的一代”作家功不可沒。首先是這一時期湧現出來的作家、作品數量巨大。據考利在《流放者的歸來》後的附錄中的不完全統計,生於1891-1905間的“迷惘的一代”青年中,到1942年已經有236人入選美國文化名人字典。在《第二次的文學繁榮》的附錄中,考利又把這個名單擴展到了385人。其次是這一時期美國文學的質量也是獲得公認的。除了耳熟能詳的海明威在1954年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以外,還有
尤金·奧尼爾 (1936)、
賽珍珠 (1938)、
福克納 (1949)、
斯坦貝克 (1962)、
索爾·貝婁 (1976)和
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 (1978)均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如此眾多的作家作品從這個時期開始出現並取得如此崇高的文學成就充分說明“迷惘的一代”時期不僅是美國文學的第二個繁榮期,也標誌著美國文學作為一個整體已經擺脫了英國殖民文學乃至歐洲文學的影子,進入了真正的成熟期。
流放者的歸來 這些作品不僅有利於從內部來理解“迷惘的一代”的思想、生活和創作原則,也便於對“迷惘的一代”進行全方位的研究。並且優秀作家、作品如此集中的出現也進一步深化了“迷惘的一代”的文學傳奇,超越了20年代的短暫時間而對後期文學持續性地產生著影響。馬克·多蘭也認為“迷惘的一代”之所以能成為20年代美國的文化象徵,是因為它是美國歷史上的頗為少見的由一群作家代表一個時代的例子。如前文所說,“迷惘的一代”從其嶄露頭角的那一刻起就具有鮮明的文化反叛性。這批青年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脫下軍裝,衝上文壇,憑著他們參戰的特殊體驗,以及留放歐州親身感受的歐洲現代藝術的啟蒙,使他們的作品在表達反戰情緒和現代青年的幻滅意識上獨樹一幟,令中年作家難以企及。“迷惘的一代”作家衝垮了中年溫和派作家在文壇的統治及其高雅斯文的傳統,征服了編輯、出版商和讀者,成為20年代美國民族文學的主導聲音。
此外,“迷惘的一代”所以影響深遠。除了他們的創作成就之外,傳記文學和回憶錄的空前繁榮也是原因之一。三、四十年代就有弗雷德里克·艾倫的《就在昨天》(1931),
馬爾科姆·考利 的《
流放者的歸來 》(1934),羅伯特·麥卡爾蒙的《天才濟濟》(1938)以及菲茨傑拉德去世後由
威爾遜 收集成冊的《
崩潰 》(1935)等總結、反思“迷惘的一代”的作品問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又目睹了一股回憶熱潮:“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或見證人紛紛推出回憶錄或自傳,包括卡蕾斯·克羅斯比的《熱情年代》(1953),西爾維婭·比奇的《
莎士比亞書店 》(1956),哈羅德·勒布的《如此往事》(1959),羅伯特·寇茲的《追憶》(1906),馬修斯·約瑟夫生的《和超現實主義者一起生活》(1962),
曼·雷 的《自畫像》(1963),
莫利·卡拉漢 的《那個巴黎之夏》(1963),海明威的《
不固定的聖節 》(1964),
多斯·帕索斯 的《最好的時光》(1966)以及南茜·卡納德的《就是那些時光》(1969)。《天才濟濟》也由凱·博伊爾重新修訂於1968年再版。這些傳記不僅有利於從其內部理解“迷惘的一代”的思想、生活和創作原則,它們如此集中的出版也進一步深化了“迷惘的一代”的文學傳奇,使其影響超越了1920年代的短短時間而對後起文學持續地產生影響。馬克·多蘭認為“迷惘的一代”之所以能成為1920年代的文化象徵,不僅由於它是美國文化歷史上頗為少見的由一群作家代表一個時代的例子,還由於它是美國文化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由一群自傳作家代表一個時代的例子。
然而“迷惘的一代”的社會影響已經遠遠超出了文學範疇,在社會思想和文化領域都觸發了革命性的轟動,影響了青年一代的思想和行為方式。美國作家馬克·多蘭(Marc Doan)在《迷惘的一代的文化再解讀》中也說:“迷惘的一代”在美國歷史上已經成了一種藝術、“迷惘的一代”也成為美國歷史中的美國特性以及一種美國人格特徵。
菲茨傑拉德的小說也在精確記錄放浪形骸、夜夜狂歡的名士派和摩登女的同時,將這一生活方式更深更廣地推行到美國全社會,從而也導致了五十年代“
垮掉的一代 ”的出現。這種文化、文學運動在“迷惘的一代”文學風靡全美國的同時,還帶動起文藝百家和大眾生活方式上的現代主義潮流。可以說在“迷惘的一代”思想的影響下,再加上哈萊姆黑人文藝復興、
女權運動 和多種移民文化的興起,現代美國文化中斑駁絢麗、雅俗並舉的多元格局開始逐漸形成。
“垮掉的一代” 另外在當時美國社會中,受到“迷惘的一代”影響的還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像音樂、電影等都受到了很大衝擊。美國作家阿諾德·蕭恩(Arnold shaw)在他的著作《爵士樂時代:二十世紀的流行音樂》中說:“爵士樂反映了蕭條的經濟和紙醉金迷的人生。是一個時代的象徵。實際上代表了西方社會對於音樂價值的重新思考,打破了音樂只是為特定階級所擁有和享受的思想,以美國黑人的生活史為例,爵士樂反映了當時人們為了艱苦奮鬥和求生的強烈願望。
“迷惘的一代”對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社會的影響是如此之巨大、影響時間是如此之久,這種現象值得深思。在二十世紀上半期,“迷惘的一代”作家們的作品反映的是全面否定歷史傳統和道德原則、悲觀厭世的虛無主義觀點。當時的美國社會總體上是一個巨大的“悖論”,思想、道德、認識上和文化態度上充滿矛盾,人們眷戀傳統,又嚮往更加自由開放的未來。這20年的美國文壇是青年作家的天下,他們強硬的文化批判態度背後,隱藏著激進和保守、反叛與戀舊等對立的因素,表現出文化動盪期的迷惘和艱難求索。
 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海明威
歐內斯特·米勒爾·海明威海明威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傑拉德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菲茨傑拉德 約翰·多斯·帕索斯
約翰·多斯·帕索斯 格特魯德·斯坦因
格特魯德·斯坦因 南北戰爭
南北戰爭 伍德羅·威爾遜
伍德羅·威爾遜 凡爾賽條約後的德國領土形勢
凡爾賽條約後的德國領土形勢 赫伯特·胡佛
赫伯特·胡佛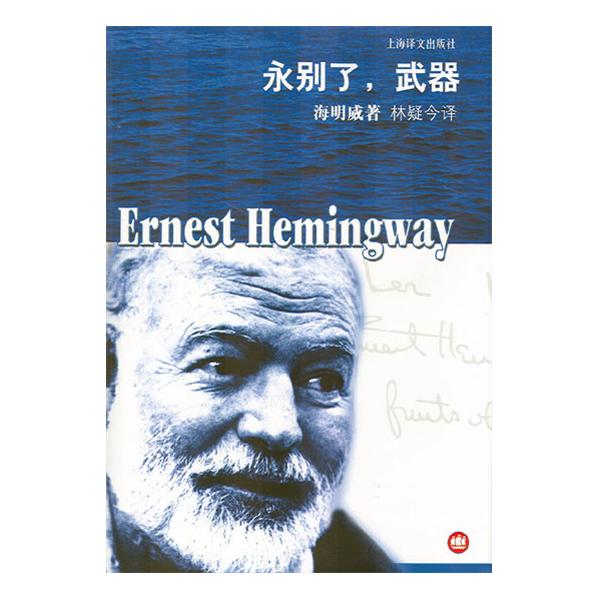 永別了,武器
永別了,武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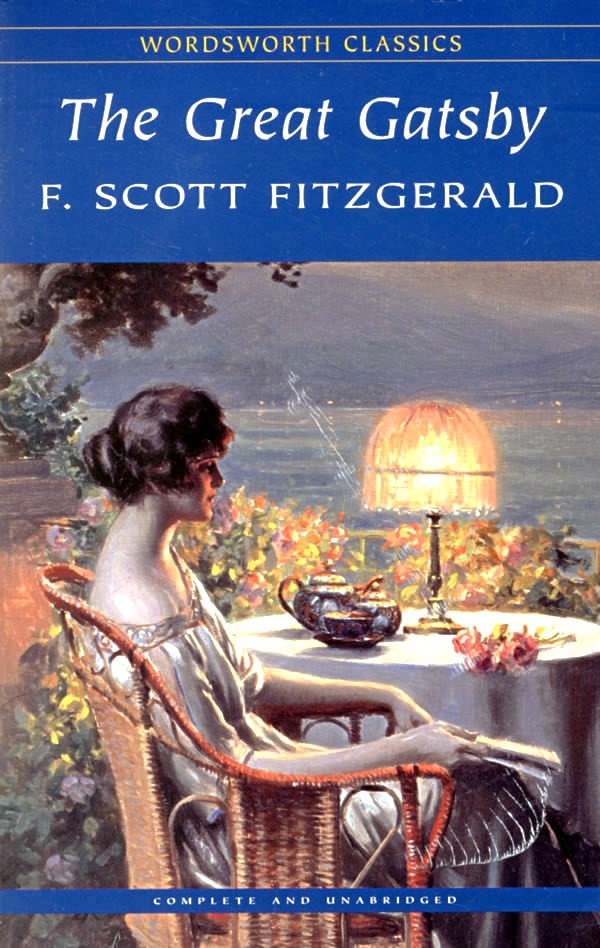 了不起的蓋茨比
了不起的蓋茨比 迷惘的一代在歐洲的據點——法國巴黎
迷惘的一代在歐洲的據點——法國巴黎 流放者的歸來
流放者的歸來 “垮掉的一代”
“垮掉的一代”
 馬爾科姆·考利
馬爾科姆·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