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所謂荒誕,也叫
怪誕,就是把不起眼的事物虛構到極點,使其完全脫離現實的一種方法,即從某種主觀感受出發來改變客觀事物的形態和屬性,直入現象的至深之處,揭示事物的本質。荒誕的
情節卻曲折地反映了當時人類存在的非理性表現。荒誕小說中的諷刺意味往往與苦澀的幽默結合在一起。通過不確定的時、空和人物來表現作品思想內容,將現實中的具體人物抽象化。現實存在的因素和非現實虛幻的因素交織於一起,用寫實的手法,來敘述非現實生活中的事件,雖然看起來非常假,卻開掘了主題的深度。
 荒誕小說作品封面
荒誕小說作品封面荒誕小說把荒誕放在日常生活之中,放在最平庸的環境裡,把它當作絲毫也沒有什麼可怪之處的東西加以表現。“在故作平淡無奇的日常形式中表達出反常的內容”,結果,使不受制於現實的事件,顯得“比虛構的世界還要虛構”。
荒誕小說給讀者很強的虛構感和可笑感,涵蓋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兩個方面,是內容和形式的有機統一。就思想而言,較為曲折地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將荒唐,人性異化看著特定歷史條件下人類社會不可避免的現象,賦予作品以濃厚的虛無主義和悲觀主義情調。就藝術而言,善於運用
怪誕和象徵的表現手法,特別是用富有表現力的手法去表現抽象的思想感情。
背景
談論人生的荒誕性,早就見諸古代西方戲劇。自古希臘悲劇開始,在
索福克勒斯、埃斯庫羅斯的劇作中就有對人類的
命運、人類的生存條件的殘酷與荒誕性表示關注的一面。20世紀的存在主義文學家、戲劇家
薩特和
加繆在他們的許多小說和劇本中,從理性出發,揭示了人的存在的荒誕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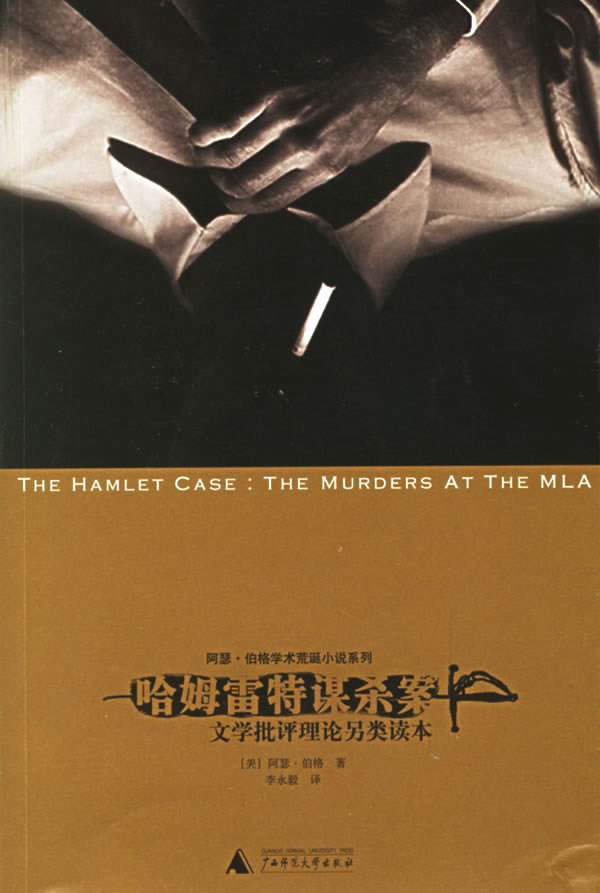 荒誕小說作品封面
荒誕小說作品封面舊的體制在近代史上發生深刻社會變革,在一股股革命浪潮的衝擊下東搖西晃,終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硝煙盡處徹底解體。資產階級共和製得到確立,但舊的矛盾還未盡數妥善解決,各種新的社會矛盾又層出不窮,這些新舊矛盾交織在一起構成了當時社會動盪不安的特點。在荒誕小說里出現的凌亂經常變換的時代背景,甚至乾脆“無時代背景”,以及複雜的社會秩序觀念,其實恰恰都是這樣的時代背景的觀照。
戰爭給整整一代人的心靈留下了難以治癒的創傷,上帝不復存在了,舊日的信仰坍塌了,美好的希望和理想破滅了。世界讓人
捉摸不透,社會令人心神不安。劫後餘生的人們,撫摸著戰爭的傷疤,開始了痛苦的反思,對傳統價值觀念和現存的秩序持否定的態度。往日的精神支柱瓦解了,新的信仰尚未找到,這種精神上的空虛反映到文學藝術上,自然形成了一個“沒有意義,荒誕,無用的主題”。
代表作家尤金.尤奈斯庫在他論述
卡夫卡的文章《在城市的武器》時指出:“荒誕是指缺乏意義,和宗教的,形上學的,先驗論的根源隔絕之後,人就不知所措,他的一切行為就變得沒有意義,荒誕而無用。”
在這動盪年代的各種矛盾中,在新舊觀念的搏擊中,在當時各種思潮的影響和啟發下,荒誕小說“以自己獨特的目光認識著這個異化的世界,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批判著這個充滿罪惡和醜陋的世界。這種認識和批判以及體現在作品中的惶恐、不安、迷惘,構成了荒誕小說創作基調。”(《卡夫卡短篇集譯序》)在荒誕小說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對人的歷史、人的本質、人的
命運、人的處境、人與人及人與社會的關係的思考,可以看到對人的前途的憂慮和不安。
荒誕小說
中國的荒誕小說並不與西方荒誕小說雷同是中國特定社會歷史環境的產物。當“
傷痕文學”、“
反思文學”主潮過去之後,荒誕小說逐漸為人們所重視。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以荒誕的手法揭示社會生活(特別是“文革”及其後遺症)的荒誕,能夠達到某種藝術的深刻,使“
反思小說”發展到一個新的思想高度。其次,在對十年動亂痛定思痛的個性解放思潮中,在西方荒誕派藝術的影響下,中國作家也以荒誕小說的形式思考人本存在的荒誕問題。其三,隨著
中國改革開放和都市文明的迅速發展,新一代中國作家也以荒誕小說反映現代人與社會的種種矛盾、荒誕的存在狀況。另外,在
魔幻現實主義的直接影響下,中國一些作家還以魔幻現實主義的手法反映地域性的、原始思維中的荒誕文化意識。
 荒誕小說作品封面
荒誕小說作品封面從內容與形式的關係著眼,中國荒誕小說的荒誕手法也可以看出有以下幾種形態。一是以現實主義的手法,寫現實中的荒誕之事,其內容(人和事)本身是荒誕的。二是描寫出現實中沒有的
怪誕事物,其內容本身是虛擬的荒誕。三是在基本寫實的內容中,包含有局部荒誕的處理,其形式含有荒誕因素。還有部分作品以荒誕的手法寫荒誕之事,內容與形式的荒誕融為一體。
從總體來看,當代中國荒誕小說對荒誕現實的揭示,往往蘊涵著某種批判現實的精神,體現著中國作家以荒誕藝術的方式對社會現實的反思。在藝術構成上,則較多地受到意識流方法的滲透。
荒誕小說只是中國當代許多作家文學實驗的一個方面,並沒有一批作家把荒誕小說作為自己主要的創作藝術。
作品
《局外人》
《局外人》運用大量描白式的簡單語言,平淡敘述,比如母死下葬、結交女友並可以隨時結婚、殺人、被判死刑。這是對任何人生來說都是重大起伏的事件,在主人公莫而索那裡卻一直無動於衷直,對世界採取既不反抗也不順從的態度。到最後才道出即便是這樣,生活仍然是幸福的。為什麼?
幸福在這裡是什麼?想要理解這種幸福並非普通生活哲理和邏輯可以解決。這是面對荒誕世界的荒誕的態度,因為莫而索對這個世界和宇宙沒有希望,正如這個世界和宇宙對他不抱希望一樣。沒有什麼過去和將來,事情就是這樣存在的。從開篇那句“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到最後“我現在仍然是幸福的,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喊叫聲。”從一個會叫母親為“媽媽”的孩子到”一個懷著殺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親”的罪人,整個過程無聲無息,我們甚至不知道也不需要這位隸屬荒誕的人在想些什麼。只是對於一點莫而索連同
加繆的態度是執著的,那就是不敬神。早於加繆之前,
尼采已經宣稱:上帝已死。被驚嚇的人們開始在無聊的無動於衷的日常生活中意識到那不一樣的東西。也就是作為已經失去信仰失去彼岸家園的時代,而又必須面臨生存的人應該如何?《
局外人》不過是加繆荒誕主題的開場白。至少在這裡我們明白了一點:直到最後,我們仍然無須將希望寄託與來世。我們仍然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面對荒謬的人。或許單憑這一點,我們至少是幸福的。
 荒誕小說作品封面
荒誕小說作品封面“真正的哲學問題是自殺。決定是否值得活是首要問題。”這是
加繆的疑問,人生之荒誕,難道非要世人或抱希望或用自殺來逃避?荒誕是否操縱死亡?自殺難道是荒誕產生之後的邏輯結論?如果加繆的荒誕哲學止於此,那么之能落入某種柔軟的傷感情緒之流。加繆說:我所感興趣的不是發現荒誕,而是是荒誕產生的何結果。
《鼠疫》
《鼠疫》是一部寓言體的小說。它是一篇有關
法西斯的寓言。當時處於法西斯專制強權統治下的法國人民———除了一部分從事抵抗運動者外———就像
歐洲中世紀鼠疫流行期間一樣,長期過著與外界隔絕的囚禁生活;他們在“鼠疫”城中,不但隨時面臨死神的威脅,而且日夜忍受著生離死別痛苦不堪的折磨。
加繆繼續他的存在主義主題:世界是荒謬的,現實本身是不可認識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加繆自己曾這樣說:“《
局外人》寫的是人在荒謬的世界中孤立無援,身不由己;《
鼠疫》寫的是面臨同樣的荒唐的生存時,儘管每個人的觀點不同,但從深處看來,卻有等同的地方。”
《變形記》
《變形記》作為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奠基之作,也是
卡夫卡也被公認為現代派的鼻祖的重要作品之一,對後來的現代主義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可以說二戰後的歐洲興起的“荒誕派戲劇”、法國的“新小說”和美國的“
黑色幽默”小說都受到了卡夫卡的啟發。
在《變形記》中,主人公格里高爾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大
甲蟲”,頓感驚慌失措,而在被父親發現後,家人更加是惶恐不已,還把他趕回臥室。在臥室里,格里高爾又渴又餓,逐漸陷入絕望之中,並且在這絕望格里高爾死去。
《變形記》這個故事表面看來
荒誕不經,實則蘊涵了豐富而深刻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它真實地表現了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裡人的異化。在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人被“物”(例如金錢,機器,產品,生產方式等)所驅使,所脅迫,所統治而不能自主,成為“物‘的奴隸,進而失去人的本性,變為非人.《變形記》主人公里高爾的故事正是人異化為非人這一哲學生存現狀。
 卡夫卡小說《變形記》封面
卡夫卡小說《變形記》封面其次,作品還表現了在現代社會裡人的一種生存恐懼,人變
甲蟲,在這裡象徵著莫明其妙的巨大災難的降臨,這種人不能掌握自己
命運的感覺表現了現代西方人的某種精神狀態,尤其是進入20世紀以後,兩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周期性的經濟危機,超級大國的軍備競賽,
核戰爭的威脅,環境污染和自然界生態平衡的破壞,這一切使人們對未來的命運處於一種不可知的
恐懼狀態之中。《變形記》中格里高爾的命運正反映了這種精神狀態本質的東西。
再次,《變形記》還表現了現代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冷漠關係,小說詳細的描寫了家人對他從關心到厭惡到必欲置其於死地的過程,這一過程實際上是希望他恢復賺錢的能力到徹底絕望的過程。這是一個為家庭奉獻了一切,卻由於失去了原有的價值而被家庭拋棄的小人物的悲劇,這類悲劇在人情冷漠的現代社會裡並不罕見。
化奇異為平凡,把最令人難以置信的,無法解釋的事件安置在最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環境中、讓荒謬悖理與合情入理、虛幻與現實這兩類對立的因素結合成為一個整體,展現出一幅神秘的、魔幻的、夢魘般的非現實的、好像又是現實中處處可以見到的畫圖,這就是《變形記》的根本的藝術特色,也即是“
卡夫卡式”特色的核心。
《城堡》
《城堡》是一部最絕望的小說。
卡夫卡的世界充滿了如此沉重的黑暗,閱讀已經喪失了最初的快樂。卡夫卡也許相信,人的存在也許是宇宙中最不可理喻的事件。我們試圖把握生命的意義,正如K徒勞地試圖走進城堡。當我們為人生的種種理想奮鬥時,我們不過正在異化的歧途越走越遠。卡夫卡有許多作品都未完成,我想,也許連作者自己都無力承擔這樣沉重的絕望了吧。
 卡夫卡小說《城堡》封面
卡夫卡小說《城堡》封面意義誕生於荒謬,這似乎就是
卡夫卡的秘密。正如他所欣賞的中國道家常說的,無中生有。他把這個可怕的秘密深深藏在城堡之中。K的出現很難說是城堡官員們的錯誤,因為即使最有效最精確的官僚機構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差錯。畢竟這是一個人的世界。除非人變成一種完美的生物,否則人的世界注定是一座不完美的世界。然而,對於K自己而言,生命卻因為這樣一個小小的偶然差錯發生了徹底改變。於是,他在城堡這座世界中的存在意義一下消失了。就在此刻,他墜入了荒誕之中。然後荒誕的對話,荒誕的人物和荒誕的感情相繼出現。K徒勞地掙扎著,仿佛撞上蛛網的小蟲,最終卻越陷越深。
K最初努力扮演一個土地
測量員的角色,但是他對自己身份的自我定位卻遭到了人們的漠視。為了獲得社會認同,他必須獲得城堡的肯定和任命。此時,
巍然聳立的城堡便以一種巨大而無形的權力之手牢牢抓住了K。其實城堡也許根本
子虛烏有,然而這已經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城堡象上帝一樣以一種神秘的權力賦予世界以意義。但是在上帝的崇高形象中體現出來的人類的敬畏和讚美,卻被在城堡的神秘形象中體現出來的人們的恐懼和諂媚所代替。人格化的上帝被非人格化的城堡所代替。
上帝死了,然而人類並未如某些人所歌頌的那樣獲得普羅米修斯式的解放。
在一個
荒謬的世界尋找一個人存在的意義,卻發現存在的意義竟誕生於荒謬之中。這似乎就是存在的最大悲劇。
其他
短篇小說《飢餓藝術家》描述了經理把絕食表演者關在鐵籠內進行表演,時間長達四十天。表演結束時,絕食者已經
骨瘦如柴,不能支持。後來他被一個馬戲團聘去,把關他的籠子放在離獸場很近的道口,為的是遊客去看野獸時能順便看到他。可是人們忘了更換記日牌,絕食者無限期地絕食下去,終於餓死。這裡的飢餓藝術家實際上已經異化為動物了。
 卡夫卡小說《鄉村醫生》封面
卡夫卡小說《鄉村醫生》封面另外一些小說是揭示現實世界的荒誕與非理性的,如《判決》和名篇《鄉村醫生》,這裡,現實和非現實的因素交織,透過這些荒誕的細節和神秘的迷霧,這裡寓意著:人類患了十分嚴重的病,已經使肌體無可救藥。人類社會的一些病症是醫生醫治不了的,這裡的醫生最後也變成了流浪者。
 荒誕小說作品封面
荒誕小說作品封面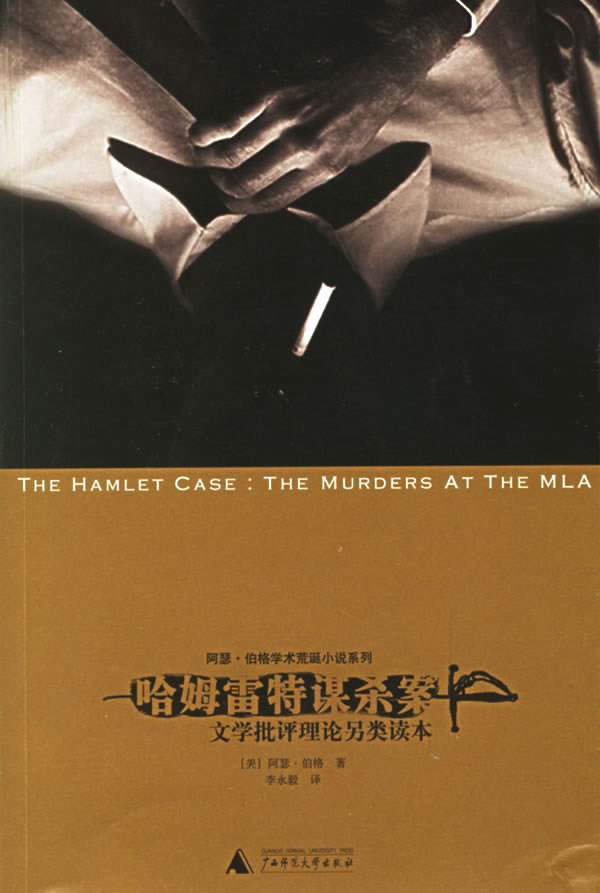 荒誕小說作品封面
荒誕小說作品封面 荒誕小說作品封面
荒誕小說作品封面 荒誕小說作品封面
荒誕小說作品封面 卡夫卡小說《變形記》封面
卡夫卡小說《變形記》封面 卡夫卡小說《城堡》封面
卡夫卡小說《城堡》封面 卡夫卡小說《鄉村醫生》封面
卡夫卡小說《鄉村醫生》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