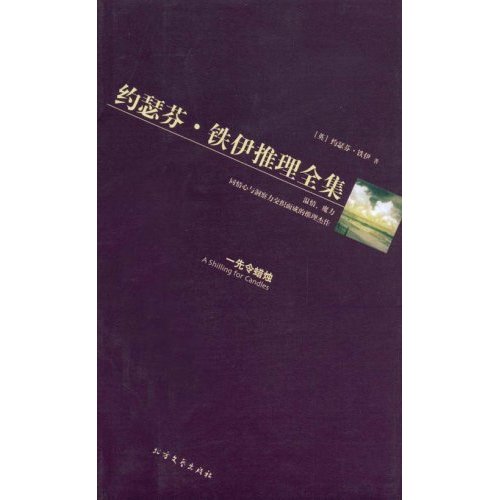《約瑟芬·鐵伊推理全集5:一先令蠟燭》講述了:清晨的海灘上橫陳著一具女人的屍體,死者染髮、腳趾甲上搽著猩紅色的指甲油,看上去就和一般人不一樣。海岸巡警說這只是一起因游泳不慎發生的意外,直到發現一顆紐扣糾結纏繞在她的頭髮中,又辨明她的身份是全英國最當紅的明星克莉斯丁·克雷。這下子,幾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和她的死亡脫不了干係。蘇格蘭場的格蘭特探長從死者生前錯綜複雜的交友關係和陳屍現場的線索中抽絲剝繭,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掙扎、迷誤,憑藉勇氣、智慧、同情與機緣,逐步揭開案情的真相。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約瑟芬•鐵伊推理全集5:一先令蠟燭
- 譯者:黃正綱
- 出版日期:2007年4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31721236
- 作者:約瑟芬·鐵伊
- 出版社:北方文藝出版社
- 頁數:224頁
- 開本:32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20世紀30年代以來,推理史最輝煌的第二黃金期三大女傑之一,也是其中最特立獨行的一位,窮盡一生之力只寫了八部推理小說——約瑟芬·鐵伊的小說,不只是情節的曲折和破案結局的震撼而已,就像張愛玲,你不會只關心故事和書中人物的結局一樣。《約瑟芬·鐵伊推理全集5:一先令蠟燭》是八部小說的其中之一,全英國最當紅的明星克莉斯丁·克雷橫屍海灘,故事由此開始……其中的案情由溫情、魔力、同情心與同洞察力交織而成,使《約瑟芬·鐵伊推理全集5:一先令蠟燭》成為一本推理傑作。
作者簡介
作者:(英國)約瑟芬·鐵伊 譯者:黃正綱
約瑟芬·鐵伊 Josephine Tey(1897—1952) 1897年出生於蘇格蘭囿弗內斯,就讀於當地的皇家學院。之後,在伯明罕的安斯地物理訓練學院接受三年訓練,然後便開始物理訓練講師的生涯。後來,她辭去教馭照顧她住在洛克耐斯的父親,並開始寫作。 這位英籍女作家,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推理史最輝煌的第二黃金期三大女傑之一,也是其中最特立獨行的一位,和她齊名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蘿西·榭爾斯都是大產量,行銷驚人的作家,鐵伊卻窮盡一生之力只寫了八部推理小說,八部水準齊一的好小說……是推理史上極少數一生沒有任何失敗作品的大師。 約瑟芬·鐵伊1952年逝世子倫敦。
約瑟芬·鐵伊 Josephine Tey(1897—1952) 1897年出生於蘇格蘭囿弗內斯,就讀於當地的皇家學院。之後,在伯明罕的安斯地物理訓練學院接受三年訓練,然後便開始物理訓練講師的生涯。後來,她辭去教馭照顧她住在洛克耐斯的父親,並開始寫作。 這位英籍女作家,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推理史最輝煌的第二黃金期三大女傑之一,也是其中最特立獨行的一位,和她齊名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蘿西·榭爾斯都是大產量,行銷驚人的作家,鐵伊卻窮盡一生之力只寫了八部推理小說,八部水準齊一的好小說……是推理史上極少數一生沒有任何失敗作品的大師。 約瑟芬·鐵伊1952年逝世子倫敦。
圖書目錄
導讀 旅程的終點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文摘
一個夏天早晨,七點剛過,威廉?帕特凱瑞照例在崖頂的短草地上散步。他身旁二百英尺底下,寂靜地躺著波光閃閃的英法海峽,像一塊乳色的蛋白石。周遭的空氣清新,見不到鳥雀的蹤影。普照的陽光下,除了遠方海灘上偶爾傳來海鷗的嗚叫,沒有一絲聲音;除了帕特凱瑞渺小孤單的身形??結實、黝暗而強硬,不見一個人影。嫩草上閃耀著無數顆露珠,仿佛是來自造物主手中的一個新世界;不過,這當然不是帕特凱瑞的想法。對他而言,草上的露珠只是代表清早地面的水氣還未被太陽曬乾。這個事實在他的下意識中一閃即過,而他的意識則正在進行一項抉擇:肚子開始餓了,是要在峽谷就折回海岸巡邏站,還是要在這美妙的晨光中繼續走到西歐佛去買份早報,好提前兩個小時知道發生了什麼謀殺案沒有。當然你可能會說,既然有了收音機,早報的優勢已經不存在了。 不過這總是一個目標。不管戰時平時,人活著總得有個目標。你總不能大老遠走到西歐佛,只是看看海岸吧。腋下夾份報紙回去吃早餐,多少會讓人感覺好一點。對,也許該走到鎮上去。 他穿著黑色方頭靴的腳步稍稍加快,光亮的鞋面在太陽下一閃一閃。這是一雙保養得很不錯的靴子。你或許會以為,既然帕特凱瑞在生命的精華年代得服從命令把靴子擦得雪亮,那么為了彰顯自己的獨特,表現自己的性格,或者就是為了徹底擺脫無聊的紀律,他現在就該讓靴子上積點灰塵。不過沒有,帕特凱瑞這個傢伙還是擦亮他的靴子,因為他就喜歡這樣。或許他有某種程度的受虐傾向,所幸他沒讀過多少這方面的資料,所以不會感到困擾。至於表現性格的部分,如果你告訴他某些症狀,當然他會了解,只是不知道那些專有名詞。在服役時,大家稱之為“唱反調”。 一隻海鷗倏地從崖頂掠過,尖叫著俯衝而下,加入下面的同伴。鳥群發出駭人的鼓譟聲。帕特凱瑞走到崖邊,看看開始退潮的海浪究竟留下什麼讓它們大驚小怪的東西。 緩緩湧起的海浪泡沫形成的白線被一塊鮮綠的東西阻斷了。看來是一塊布;粗呢之類的東西。奇怪的是,顏色還保持得如此鮮明,明明被海水泡了那么??帕特凱瑞的藍眼珠突然睜大,身體不自然地僵直起來。接著方頭靴開始在厚厚的草上奔跑,噔、噔、噔,像急促的心跳一樣。峽谷在兩百碼外,但帕特凱瑞的速度比起徑賽選手來也不遑多讓。他跑下沿著白堊山壁鑿出的粗糙階梯,直喘著氣,怒氣在激動中湧出。這就是早餐前去泡冷水的後果! 神經病,幫幫忙吧! 還耽誤了別人的早餐呢。最好用薛佛急救法,除非肋骨斷了;不大像跌斷肋骨,也許只不過是昏過去吧。要大聲向患者保證會沒事。她手腳膚色和砂子是一樣的褐色,怪不得他剛才以為是一塊布。神經病,幫幫忙吧! 若不是非得游泳,誰願意在一大早去泡冷水? 過去他曾碰到過非游泳不可的情況,就在紅海的港口,加入一個登入小組去協助阿拉伯人。不過想不通怎么會有人想幫那些傢伙??那才是該游泳的時候。當你別無選擇時。柳橙汁配薄吐司也是如此。不夠營養。神經病,幫幫忙吧! 在這片海灘上行走實在不容易。腳底大顆的白色圓石不懷好意地滑溜,偶爾露面的小片沙灘約與海潮等高,軟得陷人。不過現在他總算來到漫天的海鷗群里,淹沒在它們激動的羽翼和尖銳的叫聲中。 現在已經不需要薛佛急救法了,別的急救法也派不上用場了。他只瞄了一眼就明白,這女孩已經沒救了。雖然帕特凱瑞曾經不帶感情地在紅海的浪潮中抬過屍體,現在卻感到一陣莫名的激動。在全世界都甦醒迎接燦爛的一天時,一個如此年輕的生命卻躺在這裡,真是完全錯誤。而且她一定還蠻漂亮的,頭髮好像染過,不過其他部分倒還好。 一陣波浪衝上她的腳又退去,戲耍般流過她深紅色的腳趾。雖然知道潮水下一分鐘就會退到好幾碼之外,帕特凱瑞還是把這堆毫無生氣的東西,往上拖了一點,免得再受海浪的輕侮。 接著他想到打電話。他環顧四周,看看這女孩下水之前是否留下什麼衣物。似乎什麼都沒有。或許她把原來的穿著放在漲潮線以下,所以被潮水帶走了。也可能她根本就不是在這裡下水的。無論如何,現在找不到可以覆蓋她身體的東西,於是帕特凱瑞轉身,又開始在沙灘上疾走了,他要回海岸巡邏站,距離最近的電話在那裡。 “沙灘上有屍體,”當他拿起話筒打給警察局時,一面告訴比爾?剛特。 比爾的舌頭在齒縫間咂了咂,把頭猛地向後一仰。這個動作簡捷有力地表現他對狀況的不耐,對有人會把自己淹死的不解,同時對料中了期待的最壞情況的沾沾自喜。“如果這些人真想自殺的話,”他的聲音聽不出任何情感:“幹嗎挑上我們? 南部海岸不是有很多海灘嗎? ” “不是自殺”,帕特凱瑞在講電話的空檔說道。 比爾不理會他的話。“就因為到南岸門票錢比這裡要貴一點! 你以為他們既然連命都不要了,應該不會這么斤斤計較,乾脆讓自己死得有格調一點。可是偏偏不! 他們要買最便宜的票,一個一個到我們門前! ” “比奇角那一帶也有很多,”公正不阿的帕特凱瑞氣喘吁吁地反駁。 “反正不是自殺。” “一定是自殺。你以為有那么多懸崖是做什麼的? 保衛英國嗎? 才不是。就是方便自殺。這已經是今年第四起了。等到要報所得稅的時候,還會有更多。” 他停住話頭,帕特凱瑞的話吸引了他的注意。 “一個女孩。呃,女人。身穿鮮綠色的浴衣。”( 帕特凱瑞屬於不知道什麼叫做游泳衣的那一代。) “就在峽谷南側,大約一百碼的地方。沒有,沒有人在那裡。我得趕緊來打電話。不過我馬上就回那邊去。好,我們在那邊碰頭。 啊,喂,隊長嗎? 是,不算一天的好開始,不過我們已經習慣了。不,一件游水意外而已。救護車? 對,幾乎可以開到峽谷。在西歐佛的主幹道剛過三英里的地方轉下小路,一直通到峽谷岸旁的樹林為止。好的,待會見。” “你怎么可以斷定只是一件游水意外? ”比爾問道。 “她穿著浴衣,你沒聽到嗎? ” “誰說不能穿著浴衣跳海自殺的。故意讓它看起來像意外。” “這種季節沒辦法跳海。你會掉在沙灘上。而且這樣做太明顯了。” “可能是走進海里慢慢淹死的。”比爾說道,他天生愛抬槓。 “是嗎? 可能是吃了太多薄荷糖中毒死的。”帕特凱瑞說,他在阿拉伯時也喜歡較真,但後來卻發現這在日常生活中頗為無聊。
序言
旅程的終點 好笑到一種地步的當代旅遊作家比爾·布萊森是一個喜歡英國的美國人,他出生於廣闊乏味的愛荷華,卻跑到英國去居住,去工作,並且去結婚。他娶了個英國護士為妻,並幾乎雙腳踏遍這個有著巨大歷史榮光但依他看仍只是個小島的王國。他說英國人有一種美國人所沒有的幽默特質,他稱之為“挖苦”——包括他買火車票時要求開立一張收據,賣票的老英把這兩樣丟給他冷冷地說:“車票免費,收據十八點五英鎊。” 如此說來就不意外了不是?約瑟芬·鐵伊當然不折不扣就是個這樣的英國人——在這本《一先令蠟燭》書中,一如她的其他作品證明了她就是個這樣的英國人。此類“收據十八點五英鎊”的流彈依舊俯拾可見。
比方說,當格蘭特探長要求把犯罪的推論弄得更厚實一點時,他所得到的回答是:“事實往往都是薄弱不堪的,不是嗎?” 比方說,在談到一個過度溺愛不成材兒子的貧窮軟弱婦人時,一位中學教師說的是:“很和藹的女人,但是缺乏堅毅的性格,怯懦的人往往會很固執。” 比方說,當一位擅長扒糞的野心勃勃記者,被證實他的一篇煽情報導純屬虛構時,他悶悶不爽想的是:“你總得為那些死氣沉沉的薪水階級提供情緒上的寄託,因為他們不是太累就是太笨,無法有自己的感受,如果你不能令他們血液凝結,至少也要讓他們痛快地哭個一兩場。” 比方說,在談到痛恨某個人時,書中的女明星跟她的服裝師說的是: “仇恨真的很耗體力,你說對不對?” 又比方說,當書中蘇格蘭場所鎖定的嫌犯跑掉之後,這時我們幾乎可以看到寫書的鐵伊自己眼睛登時亮了起來。她說,才不到24小時,幾乎全英格蘭和威爾斯的每個角落都有人見到該嫌犯,又過幾小時,就連蘇格蘭也傳來訊息,有人看到他在約克夏釣魚,有人看到他在亞伯利斯維特看電影,有人說他在林肯郡租房間且沒付錢就跑了,有人說他在盧斯托夫搭船,有人說他死在潘瑞斯的一處沼澤,有人說他醉倒在倫敦的小巷子裡。他在海斯、葛蘭森、盧斯、湯布里吉、多徹斯特、阿許佛、盧頓、愛斯伯瑞、列賽斯特、恰特罕、東格林斯塔,還在倫敦四家店買了帽子,也在史旺和艾德加買安全別針,又到阿吉爾街快餐吧吃蟹肉三明治,到海華斯的喜斯飯店吃麵包和乾酪。他在每個想像得到的地方,偷過各種想像得到的東西…… 尤其是最後這一長段,多年之後,我們可在符號學學者兼小說家安博托·艾可的名著《玫瑰的名字》書中看到類似的缺德話語:在談到歐洲各教堂各修院皆各自號稱珍藏著耶穌基督的各種聖物時,書中的英國(你看,又是英國)修士威廉說:“如果傳說全然屬實,那我們的主顯然不是被釘在兩片木頭上,而是被釘在一整片樹林子裡。” 兩種旅遊策略 既然都提到比爾·布萊森了,我看我們的話題就從這個好旅行的大鬍子順流而下罷。
布萊森的旅遊方式及其哲學,有一點深獲我心,那就是他不喜歡租車開車,城鄉之間的聯絡,他寧可選擇最好是火車其次是巴土,再用雙腳步行密密實實地把其間填滿,因此,他的行程總是一站一站的——這一站一站不是過夜休息的工具性目的,而是旅程的主體,以停駐、逗留、親近、凝視來完成。
因為旅遊並不是你真的一定要到哪裡去,而是你到那裡究竟想看到什麼想到什麼甚至吃到什麼買到什麼,否則目的地不過就是另一個地名而已,你尋求的是自身的真實感受,而不是只供拿來跟別人講“我去過哪裡哪裡”的空洞炫耀與征服。
像我一個也聲稱熱愛旅行的老朋友便不是如此布萊森式的,他的樂趣在於人生苦短,世界太大,因此得每回選不同的新地點並盡其可能在一定時間內“走到”最多的新地點。為此,他總在計畫一趟旅行時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在交通工具和旅店飯館上頭,最好是能串成一條效率的數學線。當然,他老兄也絕不放過每站必有的重要景點名勝建築(畢竟這也是“我到過哪裡哪裡”的標誌),但完全沒誇張,他總是專心一意直撲這些景點,若需要用到步行,他也可以頭也不抬一路埋首於手中的旅遊手冊或地圖之中,冷不防伸手憑空一指(頭仍不抬):“這就是1583年歷史的×××××…… ” 對於這種令我敬畏有加的旅行方式,我總是保留著高度的戒心,當他告訴你哪裡好玩哪裡有意思,我總是直接在心裡翻譯成“他是說他到過哪裡而我沒去過”。當他告訴你哪裡的哪家餐館哪一種食物好吃時,一樣是 “他吃過什麼而我沒吃過”。
兩種截然不同的旅遊方式,我想,似乎也是兩種不同的小說書寫及閱讀方式。
如野馬·如塵埃 就常識來看,小說通常會認真經營個好結尾,這是書寫者的有始有終,也是對閱讀者的禮貌——要不然作為觀眾的我們怎么知道何時該起身鼓掌或開汽水呢? 但結尾真的沒那么重要。這裡所說的沒那么重要,意思當然不是說就可以草草了賬胡亂結束,而是說其他部分也一樣重要——小說家庫尼格喜歡引述一位美國大學校長的雋永話語,是這位校長在畢業典禮上對即將離校而去的畢業生致辭,大意是:“我以為重要的話應該分四年講完,而不是等到最後一天才說。” 其實這是有正經理由的,因為小說不是哲學科學,它從來不擅長對單一的命題思考,並給出簡潔漂亮的答案,不管這個命題多崇高多要緊,也不管書寫者的用心多高貴多無私,在小說的漫長歷史之中不是沒有能人試過要如此馴服小說為己所用,但下場通常不是太好,比方說喬治·歐威爾的《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比方說寇特·庫尼格《第五號屠宰場》除外的其他小說,比方說我們台灣的社會主義導師陳映真,他們也許都是認真:高貴且有想像力和才華的人,但他們窮盡畢生之力就是馴服不了小說這匹野馬。
說小說是野馬一匹可能不是個太壞的比喻,比之哲學科學試圖在紛亂的現象中找尋簡潔、具延展解釋能力的秩序及其“原理”,小說毋寧是逆向行駛。米蘭·昆德拉說,小說總是告訴你“事情遠比你想像的要複雜” ,它懸浮於不確定之中,把看似簡單尋常的事弄複雜,提出韻問題永遠比回答的問題要多,弄亂的秩序也永遠比建構的秩序要多,這是小說反動的、顛覆的、流體的本質,它破壞著既成的確定知識,但它同時又是人類的知識最具試探能力及自由的強大斥候。
因此,要它乖乖指向一個單一命題並好好回答這個單一命題,的確是件為難的事——我個人曾讀過一位文學批評者質疑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說似有“控制過度”的問題,如此的批判意見對不對我們再說,但這樣的說法是內行人講的。
好長的謎語 推理小說走的卻是我那位老友的旅遊路線,它原是高度控制之下的小說,把絕大多數的力氣集中指向一個最終的結局,最終的解答。
我們不要說這是小說的墮落云云這么刺激性這么貴族意味的話,我個人寧可講,推理小說的開端本來就只是個遊戲,相當純粹的智力遊戲,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就是猜謎,“半畝方方一塊田,一塊一塊賣銅錢”(打豆腐);“半天一個碗,下雨下不滿”(打鳥巢)——謎語,要認真經營當然就是最後那一翻兩瞪眼的答案,理所當然。
只是,謎語通常很簡短,你能想像有謎面長達一二十萬字的謎語嗎?那不是會煩死猜謎的人? 是很煩,但遺憾的是,的確有這樣的長謎語存在,而且為數還頗驚人,這就是我們今天司空見慣的長篇推理小說。
這構成了推理小說極根本上的一個困難——差不多到鐵伊所在的第二黃金期,長篇推理勢所必然取代短篇成為主流,原本比方說福爾摩斯探案那種愉悅的、即興的、帶著智力戲諂的、甚至可在晚餐桌上即席引述來考考朋友讓他們吃不下飯的輕鬆趣味,逐漸消逝了,代之而起的是沉重的、極耗體力和記憶力的大迷宮,閱讀推理,開始由當下的驚喜傾斜向長時間的拼搏。
這是個太長的旅程了。
這么長的旅程,你愈來愈需要,而且得向參加行程的人保證,旅程的終點有一個壯麗無比、怎么辛苦流汗忍飢受苦都值得的奇景,比方說像《東方夜快車謀殺案》那樣,比方說像《童謠謀殺案》那樣。
但承諾往往不見得會兌現,就像中國良莠不齊的旅行社品質一般—— 如果你是個鐵桿兒推理閱讀者,參與過足夠多次的此類行程,那你一定上過足夠多的當,並也因此培養出某種近似直覺的判斷力,你往往在行程中途就油然心生不祥的預感:“完了完了,牛吹這么大,屆時收拾得了才有鬼。” 這裡,獨獨,或謙遜點說,幾乎獨獨鐵伊轉向了布萊森式的旅程,她不允諾給你一個沒有人居、也不適人居、僅供讚嘆的大冰原大峽谷大高山,她溫柔地帶你穿梭滿是人家的每一條曲徑巷弄,甚至讓你忘了,或至少不在意你們最終會到達哪裡。
日暮途窮·放聲大哭 旅程的終點是什麼呢? 曾經,在一個我們對地球尚稱陌生、人類散居如孤島的大旅行時代,那些“我要到達那裡”的人攜回了遠方的珍稀物品(儘管充滿著掠奪的罪惡 ),攜回了遠方的逸事訊息(儘管充滿了想像、謬誤和偏見),也攜回了他們自身充滿嚴酷試驗九死一生的驚奇故事(儘管僅供讚嘆不及其他),但他們起碼有地方可去,起碼還能帶回上述充滿爭議之物回來。
然而,旅程儘管太長,地球卻顯得太小了,你當然可以給已有的終點賦予新的難度(比方說無氧或不同路徑不同季節攻珠穆朗瑪峰或南極極點) ,但就連原初那一點點人文的意義也不復存在了,當然,它可能仍比造一個幾千尺長的法國麵包成為新的吉尼斯紀錄好些——我們可能得承認,有些事物是開發殆盡了,有些時代是不會再回頭了。
我對那種個人英雄式的冒險犯難失去戰場殊少同情,但對於那些真相信可以找到新啟示的人難免心生不忍。
列維·史特勞斯在反省自身的人類學志業,寫過這么一段話:“我會不會是唯一的除了一把灰燼以外什麼也沒帶回來的人呢?我會不會是替逃避主義根本不可能這件事實做見證的唯一聲音呢?像神話中的印第安人那樣,我走到地球允許我走的最遠處,當我抵達大地的盡頭時,我詢問那裡的人,看見那裡的動物和其他東西,所得到的卻是同樣的失望:‘他筆直站立著,痛苦的哭泣、祈禱、號叫,但還是聽不到什麼神秘的聲音。他睡覺的時候,也並沒有被帶往有各種神秘動物的廟堂里去。他已完全明白確定:沒有任何人會賦予他任何力量、權力……” 直到這一刻我抄寫這段文字的當下,仍會激動悲傷。
日暮途窮,放聲大哭,人類的諸多歷史好像一直在反覆著同樣的事。
比方說,當格蘭特探長要求把犯罪的推論弄得更厚實一點時,他所得到的回答是:“事實往往都是薄弱不堪的,不是嗎?” 比方說,在談到一個過度溺愛不成材兒子的貧窮軟弱婦人時,一位中學教師說的是:“很和藹的女人,但是缺乏堅毅的性格,怯懦的人往往會很固執。” 比方說,當一位擅長扒糞的野心勃勃記者,被證實他的一篇煽情報導純屬虛構時,他悶悶不爽想的是:“你總得為那些死氣沉沉的薪水階級提供情緒上的寄託,因為他們不是太累就是太笨,無法有自己的感受,如果你不能令他們血液凝結,至少也要讓他們痛快地哭個一兩場。” 比方說,在談到痛恨某個人時,書中的女明星跟她的服裝師說的是: “仇恨真的很耗體力,你說對不對?” 又比方說,當書中蘇格蘭場所鎖定的嫌犯跑掉之後,這時我們幾乎可以看到寫書的鐵伊自己眼睛登時亮了起來。她說,才不到24小時,幾乎全英格蘭和威爾斯的每個角落都有人見到該嫌犯,又過幾小時,就連蘇格蘭也傳來訊息,有人看到他在約克夏釣魚,有人看到他在亞伯利斯維特看電影,有人說他在林肯郡租房間且沒付錢就跑了,有人說他在盧斯托夫搭船,有人說他死在潘瑞斯的一處沼澤,有人說他醉倒在倫敦的小巷子裡。他在海斯、葛蘭森、盧斯、湯布里吉、多徹斯特、阿許佛、盧頓、愛斯伯瑞、列賽斯特、恰特罕、東格林斯塔,還在倫敦四家店買了帽子,也在史旺和艾德加買安全別針,又到阿吉爾街快餐吧吃蟹肉三明治,到海華斯的喜斯飯店吃麵包和乾酪。他在每個想像得到的地方,偷過各種想像得到的東西…… 尤其是最後這一長段,多年之後,我們可在符號學學者兼小說家安博托·艾可的名著《玫瑰的名字》書中看到類似的缺德話語:在談到歐洲各教堂各修院皆各自號稱珍藏著耶穌基督的各種聖物時,書中的英國(你看,又是英國)修士威廉說:“如果傳說全然屬實,那我們的主顯然不是被釘在兩片木頭上,而是被釘在一整片樹林子裡。” 兩種旅遊策略 既然都提到比爾·布萊森了,我看我們的話題就從這個好旅行的大鬍子順流而下罷。
布萊森的旅遊方式及其哲學,有一點深獲我心,那就是他不喜歡租車開車,城鄉之間的聯絡,他寧可選擇最好是火車其次是巴土,再用雙腳步行密密實實地把其間填滿,因此,他的行程總是一站一站的——這一站一站不是過夜休息的工具性目的,而是旅程的主體,以停駐、逗留、親近、凝視來完成。
因為旅遊並不是你真的一定要到哪裡去,而是你到那裡究竟想看到什麼想到什麼甚至吃到什麼買到什麼,否則目的地不過就是另一個地名而已,你尋求的是自身的真實感受,而不是只供拿來跟別人講“我去過哪裡哪裡”的空洞炫耀與征服。
像我一個也聲稱熱愛旅行的老朋友便不是如此布萊森式的,他的樂趣在於人生苦短,世界太大,因此得每回選不同的新地點並盡其可能在一定時間內“走到”最多的新地點。為此,他總在計畫一趟旅行時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在交通工具和旅店飯館上頭,最好是能串成一條效率的數學線。當然,他老兄也絕不放過每站必有的重要景點名勝建築(畢竟這也是“我到過哪裡哪裡”的標誌),但完全沒誇張,他總是專心一意直撲這些景點,若需要用到步行,他也可以頭也不抬一路埋首於手中的旅遊手冊或地圖之中,冷不防伸手憑空一指(頭仍不抬):“這就是1583年歷史的×××××…… ” 對於這種令我敬畏有加的旅行方式,我總是保留著高度的戒心,當他告訴你哪裡好玩哪裡有意思,我總是直接在心裡翻譯成“他是說他到過哪裡而我沒去過”。當他告訴你哪裡的哪家餐館哪一種食物好吃時,一樣是 “他吃過什麼而我沒吃過”。
兩種截然不同的旅遊方式,我想,似乎也是兩種不同的小說書寫及閱讀方式。
如野馬·如塵埃 就常識來看,小說通常會認真經營個好結尾,這是書寫者的有始有終,也是對閱讀者的禮貌——要不然作為觀眾的我們怎么知道何時該起身鼓掌或開汽水呢? 但結尾真的沒那么重要。這裡所說的沒那么重要,意思當然不是說就可以草草了賬胡亂結束,而是說其他部分也一樣重要——小說家庫尼格喜歡引述一位美國大學校長的雋永話語,是這位校長在畢業典禮上對即將離校而去的畢業生致辭,大意是:“我以為重要的話應該分四年講完,而不是等到最後一天才說。” 其實這是有正經理由的,因為小說不是哲學科學,它從來不擅長對單一的命題思考,並給出簡潔漂亮的答案,不管這個命題多崇高多要緊,也不管書寫者的用心多高貴多無私,在小說的漫長歷史之中不是沒有能人試過要如此馴服小說為己所用,但下場通常不是太好,比方說喬治·歐威爾的《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比方說寇特·庫尼格《第五號屠宰場》除外的其他小說,比方說我們台灣的社會主義導師陳映真,他們也許都是認真:高貴且有想像力和才華的人,但他們窮盡畢生之力就是馴服不了小說這匹野馬。
說小說是野馬一匹可能不是個太壞的比喻,比之哲學科學試圖在紛亂的現象中找尋簡潔、具延展解釋能力的秩序及其“原理”,小說毋寧是逆向行駛。米蘭·昆德拉說,小說總是告訴你“事情遠比你想像的要複雜” ,它懸浮於不確定之中,把看似簡單尋常的事弄複雜,提出韻問題永遠比回答的問題要多,弄亂的秩序也永遠比建構的秩序要多,這是小說反動的、顛覆的、流體的本質,它破壞著既成的確定知識,但它同時又是人類的知識最具試探能力及自由的強大斥候。
因此,要它乖乖指向一個單一命題並好好回答這個單一命題,的確是件為難的事——我個人曾讀過一位文學批評者質疑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說似有“控制過度”的問題,如此的批判意見對不對我們再說,但這樣的說法是內行人講的。
好長的謎語 推理小說走的卻是我那位老友的旅遊路線,它原是高度控制之下的小說,把絕大多數的力氣集中指向一個最終的結局,最終的解答。
我們不要說這是小說的墮落云云這么刺激性這么貴族意味的話,我個人寧可講,推理小說的開端本來就只是個遊戲,相當純粹的智力遊戲,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就是猜謎,“半畝方方一塊田,一塊一塊賣銅錢”(打豆腐);“半天一個碗,下雨下不滿”(打鳥巢)——謎語,要認真經營當然就是最後那一翻兩瞪眼的答案,理所當然。
只是,謎語通常很簡短,你能想像有謎面長達一二十萬字的謎語嗎?那不是會煩死猜謎的人? 是很煩,但遺憾的是,的確有這樣的長謎語存在,而且為數還頗驚人,這就是我們今天司空見慣的長篇推理小說。
這構成了推理小說極根本上的一個困難——差不多到鐵伊所在的第二黃金期,長篇推理勢所必然取代短篇成為主流,原本比方說福爾摩斯探案那種愉悅的、即興的、帶著智力戲諂的、甚至可在晚餐桌上即席引述來考考朋友讓他們吃不下飯的輕鬆趣味,逐漸消逝了,代之而起的是沉重的、極耗體力和記憶力的大迷宮,閱讀推理,開始由當下的驚喜傾斜向長時間的拼搏。
這是個太長的旅程了。
這么長的旅程,你愈來愈需要,而且得向參加行程的人保證,旅程的終點有一個壯麗無比、怎么辛苦流汗忍飢受苦都值得的奇景,比方說像《東方夜快車謀殺案》那樣,比方說像《童謠謀殺案》那樣。
但承諾往往不見得會兌現,就像中國良莠不齊的旅行社品質一般—— 如果你是個鐵桿兒推理閱讀者,參與過足夠多次的此類行程,那你一定上過足夠多的當,並也因此培養出某種近似直覺的判斷力,你往往在行程中途就油然心生不祥的預感:“完了完了,牛吹這么大,屆時收拾得了才有鬼。” 這裡,獨獨,或謙遜點說,幾乎獨獨鐵伊轉向了布萊森式的旅程,她不允諾給你一個沒有人居、也不適人居、僅供讚嘆的大冰原大峽谷大高山,她溫柔地帶你穿梭滿是人家的每一條曲徑巷弄,甚至讓你忘了,或至少不在意你們最終會到達哪裡。
日暮途窮·放聲大哭 旅程的終點是什麼呢? 曾經,在一個我們對地球尚稱陌生、人類散居如孤島的大旅行時代,那些“我要到達那裡”的人攜回了遠方的珍稀物品(儘管充滿著掠奪的罪惡 ),攜回了遠方的逸事訊息(儘管充滿了想像、謬誤和偏見),也攜回了他們自身充滿嚴酷試驗九死一生的驚奇故事(儘管僅供讚嘆不及其他),但他們起碼有地方可去,起碼還能帶回上述充滿爭議之物回來。
然而,旅程儘管太長,地球卻顯得太小了,你當然可以給已有的終點賦予新的難度(比方說無氧或不同路徑不同季節攻珠穆朗瑪峰或南極極點) ,但就連原初那一點點人文的意義也不復存在了,當然,它可能仍比造一個幾千尺長的法國麵包成為新的吉尼斯紀錄好些——我們可能得承認,有些事物是開發殆盡了,有些時代是不會再回頭了。
我對那種個人英雄式的冒險犯難失去戰場殊少同情,但對於那些真相信可以找到新啟示的人難免心生不忍。
列維·史特勞斯在反省自身的人類學志業,寫過這么一段話:“我會不會是唯一的除了一把灰燼以外什麼也沒帶回來的人呢?我會不會是替逃避主義根本不可能這件事實做見證的唯一聲音呢?像神話中的印第安人那樣,我走到地球允許我走的最遠處,當我抵達大地的盡頭時,我詢問那裡的人,看見那裡的動物和其他東西,所得到的卻是同樣的失望:‘他筆直站立著,痛苦的哭泣、祈禱、號叫,但還是聽不到什麼神秘的聲音。他睡覺的時候,也並沒有被帶往有各種神秘動物的廟堂里去。他已完全明白確定:沒有任何人會賦予他任何力量、權力……” 直到這一刻我抄寫這段文字的當下,仍會激動悲傷。
日暮途窮,放聲大哭,人類的諸多歷史好像一直在反覆著同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