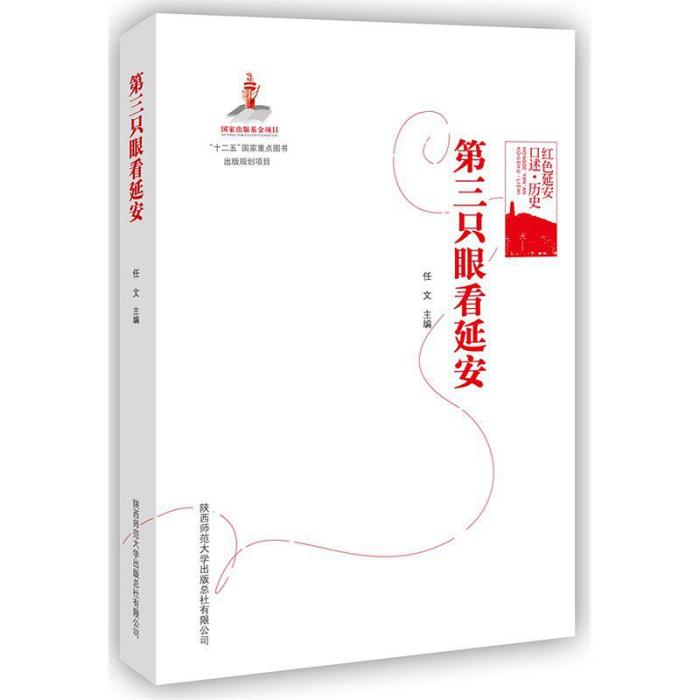內容簡介
《第三隻眼看延安》收錄了抗戰時期眾多中外人士訪問、參觀延安後所寫的
紀實性文章。全書再現了帶有正統觀念和西方文化背景的中外人士觀察、描述
延安的真實場景,提供了一個認識延安的嶄新視角,架起了中國“紅區”與“白區”、共產黨與西方國家相互了解的橋樑,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延安走向世界、世界了解延安的局面。
圖書目錄
抗戰期間外國人及民主人士對陝甘寧邊區的觀察(代前言)
民主人士、華僑領袖看延安
從上海到西安和陝北
訪問延安
參拜延安聖地
延安考察記
1942年延安參觀日記
延安標準化生活
延安歸來
外國記者、國際友人看延安
在紅色的堡壘中
—位德國女攝影家眼中的延安
進入紅色中國
新中國的胚胎
對陝北的印象
延安的政治
史實與考辨
幾位國民黨將領在陝甘寧邊區
延安是如何走向世界的
叢書信息
紅色延安口述·歷史 (共14冊), 這套叢書還有 《會師陝北》,《延安時期的大事件》,《抗戰中的延安》,《我要去延安》,《陝北鬧紅》等。
作品序言
抗戰期間外國人及民主人士
對陝甘寧邊區的觀察(代前言)
張玲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進行的一場全國全民性的戰爭。在此過程中,全國各族愛國人民、海外僑胞及全世界熱愛和平的人們都對這場反侵略戰爭的勝利做出過貢獻。而抗戰爆發後,陝甘寧邊區這塊西北的“禁地”,也開始和更大範圍的世界接觸,逐漸成為舉國矚目的焦點。但是不同的人對邊區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將邊區視為聖地,將其讚美為東方的自由樂土,還有一些人貶斥邊區是封建的割據勢力,把邊區批評得一無是處。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抗日戰爭重要力量的中國共產黨及中共最高領導層所在地陝甘寧邊區,抗戰期間在外國人、海外華人以及民主人士眼中是一個什麼樣子呢?觀察者眼中的中共領袖毛澤東
長征以來,中國共產黨逐漸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體系。到達延安後,這一體系得到了不斷的鞏固和加強,特別是1942年整風運動之後。毛澤東的權威地位就再也無人能撼動了。抗戰爆發後,正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延安的這些政治軍事人物領導了敵後的抗戰,而毛澤東也就成了外國人和民主人士觀察陝甘寧邊區的首選對象。
抗戰時期毛澤東在邊區內的權威是絕對的。他的畫像、題字掛在各個公眾場所,包括所有的工廠學校,而“回響毛主席的號召”也成為邊區幹部動員民眾的有力口號。“在工農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話是絕對的,保險的。”“他最善於綜合各種意見,而做一個大家認可的結論”,以至於趙超構在評述他時進一步說,“毛澤東是一個最能熟習中國歷史傳統的共產黨行動家!”雖然毛澤東已經獲得了這樣絕對權威的地位,但在這些觀察者眼中,此時的他卻並不是一個獨裁者,甚至在很多方面,他與普通人沒有什麼區別。在《延安一月》中,趙超構是這樣描述毛澤東的:“身材頎長,並不奇偉。一套毛呢制服,顯見已是陳舊的了。領扣是照例沒有扣的,一如他的照相畫像那樣露著襯衣。’而陳學昭是這樣描寫毛澤東的:“高高的個子,與遲緩的……笨重的腳步,使我們聯想起當年北平的李大釗先生。”
從穿著外貌上可以看出他作為共產黨人在生活作風上的簡樸,而從下面的描寫中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平易近人的一面:毛先生“不斷地讓茶讓煙,朋友似的和我們談話”@。“態度儒雅,音節清楚,詞令的安排恰當而有條理。” 趙超構還寫道:“我理解到毛先生是保有和我們一般人所共通的幽默與趣味的。他並不是那些一讀政治報告,便將趣味性靈加以貶斥的人物。”作為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也顯現出了他獨特的個人魅力,白修德在其回憶錄中對他是這樣評述的:“這個人最讓我著迷的不是他的相貌,而是他的風度所產生的力量。……他一講話,發出的聲音是乾脆的、柔和的,既不同於講台上的姿態,也沒有規勸的企圖。他對於我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他所說的都是實實在在的東西。他是個誨人不倦的聖人。當他走起路來時,一拖一拉的,輕鬆自如,有點像熊的步法。大多數時候他總是平靜地坐著,讓他的才智從那懶散的軀體中產生出來。”他還寫道:“好像在毛澤東的胸膛里藏著一本用希伯來秘密哲學符號寫成的歷史書,只有他才能把它譯解。他向同志們和領導人宣講這本書。告訴他們中國在走向何方,他怎樣把他們帶到那裡去,當他們到達那裡時必須做些什麼。沒有人對毛澤東提出過異議,他的精神力量是神聖的。……特別是他的意志,他個人的意志,和堅持不懈地要看到這意志的實施,在20世紀,也許除了列寧之外,是最令人生畏的了。”
在這些外來觀察者眼中,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顯然是有能力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抗戰的。事實上,毛澤東不但能夠把全黨思想統一到抗戰這一歷史性的任務上來,而且領導全黨和邊區人民把陝甘寧邊區建設成了一個政治作風民主、經濟有很大發展、軍民生活狀態緊張而有序的新型社會。陝甘寧邊區的思想政治作風
中國共產黨一直把思想政治工作作為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在敵後抗日中心的延安,思想政治工作同樣是至高無上的。“延安,置於其他一切事情之上的,是一座生產思想的工廠。也許只有羅馬的基督教革命或18世紀的法國和美國革命才把思想看得如此重要。也許在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過——如此有意識地察覺到,思想本身也像劇烈行動的發出者那樣具有強大的力量。”思想工作的重要性首先表現在根據地的功能上,“根據地”的作用不是人們通常想像的那樣,是一個往戰爭前線供應武器、後勤、給養和支持的安全之地。相對於提供武器、給養這些物質上的,延安的中共領導人更重視思想的作用, “延安根據地運往前線的物資等於零,所有的戰區都是自我維持。延安輸出的是人,即能夠傳播思想的幹部”。所以延安的主要功能是使這些幹部在根據地不斷地接受教育,使他們學會用新的方法思考問題,以利於更好地傳播他們的共產主義思想,也便於進一步團結各方力量投入抗日戰爭的事業當中。
雖然非常重視思想工作的作用,但中共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其政治空氣卻並不是通常人們想像的那樣令人窒息,在很大程度上還表現出比國民黨統治區更多的自由和民主。1940年5月,海外華人陳嘉庚一行到延安進行訪問。後來他在回顧這段經歷時說:“余久居南洋,對國內政府,雖屢有風聞而未知其事實究竟如何。時中共勢力尚微,且受片面宣傳,更難辨其黑白。……至延安視察經過,耳聞目睹各事實,見其勤勞誠樸,忠勇奉公,務以利民福國為前提,並實行民主化,在收復區諸鄉村,推廣實施,與民眾辛苦協作,同仇敵愾,奠勝利維新之基礎。”。“至政治方面,其領袖及一般公務員,勤儉誠樸,公忠耐苦,以身作則,紀律嚴明,秩序整然,優待學生,慎選黨員,民生安定。……喜慰莫可言喻,認為別有天地,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前憂慮建國未有其人,茲始覺悟其人乃素蒙惡名之共產黨人物。”從陳嘉庚的記述中,我們不但可以看到中共的政治作風得到了海外華人的認同,而且在未來的建國道路選擇上,以陳嘉庚為代表的海外華人在政治上也開始傾向於中國共產黨。1945年7月1目,黃炎培、褚輔成(慧僧)、冷通、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等6人從重慶飛抵延安,對延安進行了為期5天的訪問。黃炎培在訪問之後是這樣記述他的觀感的:“我們在延安,倒自自在在的。要到哪裡,看哪人,都絕對自由。你不需要帶路,你就自己去。……就所看到的,只覺得一切設施都切合乎一般的要求,而絕對不唱高調,求理論上好聽好看。……有人將懷疑中國共產黨在開倒車,然毛先生說:那些都是黨八股,萬要不得。……他主張有些書本知識的人,快回到實際工作里去。這都是中共三年來的新方針。至於執行的比較徹底,不馬虎,在延安幾天裡,隨處可以見到。”黃炎培在總結中共的政治作風時寫道:“我們應該知道中共政治作風已變了。不是變向別的,而是變向平凡。”反對黨八股是1942年整風運動以來中共在政治上實行的一項重要措施,這一方面統一了黨內的思想,另一方面也給黨內的民主創造了某種環境。邊區自由、務實的政治氛圍不但得到了海外華人和國內民主人士的讚揚,而且也得到了外國人的認同,自修德在其回憶錄中有這樣的描述:“在延安的那幾周,充滿了歡聲笑語,令人愜意。……友誼的酒杯觴觥交錯,朱德和周恩來可以不經報告,安步當車,像朋友那樣到美國觀察站走訪,一聊天就消磨幾個小時。……這是一段親善的時期——人們豁達開朗,熱情信任。……那時他們之間相互信任,渴望與我們交朋友卻是真實的。”可見,當時的延安是一種平等自由的政治氛圍,人們的心態也比較豁達,對友軍也抱以非常友好的態度。
在整個抗戰期間,雖然延安的中共非常重視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但是此時的邊區仍然保持一種自由、寬鬆的政治氛圍。通過緊抓思想工作,使軍民上下團結一致進行抗戰;創造寬鬆、良好的政治氛圍,也從另一個方面促使人們以更高的積極性投入抗戰中。邊區的經濟建設活動
陝甘寧邊區地處西北一隅,地理、氣候條件非常惡劣,制約著農業的發展。當地沒有現代化的工業基礎,與重慶相比,這裡也沒有廣大的經濟腹地。可以說整個陝甘寧邊區的經濟環境是相當差的。但是邊區人民並沒有坐以待斃,在中共的領導下,邊區的經濟建設搞得卻是有聲有色。
在農業建設上,邊區政府首先解決了土地問題。“蘇區時代已經分配的土地,現在仍舊維持現狀,而在公平的合理的融通辦法中,使原來地主也能夠滿足。”對土地所有權還未確定的土地,政府頒布了人民土地所有權條例加以解決,這樣就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地主與農民間因土地問題而產生的摩擦和鬥爭。在糧食生產方面,由於缺乏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機械,農民只能運用傳統的農具進行生產,但是更加注重了生產方式的改善,“多種雜糧(如麥子、燕麥、蔬菜等),開墾荒地,鼓勵春耕秋收”。同時注重了土地的施肥,改良土質。糧食生產量有了很大的增加,“勞動的經濟組織(如婦女與兒童的勞動合作社)也跟著普遍地發展起來了”。為了解決經濟田難,除了一般農民從事生產外,中國共產黨還指揮軍隊從事農業生產,最典型的就是三五九旅在南泥灣的墾荒。南泥灣本來是一片荒無人煙的地方,經過三五九旅官兵的開墾,變成了陝北的“江南”,所生產糧食不但可以實現自給,而且還能拿出很大一部分去支援兄弟部隊。另外,邊區政府還注重用生產運動的方式來發動人們進行農業生產。最有名的就是“吳滿有運動”。吳滿有是邊區的一個農民,他積極進行農業生產,被評為勞動英雄。邊區政府對吳滿有的英雄業績進行了大力的宣傳。號召軍民都向吳滿有學習,從而提高了邊區民眾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
邊區的農業生產雖然相當的落後,但是農民的負擔卻並不重。1938年,陳學昭就農民的負擔問題採訪了邊區財政廳廳長曹菊和,並記述了採訪的內容:“我問到關於農民的負擔,曹廳長這樣回答我:‘邊區的農民也沒有什麼負擔。土地問題,在這裡,地廣人稀,耕者有其田。去年,二十六年(1937年),冬天,我們發動救國公糧,這是邊區農民第一次的一點負擔,他們都自動地來繳,超過政府所希望的數目。原定的辦法是300斤以上的負擔百分之一,300斤以下的百分之一也不到……在他們是微乎其微,滿不在乎的。’”雖然農民的生計依然艱苦,但比起軍閥時代來,邊區民眾的生活是改善多了。“在延安,老百姓要生活,是這樣的容易,一天趕趕驢子也可賺好幾毛錢,因之這些本來非用氣力,辛辛苦苦才得謀一飽的,現在他們發現了新的路,兩個錢買進,六個錢賣出,只要經過這一番手續,錢就很容易地進來了。”
邊區經濟一個顯著的特點是除了公營經濟外,各家各戶以至於政府機關、學校都要進行生產活動,這也形成了邊區獨特的一種經濟形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手工業中的紡織業:“在邊區,無論走到哪裡,政府機關、學校、商店、農田、窯洞。到處都有粗糙的本制紡線機。幾乎是每一個人,高級的低級的,都把若干剩餘精力用在紡棉線或毛線上。”特別是大生產運動興起後,這種手工紡織業更加興盛。邊區從上到下,每個月有勞動能力的人都要制訂紡織計畫,然後根據計畫大力生產。當然這種計畫的制訂不是政府強制的,不過在那樣一種全民皆生產的氛圍中,每個人都自覺不自覺地投入到了這種緊張的生產活動中。總體而言,由於缺乏機械的供給,邊區的手工業生產是相當落後的,沒有大規模的工廠來生產人民必需的一些生活用品。但這種全民生產的運動也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邊區的經濟困難,特別是國民黨政府在相持階段逐漸把注意力從抗戰轉向對內反共之後,邊區的經濟陷入了極端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中共領導邊區軍民進行生產運動是必要的,其取得的效果也是積極而明顯的,邊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度過了那段最艱苦的歲月。
邊區經濟建設的發展還表現在商業、工礦業(如採煤、石油)、牲畜業、交通業等方面。而普通人民也逐步擺脫了貧窮的狀態,他們開始有了屬於自己的財產。黃炎培在訪問延安時有這樣的記述:“到處是新建築,我和御秋去訪問,‘你們這屋是自己築的嗎?’答:‘是。’‘有沒有公家貸款給你們或是補助你們?’答:‘沒有。’看各家的建築,各式各樣,可以證明這確是他們自己的建築。”
整個抗戰期間邊區的財政雖然很困難,但是在中共領導下,軍民上下卻以高度的熱情投入邊區的經濟建設運動中,在農、工、商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明顯成效,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邊區經濟困難,為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建設,為敵後抗戰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邊區軍民的生活狀態
抗戰的歲月是異常艱苦的,而邊區軍民的生活有緊張、單調的一面,也有輕鬆、多彩的一面。由於團結抗戰的需要,人們在許多方面顯示了高度的一致性。
抗戰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為了生產抗戰所需的各種物資,邊區人民過著一種忙碌而有序的生活。忙碌也被外來觀察者當作邊區生活的一大特徵:“忙,實在是延安生活的特徵。因為過於忙,空氣也似乎過於緊張。緊張的情緒還不止於生產忙,而在‘計畫’的嚴格,在機關學校部隊工廠工作的人,差不多每人都有一個計畫。……計畫的結果,就是一年到頭的緊張。”由於工作的緊張,人們正常的家庭生活也發生了改變:“延安的慣例,是夫婦分居的,他們流行叫做‘星期六制’,到星期六晚,丈夫接妻子,妻子接丈夫。所以這樣,聽說是為了工作的方便,使工作不至因夫婦的情感而浪費時間,或妨礙工作……”。忙碌的工作已經成為邊區人民生活的一種狀態,每個人,無論擔任哪一種工作,都為著抗戰而緊張地工作著。
邊區的生活也不全是緊張忙碌的工作,也有著輕鬆而自由的一面。雖然處於那樣一個精神生活貧乏的年代,但是邊區人民還是儘可能想出好的方式來活躍人們的精神生活:“在黨的大本營禮堂里舉行的周六之夜的舞會。幾把中國式的管弦樂器拉起來,腰鼓敲起來,口琴……就奏出悅耳的音樂,黨和軍隊的高級官員在地板上轉起了快活的舞步。……美國士兵們也離開了他們在山上的觀察崗位,應邀前來助興。”“活躍而自然的延安的氣氛和愉快熱烈而實幹的八路軍軍人,似乎把美國軍官和士兵都迷住了,他們極細緻地欣賞中共單純的毫不造作的對於客人的殷勤,在毫不拘泥形式的筵會上,著名的中國將領和他們的太太——穿著棉軍裝、不塗口紅、不講求社交儀式,但是快活而富於女性—一和美軍的青年尉官及士官坐在一起,他們對她們談他們美國的故鄉和家庭。馬廄似的禮堂里演的戲劇招引了成群的興高采烈的觀眾;特別是在那些農村氣味的星期六晚會上,人人都參加——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和八路軍總司令朱穗,大學和工廠的男女,八路軍的軍官和士兵,當然還有晚會必到的美國人也參加極度緊張的秧歌舞、華爾茲舞和狐步舞。他們想到重慶統治區里新生活運動的嚴禁跳舞和令人窒悶的死氣沉沉的情形時候就說:‘哎呀,這邊跟那邊多么不一樣呀!”這種活躍的氣氛給人們的精神帶來了愉悅,也使這些外來觀察者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整個抗戰期間,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陝甘寧邊區軍民通過艱苦的鬥爭,不斷地壯大起來,在抗戰即將勝利時,面對兩種前途和兩種命運的抉擇,國共雙方展開了一系列的爭奪。而在一些外來觀察者的眼中,國共關係曲走向卻早已經確定了。駐華武官謝偉思1944年10月在備忘錄里寫道:“共產黨已建立了既廣且深的民眾支持……除非國民黨在政治經濟的改革上和共黨有同樣的成就,並證明自己能爭取人民的領導地位……”而外交官台維斯也說:“蔣(介石)的封建的中國,不能長期與華北的一個現代化的、有活力和有人民擁護的政府並存。”“中國的命運不是蔣(介石)的命運……”而陳嘉庚更是在訪問延安之後斷言:“國民黨必敗,共產黨必勝。”通過這些外國人和民主人士對陝甘寧邊區的觀察,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不但有能力領導抗日戰爭,而且在此過程中還不斷地壯大,並為奪取全國政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本文選自《山東省青年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內容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