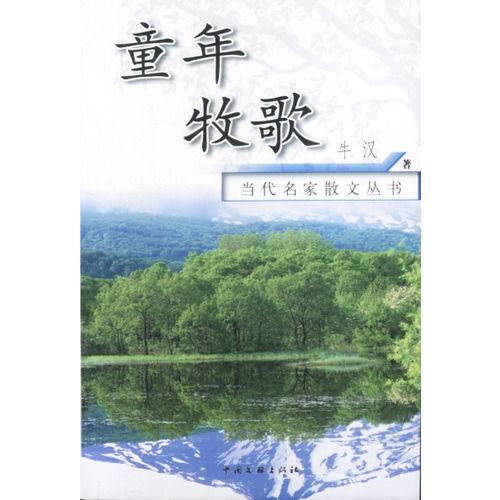基本介紹
- 書名:童年牧歌
- 作者:牛漢
- 原版名稱:童年牧歌
- ISBN:9787505928152
- 類別:文學
- 頁數:232
- 定價:14.9
- 出版社:中國文聯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3年3月
- 裝幀:平裝
- 開本:16開
作者簡介,目錄,前言,精彩書摘,
作者簡介
牛漢,原名史成漢,山西省定襄縣人,蒙古族,中共黨員。。1923年10月出生在一個有文化的傳統農民家庭,抗日戰爭初期流亡到陝甘地區讀中學,大學。1940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主要寫詩,近十年來同時寫散文。著有詩集《彩色生活》、《祖國》、《溫泉》、《蚯蚓和羽毛》、《牛漢抒情詩選》等十餘本,散文集《童年牧歌》、《中華散文珍藏本·牛漢卷》等七本,詩話集《學詩手記》、《夢遊人說詩》2本。《悼念一棵楓樹》獲1981年-1982年文學創作獎,《溫泉》獲全國優秀新詩集獎,2003年獲馬其頓共和國文學節杖獎。
曾任《中國文學》執行副主編,《新文學史料》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四文學編輯室主任,編審。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中國作家協會名譽委員,中國詩歌協會副會長等職。
2008年出版口述自傳《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
目錄
序
一、綿綿土
綿綿土
我們村
灰小子
騾王爺
滹沱河和我
上學第一天和墨刺的梅花點
我的第一本書
送牢飯和公雞打鳴
我偷了孔夫子的心——追念死去的第一個朋友
餵養小雀兒
掏甜根苗
去摘金針菜的路上
羊群回村的時候
秧歌進村
掃霽人兒
陽婆和月明爺
南山
沙漠
二、最初的記憶
我的祖先和有關傳說
燈籠紅
祖母的呼喚
祖母的憂傷
接羔
母親的第一次人生經歷
最初的記憶
一斗綠豆
打棗的季節
早熟的棗子
塑造夢的泥土
心靈的呼吸
月夜和風箏
海琴
父親,樹林和鳥
少年與螢火蟲——父親對我講的童話
三、活著的傷疤
寶大娘
黑娘·七寸人
禿手伯
活著的傷疤
小栽根兒和我
窠八哥的謎
貧窮
小張老師
四、迷人的轉蓬
我的腳與砍山鞋
買年畫出醜記
呼喚甘霖
活吞小魚仔的悲劇
吃螞蟻
玉米漿餅
柳芽,春的清香
苦香的,柳笛聲聲
第一次繪畫創作
迷人的轉蓬
船的出發
石獅子的故事
生命的探索(詩六首)
高粱情
離別故鄉
一、綿綿土
綿綿土
我們村
灰小子
騾王爺
滹沱河和我
上學第一天和墨刺的梅花點
我的第一本書
送牢飯和公雞打鳴
我偷了孔夫子的心——追念死去的第一個朋友
餵養小雀兒
掏甜根苗
去摘金針菜的路上
羊群回村的時候
秧歌進村
掃霽人兒
陽婆和月明爺
南山
沙漠
二、最初的記憶
我的祖先和有關傳說
燈籠紅
祖母的呼喚
祖母的憂傷
接羔
母親的第一次人生經歷
最初的記憶
一斗綠豆
打棗的季節
早熟的棗子
塑造夢的泥土
心靈的呼吸
月夜和風箏
海琴
父親,樹林和鳥
少年與螢火蟲——父親對我講的童話
三、活著的傷疤
寶大娘
黑娘·七寸人
禿手伯
活著的傷疤
小栽根兒和我
窠八哥的謎
貧窮
小張老師
四、迷人的轉蓬
我的腳與砍山鞋
買年畫出醜記
呼喚甘霖
活吞小魚仔的悲劇
吃螞蟻
玉米漿餅
柳芽,春的清香
苦香的,柳笛聲聲
第一次繪畫創作
迷人的轉蓬
船的出發
石獅子的故事
生命的探索(詩六首)
高粱情
離別故鄉
前言
序
第一次為自己的作品集寫序。我最怕寫序,因為必須得回顧和交代,還得寫出點什麼感悟。但是,既然是“自序”,自己就能作主,不必有什麼顧慮,可以自言自語地說說這幾年寫童年的心靈活動和創作體驗;儘管寫不成完整的文章,卻都是些未經修飾的真實的話語。
最近讀到一篇文章,題目是《的新境界》。《螢火集》是我前年出版的一本散文。作者說我的寫童年的散文是躁動的,還說:“躁動,是孕育中的節律”。措詞不多,卻摸到了我的躁動的脈患,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舞。我的血脈是外露的,因為總在躁對,不難摸到,一眼就看到了一蹦一跳隆起的血管,不像有些城府深的血脈,似無浪的深水那么奧秘,我讚嘆不已,卻難以改變自己的血性。也有論者說我這些年的創作是“冒傻氣”,不識時務。說得都不錯。總之,給人們的印象,我不是那種安生的默什麼,比起青壯年時幾年,蟄伏於斗室,里,不就是證實了這。其實,我絕對不想冒犯已經夠穩重平實的了。這文字,迷戀在童年的世界寫了多半輩子的詩,不甘熄滅的肝火一時還平抑不下來,因此。寫一些小蟲小鳥小花的散文,也偶爾禁不住冒出點什麼。常常有這樣的情況,本來寫的是散散的文字,寫著寫著卻寫成了詩,把散文跟詩本來有的一點虛點般的界限全忘在了腦後,而且寫得還格外地痛快。海德格爾說“詩的對立面並非散文,純粹的散文如同任何詩歌一樣是詩意的。”我深有體會。
這幾年,我不是返回童年世界,而是創造了一個童年世界。
這詩意的世界,並非遠在生命的背後,是過去了的,是只能憑回憶才可顯現出來的那些淡遠的景象。過去可未曾料到過竟會出現這個奇蹟;我的童年,居然還一直在成長,甚至在老年的生_命中成長著。我深深地感悟到,童年和童貞是生命天然的素質,它具有萌發生機的天性,永不衰老,堪稱是人類大詩的境界。
加西亞·馬爾克斯談到他創作《百年孤獨》的初衷時說:
“要為我童年時代所經受的全部體驗尋找一個完美無缺的文學歸宿。”他的夢想實現了。他的全部心血和眼淚,流啊流啊,一直流到了童年那裡,流到了母親身邊,流到了他的靈魂始終沒有離開過的一幢祖先們居住的古老而偌大的房子。他為童年尋找到了完美的歸宿。可是我這個人從來不讚賞歸宿這個境界,因為歸宿意味著到達和結局,永遠的停頓,生命不再成長。也許我的這個詩意的夢境是虛幻的,因而對我來說,生命、詩、散文,還有我分不清是什麼文體的文字,只能永遠地處在躁動之中,無始無終,得不到最後的平靜和安息。我的親人和友人說我這是自找苦吃,一個人不能死無葬身之地。他們希望我泅出苦海,即使不能上天堂,也該登上岸,走向天堂。我何嘗不願意活得歡快點甜美點呢!感謝童年和童年世界為我敞亮了一片心靈的世界,說它是天堂也未嘗不可。
有人說詩人“轉向”寫起散文是一種衰退現象,還說明詩的不可救藥。這是不懷好意的話。就我的情況來說,實際上,我這幾年並未放棄過詩,而且散文對我來說,同樣是一個詩意的世界,寫散文也有寫詩時的那種激情和躁動。有不少人問過我,為什麼我在九十年代以來執迷地寫起了散文?在《散文這個鬼》那篇文章里,已經訴述了我的種種心緒。對於寫散文這個人生課題,我的確也像寫詩一樣地極不安生。但是當我深深地進入(不是回返)了生氣蓬勃的童年世界,我真正獲得一種超脫和上升,與再生幾乎有著同等的重大意義,甚至有了進^“來生”的新鮮的生命體驗。這還不是詩的情境嗎?
這兩三年來,有幾位學者和評論家看了我寫童年的文字,誇獎我有良好的記憶。我對他們說,我的這些散文的形成,回憶固然十分地必需和重要,但如果沒有創造,而且是詩意的創造,我肯定寫不活童年的生命。回憶只能提供一些模糊的背景,而我的童年世界是在寫作過程中不斷地敞亮和拓展出來的。在《寶大娘》那篇顯得鬆散和冗長的散文中,我寫到了重新幻夢般地發現這個人的形象和心靈,以及她的命運的經過。但是我的所有童年的故事和人物卻絕對不是虛擬的,都是真實的寫照。他們既然是活的,當然也會與我一塊完成他們自己的一生和命運。
就在這個月的上半月(1996年5月),我的年近八旬的姐姐和卑過七旬的妹妹,先後從山西老家來看我,為我帶來了小時候愛吃的東西:莜麵和黃米糕。前年姐姐來時帶的是鮮嫩的玉米棒子。她們知道我拼著老命寫童年。我們一起回憶了難忘的童年,所有的親人在我們回憶里都活著,沒有一個死亡。半個多世紀的人世滄桑,我家的房院已經破落和消失得與遺址相差無幾了,只有一排正房經翻修後可以住人。我童年的幾十個朝步相處的夥伴,如今已凋零殆盡,只剩三五個了。土地一樣沉默的元貞還活著,住在祖傳的那幾間土屋裡。寶大娥已去世多年,妹妹說寶大娘的左臂雖不能彎曲,針線活卻樣樣都行。我幾乎把這個細節忘了。寶大娘的姿態頓時又活是活現,她納鞋時總是偏斜著上身。顯得出奇的靈巧。她右手臂上戴著銀手鐲,記得祖母說過;“銀手鐲在寶大娘手臂上才顯得明亮,一閃一閃,如眼白似的迷人,要是戴在別人的手臂上就像一個多餘的累贅來西。”可惜我寫寶大娘時沒有想到這些。
我寫了五、六十篇童年,覺得剛剛才寫開一個頭,只不過寫了人生的序幕而已。今後即使不再能寫多少,我的生命必將永遠地居住在童年的世界裡了。而只有活在童年的世界裡,才覺得生命又真正地萌動著不朽的生機。
啊,童年,啊,童年世界裡所有的親人和夥伴,還有我們的村子,那個貧窮而野性的我的誕生地,我永遠不會向你們告別的。我今生夸世感激你們對我的哺育和塑造。原諒我這個一生沒有脫掉過汗味、土味、牲口味、血腥味的遊子吧!我向你們垂下虔誠而沉重的頭領!
牛漢
1996年5月19日,於汗血齋。
第一次為自己的作品集寫序。我最怕寫序,因為必須得回顧和交代,還得寫出點什麼感悟。但是,既然是“自序”,自己就能作主,不必有什麼顧慮,可以自言自語地說說這幾年寫童年的心靈活動和創作體驗;儘管寫不成完整的文章,卻都是些未經修飾的真實的話語。
最近讀到一篇文章,題目是《的新境界》。《螢火集》是我前年出版的一本散文。作者說我的寫童年的散文是躁動的,還說:“躁動,是孕育中的節律”。措詞不多,卻摸到了我的躁動的脈患,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舞。我的血脈是外露的,因為總在躁對,不難摸到,一眼就看到了一蹦一跳隆起的血管,不像有些城府深的血脈,似無浪的深水那么奧秘,我讚嘆不已,卻難以改變自己的血性。也有論者說我這些年的創作是“冒傻氣”,不識時務。說得都不錯。總之,給人們的印象,我不是那種安生的默什麼,比起青壯年時幾年,蟄伏於斗室,里,不就是證實了這。其實,我絕對不想冒犯已經夠穩重平實的了。這文字,迷戀在童年的世界寫了多半輩子的詩,不甘熄滅的肝火一時還平抑不下來,因此。寫一些小蟲小鳥小花的散文,也偶爾禁不住冒出點什麼。常常有這樣的情況,本來寫的是散散的文字,寫著寫著卻寫成了詩,把散文跟詩本來有的一點虛點般的界限全忘在了腦後,而且寫得還格外地痛快。海德格爾說“詩的對立面並非散文,純粹的散文如同任何詩歌一樣是詩意的。”我深有體會。
這幾年,我不是返回童年世界,而是創造了一個童年世界。
這詩意的世界,並非遠在生命的背後,是過去了的,是只能憑回憶才可顯現出來的那些淡遠的景象。過去可未曾料到過竟會出現這個奇蹟;我的童年,居然還一直在成長,甚至在老年的生_命中成長著。我深深地感悟到,童年和童貞是生命天然的素質,它具有萌發生機的天性,永不衰老,堪稱是人類大詩的境界。
加西亞·馬爾克斯談到他創作《百年孤獨》的初衷時說:
“要為我童年時代所經受的全部體驗尋找一個完美無缺的文學歸宿。”他的夢想實現了。他的全部心血和眼淚,流啊流啊,一直流到了童年那裡,流到了母親身邊,流到了他的靈魂始終沒有離開過的一幢祖先們居住的古老而偌大的房子。他為童年尋找到了完美的歸宿。可是我這個人從來不讚賞歸宿這個境界,因為歸宿意味著到達和結局,永遠的停頓,生命不再成長。也許我的這個詩意的夢境是虛幻的,因而對我來說,生命、詩、散文,還有我分不清是什麼文體的文字,只能永遠地處在躁動之中,無始無終,得不到最後的平靜和安息。我的親人和友人說我這是自找苦吃,一個人不能死無葬身之地。他們希望我泅出苦海,即使不能上天堂,也該登上岸,走向天堂。我何嘗不願意活得歡快點甜美點呢!感謝童年和童年世界為我敞亮了一片心靈的世界,說它是天堂也未嘗不可。
有人說詩人“轉向”寫起散文是一種衰退現象,還說明詩的不可救藥。這是不懷好意的話。就我的情況來說,實際上,我這幾年並未放棄過詩,而且散文對我來說,同樣是一個詩意的世界,寫散文也有寫詩時的那種激情和躁動。有不少人問過我,為什麼我在九十年代以來執迷地寫起了散文?在《散文這個鬼》那篇文章里,已經訴述了我的種種心緒。對於寫散文這個人生課題,我的確也像寫詩一樣地極不安生。但是當我深深地進入(不是回返)了生氣蓬勃的童年世界,我真正獲得一種超脫和上升,與再生幾乎有著同等的重大意義,甚至有了進^“來生”的新鮮的生命體驗。這還不是詩的情境嗎?
這兩三年來,有幾位學者和評論家看了我寫童年的文字,誇獎我有良好的記憶。我對他們說,我的這些散文的形成,回憶固然十分地必需和重要,但如果沒有創造,而且是詩意的創造,我肯定寫不活童年的生命。回憶只能提供一些模糊的背景,而我的童年世界是在寫作過程中不斷地敞亮和拓展出來的。在《寶大娘》那篇顯得鬆散和冗長的散文中,我寫到了重新幻夢般地發現這個人的形象和心靈,以及她的命運的經過。但是我的所有童年的故事和人物卻絕對不是虛擬的,都是真實的寫照。他們既然是活的,當然也會與我一塊完成他們自己的一生和命運。
就在這個月的上半月(1996年5月),我的年近八旬的姐姐和卑過七旬的妹妹,先後從山西老家來看我,為我帶來了小時候愛吃的東西:莜麵和黃米糕。前年姐姐來時帶的是鮮嫩的玉米棒子。她們知道我拼著老命寫童年。我們一起回憶了難忘的童年,所有的親人在我們回憶里都活著,沒有一個死亡。半個多世紀的人世滄桑,我家的房院已經破落和消失得與遺址相差無幾了,只有一排正房經翻修後可以住人。我童年的幾十個朝步相處的夥伴,如今已凋零殆盡,只剩三五個了。土地一樣沉默的元貞還活著,住在祖傳的那幾間土屋裡。寶大娥已去世多年,妹妹說寶大娘的左臂雖不能彎曲,針線活卻樣樣都行。我幾乎把這個細節忘了。寶大娘的姿態頓時又活是活現,她納鞋時總是偏斜著上身。顯得出奇的靈巧。她右手臂上戴著銀手鐲,記得祖母說過;“銀手鐲在寶大娘手臂上才顯得明亮,一閃一閃,如眼白似的迷人,要是戴在別人的手臂上就像一個多餘的累贅來西。”可惜我寫寶大娘時沒有想到這些。
我寫了五、六十篇童年,覺得剛剛才寫開一個頭,只不過寫了人生的序幕而已。今後即使不再能寫多少,我的生命必將永遠地居住在童年的世界裡了。而只有活在童年的世界裡,才覺得生命又真正地萌動著不朽的生機。
啊,童年,啊,童年世界裡所有的親人和夥伴,還有我們的村子,那個貧窮而野性的我的誕生地,我永遠不會向你們告別的。我今生夸世感激你們對我的哺育和塑造。原諒我這個一生沒有脫掉過汗味、土味、牲口味、血腥味的遊子吧!我向你們垂下虔誠而沉重的頭領!
牛漢
1996年5月19日,於汗血齋。
精彩書摘
那是個不見落日和霞光的灰色的黃昏。天地灰得純淨,再沒有別的顏色。
踏上塔克拉瑪乾大沙漠,我恍惚回到了失落了多年的一個夢境。幾十年來,我從來不會忘記,我是誕生在沙土上的。人們準不信。可這是千真萬確的。我的第一首詩就是獻給從沒有看見過的沙漠。
年輕時,有幾年我在深深的隴山山溝里做著遙遠而甜蜜的沙漠夢,不要以為沙漠是蒼茫而乾澀的,年輕的夢都是甜的。由於我家族的歷史與故鄉走西口的人們有說不完的故事,我的心靈從小就像有著血緣關係似的嚮往沙漠,我覺得沙漠是世界上最悲壯最不可馴服的野地方。它空曠得沒有邊精,而我嚮往這種陌生的境界。
此刻,我真的踏上了沙漠,無邊無沿的沙漠,仿佛天也是沙的,雲也是沙的,連太陽都是沙的。全身心激盪著近乎重逢的狂喜。沒有模仿誰,我情不自禁地五體投地,伏在熱的沙漠上。我汗濕的前額和手心,沾了一層綿細的閃光的沙。
半個世紀以前,地處滹沱河上赫苦寒的故鄉,孩子都誕生在鋪著厚厚的綿綿土的炕上。我們那裡把極細柔的沙土叫做綿綿土。“綿綿”是我一生中覺得最溫柔的一個詞,辭典里查不到,即使查到也不是我說的意思。孩子必須誕生在綿綿土上的習俗是怎么形成的,祖祖輩輩的先人從沒有解釋過。甚至想都沒有想過。它是聖潔的領域,誰也不敢褻瀆。它是一個無法解釋的活神話。我的祖先們或許在想:人,不生在土裡沙里,還能生在哪裡?就像穀子是從土地里長出來一樣的不可懷疑。
因此,我從母體降落到人間的那一瞬間,首先接觸到的是沙土,沙土在熱炕上烘得暖呼呼的。我的潤濕的小小的身軀因沾滿金黃的沙土而閃著晶亮的光芒,就像成熟的谷穗似的。接生我的仙園姑姑那雙大而靈巧的手用綿綿土把我撫摸得乾乾淨淨,還湊到鼻子邊聞了又聞,“只有土能洗掉血氣。”她常常說這句話。
我們那裡的老人們都說,人間是玲的,出世的嬰兒當然要哭鬧,但一經觸到了與母體裡相似的溫暖的綿綿土,生命就像又回到了母體裡安生地睡去一般。我相信,老人們這些詩一樣美好的話,並沒有什麼神秘。
我長到五六歲光景,成天在土裡沙里廝混。有一天,祖母把我喊到身邊,小聲說:“限你兩天掃一罐綿綿土回來!”“做什麼用?”我真的不明白。
“這事不該你問。”祖母的眼神和聲音異常莊嚴,就像除夕夜裡迎神時那種虔誠的神情,“可不能掃粗的髒的。”她叮嚀我一定要掃聚在窗欞上的綿綿土,“那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淨土,別處的不要。”
我當然曉得。連麻雀都知道用窗欞上的綿綿土朴楞楞地清理它們的羽毛。
兩三天之後我母親生下了我的四弟。我看到他赤裸的身軀,紅潤潤的,是綿綿土擦洗成那么紅的。他的奶名就叫“紅漢”。
綿綿土是天上降下來的淨土。它是從遠遠的地方飄呀飛呀地落到我的故鄉的。現在我終於找到了綿綿土的發祥地。
我久久地伏在塔克拉瑪乾大沙漠的又厚又軟的沙上,百感交集,悠悠然夢到了我的家鄉,夢到了與母體一樣溫暖的我誕生在上面的綿綿土。
我相信故鄉現在還有綿綿土,但孩子們多半不會再降生在綿綿土上了。我祝福他們。我寫的是半個世紀前的事,它是一個遠古的夢。但是我這個有土性的人,忘不了對故鄉綿綿土的眷戀之情。原諒我這個痴愚的遊子吧!
踏上塔克拉瑪乾大沙漠,我恍惚回到了失落了多年的一個夢境。幾十年來,我從來不會忘記,我是誕生在沙土上的。人們準不信。可這是千真萬確的。我的第一首詩就是獻給從沒有看見過的沙漠。
年輕時,有幾年我在深深的隴山山溝里做著遙遠而甜蜜的沙漠夢,不要以為沙漠是蒼茫而乾澀的,年輕的夢都是甜的。由於我家族的歷史與故鄉走西口的人們有說不完的故事,我的心靈從小就像有著血緣關係似的嚮往沙漠,我覺得沙漠是世界上最悲壯最不可馴服的野地方。它空曠得沒有邊精,而我嚮往這種陌生的境界。
此刻,我真的踏上了沙漠,無邊無沿的沙漠,仿佛天也是沙的,雲也是沙的,連太陽都是沙的。全身心激盪著近乎重逢的狂喜。沒有模仿誰,我情不自禁地五體投地,伏在熱的沙漠上。我汗濕的前額和手心,沾了一層綿細的閃光的沙。
半個世紀以前,地處滹沱河上赫苦寒的故鄉,孩子都誕生在鋪著厚厚的綿綿土的炕上。我們那裡把極細柔的沙土叫做綿綿土。“綿綿”是我一生中覺得最溫柔的一個詞,辭典里查不到,即使查到也不是我說的意思。孩子必須誕生在綿綿土上的習俗是怎么形成的,祖祖輩輩的先人從沒有解釋過。甚至想都沒有想過。它是聖潔的領域,誰也不敢褻瀆。它是一個無法解釋的活神話。我的祖先們或許在想:人,不生在土裡沙里,還能生在哪裡?就像穀子是從土地里長出來一樣的不可懷疑。
因此,我從母體降落到人間的那一瞬間,首先接觸到的是沙土,沙土在熱炕上烘得暖呼呼的。我的潤濕的小小的身軀因沾滿金黃的沙土而閃著晶亮的光芒,就像成熟的谷穗似的。接生我的仙園姑姑那雙大而靈巧的手用綿綿土把我撫摸得乾乾淨淨,還湊到鼻子邊聞了又聞,“只有土能洗掉血氣。”她常常說這句話。
我們那裡的老人們都說,人間是玲的,出世的嬰兒當然要哭鬧,但一經觸到了與母體裡相似的溫暖的綿綿土,生命就像又回到了母體裡安生地睡去一般。我相信,老人們這些詩一樣美好的話,並沒有什麼神秘。
我長到五六歲光景,成天在土裡沙里廝混。有一天,祖母把我喊到身邊,小聲說:“限你兩天掃一罐綿綿土回來!”“做什麼用?”我真的不明白。
“這事不該你問。”祖母的眼神和聲音異常莊嚴,就像除夕夜裡迎神時那種虔誠的神情,“可不能掃粗的髒的。”她叮嚀我一定要掃聚在窗欞上的綿綿土,“那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淨土,別處的不要。”
我當然曉得。連麻雀都知道用窗欞上的綿綿土朴楞楞地清理它們的羽毛。
兩三天之後我母親生下了我的四弟。我看到他赤裸的身軀,紅潤潤的,是綿綿土擦洗成那么紅的。他的奶名就叫“紅漢”。
綿綿土是天上降下來的淨土。它是從遠遠的地方飄呀飛呀地落到我的故鄉的。現在我終於找到了綿綿土的發祥地。
我久久地伏在塔克拉瑪乾大沙漠的又厚又軟的沙上,百感交集,悠悠然夢到了我的家鄉,夢到了與母體一樣溫暖的我誕生在上面的綿綿土。
我相信故鄉現在還有綿綿土,但孩子們多半不會再降生在綿綿土上了。我祝福他們。我寫的是半個世紀前的事,它是一個遠古的夢。但是我這個有土性的人,忘不了對故鄉綿綿土的眷戀之情。原諒我這個痴愚的遊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