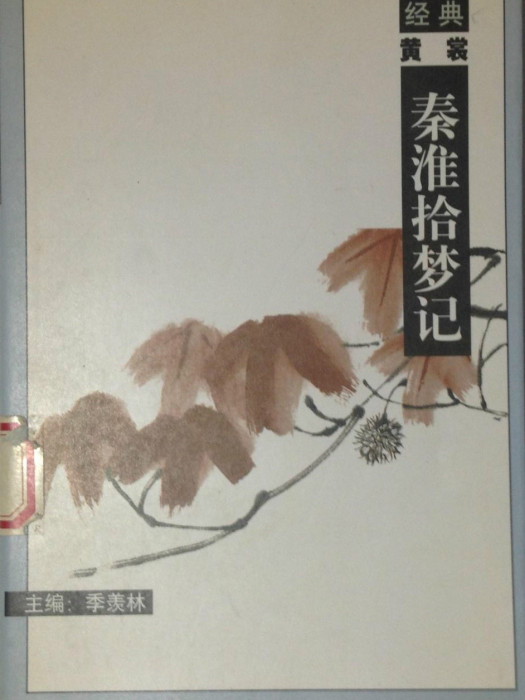作品原文
秦淮拾夢記
在住處安頓下來,主人留下一張南京地圖,囑咐我好好休息一下就離開了。遵命躺在床上,可是無論如何也睡不著。只好打開地圖來看,一面計畫著遊程。後來終於躺不住,索性走出去。
在珠江路口跳上電車,只一站就是新街口,這個鬧市中心對我來說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陌生的地方,新建的市樓吞沒了舊時僅有的幾幢“洋樓”。三十年前,按照我的記憶,這地方就像被敲掉了滿口牙齒的赤裸的牙床,只新裝了一兩顆“金牙”,此外就全是殘留著參差斷根的豁口。通往夫子廟的大路一眼望不到底,似乎可以一直看到秦淮河。
在地圖上很容易就找到了在附近的羊皮巷和戶部街。
三十三年以前,報社的辦事處就設在戶部街上。這真是一個可憐的辦事處,在十來畝大小的院落里,零落地放著許多大缸,原來這是一個醬園的作坊。前面有一排房子,辦事處借用了兩間斗室,睡覺、辦公、寫稿都在這裡。門口也沒有掛什麼招牌,在當時這倒不失為一種聰明的措置。
我就在這裡緊張而又悠閒地生活過一段日子,也並沒有什麼不滿足。特別是從《
白下瑣言》等書里發現,這裡曾經有過一座“小虹橋”,是南唐故宮遺址所在,什麼澄心堂、瑤光殿都在這附近時,就更產生了一種虛幻的滿足。這就是李後主曾經與大周后、小周后演出過多少戀愛悲喜劇的地方;也是他醉生夢死地寫下許多流傳至今的歌詞的地方;他後來被
樊若水所賣,被俘北去,倉皇辭廟、揮淚對宮娥之際,應當也曾在這座橋上走過。在我的記憶里,戶部街西面的洪武路,也就是盧妃巷的南面有一條小河,河上是一座橋,河身只剩下一潭深黑色的淤泥,橋身下半也已埋在土裡,橋背與街面幾乎已經拉平。這座可憐的橋不知是否就是當年“小虹橋”的遺蛻。
三十年前的舊夢依然保留著昔日的溫馨。這條小街曾經是很熱鬧的,每當華燈初上,街上就充滿了熙攘的人聲,還飄蕩著過往的黃包車清脆的鈴聲,小吃店裡的小籠包子正好開籠,鹹水鴨肥白的軀體就掛在案頭。一直到夜深,人聲也不會完全蕭寂。在夜半一點前後,工作結束放下電話時,還能聽到街上叫賣夜宵雲吞和滷煮雞蛋的聲音,這時我就走出去,從小販手中換取一些溫暖……總之,我已完全忽視並忘卻這條可以代表南京市內陋巷風格而無愧的小巷的種種,高低不平的路面,從路邊菜圃一直延伸過來的溝渠,污水面上還滿覆了浮萍。雨後,路上就到處布滿了一個個小水潭……
這一切,今天是大大變化了,但有的卻沒有什麼變化。那個醬園作坊的大院子,不用說,是沒有找到。戶部街的兩側,已經新建了許多工廠、機關……再也沒有了那樣的空地。但街面依舊像當年一樣逼仄。這時正在翻修下水道,路面中間挖起了一條深溝。人們只能在溝邊的泥水塘中跳來跳去,要這樣一直走到楊公井。尋找舊居的企圖是失敗了,但這跳來跳去的經驗倒還與當年無異。
還是到
秦淮河畔去看看吧。

秦淮河畔
在建康路下車,走過去就是貢院西街。我走來走去找了許久,也沒有找到那座已經成為夫子廟標記的亭子。但我毫不懷疑,那擁擠的人群,繁盛的市場,那種特有的氣氛,是只有夫子廟才會有的。晚明
顧起元在《
客座贅語》中提到這一帶時說:“百貨聚焉”、“市魁駔儈,千百嘈其中”。這樣的氣氛,依然保留了下來,但社會的性質完全改變了,一切自然也與過去不同。
與三十年前相比,黃包車、稀飯攤子、草藥鋪、測字攤、穿了長衫走來走去的人們都不見了;現在這裡是各種類型的百貨店、飲食店……還有掛了招牌,出售每斤九角一分的河蟹的小鋪,和為一個熱鬧的市井所不可少的一切店鋪,甚至在路邊上我還發現了一個舊書攤。
穿過街去,就到了著名的秦淮。河邊有一排精巧的石欄,有許多老人都在石欄上閒坐,欄桿表面發著油亮的光澤,就像出土的古玉。地上放著一排排鳥籠子。過去對河掛了“六朝小吃館”店招的地方,現在是一色新修的圍牆。走近去憑欄一望,不禁吃了一驚。秦淮河還是那么淺,甚至更淺了,記憶中慘綠的河水現在變成了暗紅,散發出來的氣味好像也與從前不同了。
在文德橋側邊是新建的“白鷺洲菜場”。卡車正停在門口卸貨。過橋就是鈔庫街,在一個堆了煤塊的曲折的小弄牆角,掛著一塊白地紅字搪瓷路牌,上面寫著“烏衣巷”。這時已是下午四時,巷口是一片照得人眼睛發花的火紅的夕陽。
烏衣巷是一條曲折的小巷,不用說汽車,腳踏車在這裡也只能慢慢地穿過,巷裡的人家屋宇還保留著古老的面貌,偶然也能看到小小的院落、花木,但王謝家族那樣的第宅是連影子也沒有,自然也不會看到什麼燕子。
巷子後半路面放寬了,兩側的建築也整齊起來。筆直穿出去就是白鷺洲公園,但卻緊緊地閉著鐵門。向一位老人請教,才知道要走到小石壩街的前門才能進去。我順便又向他探問了一些秦淮河畔的變遷,老人的興致很好,熱情地向我推薦了能吃到可口的蟹粉包子和乾絲的地方,但也時時流露出一種惆悵的顏色,當我告訴他三十多年前曾來過這裡時,老人睜大了眼睛,“噢,噢,變了,變了。”他指引給我走到小石壩街去的方向,我道了謝,走開去,找到了正門,踏進了白鷺洲公園。
這是一處完全和舊有印象不同了的園林。一切都是新的,包括了草地、新植的樹木和水泥製作的仿古亭台。乾淨、安謐,空闊甚至清冷。我找了一個臨水的地方坐下,眼前是夕陽影里的鐘山和一排城堞。我搜尋著過去的記憶,記得這裡有著一堵敗落的白堊圍牆,嵌著四字篆字“東園故址”的磚雕門額,後面是幾株枯樹,樹上吊著一個老鴉窠。這樣荒涼破敗的一座“東園”,今天是完全變了。
園裡雖然有相當寬闊的水面,但這地方並非當年李白所說的白鷺洲。幾十年前,一個聰明的商人在破敗的“東園”遺址開了一個茶館,借用了這個美麗的名字,還曾請名人撰寫過一塊碑記。碑上記下了得名的由來,也並未掩飾歷史的真相,應該還要算是老實的。
在一處經過重新修繕彩繪的曲欄迴廊後面,正舉行著菊展,菊花都安置在過去的老屋裡,這時暮色已經襲來,看不真切了。各種的菊花錯落地陳列在架上、地上,但盆上並沒有標出花的名色。像“麼鳳”、“青鸞”、“玉搔頭”、“紫雪窩”這樣的名色,一個都不見。這就使我有些失望。我不懂賞花,正如也不懂讀畫一樣。看畫時興趣只在題跋,看花就必然注意名色。從花房裡走出,無意中卻在門口發現了那塊“東園故址”的舊額,真是如逢舊識。不過看得出來,這是被捶碎以後重新鑲拼起來的。面上還塗了一層白粉。即使如此,我還是非常滿意。整個白鷺洲公園,此外再沒有一塊舊題、匾對、碑碣……這是一座風格大半西化了的園林,卻恰恰坐落在秦淮河上。
坐在生意興旺的有名的店裡吃著著名的蟹粉小籠包餃和乾絲,味道確實不壞。乾絲上面還鋪著一層切得細細的嫩黃薑絲。這是在副食品剛剛調整了價格之後,但生意似乎並未受到怎樣的影響。一位老人匆匆走進來和我同坐,他本意是來吃乾絲的,不巧賣完了,只好改叫了一碗麵。他對我說:“調整了價格,生意還是這么好。不過乾絲是素的,每碗也提高了五分錢,這是沒有道理的。”我想,他的意見不錯。
雜七搭八地和老人談話,順便也向他打聽這裡的情形,經過他的指點,才知道過去南京著名的一些酒家,六華春、太平洋……就曾開設在窗外的一條街上,我從視窗張望了一下,黝黑的一片,什麼也看不見。我記起三十多年前曾在六華春舉行過一次“盛宴”,邀請了南京電話局長途台的全體女接線員,請求她們協助,打破國民黨反動派的干擾,使我每晚打出的新聞專電暢通無阻的舊事。這些年輕女孩子嘰嘰喳喳的笑語,她們一口就答應下來的爽朗、乾脆的姿態,這一切都好像正在目前。
自公元三世紀以來,南京曾經是八個王朝的首都。宮廷政治中心一直在城市的北部、中部。城南一帶則是主要的平民生活區。像烏衣巷,曾是豪族的住宅區,不過後來敗落了,秦淮河的兩岸變成了市民經濟和文化生活的中心。明代後期這種發展趨勢尤為顯著。形成商業中心的各行各業,百工貨物,幾乎都集中在這裡。繁複的文化娛樂活動也隨之而發展。這裡既是王公貴族、官僚地主享樂的地方,也是老百姓游息的場所。不過人們記得的只是寫進《板橋雜記》、《桃花扇》里的場景,對普通市民和社會下層的狀況則所知甚少,其實他們的存在倒是更為重要的,是全部的基礎。曾國藩在鎮壓了
太平天國起義以後,第一件緊急措施就是恢復秦淮的畫舫。他不再顧及“理學名臣”的招牌,只想在娼女身上重新找回封建末世的繁榮,動機和手段都是清清楚楚的。
穿著高貴的黑色華服的王謝子弟,早已從歷史的螢幕上消失了;披了白袷春衫的明末的貴公子,也只能在舊劇舞台上看見他們的影子,今天在秦淮河畔摩肩擦背地走著的只是那些“尋常百姓”,過去如此,今後也仍將如此。不同的是今天的“尋常百姓”已經不是千多年來一直被壓迫、被侮辱損害的一群了。
從飯店裡出來,走到街上,突然被剛散場的電影院裡湧出的人群裹住,幾乎移動不得,就這樣一路被推送到電車站,被送進了候車的人群。天已經完全昏黑了,我站在車站上尋思,在三十年以後我重訪了秦淮,沒有了河房,沒有了畫舫,沒有了茶樓,也沒有了“槳聲燈影”,這一切似乎都理所當然地成了歷史的陳跡。可是我們應該怎樣更好地安排人民的休息、娛樂和文化生活呢?人們愛這個地方,愛這個祖祖輩輩的“游釣之地”。我們應該怎樣來滿足人民熾熱的願望呢?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日
詞語注釋
《白下瑣言》:清代
甘熙所撰著的一部有關金陵的筆記。成書於道光二十七年,內容略分為:金陵地勢、水利;名人故園、墓地;歷史掌故、風土人情等。1987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曾出影印本。
樊若水(943-994),字叔清,五代時南唐士人,因不得志而叛國,向宋太祖進獻架浮橋平南唐策,直接導致了南唐的滅亡。入宋後,宋太祖趙匡胤賜名為樊知古,字仲師,頗受重用。
李煜《
破陣子》詞云: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幾曾識干戈? 一旦歸為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
遺蛻:遺蹟;遺留物。
菜圃(cài pǔ):指菜園;種植蔬菜、花卉、樹苗的園地。
逼仄:狹窄。
《客座贅語》:明代顧起元所撰著的一部有關金陵的筆記。成書於萬曆年間,內容記述南都金陵的地理形勢、水陸交通、戶籍賦役、街道坊廂、山川河流、名勝古蹟、方言俗語、名人軼事等,有部分內容採錄史志,但絕大部分內容仍不失為珍貴史料,其中金陵方言俗諺、名物稱謂、衣冠服飾等,尤有價值。
市魁駔儈(shì kuí zǎng kuài):管理市場的經紀人。
城堞:城上的矮牆。
東園故址:明代中山王徐達的東花園,又名太傅園,為金陵名園之一,清末園已荒廢。其西園即今瞻園。
李白《登金陵鳳凰台》詩中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李詩中白鷺洲當在石頭城外的長江中。
吳、東晉、宋、齊、梁、陳等六個朝代曾定都南京,故南京被稱為六朝古都,加上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都於此,孫中山建立中華民國亦定都於此,故云。
《板橋雜記》:明末清初
余懷作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的一部筆記。全書分上、中、下三卷。記述了明朝末年南京十里秦淮南岸的長板橋一帶舊院諸名妓的情況及有關各方面的見聞。
《桃花扇》:清初劇作家孔尚任寫的一部傳奇,劇情以復社文人侯方域與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反映了南明弘光小朝廷覆亡的歷史悲劇。
理學名臣:
曾國藩是晚清中興重臣,在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各個方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學術思想上,他專修朱子理學,成為清朝最後一位理學大師。
尋常百姓:唐代詩人劉禹錫在懷古名篇《烏衣巷》詩中曰:“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處即化用該詩意。
槳聲燈影:1923年夏天,
俞平伯與
朱自清同游秦淮河,以《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為題,各作散文一篇,以風格不同、各有千秋而傳世,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
創作背景
1946年夏秋之交,作者黃裳作為《
文匯報》的特派員被派駐南京,在戶部街的報社辦事處工作,在那裡緊張而又悠閒地生活過一段時間,也並沒有什麼不滿足。三十三年後,即1979年冬,正值改革開放之初,作者重遊南京秦淮河,鑒於時代的變遷,重遊故地有感而作。
作品鑑賞
這篇散文,文筆散淡,十分本色,然於散淡中涵括著豐厚的意蘊,本色中孕育著作者的藝術匠心,有淡然醇厚、舉重若輕之感。
作者通過對南京這座歷史名城的重訪,表達了複雜而深摯的情感。對歷史遺蹟的深沉緬懷,對今昔變遷的無限感慨,對歷史故都文化建設的認真思考……大跨度的歷史空間,大重量的感情積澱,在作者的筆下似信手拈來、自然流出。對三十年前舊居的記憶,自然地涉及到南唐故宮的遺址,隨手帶出李後主荒淫誤國的歷史教訓;對秦淮河畔的重訪,又輕鬆地牽出“烏衣巷”、“白鷺洲”、“東園故址”、“秦淮槳聲”……三十年的變遷,一千六百年的感懷,縱橫交織,自由呈現。但是,作者在歷史與現實的感懷中,其流動的情感並不輕鬆,那看似疏淡的行文走筆,總是載負著深沉的感慨。
文章在布局上的參差錯落、疏密有致嘆為觀止。題為“秦淮拾夢”,卻並非有夢即拾,而是對未拾和將拾的舊夢做著精心的選擇。自公元三世紀以來的八代故都,可拾的舊夢實在太多,而烏衣巷與秦淮河似乎非拾不可。通過烏衣巷自然想起劉禹錫的名句:“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古代詩人從豪門貴族的興衰中,有感於世事的多變,不無哲理之思,而對尋常百姓寄與的同情,更觸發了作者的感慨,於是自然而然地生髮出對“尋常百姓”生活需要的見解。通過秦淮河,又可想起杜牧的《泊秦淮》:“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由杜牧的詩而勾聯出歷史上兩位後主和南宋、南明以及曾國藩恢復秦淮畫舫等若干遺蹟,加上當地老者的指點,典籍、野史的佐證,虛虛實實,相掩成趣。在各種回憶鏡頭中,當今與歷史的迭印,虛幻與真實的輝映,記敘與抒懷的交織,構成了參差錯落,斑斑駁駁的水墨長卷,如漫步長廊、畫舫、深園、曲池,有景隨步移、曲徑通幽之妙。
文章雖文字瑣細,卻底蘊豐厚,既不矯情,又不矜持,感情十分深摯而殷實,顯露出作者敦厚深宛的獨特風格。在中國這個歷史悠久、文化豐厚的國度里,“懷舊”是人之常情,但舊物畢竟已成既往,在蛻變中衰微,尋覓拾摭故夢,完全是為了當今。所以,作者儘管懷想那些既往的舊夢,但拾得它時,卻不能全身心地擁抱,更沒有生死契闊般的纏綿,而是始終與之保持著恰當的距離,特別對舊時的夢魘,則時時加以批評,使之在同當今的對照中,產生“滄海桑田”、”換了人間”的感受。著眼點始終落在作者處,他的筆還來不及一一記取舊夢的時候,其興致早被升騰起的新夢所壓倒,這就是他企盼著為尋常百姓描繪出一個生生患息的樂園,體現出作者對勞動人民的深厚情感。
作者簡介
黃裳(1919年—2012年),原名容鼎昌,原籍山東益都。早年在天津南開中學讀書。抗戰開始,轉學到上海,1940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1942年轉至重慶交大。1944年被徵調往昆明、桂林、貴陽、印度等地任美軍譯員。抗戰勝利後,任《文匯報》駐渝和駐南京特派員,後調回上海編輯部。1949年任復刊後《文匯報》主筆。1950年調北京,擔任軍委總政越劇團編劇。1951年調中央電影局上海劇本創作所任編劇。1956年重回《文匯報》任編委。黃裳生前與巴金、施蟄存、黃永玉等文化名人均有交往,其著作有《
錦帆集》、《
過去的足跡》、《珠還記》、《
珠還記幸》、《
來燕榭文存》等等,並譯有屠格涅夫長篇小說《
獵人筆記》等。

黃裳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