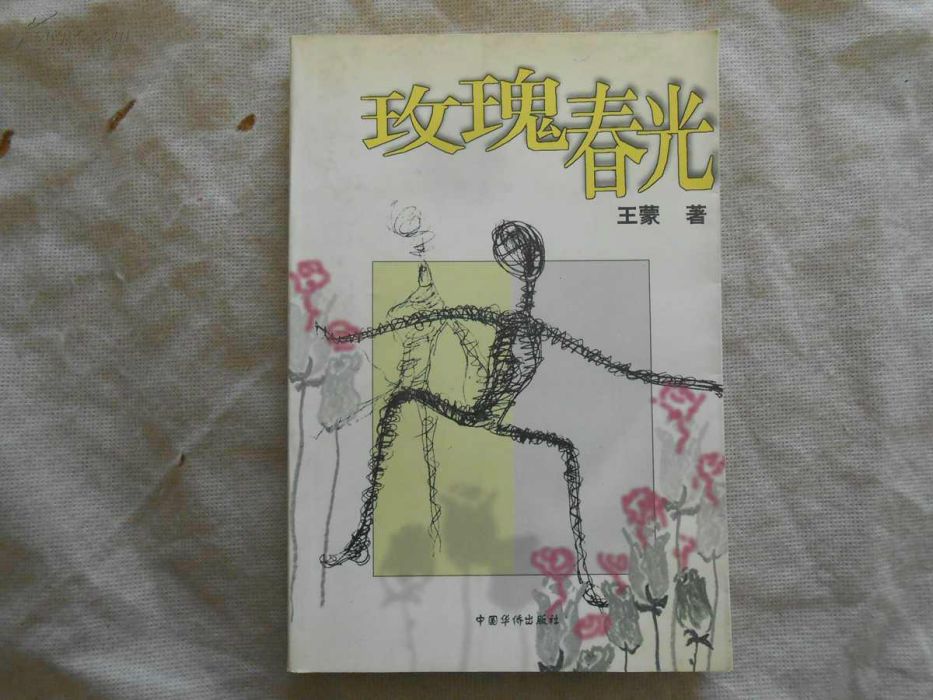《玫瑰春光》,書名,王蒙曾經說過:“寫短篇是我寫它,寫長篇是它寫我。”那么這本匯集了他九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說作品的書中,王蒙又寫進了什麼呢?它是對一段已經逝去的時光的紀念么?是一種追尋,一種拒絕---對於疲倦和麻木,對於倚老賣老的老太爺心態的拒絕么?在回憶與現時的對比中,時間成了一個怎么樣的角色!威嚴與哀婉的滄桑,不也夠喝一壺的嗎?而在某些荒唐不經如夢囈般的故事(所以要說是鄭重的啦)中,是不是還當真果然地有某個不幸而言中的預見呢。
基本介紹
- 書名:《玫瑰春光》
- 作者:王蒙
- 類別:中短篇小說
- 出版社:華僑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1年
- 定價:16.00
- 裝幀:平裝
- ISBN:9787801204769
內容簡介,前言,目錄,文章節選,
內容簡介
看下去,一捉摸,您就什麼都明晰了。
前言
九十年代以來,我集中精力寫《季節》長篇小說系列,但也寫了一點中短篇直到極短篇。
寫中短篇是一個幸福的體驗,相對來說它比較容易統籌全局,比較容易短平快地作出某種反應,比較容易見效果、見巧思、見功夫。寫完了也比較容易爛熟於心,叫做至少易於自我欣賞。我說過,寫短篇是我寫它,寫長篇是它寫我。
現承朋友們的好意在華僑出版社將近年的中短篇結集出版,它們是對一段已經逝去的時光的紀念么?是一種追尋,一種拒絕---對於疲倦和麻木,對於倚老賣老的老太爺心態的拒絕么?在回憶與現時的對比中,時間成了一個怎么樣的角色!威嚴與哀婉的滄桑,不也夠喝一壺的嗎?而在某些荒唐不經如夢囈般的故事(所以要說是鄭重的啦)中,是不是還當真果然地有某個不幸而言中的預見呢?
看下去,一捉摸,您就什麼都明晰了。
九十年代以來,我集中精力寫《季節》長篇小說系列,但也寫了一點中短篇直到極短篇。
寫中短篇是一個幸福的體驗,相對來說它比較容易統籌全局,比較容易短平快地作出某種反應,比較容易見效果、見巧思、見功夫。寫完了也比較容易爛熟於心,叫做至少易於自我欣賞。我說過,寫短篇是我寫它,寫長篇是它寫我。
現承朋友們的好意在華僑出版社將近年的中短篇結集出版,它們是對一段已經逝去的時光的紀念么?是一種追尋,一種拒絕---對於疲倦和麻木,對於倚老賣老的老太爺心態的拒絕么?在回憶與現時的對比中,時間成了一個怎么樣的角色!威嚴與哀婉的滄桑,不也夠喝一壺的嗎?而在某些荒唐不經如夢囈般的故事(所以要說是鄭重的啦)中,是不是還當真果然地有某個不幸而言中的預見呢?
看下去,一捉摸,您就什麼都明晰了。
目錄
前言:《玫瑰春光》小記 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
怒號的東門子
玫瑰大師及其他
春堤六橋
小說瘤
鄭重的故事
楓葉
滿漲的靚湯
短篇小說之�i
前言:《玫瑰春光》小記
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
怒號的東門子
玫瑰大師及其他
春堤六橋
小說瘤
鄭重的故事
楓葉
滿漲的靚湯
短篇小說之�i
文章節選
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 我多次試圖以我所喜愛的蘇俄歌曲來編織我的青年時代。
《喀秋莎》是我的少年,是我的早戀,是我的十二歲。解放前我就會唱這首歌了,我喜歡這個歌的歌詞第一段的最後一句:“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
有一個歌不曾怎么流行,它唱道:
我們大家,都是熔鐵匠。
鍛鍊著幸福的鑰匙,
讓我們舉起,高高地舉起,
打呀打呀打......
它和“兄弟們向太陽向自由,向著那光明的路”和《華沙工人歌》一樣,是我的少共青春,是我的加入地下黨,是我的十四歲。
有一個歌叫做什麼來著?它唱“聯隊最光榮,騎馬越過草原,越過了森林還有山和谷,”它唱“聯隊最光榮,你呀你該驕矜”最後歸結為:“我們的將軍,就是伏羅希洛夫,從前的工人,今天做委員。”我唱著這個歌迎接了新中國的成立。
而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們愛唱的蘇聯歌曲是:“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此外應該提到《太陽落山》“太陽落在山的後面,在河灘上升起薄霧炊煙......”它是我的十六歲。
我還要特別提到那些歌唱史達林的歌:“陽光普照美麗的祖國原野”,“在高高的山上有雄鷹在飛翔”,“我們遼闊的磊地日新月異,更充滿了自由美麗......”這是我結結實實的大革其命的青年時代的證明,是我的共青團幹部生涯的標幟,是我政治上自以為優越於許多人的證明,唱這些歌的時候我周身溫熱,自以為是在拯救全世界,創造全世界,對了,那時我走向十八歲。
在我十九歲的時候國家宣布進入了“大規模有計畫的經濟建設時期”,我開始熱衷於體味生活的美好,它的代表歌曲是詩《卓婭》的主題歌:《藍色的星》。事後再想,這個歌過於軟綿綿了。
二十一歲的時候我愛唱《小路》和幾首從來沒有聽到任何人演唱的歌。一個是《快樂的風》:“唱個歌兒給我聽吧,快樂的風啊......”請想想,哪裡還有這樣美好的歌詩,連風都是快樂的。再一個歌是“我的歌聲飛過海洋/愛人呀別悲傷/國家派我們到海外/要掀起驚天風浪”,第二段是“不怕狂風不怕巨浪......”因為我們船上有個/年輕勇敢的船長。
不是百無聊賴,不是花花草草,不是搖臀擺腰,哪個二十一歲的青年人唱過這樣好的歌?
《紡織姑娘》是我的二十二歲,是我的愛情與人生交響樂的第一樂章,是我的生命的第一個大潮漲滿,是我從金色的幻夢進入人生的開始。
與別人不同,《莫斯科近郊的傍晚》確實曾經給我帶來傍晚的情緒。那時還有費奧多洛娃五姐妹的訪華,她們的代表唱是《田野靜悄悄》,還有《山楂樹》。這些歌似乎都是表達黃昏情緒的。
到了六十年代開始,於是我的青年時代與蘇聯歌曲的流行一同結束。
包括蘇聯國家,我也很喜歡,儘管在所謂《蕭斯塔柯維奇回憶錄》里它被嘲笑了一個六夠。歌中唱道:
俄羅斯聯合各自由盟員共和國,
結成永遠不可摧毀的聯盟
呵,我們的祖國,
呵,她的光榮永無疆,
各民族友愛的團結堅強......
我要為我所喜歡的蘇聯歌曲修建一座紀念牌---牌是謙虛,而並非碑的別字。
一
上個千年的最後幾年,在我們這個城市的俄羅斯總領事館附近,開了一家俄式西餐館。對於它的烹調我不想多說什麼,反正怎么吃不出五十年代專門去北京到新落成的蘇聯殿覽館莫斯科餐廳吃兩元五角的份飯(現在叫套餐)的那個香味來了。那時的蘇聯份飯最便宜的是一元五角,最�F的是五元。到了五元,就有紅魚子沙拉或蟹肉沙拉,有莫斯科紅菜湯或烏克蘭紅菜湯,有基也輔黃油雞卷或者烤大馬哈魚,有果醬煎餅或者奶油花蛋糕或者水果沙拉,最後又有冰激凌又有咖啡了,而且冰激凌和咖啡都是放在銀托鏤花餐具里的。銀子似灰似白,似明似暗,有一種自信和大家風度,服務員是戴著民族帽飾穿著連衣裙的俄羅斯姑娘,人人都長得豐滿厚實,輪廓分明,讓你覺得有了她們生活變得何等地充足結實!那時候管年輕女子叫:“姑娘”,而現在都叫小姐,到了我國西北地區則至今還叫丫頭。也許還應該羅嗦幾句,莫斯科餐廳的柱子上是六角形雪花與長長的松鼠尾巴的圖案,我不知道為什麼,一進這個廳,激動得就想哭一場,其實這個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幾乎每一頓飯都是供不應求,要先領號,然後在餐廳前面的鋪著豪華的地毯擺著十七世紀式樣的大硬背紫天鵝絨沙發的侯吃室里等候叫號。甚至坐在那裡等叫號也覺得榮幸享受如同上了天,除了名稱與莫斯科融為一體的這家餐廳,除了做偉大的蘇聯飲食的這家餐廳,哪兒還有這么高級的候吃的地方!而等坐下來接受俄羅斯小姐---不,一定要說是俄羅斯姑娘的服務的時候,我只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只覺得革命烈士的鮮血沒有白流,我只覺得人間天堂已經歸屬於我這一代人了。
而到了二十世紀未才在這個沿江城市開業的所謂俄式西餐館卻使我始終感到疑惑。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它是一所不算太大的房子,原來是山貨店,又名日用雜品店, 簡稱“日雜”店。很多壞小子包括喜愛讀陝西作家作品的讀者對“日雜”這個簡稱想入低級下流。它現在在房頂上掛了好幾塊粗帆布,像是船帆橫懸頭上。門裡又分了幾個區域,往裡搭起略高,分三處像是劇場或宴請。廳堂本身是幾個大小不一的散桌,菲名其妙地弄了幾個木頭墩子,橫著鋸開磨光,也算是桌台,這些桌台圍著一個表演區,一圈紅紅綠綠閃閃爍爍的燈光和兩個小小的聚光燈。表演區前一塊不大的空地算是舞池,偶爾有一兩對男女在這裡隨歌隨樂起舞,再往右拐,又搭高了,然而不是包廂,而是高處的幾個方桌,進門處最窪,我稱之為若不是牆上掛著幾張畫著白樺樹和伏爾加河的鏡框油畫,我根本想不到這是一個俄式餐館。
它的紅菜湯稀薄寡淡,它的中亞細亞串烤羊肉胡煙辣臭---還不如新疆烤的,它的伏特加酒帶有一種男人不能容忍之輕,它甜不唧唧的,它的奶油雜拌粘粘乎乎。然而餐廳的小姐告訴我,他們的大廚是地道的俄羅斯外籍勞工。它的噶瓦斯還能喚起一點五十年代中蘇友好的記憶,有酵母味,有蜂蜜味。有麵包味,更有嘿啦啦嘿啦啦的味兒。那時候是這樣唱的:
嘿啦啦嘿啦啦,
哧啦啦嘿啦啦,
天空出彩霞呀,
地上開紅花呀。
中蘇人民力量大。
打敗了美國兵啊......
中蘇人民團結緊
把帝國主義連根拔
(那個)連根拔!
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
我多次試圖以我所喜愛的蘇俄歌曲來編織我的青年時代。
《喀秋莎》是我的少年,是我的早戀,是我的十二歲。解放前我就會唱這首歌了,我喜歡這個歌的歌詞第一段的最後一句:“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
有一個歌不曾怎么流行,它唱道:
我們大家,都是熔鐵匠。
鍛鍊著幸福的鑰匙,
讓我們舉起,高高地舉起,
打呀打呀打......
它和“兄弟們向太陽向自由,向著那光明的路”和《華沙工人歌》一樣,是我的少共青春,是我的加入地下黨,是我的十四歲。
有一個歌叫做什麼來著?它唱“聯隊最光榮,騎馬越過草原,越過了森林還有山和谷,”它唱“聯隊最光榮,你呀你該驕矜”最後歸結為:“我們的將軍,就是伏羅希洛夫,從前的工人,今天做委員。”我唱著這個歌迎接了新中國的成立。
而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們愛唱的蘇聯歌曲是:“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此外應該提到《太陽落山》“太陽落在山的後面,在河灘上升起薄霧炊煙......”它是我的十六歲。
我還要特別提到那些歌唱史達林的歌:“陽光普照美麗的祖國原野”,“在高高的山上有雄鷹在飛翔”,“我們遼闊的磊地日新月異,更充滿了自由美麗......”這是我結結實實的大革其命的青年時代的證明,是我的共青團幹部生涯的標幟,是我政治上自以為優越於許多人的證明,唱這些歌的時候我周身溫熱,自以為是在拯救全世界,創造全世界,對了,那時我走向十八歲。
在我十九歲的時候國家宣布進入了“大規模有計畫的經濟建設時期”,我開始熱衷於體味生活的美好,它的代表歌曲是詩《卓婭》的主題歌:《藍色的星》。事後再想,這個歌過於軟綿綿了。
二十一歲的時候我愛唱《小路》和幾首從來沒有聽到任何人演唱的歌。一個是《快樂的風》:“唱個歌兒給我聽吧,快樂的風啊......”請想想,哪裡還有這樣美好的歌詩,連風都是快樂的。再一個歌是“我的歌聲飛過海洋/愛人呀別悲傷/國家派我們到海外/要掀起驚天風浪”,第二段是“不怕狂風不怕巨浪......”因為我們船上有個/年輕勇敢的船長。
不是百無聊賴,不是花花草草,不是搖臀擺腰,哪個二十一歲的青年人唱過這樣好的歌?
《紡織姑娘》是我的二十二歲,是我的愛情與人生交響樂的第一樂章,是我的生命的第一個大潮漲滿,是我從金色的幻夢進入人生的開始。
與別人不同,《莫斯科近郊的傍晚》確實曾經給我帶來傍晚的情緒。那時還有費奧多洛娃五姐妹的訪華,她們的代表唱是《田野靜悄悄》,還有《山楂樹》。這些歌似乎都是表達黃昏情緒的。
到了六十年代開始,於是我的青年時代與蘇聯歌曲的流行一同結束。
包括蘇聯國家,我也很喜歡,儘管在所謂《蕭斯塔柯維奇回憶錄》里它被嘲笑了一個六夠。歌中唱道:
俄羅斯聯合各自由盟員共和國,
結成永遠不可摧毀的聯盟
呵,我們的祖國,
呵,她的光榮永無疆,
各民族友愛的團結堅強......
我要為我所喜歡的蘇聯歌曲修建一座紀念牌---牌是謙虛,而並非碑的別字。
一
上個千年的最後幾年,在我們這個城市的俄羅斯總領事館附近,開了一家俄式西餐館。對於它的烹調我不想多說什麼,反正怎么吃不出五十年代專門去北京到新落成的蘇聯殿覽館莫斯科餐廳吃兩元五角的份飯(現在叫套餐)的那個香味來了。那時的蘇聯份飯最便宜的是一元五角,最�F的是五元。到了五元,就有紅魚子沙拉或蟹肉沙拉,有莫斯科紅菜湯或烏克蘭紅菜湯,有基也輔黃油雞卷或者烤大馬哈魚,有果醬煎餅或者奶油花蛋糕或者水果沙拉,最後又有冰激凌又有咖啡了,而且冰激凌和咖啡都是放在銀托鏤花餐具里的。銀子似灰似白,似明似暗,有一種自信和大家風度,服務員是戴著民族帽飾穿著連衣裙的俄羅斯姑娘,人人都長得豐滿厚實,輪廓分明,讓你覺得有了她們生活變得何等地充足結實!那時候管年輕女子叫:“姑娘”,而現在都叫小姐,到了我國西北地區則至今還叫丫頭。也許還應該羅嗦幾句,莫斯科餐廳的柱子上是六角形雪花與長長的松鼠尾巴的圖案,我不知道為什麼,一進這個廳,激動得就想哭一場,其實這個廳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幾乎每一頓飯都是供不應求,要先領號,然後在餐廳前面的鋪著豪華的地毯擺著十七世紀式樣的大硬背紫天鵝絨沙發的侯吃室里等候叫號。甚至坐在那裡等叫號也覺得榮幸享受如同上了天,除了名稱與莫斯科融為一體的這家餐廳,除了做偉大的蘇聯飲食的這家餐廳,哪兒還有這么高級的候吃的地方!而等坐下來接受俄羅斯小姐---不,一定要說是俄羅斯姑娘的服務的時候,我只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只覺得革命烈士的鮮血沒有白流,我只覺得人間天堂已經歸屬於我這一代人了。
而到了二十世紀未才在這個沿江城市開業的所謂俄式西餐館卻使我始終感到疑惑。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它是一所不算太大的房子,原來是山貨店,又名日用雜品店, 簡稱“日雜”店。很多壞小子包括喜愛讀陝西作家作品的讀者對“日雜”這個簡稱想入低級下流。它現在在房頂上掛了好幾塊粗帆布,像是船帆橫懸頭上。門裡又分了幾個區域,往裡搭起略高,分三處像是劇場或宴請。廳堂本身是幾個大小不一的散桌,菲名其妙地弄了幾個木頭墩子,橫著鋸開磨光,也算是桌台,這些桌台圍著一個表演區,一圈紅紅綠綠閃閃爍爍的燈光和兩個小小的聚光燈。表演區前一塊不大的空地算是舞池,偶爾有一兩對男女在這裡隨歌隨樂起舞,再往右拐,又搭高了,然而不是包廂,而是高處的幾個方桌,進門處最窪,我稱之為若不是牆上掛著幾張畫著白樺樹和伏爾加河的鏡框油畫,我根本想不到這是一個俄式餐館。
它的紅菜湯稀薄寡淡,它的中亞細亞串烤羊肉胡煙辣臭---還不如新疆烤的,它的伏特加酒帶有一種男人不能容忍之輕,它甜不唧唧的,它的奶油雜拌粘粘乎乎。然而餐廳的小姐告訴我,他們的大廚是地道的俄羅斯外籍勞工。它的噶瓦斯還能喚起一點五十年代中蘇友好的記憶,有酵母味,有蜂蜜味。有麵包味,更有嘿啦啦嘿啦啦的味兒。那時候是這樣唱的:
嘿啦啦嘿啦啦,
哧啦啦嘿啦啦,
天空出彩霞呀,
地上開紅花呀。
中蘇人民力量大。
打敗了美國兵啊......
中蘇人民團結緊
把帝國主義連根拔
(那個)連根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