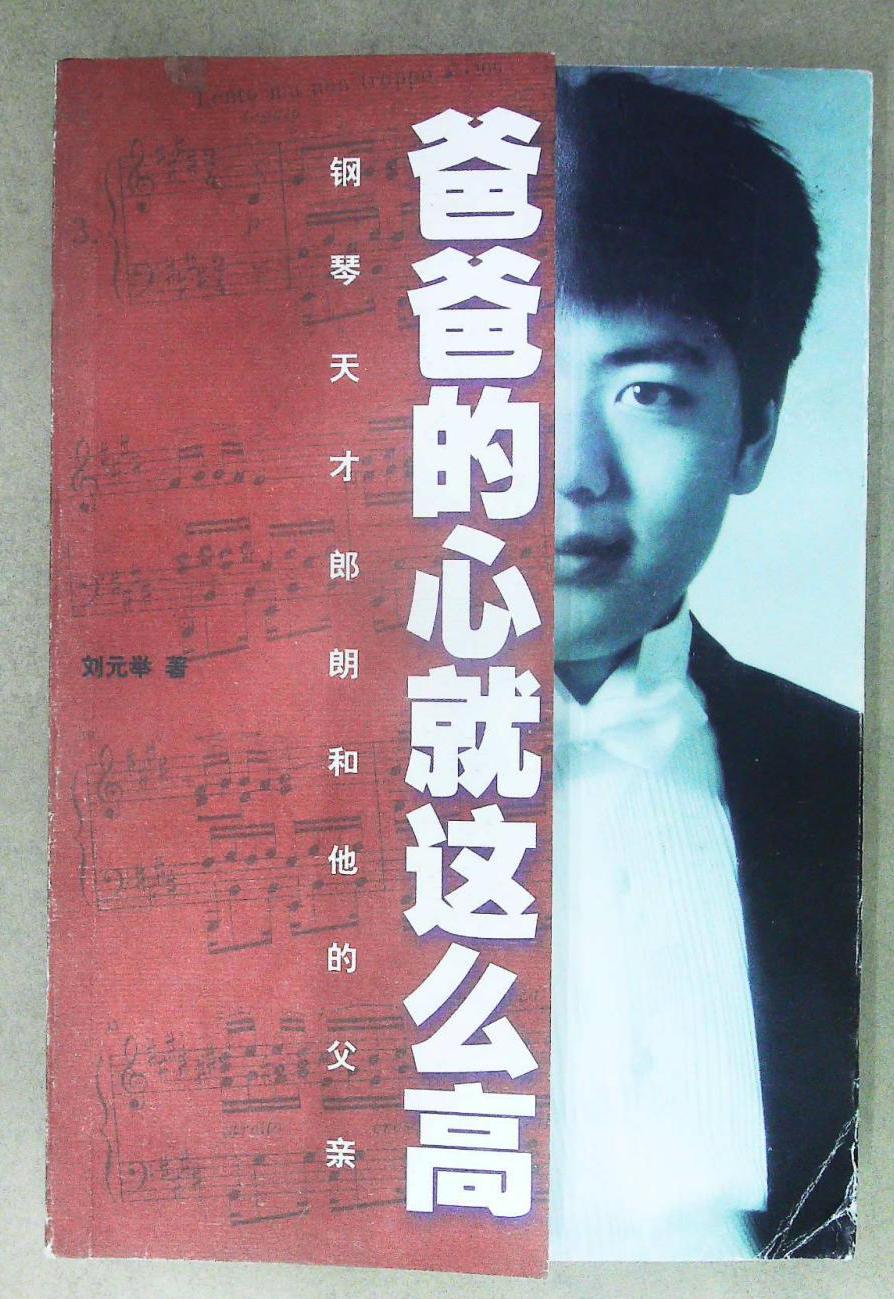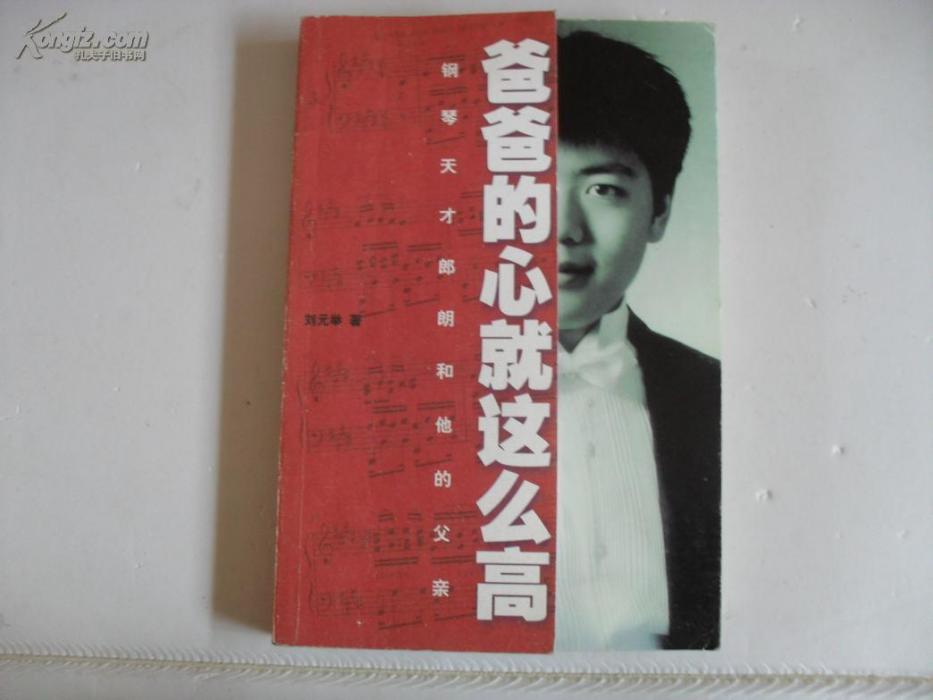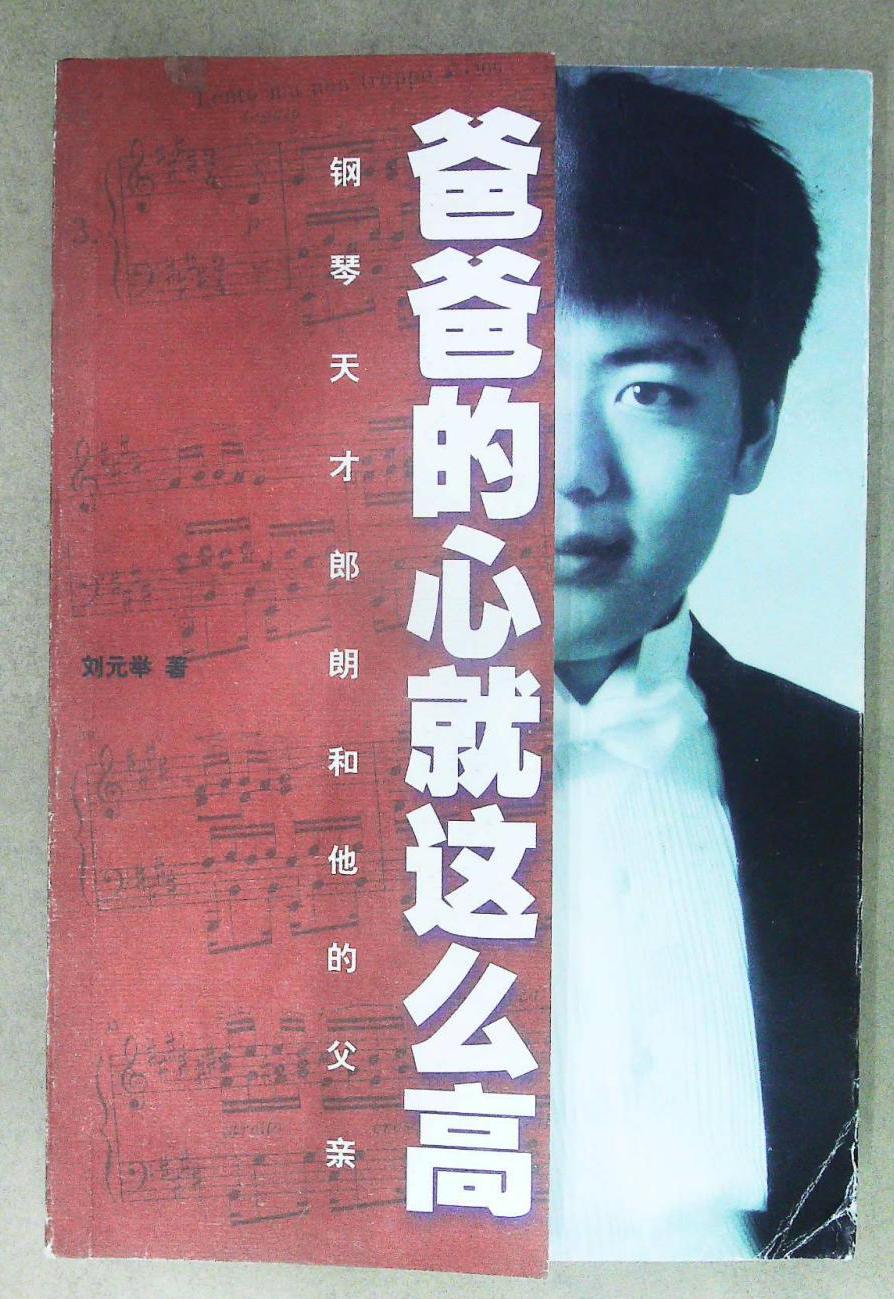內容簡介
這是一個普通父親和他鋼琴天才兒子的故事,為了兒子的成功,他犧牲了令人羨慕的職位,犧牲了一個完整和諧的家庭氛圍,犧牲了一個個成熟男人最寶貴的生命光陰……為了鋼琴,為了兒子成為大師,這位堅韌的父親犧牲了一切,奉獻了一切,可是他換來了一個鋼琴天才的誕生�D�D在德國,在日本,在美國,這位神童以他狂飆般的輝煌回報了他的父親和他的祖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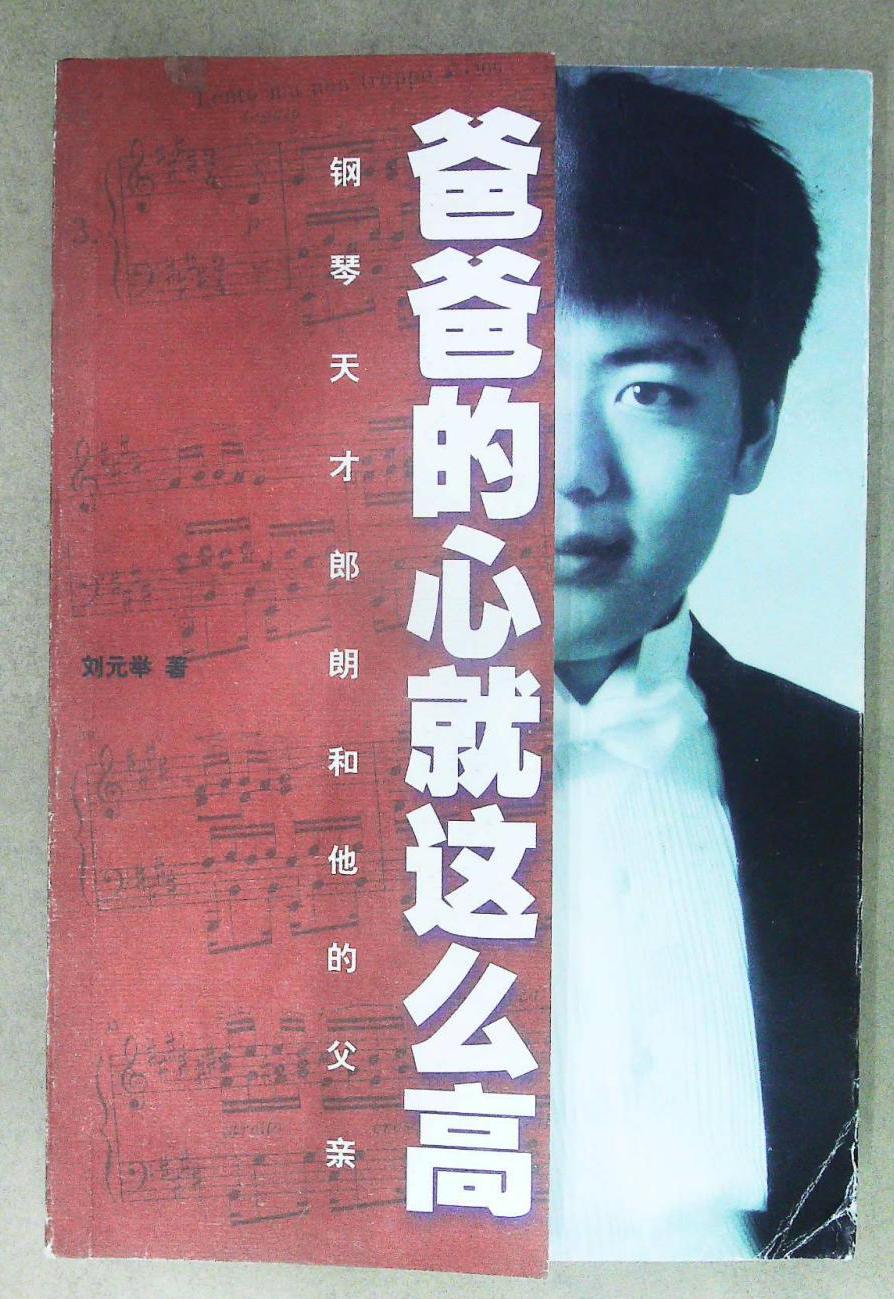
《爸爸的心就這么高--鋼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親》
書籍目錄
第一章 在葬禮的氣氛中壯行
第一節 痛灑英雄淚
第二節 昨日重現 第二章 北京的日子
第一節 無業人員
第二節 父親逼兒子去死:跳樓?還是吃藥?可以任選 第三章 父親的賭注
第一節 瀋陽一瀋陽
第二節 沈空大走廊
第三節 孤注一擲
第四章 淚灑Ettlingen
第一節 螢光屏上有條流動的小溪
第二節 好奇帶來的好運
第三節 房東尼曼婭和一條與郎朗同齡的大狼狗
第四節 淚水的真實分量 第五章 命運之神還能朝你們微笑嗎?
第一節 特殊公民
第二節 這裡也有陷阱
第三節 個性的衝突 第六章 好兒郎朗
第一節 通往仙台
第二節 頭頂五星紅旗
第三節 一張憂鬱敏感的斯拉夫面孔會被中國孩子感動嗎 第七章 再起波瀾
第一節 與殷承宗的緣分
第二節 又一次驚人的舉措
第三節 到美國考學 第八章 說不清道不明的夫妻情
第一節 大病降臨
第二節 風雨愛情
第三節 火車在流淚
第四節 聽郎朗彈琴
第九章 在美國輝煌
第一節 這是夢吧
第二節 趕緊往家跑,告訴爸爸
第三節 跨進IMG公司大門,神氣一點
第四節 在美國輝煌
第一章 在葬禮的氣氛中壯行
第一節 痛灑英雄淚
第二節 昨日重現
第二章 北京的日子
第一節 無業人員
第二節 父親逼兒子去死:跳樓?還是吃藥?可以任選
第三章 父親的賭注
第一節 瀋陽一瀋陽
第二節 沈空大走廊
第三節 孤注一擲
第四章 淚灑Ettlingen
第一節 螢光屏上有條流動的小溪
第二節 好奇帶來的好運
第三節 房東尼曼婭和一條與郎朗同齡的大狼狗
第四節 淚水的真實分量
第五章 命運之神還能朝你們微笑嗎?
第一節 特殊公民
第二節 這裡也有陷阱
第三節 個性的衝突
第六章 好兒郎朗
第一節 通往仙台
第二節 頭頂五星紅旗
第三節 一張憂鬱敏感的斯拉夫面孔會被中國孩子感動嗎
第七章 再起波瀾
第一節 與殷承宗的緣分
第二節 又一次驚人的舉措
第三節 到美國考學
第八章 說不清道不明的夫妻情
第一節 大病降臨
第二節 風雨愛情
第三節 火車在流淚
第四節 聽郎朗彈琴
第九章 在美國輝煌
第一節 這是夢吧
第二節 趕緊往家跑,告訴爸爸
第三節 跨進IMG公司大門,神氣一點
第四節 在美國輝煌
文章節選
摘錄(一) 螢光屏上有條流動的小溪 郎朗父子與趙屏國老師一同登上法航班機,在笑容殷殷的金髮空姐的迎接下,他們緩緩走進了一個高貴的空間--這是一個材料精緻、什麼都精緻的寬敞通暢的空中大客廳,順著過道往前瞅一眼,就讓人胸襟開闊。座椅兩側坐了那么多的人也不顯得擁擠,還有好幾台大彩電,螢幕不時閃現出飛行線路。線路在螢幕上溫柔地流動著,在你不經意間延展著:飛出國門之後,線條的箭頭便指向了烏蘭巴托、莫斯科,而後還有華沙、法蘭克福等城市,這一切對於郎家父子來說都是那樣的陌生。郎朗仰頭眨動著一雙好奇的大眼睛盯著那道會流動的線條去處。他可以辨認出俄羅斯的拼讀方式,他知道那片領土太遼闊了,他也嚮往著那裡,他崇拜從那裡走出來的鋼琴大師們,那是些怎樣風光璀璨的名字呵:霍洛維茲、拉赫瑪尼諾夫、普洛科菲耶夫、斯特拉文斯基,還有蕭士塔高維奇、阿什肯納吉……這些人中郎朗見到的只有阿什肯納吉,那是在中央音樂學院上大師課時。其他的那幾位他雖然沒有親耳聆聽教誨的福分,但他卻把這些人都當成他的老師,隨著琴藝的提高視野的開闊,他覺得這些大師越發親近起來。 飛過這片遼闊的土地,就到了波蘭的上空,波蘭的國家不大,巨有些軟弱,歷史上總遭受欺凌,卻出了一位偉大的彪炳千秋的鋼琴家蕭邦,在中國人的心目中,蕭邦有著特殊的地位。具有詩人氣質的蕭邦曾帶著對故園的怎樣的離情別緒,飄泊巴黎,寫出了那么多不朽的鋼琴詩篇,至今還在為世界上眾多的鋼琴家們悉心闡釋。郎朗最喜歡這位鋼琴詩人的作品,他小小的年紀已經可以熟練彈奏蕭邦的24首練習曲了。在他這小小年紀上,能夠熟練彈奏出蕭邦24首練習曲的人是不多見的。 過了波蘭直抵華沙、柏林,然後就到了法蘭克福。從螢幕上標出的飛行曲線上可以看得真真切切,途中差不多用了七個小時。 精力過剩的郎朗頭一次乘坐國際航班,頭一次一飛出國門,他像個彈性十足的皮球,從里往外膨脹的興奮使他無法在座位上坐穩當。他不斷地在過道上走動,不斷地接別人的話茬兒,他見身邊的父親坐得過於沉默,他就覺得難受,便不時地逗弄一下。這時候的郎國任顯不出一丁點的威嚴來,對於許多人來說,第一次出國,其高興的心情肯定是難以掩飾的,而郎國任卻完全不是這樣。他不僅沒有一點高興的神色,反倒顯得情緒低落,疲憊不堪地癱在座位上,不愛吱聲,甚至連眼皮都懶得往上抬。這位精力過剩、責任更過剩的中年漢子由於連日來的操勞,那繃緊的神經一旦鬆弛下來,他就再也挺不住了,他居然在如此舒適的法國民航班機上如同墜入棉花堆里,頭重腳輕,掙扎著往起爬卻怎么也爬不起來,只能閉上眼睛任其遊蕩。突然,郎朗發覺父親嘔吐起來。 郎國任像是大病一場,好容易止住嘔吐,閉上眼睛養神。他顯得很虛弱,臉色白得嚇人,汗也在往外直冒。他居然暈飛機了。 在兒子的眼裡,父親是位鋼澆鐵鑄的漢子,有點小病什麼的,不會當作一回事。在隨行的人中,也只以為郎國任出現這種異常反應不過是身體有點暫時的不適罷了,卻不會去進一步揣摩一下他的心情究竟怎樣。 在郎國任這邊,根本就沒有從這次出國中感受到一點點與旅遊相關的樂趣,因為他沒有一點輕鬆的心請。作為一個辭去公職的"無業游民"已經幾年沒有工資了,這是下了一次賭注,一次不小的賭注,問題是究竟有多大把握?這已經下取決於他了,而是取決於他的寶貝兒子。 他第一次顧不得照顧兒子了,索性就讓他自由自在吧! 圍繞著父親成長的兒子總是離不開一種管束,突然到了不受干涉與管束的時候,竟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了。要是總能這樣自由自在該有多好。可惜,飛機上時間過得太快了,似乎還沒有呆夠,就該收拾東西下飛機了。有父親在身邊,他什麼都不用管,所有的包裹統統都由老爸負責。 郎國任在飛機停穩於法蘭克福機場時及時醒來。他強打著精神,拎起包裹,緊隨在兒子身後往出走。郎國任瞅瞅機窗外面那片陌生的世界,心下里說:到了,到外國了! 法蘭克福機場是歐洲的第二大機場,僅次於倫敦的希思羅機場。這裡有260條航線與世界各地通聯,被稱作"通向世界的門戶"。這裡晝夜都有飛機降落,從來不肯寂寞,有一家雜誌稱這裡是"震動世界的地方"。 郎朗他們一行四人被空姐非常有禮貌的微笑,送出了機艙門,順著B號指狀的登機艙道緩緩走了出來。艙道四周的玻璃透視性能極好,可以望見廣闊的室外機場,停機坪泊著各國的飛機,有的正在疾速衝出跑道。就在他們的頂部設有一個大平台,作為遊人的觀賞處,可以登臨眺望整個機場景觀,以及機場周圍的城市輪廓。顯然郎朗他們不知道這個遊覽處,就是知道,他們也不會有閒心去的。他們要抓緊時間去取行李。 行李是從一條傳送帶緩緩輸出來的,人們守在旁邊,沒有一點擁擠和雜亂,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德國人一切都是講究秩序的,只要你的雙腳一踏落這片土地上,你就會感受到某種不曾有過的束縛。同行的四人中有一位女孩子,她也是自費前來參加比賽的。她的哥哥就生活在這座城市。電話中已經聯繫好了,他前來接站。有人接站,郎國任繃緊的神經多少可以放鬆了,腳步也隨之變得疲沓起來。一向精神頭十足的郎國任不知怎么,在德國的這片土地上始終打不起足夠的精神頭。郎國任有點發蔫了。 趙屏國老師顯得神清氣爽。他穿戴講究,走到哪裡都是一副興致勃勃的樣子,看上去顯得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得多。他帶了一台小型攝像機,隨時隨地拍攝著。鏡頭上凡是出現他的形象,都是滿面笑容,滿面欣慰。其中不乏透出那種久違的中國人踏入西方世界的新奇與欣喜。從神情到衣著,都具有那種解脫的輕鬆和愉悅,與郎國任的心事重重狀態恰好形成強烈的反差。 如今,我所以能夠有幸捕捉到當時他們一行進入德國後的場景,包括許多細節,這得感謝趙老師。他把他的學生郎朗第一次走出國門的情景逐一拍攝下來,這肯定是一部有價值的資料。如果不是趙老師的細心,哪能記錄下這么多生動的場景。
摘錄(二) 無業人員
走出收票口的郎國任往肩上聳了聳背包,剛剛出了一口悶氣,就有人迎上來,以一種令人懷疑和厭惡的熱情拉他爺倆住店,拉他坐計程車。郎國任以一位警察的本能予以拒絕。可這邊拒絕了那邊又湧上來。他只能加倍提高警惕,儘快離開廣場。他從廣場的右邊圍欄處繞出去,就到了捷運口。捷運口很是髒亂,擺小攤的還有乞丐照例令他的神經無法鬆弛。郎朗頭一回到北京,看什麼都覺新奇。 特別是看到躺在地上的乞丐覺得非常新奇。他這般小小的年紀對北京的感覺是從書本上和電視裡得到的,雖然不如父輩當年那么神聖,但是,畢竟是首都,怎么也有這么髒的乞丐?怎么沒有人管呢?他正遲疑著被父親拽走了。他離開時,還回頭望了一眼。 捷運站台建在地下,寬敞明淨得像一個展覽大廳。這令郎朗立刻感到心胸敞亮無比。坐上捷運,開動時一片漆黑。這漆黑又讓郎朗多少有些緊張。每一次從漆黑中駛到了亮處便是到了下一個車站。人總是希望到達某站的,到站才給人一種希望。下了捷運又換乘汽車,他記住了在哪一站上車又在哪一站下車,換乘哪一路,跑多長時間。他是個愛操心的孩子,他不斷地問父親拉東西的大解放什麼時候能到,東西會不會丟。他還問父親豐臺區多遠,那裡是不是農村。他的問題總是那么多,使得心亂如麻的父親實在失去了應有的耐心。 汽車朝北京郊外飛駛,北京顯然比瀋陽更有春天的氣息,陽光燦爛,路邊的樹木亭亭而立,遠處的田野在春天的陽光中升騰起一片熱烈的春潮,令人心胸激盪。第一次遠離家園出外闖蕩的少年郎朗禁不住漲滿豪情。他在座位上一刻也不肯安生,一會兒跪著,一會兒站起來,他想像著父親將要把他帶去的新家會是什麼樣子。從父親緊鎖的眉頭和沉默的狀態上,他猜想那裡的條件肯定糟糕透了。 呈現在郎朗眼中的豐臺區居然也是挺繁華的城區。還有那么高的大樓。從瀋陽開來的大解放已經先於他們父子到達了他們的目的地。郎朗一眼就見到了車上熟悉的東西,見到了開車的司機叔叔。他高興得手舞足蹈。這是個喜形於色的孩子,他總是那般富於激情,僅憑他的激情就可以感染所有人。在以後的歲月中,郎朗經常會遇到一些陌生的熱心人的幫忙。除了人家喜歡他的彈琴之外,更主要的是受到了他這副熱情洋溢的舉止的感染。他很精明,很會說話,很會揣度別人的心思。一個有才華的少年能夠具備這種人見人愛的性格,肯定會受益匪淺。 郎朗的新家在11樓。兩室一廳,哇,這么寬敞明亮得多少租金呀?他問父親,父親說你小孩子管這些事幹嘛,你好好彈琴就是了。但是,郎朗偏要管,偏要問個明白。租金其實很便宜的,每月150元。到北京豐臺區租這樣的房子,那租金就得翻幾番了。不過,這150元的月租金對於郎國任來說也不算輕鬆。畢竟他辭去了工作,這意味著以後的日子他們父子在北京將只有花銷而分文沒有進項。郎國任這幾年為了培養郎朗花銷不小,積蓄所剩無幾。他見兒子一定要刨根問底,便把租金多說了兩百元。唉呀媽呀!這么多錢呀?我可得好好彈琴了!郎朗這么一叫喚,當父親的心裡邊就舒坦多了。 東西從車上卸下來,得從電梯上行到門樓。來往的人用一種異樣的眼神注視著他們父子。這座大樓裡邊的住戶成分比較複雜,也有不少外地人在此租房子住。租房子的人大多是涌到北京做買賣的,而像他們父子這樣來學琴的,這裡的人還是聞所未聞。那種異樣的眼神開始讓他們父子很不習慣,那是一種審視,一種懷疑還是一種輕蔑?抑或兼而有之?無形中這一切都構成了壓力,也都構成了動力!一貫說上口,一貫盛氣凌人的特殊警官,看你如何來適應這片並不友好的環境。 東西算是搬進屋了,最沉的是鋼琴最重要的也是鋼琴。好像拉來的東西挺多,其實一擺放,也沒有多少,屋子裡倒顯得有些空蕩。那兩個在部隊時發的箱子盛著他們父子倆的全部衣物。從寢室到廚房,郎國任忙裡忙外,從此,他將以全部的耐心圍著家裡轉了。他得為柴米油鹽勞神,他得算計著每個月的生活費用,他得學會去過日常所有的生活,哪怕是他過去最不願乾最瞧不上眼的只有女人才會去做的家務活。也就是說,他得既當爹又當媽。對於一個特別看重自己的事業型奮鬥型的男人而言,這無疑是一次洗心革面脫胎換骨。一切為了兒子,也僅僅是為了兒子。這就是說一個好端端的家庭將由此而一拆兩爿。妻子在瀋陽留守,爺倆在北京這邊奮鬥,無論是做丈夫的男人還是做妻子的女人,都將接受著同樣的壓力同樣的孤獨,同樣的期盼,他們失去了自我價值,一切都圍繞著對於兒子前途的設計來體現各自的生命的形態。他們牢牢拴在了兒子的身上。小小的兒子手指還那么纖細,小手還沒有長開,鋪在鍵盤上剛剛才能碰到八度,他能夠承擔起父母如此沉重的不顧一切的付出嗎?未來會怎么樣?還得遇到怎樣的坎坷,這一切都是未知數,都有待於他們自己去奮鬥去拼搏。雖然郎國任早已做好了心理準備,但是,置身在這樣一個人地兩生之所,卻沒有一種家的安全感和踏實感,他仍然感到空前的孤立無援。 夜已經很深了,他檢查了一下房門是否關好,把明天要去老師那兒上課的該帶的教材也細心檢查了一下,儘管兒子平時在收拾這些東西時也很細心,但他還是不能完全放心。明天得起大早,因為還得等汽車。必須得提前一點到老師那兒,第一面很重要,一定要給老師留下個好印象。聽說她是音樂學院搞基礎音樂教育的好老師,也是最難請的老師。那是朱雅芬老師幫著找的,她們都是上海人。要不是看在朱雅芬老師的面子,人家可能不會接收的。郎國任是最尊重朱雅芬老師的,他甚至有點怕她。箇中原因,留待下一章再說。 郎國任為兒子總是想得很細,連明天兒子穿什麼衣服,明早起來吃什麼也都想好了,他甚至還考慮了明天上完課去哪裡買菜,買什麼菜,做什麼飯,什麼東西既有營養又可以少花錢,他都-一想過了。北京這邊想完了,他就去想瀋陽那邊。他想到了瀋陽平時接觸的那些彈琴孩子的家長,那些人有的表面上顯得特別友好,總是誇你的孩子如何如何好,而一轉身在背後卻是用另外一套話埋汰你。他不知道他們會怎么談論他。但是,他可以斷定因他這一辭職帶郎朗進京,肯定會成為人家的談資。愛怎么說就怎么說去吧,反正嘴長在人家的腦袋上。核計這些人有什麼用呢?還怪煩的。 孩子的確夠累了,從他貪睡的樣子就可以看出來。他的嘴角繃得緊緊的,好像在夢中還和誰較勁。兒子在爭強好勝這一點上非常像他,甚至比他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正是最讓他喜歡之處。但是,他無論對兒子多么滿意,卻從來不流露出來。兒子到了哪裡都能得到一迭聲的誇獎卻獨獨得不到他這位當父親的誇獎。為此,兒子耿耿於懷。每次彈琴都調動了渾身的解數,都用了最大的力氣,可父親總是沒有喜悅的表情,頂多說句還行吧!然而,郎朗一直是在別人的羨慕和讚揚聲中成長的,他怎么受得了"還行"這種評語呢?他被激發起更大的幹勁,他一定要讓父親承認他彈得最好。他甚至在夢中都在和父親叫勁,看他夸不誇獎。郎國任對兒子的要求確實嚴格得近乎嚴酷。他總能挑剔,也總能挑出毛病來。有的曲子三遍五通他也不放行,還得再摳一遍。有時氣得兒子哇啦哇啦地喊叫一通,宣洩一通,卻還得老老實實地接著父親的要求再彈一遍。媽媽在家的時候,兒子可以和媽媽撒嬌,媽媽不在時,兒子卻找不到撒嬌的人了。在郎朗成長的道路上,郎國任這位天天與兒子耳鬢廝磨的嚴父,居然從未親過兒子。郎國任對兒子表達感情的方式也是獨特的,只能是在兒子睡熟了的時候,他默默地守著兒子,多看他幾眼,給他掖掖被子,撫摸一下他的小腳。這一切,他絕不會讓兒子知道。帶好兒子太不容易了,得有極強的克制力,永遠不誇他不鼓勵他不行,可輕易誇他更是不行。不讓他怕你不行,而讓他太怕你了事情更糟。尤其郎朗這種聰明伶俐的孩子。最難忘的是兩年前,他帶著郎朗去太原參加的全國首屆少兒鋼琴比賽的情景。 因為是首屆全國舉行這樣的比賽,所以,全國各地都非常重視,參賽的選手也夠多了。瀋陽不同年齡組的都有選手參賽。比較出名的有邢軍、杜瑩,她們都比郎朗大,郎朗當時只有七歲,在瀋陽寧山路國小讀一年級。他是那種人小志不小的孩子,他到了太原就是抱著得獎的決心來的。 比賽在太原少年宮進行,競爭異常激烈。當時的郎國任還不很熟悉全國各地的少年選手情況,他只知道上海和北京厲害。他沒有抱著一定要奪冠的心,但是,他覺得郎朗也應該在全國排上上名次。另外,他也是想來見識見識,看看北京上海的孩子究竟有多么厲害。 和郎朗在一個組競爭的有上海的王魯,還有北京的李端。這兩個孩子在當時都很受寵,也都頗有名氣,而來自東北的郎朗卻不為人所知。在鋼琴評審們的眼中,東北還是塊鋼琴的荒地,雖然"文革"期間不斷地有上海的鋼琴家到那裡播火種,比如朱雅芬、金石等人,但是,東北的孩子仍然無法真正進入評審們的視野。郎朗當時的程度是彈到了740,不過比賽規定不允許彈740,只能彈299。於是,郎朗那次彈了卡巴列夫斯基和中國曲子《紅星閃閃》。這兩首曲子都是著名教授朱雅芬一手教出來的。朱雅芬有自己一套獨特的教學法。她不僅注重技巧,她更注重音樂。在技巧與音樂的融匯上她更是能夠恰到好處地把握著郎朗的內在激情。而七歲的郎朗正是有著一種小老虎的衝勁兒,只要往鋼琴前一坐,不管在什麼地方,也不管是什麼規模的比賽,哪怕是李斯特坐在台下打分,他也不會有半點怯懦,相反,他會因此更加激發出精神頭兒。他是那種越比賽越競爭越人多越來勁兒的那種孩子。他特別願意表現自己展示自己。 郎國任一直挺後悔那天不該讓郎朗穿那條背帶褲子上台。郎朗彈到激情澎湃時,渾身的勁頭兒都調動起來,正要大顯身手時,那背帶卻不合時宜地從兩個肩頭滑脫下來,束縛了他那激情的胳膊,想揮灑卻伸不開,這不能不影響演奏效果。這是十分令人遺憾的。然而,儘管如此,郎朗彈得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不但音樂感覺好,而且一個音也沒錯,他贏得了熱烈的掌聲。台下聽眾不少交頭接耳,認為這個小孩彈得好。那次比賽取前六名:一等獎1名;二等獎2名;三等獎3名。鄰國任一個不漏地看了參加決賽的10名小選手演奏之後,心裡邊有底了。他覺得郎朗肯定可以進入前六名。如果不是背帶礙事,他甚至會認為郎朗可以競爭第一。宣布比賽成績時,郎朗情緒很高地坐在父親旁邊,他自信肯定榜上有名。他手裡拿著一支原子筆,往自己支起的光腿上刎著玩。他劃什麼呢?父親隨便掃一眼,發現他寫的是自己的名宇"郎朗",他寫得一筆一畫很認真。父親當然明白兒子的心思,心裡一下子湧入了一股暖流。第一名被上海選手王魯奪得,第二名是北京的李端,第三名--主持人在公布名次這段時間裡,他寫得滿腿都是郎朗。可是,他寫得再多,前六名公布完了也沒有聽到一聲郎朗。當父親的心禁不往怦然而動。這時的郎朗突然停下了筆,只聽主持人接著往下念獲得優秀獎的名單。這回,頭一個就是郎朗。就是說郎朗的名次排在了第七名。郎朗愣頭愣腦地說:不是吧? 父親說咋不是呢?他和兒子一樣的心情。畢竟是成年人了,遇事再激動也不至於當即爆發,可是,郎朗卻不然。他一下子蹦起來,郎國任一把沒抓住,他像頭小老虎,哇哇叫著沖向主席台。他邊跑邊喊叫:"太不公平了!憑什麼?憑什麼?"整個會場一下子靜下來,人們被這突如其來的喊叫弄得不知所措。"我不要優秀獎!我不要!" "不合理!不公平!"郎朗不顧別人的阻攔,衝到主席台下對台上的評審們揮著小拳頭憤怒地喊叫。喊著喊著,他竟大聲哭起來。他像受了天大的委屈。觀眾席上一片騷動,嗡嗡的議論聲越來越高。郎國任奔過去,拉住了又蹦又跳的兒子,硬是把他拖拽出去。 郎朗哭得真傷心。圍觀的小選手紛紛勸郎朗,別哭了,有個石家莊的小選手勸他說,我不也是得了優秀獎嗎?你看,我都沒哭。下次爭取嘛!郎朗瞪他一眼:你跟我比?你彈的什麼玩藝? 任何評獎要講絕對公平都是不可能的,因為評獎的因素受很多東西制約,各種關係錯綜複雜。沒有任何背景的郎朗第一次參加全國比賽能夠獲得第七名已經是很不錯了,但是,郎朗父子卻不這么看。他們認為郎朗彈得絲毫不比第一名差。即使不給第一名,那也不應離開前三名的,可是,他們太過分了。父子倆都是那么忿忿不平。只不過郎國任沒有像獨生子那么衝擊會場大喊大叫而已。他去找評審們說理,評審們也承認郎朗的才氣,也為郎朗沒有評上前六名而惋惜。他們也只能表示一點善意的惋惜而已,沒有什麼實質性作用。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了,據理力爭又能爭出個什麼? 優秀獎也要頒發獎品,念到郎朗的名字時,他拒絕上前領取。當一位小朋友替他把獎品取回來,遞給他時,他抓過來就狠狠地摔在地上。獎品是一隻玩具小狗。那隻天真無邪的金絲毛小狗在地上打了個滾兒,黑亮的眼珠定定瞅著他,仿佛對他表示抗議。郎朗余怒未消地把它抓起來又一次摔到了地上。後來,還是父親幫他把這隻小狗撿起來放好。 郎國任是個有心人。他將小狗帶回家,就擺放在屋子裡最醒目的地方,那就是鋼琴的上方。每大郎朗彈琴時都可以看到它,再不喜歡再想躲避都是不可能的。他要讓這隻小狗成為一個教材,時時激勵兒子,讓他發憤,讓他別那么輕易忘記太原的委屈。
這篇作文被當成範文在班級念了,老師非常喜歡,父親更是喜歡。他不僅看到了兒子在彈琴上的進步,而且看到了他在思想上的進步。小狗成了他最喜歡的玩具,每天他得看上一眼。此番來北京,他有好多東西沒有帶來,但是,他卻把這隻小狗帶來了。當郎國任一掀箱蓋看到這隻金色毛髮的小狗時,感慨良久。他想到了兒子的那篇作文,他默默祝願兒子能夠實現理想,考上中央音樂學院附小。到那時,讓這隻小狗好好看看郎朗的成功。 想到成功總是給人以力量的,郎國任堅信兒子通過一年的學琴,明年肯定能考取小五。他們不會白來的。在進駐北京的頭一個晚上,郎國任想了很多,他想得最多的就是郎朗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的"小五"。郎朗跳著腳喊著,越跑越快。他在後邊追。車一輛緊隨一輛,開得非常快,就帖著郎朗身邊飛馳。眼見一國內盛滿東西的大解放朝郎朗橫衝過去,就要碾壓著郎朗了。他大叫一聲:郎朗 於此同時,響起了敲門聲。郎國任跌坐而起,神情還沒有能夠從夢境中甦醒過來。敲門聲更大更真實了,郎國任下地問是誰?他以為一定是有人走錯門了,否則,怎么會有人一大早就來敲門呢?外邊的人告訴他是派出所和街道的,登門是要辦臨時戶口。 郎國任把門打開了。一位老太太,身後跟著一位穿警服的年輕人。老太太還算客氣,沖他微笑著介紹了身邊的警察是派出所的所長。那年年輕警察卻不那么友好,一進門盯了他一眼,那神情就不大對勁兒。然後,就開始盤問他到北京乾什麼來了。問得很細,還問他什麼工作,他將辭職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如實稟告。都問完了,這才遞給他一張表格讓他填寫。他接過表格看了看,坐下來便填寫。他急著快點填完好把他們打發走,因為他還得為兒子做早飯,還得早點離家雲音樂學院找叢老師上課。 他在表上填寫自己的名字,還有籍貫,從何而來,家庭成員之類,但是,在往下的那個空格里,他難住了,遲遲不知如何下筆,那個空格是要填也的工作職業。他是警察,可那已經成了過去,那么現在填什麼?填陪同兒子學鋼琴?他只好問所長如何填。所長說得非常輕鬆:填無業人員。 "無業人員"這四個字從這位陌生的派出所所長的嘴裡吐出來,令他極不舒服。當過警察的人再明白不過了社幾字的內涵。他拿筆的手開始哆嗦了,半天不願往下落。好不容易才把這四個字寫在那上面,結果字跡不工整,有的筆劃居然還從那個規定的框格里擁擠出來了。
摘錄(一)
螢光屏上有條流動的小溪
過了波蘭直抵華沙、柏林,然後就到了法蘭克福。從螢幕上標出的飛行曲線上可以看得真真切切,途中差不多用了七個小時。
郎國任像是大病一場,好容易止住嘔吐,閉上眼睛養神。他顯得很虛弱,臉色白得嚇人,汗也在往外直冒。他居然暈飛機了。
在兒子的眼裡,父親是位鋼澆鐵鑄的漢子,有點小病什麼的,不會當作一回事。在隨行的人中,也只以為郎國任出現這種異常反應不過是身體有點暫時的不適罷了,卻不會去進一步揣摩一下他的心情究竟怎樣。
在郎國任這邊,根本就沒有從這次出國中感受到一點點與旅遊相關的樂趣,因為他沒有一點輕鬆的心請。作為一個辭去公職的"無業游民"已經幾年沒有工資了,這是下了一次賭注,一次不小的賭注,問題是究竟有多大把握?這已經下取決於他了,而是取決於他的寶貝兒子。
他第一次顧不得照顧兒子了,索性就讓他自由自在吧!
圍繞著父親成長的兒子總是離不開一種管束,突然到了不受干涉與管束的時候,竟高興得不知如何是好了。要是總能這樣自由自在該有多好。可惜,飛機上時間過得太快了,似乎還沒有呆夠,就該收拾東西下飛機了。有父親在身邊,他什麼都不用管,所有的包裹統統都由老爸負責。
郎國任在飛機停穩於法蘭克福機場時及時醒來。他強打著精神,拎起包裹,緊隨在兒子身後往出走。郎國任瞅瞅機窗外面那片陌生的世界,心下里說:到了,到外國了!
法蘭克福機場是歐洲的第二大機場,僅次於倫敦的希思羅機場。這裡有260條航線與世界各地通聯,被稱作"通向世界的門戶"。這裡晝夜都有飛機降落,從來不肯寂寞,有一家雜誌稱這裡是"震動世界的地方"。
郎朗他們一行四人被空姐非常有禮貌的微笑,送出了機艙門,順著B號指狀的登機艙道緩緩走了出來。艙道四周的玻璃透視性能極好,可以望見廣闊的室外機場,停機坪泊著各國的飛機,有的正在疾速衝出跑道。就在他們的頂部設有一個大平台,作為遊人的觀賞處,可以登臨眺望整個機場景觀,以及機場周圍的城市輪廓。顯然郎朗他們不知道這個遊覽處,就是知道,他們也不會有閒心去的。他們要抓緊時間去取行李。
趙屏國老師顯得神清氣爽。他穿戴講究,走到哪裡都是一副興致勃勃的樣子,看上去顯得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得多。他帶了一台小型攝像機,隨時隨地拍攝著。鏡頭上凡是出現他的形象,都是滿面笑容,滿面欣慰。其中不乏透出那種久違的中國人踏入西方世界的新奇與欣喜。從神情到衣著,都具有那種解脫的輕鬆和愉悅,與郎國任的心事重重狀態恰好形成強烈的反差。
如今,我所以能夠有幸捕捉到當時他們一行進入德國後的場景,包括許多細節,這得感謝趙老師。他把他的學生郎朗第一次走出國門的情景逐一拍攝下來,這肯定是一部有價值的資料。如果不是趙老師的細心,哪能記錄下這么多生動的場景。
摘錄(二)
無業人員
走出收票口的郎國任往肩上聳了聳背包,剛剛出了一口悶氣,就有人迎上來,以一種令人懷疑和厭惡的熱情拉他爺倆住店,拉他坐計程車。郎國任以一位警察的本能予以拒絕。可這邊拒絕了那邊又湧上來。他只能加倍提高警惕,儘快離開廣場。他從廣場的右邊圍欄處繞出去,就到了捷運口。捷運口很是髒亂,擺小攤的還有乞丐照例令他的神經無法鬆弛。郎朗頭一回到北京,看什麼都覺新奇。
特別是看到躺在地上的乞丐覺得非常新奇。他這般小小的年紀對北京的感覺是從書本上和電視裡得到的,雖然不如父輩當年那么神聖,但是,畢竟是首都,怎么也有這么髒的乞丐?怎么沒有人管呢?他正遲疑著被父親拽走了。他離開時,還回頭望了一眼。
汽車朝北京郊外飛駛,北京顯然比瀋陽更有春天的氣息,陽光燦爛,路邊的樹木亭亭而立,遠處的田野在春天的陽光中升騰起一片熱烈的春潮,令人心胸激盪。第一次遠離家園出外闖蕩的少年郎朗禁不住漲滿豪情。他在座位上一刻也不肯安生,一會兒跪著,一會兒站起來,他想像著父親將要把他帶去的新家會是什麼樣子。從父親緊鎖的眉頭和沉默的狀態上,他猜想那裡的條件肯定糟糕透了。
郎朗的新家在11樓。兩室一廳,哇,這么寬敞明亮得多少租金呀?他問父親,父親說你小孩子管這些事幹嘛,你好好彈琴就是了。但是,郎朗偏要管,偏要問個明白。租金其實很便宜的,每月150元。如果現在到北京豐臺區租這樣的房子,那租金就得翻幾番了。不過,這150元的月租金對於郎國任來說也不算輕鬆。畢竟他辭去了工作,這意味著以後的日子他們父子在北京將只有花銷而分文沒有進項。郎國任這幾年為了培養郎朗花銷不小,積蓄所剩無幾。他見兒子一定要刨根問底,便把租金多說了兩百元。唉呀媽呀!這么多錢呀?我可得好好彈琴了!郎朗這么一叫喚,當父親的心裡邊就舒坦多了。
東西從車上卸下來,得從電梯上行到門樓。來往的人用一種異樣的眼神注視著他們父子。這座大樓裡邊的住戶成分比較複雜,也有不少外地人在此租房子住。租房子的人大多是涌到北京做買賣的,而像他們父子這樣來學琴的,這裡的人還是聞所未聞。那種異樣的眼神開始讓他們父子很不習慣,那是一種審視,一種懷疑還是一種輕蔑?抑或兼而有之?無形中這一切都構成了壓力,也都構成了動力!一貫說上口,一貫盛氣凌人的特殊警官,看你如何來適應這片並不友好的環境。
孩子的確夠累了,從他貪睡的樣子就可以看出來。他的嘴角繃得緊緊的,好像在夢中還和誰較勁。兒子在爭強好勝這一點上非常像他,甚至比他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正是最讓他喜歡之處。但是,他無論對兒子多么滿意,卻從來不流露出來。兒子到了哪裡都能得到一迭聲的誇獎卻獨獨得不到他這位當父親的誇獎。為此,兒子耿耿於懷。每次彈琴都調動了渾身的解數,都用了最大的力氣,可父親總是沒有喜悅的表情,頂多說句還行吧!然而,郎朗一直是在別人的羨慕和讚揚聲中成長的,他怎么受得了"還行"這種評語呢?他被激發起更大的幹勁,他一定要讓父親承認他彈得最好。他甚至在夢中都在和父親叫勁,看他夸不誇獎。郎國任對兒子的要求確實嚴格得近乎嚴酷。他總能挑剔,也總能挑出毛病來。有的曲子三遍五通他也不放行,還得再摳一遍。有時氣得兒子哇啦哇啦地喊叫一通,宣洩一通,卻還得老老實實地接著父親的要求再彈一遍。媽媽在家的時候,兒子可以和媽媽撒嬌,媽媽不在時,兒子卻找不到撒嬌的人了。在郎朗成長的道路上,郎國任這位天天與兒子耳鬢廝磨的嚴父,居然從未親過兒子。郎國任對兒子表達感情的方式也是獨特的,只能是在兒子睡熟了的時候,他默默地守著兒子,多看他幾眼,給他掖掖被子,撫摸一下他的小腳。這一切,他絕不會讓兒子知道。帶好兒子太不容易了,得有極強的克制力,永遠不誇他不鼓勵他不行,可輕易誇他更是不行。不讓他怕你不行,而讓他太怕你了事情更糟。尤其郎朗這種聰明伶俐的孩子。最難忘的是兩年前,他帶著郎朗去太原參加的全國首屆少兒鋼琴比賽的情景。
因為是首屆全國舉行這樣的比賽,所以,全國各地都非常重視,參賽的選手也夠多了。瀋陽不同年齡組的都有選手參賽。比較出名的有邢軍、杜瑩,她們都比郎朗大,郎朗當時只有七歲,在瀋陽寧山路國小讀一年級。他是那種人小志不小的孩子,他到了太原就是抱著得獎的決心來的。
比賽在太原少年宮進行,競爭異常激烈。當時的郎國任還不很熟悉全國各地的少年選手情況,他只知道上海和北京厲害。他沒有抱著一定要奪冠的心,但是,他覺得郎朗也應該在全國排上上名次。另外,他也是想來見識見識,看看北京上海的孩子究竟有多么厲害。
和郎朗在一個組競爭的有上海的王魯,還有北京的李端。這兩個孩子在當時都很受寵,也都頗有名氣,而來自東北的郎朗卻不為人所知。在鋼琴評審們的眼中,東北還是塊鋼琴的荒地,雖然"文革"期間不斷地有上海的鋼琴家到那裡播火種,比如朱雅芬、金石等人,但是,東北的孩子仍然無法真正進入評審們的視野。郎朗當時的程度是彈到了740,不過比賽規定不允許彈740,只能彈299。於是,郎朗那次彈了卡巴列夫斯基和中國曲子《紅星閃閃》。這兩首曲子都是著名教授朱雅芬一手教出來的。朱雅芬有自己一套獨特的教學法。她不僅注重技巧,她更注重音樂。在技巧與音樂的融匯上她更是能夠恰到好處地把握著郎朗的內在激情。而七歲的郎朗正是有著一種小老虎的衝勁兒,只要往鋼琴前一坐,不管在什麼地方,也不管是什麼規模的比賽,哪怕是李斯特坐在台下打分,他也不會有半點怯懦,相反,他會因此更加激發出精神頭兒。他是那種越比賽越競爭越人多越來勁兒的那種孩子。他特別願意表現自己展示自己。
郎國任一直挺後悔那天不該讓郎朗穿那條背帶褲子上台。郎朗彈到激情澎湃時,渾身的勁頭兒都調動起來,正要大顯身手時,那背帶卻不合時宜地從兩個肩頭滑脫下來,束縛了他那激情的胳膊,想揮灑卻伸不開,這不能不影響演奏效果。這是十分令人遺憾的。然而,儘管如此,郎朗彈得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不但音樂感覺好,而且一個音也沒錯,他贏得了熱烈的掌聲。台下聽眾不少交頭接耳,認為這個小孩彈得好。那次比賽取前六名:一等獎1名;二等獎2名;三等獎3名。鄰國任一個不漏地看了參加決賽的10名小選手演奏之後,心裡邊有底了。他覺得郎朗肯定可以進入前六名。如果不是背帶礙事,他甚至會認為郎朗可以競爭第一。宣布比賽成績時,郎朗情緒很高地坐在父親旁邊,他自信肯定榜上有名。他手裡拿著一支原子筆,往自己支起的光腿上刎著玩。他劃什麼呢?父親隨便掃一眼,發現他寫的是自己的名宇"郎朗",他寫得一筆一畫很認真。父親當然明白兒子的心思,心裡一下子湧入了一股暖流。第一名被上海選手王魯奪得,第二名是北京的李端,第三名--主持人在公布名次這段時間裡,他寫得滿腿都是郎朗。可是,他寫得再多,前六名公布完了也沒有聽到一聲郎朗。當父親的心禁不往怦然而動。這時的郎朗突然停下了筆,只聽主持人接著往下念獲得優秀獎的名單。這回,頭一個就是郎朗。就是說郎朗的名次排在了第七名。郎朗愣頭愣腦地說:不是吧?
父親說咋不是呢?他和兒子一樣的心情。畢竟是成年人了,遇事再激動也不至於當即爆發,可是,郎朗卻不然。他一下子蹦起來,郎國任一把沒抓住,他像頭小老虎,哇哇叫著沖向主席台。他邊跑邊喊叫:"太不公平了!憑什麼?憑什麼?"整個會場一下子靜下來,人們被這突如其來的喊叫弄得不知所措。"我不要優秀獎!我不要!"
"不合理!不公平!"郎朗不顧別人的阻攔,衝到主席台下對台上的評審們揮著小拳頭憤怒地喊叫。喊著喊著,他竟大聲哭起來。他像受了天大的委屈。觀眾席上一片騷動,嗡嗡的議論聲越來越高。郎國任奔過去,拉住了又蹦又跳的兒子,硬是把他拖拽出去。
郎朗哭得真傷心。圍觀的小選手紛紛勸郎朗,別哭了,有個石家莊的小選手勸他說,我不也是得了優秀獎嗎?你看,我都沒哭。下次爭取嘛!郎朗瞪他一眼:你跟我比?你彈的什麼玩藝?
優秀獎也要頒發獎品,念到郎朗的名字時,他拒絕上前領取。當一位小朋友替他把獎品取回來,遞給他時,他抓過來就狠狠地摔在地上。獎品是一隻玩具小狗。那隻天真無邪的金絲毛小狗在地上打了個滾兒,黑亮的眼珠定定瞅著他,仿佛對他表示抗議。郎朗余怒未消地把它抓起來又一次摔到了地上。後來,還是父親幫他把這隻小狗撿起來放好。
郎國任是個有心人。他將小狗帶回家,就擺放在屋子裡最醒目的地方,那就是鋼琴的上方。每大郎朗彈琴時都可以看到它,再不喜歡再想躲避都是不可能的。他要讓這隻小狗成為一個教材,時時激勵兒子,讓他發憤,讓他別那么輕易忘記太原的委屈。
這篇作文被當成範文在班級念了,老師非常喜歡,父親更是喜歡。他不僅看到了兒子在彈琴上的進步,而且看到了他在思想上的進步。小狗成了他最喜歡的玩具,每天他得看上一眼。此番來北京,他有好多東西沒有帶來,但是,他卻把這隻小狗帶來了。當郎國任一掀箱蓋看到這隻金色毛髮的小狗時,感慨良久。他想到了兒子的那篇作文,他默默祝願兒子能夠實現理想,考上中央音樂學院附小。到那時,讓這隻小狗好好看看郎朗的成功。
想到成功總是給人以力量的,郎國任堅信兒子通過一年的學琴,明年肯定能考取小五。他們不會白來的。在進駐北京的頭一個晚上,郎國任想了很多,他想得最多的就是郎朗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的"小五"。郎朗跳著腳喊著,越跑越快。他在後邊追。車一輛緊隨一輛,開得非常快,就帖著郎朗身邊飛馳。眼見一國內盛滿東西的大解放朝郎朗橫衝過去,就要碾壓著郎朗了。他大叫一聲:郎朗
於此同時,響起了敲門聲。郎國任跌坐而起,神情還沒有能夠從夢境中甦醒過來。敲門聲更大更真實了,郎國任下地問是誰?他以為一定是有人走錯門了,否則,怎么會有人一大早就來敲門呢?外邊的人告訴他是派出所和街道的,登門是要辦臨時戶口。
郎國任把門打開了。一位老太太,身後跟著一位穿警服的年輕人。老太太還算客氣,沖他微笑著介紹了身邊的警察是派出所的所長。那年年輕警察卻不那么友好,一進門盯了他一眼,那神情就不大對勁兒。然後,就開始盤問他到北京乾什麼來了。問得很細,還問他什麼工作,他將辭職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如實稟告。都問完了,這才遞給他一張表格讓他填寫。他接過表格看了看,坐下來便填寫。他急著快點填完好把他們打發走,因為他還得為兒子做早飯,還得早點離家雲音樂學院找叢老師上課。
他在表上填寫自己的名字,還有籍貫,從何而來,家庭成員之類,但是,在往下的那個空格里,他難住了,遲遲不知如何下筆,那個空格是要填也的工作職業。他是警察,可那已經成了過去,那么現在填什麼?填陪同兒子學鋼琴?他只好問所長如何填。所長說得非常輕鬆:填無業人員。
"無業人員"這四個字從這位陌生的派出所所長的嘴裡吐出來,令他極不舒服。當過警察的人再明白不過了社幾字的內涵。他拿筆的手開始哆嗦了,半天不願往下落。好不容易才把這四個字寫在那上面,結果字跡不工整,有的筆劃居然還從那個規定的框格里擁擠出來了。
作者介紹
劉元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常務理事、鴨綠江文學月刊社常務副主編、編審。 1988年孤身闖過黃河源,1995年隻身奔赴柴達木,1995年去歐洲考察建築,遂有了散文集《西部生命》、《上帝廣場》。 《黑馬、白馬》、《黃河悲歌》是以前的獲獎作品。他在鋼琴和建築領域均有著述--長篇紀實《中國鋼琴夢》、散文集《表述空間》。 曾榮獲"遼寧優秀青年作家"稱號。
劉元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常務理事、鴨綠江文學月刊社常務副主編、編審。
1988年孤身闖過黃河源,1995年隻身奔赴柴達木,1995年去歐洲考察建築,遂有了散文集《西部生命》、《上帝廣場》。
《黑馬、白馬》、《黃河悲歌》是以前的獲獎作品。他在鋼琴和建築領域均有著述--長篇紀實《中國鋼琴夢》、散文集《表述空間》。
曾榮獲"遼寧優秀青年作家"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