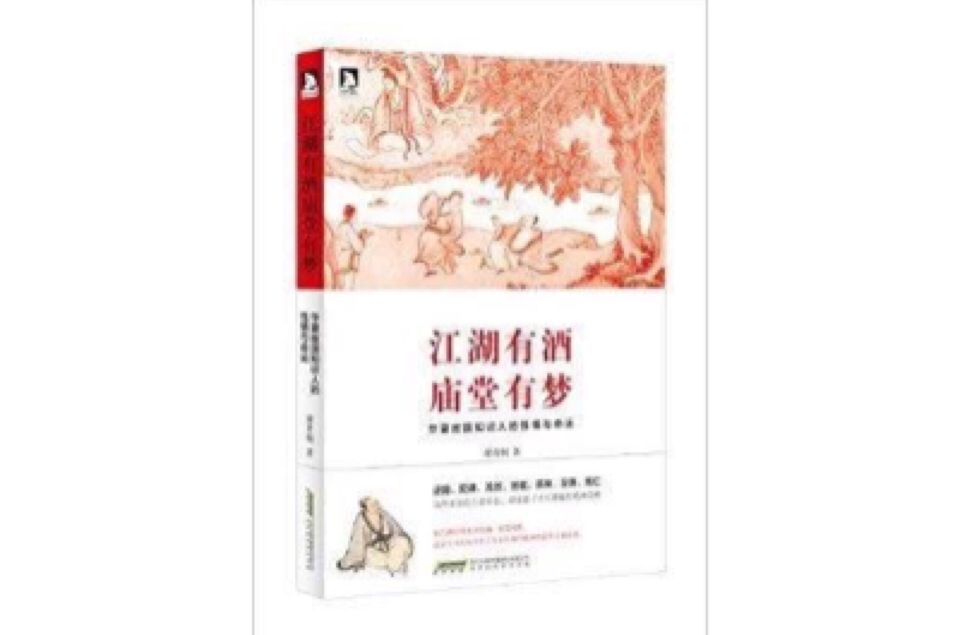《江湖有酒,廟堂有夢——華夏故國知識人的性情與命運》,作者媒體人謝青桐以通俗活潑的文筆,集通俗敘事和學術厚度為一體,以獨特的文史視角,從哲學、歷史和人性的層面,再現23位中國古代文人士子跌宕起伏的生命軌跡和豐富飽滿的生命內涵。滌盪種種“光環”或“陰影”,恢復其歷史與人性的真相。全書客觀、真實、寬容的評述,不同於一般的人物評傳,而是全景式地抒寫了中國古代士人群體在入世與出世之間取捨、徘徊和掙扎的曲折命運,呈現出在儒道釋互補的中國文化精神體系中,這些文藝大師們在心性信仰、人生意境、文藝創作中閃耀出的奇麗火花,同時更呈現出他們在遭遇現實困境擠壓和面臨歷史情境衝突時“化苦難為神奇”的奪目光芒。作者嘗試著從中國歷代名士的角度來勾畫歷史與文化的脈動,以這些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相關聯的個體生命的演進,還原歷史與文化發展的真況。所有篇章融文史哲於一爐,同時也注入了作者作為一個生活在當今時代的文化人的見解和價值觀,是當代知識分子實現歷史“穿越”,和古代文化大師進行“神交”的一本優美精細而大氣磅礴的人文讀物。
基本介紹
- 書名:江湖有酒:廟堂有夢
- 類型:傳記
- 出版日期:2014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807695783
- 作者:謝青桐
- 出版社: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 頁數:221頁
- 開本:16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23位文人,23種性情,23個理想,23類命運。
重溫23個人生軌跡,追索知識人的人格與精神
從文人士子的角度,勾畫文化的脈動;以個體生命的演進,還原歷史的真況
滌盪既往意識的“光環”與“陰影”,恢復歷史與人性的真相。
重溫23個人生軌跡,追索知識人的人格與精神
從文人士子的角度,勾畫文化的脈動;以個體生命的演進,還原歷史的真況
滌盪既往意識的“光環”與“陰影”,恢復歷史與人性的真相。
作者簡介
謝青桐,資深傳媒人,專欄作家。1995年起從事媒體工作,先後任報刊記者、編輯和主編。在《新京報》、《南方都市報》、《東方早報》等國內外報刊及新媒體刊發大量專欄文章,影響廣泛。曾在美國、澳大利亞、法國、日本從事專題採訪及訪學研究。
媒體推薦
從文人士子的角度,勾畫文化的脈動;以個體生命的演進,還原歷史的真況。
滌盪既往意識的“光環”與“陰影”,恢復歷史與人性的真相。
滌盪既往意識的“光環”與“陰影”,恢復歷史與人性的真相。
圖書目錄
序言:在政治、良知與美感之間
任自然
嵇康:推上斷頭台
阮籍:曠野的沉默
陶淵明:我的田園我做主
在巔峰
李白和杜甫:大唐斷背考
蘇軾:大宋達人秀
不羈的心
王翰:我的輕盈的夜光杯
杜牧:青樓夢好
李商隱:相見時難
柳永:井水邊的流傳
徐渭:瘋的藤
嘆浮雲
庾信:他鄉客
王之渙:失業在開元年間
王昌齡:西出長安
蔣捷:元朝樹蔭下
侯方域:桃花扇底是流離
志難酬
屈原:香草潔癖
歐陽修:醉翁之意
陸游:臨安劍和雨
辛棄疾:殺無赦
空門靜好
王維:北國紅豆
白居易:墓里有雙相思的鞋
曹雪芹:覺悟紅樓
任自然
嵇康:推上斷頭台
阮籍:曠野的沉默
陶淵明:我的田園我做主
在巔峰
李白和杜甫:大唐斷背考
蘇軾:大宋達人秀
不羈的心
王翰:我的輕盈的夜光杯
杜牧:青樓夢好
李商隱:相見時難
柳永:井水邊的流傳
徐渭:瘋的藤
嘆浮雲
庾信:他鄉客
王之渙:失業在開元年間
王昌齡:西出長安
蔣捷:元朝樹蔭下
侯方域:桃花扇底是流離
志難酬
屈原:香草潔癖
歐陽修:醉翁之意
陸游:臨安劍和雨
辛棄疾:殺無赦
空門靜好
王維:北國紅豆
白居易:墓里有雙相思的鞋
曹雪芹:覺悟紅樓
序言
序言:在政治、良知與美感之間
一
中國古代知識人的歷史性活動區域,是在政治、良知與美感之間。
中國傳統知識人崇尚絕對理性的完美,所以他們的從政方式必然是帶有浪漫的文藝色彩,而最後也只有以傳統文人慣有的悲情和幻滅的方式結束,但卻又總是產生始料未及的美學效果,抵達意想不到的哲學高度和倫理深度。
在華夏故國,中國古代知識人以士人、文士的面目活動於社會歷史的前台或幕後。無論是入仕為官,還是出世為隱,中國傳統知識人的性情體系是一套始終如一的精神價值系統。儒家的執著與厚重,道家的獨立與飄逸,佛禪的空靈與覺悟,千百年間,飽經憂患,遍嘗苦難,歷盡滄桑。佇立於綿綿不斷的群山之巔,回眸天下蒼生時,目光里閃爍的是儒者的仁厚、老莊的智慧和佛禪的慈悲。這低調而深刻的目光,恰恰就是中國知識人持久的風骨,道統與美感共存,國家與個體兼濟,政治理想與自然生命並行,濟世情懷與獨立人格同構。
《論語》里記載曾子的言論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中國士人在學習禮樂技能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追求終極的價值準繩。道,即是士人自身人格修養的理想指向,也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標準。士人以道自任的精神在儒家那裡表現得最為強烈。“篤信善學,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這些社會和人生的基本信條,被古老的中國先哲言簡意賅地指明。道,由此而成為被中國知識人苦苦實踐和堅守的精神風骨。
作為中國古代知識人的士人群體,被賦予載道、弘道乃至殉道的道德義務、政治責任和人生使命,其呈現出的獨特精神風骨就是以身承道,這是中國古代知識人風骨的第一個層面。士人風骨的現實表現,就是以道為價值標準來處理與自身行為、與歷史、與現實政治權威的關係。在諸多關係中,最能體現士人精神的是他們與政治權威的關係。道德部分的“道”和政治權威方面的“勢”出現了尖銳的衝突,面對“勢”如何護“道”,是衡量士人品格的一個標準。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在屈原、嵇康、陶淵明、杜甫、歐陽修、蘇軾、陸游等一系列中國知識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文人士大夫在積極入世與現實社會中理想得不到實現的抗爭中產生了堅貞不屈、頑強鬥爭的性格以及優秀知識分子和仁人志士追求真理、奮發進取,為實現理想而不懈努力的高風亮節、錚錚鐵骨。“風骨”正是這種抗爭精神在人生境界上、在文學審美理想上的體現,如劉勰評屈原的作品,以之“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以熔經意,亦自鑄偉辭”。
作為華夏士人性情體系核心力量的風骨,發端於先秦,成於南北朝,卻盛行於唐宋,這與唐宋士人滿腔建功立業的強烈豪情有關。在這種積極入世的精神指導下,李白的“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杜甫的“三吏”、“三別”,歐陽修的“窮而後工”,蘇軾的“有為而作”,以至明清標舉的風骨格調都論證了劉勰的“風清骨峻”不只是一種藝術美,更主要是一種人格美在生命境界和文學作品中的體現,它就是中國古代知識人高潔的情操、剛正不阿的骨氣的體現。
二
書中記載的這些風姿綽約、才情高拔的文人士大夫,一個個都是人中翹楚,他們是官員,是文士,是書生,是學者,是詩人,而根本上,是真正的知識人,一生在權力、良知與美感之間遊走徘徊。他們時而被擁戴,成為主流文化精英,高居時代文化的巔峰和領袖地位,時而被貶謫荒地、放逐江湖,迅速淪為被邊緣化的罪臣。在跌宕的人生命運中,他們驚人的相似之處在於,都是循著共同的心靈根脈走上歷史和人生的前台,青少年時代用中國傳統的儒家道德理想啟蒙自我,確立自己的教養體系和人生目標。陶淵明的“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牧的“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都是無比美好的願景;可一旦“入世”,複雜的仕宦環境和真性情立即發生衝突,政治和人性的艱難險阻與儒家的價值信條隨即發生牴牾。個人的弱點,歷史環境的缺陷,現實利益的糾結,個體與集體的矛盾,總是把熱誠的濟世願望和動人的家國理想一次次化作滿腔悲情。
當這些儒者們執著而莊嚴的家國夢破滅,他們的精神世界退向老莊,退向佛禪,退向自然,有的也退向青樓。仕與隱、進與退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永恆的宿命和持久的主題,由仕隱衝突而產生的悲劇美學成為中國古代知識人性情體系的第二個層面。
這群中國古代的知識人,從廟堂退向江湖,從權力退向審美,從集體退向個人,從公域退向私域,他們終於獲得了快樂的解放,他們最有能力用柔弱的心靈釋放天地間最強大的力量,支撐大道,擔當傷悲,背負苦難,就像到洛陽城外打鐵的嵇康,辭官歸故里的陶潛,在黃州墾荒種地的蘇軾,散淡尋常巷陌的柳永,於潦倒困苦中幡然覺悟的曹雪芹。既然這世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剪不斷理還亂,翻雲覆雨不可測,既然在歷史的滾滾車輪下,個體生命只是可憐的螳臂當車的弱者,那就把炙手可熱的官印交出,把威風凜凜的紗帽摘下,他們抱著古老的木琴走進後院,也走進自己的內心。中國歷史上少了一名小吏,多了一位大師。
幾千年來,中國古代文人學士自然地形成了非仕即隱、非隱即仕的生存方式,致力於“內聖外王”的儒家文化一向被認為是積極入世的,因此,古代隱士文化多被歸於道家文化的影響,儒家“進則仕,退則隱”的行為模式也被歸於儒道釋互補的結果。事實上,儒家思想本身就包含了進退兩個方面,“進則仕,退則隱”在儒家隱逸文化內部是自給自足的,未必外借於道家消極無為的純粹逃逸,這種“身隱心不隱”的仕隱觀,也代表中國不得志之文人的普遍情結。
江湖有酒,廟堂有夢。在儒家的人生態度里,隱逸在更大意義上是與待時而動的曲折進取聯繫在一起的,所以這不是一種精神上的放鬆,而是另一種形式的緊張參與。儒家的隱逸既是反抗的方式,也是待時而動的權變,因此在更大的意義上,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在殘酷的政治現實與士人的人格天地之間開闢了一個富有彈性的空間,這樣生命就不會因陷入死角而呈現絕望狀態,東山再起就成了普遍期待。事實上,孔、孟等先哲,雖然基本上以布衣終老,但他們的一生甚至包括生命的最後時刻,都沒有完全放棄對現實政治的關懷和投入。他們不僅在理論上奠定了儒家隱逸思想的底蘊和基調,而且本身也成為一種範式。
三
但是,我們又不能不看到,老莊和佛禪對中國知識人的人格影響是巨大的,也是深遠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儒道釋的心理互補機制,是成就中國知識人文化心理結構的關鍵機制,也是被迫選擇隱退或者主動尋求隱逸的中國士人風骨的哲學淵源和美學基礎,它給多情重義的中國士人帶來的是身心的解放、生命情調的舒展和文藝審美的風流。
宦海浮沉中,老莊、佛禪對士人的精神助益至關重要。他們常常能于山水的靜默觀照中獲得清靜圓融的體悟,山河大地無非自然,溪聲浪語無非佛法。生死枯榮,月圓月缺,法輪常轉,豈分晝夜。希望、亢奮、淒冷和踟躕,長時間的交替更換,如環無端,不知所終,也促使他們去領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去探索在紛擾爭鬥的社會關係之外個體生命存在的目的、意義、價值。這時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已與知識人的現狀經歷形成巨大反差,他們所效忠的朝廷和君王一次又一次把他們拋向痛苦的深淵。政治、功名、富貴只是一場幻夢,他們只有拿莊禪哲學來慰撫自己受傷的心性。
在中國知識人性情體系的第二個層面中,現實功利升華為政治悲情和文藝審美,向外擴散的政治作用力轉化為向內聚合的生命情調,性情在質態上呈現為風流與風雅的人生情境。士人們領悟到了有限中的無限,感受到了現實、現世、現象背後的孤獨、無常、虛妄與荒誕。這種悲劇哲學精神在他們的詩文中所體現出來的是一種對儒家的功利實現、道家的化入自然、佛家的彼岸解脫均無所待,更多的是他們否棄了生活的終極目的的審美特色。來自這些古典知識分子身心中被壓抑的強大生命力和非凡激情,轉化為審美活動中美不勝收的文章和詩行,華章璀璨,文脈深厚,一代又一代,從碑刻銘文到紙帛黃卷,隱退的文人士子們留下斑駁而綿密的文字,通過這些文字,他們究竟想退守何方呢?
“烏托邦”式的“桃花源”,晴耕雨讀的田園生活,支撐著陶淵明一生的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他特別推崇顏回、黔婁、袁安等貧士,要像他們那樣努力保持品德節操的純潔,決不為追求高官厚祿而玷污自己。他並不是一般地鄙視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也考慮貧富的問題,安貧和求富在他心中常發生矛盾,但他能用“道”來平衡,“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而那些安貧樂道的古賢人,也就成為他的榜樣。他借著“自然”的哲學躲開了人在社會中的自由這個根本問題。他在泯去後天世俗薰染後以求返歸一個“真我”,在他構造的“桃花源”中實現一種藝術化的人生。
蘇軾的《前赤壁賦》開篇展現的是一幅逍遙遊樂圖:清風明月,助人雅興,舉酒頌歌,憑虛御風,宛若仙人。這與莊子《逍遙遊》中所展現的場景頗為相似。這種情景讓人覺得心境安閒,物我和諧,與道家“虛靜”理念相吻合。蘇軾面對逆境,以道家的無為思想特別是莊子的《齊物論》涵養心靈,他用超然的智者心態,運用道家的自然觀、宇宙觀進行自我寬慰:“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對生命濃烈的熱愛之情,對功名狂熱的進取之心,對國家執著的愛戀之火,在冷靜、熄滅之後,化為“緣起性空”的輕煙縷縷。濃情淡去,深愛消融,這是一個由愛向空的歷程,這是一個美學和哲學上的愴然轉身,這是一個層層蛻變的覺悟過程。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行至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王維自信一顆禪寂的內心就足以驅散世間紛擾,一門一戶就足以從精神上隔絕喧鬧紛逐的人世。他的詩總是滲透著這種空性,不管是“暮雨空山”,還是“空山新雨”,到處都充滿著天真靈性之美,詩人在自然的融合之中看空了外在之相,也看空了內在之心。正如王維自己所說,“色空無得,不物物也”。
在佛家不二精神的啟示下,蘇軾悟到了人生的空幻,並在作品中多次表達了對人生虛空的感受,但他並未執著於空而否定人生。儘管他在詞里寫過“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但他從未真正做到離棄人世,而是始終在不入不出之間,超越有無之境,游於物之外,無往而不樂。也正因為如此,他才在坎坷的人生中“一蓑煙雨任平生”,出離“風雨”和“陰晴”二邊,達到“也無風雨也無晴”的不二境界,實現了人生審美化的超越。從這一點上來說,蘇軾更能代表宋元以來吸收了佛學禪宗的中國哲學和華夏美學。
到了曹雪芹,《紅樓夢》第一回就點明:“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佛教將世間萬物(佛家叫作“大千世界”)稱之為“色”(泛指紅塵、物質的情慾世界),同時認為,世界萬物(色)只不過是萬物本體(空)瞬息生滅的假“相”(又稱色相),皆是虛妄,終屬虛空,因此“色即是空”。小說第118回中,有一段寶玉與寶釵討論“赤子之心”的對話。寶玉說:“那赤子之心有什麼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們生來已陷在貪嗔痴愛中,猶如污泥一般,怎么能跳出這般塵網?如今才曉得聚散浮生四個字。”一條苦難的人生之路,是一條執有的人生迷途。這條人生的迷途反過來卻成了自由從假回歸真的覺悟的人生之路。能找到生死的最終因緣是無明,便達到無無明之覺悟,即謂悟空。對曹雪芹和他的代言人賈寶玉來說,能找到自己究竟的情種和痴根便是悟空了。
對於書中描述的文人學士們來說,出仕與隱逸在他們的生命中交叉而過,分別勾勒了屬於自己時代的仕隱情結。在仕隱之間的天平上,有著不同的傾斜,有的重在仕,有的重在隱。隱中藏仕,仕中戀隱,或者仕中戀隱,歸依於隱,隱中藏仕。不同的傾斜從而造成不同的人生軌跡:前者從此成為“欲回天地”(李商隱《安定城樓》)者的楷模,後者則成為出世精神的象徵。但他們共同見證的是華夏文人道統精神體系中的絕代風骨。
這樣的絕代風骨,這樣的性情體系,時而厚重,時而飄逸。當士子的心靈天平傾向國家與政治時,風骨是深沉而凝重的;當他們的心性情懷轉向自然與宇宙時,風骨是自由而飄逸的。這樣獨立的風骨,進退自如的生命智慧和百折不撓的心理韌性,在全世界的知識分子品格中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當今人在公共媒體上津津樂道於歐洲知識分子起源、法國知識分子現象、民國知識分子群體等話題時,殊不知,豐碑早已聳立在中華文化的古老史詩里。
四
獨立的性情體系導致了獨特的命運軌跡。書中涉及的23人皆為中國古代不同時代、不同風格、不同類型的古代知識人,他們各自用既迥異又相似的人生遭際,撰寫了豐厚而深刻的心靈史詩。這些跨越不同歷史時空的文人士子,有的活得隆重,有的活得典雅,有的活得潦倒,有的活得沉痛,但不論屬於哪一種,都活得極其飽滿、極其純粹,這是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無法具備的精神特質,也是難以企及的靈魂高度,而恰恰又是這種在歷史的漫漫長河中消逝了的精神奇觀,對當代知識人具有深遠的啟示意義。
這組文章的特點,就是採用“新史記”的點評法,全景式、史詩化呈現23位中國古代名士一生跌宕起伏的生命軌跡。在當今諸多讀者無暇閱讀大部頭傳記的時代,讓讀者像看電影一樣,在一兩個小時內飽覽一位人物,閱盡其一生信息,理解古代士子的精神風骨和華夏道統文化的特質。這種“縱觀一生,全景呈現;邊講故事,邊做學問;視角全新,材料獨特”的寫法受美國《紐約客》雜誌新專欄的啟發,是近年來歐美文史讀物的一種風尚潮流,尤其受青年讀者喜愛。
從文人士子的角度來勾畫文化與歷史的脈動,以尋求中國文化精神的獨特之處,通過這些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相關聯的個體生命的演進,還原歷史與文化發展的真況,讓我和讀者一道實現歷史“穿越”,和古代文化大師進行“神交”。我歷經3年的研究和寫作工程,寫完這一系列人物,只是希望作出一種嘗試,滌盪既往社會意識形態、主流文史研究和文化思維定勢強加、附加給這些文人士子們的種種“光環”或“陰影”,恢復其歷史與人性的真相。3年多來,我潛心書齋,竭盡全力對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批文人士大夫作出客觀、真實、寬容的講述,在文獻選擇和價值判斷上力求尊重歷史、人生、審美的多義性和複雜性,通過對23位中國古代文士跌宕起伏的人生命運的重新梳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在抵禦人生困境、歷史困境時所產生的非凡的人格力量、生命韌度和文藝美感。
在這組文章中,我特別注重的是書寫中國古代知識人群體在入世與出世之間取捨、徘徊和掙扎的曲折命運,呈現出在儒道釋互補的中國文化精神體系中,這些文化大師們在心性信仰、人生意境、文學創作中閃耀出的奇麗火花,體現出他們在遭遇現實逆境擠壓和面臨歷史困境衝突時“化苦難為神奇”的奪目光芒。他們的一曲曲“悲歌”,是政治的悲歌、歷史的悲歌、人性的悲歌,更是哲學和美學意義上的悲歌。
退隱、貶謫、流放、挫敗、孤獨、沒落、死亡,這些都是看上去很弱的生命形態,最終卻成就了一座座奇麗的文化巔峰和不可攀越的精神海拔。在偉大的中華文明中,世間最強大的風骨一定是以最弱的方式呈現的,佛陀的淚,孔子的仁愛,孟子的惻隱,老子的玄淡,莊子的逍遙。這種“弱的哲學”是中國文化精神中最玄妙、最精深的部分。中國的知識人,用詩化的生命軌跡和詩性的文學篇章身體力行了“弱的哲學”、“弱的美學”,鑄就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外柔內剛的東方風骨。
強與弱的思辨多么有趣!在佛禪那裡,柔弱到“空”,強大到“空”。佛教中有一本經叫《圓覺經》,上面寫到:佛在菩提樹下悟出了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明。所以佛教全部學說的一切都是按照“空”這個主題來展開的。在動筆寫這組文章之前,剛回國不久的我專程去了一趟敦煌。在海外生活兩年之後,回歸東方文化的心態是親切而精微的,也是百感交集的。從印度孔雀王朝開始,在佛教傳播的洪流中,有一支從西域到達河西走廊,再由河西走廊傳入中原。這條與古代絲綢之路相融合的佛教傳播之路被稱為佛教的東傳。沿著這條路線,能看到古老的中國如何接納一種空前偉大的智慧的過程,這個交融的過程中,佛教與本土儒、道一旦合流,竟然就產生了可以征服宇宙間一切苦難的威力。
有了這股儒道佛互補合流之力產生的雄健瀟灑的東方風骨,中國古代士人就可進可退,可生可死,可榮可辱,可福可禍,就可以自由選擇。最弱的形態,卻產生一種始料未及、無所畏懼的堅韌力量。人生可進可退,而且進退不刻意。頭頂有一片“道”的星空,身後是一片山水田園。星空下的田園,哪怕孤獨一人。世界上,總有一種生活遠離苦難。
遙想中國古典歲月里的知識人群體,遙想他們曾經到達過的城市、山川和村莊,長江兩岸的香樟樹遮掩著古老的村落,上船啟程的地方就是離家的碼頭,去國離鄉多少年,在長安、在洛陽、在杭州,夢裡始終有那個香樟掩映的碼頭。他們的身影出現在雲繞霧繚的青山深處,清淨寂寥之域,魚影穿梭於深潭,花香飄揚於幽谷,他們單純地行走著,吟誦著,傾聽潺潺之水聲,拜謁中原或者江南的古剎。穿過紫竹林,登幾級台階,飲新茶,訪禪師,清香滿衣,天意茫茫。
一
中國古代知識人的歷史性活動區域,是在政治、良知與美感之間。
中國傳統知識人崇尚絕對理性的完美,所以他們的從政方式必然是帶有浪漫的文藝色彩,而最後也只有以傳統文人慣有的悲情和幻滅的方式結束,但卻又總是產生始料未及的美學效果,抵達意想不到的哲學高度和倫理深度。
在華夏故國,中國古代知識人以士人、文士的面目活動於社會歷史的前台或幕後。無論是入仕為官,還是出世為隱,中國傳統知識人的性情體系是一套始終如一的精神價值系統。儒家的執著與厚重,道家的獨立與飄逸,佛禪的空靈與覺悟,千百年間,飽經憂患,遍嘗苦難,歷盡滄桑。佇立於綿綿不斷的群山之巔,回眸天下蒼生時,目光里閃爍的是儒者的仁厚、老莊的智慧和佛禪的慈悲。這低調而深刻的目光,恰恰就是中國知識人持久的風骨,道統與美感共存,國家與個體兼濟,政治理想與自然生命並行,濟世情懷與獨立人格同構。
《論語》里記載曾子的言論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中國士人在學習禮樂技能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追求終極的價值準繩。道,即是士人自身人格修養的理想指向,也就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標準。士人以道自任的精神在儒家那裡表現得最為強烈。“篤信善學,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這些社會和人生的基本信條,被古老的中國先哲言簡意賅地指明。道,由此而成為被中國知識人苦苦實踐和堅守的精神風骨。
作為中國古代知識人的士人群體,被賦予載道、弘道乃至殉道的道德義務、政治責任和人生使命,其呈現出的獨特精神風骨就是以身承道,這是中國古代知識人風骨的第一個層面。士人風骨的現實表現,就是以道為價值標準來處理與自身行為、與歷史、與現實政治權威的關係。在諸多關係中,最能體現士人精神的是他們與政治權威的關係。道德部分的“道”和政治權威方面的“勢”出現了尖銳的衝突,面對“勢”如何護“道”,是衡量士人品格的一個標準。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在屈原、嵇康、陶淵明、杜甫、歐陽修、蘇軾、陸游等一系列中國知識人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文人士大夫在積極入世與現實社會中理想得不到實現的抗爭中產生了堅貞不屈、頑強鬥爭的性格以及優秀知識分子和仁人志士追求真理、奮發進取,為實現理想而不懈努力的高風亮節、錚錚鐵骨。“風骨”正是這種抗爭精神在人生境界上、在文學審美理想上的體現,如劉勰評屈原的作品,以之“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以熔經意,亦自鑄偉辭”。
作為華夏士人性情體系核心力量的風骨,發端於先秦,成於南北朝,卻盛行於唐宋,這與唐宋士人滿腔建功立業的強烈豪情有關。在這種積極入世的精神指導下,李白的“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杜甫的“三吏”、“三別”,歐陽修的“窮而後工”,蘇軾的“有為而作”,以至明清標舉的風骨格調都論證了劉勰的“風清骨峻”不只是一種藝術美,更主要是一種人格美在生命境界和文學作品中的體現,它就是中國古代知識人高潔的情操、剛正不阿的骨氣的體現。
二
書中記載的這些風姿綽約、才情高拔的文人士大夫,一個個都是人中翹楚,他們是官員,是文士,是書生,是學者,是詩人,而根本上,是真正的知識人,一生在權力、良知與美感之間遊走徘徊。他們時而被擁戴,成為主流文化精英,高居時代文化的巔峰和領袖地位,時而被貶謫荒地、放逐江湖,迅速淪為被邊緣化的罪臣。在跌宕的人生命運中,他們驚人的相似之處在於,都是循著共同的心靈根脈走上歷史和人生的前台,青少年時代用中國傳統的儒家道德理想啟蒙自我,確立自己的教養體系和人生目標。陶淵明的“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杜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牧的“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都是無比美好的願景;可一旦“入世”,複雜的仕宦環境和真性情立即發生衝突,政治和人性的艱難險阻與儒家的價值信條隨即發生牴牾。個人的弱點,歷史環境的缺陷,現實利益的糾結,個體與集體的矛盾,總是把熱誠的濟世願望和動人的家國理想一次次化作滿腔悲情。
當這些儒者們執著而莊嚴的家國夢破滅,他們的精神世界退向老莊,退向佛禪,退向自然,有的也退向青樓。仕與隱、進與退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永恆的宿命和持久的主題,由仕隱衝突而產生的悲劇美學成為中國古代知識人性情體系的第二個層面。
這群中國古代的知識人,從廟堂退向江湖,從權力退向審美,從集體退向個人,從公域退向私域,他們終於獲得了快樂的解放,他們最有能力用柔弱的心靈釋放天地間最強大的力量,支撐大道,擔當傷悲,背負苦難,就像到洛陽城外打鐵的嵇康,辭官歸故里的陶潛,在黃州墾荒種地的蘇軾,散淡尋常巷陌的柳永,於潦倒困苦中幡然覺悟的曹雪芹。既然這世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剪不斷理還亂,翻雲覆雨不可測,既然在歷史的滾滾車輪下,個體生命只是可憐的螳臂當車的弱者,那就把炙手可熱的官印交出,把威風凜凜的紗帽摘下,他們抱著古老的木琴走進後院,也走進自己的內心。中國歷史上少了一名小吏,多了一位大師。
幾千年來,中國古代文人學士自然地形成了非仕即隱、非隱即仕的生存方式,致力於“內聖外王”的儒家文化一向被認為是積極入世的,因此,古代隱士文化多被歸於道家文化的影響,儒家“進則仕,退則隱”的行為模式也被歸於儒道釋互補的結果。事實上,儒家思想本身就包含了進退兩個方面,“進則仕,退則隱”在儒家隱逸文化內部是自給自足的,未必外借於道家消極無為的純粹逃逸,這種“身隱心不隱”的仕隱觀,也代表中國不得志之文人的普遍情結。
江湖有酒,廟堂有夢。在儒家的人生態度里,隱逸在更大意義上是與待時而動的曲折進取聯繫在一起的,所以這不是一種精神上的放鬆,而是另一種形式的緊張參與。儒家的隱逸既是反抗的方式,也是待時而動的權變,因此在更大的意義上,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在殘酷的政治現實與士人的人格天地之間開闢了一個富有彈性的空間,這樣生命就不會因陷入死角而呈現絕望狀態,東山再起就成了普遍期待。事實上,孔、孟等先哲,雖然基本上以布衣終老,但他們的一生甚至包括生命的最後時刻,都沒有完全放棄對現實政治的關懷和投入。他們不僅在理論上奠定了儒家隱逸思想的底蘊和基調,而且本身也成為一種範式。
三
但是,我們又不能不看到,老莊和佛禪對中國知識人的人格影響是巨大的,也是深遠的,甚至是決定性的。儒道釋的心理互補機制,是成就中國知識人文化心理結構的關鍵機制,也是被迫選擇隱退或者主動尋求隱逸的中國士人風骨的哲學淵源和美學基礎,它給多情重義的中國士人帶來的是身心的解放、生命情調的舒展和文藝審美的風流。
宦海浮沉中,老莊、佛禪對士人的精神助益至關重要。他們常常能于山水的靜默觀照中獲得清靜圓融的體悟,山河大地無非自然,溪聲浪語無非佛法。生死枯榮,月圓月缺,法輪常轉,豈分晝夜。希望、亢奮、淒冷和踟躕,長時間的交替更換,如環無端,不知所終,也促使他們去領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去探索在紛擾爭鬥的社會關係之外個體生命存在的目的、意義、價值。這時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已與知識人的現狀經歷形成巨大反差,他們所效忠的朝廷和君王一次又一次把他們拋向痛苦的深淵。政治、功名、富貴只是一場幻夢,他們只有拿莊禪哲學來慰撫自己受傷的心性。
在中國知識人性情體系的第二個層面中,現實功利升華為政治悲情和文藝審美,向外擴散的政治作用力轉化為向內聚合的生命情調,性情在質態上呈現為風流與風雅的人生情境。士人們領悟到了有限中的無限,感受到了現實、現世、現象背後的孤獨、無常、虛妄與荒誕。這種悲劇哲學精神在他們的詩文中所體現出來的是一種對儒家的功利實現、道家的化入自然、佛家的彼岸解脫均無所待,更多的是他們否棄了生活的終極目的的審美特色。來自這些古典知識分子身心中被壓抑的強大生命力和非凡激情,轉化為審美活動中美不勝收的文章和詩行,華章璀璨,文脈深厚,一代又一代,從碑刻銘文到紙帛黃卷,隱退的文人士子們留下斑駁而綿密的文字,通過這些文字,他們究竟想退守何方呢?
“烏托邦”式的“桃花源”,晴耕雨讀的田園生活,支撐著陶淵明一生的安貧樂道與崇尚自然。他特別推崇顏回、黔婁、袁安等貧士,要像他們那樣努力保持品德節操的純潔,決不為追求高官厚祿而玷污自己。他並不是一般地鄙視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也考慮貧富的問題,安貧和求富在他心中常發生矛盾,但他能用“道”來平衡,“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而那些安貧樂道的古賢人,也就成為他的榜樣。他借著“自然”的哲學躲開了人在社會中的自由這個根本問題。他在泯去後天世俗薰染後以求返歸一個“真我”,在他構造的“桃花源”中實現一種藝術化的人生。
蘇軾的《前赤壁賦》開篇展現的是一幅逍遙遊樂圖:清風明月,助人雅興,舉酒頌歌,憑虛御風,宛若仙人。這與莊子《逍遙遊》中所展現的場景頗為相似。這種情景讓人覺得心境安閒,物我和諧,與道家“虛靜”理念相吻合。蘇軾面對逆境,以道家的無為思想特別是莊子的《齊物論》涵養心靈,他用超然的智者心態,運用道家的自然觀、宇宙觀進行自我寬慰:“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對生命濃烈的熱愛之情,對功名狂熱的進取之心,對國家執著的愛戀之火,在冷靜、熄滅之後,化為“緣起性空”的輕煙縷縷。濃情淡去,深愛消融,這是一個由愛向空的歷程,這是一個美學和哲學上的愴然轉身,這是一個層層蛻變的覺悟過程。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行至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王維自信一顆禪寂的內心就足以驅散世間紛擾,一門一戶就足以從精神上隔絕喧鬧紛逐的人世。他的詩總是滲透著這種空性,不管是“暮雨空山”,還是“空山新雨”,到處都充滿著天真靈性之美,詩人在自然的融合之中看空了外在之相,也看空了內在之心。正如王維自己所說,“色空無得,不物物也”。
在佛家不二精神的啟示下,蘇軾悟到了人生的空幻,並在作品中多次表達了對人生虛空的感受,但他並未執著於空而否定人生。儘管他在詞里寫過“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但他從未真正做到離棄人世,而是始終在不入不出之間,超越有無之境,游於物之外,無往而不樂。也正因為如此,他才在坎坷的人生中“一蓑煙雨任平生”,出離“風雨”和“陰晴”二邊,達到“也無風雨也無晴”的不二境界,實現了人生審美化的超越。從這一點上來說,蘇軾更能代表宋元以來吸收了佛學禪宗的中國哲學和華夏美學。
到了曹雪芹,《紅樓夢》第一回就點明:“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佛教將世間萬物(佛家叫作“大千世界”)稱之為“色”(泛指紅塵、物質的情慾世界),同時認為,世界萬物(色)只不過是萬物本體(空)瞬息生滅的假“相”(又稱色相),皆是虛妄,終屬虛空,因此“色即是空”。小說第118回中,有一段寶玉與寶釵討論“赤子之心”的對話。寶玉說:“那赤子之心有什麼好處?不過是無知無識無貪無忌。我們生來已陷在貪嗔痴愛中,猶如污泥一般,怎么能跳出這般塵網?如今才曉得聚散浮生四個字。”一條苦難的人生之路,是一條執有的人生迷途。這條人生的迷途反過來卻成了自由從假回歸真的覺悟的人生之路。能找到生死的最終因緣是無明,便達到無無明之覺悟,即謂悟空。對曹雪芹和他的代言人賈寶玉來說,能找到自己究竟的情種和痴根便是悟空了。
對於書中描述的文人學士們來說,出仕與隱逸在他們的生命中交叉而過,分別勾勒了屬於自己時代的仕隱情結。在仕隱之間的天平上,有著不同的傾斜,有的重在仕,有的重在隱。隱中藏仕,仕中戀隱,或者仕中戀隱,歸依於隱,隱中藏仕。不同的傾斜從而造成不同的人生軌跡:前者從此成為“欲回天地”(李商隱《安定城樓》)者的楷模,後者則成為出世精神的象徵。但他們共同見證的是華夏文人道統精神體系中的絕代風骨。
這樣的絕代風骨,這樣的性情體系,時而厚重,時而飄逸。當士子的心靈天平傾向國家與政治時,風骨是深沉而凝重的;當他們的心性情懷轉向自然與宇宙時,風骨是自由而飄逸的。這樣獨立的風骨,進退自如的生命智慧和百折不撓的心理韌性,在全世界的知識分子品格中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當今人在公共媒體上津津樂道於歐洲知識分子起源、法國知識分子現象、民國知識分子群體等話題時,殊不知,豐碑早已聳立在中華文化的古老史詩里。
四
獨立的性情體系導致了獨特的命運軌跡。書中涉及的23人皆為中國古代不同時代、不同風格、不同類型的古代知識人,他們各自用既迥異又相似的人生遭際,撰寫了豐厚而深刻的心靈史詩。這些跨越不同歷史時空的文人士子,有的活得隆重,有的活得典雅,有的活得潦倒,有的活得沉痛,但不論屬於哪一種,都活得極其飽滿、極其純粹,這是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無法具備的精神特質,也是難以企及的靈魂高度,而恰恰又是這種在歷史的漫漫長河中消逝了的精神奇觀,對當代知識人具有深遠的啟示意義。
這組文章的特點,就是採用“新史記”的點評法,全景式、史詩化呈現23位中國古代名士一生跌宕起伏的生命軌跡。在當今諸多讀者無暇閱讀大部頭傳記的時代,讓讀者像看電影一樣,在一兩個小時內飽覽一位人物,閱盡其一生信息,理解古代士子的精神風骨和華夏道統文化的特質。這種“縱觀一生,全景呈現;邊講故事,邊做學問;視角全新,材料獨特”的寫法受美國《紐約客》雜誌新專欄的啟發,是近年來歐美文史讀物的一種風尚潮流,尤其受青年讀者喜愛。
從文人士子的角度來勾畫文化與歷史的脈動,以尋求中國文化精神的獨特之處,通過這些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相關聯的個體生命的演進,還原歷史與文化發展的真況,讓我和讀者一道實現歷史“穿越”,和古代文化大師進行“神交”。我歷經3年的研究和寫作工程,寫完這一系列人物,只是希望作出一種嘗試,滌盪既往社會意識形態、主流文史研究和文化思維定勢強加、附加給這些文人士子們的種種“光環”或“陰影”,恢復其歷史與人性的真相。3年多來,我潛心書齋,竭盡全力對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批文人士大夫作出客觀、真實、寬容的講述,在文獻選擇和價值判斷上力求尊重歷史、人生、審美的多義性和複雜性,通過對23位中國古代文士跌宕起伏的人生命運的重新梳理,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在抵禦人生困境、歷史困境時所產生的非凡的人格力量、生命韌度和文藝美感。
在這組文章中,我特別注重的是書寫中國古代知識人群體在入世與出世之間取捨、徘徊和掙扎的曲折命運,呈現出在儒道釋互補的中國文化精神體系中,這些文化大師們在心性信仰、人生意境、文學創作中閃耀出的奇麗火花,體現出他們在遭遇現實逆境擠壓和面臨歷史困境衝突時“化苦難為神奇”的奪目光芒。他們的一曲曲“悲歌”,是政治的悲歌、歷史的悲歌、人性的悲歌,更是哲學和美學意義上的悲歌。
退隱、貶謫、流放、挫敗、孤獨、沒落、死亡,這些都是看上去很弱的生命形態,最終卻成就了一座座奇麗的文化巔峰和不可攀越的精神海拔。在偉大的中華文明中,世間最強大的風骨一定是以最弱的方式呈現的,佛陀的淚,孔子的仁愛,孟子的惻隱,老子的玄淡,莊子的逍遙。這種“弱的哲學”是中國文化精神中最玄妙、最精深的部分。中國的知識人,用詩化的生命軌跡和詩性的文學篇章身體力行了“弱的哲學”、“弱的美學”,鑄就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外柔內剛的東方風骨。
強與弱的思辨多么有趣!在佛禪那裡,柔弱到“空”,強大到“空”。佛教中有一本經叫《圓覺經》,上面寫到:佛在菩提樹下悟出了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明。所以佛教全部學說的一切都是按照“空”這個主題來展開的。在動筆寫這組文章之前,剛回國不久的我專程去了一趟敦煌。在海外生活兩年之後,回歸東方文化的心態是親切而精微的,也是百感交集的。從印度孔雀王朝開始,在佛教傳播的洪流中,有一支從西域到達河西走廊,再由河西走廊傳入中原。這條與古代絲綢之路相融合的佛教傳播之路被稱為佛教的東傳。沿著這條路線,能看到古老的中國如何接納一種空前偉大的智慧的過程,這個交融的過程中,佛教與本土儒、道一旦合流,竟然就產生了可以征服宇宙間一切苦難的威力。
有了這股儒道佛互補合流之力產生的雄健瀟灑的東方風骨,中國古代士人就可進可退,可生可死,可榮可辱,可福可禍,就可以自由選擇。最弱的形態,卻產生一種始料未及、無所畏懼的堅韌力量。人生可進可退,而且進退不刻意。頭頂有一片“道”的星空,身後是一片山水田園。星空下的田園,哪怕孤獨一人。世界上,總有一種生活遠離苦難。
遙想中國古典歲月里的知識人群體,遙想他們曾經到達過的城市、山川和村莊,長江兩岸的香樟樹遮掩著古老的村落,上船啟程的地方就是離家的碼頭,去國離鄉多少年,在長安、在洛陽、在杭州,夢裡始終有那個香樟掩映的碼頭。他們的身影出現在雲繞霧繚的青山深處,清淨寂寥之域,魚影穿梭於深潭,花香飄揚於幽谷,他們單純地行走著,吟誦著,傾聽潺潺之水聲,拜謁中原或者江南的古剎。穿過紫竹林,登幾級台階,飲新茶,訪禪師,清香滿衣,天意茫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