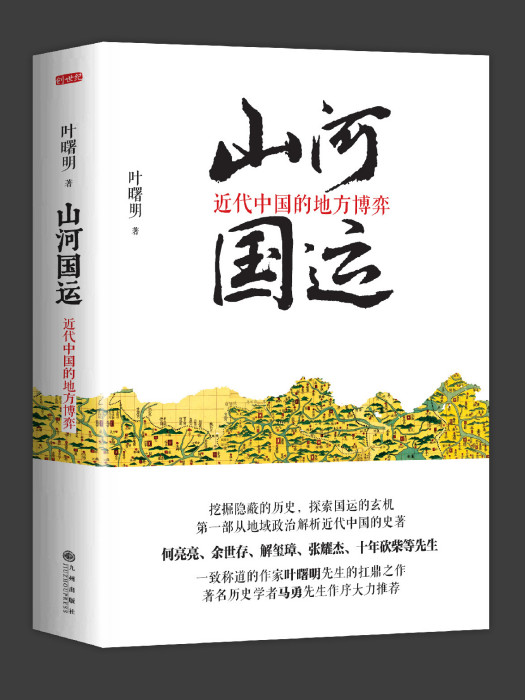作者簡介
葉曙明,作家,學者,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成績斐然。著有《大變局:1911》《重返五四現場》《中國1927·誰主沉浮》《國會現場》《草莽中國》等。代表作《山河國運》,建立了對中國近代史的一個新分析框架,於眾多相關著述中別樹一幟。
主要內容
這是一部角度獨特的中國近代史,始於太平天國運動,止於西安事變,生動地再現了晚清至民國的變遷。作者把社會政治文化形成及演變的原因,與地理環境、自然氣候、文化背景、族群心理,甚至生理原因聯繫起來考查,系統地從地域政治與文化的視角,重新解讀了近百年中國社會激盪與轉型的軌跡,令人耳目一新。
作品目錄
序言:從大歷史回望近代中國(馬勇)
引言:地域文化決定中國歷史
南方卷:異端與革命
第一章 反抗大清:一場民族革命
一、 洪秀全與曾國藩:南方的崛興
二、 依靠會黨的反抗運動
三、 會黨革命,能創造美好的世界嗎?
第二章 反抗北洋:髒水與孩子一起倒掉
一、 把政權交給袁世凱對不對?
二、 重蹈秘密幫會的老路
三、 南方的聯治運動的興與敗
第三章 贏了軍事 輸了政治
一、 向北方伸出橄欖枝
二、 與商人決裂:意味著放棄南方
三、 南方革命的退潮
北方卷:斬不斷的龍脈
第四章 帝都面孔:凝固與陰沉
一、 北方草莽與官僚
二、 恢復帝制的死胡同
三、 北洋實業的台前幕後
第五章 還政於清 輸得更慘
一、 參戰問題:北方亂象紛呈
二、 帝國的叫魂:年月日
三、 再造共和,還是贗品
第六章 民族主義與道德主義的標本
一、 吳佩孚:是華盛頓還是岳武穆
二、 沒完沒了的戰亂
三、 內聖外王幻覺的破滅
西方卷:固守著黃土高原
第七章 土圍子裡的皇帝們
一、 與文明的時差
二、 閻錫山:山西土老財
三、 馮玉祥:大鬧天宮的農民
第八章 逆淘汰:西北的介入
一、 黎元洪第二次引狼入室
二、 曹錕賄選:北洋潰敗的關鍵
三、 成則問鼎中原,敗則退回西北
第九章 南北相爭中的“漁翁”
一、 西北農夫如何謀取利益最大化
二、 南方、西北和東部鼎足而立
三、 東部擊退了西南
東方卷:在高原與海洋之間
第十章 夾縫中的奮鬥
一、 東部幫會的特點
二、 農民大聯合:西北與西南合作反蔣
三、 更廣泛的農民革命起來了
第十一章 儒家與基督
一、 在國際上試圖強硬起來
二、 白山黑水的淪喪
三、 輪到上海:東部財團的崩坍
第十二章 日落西方
一、 一個低效政府的艱難運作
二、 以空間換時間:東部的空間換沒了
三、 又回到了西北原點
結束語:歷史的餘音
作品試讀
第七章 土圍子裡的皇帝們
一、與文明的時差
在一望無際的荒原上,乾燥的熱風時而貼著山岡的脊背呼嘯而過,時而又捲起巨大的塵柱,向混濁的天空升騰而起。狹窄而乾涸的河床在赤色的土地上蜿蜒伸展,河岸兩側是一片荒涼,幾株營養不良、枝葉稀疏的喬木,在風中瑟瑟顫抖。
落日紅紅的,黯黯的,使每棵樹和向西的山坡都染上黃黃的顏色,愈往高處看,黃色就愈顯著,色調優美、渾厚,透著無限的蒼涼。在高曠的天空飄著幾縷淡淡的白雲,凝然不動,那幾乎沒有熱力的太陽在深邃的天空中發著光。
這是中華民族最初誕生的地方。
這裡是世界上最大的黃土高原,面積達四十萬平方公里,跨越山西、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河南等省區。
從歷史上看,它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搖籃,六千年前,太昊伏羲上觀天象,下觀地法,中觀萬物,畫出八卦圖像,成為中國文化思想的神髓;軒轅黃帝發明創製了舟車、文字、音律、醫學、算數、冕旒、衣裳、釜甑等等,以顯赫的文治武功,被後世尊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黃帝相傳都是西北人。
中國的古都多在西北。堯都平陽,舜都蒲板,禹都安邑,均在山西汾河下游一帶。周朝的首都設在陝西,而秦朝也是從西北東征中原,最終統一中國。自周以降,先後有十多個王朝在西北定都。中國文明的腳步,就是從黃河、渭水的八百里秦川開始,緩慢地走向東南沿海。
然而,儘管文明所到之處,就像春天一樣,令一切蓬蓬勃勃,生機盎然,迸發出巨大的活力,但它一旦走過,時間就好像停滯了下來,進化中止,漸漸衰落。在漫長的歲月里,黃土高原備受雨水侵蝕,溝壑交錯,塬峁起伏,舉步維艱,滿目荒涼。當文明已經走到了沿海地區,世界已進入了煤炭與蒸汽的時代,這裡卻依然“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除了大西北,中國沒有一個地方會如此完美地保存,五百年前的風貌,也沒有一個地方會讓人感受到人和土地的關係是如此密切。西北的工商業依然停留在非常原始落後的階段。西北有豐富的煤礦和鐵礦,但由於交通不便,即使開採出來,也不易運出去。
西北文化就像它的地理一樣,凝固、封閉,和土地緊密相連。人們靠土地生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亘古不變的循環之中,孳息不絕,進進不已。這裡是貧苦農民的地獄,是刀客和盜匪的樂園。和南方會黨不同,西北的刀客並非革命的同盟者,他們只是一群由破產農民嘯聚而成的破壞者和掠奪者。
西北人從來沒有改變這種狀況的欲望。相反,交通的閉塞倒成了他們保存固有文化傳統的有利條件。20世紀西方文明雖然像潮水一樣湧入中國,但在海拔一千五百米的黃土高原面前,也只能望“土”興嘆,徒呼奈何。
如果說中國北方確實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官僚文化,那么,它的發源地是在這片遙遠而荒涼的西北黃土高原。所謂以北京為核心的北方官僚文化,和植根於黃土高原的西北文化,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血統相承,一脈互通。
西北是沉默的,但是,它對中原影響之巨大,也許再過幾個世紀也無法磨滅。一曲“信天游”,就像周滅殷商,秦滅六國一樣,它將改變中國的命運。
西北一向是秘密幫會、教門橫行的地區,清代影響最大的收元教,主要就活躍于山西、陝西、河南一帶。據清雍正年間的統計,山西有白蓮教、混元教、混沌教、龍華會、皇天教等教門的流行;在豫西地區也有橋樑教、哈哈教、悟真教、大成教等五花八門的秘密教門,成為教案頻發的地區。
哥老會是下層社會的真正主人。自從清末廢科舉之後,傳統的入仕之途斷絕了,鄉村的士紳精英紛紛跑到城裡,因為只有在城裡,才有機會爬到社會的上層。而他們在鄉下的空缺,就由土豪、惡霸、流氓、黑社會填補了。辛亥革命時,西北會黨、刀客、盜匪串合糾結,群起嘯聚,到處搶掠。陝西的軍政府幾乎全被哥老會控制,軍政府張貼的布告,除了蓋有兵馬都督關防外,還要一律加蓋“洪會公議”的戳記,方才生效。幫會的碼頭,直凌駕於地方行政之上,“但聞有洪會命令,幾至不知其他”。[參見:陝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員會編《西北革命史徵稿》(中卷)。1949年版。]哥老會根本不理會什麼民主,什麼共和,只知道革命就是會黨打天下、搶碼頭,就是會黨出頭之日。
民國以來,因戰亂困擾,地方長官頻頻易人,造成政治上混亂不堪。各小軍閥分割防區,就地籌款,陝西省1926年已經預征了1929年的錢糧。苛捐雜稅的名目數不勝數,牲畜稅、斗傭、秤傭、血稅、門牌捐,還有各縣駐軍直接勒索的維持費、修造費、糧秣費、犒賞費、購置軍械費、棉襖單衣費、鞋襪費、年節費,五花八門,不一而足。田租本身也是重得驚人。農民無路可走,只好以土地、窯洞作抵押,借高利貸。
據華洋義賑會在1923年10月至1924年3月間的調查,農村每人至少擁有四五畝田地,才能生活;較肥沃的田地也要三畝。但1922年,山西的農民平均每人才有一畝四分六厘畝,甘肅只有八分。河南、陝西的情況比較好,每人可有三畝三分到三畝八分。[參見:李大釗《土地與農民》。《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照統計數字看,河南、陝西兩省完全有能力自給自足,但事實上這兩省的情形比山西還糟。
究其原因,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由於連年戰爭,各省軍隊數目激增。1925年河南省有案可考的軍隊,就有十五個師十四個旅,全年軍費近兩千萬元。而河南全省一年收入,僅夠軍費開支。軍隊就地勒索、竭澤而漁,把大量土地用來種鴉片。
馮玉祥當陝西督軍時,宣布嚴厲禁菸。他說:“真的餓死也是可以的,鴉片卻非禁種不可!你們若定要種,請先用手槍把我打死!”但實際上,馮玉祥自己的軍隊,就是靠強迫種植罌粟,徵收鴉片稅養活的。軍閥們的所謂新政,大抵如此。
在西北地區,當兵似乎是無地農民唯一的合法出路,但軍隊生活十分艱苦,餉銀常被剋扣,人身也沒有自由,並不是人人都捱得住的,於是便紛紛逃跑,據說民國初年軍隊開小差的比例,大約在15%~30%之間,[參見:(英)比林斯利《民國時期的土匪》。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許多逃兵都當土匪去了。和中國歷代王朝一樣,破產農民的不斷激增,最後必會釀成大亂。這是古老的循環法則。
河南省是華北平原和秦嶺山脈接壤的地方,黃河由西向東,貫穿全省。這裡是西北人問鼎中原的必經之路,亦是草寇的天下。當地有一句諺語,“男子不當刀客(強盜)不算好漢。”一位在河南當過縣長的人慨嘆:“士紳富戶,無不通匪,否則無以保其身家。其桀驁者更為土匪作掩護,坐地分贓。於是匪風益熾,綁票的案子,幾乎天天發生。”當人們的生活無法維持下去時,當土匪便成了還有一線生機的出路。
1912年,豫西農民白朗(又稱白狼)揭竿暴動,先後攻占禹縣、新野、鄧縣及湖北隨縣各地,然後又回師占領河南唐縣、方城、盧氏等縣,1914年橫越京漢鐵路,取商城、固始、光山及安徽的六安、霍山等地,再殺入隴南,連克十三州縣。
白朗起義震動中原,乃至在國際上也引人注目,南方的共和派革命黨與白朗聯絡,北方的帝制派宗社黨也與白朗聯絡,大家都想借刀殺人,打擊袁世凱。俄、美、英、法國先後派軍事人員到信陽等地觀戰。段祺瑞調動了二十萬大軍,對白朗軍進行“圍剿”。大軍所過之處,只見白骨高於太行雪,血飛迸作汾流紫。
1914年8月,白朗起義失敗,但鄉間的騷亂,卻此起彼伏。1914年至1915年,環縣農民暴動,殺死縣知事,分了鄉間豪紳的財物。先後回響有幾萬人,震動了陝甘寧邊界上十幾個縣。1923年至1924年間,河南廬縣十幾萬紅槍會、硬肚會、守望社、保衛團的人馬,三次圍攻縣城,把陝西軍隊趕走。1926年渭南有幾萬農民因徵稅太重,發起“交農”運動。就是把農具統統交到縣衙門,實行罷耕。同年綏德、清澗一帶農民,組織了六七百個“神兵”(紅槍會)反對苛捐雜稅,占領了一二百里地方。
在三山五嶽的各路英雄中,牌子最響,勢力最大的,要算紅槍會。
紅槍會發源於山東,逐漸向西流傳,它的淵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白蓮教。1914年傳到豫西,一下子蔓延了十幾個縣。因為每個入會的人都要拿一桿紅纓梭鏢為武器,故稱紅槍會。它既不是土匪,也不屬黑社會,而是農民為抵抗土匪而組成的自衛組織,但後來帶有很濃的政治色彩,有的則被土豪軍閥利用,成為他們互爭雄長的工具;有的江湖盜匪也自稱紅槍會,燒殺擄掠,無所不為。
除了紅槍會,在江湖上橫行的,還有黃槍會、藍槍會、白槍會、黑槍會、綠槍會,還有大刀會、小刀會、扇子會、提籃會、天門會、清道會等二三十種名目的組織。他們有的信奉孔子,有的信奉關帝、觀音,有的信奉土地爺爺,有的信奉太上老君,還有的信奉豬八戒、孫悟空,巫醫符咒、乩台沙語、陰陽卜筮、八卦五行,可謂無所不有。
紅槍會信仰祖師,由傳教師傳授“神術”。其會員大多是愚笨的鄉人。所謂神術,就是先在祖師神牌前燒上香,然後掐訣,念咒,把上身衣服脫光,右手拿磚頭打左肋三下,再用左手拿磚頭打右肋三下,然後雙手拿磚打左右腿、膝蓋各三下,接著打脊背三下,最後打頭三下。每打一下,口裡發出哈聲。如此練一個月。然後增加“喝火”、“排刀”。喝火是用一個飯碗裝上油,點起三寸高的火頭,對著火頭由上往下吸,要把火頭吸滅。排刀是用一把刀背,用右手拿住,砍左肋三下;左手拿住,砍右肋三下,再用右手向腹上砍三下,砍時照樣發出哈聲。每晚如此,兩個月後,就可以“刀槍不入”了。
還有一種“鐵扇子”法術,據說經過一段時間的修煉之後,就可以靠念咒語,用扇子把敵人的子彈打落。
從這些神術可以看出,西北地區的江湖文化,與北方的義和團是一脈相承的,都屬於畫符念咒一派,與東南方城市型的黑社會,有很大的不同。東南方的黑社會,不乏金融家、實業家、知識分子,在賑災慈善機構、紅十字會、市政建設部門、治安部門都有相當的影響力,和海外也有密切的聯繫。他們的信仰、行為準則、做事方式,和西北有天壤之別。
在西北,軍隊、土匪、紅槍會,形成互相對抗,又互相依存的三角關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百姓與土匪之間,並沒有很明顯的界線。關於紅槍會的“神術”,愈傳愈神。連正規軍隊都懼怕三分,在碰上紅槍會時,往往不戰自潰。紅槍會因此獲得了大批裝備,聲勢愈加浩大。
官府沒辦法平息匪患,就採取收編招撫的辦法。其直接後果是造成兵匪不分。在軍隊里有許多官兵都是土匪出身,有些軍隊為了擴充實力,甚至把一些已經收編的下級軍官又放出去拉桿子,等拉起了人馬,再收撫回來,連長變營長,營長變團長。有些白天是兵,晚上是匪;打勝仗是兵,打敗仗是匪;也有些上半年是兵,下半年是匪。在西北軍隊中,黑白兩碗飯一齊吃的人,比比皆是。最為著名的有劉鎮華和樊鐘秀二人。
劉鎮華本人並不是土匪,他出生在嵩山北麓的鞏縣,父親是讀書人,他自己是清末秀才,後來又在保定入北洋法政學堂,當過河南中州公學庶務。在動盪不安的20世紀初,劉鎮華是當地一位活躍的革命分子。辛亥革命,陝西的義軍從潼關打入河南,在劉鎮華的奔走活動下,豫西大部分和民黨有聯繫的綠林豪傑都投奔到革命軍中。後來,以這些盜匪為骨幹,成立了“鎮嵩軍”,劉鎮華擔任協統。
開始,這支軍隊並未得到中央的承認,糧餉無著,處境險惡。1912年,鎮嵩軍奉命開回豫西,任務是“剿匪”。劉鎮華“剿匪”的策略有兩點:一是放人出去拉桿子,把盜匪收編回來;二是把一些不服收編的悍匪殺掉。在這次大“剿匪”中,鎮嵩軍殺了三千多人。伊川、洛寧、嵩縣、伊陽、盧氏、宜陽一帶的盜匪,聞風而逃。鎮嵩軍因而得到中央的承認。
1917年,劉鎮華出任陝西省長,鎮嵩軍進駐周至、戶縣。這裡是著名的鴉片產區,陝西的煙價每兩一元,運到洛陽就可以賣七元。鎮嵩軍一方面自己向河南運煙土,另一方面又徵收煙稅,從而發了大財。從鎮嵩軍的成長,可見西北地方軍閥勢力形成的訣竅。
樊鐘秀是河南寶豐縣人,父親也是個教書先生。樊家擁有一百零五畝田地,自己耕種,是自給自足的小農。1913年,因為受到土匪騷擾,全家逃往陝西宜川縣。但次年又受到當地土匪騷擾。樊鐘秀一氣之下,索性自己拉桿子落草為寇。在陝西的河南同鄉,怕受牽連,也都紛紛揭竿相從,他的隊伍一下子擴充到兩百多人。
1915年,樊鐘秀接受陝北鎮守使的收編,由盜匪變成官兵。1918年,胡景翼等人豎起靖國軍旗號,要驅逐陝西督軍。樊鐘秀率部在西安城外和靖國軍激戰了一個星期,然後把隊伍拉走,聲稱要開回河南老家,實際是投靠靖國軍。
當北洋政府派奉軍進入陝西,向靖國軍進攻時,樊鐘秀又投靠了奉軍。後來又把隊伍拉回河南,投靠河南督軍。馮玉祥把河南督軍趕走後,樊鐘秀又投靠了吳佩孚。1923年甚至不遠千里,跑到廣州投靠孫文。
這些綠林出身的大小軍閥,大多沒有政治信仰,也沒有相對穩定的政治背景,今天投靠這個,明天投靠那個,忽左忽右,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然而,最後改變中國命運的,往往是這些桀驁不馴的土皇帝。
二、閻錫山:山西土老財
在北洋官僚集團里,西北有兩位顯赫人物,一位是馮玉祥,一位是閻錫山。馮玉祥出身於北洋正統,從袁世凱的新軍衛隊一名正兵做起,慢慢地由副目、正目、哨長、營管帶,成為權傾一時的佩劍將軍。而閻錫山則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毫無關係,他就讀的山西武備學堂,也不屬於由段祺瑞督辦的北洋陸軍學堂系統。
然而,由於政治風雲的變幻,使這兩個人在西北相遇,並結下了不解之緣。
1883年,閻錫山出生在山西省五台縣河邊村永和堡一個地主兼開錢鋪的家庭,六歲喪母,九歲啟蒙,在私塾讀過《三字經》《百家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儒家典籍。十六歲成親,在五台縣城的積慶昌商號當相公,從“五壺四把”(茶壺、酒壺、水煙壺、噴壺、夜壺和笤帚、撣子、毛巾、抹布)做起,學習怎么記賬,怎么算利息,怎么出外討債、打探行情和做投機生意。
明清是晉商的黃金年代,雄踞中國十大商幫之首。但山西為什麼不能像江、浙那樣,進化為一個繁榮的現代商業社會呢?看看晉商經商的路線就清楚了,幾百年來,他們主要是和俄羅斯、蒙古、新疆、東北等地的遊牧民族做生意。這種農耕社會與遊牧社會之間的生意,再做一百年,也做不出一個以海洋文明為背景的現代商業社會來。
五台縣的經商風氣,雖然也是盛極一時,但閻錫山卻無心經商,1902年,他憑著一篇《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論》的文章,考取了山西武備學堂。兩年後,由巡撫衙門指定派往日本留學。和許多熱血青年一樣,在日本接觸到了孫文的民族主義思想,並為之心醉神迷。不久他便加入了同盟會,又參加了“鐵血丈夫團”——其名取自《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1907年,閻錫山正式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成為第六期生。日本教官向他們講授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打敗列強的歷史,講授日本明治維新後,實行軍國主義、徵兵練武、發展工商業,從而稱雄世界的歷史。閻錫山對這些課程興趣盎然。畢業回國後,他便加入了山西軍界。
這時候,他的思想和南方的革命黨十分接近,經他一手安排,同盟會在山西新軍里異常活躍。
1911年辛亥革命席捲全國。10月29日,太原起義成功,閻錫山被推舉為軍政府大都督。在軍政府門前飄揚的既不是十八星旗,也不是五色旗,而是一面源自河圖洛書的“八卦太極圖”旗。後來有人批評閻錫山,參加辛亥革命,動機不純,是偽裝革命,“投機取巧”、“竊取革命成果”。
其實,從閻錫山把八卦太極旗定為軍政府的旗號,可以看出,這場革命在他的心目中,不過是一場紫氣東來、真人出世的“湯武革命”。這正是他內心的理想所在,何偽裝之有?中國的民主,就在八卦太極圖下,開始了一幕幕痴人說夢的鬧劇。
1912年,閻錫山兼任山西民政長,1914年,改任為同武將軍督理山西軍務,嗣又晉任為同武上將軍督理山西軍務。1916年改任為山西督軍,1917年兼任山西省長。閻錫山抱定宗旨,不參加中原逐鹿,以保境安民為目的,因此對外聲明,晉軍不出山西一步,但有來侵者,必唯力是視。閻錫山宣稱,終北洋時代,晉軍唯一一次殺出雁門,是張勛復辟時,段祺瑞在津門宣布討逆,約山西派軍參戰,閻錫山派出了一個旅前往北京參加作戰,戰畢即撤回山西。[參見:《閻錫山先生答客問的自述》。台灣,《傳記文學》第186號。]
閻錫山關起門來,一心一意經營山西。他痛感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現狀,於是按照自己土財主的理想,制定了一整套以古人訓誡來治理山西的宏圖大計。
他的農村改造計畫,從訓練村一級的行政人員開始,以“民德、民智、民財”為施政大綱,從清丈土地、調查戶口入手,以村為單位,村有村長,設村公所,村下面有閭,閭下面有鄰。經過數年努力,他在山西建立起一支由五十萬個鄰長、閭長、村副、村長組成的基層幹部隊伍,管理著全省四萬多個村莊。
他把“村村無訟,家家有餘”、“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作為宗旨,以期“裕民生、正民行、敦民風”,進而實現古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妻賢、友信、鄰睦的理想。他還成立了好人團,大力宣傳種地的人好,當兵的人好,推行育兵育農的政策。
1918年,閻錫山大力實施“六政”、“三事”。所謂“六政”,即禁止留辮、禁止纏足、禁止吸毒和興水利、種樹木、養蠶桑。所謂“三事”,即造林、植棉和畜牧。他把信、實、進取、愛群,作為社會道德的標準,推而廣之。同時整頓村制,開村民會議,整理村范,訂立村約,立息訟會,設保衛團,為“村民自辦村政之時代”的到來奠定基礎。閻錫山甚至構想,以村自治作為起點,有朝一日,可以廢除代議政制和政黨政治,使中國人民行使直接民權。
1920年6月,在閻錫山的主持下,召開了著名的“進山會議”。與會者多是當地的名流耆宿。會議在公署後面的假山(閻錫山稱之為“進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館”召開。歷時一年,開始時只有十二人參加,後來陸續有人加入,多至一百三十四人。會場也由“邃密深沉之館”遷到了山前的大自省堂。
當直皖兩系在北方開始兵戎相見,南方也被內部的戰爭深深困擾著的時候,閻錫山所考慮的,是如何在山西從事道德重建的大業。他覺得自己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途徑,能夠使大西北的衣冠文物,在這個渾渾濁世中保存下來,並且發揚光大。
會議研究的目標,是“人群組織怎樣對”的問題。閻錫山認為,人是有理性、有欲性、有精神、有物質的一個生物體。按東方文化看,人的價值很高,號為三才之一,二五之精。人與天地合德,人為天地立心。惟其認人之本體如此其高也,故最尊崇人道主義。如“仁者人也”一語,即足以代表東亞先聖先哲對於人生之觀念。
人都是想過好生活的,但究竟如何才能使人人都有好生活?按照閻錫山的解釋,消極地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若積極地說,就是如何使自己有好生活,別人也有好生活。此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成己成物之謂也。過去聖哲對此持論,有所謂理想國者,有所謂死後天堂者。如何而能有實現之理想,如何而能得人世之天堂,就是閻錫山為這次會議定下的研究題目。
會議開了一年之後,對工業問題得出了以下結論:
“工業應有限制;除必須之大工業外,應偏重小工業。”
對商業問題的結論是:
“商業應有限制。”
對土地問題的結論是:
“土地公有私種。凡屬農民生則自種,死則歸公,產業既均,人慾亦遂。”[參見: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站在西北的立場上,對現代工商業,持懷疑與否定態度。1921年,閻錫山和到訪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孟祿博士有一番談話,談到對工商業的看法。
孟祿是教育學的權威,他們的話題也從教育開始。閻錫山認為,人群賴文化以維持;文化以教育為代表。人群需要什麼東西,教育即應預備什麼東西。
孟祿問,人群現在需要什麼?
閻回答:“近來我考察山西各縣教育的結果,覺得作飯的人愈沒有飯吃;作衣的人愈沒有衣穿;作器的人愈沒有器用。小民終日勞碌,若問他們作什麼,他們便答說:‘我為你們作衣穿,作飯吃,作物用。’山西的情形如此,所以我們的問題,是如何使作飯者有飯吃,作衣者有衣穿,作器者有器用。”
這個問題,自古以來許多人都提出過,也嘗試過各種不同的解決辦法。孟祿認為,在現代社會,要解決這個千古難題,就要用好的方法,改良農業、工業與商業,及改良教育,使人得到實用的知識技能,能利用天然物以為人用,不久即可得到此種結果。
閻錫山一聽見工商業,立即搖頭。他說:“我很早有個疑問,就是工商業發達的結果,人民是否真正能夠得到飯吃、衣穿,與物用,我害怕工商業愈發達,作飯的人民愈無飯吃,無衣穿,與無物用。工商業發達的結果,我害怕不但不能救了人民的苦,反倒更為壞事。”
他的理由是:別的國家工業發達,可運貨來到中國換飯,將來中國的工業若發達,不知能運貨到什麼地方換飯。運往蒙古嗎?蒙古人不作飯,怎么辦才好?
在閻錫山的想像中,工商業和“走口外”、“闖關東”是一回事。山西人走了上千年口外,闖了上千年的關東,也沒見人間天堂的出現!路通財通,道路工商業發達的重要因素之一,試看大江南北,鐵路沿線無不是最富裕的地區,但閻錫山在山西修鐵路時,卻偏偏要修成窄軌,與中原的鐵路不接軌,弄得火車想進進不來,想出出不去。
明清盛極一時的山西票號,就是因為它們因循守舊,不肯融入現代金融體系,才步入衰落之途,但閻錫山依然沒有跳出晉商那種陳舊的思維方式。
在他的內心深處,對一切來自洋人的“思潮”、“主義”,統統抱懷疑態度。他自創了一門“公道主義”,並把它封為“無論何時何地,皆處於對之地位,故能博人人欣喜,處處為人樂於接受”的萬金油,是人類通向幸福之門。
究竟什麼是公道主義?它聽起來就像一個倫理學的概念。閻錫山認為這是他的一大發明。不論場合,百說不厭。但他始終沒有能夠說清楚公道主義的基本要點,他只是誇張地聲稱公道主義囊括了一切主義的優點。他這么解釋:
“公道主義,為各種主義之本源,乃宇宙間之元氣。其為物也,是整個的圓之單體,非零星的枝節湊合。是時中的,非執一的;是養生的,非治病的;是靈活的,非板滯的。舉一足以統萬,執簡可以馭繁,神而明之,事物之真是非可知,宇宙之真主宰可得。”
他的靈感無疑是來自最古老的宗法制度。他所極力倡導的“用民政治”,乃是一種敬慎勿怠、寬容勿矜、禮讓忠信的道德實踐。他所讚不絕口的公道主義,集中了將家庭、社會、政治、宗教合而為一的文化精神。閻錫山所夢想的,就是恢復“立地上以承天,承天道以隆人”的中國文化基礎。
中原大戰時,陳公博為了動員閻錫山反蔣,曾到山西跑了一趟,他發現“山西對於新文化的接受,還是遲緩,比之山西以外,恐怕要遲到20年。”[參見:陳公博《苦笑錄》。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一位南方將領在分析閻錫山的思想時,毫不留情地說:“這位先生,自從在山西與世不通聞問,故步自封,絕不見有新人物到山西和他共事,只邀些名士去講舊學,受他尊崇。二十年來,山西充滿了儒釋道三教九流的風氣,和似是而非的學理,新一點的文化,簡直不進山西。”
閻錫山認為他發明的“土地村公有”就是體現了公道主義。所謂土地村公有,即以公債形式把土地收歸村公有,再分給農民耕作,受田之人到死時就把田還給村里;以直接稅償還收買土地的公債。這樣既可以保證人人有田種,又避免土地集中到少數地主手中。這個被閻錫山視作得意之作的改革,在1939年就以失敗告終了,弄得地主也反感,農民也反感,70%的人都不高興。因為山西以自耕農居多,這個改革是先把土地公有,再重新分配,他們覺得這太不公道,當然怨氣衝天了。
山西官場承晚清頹風,敷衍搪塞、瞞上欺下的道行,比儒家典籍要高深得多。閻錫山鼓勵種樹,大家就用草包裹樹枝、鞭桿、木棍插在地上冒充樹苗。閻錫山嚴厲禁菸,種、運、吸一併懸為厲禁,但1920年破獲販賣煙土、嗎啡、金丹的案件,是1918年的四倍。山西禁種,煙土就從鄰省大量湧入。
閻錫山對各縣知事感慨地說:“六政考核處辦理已經三年,有甚效果?像這樣辦下去,再辦三年,也是無效。”他又抱怨:“照中央所定的法律,禁菸丹無異於獎勵煙丹,禁得愈緊,價值愈大,販賣的人也愈多。”[參見:吳文蔚《閻錫山傳》(第一集)。台灣,1983年版。]
為了推行新法,不得不藉助於嚴刑峻法:販賣煙土者處死,吸食者判刑。同時強化村制,保衛團用武力推行教化。但仍不見效,硬功不行,又改施軟功,設立戒菸會,勸人自動戒菸,然貼標語、寫文章、官吏宣講、學生宣傳,折騰了數年,還是吃力不討好。
六政三事推行了五年半,有成有敗,但總的說來,讚揚的聲音居多,為山西贏得了“模範省”的美譽。山西簡直成了太平盛世的標本,據說連一個乞丐也沒有。但實際上,1924年至少有超過兩萬五千名土匪,在山西的地界上橫行。[參見:朱新繁《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質》。上海新生命書局,1930年版。]
20世紀30年代以後,隨著內戰向西北蔓延,閻錫山的門羅主義也失效了,山西農村更是一片凋敝。他不得不承認:“年來山西經濟,整個破產。自耕農淪為半自耕農,半自耕農淪為佃農僱農,以致十村九困、十家九窮。”[參見:《呈中央請由山西試辦土地村公有制以弭共禍文》。《防共聯席會議紀錄彙編》。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
三、馮玉祥:大鬧天宮的農民
馮玉祥是典型的農民兒子。
他的原籍在安徽巢縣。父親是鄉下的泥瓦匠,後來投身行伍,全家遷到保定府郊外定居。馮玉祥的原名叫馮御香——“朝罷衣冠沾御香”,也許,他們家從巢縣遷到保定,也是為了離天子腳下近一點,好方便“沾御香”吧。然而,他們實際上過著農夫的生活,春耕秋收,拔草拾柴,每逢青黃不接之際,就要把家用雜物送去典當。
馮玉祥的性格非常敏感,這一切在他幼小的心靈里種下了憤世嫉俗的種子。他恨當鋪;也恨雜糧店,因為他們家日常吃的米麵要靠雜糧店賒賬;他恨鴉片煙,因為他的父母飽受其害;他恨貪官污吏;他恨土豪劣紳。總之,鄉下貧困的生活,使他滿腦子都是怨恨。他的童年只念過一年零三個月的書,從十二歲開始,就到新兵二十鎮的軍營里練槍打靶,他是一名真正的大兵。
“御香”這個名字確實給他帶來不少好運,據說當年慈禧太后從西北回鸞,二十鎮要挑選身材健碩、名字吉利的兵丁去站道迎駕,他沾了御香二字的便宜,雀屏中選,真的一沾御香了!馮玉祥第一次和西北發生關係,是在1914年,他作為北洋警衛軍第一旅旅長率領部隊到陝西一帶追剿白朗匪幫,足跡踏遍了陝州、潼關、西安、靈寶、渭南一帶。“尋河愁地盡,過磧覺天低”,大西北的景色,深深地烙在他的腦海之中。
直皖戰爭以後,直軍第二十師在閻相文師長率領下,開入陝西,驅逐皖系督軍。馮玉祥的隊伍取道潼關,第二次進入西北。事先馮玉祥請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孫岳給胡景翼寫信,請他夾攻皖系督軍,胡景翼慨然允諾。胡是渭北刀客中一名頭面人物,黑道中人沒有不認識他的。
北洋政府任命閻相文為陝西督軍。不料上任不到兩個月,突然吞服生鴉自殺,成為民國以來最短命的督軍。他的自殺,並無特別理由,只說擔心自己不能統一陝西。對一個剛剛以勝利者身份走馬上任的將軍來說,這個理由近乎荒謬。
閻督軍死後,馮玉祥由旅長一躍而為陝西督軍,成為民國以來升遷最快的軍人。外間哄傳閻相文的死與馮玉祥有關,後來,更有人寫書,直指是馮玉祥在酒宴之上,以毒酒毒死閻相文,收編了他的隊伍。但說歸說,還是查無實據,遂成轟動一時的疑案。[參見:昌人《馮玉祥的轉變》。《現代史料》(第三集),海天出版社,1934年版。]民國以來,疑案、懸案、無頭公案,多不勝數,閻督軍之死,不過小兒科耳,連歷史學家也提不起破解的興趣。
馮玉祥拒絕搬進閻留下的督軍署,他在西安城西北角另建一座新的督軍署。這塊地方在明代稱作皇城,在清代稱作滿城。辛亥武昌首義後,陝西回響,關中豪傑攻入滿城,把裡面的滿人殺得雞犬不留,屍積如山,房子也燒成一片焦土。馮玉祥就在這個地方,作為駐兵之地,修建他的督軍署。
這位農民的兒子終於有了自己的衙門,可以坐在高堂之上發號施令了。
馮玉祥上任後,立即疏遠了曾為他出過力的胡景翼,他派人對孫岳說:“胡部完全是土匪,擾亂地方,絕不能容的。”
孫岳對馮翻臉之速,感到十分驚訝:“煥章(馮玉祥字)太不夠朋友。胡笠僧(胡景翼字)剛幫了他一個忙,他就要反過來收拾他。”胡景翼也深感失望地說:“吳佩孚、馮玉祥要把我擠出陝西,要收編我的隊伍。”
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後,馮玉祥認為是向中原發展的機會,於是積極向吳佩孚請纓。不料吳佩孚對他素無好感,不肯讓他上前線。馮玉祥勃然大怒,擅自將隊伍拉出潼關。當時吳佩孚在前方忙得不亦樂乎,無暇後顧,只好委任馮玉祥為後方總司令,負責監視河南。
出發前,馮玉祥把陝西的軍政大權,全部交給了兒女親家劉鎮華,他把官兵們召集起來說:“這次出征,不是為了個人的私利,而是為了討伐媚日賣國的奉系軍閥。”他抬起腳,把布鞋踢出老遠,大聲說:“我看督軍的位置,如同這隻破鞋,我們這次參加戰事,完全是為盡我軍人保國愛民的神聖天職!”
壯哉斯言!然而,如果在民主國家,一個總統候選人說他視總統職位如破鞋,選民們還會投他的票嗎?人們怎么指望一個把自己職位看作破鞋的人,能在這個職位上為國、為民效勞?好在中國的官員都不是老百姓選的,不煩操心。馮玉祥把陝西督軍看作一隻破鞋,是因為他一心想得到河南督軍這個位置。馮玉祥絕不是一個甘於寂寞的人。
河南督軍和奉系暗通款曲,宣布武裝中立,凡是參戰客軍逗留豫境,一律解除武裝。但馮玉祥的武裝,又豈是凡夫俗子所能解除的?雙方激戰一天,豫軍大敗。馮玉祥乘機掃蕩河南全境。幾天以後,政府下令由馮玉祥出任河南督軍。
河南是吳佩孚的老地盤,他的大本營就設在洛陽,河南督軍在吳玉帥面前,從來就像小媳婦一樣。而馮玉祥又是個一貫自行其是,不聽號令的人。翩翩儒將和草莽英雄之間,必然水火不容。
上任沒幾天,吳佩孚便勒令馮玉祥協餉八十萬元,以後每月協餉二十萬元,馮玉祥就算能籌得出這么一大筆錢,也不會白白送給吳佩孚。他復電拒絕了。吳佩孚明確告訴他,如果他做不到,就請讓出河南督軍的位置。
馮玉祥感到在河南沒辦法待下去了,於是跑到保定向曹錕哭訴,他的用意是向吳佩孚擺出投靠保定系的姿態。不料曹錕對河南小媳婦的處境,大表同情,勸馮玉祥乾脆調到北京。馮玉祥吃了一個啞巴虧,有苦說不出。
1922年10月,大總統頒布明令,任命馮玉祥為陸軍檢閱使,交出河南地盤。馮玉祥百般無奈,只好到洛陽向吳佩孚辭行。吳佩孚向馮玉祥提出三個條件:一、河南可以每月為馮玉祥的第十一師協餉二十萬元;二、馮玉祥只準帶走他的第十一師;三、近幾個月來馮玉祥在河南新招募的三個混成旅,應該留在河南。
“一切悉聽大帥安排。”馮玉祥畢恭畢敬,倒行而出。但一回到開封,他立即命令新招的三個混成旅以第十一師的旗號,連夜向北京開拔。他們走後,把旗號運回開封,第十一師才正式動身。就這樣,他的西北軍隊終於堂而皇之地開入了北京帝都。
馮玉祥的西北軍是一支訓練很嚴格的隊伍。從招兵開始,就非常重視士兵的素質。普通士兵以青壯年農民以主,挑選新兵時要先看看頭上有沒有辮子,沒有不行;再看看手掌有沒有厚繭,沒有也不行。頭上有辮、手上有繭,是老實巴交、單純保守、能夠吃苦耐勞的標記。
馮玉祥喜歡問士兵:“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
士兵們要回答:“我們是從鄉間來的。”
“你們的父母、親戚、朋友是什麼人?”
“都是老百姓。”
他也常問自己的兒子:“你的曾祖父和祖父乾什麼的?”
兒子要回答:“當過農民、漁夫、兵丁。”
聽到這樣的回答,他便高興地笑起來。
馮玉祥利用一切機會,向他的官兵灌輸平民意識。但西北軍里的等級是非常森嚴的,馮玉祥的命令就是聖旨,任何人不得違抗。在馮玉祥的心腹軍官里,沒有一個在國外接受過教育。他們的文化水平都很低下。他們打仗靠的是經驗和從說書藝人那兒聽回來的故事,直至模仿《三國演義》里的諸葛亮來指揮戰鬥。
為了維護馮玉祥本人在軍隊中的絕對權威,他把士兵們“結盟”、“入會”一類的活動懸為厲禁。但實際上,幫會勢力早已滲透他的軍隊,他的長兄馮基道就是一個黑社會大佬,他手下第一戰將張之江也是一名幫會分子。
馮玉祥利用基督教作為維繫他的軍隊的基礎。他要求全體官兵都受洗入教。這位大老粗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消防水龍頭給他的官兵行受洗禮。但對於那些老實巴交的農家子弟來說,基督教不過是一個可以公開的幫會而已。
馮玉祥認為基督教有助於向士兵灌輸禁慾主義,對加強軍隊的紀律非常有用。不過,西北農民對基督教,並非真正接受,連馮玉祥也不是認真信仰。他生平除了自己以外,沒有真正信仰的人物,也沒有真正信仰的思想。孔子、孟子、關公、岳飛、曾國藩、胡林翼、耶穌、列寧、甘地、孫中山等,都在他的腦子裡,占了一席之地。而萬物的軸心,就是馮玉祥自己。
他治軍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鼓勵官佐家的弟妹子女互相通婚。這有利於把軍隊變成一個大家庭,而馮玉祥就是這個大家庭的唯一家長。他總是給結婚的雙方都送些禮物,以示威嚴而有慈。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官佐家的聯姻,“一來因為他們父兄都是同事,彼此熟識,相互擇配,必較能滿意;二來團體的關係也可以因此愈加鞏固。”[參見:馮玉祥《我的生活》(下冊)。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馮玉祥希望扮演一個民族主義者的角色,但卻常常力不從心;他是社會改革的積極推行者,但這些改革卻往往停留在皮毛瑣事上面,諸如不讓妓女穿漂亮衣服、宴會菜式的豐儉之類。
馮玉祥對閻錫山在山西的政績,非常羨慕,他在河南時也模仿山西制訂十項治豫大綱。當有人向馮玉祥揭露山西的種種虛假做法時,他不以為然地反駁:“有老王時恨老王,沒老王時想老王。其實看山西的完整,今天有哪一省可以比得上?”
然而,就地方建設來說,他連閻錫山的十分之一都沒有能夠學到。
他不如閻錫山之處,在於他的政治理想是非常模糊的。
西北軍每到一處,所謂的政治宣傳工作,就是在牆壁上畫滿紅紅綠綠的國恥地圖和二十四孝圖像,在電線桿上釘滿寫著古聖賢格言的木牌。連士兵們的衣服前後,都縫上白底紅字的標語。如果說中國有“標語治國”的傳統,那么馮玉祥是開山祖之一了。
馮玉祥手下有一位重要的政治幹部,在擔任陝西省民政廳長時,為了禁止婦女纏足,限令各縣縣長按月繳送一定數量的婦女纏足布,以纏足布的多少作為銓敘的標準。結果,堂堂的民政廳里,纏足布堆積如山,臭不可聞。
馮玉祥最大的特點,就是能夠不厭其煩地宣揚一些連他自己也不打算實踐的政治主張。從基督教教義到三民主義,莫不如是。他常常自稱是農夫兒子,但他對農民的生活並不真正關心。陝西的捐稅預征了五年,到處民怨沸騰。馮玉祥在河南時連開徵“古玩出土捐”這樣的主意都想到了,還有什麼會從他的指縫中漏掉呢?
1927年,在他治下的西北,農民已經完全破產,乃至遍地土匪。當時的觀察者指出:“自民十四年(1925年)馮玉祥占甘肅,隨下陝豫後,不但沒有把舊有小股土匪使之斂跡,倒反給西北各地增加了不少匪眾,弄得匪氛益熾,冠於全國。”[參見:康天國編《西北最近十年來史料》。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版。]陝西與寧夏、甘肅、綏遠、山西、河南、湖北、四川交界之處,幾成土匪的天下。
因此,當農民協會成立時,入會者非常踴躍,僅陝西一省,一下子便達十五萬人。農民已身陷絕境,忍無可忍了。他們提著裝著“土豪劣紳”腦袋的籠子,到西安送給政府。他們說,我們懲辦了一名反革命分子,現在把他給你們送來了。
真正令馮玉祥擔心的不是激化階級對抗,而是過分活躍的農民運動,影響到他在西北的絕對權威。他訓斥農民:“這裡有駐陝司令,還有省政府,若你們管這類事,還要他們做什麼?”真正的農民很冤枉,本來是老老實實的莊稼人,回響號召起來造反了,但鬧騰了半天,最後落得里外不是人,連原來還有的一點家產也賠進去了。
如果說閻錫山像一位幾代相傳的老財主,那么馮玉祥就像一夜暴富的新財主。他雖然經常自稱是農夫的兒子,但一旦手裡有了槍桿子,有了權力,馬上就以農民的東家自居,他的政治邏輯,不過就是西北刀客與馬匪的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