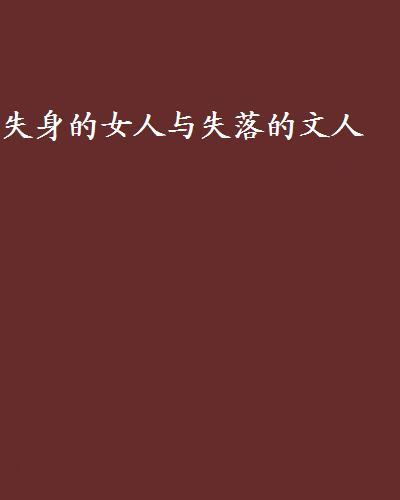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失身的女人與失落的文人
- 類別:失身的女人與失落的文人
市文聯《陽春白雪》雜誌的主編老水,在參加完全市宣傳文化工作會議準備回家時,發現自己那輛騎了十幾年的舊腳踏車不翼而飛了。他覺得這是一個不好的徵兆,這使他本來已經十分煩躁的心情變得更加沮喪。
今天這次會議,對老水和《陽春白雪》雜誌來說,其實就是一次“斷奶”會,市委宣傳部的林副部長在會上宣布:“從今年下半年開始,市財政就正式停止給你們這些刊物撥經費了!市場經濟了嘛,你們要學會自己養活自己!”
自己養活自己?就憑《陽春白雪》那幾千份的發行量,連印刷費都不夠,還有那一幫人的開銷怎么辦?難道一個辦了幾十年的刊物,今天要斷送在自己手裡?難道我們這幫人搞了一輩子文學,最後竟連飯碗子都保不住了?老水一下子就急昏了頭,散會的時候,他攔住林副部長質問:“難道《陽春白雪》不是在為黨為政府做工作?難道這些年我們是在白吃黨的飯?憑什麼給我們‘斷奶’?怎么不給你們‘斷奶’不給市委市政府‘斷奶’?”林副部長笑笑:“水老,你不要跟我著急。我只不過是傳達市裡的決定,有意見你可以向市領導反映!再說,如今像這種你認為不合情不合理但合法的事情,多著呢,哪裡說得清喲!”老水更激動了,他幾乎是痛心疾首地說:“天天講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可現在整個社會都成了一個大染缸,還剩下多少像《陽春白雪》這樣的文化淨土?你們怎么就不保護她?怎么就忍心再把她推向泥潭呢?”老水這么大聲嚷了一陣,引得好多人圍觀,林副部長趁機鑽出人群溜掉了。老水只好昏頭昏腦地下了樓,結果就發現自己那輛舊腳踏車不見了。他只好徒步向大街上走去。
那是盛夏時節,熾烈的日頭在天空隆隆滾動,空氣被燒烤得火爆爆的,仿佛劃根火柴就能燃燒起來;街道上人流車流蕩起的灰塵在半空中遊蕩,落滿灰塵的風景樹葉子倦曲著,不時發出叭叭的焦枯的聲響。老水覺得細汗像小蟲子似的在渾身亂鑽,隨手在身上一抹,就是滿滿的一把水,衣服已經像洗了澡一樣整個地粘在身上了。
一輛褐色的烏龜形轎車從老水身旁輕快地駛過,猛然在前面不遠處停下來,一個鮮紅的禿頭從車窗探出來,高喊:“老水,老水!”
老水愣神的工夫,禿頭已經從車上跳下來,嚷嚷著:“老水,你是屬兔子的呀?一散會就沒了影,害得我駕著鷹都追不上你!”
是毛縣的文聯主席老芶。老芶也是來開會的,老水在會場上好像看到了他。說起來老芶和老水是老相識了,他們是同鄉,又是早期的文友。只是老芶這人悟性差了點兒,同樣搞了多年的文學,老水的小說已經在全國打響的時候,老芶的作品還沒有公開發表過。直到老水從縣裡調市文聯當編輯以後,才幫他在《陽春白雪》雜誌發了一個豆腐塊。當時捧著那來之不易的處女作,老芶激動得熱淚盈眶,心想這多年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不過高興之餘,又覺得自己辛辛苦苦搞了這么多年,就搞出這么個東西,也真是太虧了,自己也是往四十上奔的人了,再搞下去還能有什麼出息?他心一橫,把那處女作撕個粉碎,一行熱淚淌下來,從此金盆洗手,棄文從政了。別看老芶搞文學悟性差點兒,在政界混還真是那么回事,幾年工夫居然熬了個正科級,當上了縣文聯主席。當然,這是個虛職、閒職,沒權也沒錢。老芶又偏偏是個不甘寂寞的人,看看人家別的科局級幹部都有小車坐,有油水撈,甚至還有小蜜泡,他心裡也覺得酸溜溜的。在政界混了這幾年,老芶心眼兒也活泛多了,他就靠山吃山,打著文聯的旗號成立了一個文化發展中心,專門給企業的老闆、商界的大亨、政界的權貴們寫一些收費的吹捧文章,在他的筆下,那些坑蒙拐騙的暴發戶搖身一變成了披荊斬棘的創業者,橫行霸道的貪官污吏成了廉潔奉公的人民公僕,甚至賣淫的婊子都成了高雅聖潔的貞女。老芶的行徑引起了圈子內一些正派文人的反感,老水就曾在一次公開場合說:“老芶這種人的存在,是我們文壇的恥辱!”這話不知怎么就傳到了老芶耳朵里,他也在一個公開場合大罵老水說:“你老水有什麼了不起?不就是在那么幾個沒有發行量的所謂高雅刊物上發了幾篇酸臭文章嗎?自以為清高,自以為神聖,依我看狗屁不值!”話說到這份兒上,兩人就算志不同道不合了,漸漸就變得疏遠了。
今天老芶怎么又突然熱情起來了?老水狐疑地望著老芶,說:“是芶主席呀!有事?”老芶哈哈大笑著說:“大主編,難得一見呀!走,喝酒去!今天我請客!”不容分說就把老水拉進了小車。車裡嗡嗡地開著空調,冷風呼呼一吹,老水身上立時變得乾乾爽爽的了。老水禁不住感嘆道:“還是坐小車舒服!老芶你真夠能折騰的,才幾年工夫,就混上了這么高級的轎車!”老芶撇撇嘴,說:“大主編,你別挖苦我!縣級文聯是怎么個熊樣,你還不清楚?去偷這么豪華的轎車吧!——這車是人家胡老闆的。胡老闆你還記得吧,就是你們原來那個廠的司機胡天才,現如今人家算得上千萬富翁了!”
2
老水到毛縣油泵廠當學徒的時候,只有十六七歲的年紀,還是一個不諳世事的毛頭小伙子。他的師傅姓姜,曾在縣農機局當過工程師,因為脾氣倔,屢屢受到排擠,一氣之下,就調到這家工廠來了。
廠子其實很小,只有一個小院,兩排車間,三十幾個工人,而且大多是二十來歲的女操作工,整天在車間裡唧唧喳喳地說笑個不停,沒少挨廠長的訓斥。像姜師傅這樣的男維修工只有七八個,師傅領著小水向他們做介紹,小水很靦腆地一一握過手,就算彼此認識了。
廠子雖然小,車卻養了兩部,一部上海轎,一部舊雙排,司機倒只有一個,叫胡天才,是廠長的小舅子。小水去廠里上班的那一天,胡天才沒在,據說到外地送貨去了。第二天小水正在車間裡幹活,一個蝦米腰包子臉約摸三十來歲的男人闖進來,徑直走到他面前,嘻皮笑臉道:“聽說廠里來了個童子哥兒,你就是吧?”小水不大明白他說的什麼意思,一時不知說什麼好。旁邊一個年歲稍大些的女工說:“胡天才,人家還是個孩子,你別瞎胡鬧!”小水這才知道眼前這個人叫胡天才。胡天才馬上轉向那個女工,冷不丁摸一把人家的臉蛋,說:“呀哈,大妹子,我這兩天不在,你褲襠里又痒痒了吧?要不然怎么這么護著他?想換這個童子雞吃呀!”女工羞臊得滿臉通紅,順手抄起一根鐵棒,惱怒地說:“胡天才,你還有人話沒有?你再滿嘴噴糞,我——”嚇得胡天才抱頭鼠竄。
事後,小水把這件事說給姜師傅聽,姜師傅說:“你以後少搭理胡天才,他不是什麼好鳥,早晚要遭報應的!”
話還真讓姜師傅說中了,沒出幾個月,胡天才就犯事了。這就得說到廠里的女會計小米。小米有二十四五歲,高挑身材,烏髮披肩,冰雪似的肌膚,銀盆似的臉兒,小模樣要多可人有多可人。小米喜歡穿一身黑色衣裙,她不像別的女人整天唧唧喳喳的,你很少聽見她在公眾場合說話。她似乎有點憂鬱,但這並不妨礙她的美麗,反而使她的美麗更眩目起來,在體貌的姣好之外,又附帶上一種氣息的美,透著幾分幽冶,幾分冷艷,看上去就像一個冰美人。誰也沒想到小米這樣的女人會出問題,可偏偏就是小米出了問題。
小米是個心氣很高的女子,卻嫁了個從長相到氣質都十分窩囊的男人。男人在一家國營廠後勤科室工作,小米嫁給她其實是看中了他有一個當副廠長的老子做靠山。可是小米萬萬沒有想到,她嫁過去沒幾天,窩囊男人的老子就因為權力鬥爭被趕下台,窩囊男人也從後勤科室發配到了車間。這且不說,窩囊男人還不是一個真正的男人。剛結婚那陣子,他天天晚上涎著臉皮向小米求歡,小米本來對做那種事沒多大興趣,可禁不住他一再撩撥,漸漸地欲望就被開發出來,那生命的激情像決了堤的洪水要奔流而下,像積蓄了多年的火山要噴薄而出。可就在這關鍵時刻,窩囊男人卻不行了,真刀真槍一比劃,只三五下就敗下陣來。小米這個氣呀,她有一種被愚弄被侮辱的感覺,她用最惡毒的話咒罵他,發了瘋似地掐他咬他,可越是這樣,窩囊男人越疲軟,後來竟像避貓鼠似地躲著她不敢上床。小米絕望了。多少個漫漫長夜,她孤燈獨伴,強迫著欲望的火苗慢慢地熄滅,激情的潮水緩緩地消退,讓原本鮮活的身體一點點變得僵死……
就在這時候,胡天才出現在小米落寞的生活里。他似乎洞察了小米的鬱鬱寡歡和隱藏其後的全部秘密,千方百計地接近她、討好她。他常常趁到外地送貨之機為小米買一些並不貴重卻十分珍稀的禮物,或者找個藉口用小車拉上小米到外地的旅遊景點去兜風。一開始,小米覺得自己無功不受祿,不大好意思接受。但女人畢竟是一種很虛榮的動物,落寞的女人就更禁不住這種誘惑,漸漸地,小米對這一切就覺得習以為常了。
問題最終出在了麻將上。胡天才是小城裡有名的賭王,在他的教唆下,小米輕而易舉地就染上了賭癮。他們玩得很大,一夜就有上千塊錢輸贏。當初小米看著那驚心動魄的陣勢,還真有點畏怯。胡天才就給她打氣,說:“你只管放開膽子玩兒,贏了歸你,輸了算在我頭上!”小米畢竟是生手,輸多贏少,輸的錢就全由胡天才包了,但賬還是要記的。幾個月下來,有一天晚上玩完麻將,胡天才用小車送小米回家,小米忽然心血來潮,說:“你算算我到底輸了多少錢?”胡天才就拿出賬本,一算,小米傻了眼——足足輸了上萬塊。小米邊落淚邊說:“這可怎么辦呢?就是把我賣了也還不清了!”胡天才眯縫著小眼睛只是笑,其實小米的錢大多進了他的腰包。他摟著小米安慰說:“這有什麼呢?你別哭,我的錢不用你還,咱倆這種關係怎么能讓你還錢呢!”說著就把小米扳倒在車座上。這時的女人是真正沒了靈魂的女人,只剩下了一具肉體,任男人隨意怎么樣……
這其實也沒什麼,只不過是兩個男女之間的一點小花絮而已。可問題壞在胡天才那張臭嘴上,他把這種事當作一種榮耀,在麻將桌上公開了,這便勾起了那些狗一樣的男人的欲望。他們合起伙來贏小米的錢,贏了錢也是記賬,結果小米就輸得更慘,最後小米就和所有的麻友都有了那種男女之事。
3
小車在水芙蓉飯莊門前停下來。老芶引著老水往裡走,迎面一幫袒胸露腹的小姐圍上來,騷里騷氣地問兩位先生需不需要服務。老芶沖老水冒出一臉壞笑,說:“大主編,要不給你弄個小姐玩玩?”老水連連擺手,說:“別,別弄那亂七八糟的,咱消費不了!”兩人撥開小姐們進了屋,身後傳來一陣放蕩的鬨笑。
酒菜上來,接連幹了十來杯,兩人臉上就都見了些酒色。老芶說:“說句真心話,在圈子內我最佩服的就是你水老兄了!想當年,咱們那裡滿大街都是文學青年,可最後搞出大名堂的不就你老水一個人嗎?”老水擺擺手,說:“徒有虛名,徒有虛名啊!又不能當飯吃!今天這會你也參加了,這不明擺著,我們連飯碗都丟了!”老芶眼睛瞪得老大,說:“就憑你老水的名氣,還愁沒飯吃?憑《陽春白雪》在全市文化界獨一無二的優勢,還愁辦不下去?依我看,你們這叫守著金飯碗討飯吃!眼下關鍵是要解放思想,轉變觀念,要放下文人的臭架子,別搞什麼陽春白雪了,那玩藝兒曲高和寡,這年頭兒你就得搞市場需要的——”
吱扭——,門一開,又一道菜端上來,一同傳進來的還有門外坐檯小姐和食客們淫蕩的調笑聲。老芶接著說:“你就說這小姐行吧,為什麼屢禁不止?不就是有市場嗎?你想這幫小姐們,當初不是鄉野村姑就是下崗工人,恐怕連飯都吃不上,可觀念一轉,如今哪一個不腰纏萬貫?”老水苦笑道:“你不能讓我們也去當婊子吧?”老芶說:“我也就打這么個比方!不瞞你說,我今天是受胡老闆之託,來跟你談一筆交易的!他打算請你出山,給他寫一部個人傳記,在《陽春白雪》上發一發。人家看中的是你老水和《陽春白雪》的知名度,他說了,花錢咱不怕,只要能辦成,幾十萬不在話下!”
一番話把老水說得一陣心動,他想《陽春白雪》現在多么需要這樣一筆錢呀!但緊接著他還是搖了搖頭,嘆道:“可是——,多年來我對自己對刊物都有一個要求,那就是不寫不發吹捧的文章,不用文學去做任何的交易!雖然現在這個社會是個污染的社會,但我要在自己的心靈深處,要在《陽春白雪》這片文學聖地里,保留一塊淨土!”老芶不可理喻地搖搖頭:“都二十一世紀了,你怎么還是這樣一種心態?如今文企聯姻是時代潮流,是互惠互利、一舉兩得的事,怎么能說是污染了你那塊淨土呢?時代不同了,這年頭兒,聖人也得食人間煙火!”老水說:“你那叫既當婊子又立貞潔牌坊,我乾不來!”
來請老水之前,老芶在胡天才面前是拍了胸脯打了包票的。他沒料到老水這么固執,就有點著急道:“難道送上門的幾十萬你真的不想要?你那《陽春白雪》也不想辦下去了?”這話顯然戳到了老水的痛處,他顯出很矛盾很痛苦的樣子,擺擺手道:“我現在心裡很亂,你要是還把我當朋友的話,就請你不要拉我下水,不要再向我進攻了!”
老水回到單位,編輯們一聽說鐵飯碗砸了,一下子就炸了營,一個個變得六神無主,吵吵嚷嚷地亂作一團。老水心裡更煩,揮揮手道:“慌什麼?天塌下來有我頂著!我這就去找市委項書記,我就不相信文學就真的沒人關心了!”
項書記是分管文化的副書記,又是個業餘散文作家,對文學事業一向很熱心,給過《陽春白雪》很多的關照和支持。老水想,無論別人怎么樣,項書記是不會撒手不管的!
找到項書記,項書記卻苦笑道:“老水呀,現在我說話也不抵事了,不瞞你說,過幾天市領導班子換屆,我就到政協去了!”老水一驚:“什麼?項書記,你才多大年紀?怎么——”項書記擺擺手:“這事先不要聲張,你知道就行了,不是我不幫你呀!”
老水沒想到是這樣一種結果,他幾乎是失魂落魄地回到雜誌社,懵懵懂懂地感到到處瀰漫著一種低沉的情緒,亂亂鬨鬨的議論聲像蠅子似的充盈了整個樓道。人們都拿一種企盼的目光望著他,他羞愧地躲避開,徑直走到自己屋裡去。在屋裡愣怔了一下午,快下班的時候,他像突然想通了什麼似的,拿起電話,撥通了一個號碼,說:“喂,老芶嘛——”
4
麻將事件使小水所在的油泵廠遭受了嚴重的創傷,除了女會計小米和司機胡天才,廠長、副廠長和財務科長也牽涉在內,一下子就判了五六個。廠子從此臭名遠揚、一蹶不振,漸漸地連工資都發不出了,這在那個年代還是十分稀奇的事,工人們就投門子扒窗戶地紛紛調離。
當時小水已經開始在寫作上嶄露頭角,一年之中就有好幾篇詩歌和小品段子在縣報上發表。姜師傅就對小水說:“你看你文化底子這么厚,在這么個破廠也派不上用場,我給你往文化館推薦推薦吧!”文化館長是姜師傅的遠房表親,姜師傅一推薦,他就滿口答應了,說:“我們正缺這樣的筆桿子呢!”就把小水調過去當了專職創作員。幾年後,小水的小說在全國打響,後來又調到了市文聯。
這期間,胡天才還在獄中,不過誰也沒料到,正是這幾年的監獄生活,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同室的獄友當中,有一個被稱作小華僑的人,他的父親“文革”期間偷渡到南洋,因此連累了他。胡天才知道外面對海外關係的政策已經開始鬆動,所以一入獄就想方設法和小華僑套近乎,他有一種把任何人都能哄得嘀溜溜轉的特殊本事,很快就成了小華僑的“莫逆之交”。
事情朝著胡天才預料的方向發展。一年後小華僑平反出獄,已經成為南洋富翁的老父親重返故里,一次就給他留下好幾百萬。小華僑是很重義氣的人,幾次到獄中探望胡天才,最後居然花重金為他買了個保外就醫。
出獄後的胡天才就成了小華僑最親密的朋友,他陪著小華僑搓麻將、逛舞廳、泡小姐,天天形影不離。這樣過了半年,有一天下午玩完麻將,胡天才拉著小華僑到飯店喝酒。喝到天黑,胡天才說:“小爺兒,咱弄個野雞玩玩?”小華僑自從有了錢,沒少玩女人,這時候更是酒壯色膽,說:“玩玩就玩玩!”胡天才就神秘兮兮地在小華僑耳邊說:“隔壁屋裡有小姐等著你!”
小華僑心花怒放,醉醺醺地闖進去,一看床上果然躺著一個身穿透明紗裙的漂亮女人,就猛地撲上去。女人象徵性地做著反抗,這使得小華僑輕而易舉地就進入了她身體的深處,女人的身體就開始變得柔軟起來,嘴裡哼哼唧唧地發出一種讓人消魂的聲音。
小華僑幹得更起勁兒,他感覺到身體裡滿膛的子彈呼嘯而出……呯地一聲,屋門被撞開,幾個壯漢拿著棍棒闖進來,劈頭蓋臉就是一頓打。小華僑被打得頭破血流,在屋子裡四處亂竄。這時候胡天才跑進來,拉住小華僑大喊:“小爺兒,你上錯床了!”旁邊的幾個人掄著棍棒喊:“打死他!打死他!”小華僑抱住胡天才的大腿,殺豬般嚎叫:“老胡救命啊!”胡天才忙攔住那些人,說:“別,別,小爺兒的命值錢,打死錢就沒了!你們聽我的!”就把幾個人拉到門外。
過了一會兒,胡天才進來對小華僑說:“小爺兒,你闖大禍了!你知道你今天干的是誰?是趙閻王的表妹!人家是來走親的,還是黃花閨女呢!趙閻王說了,今天就要你的命!”小華僑一聽嚇得尿了一褲,差點兒昏死過去。趙閻王是這家飯店的老闆,當地黑幫的頭頭兒,殺人都不眨眼呀!他抱住胡天才的腿哭嚎:“老胡,這可怎么辦呀!你救救我呀!”胡天才說:“事到如今,只有花錢買命了!剛才趙閻王開了個價,這樣吧,你掏三百萬,我來幫你擺平!”
那天夜裡胡天才提了三百萬現款,和趙閻王的表妹一起鑽進了一輛計程車,後來有眼尖的人說趙閻王的表妹看上去好眼熟噢,好像就是前些年抓進去的女會計小米。
5
老水走進油泵總廠,不由得暗暗吃了一驚。好氣派好壯觀的一大片廠區呀,一眼都望不到邊兒!老水遠遠近近地審視著,想在這裡找回當年的歲月,後來,他搖了搖頭。老芶指著遠處一棟漂亮的白樓,詭秘地笑笑,說:“那就是總經理公寓樓,平時是不允許隨便出進的!裡面只有幾個女秘書和胡總一起住,其實他們就是那種關係,你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兩人來到樓前,幾個保全正揮舞著警棍堵在門口,一幫人圍在那裡吵吵嚷嚷的。老水問:“這是怎么回事?”老芶說:“去年企業搞改制,對職工一次性買斷了工齡,這幫職工覺得吃了虧,經常到廠里來搗亂!”
這話讓旁邊一個老工人聽到了,他立即沖老芶吼起來:“你胡說!怎么是我們搗亂?我們這些人為油泵廠拼死拼活幹了幾十年,讓他胡天才幾千塊錢就打發了!榨乾了油水就一腳踢開,他還有一點兒人腸子嗎?”老水望了他一眼,驚得差點叫出聲來——這個滿頭霜雪、面目清瘦、看上去已經老態龍鐘的人不就是姜師傅嗎?姜師傅顯然並沒有認出老水,他接著憤慨地嚷著:“他胡天才一夜暴富,還不是靠坑蒙拐騙,靠挖國家牆角、瓜分國家財富發的家?油泵廠發展了幾十年,光固定資產就上億元,還有那些無形資產呢,那是幾代業務員用火車票一張一張鋪出來的呀!只可惜我們用血汗掙來的這么一塊風水寶地、一塊淨土,最後失落到胡天才手裡,讓他五千萬就買下來了!這當中玩的什麼花活,能騙得了誰呀!檢察院要是真查一查,有的人早該槍斃多少回了!”
一個保全走過來,沖姜師傅吼道:“你胡說什麼!”隨手就是一電棒,把姜師傅擊倒在地。姜師傅掙扎著,破口大罵:“畜生!胡天才你們這幫喪盡天良的畜生!”緊接著圍過來幾個保全,像拎小雞似的把姜師傅連拉帶扯地拖走了。
老水被這場面驚得目瞪口呆,一顆心在嗓子眼兒里突突亂跳,然後又仿佛失重似的猛地跌落下去……他就這樣心神恍惚地隨著老芶上了樓,一個風情萬種的女秘書迎出來說:“胡總早躲出去了,不過他留下話,說晚上在野鴨子美食娛樂城為客人接風。”
野鴨子美食娛樂城位於城郊,單檐歇山式的建築,曲走的遊廊,幽暗的包間,低垂的帷幔,袒胸露乳的小姐,到處都瀰漫著一種曖昧纏綿的氣氛。晚上胡天才在這裡設宴款待老水,坐陪的都是縣裡有頭有臉的人物,除了幾個局長、廠長,還有一個主管工業的副縣長。幾個風騷狐媚的小姐分坐在老水他們中間。小姐們顯然和胡天才他們混得爛熟,除了斟茶倒酒,還不停地和他們打情罵俏,搞一些“摸瓜摘棗”的小動作。
按照當地的風俗,全桌的人共同喝過三杯酒,下面就自由結合,各找對手了。胡天才端起酒杯,來給老水敬酒。一連乾過三杯,胡天才感慨道:“真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想當初你老水在廠里當學徒工,還是一個小毛孩子,誰能想到如今居然成了一個大人物!”老水擺擺手,說:“我算什麼大人物?你胡總才是真正的大人物呢!光油泵總廠資產就上億元,這在全市才有幾個?”胡天才說:“說到底,是趕上好時候了,這年頭人家硬把錢往你手裡塞,就看你敢不敢要!要是前些年,你也知道,就為那么點事,我愣蹲了好幾年大牢。要不現在誰罵娘我跟誰急,我說這年頭兒多好,有錢花,有車坐,還有小姐玩,你還不滿足!”說著摟過身邊的小姐,把手伸進她懷裡,撫摸著那高聳的奶子,嘿嘿地笑,“老弟,只要你有一個好身子骨,有一個好腎,你就盡情享受吧!”
老水感到臉上火辣辣的,幾個廠長卻怪聲怪調地拍手喝彩,老芶接過話碴說:“要論懂女人,胡總是行家呀!”一個廠長壞笑道:“那當然,人家說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總有一個堅強的女人支撐著,我看像胡總這樣成功的男人身下,也必然有多個女人支撐著!”全桌人一片鬨笑。
老芶低聲對老水說:“這野鴨子是縣城最高檔的消費場所了,夠得上星級標準!”老水不解地望他一眼。老芶笑笑,說:“倒不是說飯菜有多好,主要是這裡美女如雲,有特色風味!這裡的陪侍小姐都是從全國各地挑選的,還有泰國、日本、俄羅斯的,要什麼味有什麼味!要不怎么叫野鴨子呢?今晚讓胡總給安排幾個外國小姐,咱也嘗嘗異國風味!”
鬨笑過後,副縣長帶頭與老水喝酒,他說:“水主編的大名我早就聽說過,今天能把你請來,是我們的榮幸啊!來,我敬你一杯!”老水受寵若驚,連連說:“不敢當,不敢當!”端起杯來一飲而盡。副縣長又說:“胡總是咱們縣改革開放中湧現出來的傑出企業家,幹了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去年購買油泵總廠,出手就是五千萬,這需要多大的膽識和氣魄!今天把你請來,就是要藉助你的神筆,把他的先進事跡宣傳出去!這件事就拜託你了!”說著又端起酒,與老水幹了杯。
接下來幾個局長廠長輪番來給老水敬酒,幾圈下來,老水就覺得騰雲駕霧似的飄忽起來。又吃喝一通,幾個廠長嚷嚷著要自由活動,就率先摟著小姐出去了。胡天才拍拍身邊的一個小姐,指著老水說:“這是今天最尊貴的客人,你一定要陪他玩好!”小姐就上來拉老水,嗲聲嗲氣地說:“走,咱出去活動活動!”老水醉眼矇矓地不知所云,低聲問身邊的老芶:“活動什麼?”旁邊的幾個人大笑。老芶慫恿說:“你去了就知道了!”就和胡天才一起往外推他。老水被小姐熱情地拉扯著離了席,恍恍惚惚地進了包間。
包間裡光線很昏暗,僅有的一隻小型螢光燈高高地掛在屋頂。隱隱約約能分辨出,靠牆放著一張單人床,上面擺著枕頭,鋪著被褥。借著昏暗的燈光,老水這才注意到小姐長髮披肩,身材苗條,長相說不上多么漂亮,但很媚人。她臉上顯然化了濃妝,散發著一股濃濃的令人眩暈的甜香。
“脫衣服吧!”小姐很溫柔地說著,便很熟練很大方地脫了裙子,坐到床上去。
那一瞬間老水腦子裡一片空白,體內過量的酒精麻痹了他的神經,使他的思維還處在混沌停滯狀態。小姐白花花的身體在他眼前晃動,小姐的乳房豐滿而高聳,乳頭鮮紅鮮紅的,像兩隻紅櫻桃;小姐的腿修長而圓潤,肌膚光滑而細膩,屁股圓鼓鼓的,像兩隻小皮球,又像兩隻青蘋果;腰很細很靈活,腹部也很平坦……
老水愣神的工夫,小姐把他拉到了床邊,一隻手很溫柔地撫摸到了他兩腿中間……這種強烈的刺激使老水猛地一驚,出了一身冷汗,酒先醒了一半。他用力地把小姐推出老遠。一股無名的怒火倏然從他心底升騰起來,他伸手抓起床上的裙子,猛地摔到小姐臉上,低聲惡狠狠地吼了一句:“婊子!”然後摔門而去,門猛地撞到牆上,又咚地一聲彈回來……
老水走出娛樂城,一直走到冷冷清清的大街上。街燈已經熄了,只有像野鴨子這樣的幾座娛樂城還閃爍著光怪陸離的燈火,把這小城的夜晚渲染成一團看不透的混沌。老水邁著生硬的腳步,沿著蒼白的街道一直走下去,他不知前面通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