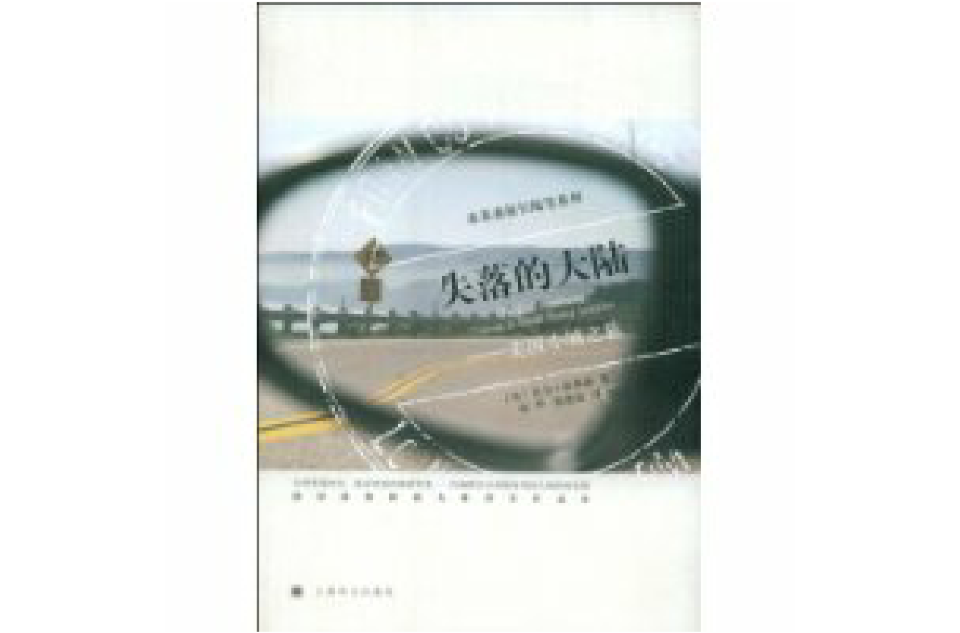作者簡介
比爾·布萊森,世界知名的非虛構作家,1951年出生於美國愛荷華卅『,曾任職於倫敦《泰晤士報》與《獨立報》,同時也為《紐約時報》、《國家地理雜誌》等撰文。作品主要包括旅遊類隨筆、幽默獨特的科普作品——比如《萬物簡史》、《母語》等等,橫跨多種領域,皆為非學院派的幽默之作。他的作品詼諧嘲謔的風格堪稱一絕,整體上舉重若輕,能讓普通讀者產生很強的認同感,不失為雅俗共賞的典範,深受讀者喜愛,也獲得很高的評價。每部作品均高踞美國、英國、加拿大暢銷排行榜前茅。
比爾·布萊森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紀的旅遊文學中占據一席之地,並成為目前世界公認的最有趣的旅遊文學作家,是因為他擅長用不同的眼光來看待他所遊歷的世界,他真切地捕捉到了一個旅人的內心感受。自然地理、生活情趣、社會時態,布萊森信手拈來無不奇趣。他的尖刻加上他的博學,讓他的文字充滿了智慧、機敏和幽默。作為在英國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美國人,他的作品又兼具了開朗風趣、絕不怕粗俗的美式調侃和冷峻犀利、一針見血的英式嘲諷。
序言
“俏鬍子”比爾·布萊森
1
本文介紹的比爾·布萊森(Bill Bryson)是當今英語世界非常多產且又“最能逗樂”的遊記作家之一,鋒頭之健不亞於當年的“披頭士”樂隊(據從網際網路上查得之Powells.com對布萊森的訪問記。訪員Dave Weich稱,在書店曾見排名前二十五位的暢銷書,其中布氏一人的作品即占五種。“鋒頭健過‘披頭士”’則是訪談錄的文題)。“俏鬍子”這個稱呼借自台灣皇冠叢書的系列書目:“俏鬍子,逛世界”——雖說從作者照片看,毛茸茸的紅鬍子配上黑眉烏嘴,用一個“俏”字形容,不免有些過譽了。
我的親家住在美國新罕布夏州的漢諾瓦小城,小城除了一所名氣不小的達特默思大學以外乏善可陳。恰好,布萊森於1996年攜妻孥返回美國定居時也選中了這座安靜的小城。今夏我赴美國省親,原想由鄙戚介紹,與布萊森會上一面,一睹“俏”容,再求個合影或簽名什麼的,誰知道閒不住的“俏鬍子”義出門高蹈雲遊去也!
最初引起我注意到比爾·布萊森的是他的兩本英語和美語的通俗史話,書題分別是《母語》(The Mother Tongue,1990年)和《美國製造》(Made in America,1994年)。兩本書雖說也附有詳盡的注釋和索引,像是學術著作,卻絕無經院派高頭講章嚇人的架勢,而是軼事趣聞迭出,基本上屬於清通曉暢又洞見深巾的社會語言學一類讀物,讀著讀著保你非笑出聲來不可。我一向主張學外文得激發必趣,一味苦苦“咬子彈”(bite the bullet)不行,所以曾從兩書中選出若干章節作為教材,使用效果良好。當然,過多的插科打諢有時不免影響敘事的準確性。例如,布萊森在《美囝製造》中斷言,作為美國開國元勛之一的班傑明。富蘭克林曾勸人吞飲香水以免屁臭。後有專家查實,說是關於香水和放屁的關係,富蘭克林一生中只提到過一次,那是在致布魯塞爾科學院的一封信里,富氏以打趣的口吻向科學家們挑戰,看看誰有本領讓腸道排氣時飄出香水味來。
據記載,在這兩部書之前,布萊森還編過一本叫作《煩難字解》(A Dictionaryof Troublesome Words,年代不詳)的詞典。此書我未見過,無由置評,但據識者稱,作者善解難詞,足見精於藻鑒,可說是為日後從事新聞工作和遊記寫作做好了充分的文字準備。
接著要談到的自然就是布萊森的遊記作品了。比爾·布萊森於1951年出牛在美國愛荷華州,二十一歲那年跳上冰島航空公司的飛機抵達盧森堡,復從挪威的漢默菲斯特出發,背負行囊,步行至伊斯坦堡,歷時四月有餘。1973年,布萊森首次踏上英國土地,兩年後娶妻成家,生兒育女,並於1977年在倫敦定居,開始為《泰晤士報》和《獨立報》工作。布萊森初寫旅行札記,原不無補貼家用的實利考慮,不曾想作品發表之後,好評如潮,出版商的稿約踵趾相接,這樣,布萊森便漸漸成了自由撰稿的專業作家,又舉家離開鬧市,遷往約克郡鄉間。1995年,布萊森和他的英國妻子辛西婭決定讓他們的四個子女換一種文化環境,兼之蓋洛普民意測驗恰在此時發表調查結果,聲稱有三百七十萬之多的美國人都認定自己曾遺外星人劫持,面對如此混沌民智,布萊森說“祖國需要我”,於是在對英國作了一次告別旅行後,他便帶著家人迂迴美國。到得此時,寫遊記已不再是一味的實利考慮,而是身心雙雙嚮往的至上白怡,按他自己的說法,“旅途發出海妖之歌般的蠱惑”,誘他一次又一次卜路,這才有了1998年阿巴拉契山問小道的跋涉,返回英國曆時五十四天的遠足,以及1999年的澳洲之旅。
2
儘管布萊森不把自己看作旅行家和遊記作家(“真正的旅行家郜要冒險,睡硬地,我卻總是住旅館”),他的如下一些作品通常都出現在書店的遊記柜上:《失落的大陸》(The Lost Continent,1990年)、《無處歸屬》(Neither Here Nor There,1993年)、《小島札記》(Notesfrom a Small Island,1996年)、《大國札記》(Notesfrom a Big Country,1998年)、《林中遠足》(A Walk in the Woods,1998年)和《烈日暴曬的地方》(In a Sunburned Country,2000年)。按布萊森本人的說法,上述第一部作品《失落的大陸》雖以“美國小城之旅”(Travels in Small Town America)為副題,重點在“失落”一詞,本質是懷舊和追逐,懷童年巡遊之舊,尋覓理想中的美國小城,但在涉足三十八個州以後,理想終歸烏有。《無處歸屬》,依我個人之見,是迄今為止布萊森最精彩的作品,寫作的緣起似乎仍在憶舊,即重現二十年前從挪威到伊斯坦堡的歐洲之旅:傲慢的巴黎人;橫衝直撞的義大利司機;以剷除英國特色樹籬為榮的推土機;挪威催人昏睡的電視;瑞士城鄉遍地高聳的高壓電線塔……《小島札記》是對英國告別旅行的產物,寫得很有感情,布萊森自稱這次旅行“就像跑完全程的運動員為向觀眾致敬而加跑的一圈”;“雖有百分之八十五或百分之六十五的英國人想不出英國有什麼東西值得他們自豪,我仍願為英國鼓吹。”《大國札記》是在英國報紙上連載時以及最後結集出版時所採用的書題,同書稍後在美國出版時改題為《故國陌路》(I'm a Stranger Here Myself)。布萊森在本書中詳盡描述了迂迴美國的頭十八個月中,他和自t2的英籍家人所經受的文化震撼,諸如“百分之九十三的離家外出之行,不管距離遠近,也不論目的何在,美國人都要開車!”《林中遠足》為布萊森贏得的文名可能勝於他的任何其他作品,因為這一回旅人要動真格了,須知阿巴拉契山問小路全長二千二百英里,乃是世上有人工標誌的最長山路,走完全程約需五個月!百分之九十的人半途而廢;百分之二十的人走完一周便敗下陣來,布萊森和旅伴走了整整一個夏天,走完八百七十英里的距離(相當於從紐約走到芝加哥),總算了卻一樁心愿。關於這個心愿,作家本人是這樣說的:
頭腦里有個微弱的聲音在說:“聽上去真帶勁!咱們乾吧!”我又想出好幾個理由。多年懶散之後,長途步行可使我保持健康;這還是個發人思考的好方法,使我得以重新領略故國的廣袤和美麗……當那些身穿迷彩褲、頭戴獵人帽的男子漢們在四A小餐館圍坐在一起,談論野外完成的非凡業績時,我將不再自慚形穢。我要帶上一點傲氣,眯起雙眼,眺望遠方的地平線,並拖長著聲調,像個男子漢般地哼哼說:“是啊,我在林子裡拉過屎呢。”
《烈日暴曬的地方》的寫作時機與2000年悉尼奧運會有關,因為出版商催得緊,據說不少有趣的素材都被割愛不用了。儘管如此,讀者仍可看到歷史上因為偷了十二根黃瓜而被放逐到澳洲蠻荒來的英國罪犯的故事;比之庫克船長晚到幾小時的法國船隊;蹈海的總理以及澳人為紀念他而修建的游泳池!等等等等。
不管是在蕞爾小島,或是莽莽林原,或是熙攘鬧市,布萊森總能在尋常的景物或人事中發現不尋常而值得一寫(有時是大書特書)的東西,並挖掘笑料,生髮出獨特的觀感。阿對差強人意的現實,他能領略有缺陷的美。他寧可用冷嘲的口吻對讀者詳述所見所聞;除了極個別的動情的例外,決不贊同在旅行紀實文字中作浪漫主義的美化,兼發矜誇高論。應當說,這既是布萊森寫作的特色,在不同程度上,也是現當代旅行紀實文學的共性。“文革”期間某位義大利導演在中國這片異域以上述手法拍了一部紀實電影,結果被汀青大批特批,其實如果了解上述手法普遍件的話,那批判多半是對著影子打拳了(shadow boxing)。
3
要說布萊森有什麼突出於共性之外的特點,表現在作品的內容方面,首先是他強烈的環保意識,無怪乎有評家把他的作品統稱為eco—literature(生態文學)。布萊森不但在阿巴拉契山道上對美國國家園林服務局聽任林木大片被伐提出嚴厲抨擊,又對美罔的汽車拜物教作了辛辣諷刺,更在回到英國約克郡作短訪期間發表公開演說,堅決反對醜陋的高壓電線塔污染約克郡谷地之美。
在寫作風格方面,布萊森的特點表現在英式和關式幽默時常集於一身。不少評家,包括布萊森本人,屢次提到英國文化對布氏影響之深,說他學會了“板著面孔說笑話,冷嘲和說話留有餘地”。作為在英囤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美國人,這種特點首先被人注意到也在情理之中。據有的訪員介紹,布萊森說話輕聲輕氣,不疾不徐,態度溫文爾雅,頗有英儒之風。但筆者從他的作品中看出,此人的美國本性根深蒂固,仍會不時流露。布萊森把英國式的冷嘲稱為“睿智幽默”(cerebral humor),其特點是曲折的譏消,促狹的戲謔,引得你會心微笑。的確,如讀者細品以下幾段引文,可以看出布氏老於此道;但是與此同時,那種直接、明快、誇張、不怕粗俗的美國式搞笑幽默是常與英式“睿智幽默”比肩並現的:
義大利人開車因為太忙而從不顧及車前路況。他們忙著摁喇叭,忙著做各種誇張的手勢,忙著阻擋別人超車,忙著做愛,忙著回頭教訓后座的孩子,還忙著大啖比板球球拍還大的夾肉麵包。而且常常是同時做著這幾樁事情。結果,待他們首次注意到你時,你已倒在他們車後的路上,出現在汽車的後視鏡里。
我給尿憋急了,又想趕到酒吧去,可是這位足有一百十二歲的旅館雜役是個盡職分子,非把客房裡的東西一一向你介紹,還要你跟著看他演示蓮蓬水龍和電視的操作法。“多謝了,沒有你我肯定連壁櫥也找不到,”我說著塞了一千里拉的小費在他袋裡,多少用上一點暴力把他推出門去。我不喜歡粗暴待人,但這會兒我覺著憋得好像胡佛大壩快要決堤了。
(上述兩段摘譯自《無處歸屬》)
我大汗淋淋上了船,心中有些發悚。我不好水,連在腳踏船上都會鬧頭暈。而今置身在這叫作“搖啊搖”(定是“住前搖,翻個身”的縮寫)的渡船上,把性命託付給了這么一家輪船公司,情況自然更糟了。這家公司的紀錄遠非完美,時常忘記關上船頭的門,航行途中這樣做相當於跨進浴缸時忘記脫鞋。
(譯自《小島札記》)
她不停地嘮叨,唯有在疏通一下耳咽管時才稍歇一下。所謂疏通,就是頻頻捏莊自己的鼻子,然後噴發出一串帶爆破聲的鼻息,叫人驚跳,而且足以嚇得狗兒跳下沙發,逃到鄰室的桌子底下去。
(譯自《林中遠足》)
本人睡覺既非肅默無聲,模樣更不雅觀。多數人打瞌睡時的樣子似乎表示他們需要一條毯子,而我的樣子似乎更需要醫生的關照。我睡覺時像是注射過了一種強效的實驗用肌鬆弛劑:兩腿大張,像在誘惑別人來做什麼壞事情。我的頭不時前傾,就像不住點頭的玩具鴨,把滿嘴約四分之一黏乎乎的流涎傾瀉在膝上,然後一個後仰,開始重新充注口水,並發出一種馬桶水箱灌水漸滿的聲音。
(譯自《烈日暴曬的地方》)
採訪布萊森的人時常問起他受其他遊記文學作家影響的程度,布萊森多作規避,說什麼“遊記文學就像是遊人從某一景點往家裡發回的叫信片內容的總和,自然是因人而異的”。但同時他又承認,自己非常喜愛保羅·希羅克斯(Paul Theroux)的寫景義字。希氏參加過“和平隊”,閱歷遠比布萊森豐富,對亞非兩大洲的了解,遠非布萊森可及萬一,除遊記類文字,還寫小說。唯有在“迷戀新鮮空氣”(希羅克斯作品書題Fresh Aif Fiend之擬譯)方面,兩人才頗相似。布萊森在2000年10月編了一部《最件美國遊記作品》的集子,或許讀者從中可以看到他欣賞的是威爾·弗戈森(Will Ferguson)還是戴維·西達律斯(David Sedaris)?有一個奇怪的現象:我國出版界近年來很善於捕捉域外書汛,然後隨俗急進。趕譯快出兒童讀物哈利·波特系列就是一例。在遊記文字方面,筆者看到彼得·梅爾的《重返普羅旺斯》等早已譯出,唯有比爾·布萊森猶是一片空白。出版界哪位有識之十願來填補這一空白呢?
本文最後借用“傳媒上的書”(Books in the Media)一位評家的話作結:come back soon,Bill 1我借用這活有三層意思:一、快把布萊森的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二、願布萊森早H到亞非拉來旅行(伊斯坦堡可不是亞洲!);三、願下次冉訪漢諾瓦時不再緣慳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