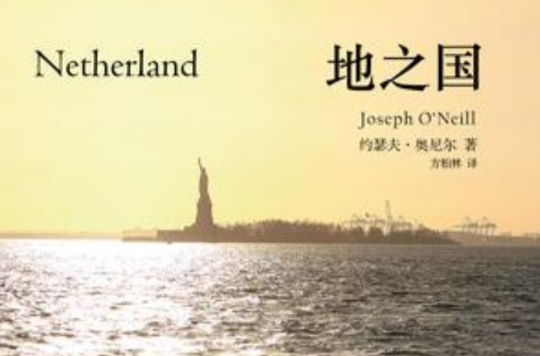內容簡介
漢斯一家在“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前的住所靠近世貿中心,“9·11”後,當局要求他們短暫地搬離住所,他們因此住進了切爾西酒店。酒店的房間,根本無法跟他們位於特里貝卡頂樓的舒適公寓相比,在當局允許他們搬回去住後,漢斯他們卻還是選擇留在了酒店。這其實是迴避表現,害怕觸景生情。漢斯還遭遇了睡眠障礙,常常到夜深人靜還無法入睡,大貨車駛經路面坑窪處的聲音在他聽來“大得有如爆炸”;有時他會分不清到底是警車在叫,還是兒子在哭,於是就會從床上一躍而起,走到兒子的臥室,“無助地親吻他”,然後溜到陽台上,站崗放哨。好不容易睡著了,卻反覆做同一個噩夢,夢見他在捷運上撲向一個炸彈,從而挽救了全家,而且這確實是個噩夢,夢中的炸彈每次都爆炸了,將他驚醒。
早上起來上班時,他害怕經過時報廣場捷運站,因為車站大廳里有一個小個子西裔,在和一個真人大小的假人跳舞,這會讓他“生起一陣驚恐”。對日常生活,漢斯也失去了原先的興趣,唯一的感覺就是“累”。同時,他發現和妻子已經難以溝通,他們夫妻已經喪失了對話的能力。此外,不時出現的“閃回”記憶也不斷困擾著他。
這種種現象,都讓漢斯誤以為是自己和妻子之間出了問題。可是從他親吻兒子以及在夢中還不忘保護家人的舉動,可以看出,他其實是深愛妻兒的。他是遭到了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困擾。這種心理創傷已經深深影響到他的生活,而他並不自覺,也從來沒有與妻子蕾切爾談論過“9·11”。
漢斯的妻子蕾切爾主動提出分居,其實她的創傷後應激障礙比漢斯還要嚴重。機車駛過的聲音,有時都能把她嚇得“吐了起來”,救護車的聲音與警車的聲音在她聽來象是“哭叫”。與丈夫一樣,蕾切爾也不願意經過時報廣場,因為害怕時報廣場“會成為下一個攻擊目標”。她動輒哭泣,有時睜著眼睛躺在床上一動不動,其實並沒有睡,漢斯認為,他妻子是過度“興奮”的表現,其實都是
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典型症狀。蕾切爾最終決定返回英國。這其實是一種極端的“迴避”表現。因為繼續住在美國的恐懼讓她難以忍受,甚至連看到丈夫都會讓她觸景生情,所以當漢斯提出和她一起回去時,她一口回絕了。這種回絕在丈夫看來,卻成了分居的信號。
就連漢斯夫婦幼小的孩子,也不可避免地留下“9·11”事件的心理創傷。雖然孩子還不可能理解“9·11”,但父母的心理創傷會“以尚未被確認的方式,從父母的無意識轉入孩子的無意識,在主體自己的心理空間中,它像腹語者、像陌生人那樣活動”。孩子每晚做噩夢就是這種心理創傷的具體表現。
創作背景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美國民航4架客機,兩架撞毀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大廈”,一架撞塌華盛頓五角大樓的一角,一架墜毀。這一系列襲擊導致3000多人死亡,並造成數千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約瑟夫·奧尼爾從“9·11”事件後就開始動筆,用了7年時間,創作出《地之國》作品。
人物介紹
漢斯——“我”
漢斯來自荷蘭海牙,從小就喜歡打板球。七歲時,加入足球和板球俱樂部胡特·布萊特·斯坦特俱樂部,既踢足球又打板球。至15、16歲時,他更愛板球。漢斯的母親他帶加入了當地的板球隊,她在場外靜靜地觀看他打球,有時候甚至從上午十一點坐到下午六、七點;漢斯十三歲那年,他為了溜冰而逃學,母親高大的身影出現在冰面上,她沒有責備已經羞愧知錯的漢斯;每個星期六,“漢斯要去打球,身為教師的母親就會騎著車子跑兩個小時替他送報紙,紅色的挎包、鮮艷的雞心領套頭衫、母親看漢斯打球時,腿上搭著的紅色毯子營造出記憶中溫暖的氛圍。漢斯原本以為,母親所做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都是父母天經地義該做的。漢斯開始明白,母親給予自己的不只是關懷和愛,還有面對生活所需要的樂觀、堅強、寬容和責任。
到萊頓大學學古典文學後,其板球生涯開始走下坡路。24歲回海牙工作。數年後,他到倫敦D銀行做分析師時,加入南方銀行板球俱樂部。可數個賽季後,他就退出了。
“9·11”之後,漢斯的妻子蕾切爾執意帶著孩子回到倫敦,他們二人的婚姻瀕臨崩潰。漢斯如此形容自己的境況:“生活本身都已虛幻,‘我’的家庭,‘我’生活的脊樑,突然瓦解了,‘我’迷失在一個無脊椎動物時代”。漢斯平素因為忙於生活而疏忽母親,對此他並不覺察。是母親的死刺激了他,重新勾起他對母愛的懷念。
恰克
恰克來自加勒比島國特立尼達郊外的拉斯·拉姆斯,1975年帶著新婚妻子安妮到美國,曾做過水泥工,乾過修屋頂、裝卸等工作。他承包裝修工程,漸漸得到認可後,便承包各種其他工程了。工程隊成員來自世界各國,有孟加拉人做水泥活,愛爾蘭人做粉刷活,義大利人做屋頂,格瑞那達人做木匠活。1992年,恰克自己買樓並裝修,還與艾貝爾斯基成立房地產公司,但這位移民中的“蓋茨比”卻一直處於身份認同危機之中。
作品鑑賞
主題思想
對生命意義之追尋
作者在《地之國》小說中,通過主人公漢斯一家和恰克在“9·11”恐怖攻擊事件後的經歷,展示了這一事件給美國普通民眾造成的個人心理創傷,並探討了克服創傷的正確途徑。
雙子塔樓之被炸毀使漢斯深感無助,其妻攜子回倫敦後,他陷入“恐懼與顫慄”,患上人類生存普遍的“精神疾病”——絕望,更面臨生存與毀滅的人生十字路口。於是,他孤身蜷縮於切爾西酒店,感覺像在住院,獨自臥床近一周,似已進入一種非我之“耗盡”狀態。他所體驗的是“難以名狀的痛苦”,是分離的、變形的世界和類似吸毒幻游者的“非我”存在。他成了“空心人”。就在漢斯被邊緣化及被從心靈中放逐的過程中,他結識了特立尼達移民恰克,重拾板球並參加比賽,這使漢斯幾近破碎的生活,重新綻放出生命之花。
板球將漢斯帶回到過去,成為連線其在歐洲的往昔與美國的當下之橋樑,亦給漢斯破碎的人生帶來一致性與連貫性,在漢斯昔日生活的不同國家的城市與其似乎封閉的人生間建立了一種聯繫。雖然此時板球與昔日大為不同,然在其內心深處,板球鬱積的是一種“無言的渴望”,此種渴望關係他曾見過幻想過,而消逝已久的那些視野,那些潛在的可能性,那些曾經的誘惑——它觸及他那些私人化、令人內疚的“傷逝感”。在一個“叫人不堪承受的急速地獄化”的後9·11世界,當難以入眠時,漢斯就回憶起在阿姆斯特爾芬的擊球、在鹿特丹第二外野手位置的俯衝撲球、在海牙板球俱樂部三次讓擊球手撲空,這些板球片段深深烙印在他記憶深處,幫他在現實中度過漫漫長夜。板球亦將漢斯與其他移民、與紐約城聯繫起來,而在不同公園和板球場地的比賽,則成為其打開後9·11時代的紐約之鑰匙。
城郊不同環境的板球比賽不僅賦予漢斯的生命以新的內涵,而且與其童年、母親和母國荷蘭建立起新的聯繫,從而使其生活呈現連續而完整的生命“樣態”。板球喚醒了漢斯沉睡已久的情感與激情,使其生命形成跨越大洋與國界的視界與關聯。
板球使漢斯適應因9·11而產生劇變的紐約,成為其精神寄託,亦成為其從都市、集體、社會與個人創傷中回歸與重尋生命價值與意義的載體。2002年夏,漢斯在荒廢數年後重新開始打板球。他在斯塔騰島倫道夫·沃爾克公園打板球時,結識了恰克。其隊友是來自特立尼達、蓋亞那、牙買加、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國家的移民,有印度教徒、基督教徒、錫克教徒和穆斯林。雖是國際混合隊,他們賽前卻在隊友拉麥什帶領下“攏成一圈禱告”。雖是紐約唯一打板球的白人,漢斯卻在板球比賽中、在這些移民隊友中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和歸屬感,以至於回英國後,當蕾切爾在儲藏室找到其板球棒和板球包時,他激動地拿著球棒,不忍釋手。
板球是漢斯克服9·11事件及其對他生活創傷性影響的方式,亦是他重新定位、重找秩序而回歸正常生活的方式,從而使其生命在板球比賽中重新綻放。2003年夏,漢斯別的一切都不乾,而只打板球了。他甚至喜歡躺在布賴恩特公園草地上,聞到板球的氣息。他還和恰克開車到弗洛伊德·本尼特機場,即恰克所謂的“禿頭鷹機場”。他們給外場割草,品味割草的節奏與氣味,體驗在柴油機突突聲中“時光流逝的那種充實感和滿足感”,享受“這整個事業的榮耀和懸念”。在獲悉恰剋死訊後,漢斯還打開谷歌地圖,飛臨美國,到長島、曼哈頓、布魯克林,然後到弗洛伊德·本尼特機場,去看恰克欲實現其“美國夢”的地方。
恰克及其他移民以“他者”的身份生活於斯皮瓦克所言的“在他者的世界裡”,故存在一種身份焦慮。正是對自己身份的焦慮,才使他們更渴望在美國建構其身份,使其身份得到主流文化的認同。在這一身份建構與身份認同過程中,作為移民的他們不僅使其生活得以為繼,而且使其生命得以延續,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也就體現在這一建構與認同的過程中了。
恰克欲通過打板球比賽,建立板球俱樂部,推廣板球運動等活動,使其移民身體得到認同,並最終將他自己融入“他者”文化之中。板球比賽,可使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找到共同之處。“隨著紐約板球俱樂部的發明,‘我們’會在美國的歷史上掀開嶄新一頁。”
恰克欲建立紐約板球俱樂部並在美國推廣此項運動,通過板球文明規則使各族裔平等團結,讓世界和平。此乃其在被邊緣化的語境中所欲實現的一種現時話語權力。恰克試圖將混雜的個體成分聯成一體,以板球為媒介而創建一種“共同文化”,隨時準備將這一切變成現實。恰克找到了生命外的“立足點”,其生命價值在災難中得到了體現。
9·11事件、反恐戰爭所帶來的死亡,以及恰克之死證明生存的荒謬性,但更重要的是,死亡使漢斯發現生存的價值與生命的意義,此乃生活全部意義之所在。因此,他在人生的關鍵時刻進行選擇,敢於進入生活,即負起責任,切實進入有限的生命存在。當在賭場面對輪盤賭桌而想到其人生篇章如此悽慘如此倒霉時,他突然“經歷了內心的一個大轉向”而頓悟了,他“決定搬回倫敦去”。
漢斯從紐約調回倫敦後,相信倫敦“會回到原來的面目”。銀行派人從紐約來協助,當這位同處異國的“老鄉”向他諮詢有關婚姻建議時,漢斯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個以身作則的年紀,長大成人了”。在成長過程中,漢斯不斷有“閃回的體驗”,這種記憶成了連線過去與現在的紐帶,使“存在的短暫悲劇轉變成永恆的喜劇”。
漢斯與蕾切爾的超越,則是回歸家庭,回歸世俗生活。蕾切爾覺得自己有責任與漢斯白頭到老,這責任是“幸福的責任”,其複合是過去的延續,而漢斯卻從男孩成長為男人。漢斯來到蕾切爾身邊,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說,只是將手搭在她肩膀上。生命“就是那個必須不斷超越自己的東西”,在超越中,生命也就得到了“升華”。漢斯帶著笑容,面對家人。他將目光從兒子轉向妻子,又回到兒子身上。生命終於在回歸家庭後“讓一切都升華了”。
藝術特色
將創傷記憶轉化為敘事記憶
通過書面或述說的方式,將創傷記憶轉化為敘事記憶,也是治癒創傷的一種有效手段。在敘述的過程中,創傷者的內心傷痛得以宣洩,並慢慢地接受了過去所發生的事情。這樣,過去的創傷得以解構,也能重拾自我,並重新認知和定義現實世界。回到倫敦開始新生活兩年後,恰克的死訊再次勾起了漢斯對“9·11”及其後那兩年迷惘、苦悶生活的記憶,並促使他以回憶錄的方式重新梳理那段經歷。在該小說的結尾,漢斯完成了他的回憶,步行去倫敦眼大轉輪與家人會合。這時的他覺得,“這么走著我很開心”,當他轉過身找到家人時,注意到的是“‘我們’個個都在笑”。通過回憶,漢斯又一次對自己的心理創傷進行了治療,心理狀況得以進一步好轉。
詞語意象
該作品中多次出現照片這一意象。照片作為記憶的重要載體,被稱為“帶有記憶的鏡子”。而裝入相冊中的照片,非但記載了人生歷程中的重要節點,連線起來實際上就是完整的人生印記。漢斯有一個盒子,盒子裡裝滿了從小到大的照片,但是自己從未整理過。凌亂的照片象徵著漢斯以往雜亂無章的記憶碎片。恰克的女友,伊莉莎就專門從事給別人整理照片製作影集的生意。在她看來,將照片有序排列整理,就是將一個人的過去與現在有機地聯繫以來,見證每個人的歷史。伊莉莎的生意不錯,以此暗示現代人如漢斯者不在少數。漢斯離開紐約前,將兒子傑克的照片拿去給伊莉莎整理。面對整理過的照片,漢斯感慨道:“她的作品確實讓‘我’開心——孩子微笑的照片,那誘惑誰能抵擋呢——這影集,記錄了兒子永不停息,自我消解的過程。”
作品影響
2008年《地之國》被《紐約時報》評為年度十佳圖書之一。2009年《地之國》獲得美國筆會福克納獎文學獎。
作品評價
《地之國》小說,是“最風趣、最憤怒、最嚴肅、最淒涼”的小說。
——《紐約時報》
《地之國》就是人們所期待的“後9·11小說”。
《地之國》小說是書寫記憶之傑作,它通過跨文化視野再現歷史並表達對人類生存與悲情的審慎思考。
——朴玉(吉林大學公共外語教育學院副教授)
作者簡介
約瑟夫·奧尼爾(Joseph O’Neill)美國作家,1964年2月23日生於愛爾蘭,先後在莫三比克、南非、伊朗、土耳其、荷蘭長大,曾在英國劍橋大學學習法律,做過律師。作品有:《生命如斯》、《微風輕揚》、《地之國》等。
 約瑟夫·奧尼爾
約瑟夫·奧尼爾
 約瑟夫·奧尼爾
約瑟夫·奧尼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