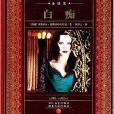陀妥耶夫基(1821-1881),俄國十九世紀著名作家。《白痴》是他的重作品。 娜斯塔霞是個外慧中的絕色女子,惜乎命途多舛,成了得堡某巨富的情婦。然而她對此人只有極度的輕蔑和憎恨,當她聽說那個淫棍即將“明媒娶”名門千金時,便萌生了的念頭。她的對手們則在各種利益驅動下正陰謀編織一張制伏這個弱女子的羅網。就在錯綜復的關係決定了極度敏感的時間和地點,被那些“聰明人“目為十足的“白痴“先天有病的破落貴族梅詩金公爵糊塗闖進了衝突一觸即發的旋渦…… 無論是《白痴》的讀者還是觀眾乃至讀者兼觀眾,看到女主人公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將十萬盧布一捆鈔票扔進壁爐付之一炬,恐怕任誰的心靈都會經受一次強烈的衝擊。這一堆燒錢的烈火,象徵著陀氏創作的一個高峰,它不僅在星光燦爛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壇,而且在整個世界文學寶庫中也當之無愧地堪稱經典。
基本介紹
- 書名:世界文學名著典藏•全譯本:白痴
- 譯者:耿清之
- 出版日期:2006年9月1日
- 開本:32開
- 品牌:墨人圖書
- 作者:費奧多爾·陀斯妥耶夫斯基
-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 頁數:712頁
- ISBN:7216047184, 9787216047180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文摘,
內容簡介
無論是《白痴》的讀者還是觀眾乃至讀者兼觀眾,看到女主人公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將十萬盧布一捆鈔票扔進壁爐付之一炬,恐怕任誰的心靈都會經受一次強烈的衝擊。這一堆燒錢的烈火,象徵著陀氏創作的一個高峰,它不僅在星光燦爛的十九世紀俄國文壇,而且在整個世界文學寶庫中也當之無愧地堪稱經典
作者簡介
作者:(俄)費奧多爾·陀斯妥耶夫斯基 譯者:耿清之
文摘
書摘
十一月底,融凍的日子,早晨九點鐘左右,彼得堡一華沙鐵路上有一節列車開足了馬力,駛近彼得堡城。天氣潮濕,且有重霧。鐵路兩旁,十步以外,難於從車窗內辨清什麼。旅客
中有從國外回來的.但是最擁擠的是三等車,全是些做生意的小人物,不是遠處來的。大家自然都很疲乏,在一夜之間大家的眼睛全疲乏無力,大家全凍僵了,臉全是灰黃的,和霧色相似。
在一輛三等車內,有兩個旅客,從黎明時起在窗旁對坐。兩人都是青年,都不帶多少行李,都不穿漂亮的衣服,兩人的臉貌都十分特殊,兩人都願意彼此搭談。假使他們兩人彼此知道他們在這時候如何的特別顯著,自然會驚訝何以機會竟如此奇怪地使他們兩人對坐在彼得堡一華沙列車的三等車廂里。他們中間一個身材不高,二十七歲模樣,頭髮蜷曲,且呈黑色;灰色的眼睛小而發光;他的鼻子寬闊平扁,臉上顴骨聳起;柔薄的嘴唇不斷地疊成一種橫霸的、嘲笑的、甚至惡狠狠的微笑;但是他的額角很高,構造得極好,可以抵消臉的下部的不正直的發展。在這臉上特別顯出死般的慘白,給這青年人的全部面貌增添疲乏的神色,儘管他具有充分堅固的體乾。同時他還帶著一種情熱到痛苦地步的樣子,和他的橫霸的、粗暴的微笑,嚴厲的、自滿的眼神不相諧和。他穿得很暖和,穿了一件寬大的、小狗熊皮的、黑色的、緊領的大氅,因此夜裡沒有受凍,但是他的鄰人不得不在發戰慄的背上忍受俄羅斯的、十一月的、潮濕的寒夜的一切冰冷。對於這寒夜他顯然毫無準備。他身上穿著極寬闊的、厚重的、沒有袖子的披肩,外帶大兜囊,就和在遼遠的國外,例如瑞士或義大利北部,旅客們在冬天時常穿著的一模一樣,自然他們並不想趕從埃特庫能到彼得堡那樣長的路程。在義大利有用,而且感到滿意的一切,到了俄羅斯便不完全有用了。這披肩和兜囊的主人是一位青年,也有二十六、七歲,身材比普通人高些,頭髮金黃得厲害,且極濃密;臉頰陷凹,長著輕輕的、尖銳的、幾乎完全白色的小胡。他的眼睛是大的、蔚藍的、凝聚的。眼神里有一點靜謐的、嚴重的東西,充滿一種奇怪的神色,使有些人一看就猜出這人有癲癇症。但是這青年人的臉是愉快的、柔細的、乾淨的,不過沒有色彩,而現在甚至凍得發紫。他的手裡握著一隻小小的包袱,這包袱是一塊褪色的舊綢布,大概這就算他的全部的行李。他的腳上穿著厚底的皮鞋和鞋罩——全不是俄國式樣。穿著狹領皮大氅的、黑髮的鄰座的人看清了這一切,一部分是由於無事可做,終於發問起來,帶著一種無禮貌的嘲笑,在這裡面,遇到鄰人有所失意時,有時會不客氣而且忽略地表露出一種快樂來的:
“凍僵了么?”
他當時聳了聳肩膀。
“冷得厲害,”鄰座的人異常欣悅地回答,“您要注意,這還是融凍的日子。假使是冰凍的天氣,會怎樣呢?我甚至沒有想著我們這裡會這樣冷,不習慣了。”
“從外國回來么?”
“是的,從瑞士來。”
“啊!原來如此!……”
黑髮的人打了口哨,哈哈地笑了。
P5-6
十一月底,融凍的日子,早晨九點鐘左右,彼得堡一華沙鐵路上有一節列車開足了馬力,駛近彼得堡城。天氣潮濕,且有重霧。鐵路兩旁,十步以外,難於從車窗內辨清什麼。旅客
中有從國外回來的.但是最擁擠的是三等車,全是些做生意的小人物,不是遠處來的。大家自然都很疲乏,在一夜之間大家的眼睛全疲乏無力,大家全凍僵了,臉全是灰黃的,和霧色相似。
在一輛三等車內,有兩個旅客,從黎明時起在窗旁對坐。兩人都是青年,都不帶多少行李,都不穿漂亮的衣服,兩人的臉貌都十分特殊,兩人都願意彼此搭談。假使他們兩人彼此知道他們在這時候如何的特別顯著,自然會驚訝何以機會竟如此奇怪地使他們兩人對坐在彼得堡一華沙列車的三等車廂里。他們中間一個身材不高,二十七歲模樣,頭髮蜷曲,且呈黑色;灰色的眼睛小而發光;他的鼻子寬闊平扁,臉上顴骨聳起;柔薄的嘴唇不斷地疊成一種橫霸的、嘲笑的、甚至惡狠狠的微笑;但是他的額角很高,構造得極好,可以抵消臉的下部的不正直的發展。在這臉上特別顯出死般的慘白,給這青年人的全部面貌增添疲乏的神色,儘管他具有充分堅固的體乾。同時他還帶著一種情熱到痛苦地步的樣子,和他的橫霸的、粗暴的微笑,嚴厲的、自滿的眼神不相諧和。他穿得很暖和,穿了一件寬大的、小狗熊皮的、黑色的、緊領的大氅,因此夜裡沒有受凍,但是他的鄰人不得不在發戰慄的背上忍受俄羅斯的、十一月的、潮濕的寒夜的一切冰冷。對於這寒夜他顯然毫無準備。他身上穿著極寬闊的、厚重的、沒有袖子的披肩,外帶大兜囊,就和在遼遠的國外,例如瑞士或義大利北部,旅客們在冬天時常穿著的一模一樣,自然他們並不想趕從埃特庫能到彼得堡那樣長的路程。在義大利有用,而且感到滿意的一切,到了俄羅斯便不完全有用了。這披肩和兜囊的主人是一位青年,也有二十六、七歲,身材比普通人高些,頭髮金黃得厲害,且極濃密;臉頰陷凹,長著輕輕的、尖銳的、幾乎完全白色的小胡。他的眼睛是大的、蔚藍的、凝聚的。眼神里有一點靜謐的、嚴重的東西,充滿一種奇怪的神色,使有些人一看就猜出這人有癲癇症。但是這青年人的臉是愉快的、柔細的、乾淨的,不過沒有色彩,而現在甚至凍得發紫。他的手裡握著一隻小小的包袱,這包袱是一塊褪色的舊綢布,大概這就算他的全部的行李。他的腳上穿著厚底的皮鞋和鞋罩——全不是俄國式樣。穿著狹領皮大氅的、黑髮的鄰座的人看清了這一切,一部分是由於無事可做,終於發問起來,帶著一種無禮貌的嘲笑,在這裡面,遇到鄰人有所失意時,有時會不客氣而且忽略地表露出一種快樂來的:
“凍僵了么?”
他當時聳了聳肩膀。
“冷得厲害,”鄰座的人異常欣悅地回答,“您要注意,這還是融凍的日子。假使是冰凍的天氣,會怎樣呢?我甚至沒有想著我們這裡會這樣冷,不習慣了。”
“從外國回來么?”
“是的,從瑞士來。”
“啊!原來如此!……”
黑髮的人打了口哨,哈哈地笑了。
P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