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國內二手奢侈品行業悄然興旺,我們訪談了若干二奢從業者,希望了解市場上被釋放的大批奢侈品從何而來,以及,透過這些美麗又昂貴的東西從被渴望到被忘卻的故事,來觀察那些正在出售它們的職業女性。上世紀90年代,日本曾由第一奢侈品大國轉為第一二手奢侈品大國,在不少業內人士眼中,中國也出現了類似的苗頭。
處理舊包,就像割捨一段記憶和關係,黃金也有重量,負重太久,總有拿不動的時候。
想賣包的人太多了
冬日,北京長楹天街的架空走廊,臨時圍起了一座玻璃房,像水果集市一樣展示著總價超過五千萬的數百個名牌二手包。從早上10點商場開業起,玻璃房外就排起了長隊,每人在進入前需要先領取一次性手套。不過,令路人紛紛側目的是對面的一條更長的隊伍,女人們拎著行李箱或大的蛇皮袋,裡面都是她們想來賣掉的包。
一個穿貂的濃妝小個子女生放倒箱子,把用到褪色的數個香奈兒擺了一桌。“你這是有錢的比較早啊”,老孟摸著包像往常一樣拉起家常。他是一名二奢公司老闆,也是中檢認證的奢侈品鑑定師,見過超過一萬隻香奈兒,只要看一眼包,判斷它是哪一年產的,就能知道眼前的人財富的爬升點。“一隻三四萬,加起來幾十萬,那時候在北京能買個房了。”但這些舊包最後一共只賣了四萬二。
買包那一刻是溫情的,行業的回收估價是冰冷的。一個70後帶來了一整箱LV,說起手裡一隻LV,是她在北京奧運會前後買的。“我人生第一個LV啊”,當年sales力薦,說這是最新款,她當場花6000買下,現在只能賣2000。年輕時候她迷戀LV,現在終於厭棄,說以後想買Celine。老孟笑了,那這比LV還不保值。
想保值買什麼?買香奈兒。他笑眯眯地給了每個來客一點保值建議。
我之所以聯繫老孟,是在抖音上刷到了他發的回收紀錄視頻。在老孟的鏡頭裡,富人家庭像堆放雜物一樣胡亂堆砌著價值不菲的名包,隨後,老孟用手一拈,就像回收舊紙皮一樣,飛速報出數字、痛快打款。因為價格公開透明,每天,都有超過四十箱的包離開原來的主人,抵達他位於天津的辦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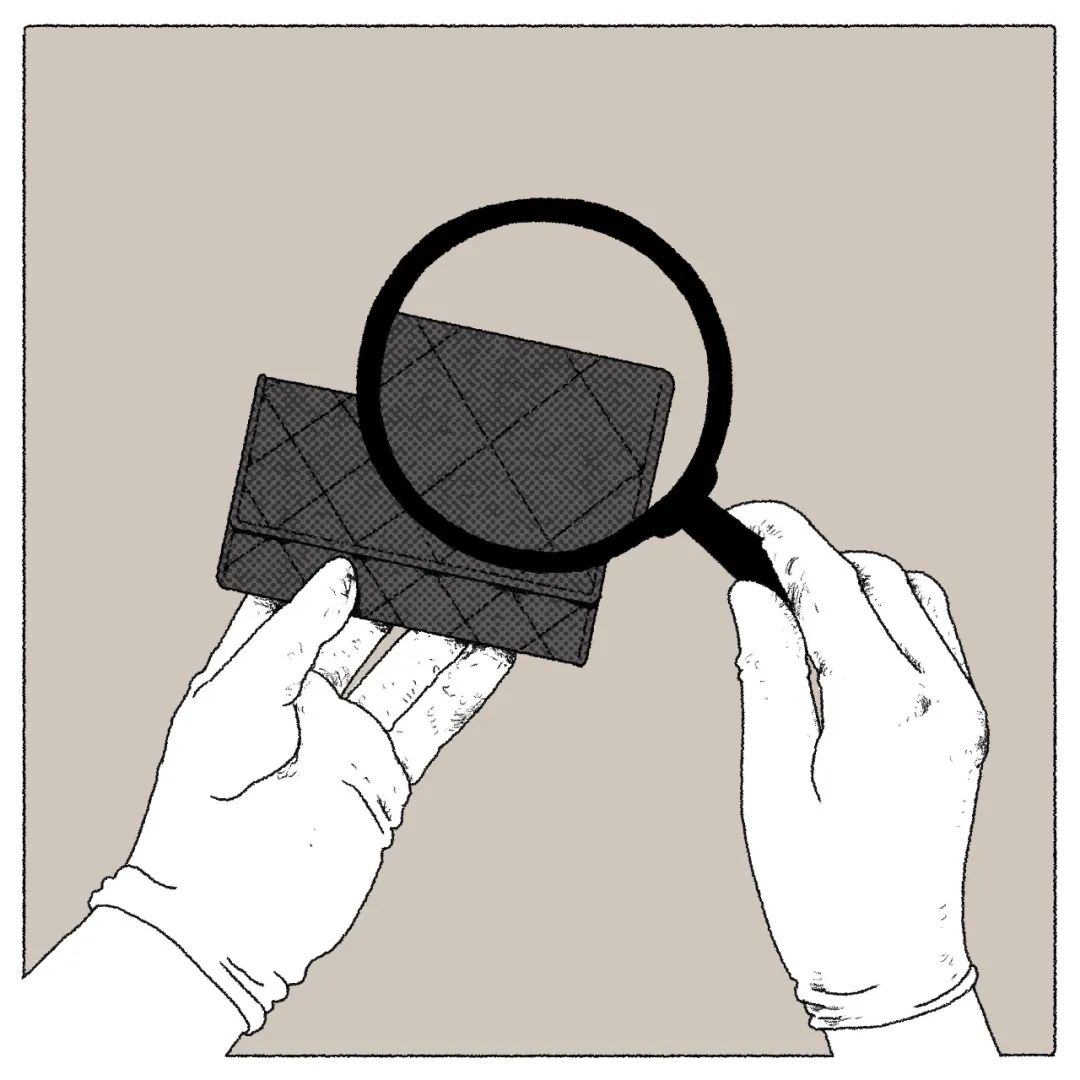
近年來,在大眾因疫情無法出國購物,以及直播帶貨助推等諸多原因下,二奢產業悄然風靡。一些藝人開始在直播間賣二手名牌包,銷量斐然,胡兵曾創下開播僅10分鐘就登上抖音帶貨榜第一名的記錄,一場銷售額破千萬。我想了解,這個存在已久的行業突然爆火的原因。
在長楹天街現場,我目睹了形形色色的包被放棄的理由。不少嶄新的包只是衝動購物的結果。有顧客在國外購物時,跟另一個中國顧客看上同一款包,為了較勁而買下來,買下的那刻很爽,回來就沒再用過。
有的包只是為了“買”,而不是“用”。一個戴著扎眼的香奈兒logo的毛帽子、穿著香奈兒全黑套裝、背一個香奈兒黑包的中年女人在桌前坐下,掏出數個黑色的盒子。周圍的目光聚集過來,像現場拆禮物一樣,老孟依次解開盒子上的山茶花絲帶、拆開墊紙,取出這些還散發著新品特有光澤的黑包,包上裝飾著碩大的白珍珠。其中一個包,老孟在原價基礎上減了兩千就收了。
老孟說,她每次來,都賣全新的香奈兒。“她太愛買了,很多北京的顧客工作壓力都很大,都是女強人、女總裁,她們就覺得,到香奈兒我就一通買,就開心,她知道賠錢,賠錢也買。她們通過消費去解壓,你有這種感覺嗎?”
“我嘗試理解下這個感覺。”我回答。
據一些業內觀察,從去年開始,大量有錢人開始出清自己的閒置,使得二手市場的供給突然增多。在老孟看來,大部分富人賣包,並不是缺錢用,只是因為家裡快放不下了,畢竟存放包的房子的空間價格比包更貴。
“他們極少是因為資金問題來賣包的,我一個月要收幾千家,連5家這樣情況的都沒有。”在實現財富自由的人的資產配置裡面,包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只是,他們眼下也需要維持資產的保值,“收一家貨十幾二十萬,能解決什麼事?賣點什麼都比賣包錢多。”破產富豪他也見過,那是連房子、車、表也賣了。他也接觸過生重病的人,她的愛馬仕包是剛從專櫃拿出來就賣給他了,她說,以後也用不上了。
現場,不少包被鑑定出是假的,其中不少是來自閨蜜、男友的禮物。得知是假包的那一刻,有人當場就哭出來。老孟曾經見到過有人帶來二三十個包,全是假的。至於箇中故事,他往往也不會過問,“有時我也會給顧客台階下,我會故意說是不是代購弄的?為了便宜而不小心買到假的,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人心裡知道這可能是假的。賣假包的人早把你心理分析得透透的,這個東西專櫃一萬三,賣你一萬,事實上全球哪LV都不打折,但架不住你就信。”

幾乎每個人都想把自己的奢侈品錢包賣了,但它也是一種嚴重折價的商品,原價幾千買來的出手只能賣幾百。老孟通常把這樣的貨賣到國外,“中國人現在不怎么用現金了。”
這次在展會上,他三五百塊錢收走不少堪稱破舊的名牌包,“那都是70後的東西,如果在八年前賣,也是能賣兩三千的,但就是不捨得,到明年,連三百都沒有了。”如果不是絕版的中古包,普通的名牌包會隨著時間而變脆、褪色,不斷跌價。老孟會如實告知她們,明年再賣,更不值錢。
買包錄
對有些職場新人來說,對奢侈品包的渴望可能是一座需要被翻越的山。有個朋友給我講過一個故事,她剛進時尚雜誌時,首先注意到的是每個人桌子上都放著的名牌包,這一幕給了她不小的衝擊。雜誌樓下就是北京的SKP商場,寫不出稿子的中午她時常去閒逛,半年後,她攢好錢去樓下拎回來一個Celine。這一瞬間的舉動纏繞了她多年,為什麼要這樣花掉這2萬塊?
我也曾分期12個月來買一個奢侈品包,後來,我在義大利作家毛拉·甘奇塔諾的《服美役》里看到這段話,感到刺痛,“女性的工資低於男性,花銷卻更大,這樣一來,她們幾乎將賺來的錢都扔回了市場……幾乎所有的廣告都是針對女性的……女性一方面仍被認為是弱者,是低等的,受到輕視;另一方面又是僱傭勞動、無償家務勞動、再生產和消費領域的巨大資源。”這本書寫到廣告與新自由主義體系的虛偽,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我知道,買包的人內心有更複雜的渴求。
在採訪中,我看到了女性各式各樣的買包原因:辛苦工作後、簽單後、出差轉機期間,但不論尋常或富有,不少人都提到一個詞,情緒價值。“這個年頭,能給你確定的情緒價值的東西並不多,談一場戀愛,可能會讓你心慌,買個包我會持續高興很久,尤其是對一個工作非常多、壓力很大的女性來說。”二手奢侈品平台紅布林的創始人兼CEO徐薇笑著對我說,她是許多奢侈品牌的VIC。VIC的全稱是Very Important Client,是一種用來區分VIP的頭銜,有比VIP更高的消費門檻,可以理解為“超級貴賓”。

那么,男性如何看待奢侈品呢?我曾採訪過一位專門研究汽車文化的學者,她在調研中發現,中國的男性有著超乎其他國家的對奢侈品腕錶和豪華車的追求欲,但他們很少會為買了一台寶馬和賓士有罪惡感,他們甚至會說,我買這個車是為了我的家人(普通的車不能接送家人?),或者為了方便談下客戶。他們從來不承認這也是情緒價值。
不過,無論對男性還是女性職場人而言,奢侈品都是他們對自己辛勤工作的一種獎勵。不少人會在攢到第一筆小錢後,去買人生第一個奢侈品包,然後,在升職加薪以後,買下第二個。
其中的悖論也是顯而易見的。一個朋友曾在4A廣告公司做項目小組長,熬夜頻繁,作為項目管理者,她常常要在一天內交付好幾個項目,一度失去私人生活。而網購,成了她僅有能感受到的放風。每次付完錢,她馬上感覺自己需要更努力地賺錢,包成為驢腦袋前的胡蘿蔔。當你年輕,能夠賺很多,並相信日後會賺更多的時候,你可能就會想去買個包,這是個自然反應。
我聯繫上麥小姐,是因為看到她正在閒魚上出售幾十個二手包。她今年41歲,是一個單親媽媽,在昆明開一家承接政府與企業活動的公司。我們打電話時是夜裡11點,她還在活動現場做搭建。
麥小姐是在28歲遇到她的第一個奢侈品包的,那是街邊櫥窗里的一個Gucci錢夾,“那時年輕,看到上面有一個小愛心,又是玫紅的,覺得真是寫著我的名字”。當時,她剛成為一個4S店的市場經理,月薪不到一萬,錢包的價格是她工資的五分之一。
她從雲南山區的一個縣城考到昆明的大學,融入這個大城市之後,也有了努力的目標。“更好的意義是什麼?就是我除了精神層面以外,應該用越來越好的東西。我不覺得這是虛榮,有欲望才會有動力,那句歌詞怎么說的,‘欲望是堅強背後的一道光’。”
29歲,她辭職離開穩定的單位,開始創業,賺到了錢,也開始了自己的買包之旅。她看到一句話,如果女人一生中只能擁有一個名牌包,那么一定是Chanel 2.55。她把這句話寫到了微博願望清單里。
昆明當時沒有香奈兒的專櫃,三四年里,她每次去外地出差,都會去專櫃看看,但都沒貨。直到2017年去北京,逛到王府井,一個銷售突然從倉庫裡面拿了一個羊皮的2.55。銷售說,這隻包本來被人定了,那個人在國外回不來。她看了一下,上面還貼著別人的名字和電話,她立馬就說我要。那時她已經創業2年,年收入漲到近30萬。
“我也不完全是為了要證明自己,因為當時我賺錢能力很好,市場也很好。”那時,她經常在簽了契約以後,或者年終拿到一筆錢,就去下單。旅遊每到一個國家,她也會買一隻包,不一定是奢侈品,也買手工包。她尤其喜歡買色彩艷麗的包——雖然這些顏色後來在二手市場都比黑色保值性差很多。
她最常背LV去見客戶,它一定程度起到了社交貨幣的作用,“我們小地方暴發戶會比較多”。她有一個做生意的老鄉,談客戶時開了一輛斯柯達,客戶出來看到斯柯達,頭也不回就走掉了,後來他就換了寶馬。老鄉用這個例子勸她換台好車,但她沒理會,她的武器是包,不是汽車。
不同的包為麥小姐裝扮了不同的社會角色,見比較高端的客戶,她會背香奈兒,“讓人家覺得你是一個有審美的人,才敢把活動交給你。”這一度能拉近和客戶的距離。有個甲方的高管很愛買包,有一次,這個高管突然對她說,以後不要讓你們公司的A姑娘來做方案了,你來跟我談。麥小姐問為什麼,她說,看A姑娘背的包,都覺得她做不好。A姑娘對包沒有任何追求,但其實最後做執行、寫方案和報價單的都是A。
對於陌生的客戶,她就會背蔻馳,或者更便宜的牌子,這樣“他們就不容易朝死里跟你砍價。”
麥小姐並不喜歡昆明,她喜歡快節奏的生活,但這裡的客戶太悠哉了。她一直是個不安分的人,畢業時,電力系統分配了她四次,她都沒去。她一度嚮往去北京,想進時尚雜誌,大學第一志願報的是北京廣播學院的廣播電視新聞,差了8分。
“從小我就相信,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大於一切,我努力了,回報我是看得到的,總好過我把希望寄托在別人的身上。”這種信念一部分是家庭帶來的——上國中,她的爸媽就離婚了,她的媽媽,一位善良堅忍的雲南縣城教師,沒要撫養費,獨自將女兒養大。大學有攝影課,老師總說,攝影這個活不是女生乾的,她不信,也去扛攝像機。
她談過富二代男朋友,對方的媽媽通過旁人來遊說,希望她以後在家相夫教子,她不同意,這段感情慢慢就黃了。懷孕是意外,也是她自己的決定,當時的男友執意想做丁克,而她喜歡孩子,沒有花太多時間猶豫,兩人和平分手。
把懷孕的訊息告訴母親之前,她躊躇了很久,因為母親有心臟病。她勸母親先把心臟病、高血壓的藥吃好,母親不吃,讓她直說。出乎意料的是母親平靜的反應,母親只說,你自己做決定,並叮囑了一句,以後不要喝薏仁水了。
生了孩子後,她很少再有時間買包,隨後,疫情到來,三年里,公司的活兒大量取消,款收不回來,卻還是要持續墊款做活動,公司的資金鍊多次陷入焦灼,她開始考慮賣包換點錢。
環境變化後,她的心境也變了,“以前我也覺得女人就是要乾一番事業,但是現實看得多了,我也動搖了。包包以前真的對我來說是激勵,一種象徵性的東西,覺得我的努力是會得到回報的,現在我看開了。”
新的自由,是放棄帶來的——“人家說斷舍離,其實斷舍離的不一定是物質,也可能是一段關係,舊的關係你丟掉,整個人能輕鬆點。”她的五六十個包里,有三分之一都拿出來賣了。

去年,58歲的吳美君決定把她的奢侈品全賣掉。當時,她剛從一家外企的總經理崗位上被裁掉,在家整理很久不穿的衣服,一下清點出價值50萬的衣服、包包、鑽戒,她想,賣掉還可以換點錢。
到35歲之前,她都沒有好好逛過奢侈品店。1987年,她大學畢業,到29歲時就升任中國台灣某企業總經理,之後一直在不同的外企做高管,拿很多的薪水。她愛美,但她不愛消費,“(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台灣社會的主旋律是愛拼才會贏,賺了薪水是一定要存起來等著買房子,街上走過滿身都是香奈兒的人,人們會有偏見,覺得那一定是貴婦。那時候我們覺得,拿工作所得去買奢侈品包包,不是年輕女孩該做的事。”
一直到2006年,她進入Timberland做中國台灣區總經理,有一天,在下屬陪同著巡店的過程中,她忽然一個閃念,走進了香奈兒店,買下了一個香奈兒黑色漆皮包。
當時,她正要進入職業生涯的一段高光時期,公司給了她極大的發展舞台,開拓4個市場,她開始在出差期間買包。在中國香港機場轉機看到香奈兒鑽戒,試戴的時候她就想,自己這么辛苦,實在值得一個這么棒的禮物。在新加坡出差,她就進最大的香奈兒店,有喜歡的,當場買下。那時,她背香奈兒包包,穿香奈兒外套,配輕盈的牛仔褲和帆布鞋,在美國、歐洲開會,在老闆的私人飛機上拍照,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在乎的。
那些年,同樣也是全球經濟繁榮、開放的時期,“那時公司業績很好,年終獎金、升職加薪的幅度都很高,比較有安全感,覺得我肯定不可能明天就失業。”買了包,她喜歡借給團隊的人背,這種快樂激勵著每一個人,“每個人都在摸來摸去,他們就覺得,我在那個職位上做得這么遊刃有餘,還可以背名牌包包,那他們通過努力也可以。”
2014年,吳美君調來大陸工作,之後,她一個包也沒買了,一是發現在上海很容易買到高仿,另一方面,她對奢侈品的新鮮感也過了。來大陸八年後,工作不太順利,她決定賣掉奢侈品換點現金,“反正我大概永遠也不會再用它們了。”
全職做博主後,她在小紅書上講過一句話,勸所有的女生都不要去買奢侈品,“說實話我覺得,女生把錢存下來,最好的方式還是買房子,不動產。我台北跟上海各一棟房子,這給我很大的底氣。要買在對的地段,它不會貶值。”
不過,底下有幾千則留言都對此提出了反駁,認為她能這樣輕鬆,是因為她已經擁有過了。
包包里的金字塔
過去十年里,中國人展現的驚人購買力一度占據話題的中心,自2018年起,中國人的奢侈品消費就占到了全球奢侈品消費總額的三分之一。疫情期間,全球奢侈品消費暴跌,只有中國市場相對穩健。到2023年,在全球政治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下,中國奢侈品行業仍有輕微的正向增長。
只不過,這些增長中,有不少值得玩味的變化。過去一年,我頻繁在消費市場裡聽到“香奈兒現象”,有人戲稱,這個品牌是要“甩開中產一度狂奔”。網上有人說,上海白領喜歡背Celine,彰顯格調,到東北街上看到的都是香奈兒爆款。但到現在,一個二手商業內的共識是,“有錢沒錢都喜歡香奈兒。”
另一個吸引了矚目的品牌則是LV,據不完全統計,過去3年,香奈兒漲價了8次,LV漲價了10次。當我們聊到這裡,紅布林CEO徐薇笑了,她說,近年來,漲價的並不只是這兩個品牌,其他的品牌也在漲,只是大眾不知道而已,在她看來,在全球奢侈品行業不景氣下,漲價是奢侈品集團的一個自救策略。
“奢侈品品牌能做到今天,在一百年前肯定是憑藉產品力的,慢慢在產品力取勝以後,第二步,是形成自上而下的影響力,跟身份、社會地位形成綁定關係;再下一步,就是它的價格體系,我要保持自己的價位段,香奈兒往上漲了,愛馬仕看到香奈兒漲,我也得漲,我不漲就跟你在一個檔位了。那么在這種情況下,漲價就會是一個大家之間彼此競爭的遊戲。”
那為什麼漲完之後用戶還是買單呢?“因為沒有更多選擇,當他們可以買得起LV及以上產品的時候,不會再往下去做比較。”
近一年來,在紅布林平台,香奈兒和LV的經典款是最受歡迎的,它們受歡迎的原因各有不同,徐薇認為,前者跟近年來專櫃頻繁漲價有一定關係,後者則更多地與其品牌認知度廣,以及相對比較保值有關。“雖然經濟增速放緩,但大家還是在買,只是更多人會選最保值、長期具有流行度的單品了。”
愛馬仕也是人們追漲購買的一個典型,作為愛馬仕入門款的Evelyne大象灰斜挎包,在紅布林平台,2024年相比2022年均價增長33%。“這類型的包會在現在的經濟情況下成為一個保值品選擇。”徐薇說。
不過,個體二手商老孟感覺,如今被關注和瘋搶的包也只剩爆款,其他的貨變得更難賣了,尤其難賣掉的,是那些色彩昂揚、誇張的顏色。他有一整面牆的紅色包,即使價格打了折,一個月也賣不出一個。
二手奢侈品平台只二CEO祝泰倪奇曾表示,他正在減少一些小品牌的回收。大數據顯示,一些便宜品牌因為不保值而流通性持續下滑,現在,人們都傾向於選擇標準色(通常是黑色)、好流通的強勢品牌。而花哨款式都屬於擴張消費時期會選擇的產品。
在長楹天街開辦的為期三天的快閃店,老孟帶了約五千萬的貨來,打了不小的折扣,最後只賣了一千萬,大部分的人排隊進去後,只是頻繁地比價、查價,就走了。麥小姐在閒魚賣自己的包,發現大部分時候遇到的都是二手販子,不是真買家,“能賣掉的還是那些流通款。蔻馳、MK那些包都出不了,連Gucci都難出了。”
事實上,相比專櫃,二手市場的價格往往更能反應真實的市場行情——老孟抱怨,雖然香奈兒專櫃一路漲價,但它的二手價格並沒有一路跟漲,相反,價格一直停留在疫情之前,畢竟,會買二手包的人還是普通中產,他們拿不出更多的錢來承擔溢價。“這是供需決定的。”
無人問津的包就像賣不出去的房子一樣,會隨著賣不出去的持續而不斷降價,但越降價的奢侈品,越沒人敢買。這一年裡,最賠錢的包之一,是愛馬仕鱷魚包——洪晃曾在一篇《只知Birkin 不知Jane》的文章里寫道,“我認識不止一個女人,可以為一個Birkin包去殺人。如果是個鱷魚Birkin,那是可以開始大屠殺的。”這個故事如今已經調轉過來。
2023年初,愛馬仕出了一個稀缺尺寸的鱷魚皮birkin,當時,有非常多二手商爭搶囤貨,甚至溢價收購,原價四五十萬的包,炒作的價格一度過百萬。然而,一季度之後,市場情況急轉直下,這些包全部都壓在二手商手裡。到7、8月份,她再去詢價,這個包在同行交易中已回落到了60萬左右。“這跟最近一年北京、上海的大宗資產的價格變化非常類似。富人會重新對他們的一些核心資產進行梳理,包括賣掉一些房產、貴重的包包,而不是再花錢去買入。那么,等這種資產的價格掉到一定程度,水分其實也去掉了一些,也不會再往下降了,但是有價無市。富人不買了,但中產還夠不到它。”徐薇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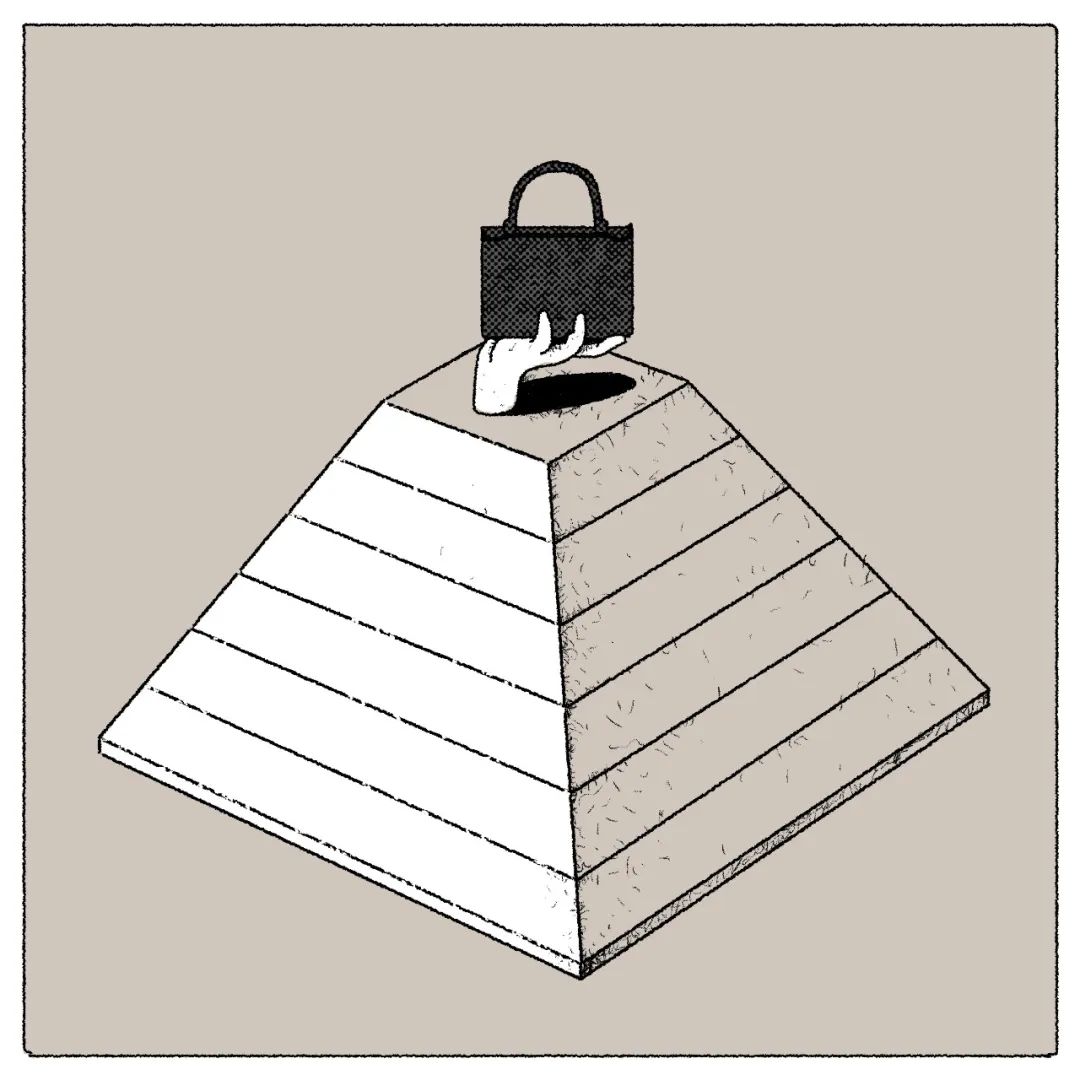
包的世界裡,有一個穩定的財富的金字塔,最頂尖的富人幾乎不賣包,再往下,是賣包的普通富人,再往下,才是買二手的人,隨之財富遞減、年紀遞減。《2020年中國二手奢侈品市場發展研究報告》顯示,76%的二手奢侈品用戶為35歲以下。據只二公布的數據,老賣家提供了70%的上架商品,59%的人年收入超過40萬人民幣。老孟說,有錢人在包上花的只算小錢,他們還會購買奢侈品牌的衣服、領帶、絲巾、帽子、馬鞍、餐具,甚至垃圾桶和狗窩。
老孟去過很多富人的家收包,海南黃花梨的床、桌子,擺滿茅台的酒櫃,車庫裡庫里南的車停一排,理察米勒的表擺了二十多塊,各種克拉數的大鑽戒。他們不會把包當奢侈品,有的已經用得成色很爛。漂亮的展示櫃裡,被整齊擺放的基本上只有愛馬仕鱷魚皮,香奈兒都是混亂堆疊著。很多愛馬仕年份都挺老,2013年、2014年買的最多。不少富人告訴他,對於奢侈品,他們只是剛有錢的時候才感覺需要。
買包不光是因為喜歡,有的客戶上千萬一年地在專櫃消費,只是為了保持在愛馬仕或香奈兒的VIC身份,像北京這樣的地區,買家競爭尤其激烈,每半年就要重新更新VIC的名單。品牌的VIC體系,是一種高度篩選的身份象徵,是奢侈品在階級性上表現到極致的體系,也是奢侈品牌一種抓住客人的手段,成為VIC,會得到專屬的貴賓室接待、節日和生日會收到定製的高端禮品,其中被邀請至國外看秀、參加品牌的時尚晚宴,與品牌的形象大使共進晚宴。這些場合也為他們提供了擴展人脈、維持身份的機會,不少VIC也成為了網紅。為了保住自己的身份,有的人每兩個月上新就去買些自己不喜歡的東西,老孟幾乎每個月都會接待一到兩個VIC,他收到這些包和鞋時,上面往往還包著膜和包裝紙。有客戶打趣說,自己不是VIC,是VIP中“P”。
所有的二奢老闆都珍視這樣的賣家客戶,收包時,老孟經常在算好的價格上加幾百,他把這當一種情緒價值服務,“你說我收人家十幾萬的貨,給人加三五百,為什麼她能那么開心?她不是差這一點,她就是需要情緒價值。比如蔻馳的二手,很多商家都不收的,收這個包我可能賠錢,但我是覺得,這個人能買五個蔻馳,也要花一萬塊錢,十幾年前能實現蔻馳自由的人,也不是一般人,你賠一點錢,交個朋友,以後別人有好包才能賣給你。”
不過,把包賣掉,很多人並不是不買了,換包有喜新厭舊,但隱形的規律永遠是“升級”,而升級的終點往往只有香奈兒和愛馬仕。有人把愛馬仕銀扣喜馬拉雅鱷魚皮出給二手商人,這是一款在某些地區要累計消費上千萬才有資格排到的包,二手價在上百萬。她解釋,把它賣掉,是因為自己已經買到鑽扣了(二手價200多萬)。
什麼樣的人在買二手包?
這么大量的、不少看起來很過時的二手包,真的能被市場消化掉嗎?懷著疑問,我來到徐薇的公司紅布林,這是位於北京東北五環順義的一座科技大樓,同一棟樓里,另一家科技公司正在造車。這是國內最大的二手奢侈品回收公司之一,提供寄賣和回收兩種服務,已有數百萬件商品從這裡循環出去。
每一個寄來的二手包首先抵達紅布林的處理中心,這是一個半個足球場大小的開闊空間,從收貨,到過鑑定,再到上架編輯,有一套標準化流程。再一轉,我們就到了庫房與直播區,這裡就像一個博物館,密密麻麻陳列著各色的舊包,貨架之間則點綴著數十個直播台。每天中午開始,若干皮膚光滑白皙的年輕女主播在貨架之間坐下,客戶只要在手機app前點單,平台就會像打車派單一樣把包派給一個女主播。說著,公關給我指了一個位置,這裡業績最好的女主播,曾經是央視記者。賣奢侈品不能僅展示商品,她們還需要講解它古老的藝術文化。
不過,讓中國買家對二手包感興趣的最主要原因,是便宜。只二CEO祝泰倪奇曾表示,中國買家對傳統二手時尚行業背後承載的環保、減碳、循環利用、社區互助等主題興趣不大,更關注的是“性價比”。
根據紅布林的統計,經常買二手包的用戶主要是30歲左右的女性用戶,一二線城市居多,職業分布比較廣泛,主持人、律師、教師占比較高。同樣,對商家來說,選擇收哪些二手包,需要考慮一二線城市的35歲以下人群的喜好。在老孟收包的現場,一個年輕男學生帶來兩兜男包,說都是家裡收到的禮品,然而最後,他不得不帶回家一兜子,因為沒有那么多男性在求購二手男包品牌,“用他那些登喜路包的都得60後了,60後不會消費二手奢侈品的。”

《中國二手奢侈品市場發展研究報告2020》提到,我國二手奢侈品市場規模僅占奢侈品行業市場規模的5%。而在已開發國家,這一比例達到20%以上。8年前,天津人老孟進入二奢行業,發現當時大眾普遍對二手不太接受,也很怕被人知道自己在賣包。“當時來買的客戶總是問,這些賣包的人是不是因為沒錢了才把包賣了?這種包多便宜我也不買。我的顧客90%都是做生意的人,本來就講風水。”
徐薇曾試圖遊說某60後業內著名投資人來投資,該投資人投過中國許多知名企業,她只投“大的東西”。電話中,她全程表示質疑,不相信二手會變成大的消費趨勢。徐薇給她解釋,因為年輕人需要出入一些社交場合,有背好點的包、戴貴點的手錶的需求。投資人的第一反應就是,再攢點錢買新的唄。最後這個投資就散架了。
在我們採訪前一天,日本三井集團的投資人正好來紅布林拜訪,這個投資人投了日本最大的二手交易的平台。投資人對徐薇感慨,日本在七八十年代也曾經是全球奢侈品的第一大消費市場,在泡沫經濟破滅後的幾年,就逐漸成了最大的二手奢侈品供給中心——當經濟成長放緩,而年輕人已經習慣了好的品牌,很難接受直接意義上的消費降級,這時候,一些替代性的消費選擇會出現,二手是其中一個。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一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強國,到處充斥著“買下紐約”的豪言,社會的消費信心高漲,人們擠滿紐約、巴黎的奢侈品店,有的地區曾一度人均持有14個LV包。“因為東亞文化里的權威制是非常顯著的,我們特別需要代表身份象徵的東西。”眼下,徐薇相信,二手觀念會慢慢滲透市場,“中國過去經濟快速增長,出現了本土一代的超級富豪們,奢侈品牌給中國市場做了很多的定製款,所以我們市場上會有很多的硬貨。跟日本投資人交流中提到,前些年,二手奢侈品市場的供給端,很大程度轉移到了中國市場。接下來,國內市場可能就會成為一個最大的二手供給中心。”
在徐薇看來,中國職業女性與包的故事並沒有我們想像得那么長——事實上,在最早一批女性職場人賺到錢時,大部分人還不敢消費奢侈品。21世紀初,徐薇考上北京大學,大二時,她去香港大學交換念書,發現香港簡直就是個“花花世界”,那時候北京還沒開發三里屯,沒有SKP,半年後結束交換,她運了一大箱時髦不貴的香港本土品牌的衣服回來,但回來之後再沒穿過,太“先鋒”,露肚子、露肩膀,走在校園格格不入。
再後來,她去東京、紐約、倫敦出差,著迷於街上的人們各式各樣的穿搭,“我覺得是一種自我表達”。研究生,她考上英國牛津,用獎學金買了她的第一個大牌包。十年後,她再回到北京,那已經是2010年,她還是疑惑,“中國的女孩子一直都在學習、辛苦地工作,我們掙錢的能力也不亞於全球的一線城市,但我們的穿搭和審美為什麼還是這么趨同和保守?”
不過,就在她發出感慨不久,消費大爆炸的時代來了。但她也發現,另一種審美的日漸趨同也開始了,在社交媒體與算法的影響下,人們喜歡的包的品牌、款式正在變得雷同、整齊劃一,這是另一種保守。也是因此,她有了做二手的願望。
寫這篇稿子的日子裡,我聽了太多的職業女性買包的故事,它有充滿華彩與鼓舞性的一面,但我也逐漸被一種匱乏感包圍,我感覺到意義感的稀薄。消費似乎成了我們重要的公共生活,對於努力的人而言,名牌包包恰逢其時成了承載意義的自我獎賞。買包的女人都知道,買包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穿出去讓別人看,而是我們想要向自己證明,我配得到它。但是,為什麼我們總是如此迫切地想要證明這一點?
不過,老孟的一席話也讓我對買包這件事有了另一種理解,“人是要一直挑戰自己的,你要一點欲望都沒有了,就沒意思了。你覺得背個帆布袋挺好,那你不需要賺那么多錢。人要往上走,奢侈品行業就是一個為了讓更多的人往上爬而生的產業,讓他們知道,只要努力,他就能夠到一些他想買的東西,人每天是要進步的,不然怎么辦呢?”
聊了3個小時,麥小姐已經離開搭建的現場, 一手推著電瓶車,一手拿著電話,走在回辦公室的路上。孩子已經由姥姥帶著在家睡了。她的辦公室就安在家樓下,這是為了照顧小孩和媽媽,媽媽前年做了兩次心臟支架手術。
在閒魚上架一年後,她已經成功賣掉了四個Gucci、兩個愛馬仕(的入門款)、若干愛馬仕的包裝盒子(這也有人買)。我們對話的前一天,她剛把一個Gucci絲絨包打包寄去西藏。她的第一件奢侈品,一千多的錢夾,已經500塊賣掉了。我發現那隻香奈兒2.55也出現在了她的閒魚列表里,但她說絕對不會賣,只是想看看市場上還能值多少。她買下這款包時,花了三萬三,後來它不斷提價,新款已經漲到八萬多了。她告訴我,她在做的是“騰倉”,品牌升級,她只準備保留香奈兒和愛馬仕。“雖然我的夢想清單里還有一個愛馬仕,但可能有一天我存夠錢也不會買了。”
而在那一頭,西藏的買家已經收到了她的Gucci絲絨包,那是一個年輕的保險公司職員,另一場職場進階之路開始了。
採訪、撰文:劉楚楚
編輯:王婧禕
插畫:陳禹
視覺:aube
運營編輯:Yuki
